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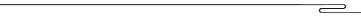
让我们更进一步,考察一则相当晚近的案例,以使我们可以充分地用上“文明人”的眼光。19世纪80年代,一个名叫海尔默斯的丹麦青年以动人心魄的笔调记述了自己在巴厘岛的一段见闻,其内容完全不同于高更用他那支著名的画笔告诉我们的。
其时正值一位邻国酋长的葬礼,这同时也是巴厘人一次盛况空前的庆典,所有的巴厘酋长或王公都带着大批仆从迤逦而至,以“与民同乐”的姿态观赏那位死者的尸身如何被焚化,以及他的三位王妃如何在火焰中献身燔祭。“那是一个晴美的日子,沿着把葱茏的无尽的梯形稻田截然划开的柔滑的培堤埂地遥遥望过去,一群群的巴厘人身着节日的盛装,逶迤朝着火葬地走去。他们色彩缤纷的装束与他们所经过道路上柔嫩的绿地形成了艳丽的对比。他们看上去几乎不像野蛮人,倒是更像一伙逢年过节的好人儿在进行一次欢愉的远足。整个环境看上去是那么富足、祥和和幸福,在某种意义上看上去是那么的文明,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就在这样场景的几英里之内,有三个无辜的女人,为了宗教名义上的爱的缘故,将在成千上万的她们同胞面前来承受最可怕的一种死的折磨。”
围观者足有四五万人,大约占到全岛总人口的5%,而从那三位即将赴死的王妃脸上看不出一点惊慌或恐惧的神色,因为她们深信有一个无比华美的极乐世界正近在咫尺地等待着她们的到来。三位王妃的亲友们也在围观群众当中,和大家一样满怀期待。最后,有两位王妃盛妆着毫不犹豫地纵入火海,第三位王妃略微有些踟蹰,但在颤抖地蹒跚了一刻之后,也紧随着两位姐妹而去,没有丝毫的叹息哀恳。
作为一名来自“文明社会”的旁观者,海尔默斯如此满怀庆幸地记录着自己的观感:
这场可怕的场景在这巨大的人群中并非引起任何情感的波动,而且这场面是在野蛮的音乐声和鸣枪声中终结的。这是一个使亲睹者永远难以忘怀的场景,它带给我的心里一种非常奇异的情感去感激我所身履的文明,感激它所有的过失及所有的仁慈,感激它越来越致力于把妇女从欺诈和残忍中拯救出来的趋势。对英国统治者而言,在印度,这臭名昭著瘟疫般的寡妇殉夫习俗已经根绝了。而且无疑地,荷兰人此前也在巴厘人那儿根绝了这一制度。像这样的文献录载的是一种昭示西方文明有权去征服和以人道的名义驯化野蛮种族和取代他们的古代文明的信证。

从海尔默斯的这段感言里,敏感的东方人很容易看出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影子,甚或相信这是在为侵略与殖民所寻找的所谓“正义的口实”,就像中国在一千年前赵匡胤对南汉所做的事情一样。不知幸或不幸,历史的确像海尔默斯所期望的,同时也像巴厘岛的“民主主义者”或“社群主义者”所痛恨的,荷兰侵略者悍然干预了人殉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以西方所谓文明世界的价值观强加于这座属于艺术的、充满牧歌风情的天堂小岛。
这种西方价值观显然不是自由主义的——让我们回顾一下米塞斯的行为通则(general theory of choice):任何人的行为都只受到唯一的限制,即不对他人造成损害。换一种我们较为熟悉的说法,即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那么,在巴厘岛的案例里,谁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呢?
是那三位蹈火而死的王妃吗?——在所有巴厘岛人的心里,她们明明是走上了一条被人艳羡的幸福之路,就连她们自己和她们的亲友们也都这样相信着,她们是完全自愿地跳进了火海,热情地追求着来世的福祉。谁能证明她们想错了呢?
这种情形绝不只在巴厘岛才有。如果我们相信蒙田的记述,那么,“在纳森克王国,至今教士的妻子在丈夫去世时,随死者一起活埋。其他女人则在她们丈夫的葬礼上活活烧死,此时,她们不仅表现得勇敢坚强,而且喜形于色。国王的遗体火化时,他所有的妻妾、嬖幸、各种官员、奴仆都兴高采烈地扑向烈火。对他们来说,能陪伴国王的遗体一起火化,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这些人都是受了欺骗吗,就像巴厘岛的那三位王妃一样?
只要利益是主观的——像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的那样——那么在巴厘岛这个社群内部,虽然死掉了三个无辜者,但这不但不违背自由主义的行为通则,甚至还会取悦于最苛刻的功利主义者,因为这样的行为毫无疑问地促进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甚至还是一种十足的帕累托改进:在增进福祉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美国的人类学家吉尔兹在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演讲当中不惮篇幅地引述了海尔默斯的故事,最后毫无悬念地指出:“这正是西方人可以征服和改造东方的证明文书。如英国人在印度、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和可以设想的比利时人、法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可以有权去用他们自己的文明标准代替、更换当地古代的文明,因为他们是站在仁慈和解放生灵的一边,反对奸邪和暴虐的。”——是的,即便是穆勒这样的学者也坦然地站在这个立场上,他一定会支持西方人对巴厘岛的文化殖民,甚至是武力殖民,因为在他看来,美国白人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就“不但是正义的,而且是高尚的”。
 如果是中国儒家,甚至就是孔孟本人,是否同样会以“君子坦荡荡”的心态主张对巴厘岛的入侵呢?
如果是中国儒家,甚至就是孔孟本人,是否同样会以“君子坦荡荡”的心态主张对巴厘岛的入侵呢?
但是,吉尔兹继而又无可奈何一般地说道:“当我们读完这些奇异的文献,我们觉得不仅仅是巴厘人或海尔默斯看上去在道德上是不可捉摸的;而且,我觉得除非我们有志于去解决诸如‘人吃人是错的’之类的润饰性箴言之外,我们本身也是如此。”

作为人类学家的吉尔兹在一个伦理学或政治哲学的问题上颇有自知之明地止步不前了,但他的确触到了症结所在。是的,“人吃人是错的”,这样一个看似不言而喻的、简单到无可复加的命题,一旦深思起来,的确是难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