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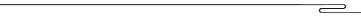
在这个问题之先,还有两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1)人可不可以杀人,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杀人?(2)谁有权利为奥米拉斯的那个无辜的孩子讨还公道?
对于第一个问题,似乎只有在神学范畴里才能为“不可杀人”找到坚实的理据。譬如在《旧约》传统里,杀人的罪恶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渎神。《创世记》9:6“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这是洪水之后上帝与挪亚的立约,作为立约记认的虹至今仍会出现在雨后的天空。
让我们再看一个事例:《旧约·撒母耳记下》记载大卫王和拔示巴通奸,设计杀害了拔示巴的丈夫,那位忠心耿耿又能征惯战的武将乌利亚。《旧约·诗篇》第51章则是大卫王的忏悔诗,向耶和华忏悔自己的罪孽。诗中有一句话非常奇特,是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也就是说,大卫认为自己所犯之罪仅仅是得罪了耶和华,却不曾对乌利亚和拔示巴有任何侵犯。霍布斯就抓住过这一句话作为佐证,用以说明主权君主处死无辜的臣民是完全正当的:“原因是任意做他所愿做的事情的权利已经由乌利亚本人交付给大卫了,所以对乌利亚不能构成侵害。但对上帝说来却构成侵害,因为大卫是上帝的臣民,自然律禁止他做一切不公道的事。”

这就意味着,大卫王害死乌利亚,罪行不是杀人,而是渎神,他只需要向上帝忏悔,而不需要对拔示巴和乌利亚表示任何歉疚。
这似乎就是问题的终点,然而事实上只要我们也甘愿冒一点渎神的风险,还是可以再追问下去的,亦即为什么凡是渎神的就一定是不道德的?—即便在神学范畴之内,这个问题依然是个问题。如果上帝赋予人类自由意志,人就被授权通过自己的认知能力来判断自己是否应当信仰上帝。上帝是全能的,但全能未必构成你向他膜拜的理由;上帝是至善至公的,但我们完全可以因此而敬佩他,却不一定非要膜拜他;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我们的创造者,并且全心全意地爱着我们,但我们并不一定喜欢这个宇宙,也不一定喜欢自己,不喜欢上帝未经我们同意就把我们置诸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愿意膜拜上帝。
自由主义的“同意”原则在这里发生着作用,父母虽然没有能力先征得子女的同意再把他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但全能的上帝一定有办法先征得我们的同意再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甚至他的全知完全可以预先洞悉我们的意愿,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一些完全可以预先征得我们同意却不曾如此的事情承担义务呢,尽管交给我们的可能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天堂?
如此,只要我们保持“同意”原则的一贯性,渎神的罪恶也就失去了道德依据,而“同意”原则恰恰是自由意志的最醒目的彰显,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对自由意志的意义的认识保持神学上的一贯性,就有理由保持“同意”原则的一贯性。
如果换到世俗的角度来看杀人的理由,那么依照孔子“以直报怨”的原则,血债血偿是无可厚非的;公平被立为第一原则,人的生命低于公平的原则。这会令人顺理成章地想到《墨子·小取》提出过的“杀盗非杀人”的著名命题,其推理结构是:某人的亲人是人,但他侍奉亲人并不是侍奉人;某人的弟弟是美人,但他爱弟弟并不是爱美人。车子是木头制成的,但乘坐车子不是乘坐木头;船也是木头制成的,但进入船舱并不是进入木头。盗贼是人,但盗贼多不是人多,没有盗贼并不是没有人。爱盗贼不是爱人,杀盗贼不是杀人。
《墨子·小取》讨论的着眼点是逻辑问题,哲学倾向只是附带出来的,但《荀子·正名》批评它是“此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虽然《荀子》不曾仔细阐发,但根据《荀子》上下文的正名原则以及现当代学者们近乎一致的意见,荀子是说只要是盗,首先必然是人,盗的概念已然蕴含在人的概念当中。
但我以为荀子误解了墨子,今天的研究者们依然承袭着这个误解。墨子明明承认盗就是人,所要区分的并不是盗与人,而是杀盗与杀人。这在推论的第一步就已经表达清楚了:某人的亲人是人(首先承认了“亲人”蕴含在“人”的范畴之中,正如“盗”蕴含在“人”的范畴之中一样),但他侍奉亲人并不是侍奉人;某人的弟弟是美人,但他爱弟弟并不是爱美人——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某人爱自己的弟弟以及他的弟弟是美人这两点上推断出他爱美人的结论,这才是《墨子》的这段文字所表达出来的确切含义。何况墨子对概念的外延、内涵清楚得很,譬如《墨子·大取》讲逻辑,说某人有一匹秦马,也就是有一匹马,所以知道他牵来的是马。
《墨子·大取》讲过“杀一人以存天下”的问题,大意是讲权衡轻重的道理:天下为重,一人为轻,似乎应该取重不取轻,但只有杀的是自己才具有道德价值,杀的若是他人,就没有道德价值。

也就是说,杀一人以存天下,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原本天下人既不该死,哪一个人也不该杀,只可惜我们被逼入这一两难的境地,必须二者选一,那就只好“杀一人”了。这是极端境况之下的被迫的选择,没有任何道德权重可言。
这个问题恰恰带出了功利原则的适用范围问题,理性人在做选择的时候的确都会权衡轻重,但是,一个人如果越出私域,代替别人去权衡轻重,这算不算越俎代庖呢?如果算的话,这就意味着当你在“杀一人”和“存天下”之间艰难权衡的时候,你其实没有任何权利去决定别人的生死,无论对方是一个人还是所有人。
退一步讲,即便依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的著名原则,这个生死抉择仍然不容易做。首先,遭人诟病的是,这一原则本身无法自洽,因为任何这类命题都不能包含两个“最大”,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很可能会和最大幸福发生冲突。其次,即便两者不矛盾的时候,也有可能产生令人不易接受的结果。
就第二点而言,譬如为了“存天下”而面临灭顶之灾的那个人,他对生活的热爱与满意度超过所有其他人的总和,而即便杀掉了他,保全了天下,所有其他人仍然会继续以往的生不如死的艰难时世。当我们把所有人的幸福度加总(假定幸福度当真可以精确计算的话),会发现这是一个负值,而如果杀掉那个人,这个幸福度的负值还会陡然下降;假如反过来,不杀他,听任所有其他人死掉,全社会(虽然是只剩一个人的社会)的幸福度会大大增加。这就意味着,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让那一个人活下来,听任所有其他人死掉,这才是最优选择。如果不杀那个人,则既无法保全其他所有人,也无法保全他自己的话,不去“杀一人”而听任所有人死掉仍然是最优选择,因为在幸福度的总值上,零无论如何也是好过负值的。
如果我们感觉有必要反对这种见解的话,那么康德的实践伦理所谓的“人不应该以人为手段”的说法或许就是我们最顺手的理据。但只要我们追问下去,人为什么不能以人为手段,那我们就只能走入前述所谓的基本人权的领域了。
当今的西方国家陆续废除了死刑,似乎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应该剥夺他人的生命,但吊诡的是,战争行为在道德上依然是被许可的。这似乎说明了一个奇怪的道理:国界就是基本人权的边界。因为,如果基本人权当真是最高原则的话,国家之间便没有理由开战。
可以构成辩护的理由是:因为对方侵犯了自己的基本人权,而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便有必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侵犯对方的基本人权。这样说来,最高原则便不是基本人权本身,而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的“自己的基本人权”。每个人都没有天然的义务去尊重别人的基本人权,但当自己的基本人权遭到侵犯的时候,在捍卫的过程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有权侵犯对方的基本人权。这当然不是那种绝对的原则主义的道德范式,因为它不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侵犯任何人的基本人权。
如果你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有人正在侵犯你的生命权,而你只有通过剥夺对方生命权的方式才能捍卫自己的生命权,你会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当然不乏真实的例证,譬如一名“二战”时期的犹太人,在种族屠杀的威胁面前,如果他有机会杀出一条血路,他应不应该这样做呢?——看上去这是一个无比愚蠢的问题,然而圣雄甘地的建议是:他应该自杀,而不是反击。
 我们当然可以不接受甘地的意见,但没理由怀疑他的真诚。
我们当然可以不接受甘地的意见,但没理由怀疑他的真诚。
接下来让我们虚拟一个情境:你和一个同伴一起被困在一座荒岛上,你们无冤无仇,但在获救之前,岛上的食物只够一个人吃的。这就意味着,你们每个人的存在,其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对方的生命权的侵犯:你们每吃一口粮食都是在伤害对方,你们也都同样清楚这个道理。
如果仅仅因为对方“正常进食”而杀掉对方,这可不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必要的反抗,是出于捍卫自己被侵犯的生命权的一种反抗?而对方是如何实施侵犯的呢——是通过“正常进食”的方式,他每吃一口饭,都是在减损你一分的生命,而他和你一样地清楚这点。那么问题是:吃饭,是否构成了谋杀?此情此景之下,吃饭是否就是一个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而对别人实施谋杀的一种手法呢?
我相信有许多道德高尚的人宁可选择让自己饿死,最有道德权重的结果也许是两个人一起饿死——他们明知道对方的操守和心意,也明知道自己饿死会辜负对方的牺牲,并且只会使结果更糟,但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不可以妥协的。
但是,理据何在呢?如果不是两个个体,而是两个国家处于这种关系之中,正义性会有任何不同吗?

为了解决理据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把小岛的情境稍稍改换一下:和你在一起的并不是你的人类同伴,而是一只猩猩,这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一旦换到这样的情境,似乎所有的道德难题瞬间便被一扫而光,你当然应该抢过所有的食品,甚至,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杀掉那只猩猩,吃它的肉来改善伙食。你的理由会非常简单:猩猩不是人。斯多葛学派在两千年前的论断直到今天依然深合人心:“这一学派的人大部分都主张人类对于其他动物不受公正的义务的约束,因为它们和我们不同类。”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连“君子远庖厨”的恻隐之心都不必有,因为在洪水之后,上帝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过:“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创世记》9:3)上帝放宽了对人(应当也包括动物)的限制,从此以后,人类便不再是可以与动物和平共处的素食主义者了。

或许我们的特殊性就在于我们是人,对他人的基本人权的尊重来自于我们对“人类共同体”的尊重,而对“人类共同体”的尊重则是从个人的同情心扩展来的,进而从实然变为应然,从客观事实固化为道德规范。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至多可以说我们愿意接受这种道德,但没法论证这就是对的。
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接受这种解释,恐怕不但杀不得那只猩猩,还有必要像尊重自己的基本人权一样尊重它的基本人权,甚至干脆用“他”或“她”来称呼这位多毛的同伴。——以下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儒生自幼读熟的“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受到严峻挑战,鹦鹉和猩猩都有着被纳入人类的可能。
受到严峻挑战,鹦鹉和猩猩都有着被纳入人类的可能。
《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2003年发表了一篇显然可以支持上述意见的文章,题为《基因研究指出:黑猩猩是人》。文章介绍了新的科研成果,说人和黑猩猩的关键基因重合度高达99.4%,在现存的黑猩猩当中,有两个种类在生物学上都可以算作人类。

这个发现并没有被限定在纯科学的范畴里,早在1994年,就有一些灵长类动物研究专家、人类学家和伦理学家发起了一个叫作GAP(Great Ape Project)的世界性组织,专门为猩猩们争取人权,也的确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支持着他们的主张。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猩猩的确会被自然地视为我们当中的一员,那时候的我们追忆起当年种种对猩猩的歧视,那种心态或许会像今天的美国白人追忆黑奴时代一样吧——美国人贩卖黑奴的时候,的确把黑人当成猩猩来看的。

这会使我们重新审视一个从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人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们”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事实上这是一个直到今天依然争议不休、莫衷一是的问题。生命伦理学的创始人弗莱彻在1979年出版的《人性》一书里,为“什么是人”提出了15条判断标准。这虽然是一次很有勇气的尝试,但我相信,即便在30多年后的今天,完全赞同这15条标准的人一定不会很多。例如标准(1)是“最低限度智力”,即智商不低于20;再如标准(8)是“关心他人”。
我们一方面有可能把平日里视为同胞的人排除在人类共同体之外,另一方面却有可能把一些一般视为“非人”的东西引为最亲密的同类。先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当我们说“大地母亲”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把这个短语做字面上的理解,但是,一位印第安的先知,万阿波(Wanapum)部落的首领苏姆哈拉(Smohalla)就是极少数的例外之一。他当真把大地当作母亲,所以拒绝开垦和耕作,因为他认为这是对大地母亲的残害,是一种罪恶的行为:“你要我耕地!要我用一把刀撕开我母亲的胸脯?那么当我死了以后,她就不会再把我拥到她的怀里使我安息。你要我为了一块石头而掘地?要我在母亲的皮肤之下挖掘她的骨头?那么当我死后,我就不能进入她的体内求得再一次的重生。你要我割掉大地上的青草,晒干后把它们卖掉,使自己富得像一个白人?但是我怎么敢割掉我母亲的头发?”

这番话仅仅来自半个多世纪以前,如果我们确有为之打动的话,那么考虑到猩猩和大地母亲的差异远大于人类和猩猩的差异,接纳猩猩作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也就算不得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了。
为什么猩猩会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呢?科学家说,因为基因证据给出了充足的证明。那么,又为什么应该使用基因为标准来确定“我们”的边界呢?——基因的相似度到底是多少,是99.4%还是100%,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一个实然问题;该不该以基因相似度来做标准,这就是一个伦理问题、一个应然问题了。
理论上说,我们完全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标准来确定“我们”的边界。最极端的例子恐怕要数佛教理论中“佛性论”的一种主张:“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说的就是植物的佛性;苏轼有诗“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说的是高山流水的佛性;由动物、植物、乃至无机物,万事万物皆有佛性,皆有成佛的潜质。以这个标准而论,石头、瓦片都可以说是我们的“同胞”。
道家学说里也有类似的看法,譬如五代年间,黄老一系的学者谭峭,也就是道教当中的紫霄真人,在《化书·道化》里做过理论总结,说老枫化为羽人,朽麦化为蝴蝶,这是无情之物化为有情之物的例子;贤女化为贞石,山蚯化为百合,这是有情之物化为无情之物的例子。所以说“土木金石皆有情”,万物都是一物。
以今天的知识来看,这样的观点绝不像乍看上去的那样荒诞不经,因为在进化论的意义上,复杂的生命形式正是从无机物演化而来的。
另外或嫌蹊跷的例子是,刘宋年间,何承天与颜延之辩论佛法,纠结在佛教“众生”这一概念。颜延之认为,“圣人”与天地合德,并称“三才”,普罗大众则与猪狗牛羊一类属于“众生”。
 但是,我想今天的人们或许更乐于接受布封定下的标准:“相互交配繁育出有生殖能力的幼崽的动物(无论其形态怎样不同)属于同一个自然的类。”康德认为,不同于按照相似性划分动物门类的“学术体系”,布封建立的是一个“自然体系”,基于布封的概念,“辽阔的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个自然类,因为无论在其形态上可以发现多大的差异,他们都能相互交配繁育出有生殖能力的孩子。……对此,人们只能提出一个唯一的原因:即他们都属于一个唯一的祖源”。
但是,我想今天的人们或许更乐于接受布封定下的标准:“相互交配繁育出有生殖能力的幼崽的动物(无论其形态怎样不同)属于同一个自然的类。”康德认为,不同于按照相似性划分动物门类的“学术体系”,布封建立的是一个“自然体系”,基于布封的概念,“辽阔的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个自然类,因为无论在其形态上可以发现多大的差异,他们都能相互交配繁育出有生殖能力的孩子。……对此,人们只能提出一个唯一的原因:即他们都属于一个唯一的祖源”。

不知道用布封的标准应该怎么检验猩猩和人的关系,但这个标准一定就比基因相似性更加“应该”吗?甚至,若不考虑应用的便利性的话,它就一定比其他的一些标准(譬如身高、体重、肤色等等)更加“应该”吗?如果不应该的话,理由难道仅仅是应用的便利性吗?
譬如我们不妨以颜色做标准,可以说黄种人和棕熊是一类,白人和白熊是一类,黑人和黑熊是一类,这并不比蜘蛛不是昆虫,鲸不是鱼类,蝙蝠不是鸟类更加荒谬。这甚至不是什么奇思异想,而是有着心理和历史上的双重依据。——特鲁玛伊人是巴西北部的一个部族,他们相信自己是水生动物;邻近的波罗罗人自豪地说自己是红金刚鹦哥(这是一种鹦鹉)。我们很自然地以图腾崇拜来做解释,但是,据欧洲考察者的记载:“波罗罗人硬要人相信他们‘现在’就已经是真正的金刚鹦哥了,就像蝴蝶的毛虫声称自己是蝴蝶一样。”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里援引了这一记载以说明自己的“互渗律”理论:“这不是他们给自己起的名字,也不是宣布他们与金刚鹦哥有亲族关系。他们这样说,是想要表示他们与金刚鹦哥的实际上的同一。……对于受‘互渗律’支配的思维来说,在这一点上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思路,如果以沟通程度作为指标,比起一些交流起来完全鸡同鸭讲的同胞,我们对某些动物可能更感觉像是同类。
 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8月的一篇封面文章是《动物想些什么》,文中介绍了一只名叫Kanzi的倭黑猩猩,它掌握了将近400个单词,能够用句子表达思想(当然不是用说而是用手指),不但会用简单的名词和动词,还晓得from和later这类概念以及-ing和-ed之类的时态变化。
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8月的一篇封面文章是《动物想些什么》,文中介绍了一只名叫Kanzi的倭黑猩猩,它掌握了将近400个单词,能够用句子表达思想(当然不是用说而是用手指),不但会用简单的名词和动词,还晓得from和later这类概念以及-ing和-ed之类的时态变化。

卡西尔曾经试图以“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cum)来取代“理性的动物”为“人”定义,他在当时就已经遇到了来自猩猩和类人猿的挑战,但他勇敢地战胜了它们。卡西尔利用当时的动物学研究成果,认为猩猩们所能够掌握的符号系统只能表达情感而无法表达意义,“这就是我们全部问题的关键:命题语言与情感语言之间的区别,就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真正分界线”。
 显而易见,卡西尔在今天应该好好修订这个结论了。
显而易见,卡西尔在今天应该好好修订这个结论了。
至于为我们更熟悉的说法,譬如马克思说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会制造并使用工具,但今天我们知道许多动物同样能够做到这些,只是程度较低罢了。
 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按照亚氏“种加属差”的定义方式,这实际意味着“人是‘唯一’有理性的动物”(卢梭就是这么理解的)。或者我们可以诗意一些,采用帕斯卡尔的表达:人是一株有思想的芦苇。是的,虽然具有理性,但是非常脆弱。
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按照亚氏“种加属差”的定义方式,这实际意味着“人是‘唯一’有理性的动物”(卢梭就是这么理解的)。或者我们可以诗意一些,采用帕斯卡尔的表达:人是一株有思想的芦苇。是的,虽然具有理性,但是非常脆弱。
以理性为人类所独有,这是一种相当常见的看法,至少在休谟的时代仍然如此,所以休谟才会在《人类理解研究》一书里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另辟蹊径来谈所谓“动物的理性”。
 其中的见解并不高深,因为我们仅仅从生活经验也会知道,一只饥饿的狗不会去抢狮子嘴里的骨头,那么,这难道不是一种理性权衡的结果,不是理性压抑了冲动吗?
其中的见解并不高深,因为我们仅仅从生活经验也会知道,一只饥饿的狗不会去抢狮子嘴里的骨头,那么,这难道不是一种理性权衡的结果,不是理性压抑了冲动吗?
如果按照米塞斯的界定,“人之异于禽兽者,正在于他会着意于调整他的行动。人这个东西,有自制力,能够操纵他的冲动和情欲,有能力抑制本能的情欲和本能的冲动”
 ,那么,上述那只狗分明晓得,去抢那块骨头虽然能够满足眼前利益,屈服于本能的冲动与食欲,但较之长远利益将会受到的重大损害,还是牺牲眼前利益、抑制冲动与食欲为好。以我的生活经验为证,不是任何一名人类成员都有这只狗这么高的理性水平。
,那么,上述那只狗分明晓得,去抢那块骨头虽然能够满足眼前利益,屈服于本能的冲动与食欲,但较之长远利益将会受到的重大损害,还是牺牲眼前利益、抑制冲动与食欲为好。以我的生活经验为证,不是任何一名人类成员都有这只狗这么高的理性水平。
和休谟一样热衷于研究人类理解力的洛克也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他援引了17世纪的一篇在他看来相当可靠的文献,该文献记载了巴西的一只老鹦鹉是如何以流利的巴西话以及不亚于人类的智力水平和人类交谈的,洛克无法接受将这只鹦鹉看作人类的一分子,因为关键的区别是:鹦鹉不具备人类的外形。所以洛克说道:“任何人只要看到一个同自己形象和组织相同的生物,则那个活物虽然终生没有理智,正如猪或鹦鹉一样,他亦会叫那个活物为人。并且我相信,一个人虽然听到一只猫或鹦鹉谈话,想来他亦只会叫它(或以为它)是一只猫或鹦鹉。他一定会说,前一种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后一种是很聪明、很有理性的鹦鹉。”

莱布尼茨也认为我们身体外貌是一个关键的区分标准,仅凭理性来区分人与动物是很危险的,因为“我承认,人肯定可能变得像一个猩猩一样愚蠢”,并且,“丝毫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止有一些和我们不同类的理性动物,就像那些在太阳上的飞鸟的诗意王国中的居民那样,或者像一只鹦鹉那样,在它死后从尘世来到这里,救了一位在世上时曾对它做过好事的旅行者的性命”。所以,莱布尼茨对亚里士多德的修正是:“当我们说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时,在人的定义中似乎必须加上某种关于形状和身体构造的东西,否则照我看来那些精灵也就会是人了。”

读过教会学校的好心女士们不会把问题想得像哲学家们那样复杂,她们一般会把道德的存在与否作为人畜的核心区别,但是,早在1840年,蒲鲁东就提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人类的道德感和禽兽的道德感之间的区别是本质上的不同呢,还是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
 蒲鲁东举证如下:
蒲鲁东举证如下:
在禽兽方面,当幼小动物的孱弱使它们受到母亲的爱怜……人们可以看到这些母亲用一种类似我们那些为祖国牺牲的英雄的勇气,在小动物的生命遭到危险时尽力加以保护。某些种类的动物知道团结起来猎取食物、互相寻找、互相招呼(一个诗人也许会把这种情形说成是互相邀请)来分享它们的猎获物;有人看到它们在危难中互相救助、互相保卫、互相警告。大象懂得怎样把它的陷落在坑沟中的同伴挽救出来;母牛会把它们的牛犊放在中间,而它们自己围成圆圈,角尖向外来打退狼群的进攻;马匹和猪在听见有同伴发出痛苦的叫声时会拥到发出声音的地点去。如果谈起它们的交配、雄兽对于雌兽的恩情以及它们爱情方面的忠诚,我可以写出何等生动的描述!但是为了在各方面保持正确起见,让我们补充说,这些结群友爱的、同类相爱的动人表现并不妨碍它们为了食物和争向雌兽献媚而互相争吵、互相搏斗、用坚利的牙齿互相撕裂;它们和我们是完全相像的。

当然,我们既会把禽兽看得像人,也会把人看得像禽兽。考察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界分标准,中国华夏文明往往不把“蛮夷”当作同类而视同禽兽,西方基督教(取其广义)也曾经不把异教徒当作同类而视同魔鬼,同为人类一员的观念只是在相当晚近方才普世化的。譬如汉朝和楼兰王国,在今天看来是完全对等的两个独立主权国,汉人和楼兰人都是一样的人类,但直到明末清初,当时第一流的大学者王夫之评点傅介子诱杀楼兰王这段历史,认为楼兰是夷狄,夷狄是“非人”,既然不是人类,就不配得到只有人类才能得到的尊重,所以“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
 标准都是人定的,是人定的就必然摆不脱个人的主观性,这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那个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就意味着,我们界分事物的标准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主观感受。GAP组织如果将来获得成功,不可能是因为基因上的事实,只可能是因为人们的普遍的主观认同。
标准都是人定的,是人定的就必然摆不脱个人的主观性,这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那个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就意味着,我们界分事物的标准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主观感受。GAP组织如果将来获得成功,不可能是因为基因上的事实,只可能是因为人们的普遍的主观认同。
既然是普遍的主观认同,就难免世易时移,没有永恒不变的标准。人界分万事万物的标准如此,道德的标准同样如此。所有的道德标准都是世易时移的,是人在相互作用中逐渐磨合出来的,出于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同。
 那么,回到前述的“人可不可以杀人”的问题,“人”是什么首先就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夷狄不是人,可杀;异教徒不是人,可杀;黑人不是人,可杀;猩猩不是人,可杀……
那么,回到前述的“人可不可以杀人”的问题,“人”是什么首先就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夷狄不是人,可杀;异教徒不是人,可杀;黑人不是人,可杀;猩猩不是人,可杀……
再者,即便“是人”,也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突然变为“非人”,譬如洛克论述在自然状态中犯下了杀人罪行的人:“这个罪犯既已绝灭理性——上帝赐给人类的共同准则——以他对另一个人所施加的不义暴力和残杀而向全人类宣战,因而可以当作狮子或老虎加以毁灭,当作人类不能与之共处和不能有安全保障的一种野兽加以毁灭。”
 同类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屡屡发生,不是在自然状态,反而是在所谓的文明世界,往往回顾起来并不觉得有任何正义可言。
同类事情在人类历史上屡屡发生,不是在自然状态,反而是在所谓的文明世界,往往回顾起来并不觉得有任何正义可言。
即便有了清晰的标准,问题依然难以解决。譬如对“人”的界定就是永恒不变的,其内涵就是我们当下的主流认识,那么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牛不是人。但我们应不应该杀牛呢?杀牛,对于一个人来讲,是否不存在任何道德瑕疵呢?
这看上去是一个蠢问题,是的,许多人吃肉,不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的。即便是宣扬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佛教徒,也只会说吃肉是你在造恶业,会使你在轮回之中饱尝恶果—这关乎你的切身利益,但无关于你的道德。而诺齐克为我们设想过这样一种境况:有某些比我们高级得多的外星人(譬如他们和我们的差别至少不小于我们和牛的差别),为了自身利益准备杀掉我们,这是否也不存在道德问题?

这是一个富于启发性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也可以的话,是否意味着我们之所以会问心无愧地杀牛,仅仅是因为在牛的面前,我们是当之无愧的强者?如果说只有在同类之间的残杀才是不道德的,那么既然我们确定同类的标准是如此的主观,如此的游移不定,是否可以以力量等级为标准,在某个力量等级以上的强者视彼此为同类,认为彼此不可相残,而杀害被定义为另一种群的弱者则不必负有任何内疚?
这会使我们归向臭名昭著的尼采哲学:尼采认为一个善良健全的贵族应当毫无愧疚地接受千万人的牺牲,这些牺牲者必须降为奴隶,降为工具。从尼采的意见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出:在同样具有感知能力和思考能力的物种当中,能力较差者“理应”为能力较强者做出牺牲,正如猩猩或牛马“理应”为人类做出牺牲一样;如果一个人,一个高贵的人,对猩猩或牛马表现出任何谦卑的姿态,那么他无疑是在自取其辱、自甘堕落。
那么,接下来的推论将是令人不快的:一个赞成对猩猩或牛马可以生杀予夺的人,只要真诚地保持逻辑一贯性的话,就没有足够理由反对尼采的意见,进而对杀人问题的态度会宽容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