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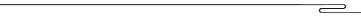
真实的世界的确复杂得多,牺牲少数人以维护多数人利益,这在很多人看来都不仅是可以接受,甚至是应当如此的,尤其当涉及不计私利的“高尚的牺牲”的时候。
比如说,战争中的杀俘问题。战俘有没有权利,这是一个很令人纠结的问题。离开奥米拉斯的人们认为奥米拉斯的幸福生活建立在践踏那个无辜孩子的基本人权之上,所以宁可抛弃现成的幸福。但是,战俘是不是无辜的呢?
可想而知的是,战俘当中必定有无辜者的存在,哪怕为数甚少。但忙于作战的部队不可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巨细靡遗的甄别工作,何况战争中伤及无辜总是在所难免。那么,在无力甄别战俘的情形下展开杀戮,这是不是一种“故意”的杀害无辜的行为呢?那么,更进一步,故意屠杀敌国的平民,这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吗?
丘吉尔回忆1945年7月17日的下午,他突然收到了美国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随后,杜鲁门总统邀他一同商量对日作战方针,并决定对日本本土实施严厉的空袭。丘吉尔对冲绳之战的结束场面记忆犹新,那个时候,走投无路的日军拒不投降,先是军官们在庄严的仪式中切腹而死,随后,成千上万的日军排成队列,用手榴弹自尽而亡。
所以,丘吉尔和杜鲁门都预计到,和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军正面交锋,会造成英美军队巨大的人员伤亡。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现在,所有这些噩梦般的画面终于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个清清楚楚的景象:只消一两次的剧烈爆炸,战争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根本就没去讨论原子弹到底该不该用。显而易见,为了避免一场巨大而不确定的杀戮,为了结束战争,为了给世界带来和平,为了解救那些饱受磨难的人民,如果以几次轰炸的代价就可以威慑敌人而达到这些目的,那么,在经历过我们所有的劳苦与危难之后,这看上去真是一种奇迹般的解脱。”
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丘吉尔说:“连一丁点其他声音都没有。”丘吉尔并非没有意识到日本平民将会遭受的巨大伤亡,但他相信,“这种新式武器不仅会毁灭城市,还会挽救我们的朋友和敌人的生命”。

之所以能够挽救敌人的生命,丘吉尔认为,原子弹的沛莫能御的威力会给奉行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一个投降的台阶,否则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1945年迄今,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始终都是伦理上的争议问题,在和平来临之后,即便在很多西方人看来,这种以超级武器屠杀敌国平民的事情也是不可原谅的。平民,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纳入专业军人的攻击目标。
侵略与反侵略的不同性质有可能成为一个辩护理由。作为反侵略同盟的一方,出于正义的目的不妨采用一些非常手段。但反方会这样质疑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本身就违背了正义规则,如果这也可以的话,那么战争的双方究竟谁才是正义的,难道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相应而起的辩护可能是这样的:战争把人类带入自然状态,在自然法的支配下,人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如果在1945年可以做一次广泛的民意调查,问一问英国、美国,也包括中国,问问这些国家的所有人民,如果两颗针对日本平民的原子弹就可以结束战争,有多少人愿意?想来结果就算不是全票的话,至少也是压倒性的多数。就算投放更多的原子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这个估计有可能是准确的,但它意味着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道理:在生死攸关的时候,道德可以被弃之脑后,或者说,保种图存才是最高的道德准则。这就意味着,道德的要求其实不外是基因的要求;一切文明的粉饰,其根底不外是人类的生物性罢了。
普通人更愿意接受的情形也许是这样的:奥米拉斯被一个独裁政府控制着,统治者都是一些铁石心肠的人,他们在确保私利之余确实也操心着国民福利,他们相信任何统治者都需要一些忠心耿耿的佞臣去做“一些必要的脏事”。于是,关于那个可怜孩子的所有消息被佞臣们妥善地封锁了起来,永远不让那些善良而软心肠的子民知道。
事实上,这正是独裁政府的魅力所在,子民们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自己的道德责任,再不用纠结于那些两难的选择,同时安享着稳定的生活。即便政府倒台,事情败露,也是由那些统治者和佞臣去承担责任,一切与己无关。
的确有人支持这样的解决方案。譬如蒙田,这位高尚的知识分子,相信自然界没有无用之物,甚至不存在所谓无用,就连我们人性中那些肮脏丑陋的东西,诸如残忍、野心、嫉妒,也都是必要的:“倘若有谁消除人类身上这些病态品格的种子,他就破坏了人类生存的根本条件。同样,任何政府都有一些必要的机构,这些机构不仅卑鄙,而且腐败;恶行在那里得其所哉,并被用以维持这个社会,犹如毒药被用来维护我们的健康。虽说这些机构有了存在的理由——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而共同的必要性掩盖了它们真正的性质,但是这游戏应该让那些比较刚强、比较大胆的公民去玩。他们牺牲自己的诚实和良知,一如有些古人为保卫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我们这些比较脆弱的人,还是承担一些比较轻松、风险比较小的角色吧。公众利益要求人背信弃义、颠倒黑白、杀戮同类,让我们把这类差事让给那些更听话、更机灵的人去干吧。”

看来,也许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价那些臭名昭著的政客和政府部门,他们为了“公众利益”去做那些不得不做的脏事,去背信弃义、颠倒黑白、杀戮同类。设若他们的卑鄙、残忍、狡诈确实提高了公众利益,而我们自己恰恰就是这一公众利益的受益者之一,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道德选择呢?
在战争时代,人们更容易接受铁石心肠、不怕做脏事的领袖。当然,也有一些人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坚持道德的准则,尤其是绝不使用暴力,这往往见于一些真诚地尊重教义的宗教人士以及坚定的原则主义人士。反抗虽然要坚持到底,但不能以任何人的生命为代价,无论是自己人的还是敌人的。
圣雄甘地在印度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一个显例。他以非暴力为第一原则,为此宁肯忍受失败。幸运的是,他成功了,否则不知道会给这一看似纯属“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斗争方式赢来怎样的名声。
 另外的问题是,当真以严苛的宗教标准衡量的话,或许连甘地这种程度的反抗也是不应该的,但这就不在当下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另外的问题是,当真以严苛的宗教标准衡量的话,或许连甘地这种程度的反抗也是不应该的,但这就不在当下的讨论范围之内了。
可以肯定的是,甘地会是奥米拉斯的出走者之一,孟子应当也是。当公孙丑问及伯夷、叔齐和孔子这三位圣贤的相同之处的时候,孟子答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也就是说,如果让他们做哪怕一件不合道义的事,杀掉哪怕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他们都不会做。

这样的问题,在坚定的原则主义者那里算不得太大的难题,而如果把问题换一个方式:假若必须做一件不合道义的事,杀掉一个无辜的人,才能挽救天下人的性命,他们会做吗?这个问题同样会把奥米拉斯的困境推向极端:假若那个无辜小孩的悲惨命运换来的不是全城居民的生活福祉,而是所有人的生命的话,该不该牺牲他呢?
如果答案是“应该”的话,那就意味着结果确实重于原则,所谓基本人权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被忽略掉的。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假若那些奥米拉斯的出走者认为在道义上应该救下那个孩子,却面临着全城绝大多数居民的抵制,不诉诸暴力则无法达到目标,那么他们该不该、又该在何种程度上诉诸暴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