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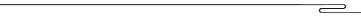
1973年,勒昆发表了一部幻想题材的短篇小说《走出奥米拉斯的人》,描述了一个叫作奥米拉斯的乌托邦,每个人在那里都过着人间天堂的日子,也都会在懂事之后被告知这座城市里的一个不太光彩的秘密:奥米拉斯所有生活福祉的存在(甚至包括清澈的蓝天和清新的空气),都有赖于一个被藏匿起来的孩子。这孩子被封闭在城里一个肮脏污秽的角落,饱受虐待和忽视,整日见不到一丝阳光。但如果我们把这孩子带到阳光之下,爱护他,关照他,那么奥米拉斯所有的福祉都会烟消云散。
桑德尔的《正义》引述了勒昆的这个故事,把它作为反对功利主义的一则生动鲜活的例证,认为反对边沁式的功利主义的人们会诉诸基本人权(fundamental human rights)以拒绝奥米拉斯的幸福生活。

事实上,在勒昆的小说里,的确有一些人默默地离开了奥米拉斯,没有人知道他们走向了哪里。但是,不管他们最后去了哪里,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再也找不到一个像奥米拉斯这样的人间天堂。他们也许根本就走投无路,但勒昆写到,这些离开了奥米拉斯的人“很清楚自己走向何方”。

面对奥米拉斯的问题,也许很多人都会选择离开,尽管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的离开不会对那个可怜的孩子有任何的帮助,对奥米拉斯的居民们也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唯一的实际后果就是使自己的生活变差。自己的离开只是一种表态,一种代价惨痛的表态,这就是原则主义的生活态度。
在小说里,勒昆对那个无辜孩子的生活处境的不惜篇幅的描绘足以使任何一颗善良的心抑郁许久,但如果我们抛开艺术的感染力不谈,假定那孩子仅仅忍耐着轻微的痛楚,故事的结局又会如何呢?
可想而知的是,会有更多的人心安理得地继续在奥米拉斯生活下去,他们或许仍然会认识到,加诸那个无辜孩子身上的不幸,无论是惨绝人寰的悲剧还是微不足道的小小不适,都使自己的生活在道德上有了瑕疵。
就小说的艺术而言,勒昆的这个故事属于典型的观念先行的作品,或许会使那些怀有纯文学兴趣的读者感到不快。其先行之观念取自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士,后者在1891年向耶鲁哲学俱乐部的一篇致辞里谈道:“假若给我们这样一个世界,足以胜过傅里叶、贝拉米和莫里斯所描述的乌托邦的世界,所有人都可以永远过上幸福生活,但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有某个人做出牺牲,自己去世界的边缘独自忍受孤独的折磨。”

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它不仅挑战了边沁式的功利主义,甚至还可以拿来对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发出质疑:威廉·詹姆士所设计的这个条件,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在“无知之幕”之下都应该投票选择的,虽然自己有可能成为那个不幸的牺牲品,但理性人(或许康德除外)不应该考虑小概率事件,换句话说,这个风险是值得冒的。只是,这样一个世界,难道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着道德瑕疵的吗?如果让康德来看,这算不算“以人为手段”的不道德的行为呢?
然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奥米拉斯的居民是因为“发现”了这个残忍的事实而良心不安,而在无知之幕下签订一个缔结奥米拉斯社会的契约却可以使人们心安理得地享受奥米拉斯的幸福生活,再也不会对那个牺牲者怀有任何的愧疚—因为他只是“中了彩票”,而每个人事前都自愿地投了注。
这看上去相当公平,但是,我们可以说每个人基于这一契约而享有的幸福生活是道德的吗?——公平,但未必道德,甚至并不是真正的幸福,因为至少在康德看来,奥米拉斯居民所享有的幸福并不与他们的德性匹配,而任何不基于德性的幸福都是毫无价值的。当然,奥米拉斯的幸福新居民们想来不会有太多人在意康德这种过苛的幸福标准,只是径自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不幸福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