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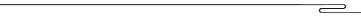
迦太基的圣西彼廉教堂里,圣奥古斯丁用《诗篇》(2:10)中的“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作为布道的开场白,继而阐释道:“审判尘俗就是驯服身体。让我们听听使徒保罗是怎么审判尘俗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哥林多前书》9:26-7)
圣奥古斯丁的这番布道既有中国先秦“赋诗断章”的风格,又充满了双关意涵和修辞趣味,总之是告诫世人,只有驯服身体才有望走向天国,否则只能“终身吃土”(《创世记》3:14),而那些“世上的审判官”应该追求贞洁,扼制激情,喜爱智慧,克服粗俗的欲望。他们应该受到这样的管教,然后才好这样去做。而这些管教概而言之,就是“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诗篇》2:11)

在奥古斯丁引述的诗篇里,所谓“世上的审判官”正是博絮埃所理解的“诸神”,只不过奥古斯丁做了特殊的引申,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自己的审判官。
教会中的虔敬女士们会很容易从中读出“人心中的上帝之音”,甚至连佛教徒都有可能从中产生“因戒生定,因定生慧”的同情的理解,但是,在把正义引入纯然的内省之前,我们有必要参考一下上帝本人是如何在人间主持正义的。
在正义问题上,上帝绝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或功利主义者,更不是康德和罗尔斯的信徒,但他的确有可能是一个社群主义者。
从巴别塔的故事来看,上帝很可能并不希望人类社会结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共同体,而是使其分散成若干个彼此难以沟通的小型社群。
 在社群内部,每个人的道德责任都是和他人关联的,甚至可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社群内部,每个人的道德责任都是和他人关联的,甚至可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旧约·创世记》第18章,上帝听说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座城市道德败坏,便带着两位天使打算实地考察一下,以便决定到底要不要毁灭这座城市。义人亚伯拉罕当时正为上帝送行,于是发生了如下一段对话:
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同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巧妙地运用了得寸进尺的心理战术,从他的担心和上帝的回答里可以看出,上帝是把所多玛的全部人民一体看待的,要么玉石俱焚,要么全城保留,并不会对城中特定的恶人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

但上帝对选民的要求并非如此。《旧约·申命记》24:16:“不可因儿子的罪处死父亲,也不可因父亲的罪处死儿子;各人要因自己的罪被处死。”《列王记下》和14:6引述这条记载,称之为“这是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是耶和华的吩咐”,尽管选民们并不曾严格奉行这条律法,而是或多或少地模仿了上帝的株连式的惩恶风格。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持《新约》信仰的人一般会相信“最终”每个人都会得到公正的审判,或上天堂,或下地狱,泾渭分明,但若仅从文本来看,《新约》重视心灵与天堂的福祉,《旧约》却表现得相当世俗化,上帝的赏赐往往是财富丰饶、子孙繁衍,惩罚则是现实的、肉体上的毁灭—最突出的例子恐怕就是诺亚方舟的故事,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并不是待他们度过一生之后给以最终审判,而是以一场洪水对人类做肉体上的消灭。
再如《诗篇》第88章,这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在临死之时吁求上帝的声音,他说“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他们是你不再记念的,与你隔绝了”(88:5),又因为始终不曾获得上帝的垂怜而哀号道:“耶和华啊,我天天求你,向你举手。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88:9-12)在罗马人的斗兽场上欣然赴死的早期基督徒们恐怕很难理解,这一诗篇的作者为什么对忧患的生命如此恋恋不舍,又为什么会认为人死之后就无知无觉,不再被上帝记念?
一般来说,犹太教一直坚守《旧约》信仰,只承认耶稣是一位先知,天主教和新教则持《新约》信仰。涂尔干在研究宗教对自杀的影响时谈道: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样相信上帝和灵魂不灭,犹太教则是灵魂不灭的思想最不起作用的宗教,《旧约》有关来世的信仰是很不明确的。
 所以,在所多玛事件里,我们有必要在《旧约》背景下理解上帝与亚伯拉罕那一段对话的含义所在。
所以,在所多玛事件里,我们有必要在《旧约》背景下理解上帝与亚伯拉罕那一段对话的含义所在。
所多玛城里可能存在的寥寥可数的义人该不该为同城恶人们的罪行负责呢?或者,那些恶人该不该因为义人的存在而受到宽恕?全能的上帝当然有能力实施精确打击,所以他的一体看待的做法一定是有道理的。即便在无神论者看来,这至少反映了《旧约》先民们的道德观念,他们假想出的是一位至公而全能的上帝,所以上帝对所多玛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一定符合完美的公正。
这就意味着,每个人并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个体,至少个人的责任和命运是与共同体的责任和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但“不得不”如此,甚至“应该”如此。
这关乎人的另外一种心理:你接受了某种恩惠,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尽管给你的这份恩惠并不曾(甚至并不可能)得到你的同意。
最简单的例子,譬如出生到这个世界从来不是任何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但父母既然给了你生命,你便理所当然地对父母承担责任—尽管存有些许争议,但这毕竟是千百年来普世性的共识。“我把孩子养育,使他们成长,他们却背叛了我”(《旧约·以赛亚书》1:2),这是连上帝都无法接受的事情。那么,对于父母的罪过,在生育自己之前所犯的罪过,自己“是不是”或者“该不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
自由主义者对这种问题一般都会说“不”,但在上帝的眼里,责任是明显具备连带性的。“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毗夺人比珥的儿子巴兰来诅咒你们。……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申命记》23:2-8)
亚扪人和摩押人的子孙因为祖先的过错而永远地成为了上帝的弃民,这对原罪理论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自由主义者不会认同这样的道理,但自由主义的基督徒,如果他们接受奠基于圣奥古斯丁并在今天被定为正统神学的原罪理论,并且对信仰足够真诚的话,那就必然会踏进一个两难的处境:何止是父母的罪过,就连人类始祖的罪过都是担在我们每个人肩头的。
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凭什么要为远远生活在山顶洞人、元谋人之前的人类始祖的过错负责?但是,无论在基督教的理论体系里,还是在现实世界本身,这首先不是一个应然问题,而是一个实然问题。这个责任即便我们不想担,即便认为不应该担,但它实实在在地就担在我们每个人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