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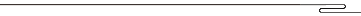
信息控制是主人控制奴隶的一项重要的管理技术。一名黑人老者在回忆南北战争之前的奴隶生涯时谈到,像他这样的黑人穷鬼是不许读书识字的,主人说这有助于黑奴们安守本分,但有过一个聪明绝顶的黑人孩子居然学会了读写,他常在地里向同伴们讲解《圣经》,可同伴们没他那么聪明,从来都是随学随忘。

但这不大适宜解释清朝的政治传统,满汉大臣们虽然在阅读范围上分别受到了一些局限,但他们都是当时社会里的精英分子,即便称不上学识渊博,至少也有最基本的文化教养并且见多识广,他们难道真的不曾想过要讨还自己的某些权利吗?
严格辨析起来,人们是否享有天赋人权是一回事,在发现自己的天赋人权遭到侵犯之后是否具有讨还天赋人权的权利,这是另一回事。统治者或许具有这种权利,但人民只有逆来顺受的义务。——令人吃惊的是,这并不是古老的“君权神授”理论的结果,而是康德在1797年基于实践理性原理缜密地论证出来的,从人的自由意志、天赋权利、人不能以人为手段、建设法治社会,推理出“人民有义务去忍受最高权力的任意滥用,即使觉得这种滥用是不能忍受的”。

我们从中似乎隐约看到了色拉叙马霍斯那狂妄的身影,然而不仅康德,黑格尔也紧承其后,论证“德性就是服从政府”。今天的人们并不因为这些论调才崇敬康德和黑格尔,这或许是一件好事。

近年的一大思想主流是自由主义,米塞斯提出过一个行为通则(general theory of choice),被自由主义者奉为典范:任何人的行为都只受到唯一的限制,即不对他人造成损害。穆勒则早在1859年出版的经典之作《论自由》一书中试图确立“一条极为简单的原则”,即“人类获权——无论以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方式——干涉他们当中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就是自我保护”。
 依照这样的标准,上述那位八旗亲贵如果真去追求天赋人权,当然会损害到主人的利益。——米塞斯本人不会同意这个结论,因为他的行为通则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所有人都已经享有了基本人权,他们在基本权利上是完全对等的。
依照这样的标准,上述那位八旗亲贵如果真去追求天赋人权,当然会损害到主人的利益。——米塞斯本人不会同意这个结论,因为他的行为通则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所有人都已经享有了基本人权,他们在基本权利上是完全对等的。
那么,对于这位八旗亲贵而言,他首先要做的只能是夺回自己的天赋人权,又或者“以直报怨”的准则才是更加可取的——因为他的天赋人权受到了主人的侵夺,所以他应当行使等值的报复。
但是,对利害关系的权衡很可能使他放弃这份努力,从而安心享受做奴才的好处。是的,如果“天赋人权”和“以直报怨”都只是平衡私利的行为,为什么“甘做奴才”的选择偏偏就该受到任何的道德责难呢?——问题在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起点。

如果我们说,为了利益而牺牲人格,这是可耻的,不道德的。那就有必要追问:为什么做奴才就是牺牲人格呢?卢梭或许会用他那句“人人生而平等”的名言来回答这个问题,并且可想而知的是,他会得到相当广泛的赞同。遗憾的是,这同“天赋人权”一样,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一个“高贵的谎言”,找不到任何有力的依据。仅仅认为人人“应当”生而平等并不能证明人人“确实”生而平等。
所以,美国《独立宣言》在采信卢梭这一观点的时候,做了一些必要的限定:“我们认为下列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首先这观点是“我们认为”的,其次这些权利是“造物主赋予”的,并不来自于任何扎实的、学理上的论证。
的确,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真正不言而喻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生而平等。
更有甚者,“生而平等”固然论证不出,“生而不平等”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即便抛开出身的不平等,人的天赋、性情也是不平等的。如果我们认同《中庸》这部儒家经典所提出的自由主义式的理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认同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每个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天性自由发展,那么,既然可以存在卡里斯玛型的天生领袖,为什么不可以存在某种类型的天生的奴才呢?
自由主义式的回答是:天生具有奴才禀赋的人当然有权去做奴才,这在道德上没有任何不光彩的地方,只要让渡基本权利的行为是自愿的,这就无可指责。这就意味着,人首先必须拥有天赋人权,然后可以经由自愿原则,把天赋人权让渡出去。(尽管很难想象,权利如果是天赋的[natural]、固有的,又怎么可能被让渡出去。)
那位八旗亲贵就可以采用这样的办法,在求得主人的同意之后完成以下的程序:先把自己的天赋人权争取过来,然后再让渡出去,在自愿的前提下重新投身为奴。—穆勒曾经专门讨论过人有没有卖身为奴的自由,他的结论是否定的:自由原则不能使人拥有放弃自由的自由。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穆勒感情用事的一面,他的结论并没有足够的逻辑支持。而只要我们甘愿做一个铁石心肠却头脑清晰的人,那么,我们显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八旗亲贵的如此做法违反了自愿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穆勒感情用事的一面,他的结论并没有足够的逻辑支持。而只要我们甘愿做一个铁石心肠却头脑清晰的人,那么,我们显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八旗亲贵的如此做法违反了自愿原则。
这就意味着,做奴才这件事本身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当然会有很多人不会赞同这个论调,而是认为做奴才有损于人的尊严。出现这种心态并不足为奇,正如迈克·桑德尔举过的一个拉拉队员的例子:凯莉·斯玛特是学校里一名人气很旺的拉拉队员,因为身体的缘故,她只能坐在轮椅上为比赛打气,尽管她做得很出色,但终于还是被踢出了队伍,因为这正是其他一些拉拉队员和她们的父母强烈要求的。
桑德尔推测那位呼吁最出力的拉拉队长的父亲的心态:他既不是担心凯莉占了拉拉队的名额而使自己的女儿无法入选,因为女儿已经是队里的一员了;也不是嫉妒凯莉盖过自己女儿的风头,因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最有可能的是,他认为凯莉僭取了她不配取得的荣誉—如果拉拉队的表演可以在轮椅上完成的话,那么,那些擅长翻跟头、踢腿的女孩子的荣耀就会受到贬损。

如果凯莉·斯玛特可以因为这个理由被踢出局外的话,我们似乎有同样的理由鄙视那位八旗亲贵,奴才的存在就是对人类尊严的贬损。
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如果仅仅是贬损人的尊严,并不必然就是不道德的,甚至还会恰恰相反。譬如基督徒奉行谦卑,在神面前极力贬损自己的尊严,越是做到极致的信徒越是容易赢得道德的美誉。
《旧约·撒母耳记下》记载,当耶和华的约柜被运送进城的时候,大卫王为之跳跃舞蹈,他的妻子米甲(扫罗之女)从窗口看到了这一幕,只感觉莫大的羞耻。她语带讥讽,对大卫王说:“以色列王今天多么荣耀啊!他今天竟在众臣仆的婢女眼前,赤身露体,就像一个卑贱的人无耻地露体一样。”但大卫王不以为然道:“我是在耶和华面前跳舞;耶和华拣选了我,使我高过你父亲和他的全家,立我作耶和华的子民以色列的领袖,所以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跳舞作乐。我还要比今天这样更卑贱,我要自视卑微。至于你所说的那些婢女,她们倒要尊重我。”——《撒母耳记》的作者显然是褒扬大卫王和贬低米甲的,他继而写道:“扫罗的女儿米甲,一直到她死的日子,都没有生育。”(《撒母耳记下》6:16-23)
 熟悉《旧约》自然知道,无法生育对当时的女人来说可谓最严厉的惩罚。
熟悉《旧约》自然知道,无法生育对当时的女人来说可谓最严厉的惩罚。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同类的事例,以佞佛著称的梁武帝就曾多次舍身佛寺,以帝王之尊甘为“寺奴”。人们往往只是批评他的愚顽,却不大论及这份对舍身为奴的执著是否有伤做人的尊严。
即便是无神论者,他们会嘲讽神的虚妄,却很少会把宗教信徒和奴才画上等号。也就是说,在绝大多数的无神论者看来,即便是侍奉一位被人类自己臆想出来的虚妄的神,在道德上也远远高于侍奉一位有着血肉之躯的主人。
一个耐人寻味的对照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不卑不亢、恢弘大度自古以来都被看作君子的美德,亦即一个人在道德上应当表现出来的中庸之道。若超过这个标准则是高傲,低于这个标准则是谦卑,高傲与谦卑都不可取。而谦卑,尤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比高傲更加远离中庸之道,因为它更普遍,而且更坏。

可资对照的是,宋儒李觏对传统儒家的中庸之道提出过另一种意见,认为“过犹不及”可以细辨,“不及”可以使人勉励上进,“过”却是无法挽回的。
 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对“不及”的清醒认识会使人抱有谦卑的姿态,这更容易培育美德。
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对“不及”的清醒认识会使人抱有谦卑的姿态,这更容易培育美德。
正反两方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里,高傲即自视过高,谦卑即自视过低,然而在许多宗教信徒看来,人在神的面前无论怎样贬低自己也不会存在自视过低的问题,问题仅仅在于,即便不折不扣地认可这种神与人的悬殊,人的不卑不亢是否仍然可以被看作一种美德,我们是否应该像约伯一样以极尽谦卑的姿态来承受命运的(至少看上去的)不公,
 还是不妨像尼采一样径将基督徒的谦卑看作一种该当鄙视的奴隶的道德?
还是不妨像尼采一样径将基督徒的谦卑看作一种该当鄙视的奴隶的道德?
若从应然返回实然,我们便会发现,事实上即便在人与人之间,融洽的主奴关系往往也是人们喜闻乐见的。美国在1936—1938年间开展过一个文化项目,走访了大量曾经做过黑奴的老人,记录他们对奴隶生活的回忆。在这些记录里,既有我们意料之中的血泪史,也有一些温暖的、甚至称得上甜蜜的日子。
W. L.波斯特回忆自己的奴隶生涯,说太太是个很好的人,从不允许主人买卖任何奴隶,种植园里也不设监工,总是由年长的黑人来照顾大家。
玛丽·安德森,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86岁高龄,她在1851年出生于北卡罗来纳的一座种植园里,父母都是这里的奴隶。玛丽回忆道,这里大约有162名奴隶,大家的伙食不错,衣服也有不少,住的是舒适的两居室。每个星期天都是奴隶们的大日子,大人们去主人的宅子里领取饼干和面粉,孩子们到主人的宅子去吃早饭,每个孩子都能领到足够的水果。如果主人和太太发现哪个孩子吃不下饭或者健康状态不佳,就会留下他来,给他吃饭、服药,直到好转。
后来北方军队打了过来,主人和太太逃走了,奴隶们获得了解放。直到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的第二年,主人和太太这才坐着马车回来,四处寻访当初的奴隶。每找到一个奴隶,主人和太太都会说:“这下好了,回家吧。”玛丽的父母,还有两个叔叔的全家,都跟着主人回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回去了。有些人甚至为此喜极而泣,因为他们在“解放”之后的日子过得很苦,连饭都吃不饱。
玛丽·阿姆斯特朗,一位91岁的老奶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动情地回忆起自己做奴隶时候的温暖时光。日子一开始是相当可怕的,因为太太是个极其凶残的人,有一次因为厌烦孩子的哭声,把玛丽才9个月大的妹妹鞭打致死。
后来小姐嫁了人,玛丽跟着小姐,从此有了新的归宿。小姐很护着玛丽,即便玛丽在愤怒中打伤了太太的眼睛,小姐也坚持不肯交出“凶手”。玛丽回忆道:“威尔先生和奥莉薇娅小姐对我很好。我从来不叫威尔先生作‘主人’,有外人在场的时候,我就叫他‘威尔先生’,私下里我叫他们‘爸爸’和‘妈妈’,因为正是他们把我抚养成人的。”

融洽的主奴关系甚至连上帝也会为之欣悦。《旧约·申命记》专有一节记载对待奴婢的条例,首先规定了同族奴隶的服役期限:“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15:12)如果满了期限之后,奴隶并不愿意离你而去,“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为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15:16-17)

人做人的奴仆会做到留恋而不愿离开,人做神的奴仆就更会是一件快乐的事。《旧约·诗篇》有这样一句话:“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2:11)如果一名虔诚的信徒缺乏了这种畏惧,反而有可能怅然若失。——弗洛姆就谈到过这样一个例子:一名信徒向上帝祈祷:“主啊!我是如此地爱您,但并不很惧怕您。让我敬畏您吧,就像您的一位天使一样,他为您充满了敬畏的名字所打动。”

这种人与神的关系可以顺理成章地转变为人与人的关系—圣依纳爵·罗耀拉在一封书信里真诚地写道:“我应该期望,我的上级强迫我放弃自己的判断,压制自己的心灵。我不应该区分这个上级还是那个上级……而应承认他们在上帝面前统统平等,他们都代表上帝……我在上级手里,必须成为一块柔软的蜡,一个玩意儿,投其所好,任他摆布……我绝不询问上级要把我派到什么地方,将差我执行什么特殊使命……我绝不认为有什么事务属于我个人,绝不顾及我所用的东西,我就像一尊雕像,任人将衣衫脱去,绝无任何抵抗。”

罗耀拉的信可以看作《致加西亚的信》的加强版,后者作为国内近10年来的超级畅销书,其所传达的价值观不可思议地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是的,即便在今天的流行文化里,人与人之间的主奴关系依然大受青睐。不妨以红极一时的韩剧《大长今》为例,剧中的宫女们伺候皇上也完全就是这样的心态,该剧令人咋舌的收视率充分说明了今天的广大观众对此竟然全无恶感。个中缘由,是女性在东方传统里始终被定义为服从的角色。如果以同样的模式拍一部李连英伺候慈禧太后的电视剧,观众或许不会觉得舒服。
更有甚者的是,即便在幻想着人人平等、财产公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也并不全然排斥奴隶的存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就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奴隶,那是另一国家的贫苦无以为生的苦工,他们有时自愿到乌托邦过奴隶的生活。这些人受到良好的待遇,只是工作重些,也是他们所习惯了的,此外他们如乌托邦公民一样享有几乎同样宽大的优待。其中如有人想离去(这种情况不多),乌托邦人不勉强他们留下,也不让他们空着手走开。”
 这会使我们联想到当今国际社会上的偷渡客的问题,伟大而充满人文关怀的乌托邦并没有给予偷渡客们平等的公民身份,而是以良好的待遇和相当程度的人身自由役使他们为奴。在莫尔看来,这非但没有一点可耻,反而提升了乌托邦的形象。
这会使我们联想到当今国际社会上的偷渡客的问题,伟大而充满人文关怀的乌托邦并没有给予偷渡客们平等的公民身份,而是以良好的待遇和相当程度的人身自由役使他们为奴。在莫尔看来,这非但没有一点可耻,反而提升了乌托邦的形象。
从古至今,主奴关系从未受到普遍的排斥,这也就意味着,普遍的平等(权利上的平等)从来就没有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平等从来都只是平等者内部的平等——这是第九章将要详细论述的。除此之外,相当程度上这是嫉妒心作祟。正如“文人相轻”这句话告诉我们的,文人总是吝于赞美同辈的文人,对前辈,尤其是古代文人,以及其他领域的杰出人士却不乏溢美之词。这当然不是文人独有的心态,而是人类的心理通则,只不过文人往往将之形诸笔墨,才显得尤其醒目罢了。在人神并存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就变成了相对而言的同类小圈子,神的世界则属于“其他领域”。人对神的崇拜引不起其他人的嫉妒,人对人的崇拜却足以令项羽之辈生出“彼可取而代也”的艳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