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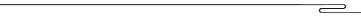
追溯历史的话,会发现卢梭提出的天赋人权论以及人们对它的如此狂热的追捧,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即人类长期以来都相信自己只能发现权利,但不能创造权利。这在立法领域里表现得最为显著,如哈耶克所谓:“国王或是任何其他的人类当权者只能公布或发现现有的法律,或者更改潜移默化地发生的滥用,可是他们不能创立法律,这是数百年来被公认的理论。有意识地创制法律(即我们所理解的立法)的观念在中世纪晚期才逐步地被人们接受。”雷费尔特《法律的根源》写道:“立法现象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意味着发明了制定法律的艺术。到那时为止,人们确曾以为,人们不能确定权利,而只能把它作为一件一向存在的东西去使用它。”

这种观念至少直到18世纪末仍然在欧洲深入人心,这使得法律上的推论全部属于演绎法而非归纳法。
 而实际上,卢梭所做的事情正是一种立法工作,以中世纪的“权利发现者”的风格,为最宽泛意义上的“人”确定最宽泛意义上的“权利”。
而实际上,卢梭所做的事情正是一种立法工作,以中世纪的“权利发现者”的风格,为最宽泛意义上的“人”确定最宽泛意义上的“权利”。
的确,仔细辨析的话,所谓权利完全是人的社会属性,并且属于应然范畴。我们可以说人天生有吃饭的欲望和能力,但没法说人天生拥有吃饭的权利。显而易见的是,天赋人权是一个应然问题,而任何应然问题都不可能是“天赋”(natural)的,而只能是道德的诉求,是人与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各自出于最大限度地争夺私利的目的,经过种种斗争与妥协而逐渐磨合出来的。
也就是说,所谓天赋人权,并不是一个事实,而在事实上仅仅是一种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追求是为另一个目标服务的,即增进生活的福祉。以法国1879年的《人权宣言》为例,宣言的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讲道:“代表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这就是说,天赋人权是被作为解决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一块基石,或者说是公众用以增进生活福祉的一件工具,或者说是公众的一种联合逐利的手段。
那么,不妨试问一个问题:如果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君权神授”或“天赋奴权”是否可以和“天赋人权”获得同样的道德权重?或者,人们之所以抛弃“君权神授”或“天赋奴权”,只是因为它们无法达到与“天赋人权”所可能带来的同等程度的福祉增进?
仅仅在心理学的层面上,“天赋人权”才是一个实然问题,即其源自人类天生的嫉妒或攀比心理。譬如陈胜那句激荡人心的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有项羽在看到秦始皇车驾之盛时所感叹的“彼可取而代也”,陈胜和项羽虽然看到自己与王侯将相或秦始皇之间的现实悬殊,但显然认为对方所享有的权利自己同样有权享受。
秦始皇所享有的权利之所以不会被卢梭认定为天赋人权,这和“天赋”并没有半分关系。所谓天赋人权,只是私心在博弈中艰难赢得的战利品,是竞争中的人与人一个阶段性妥协的结果,既非自然的事实,也没有任何高尚感可言。
那么,既然天赋人权既是逐利的结果,又是逐利的手段,若它与利益发生了冲突,应当怎么解决呢?譬如有这样一位八旗亲贵,世代包衣,饱受皇恩眷顾,但假定他读过了卢梭的书,又了解美国独立战争的全部经过,深知自己和皇帝拥有同样的天赋人权,他应当何去何从呢?
作为理性人,这个选择并不复杂,无非是权衡自己心里那只天平的两端孰轻孰重。但是,套用迈克·桑德尔的标题:“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怎么做才是“对”的,才是在道德上正确无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