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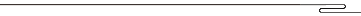
依清代典章制度,满臣上疏自称奴才,汉臣上疏则当称臣。乾隆三十八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联合上了一道奏章,因为天保署名在前,便连书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帝对这个署名大为光火,斥责马人龙“冒称”奴才。为了杜绝这种现象,乾隆帝规定,若再有满汉大臣联名奏事,署名一律称臣。——这就是说,为了不让汉臣冒称奴才,宁可让满臣受点委屈。
奴才,这个极具侮辱性的称谓在清代却代表着尊荣和特权,是许多只能称臣的汉人企慕不及的。如果我们援引“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等值原则,一个人当了奴才,这到底是德还是怨呢?
今天看来,主奴关系显然标志着对奴才的基本人权的践踏,但在许多缺乏现代人权观念且世代为奴的古人看来,主奴关系恐怕却是一个人所能想象的最好的人际关系,既有温情脉脉的家庭之感,又是幸福生活的妥善保障。
如果以追求幸福或增进生活福祉为目的,那么,维护或建设和谐的主奴关系至少是众多可取的社会改良方案当中的一种,如此一来,编造一些“天赋主权”与“天赋奴权”之类的神话当然合乎正义。
柏拉图在设计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问题,因为他必须使理想国里分属三大等级的人们各安其位,否则若有人产生僭越的念头,社会的和谐结构就会动摇。于是,柏拉图认为应当编造一种“高贵的谎言”,说是神创造了这三种人,最好的一种人是用黄金做的,次优的是用白银做的,普通群众则是用铜铁做的。黄金等级天然适合做卫国者,白银等级组成军队,铜铁等级则去从事各种体力劳动。柏拉图相当清醒地认为,使当代的人相信这个神话是不太可能的,但是通过有效而持久的教育,完全可以使下一代,乃至以后所有的世代都对此深信不疑。

柏拉图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用心险恶,这在他而言的确是一种正义的追求。
 事实上,柏拉图的这一理想确曾在历史上得到过许许多多不同程度的不谋而合的实践,譬如《荀子·礼论》所谓:
事实上,柏拉图的这一理想确曾在历史上得到过许许多多不同程度的不谋而合的实践,譬如《荀子·礼论》所谓: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诡唈僾而不能无时至焉。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愅诡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动也;案屈然已,则其于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于礼节者阙然不具。故先王案为之立文,尊尊亲亲之义至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故钟、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护、武、汋、桓、箾、象,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喜乐之文也。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哀痛之文也。师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称罪,是君子之所以为愅诡其所敦恶之文也。卜筮、视日、斋戒、修涂、几筵、馈荐、告祝,如或飨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尝之。毋利举爵,主人有尊,如或觞之。宾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状乎无形影,然而成文。
《荀子》这段话先是强调祭祀要表达真情实感,像忠臣怀念去世的国君,孝子怀念去世的双亲,这些感情都是自然而然的,需要渠道来表达出来。先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制定了祭祀的礼仪制度。接下来就点明为政之道中自觉不自觉的“高贵的谎言”了:感情的妥善表达和礼仪的繁复呈献,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圣人才能明白。圣人心知肚明,士君子安然施行,官员把这当作自己职责的一部分,老百姓把这当作风俗习惯。在君子眼里,祭祀是在尽人事;在老百姓眼里,祭祀则是和鬼神在打交道。所以,各种名堂的音乐都是君子们表达感情的工具,各种形式的服丧礼节都是君子们表达哀恸的手段,就好比军队有军纪,刑罚有尺度,君子感情的发泄一样是有规则和尺度的。虔诚地奉献祭品,如同鬼神真的前来享用似的;主人脱下祭服,换上丧服,送走客人之后回到原位哭号,如同鬼神真的离去了似的。悲哀啊!虔敬啊!对待死者如同对待生者,侍奉亡人如同侍奉活人,这就是礼仪。
《荀子·天论》还讲到作为一种“高贵的谎言”的雩祭: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首先是一个设问:“搞雩祭求雨,结果真就下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回答是:“不为什么,就算不搞雩祭,到下雨的时候自然下雨。日蚀、月蚀发生的时候,人们敲锣打鼓想把日月救出来,天旱的时候人们搞雩祭来求雨,有了疑难问题就占卜决定,这些事情道理都是一样的。难道搞雩祭、占卜什么的真就管用吗?不过是个幌子罢了。君子知道这些都是幌子,可老百姓却以为是神灵的作用……”
《礼记·檀弓》有一段孔子之言可资参考,大意是说,吊唁死者,若认为死者无知无觉,这是缺乏仁心;若认为死者有知有觉,这是欠缺理智。所以送葬的物品,竹器不堪使用,瓦器不能盛放食物,木器不可雕琢,琴瑟虽然张弦但弦不绷紧,竽笙虽然具备却不成声调,有钟磬而没有悬挂的支架。这些器物叫作明器,意思是视死者如神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故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故而“礼者,众人法而不知,圣人法而知之”
,故而“礼者,众人法而不知,圣人法而知之”
 。
。
儒家这种做法看上去表里不一,所以遭到过墨子的讥讽,显然墨子没看明白其中的“深意”。
 即便是儒家后学也往往忘记了先师的这一“深意”,譬如范缜在“神灭论”的著名争议中居然就遭遇过论敌这样的提问:儒家经典上说“为之宗庙,以鬼享之”,难道不是有鬼之论吗?范缜的回答是:这只是圣人的神道设教罢了。
即便是儒家后学也往往忘记了先师的这一“深意”,譬如范缜在“神灭论”的著名争议中居然就遭遇过论敌这样的提问:儒家经典上说“为之宗庙,以鬼享之”,难道不是有鬼之论吗?范缜的回答是:这只是圣人的神道设教罢了。

儒家圣人的这层“深意”很有普世价值——176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效仿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写了一篇虚构的《中国皇帝的使臣菲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谈到这位使臣对基督教世界大感隔膜,幸好在返归途中有一位知情晓理的男人和他闲聊:“他察觉到我对所见的一切都感到惊讶,便对我说:‘您不认为,每个宗教都必须有一些打动人心的东西吗?我们的信仰就是为了打动人心而存在着的,这东西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当人们给予一种信仰以某种——您认为是虚张声势的——礼拜仪式时,人们就得服从宗教的戒律和习俗。只要您考察一下我们的道德,就会看到这点。’说着,他递给我一本由他们的一位学者撰著的书。我发现该书内容与孔子的道德学说几乎相同。”

是的,不仅儒家,这种神道设教的精英主义政治哲学在人类历史上始终长盛不衰,其支持者既有著名的学术正统(如亚里士多德),也有臭名昭著的卑鄙小人(如马基雅维利)。
 他们主张着自己一点都不相信的东西,认为这对社会—至少对统治者们——大有裨益。即便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和维拉斯的塞瓦兰人的世界里,“神道设教”都是理想政治体制的第一块基石。杨庆堃在其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名著中做过这样一句断言:“在前科学时代,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化的学说完全建立在世俗的基础之上。”
他们主张着自己一点都不相信的东西,认为这对社会—至少对统治者们——大有裨益。即便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里和维拉斯的塞瓦兰人的世界里,“神道设教”都是理想政治体制的第一块基石。杨庆堃在其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名著中做过这样一句断言:“在前科学时代,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化的学说完全建立在世俗的基础之上。”

这当然不是“前科学时代”特有的现象,事实上,为现代人耳熟能详的一些极具正义感的社会追求正是建立在各种各样的“高贵的谎言”之上。譬如卢梭创立“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s)的观念,成为法国《人权宣言》、美国宪法等西方社会纲领性文件的思想奠基,对人类福祉的增进不可不谓居功至伟,但就这一概念本身来说,仍不过是一个“高贵的谎言”,谁也证明不出人为什么会“天然地”享有某些权利,即便诉诸神学也很难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