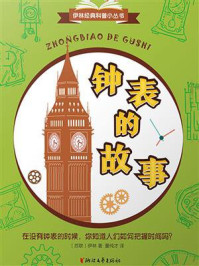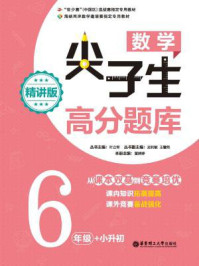布兰卡港/地质/大量的大型四足动物/近期的动物灭绝/物种存在的时间/大型动物并不需要繁茂植被养活/南部非洲/西伯利亚的化石/两种鸵鸟/灶鸟的习性/犰狳/毒蛇、蟾蜍、蜥蜴/动物冬眠/海鳃的习性/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和屠杀/箭头,古代遗物

拉普拉塔河鸟瞰图
小猎犬号于8月24日到达布兰卡港,一周后驶往拉普拉塔河。征得菲茨罗伊船长的同意后,我留下来,走陆路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把这一次和小猎犬号测量海港那次所作的观察,合并在一起谈。
离海岸几英里远以外的平原都属于大潘帕斯地质构造,由发红的粘土和含大量石灰的泥灰岩构成。更靠近海岸的几片小平原则是来自上游平原的碎土块与陆地缓慢上升期间从大海里抛上来的淤泥、砾石和沙子形成的。陆地上升的证据包括升高的岩床里埋有现存的海贝类,以及散落各处的浑圆的浮石鹅卵石。阿尔塔角有一片地区就属于这种后来形成的小平原。这里埋有很多结构特异的巨大陆地动物的遗骸,意义非同小可。欧文教授在《小猎犬号航海之动物学》里对这些遗骸有系统的描述,遗骸本身收藏在英国外科医学院。我在这里只说说它们的大致特点。
第一,三头大地懒( Megatherium )的部分头骨和其他骨骼,看名字就知其尺寸之大。第二,巨爪地懒( Megalonyx ),大地懒的近亲,也是庞然大物。第三,伏地懒( Scelidotherium ),与前两者近缘,我收集到了一具近乎完整的骨骼,应该跟犀牛一样大。欧文先生说,它的头骨结构最接近好望角食蚁兽,但有的部位则更像犰狳。第四,达氏磨齿兽( Mylodon Darwinii ),前几种动物的近缘属,但体型略小。第五,一个巨大的贫齿目(edental)四足动物。第六个大动物具有像犰狳那样分块的骨质甲。第七,已绝种的马,我会在后面再讲到。第八,一种厚皮动物( Pachydermatous )的牙齿,很可能就是长颈驼( Macrauchenia ),一种像骆驼一样有长脖子的巨型野兽,我后面也会再提及。最后一个箭齿兽( Toxodon )或许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怪异的动物之一。它的尺寸与大象或大地懒相当;但欧文先生指出,它的牙齿结构无可争议地表明它与啮齿类动物(Gnawers)是近亲,虽然现今的啮齿类包揽了大多数最小的四足动物。在很多细节上,箭齿兽与厚皮动物近缘;但从眼睛、耳朵和鼻孔的位置来看,它可能生活在水里,与儒艮(Dugong)和海牛(Manatee)也是近亲。换句话说,如今已经大相径庭的几个目的特征,都可以在其结构的不同部位上找到,却浑然一体而构成箭齿兽。这是多么奇妙的事!

大懒兽的骨骼

1796年左右在巴拉圭发现的大地懒骨骼平版印刷画

臀兽的骨骼

磨齿兽的骨骼

箭齿兽的骨骼
这九种大型四足动物的遗骸,以及更多散落的骨头,埋在海滩上大约两百平方码的区域内。在同一地点发现这么多不同的动物非同寻常,说明远古时代这个地区的动物种类繁多。我还在离阿尔塔角约三十英里的红土崖里找到了几块骨头片段,有的也很大。其中有一颗啮齿动物的牙齿,大小和形状都像水豚的牙。水豚的习性前面已经描述过了,因此,这一个大概也是水生动物。还有一个栉鼠属动物的部分头骨。它与栉鼠是不同种,但大体上相似。根据埃伦伯格教授的分析,这里的红土跟潘帕斯草原上的一样,里面埋有八种淡水和一种海水滴虫类微动物,因此很可能也是一个河口的冲积层。

达氏磨齿兽素描
阿尔塔角的遗骸埋在分层的沙砾和发红的泥土里,就像大海冲击浅海岸形成的那样。埋在一起的还有二十三种贝壳,其中十三种是现在仍然生活的种类,另外四种与它们非常相近
 。伏地懒的骨头,包括膝盖,埋在土里却依然保持着相应的位置;那个巨大的犰狳状的动物的骨铠甲,连同一块腿骨也保存完好。根据这些观察,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遗骸在跟贝壳一起被埋入沙砾里时仍然是新鲜的,仍由韧带连接在一起
。伏地懒的骨头,包括膝盖,埋在土里却依然保持着相应的位置;那个巨大的犰狳状的动物的骨铠甲,连同一块腿骨也保存完好。根据这些观察,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遗骸在跟贝壳一起被埋入沙砾里时仍然是新鲜的,仍由韧带连接在一起
 。因此,我们的证据充分表明,在它们生活的时代,大多数今天的海洋动物已经定居大海了。因为这些庞然大物跟欧洲第三纪最古老的四足动物更接近,而与现在生存的动物差别很大,这也就证实了莱尔先生常常强调的规律,即“总的说来,与有壳类相比,哺乳类的物种存在的时间跨度更短”。
。因此,我们的证据充分表明,在它们生活的时代,大多数今天的海洋动物已经定居大海了。因为这些庞然大物跟欧洲第三纪最古老的四足动物更接近,而与现在生存的动物差别很大,这也就证实了莱尔先生常常强调的规律,即“总的说来,与有壳类相比,哺乳类的物种存在的时间跨度更短”。

大地懒、巨爪地懒、伏地懒和磨齿兽这几个大懒兽类动物的骨骼之大,堪称奇异。这些动物的生活习性曾像谜一样让博物学家困惑,直到欧文教授 [1] 巧妙地解答了这个问题。结构简单的牙齿表明这些大懒兽动物是靠植物为生,可能就是树叶和嫩枝。它们笨重的体型和巨大有力的弯爪似乎不适合跑动,一些著名的博物学家甚至相信它们如同近缘的树懒,可以倒挂在树上爬行,以树叶为食。这样的猜想,即使不算荒谬也过于大胆了一些,居然能想象出史前树木的树枝结实到足以承受体大如象的动物。欧文教授的说法更合理,他认为它们并不爬树,而是把树枝拽下来,或把小一些的树连根拔起,吃上面的树叶。顺着这个思路去想,它们肥厚笨重的臀部(没见过的话都难以想象)就不是累赘,而是变得有用了,看似笨拙的形象也就消失了。巨大的尾巴和后脚跟像三脚架一样稳稳地支在地上,它们就可以自如地发挥强有力的胳膊和爪子的优势了。倒是树必须根深蒂固,才能对抗这么强大的力量!这个磨齿兽还跟长颈鹿一样,有一条长长的、伸缩自如的舌头。用这个大自然赐予的珍贵礼物,它可以靠长脖子去够那些枝肥叶厚的美餐。我再加一个小插曲,据布鲁斯(Bruce)说,阿比西尼亚(Abyssinia)的大象长鼻子够不着树枝时,会用象牙去切树干,上上下下、团团转转地切出很深的沟痕,直到树干支持不住而折断。
埋有这些化石遗骸的岩层仅比最高水位高出十五到二十英尺,就是说,从这些巨型兽在平原上漫游的时代到今天,陆地上升得并不多(没有证据表明上升时期之间还出现过下沉),那么该地区的地貌特征应该也几乎没变。我们自然会问,那时候的植被是什么样子?这个地区跟现在一样惨淡荒芜吗?因为同时被埋葬的贝壳与现在生活在海湾里的一样,我起初也倾向于认为,那时的植被可能也跟现在的差不多。但这会是一个错误的推测,因为其中一些贝壳也生活在富饶的巴西海岸;并且一般而言,不能用海洋生物的特征来推测陆地生物是什么样。然而,基于以下几点理由,我认为,我们不能根据布兰卡港附近的平原上曾经生活过这许多巨型四足动物的事实,得出这里曾经有过繁茂植被的结论。我毫不怀疑,再往南一点、靠近内格罗河的长着零零落落的多棘树木的地区就足够养活许多大型四足动物了。
大型动物需要繁茂的植被才能生存是一个大家都信以为真的假设,每本书都这样讲,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这个错误已经影响到地质学家对世界古代史的很多关键问题的分析判断。这个偏见可能来自印度和东印度群岛,那里成群结队的大象、伟岸的森林和密不透风的丛林,在每个人的脑海中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读任何南部非洲地区的游记,我们都会发现,几乎每一页里,不是论及那里的沙漠风光,就是描述栖息在那里的大型动物之多。这在描绘非洲内陆各地区的众多版画里也很明显。小猎犬号停在开普敦(Cape Town)时,我深入内陆数日,至少对读到的那些内容有了足够的切身体会。
安德鲁·史密斯(Andrew Smith)博士带领的一个探险队最近成功地越过了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他告诉我说,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基本上算荒芜之地。在南部和东南部沿海有一些不错的森林,但除此之外,旅行者常常会连续几天在开阔的平原上跋涉,地面只覆盖有极贫瘠稀疏的植被。很难把土地的相对肥沃程度这个概念表达清楚,但可以肯定地说,在任何时刻
 英国土地上植物的数量都比南部非洲内陆地区同等面积上的多出恐怕十倍都不止。这样描述或许使植被稀疏的概念更清晰:那里除了海岸一带,除了偶尔需要花不到半小时砍掉一些灌木外,牛车可以沿任何方向行驶。但放眼看看栖息在这些辽阔平原上的动物,我们却发现其数量庞大,而且个体的体积也很大。我们可以列出大象、三种犀牛(据史密斯博士所言,或许还有另外两种)、河马、长颈鹿、块头与成年公牛一样大的非洲野牛、小不了太多的伊兰羚羊(elan)、两种斑马、斑驴(quaccha)、两种角马(gnus),以及好几种比后面这几种更大的羚羊。或曰,虽然动物种类繁多,每一种的数目却很少。但有史密斯博士的热心帮助,我能证明事实恰恰相反。他告诉我,在纬度24度的地方,他跟着牛车走了一天,并且没有特意离开车往两边跑很远,就看见了大约一百到一百五十头三种不同的犀牛。同一天,他还看见几群长颈鹿,加起来也近百头。他知道那个地区还有大象,虽然当天没看见。离开头天晚上宿营的地方走了一个小时多一点,他那帮人在同一个地点就杀了八头河马,看见的更多。同一条河里还有鳄鱼。当然,能看到这么多的大动物聚集在一处,也是很不寻常的一天了,但这显然证明它们数目众多。史密斯博士描述那一天经过的地区有“稀稀拉拉的草和灌木丛覆盖地面,约有四英尺高;更稀稀拉拉的,还有一些含羞草树”。牛车几乎沿直线行驶,没有阻碍。
英国土地上植物的数量都比南部非洲内陆地区同等面积上的多出恐怕十倍都不止。这样描述或许使植被稀疏的概念更清晰:那里除了海岸一带,除了偶尔需要花不到半小时砍掉一些灌木外,牛车可以沿任何方向行驶。但放眼看看栖息在这些辽阔平原上的动物,我们却发现其数量庞大,而且个体的体积也很大。我们可以列出大象、三种犀牛(据史密斯博士所言,或许还有另外两种)、河马、长颈鹿、块头与成年公牛一样大的非洲野牛、小不了太多的伊兰羚羊(elan)、两种斑马、斑驴(quaccha)、两种角马(gnus),以及好几种比后面这几种更大的羚羊。或曰,虽然动物种类繁多,每一种的数目却很少。但有史密斯博士的热心帮助,我能证明事实恰恰相反。他告诉我,在纬度24度的地方,他跟着牛车走了一天,并且没有特意离开车往两边跑很远,就看见了大约一百到一百五十头三种不同的犀牛。同一天,他还看见几群长颈鹿,加起来也近百头。他知道那个地区还有大象,虽然当天没看见。离开头天晚上宿营的地方走了一个小时多一点,他那帮人在同一个地点就杀了八头河马,看见的更多。同一条河里还有鳄鱼。当然,能看到这么多的大动物聚集在一处,也是很不寻常的一天了,但这显然证明它们数目众多。史密斯博士描述那一天经过的地区有“稀稀拉拉的草和灌木丛覆盖地面,约有四英尺高;更稀稀拉拉的,还有一些含羞草树”。牛车几乎沿直线行驶,没有阻碍。
除了这些大型动物,对开普敦的自然史略知一二的人都读到过,那里的羚羊群规模之大只有候鸟群能比。大量的狮子、豹子和鬣狗,众多的猛禽,清清楚楚地表明小型四足动物也多不胜数。有天晚上,在史密斯博士的营地周围窜来窜去的狮子竟有七头之多。这位精明能干的博物学家跟我感叹道,日日夜夜发生在南部非洲的弱肉强食该是多么的惨烈!我承认食物这么少的地区却可以供养这么多的动物确实让人惊讶。较大的四足动物无疑可以在更大的地盘里觅食,而且它们的食物主要是树木下的草丛,营养密度可能更高。史密斯博士还告诉我,那里的植被长得极快,刚被吃掉,新的又长出来了。但有一点毫无疑问,我们恐怕把大型四足动物所需食物的量估计得过高了。别忘了,骆驼块头也不小,却是沙漠的象征。

威尔士王子与大象在泰瑞合影,印度,1875年左右
有大型四足动物的地方必然有茂盛植被的观点尤显突兀,因为反之也不然。伯切尔(Burchell)先生跟我说,他进入巴西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南部非洲相比,南美地区植被旺盛壮美,却没有任何大型四足动物。他在游记里
 提到,列出每个地区前几种最大的食草四足动物,比较其总重量(如果有足够的数据的话)应该很有启发。比如一边是大象
提到,列出每个地区前几种最大的食草四足动物,比较其总重量(如果有足够的数据的话)应该很有启发。比如一边是大象
 、河马、长颈鹿、非洲野牛、伊兰羚羊及至少三种甚至可能有五种犀牛,美洲这一边则是两种貘(tapir)、原驼、三种鹿、小羊驼(vicuna)、西貒(peccari)和水豚(我们必须再加上猴子才能凑足十种),然后让它们并排站着。恐怕难以想出比这更不成比例的两组动物了。有了上述事实,我们只能得出与预先假定
、河马、长颈鹿、非洲野牛、伊兰羚羊及至少三种甚至可能有五种犀牛,美洲这一边则是两种貘(tapir)、原驼、三种鹿、小羊驼(vicuna)、西貒(peccari)和水豚(我们必须再加上猴子才能凑足十种),然后让它们并排站着。恐怕难以想出比这更不成比例的两组动物了。有了上述事实,我们只能得出与预先假定
 相反的结论,即哺乳类动物体型的大小与它们生活地区的植被的数量之间并没有密切的关系。
相反的结论,即哺乳类动物体型的大小与它们生活地区的植被的数量之间并没有密切的关系。
言及大型四足动物的数量,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与南部非洲相提并论。根据前面提到的证据,说该地区极端沙漠化也不会有争议。至于欧洲地区,我们必须回溯到第三纪才能找到类似于现在好望角的哺乳类动物繁多的情形。我们笃信第三纪的时候它们数量惊人,主要是因为在一些地方发现了大量的大型哺乳动物的遗骸,但那是漫长岁月积累的结果,它们不可能比目前的南部非洲的动物数量更多。如果要猜测那些纪元的植被状况的话,我们至少也得同意繁茂植被不是必然的,因为在好望角看到的并非如此。
我们知道
 ,在北美的最边远之处,比大地终年冻结深达几英尺的地方再往北几个纬度的地方,依然覆盖着高大的森林。与之类似,在西伯利亚北纬64度的地区
,在北美的最边远之处,比大地终年冻结深达几英尺的地方再往北几个纬度的地方,依然覆盖着高大的森林。与之类似,在西伯利亚北纬64度的地区
 ,平均气温低于冰点,大地完全冻结,以至于掩埋的动物尸体可以保存完好,那里仍有桦木、冷杉、白杨和落叶松的树林。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必须同意,仅就植被的“数量”而言,在北部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第三纪的大型四足动物可能就生活在其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在这里我不是指供养它们的植被种类,因为既然证据表明这些地方经历了物理变化,而且这些动物已经灭绝,我们可以认定,植物的种类也同样地发生了改变。
,平均气温低于冰点,大地完全冻结,以至于掩埋的动物尸体可以保存完好,那里仍有桦木、冷杉、白杨和落叶松的树林。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必须同意,仅就植被的“数量”而言,在北部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第三纪的大型四足动物可能就生活在其尸体被发现的地点。在这里我不是指供养它们的植被种类,因为既然证据表明这些地方经历了物理变化,而且这些动物已经灭绝,我们可以认定,植物的种类也同样地发生了改变。
容我补充几句话,这些讨论与西伯利亚冰冻的大地里有保存完好的动物尸体直接相关。笃信繁茂如热带地区一般的植被才能支持大型动物的信念,与经年冰冻的地方有动物生活的事实不可调和,人们才臆想出了气候突然变化或各种毁灭性的天灾理论来解释这个动物被冰葬的现象。我当然不会断言,自从这些如今长眠于冰冻中的动物生活的时代起,气候就未曾改变过。目前我只想指出,仅就食物的“数量”而言,古犀牛完全可能就在现今的西伯利亚中部的干草原上(那时北部地区可能还在海里)漫游,如同今天的犀牛和大象生活在南部非洲干旱的台地高原上一般。
现在讲一讲北巴塔哥尼亚荒原上一些比较有趣的常见鸟的习性。先说最大的南美鸵鸟。鸵鸟的一般习性众所周知。它们以吃植物的根或草为生,但在布兰卡港,我曾多次看到它们三四个一群站在退潮后干涸的淤泥滩里。高乔人说,它们是在找小鱼吃。虽然鸵鸟很害羞、谨慎、好独处,腿长跑得也快,但印第安人和高乔人用流星索捉它们毫不费劲。几个人骑着马拉弧线一围,它就惊慌失措,不知道往哪个方向逃。鸵鸟喜欢迎风跑,但全速起飞时则会马上张开翅膀,像船一样鼓帆而行。一个晴朗炎热的日子,我看到几只鸵鸟钻进高大的灯芯草丛里很隐蔽地蹲下来,直到我离它们已经很近了。一般人不知道,鸵鸟会水。金先生(M. King)告诉我,在圣布拉斯湾(San Blas)和巴塔哥尼亚的巴尔德斯港(Port Valdes),他看到过鸵鸟在岛屿之间来回游。如果被追急了,它们会跑进水里,但没受惊时自己也会涉水,能游大约二百码。游泳时,大部分身体都在水下,脖子略往前伸,慢悠悠的。有两次我看到一些鸵鸟横渡圣克鲁斯河(Santa Cruz)。河有四百码宽,水流湍急。斯特尔特(Sturt)船长
 在澳大利亚顺马兰比吉河(Murrumbidgee)而下时,也见过两只鸸鹋(emu),即澳洲鸵鸟,在游水。
在澳大利亚顺马兰比吉河(Murrumbidgee)而下时,也见过两只鸸鹋(emu),即澳洲鸵鸟,在游水。
本地人离得很远就能分出雌雄鸵鸟。雄鸟个头更大,颜色更深
 ,头也大一些。有的鸵鸟,我猜是雄的,会发出奇特低沉的嘶嘶声。站在沙丘中第一次听见时,我还以为是野兽叫,因为根据声音难以判断叫声从何来、有多远。9、10月的布兰卡港附近,到处都是鸵鸟蛋,多极了。有的单个落在地上,这些不会被孵化,西班牙人管它们叫“乌阿乔”(huachos)。有的堆在刨得很浅的坑里,那就是鸟窝了。我一共找到过四个鸟窝,三个窝里每个都有二十二枚蛋,第四个窝里有二十七枚。有一天骑着马,我一共捡了六十四枚蛋,两个窝里找到四十四枚,其余二十枚是散落在地上的乌阿乔。高乔人众口一词地说(也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说法),都是雄鸟负责孵蛋,而且小鸟孵出来后,雄鸟还会照顾一段时间。雄鸟抱窝时伏在地上很低,我有次骑着马差点踩翻一只。据说在这种时候,它们很凶猛,甚至危险,还攻击过马背上的人,用腿踢他,往他身上扑。告诉我这些信息的人还指着一个老头,说亲眼看见他被鸵鸟追得惊慌逃窜。伯切尔在他的非洲游记里提到,“杀了一只雄鸵鸟,羽毛很脏,霍屯督人说是一只正在孵蛋的鸟”。据我所知,动物园里的澳洲鸵鸟
,头也大一些。有的鸵鸟,我猜是雄的,会发出奇特低沉的嘶嘶声。站在沙丘中第一次听见时,我还以为是野兽叫,因为根据声音难以判断叫声从何来、有多远。9、10月的布兰卡港附近,到处都是鸵鸟蛋,多极了。有的单个落在地上,这些不会被孵化,西班牙人管它们叫“乌阿乔”(huachos)。有的堆在刨得很浅的坑里,那就是鸟窝了。我一共找到过四个鸟窝,三个窝里每个都有二十二枚蛋,第四个窝里有二十七枚。有一天骑着马,我一共捡了六十四枚蛋,两个窝里找到四十四枚,其余二十枚是散落在地上的乌阿乔。高乔人众口一词地说(也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说法),都是雄鸟负责孵蛋,而且小鸟孵出来后,雄鸟还会照顾一段时间。雄鸟抱窝时伏在地上很低,我有次骑着马差点踩翻一只。据说在这种时候,它们很凶猛,甚至危险,还攻击过马背上的人,用腿踢他,往他身上扑。告诉我这些信息的人还指着一个老头,说亲眼看见他被鸵鸟追得惊慌逃窜。伯切尔在他的非洲游记里提到,“杀了一只雄鸵鸟,羽毛很脏,霍屯督人说是一只正在孵蛋的鸟”。据我所知,动物园里的澳洲鸵鸟
 也是雄的抱窝,看来是这一科鸟的共同习性。
也是雄的抱窝,看来是这一科鸟的共同习性。

大鸵鸟( Rhea americana )的成年鸟与幼鸟

大鸵鸟
高乔人众口一词地说,总是几只雌鸟把蛋下在同一个窝里。他们告诉我,亲眼看见过大白天里四五只雌鸟一只接一只去同一个窝。我还可以补充说明,据信在非洲也是两只以上的雌鸟同窝
 。这种习性初看让人觉得奇怪,但我想可以有很简单的解释。鸟窝里的蛋从二十到四十枚不止,甚至五十枚。据阿扎拉说,有时还多到七八十枚。无论是根据一个地区如此大量的鸟蛋与雌雄鸟的比例,还是考虑雌鸟卵巢的生殖能力,一只鸟在繁殖季节生这么多蛋都是完全可能的,只是所需的时间一定会拖得很长。根据阿扎拉的记载
。这种习性初看让人觉得奇怪,但我想可以有很简单的解释。鸟窝里的蛋从二十到四十枚不止,甚至五十枚。据阿扎拉说,有时还多到七八十枚。无论是根据一个地区如此大量的鸟蛋与雌雄鸟的比例,还是考虑雌鸟卵巢的生殖能力,一只鸟在繁殖季节生这么多蛋都是完全可能的,只是所需的时间一定会拖得很长。根据阿扎拉的记载
 ,饲养的一只雌鸟一共下了十七枚蛋,但每隔三天下一枚。如果雌鸟必须亲自孵蛋的话,那恐怕最后一枚蛋还没下,第一枚已经坏了。但如果每只雌鸟把每枚蛋都下在不同的鸟窝里,几只雌鸟如法炮制(据称事实如此),那么同一个窝里的蛋就几乎同龄。如果平均而言,每个窝里的鸟蛋不多于每只雌鸟一个季节下的蛋的总数,那么鸟巢数目就应该与雌鸟数目一样多,那么每个雄鸟孵的蛋也是它份内的数,那是在雌鸟还未下完蛋,不能坐下来孵蛋期间
,饲养的一只雌鸟一共下了十七枚蛋,但每隔三天下一枚。如果雌鸟必须亲自孵蛋的话,那恐怕最后一枚蛋还没下,第一枚已经坏了。但如果每只雌鸟把每枚蛋都下在不同的鸟窝里,几只雌鸟如法炮制(据称事实如此),那么同一个窝里的蛋就几乎同龄。如果平均而言,每个窝里的鸟蛋不多于每只雌鸟一个季节下的蛋的总数,那么鸟巢数目就应该与雌鸟数目一样多,那么每个雄鸟孵的蛋也是它份内的数,那是在雌鸟还未下完蛋,不能坐下来孵蛋期间
 。我前面还说过乌阿乔(被遗弃的蛋)很多,我一天就捡了二十枚。浪费这么大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几只雌鸟结成伴儿并刚好有一只雄鸟准备抱窝也非易事。显然,至少先得有两只雌鸟做伴,否则在这么宽阔的平原上,鸟蛋会完全分散,彼此相隔过远,雄鸟不太可能去一一捡进窝里。有些学者认为,散落的蛋是喂幼鸟用的。这个理论完全不符合美洲的情况:很多乌阿乔已烂掉了,外表却完好无损。
。我前面还说过乌阿乔(被遗弃的蛋)很多,我一天就捡了二十枚。浪费这么大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几只雌鸟结成伴儿并刚好有一只雄鸟准备抱窝也非易事。显然,至少先得有两只雌鸟做伴,否则在这么宽阔的平原上,鸟蛋会完全分散,彼此相隔过远,雄鸟不太可能去一一捡进窝里。有些学者认为,散落的蛋是喂幼鸟用的。这个理论完全不符合美洲的情况:很多乌阿乔已烂掉了,外表却完好无损。

小鸵鸟(即达尔文驼鸟, Rhea darwinii )
在北巴塔哥尼亚的内格罗河,我常常听高乔人说起一种非常罕见的鸟,称为小鸵鸟( Avestruz Petise )。他们将其形容为比这里常见的普通鸵鸟小一些,但大体上非常相似。据说它的羽毛色更深,上面有斑点,腿短一些,绒毛长得更靠近脚面。用流星索抓也更容易一些。两种都见过的人言之凿凿地说从很远的距离就能分辨出来。见过小鸵鸟蛋的人似乎更多,常有人很惊讶地评论说,怎么比大鸵鸟的蛋小不了多少呢?其形状稍有不同,并带一点淡蓝色。小鸵鸟在内格罗河两岸的平原上非常稀少,但再往南纬1.5度左右,就多起来了。在巴塔哥尼亚的盼望港(南纬48度)时,马腾先生射杀了一只鸵鸟。我当时不可思议地完全把小鸵鸟这档子事忘了,以为就是一只没完全长大的普通鸵鸟。煮熟吃光后,我才想起来。幸好我把它的头、颈、腿、翅膀、大羽毛和大部分鸟皮都保存下来了。把这些拼在一起做成的几乎完整的标本,现在陈列在动物学会的博物馆里。非常荣幸的是,古尔德先生描述这个新物种时,把它正式命名为达尔文鸵鸟。
在麦哲伦海峡的巴塔哥尼亚印第安人部落里,我们碰上个有一半印第安人血统的混血儿。他跟随这个部落多年了,但出生在北方某省。我问他是否听说过小鸵鸟,他回答说:“当然知道,南方地区没有别的鸵鸟。”他告诉我说,小鸵鸟的窝里蛋少得多,不超过十五枚,但他断言,也是两只以上的雌鸟把蛋生在同一个窝里。我们在圣克鲁斯看见几只小鸵鸟,但它们特别警觉。我觉得远在人能看清它们时,它们已经看见人了。往上游走没看见几只,但我们静静地顺流直下时,经常能看见两只一对,或四五只一群。据说,这种鸵鸟开始全速起飞时,不像北方鸵鸟那样马上展开双翅。小结一下观察到的情况,美洲鸵鸟(
Struthio rhea
)栖息在拉普拉塔河区域,直到内格罗河更南一点、南纬41度的地区,而达尔文鸵鸟(
Struthio Darwinii
)主要生活在巴塔哥尼亚的南部,内格罗河则属于中间地带。阿尔西德·多尔比尼先生
 在内格罗河时,为收集这种鸟费了很大的工夫,但运气不好未能成功。多勃利茨霍费尔(Dobrizhoffer)
在内格罗河时,为收集这种鸟费了很大的工夫,但运气不好未能成功。多勃利茨霍费尔(Dobrizhoffer)
 早就知道可能有两种鸵鸟,他说:“你要知道,不同地区的鸵鸟的大小和习性是不一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土库曼平原上的鸵鸟,个头较大,并有黑、白和灰色的羽毛;麦哲伦海峡周围的则更小,也更漂亮,因为它们的白羽毛末端是黑的,而黑羽毛的末端又是白的。”
早就知道可能有两种鸵鸟,他说:“你要知道,不同地区的鸵鸟的大小和习性是不一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土库曼平原上的鸵鸟,个头较大,并有黑、白和灰色的羽毛;麦哲伦海峡周围的则更小,也更漂亮,因为它们的白羽毛末端是黑的,而黑羽毛的末端又是白的。”

小籽鹬
这里常见一种非常特别的小鸟,叫小籽鹬( Tinochorus rumicivorus )。其生活习性和大致外观,几乎是一半像鹌鹑,一半像沙锥鸟,虽然鹌鹑和沙锥鸟全然不同。南美洲的整个南部地区,只要有荒芜的平原或开阔干枯的草地,就有小籽鹬。它们成对或成群地流连在几乎没有其他生物可以生存之荒凉地带。一旦你离得太近,它们就会伏下来,与地面浑然一体,难以注意到。吃草时它们双腿叉开,慢慢地走。小籽鹬常在道路的灰尘和沙土里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它们日复一日地去同一个地方,会像山鹑一样结群而飞。根据下面这些特点,它的利于消化植物的强有力的砂囊、拱形喙、肉嘟嘟的鼻孔、短腿及脚的形状等,小籽鹬都显出与鹌鹑很近的亲缘关系。可一旦飞起来,它的整个外形就变了,长而尖的翅膀,跟鸡形目的区别极大,再加上不规则的飞行动作,起飞那一刻发出的哀叫声,都让人想起沙锥鸟。小猎犬号的猎人们一致地把它称为短喙沙锥。其骨骼显示它确实与沙锥属,或者说涉禽科的鸟类更接近。
这个小籽鹬与其他一些南美鸟类也是近亲。阿塔奇属(
Attagis
)的两种鸟的习性几乎方方面面都跟雷鸟(
Ptarmigans
)相同,其中一种生活在火地岛的森林的树线以上,而另一种在智利中部的科迪勒拉山脉接近雪线的地方。另一个近缘属的白鞘嘴鸥(
Chionis alba
),则是南极地区的居民,以海草和潮汐岩上的贝壳为生。由于不为人知的习性,虽然趾间没有脚蹼,白鞘嘴鸥却经常出现在远离陆地的海上
 。这个小小的鸟科,与其他鸟科的关系错综复杂,目前只是让致力于分类学的博物学家头疼,但最终可能有助于揭示造就古往今来所有生物的宏伟蓝图。
。这个小小的鸟科,与其他鸟科的关系错综复杂,目前只是让致力于分类学的博物学家头疼,但最终可能有助于揭示造就古往今来所有生物的宏伟蓝图。
灶鸟属( Furnarius )的几种鸟都很小。它们栖居在开阔干旱的地区,在地面上觅食。它们与欧洲所有的鸟在身体结构上都很不一样。鸟类学家一般把它们归在旋木雀科下,但它们与这科的其他鸟的习性完全不同。最广为人知的是拉普拉塔的普通灶鸟,西班牙人管它叫“卡萨拉”(Casara),筑巢鸟的意思。它因之而得名的鸟巢总是建在最显眼的地方:柱子顶、光秃的岩石或仙人掌上。鸟巢由泥土和稻草碎片筑成,砌得厚而结实。其形状酷似烤箱,或压扁的蜂窝。鸟巢有一个大的拱形入口,进门就是一个几乎延伸到巢顶的隔墙,从而形成一个通道或前厅,通向后面真正的鸟窝。
另一种较小的鸟( F. cunicularius ),跟灶鸟很像,羽毛也略带红色,会一声接一声地哀叫,跑起来也一蹦一跳的。因此,西班牙人称它为“卡萨丽达”(Casarita),即小筑巢鸟,其实它做的鸟巢完全不同。卡萨丽达把鸟巢建在一个狭窄的圆柱形的地洞尽头。据说地洞可以往水平方向延伸到六英尺那么长。几个本地人告诉我,他们还是小男孩时喜欢掏鸟窝,但很少能成功地挖到地洞的尽头。小灶鸟总是选路边或溪流边有坚硬沙土的低岸处做巢。在布兰卡港一带,环绕房子的围墙是硬泥砌的。我注意到我住的这家院墙上有十几个洞。问主人这是怎么回事,他愤愤地抱怨,说是卡萨丽达干的好事。后来我还真看见它们忙乎。奇怪的是,这些鸟似乎毫无厚度的概念,虽然它们在矮墙上飞来飞去,却徒劳地在墙上凿洞,以为这是做窝很理想的堤坝。毫无疑问,每只鸟看见日光从打通的洞的另一面射入时,都大吃一惊。
我已经提过了几乎所有这里常见的哺乳类。有三种犰狳,即小犰狳( Dasypus minutus ,西班牙名叫 Pichy )、毛犰狳( D. villosus ,西班牙名叫 Peludo )及懒犰狳( Apar )。小犰狳与另外两种相比,分布范围更大,遍及再往南10度的地区。第四种七带犰狳( Mulita ),则主要在布兰卡港以北。这些犰狳都有类似的习性,除了毛犰狳昼伏夜出以外,其他的都是大白天在开阔的平原上出没,以甲虫、幼虫、植物根甚至小蛇为食。懒犰狳也常被称作三带犰狳( Mataco ),只有三片可移动的鳞甲,其他交织的鳞片几乎完全固定不能动。它可以像英国土鳖那样把自己裹成一个圆球,以免遭受狗的攻击。狗不能把它一口咬住,试图咬一边时,球就滚跑了。三带犰狳平滑坚硬的鳞甲比刺猬的尖刺利于防守。小犰狳喜欢非常干燥的地方。沿海的沙丘地带,几个月没一口水喝,是其最钟爱的度假村。为了逃避注意,它常常紧紧地伏在地面上。在布兰卡港附近骑行一天,往往能看见好几个。一旦看见并想抓它的话,几乎得翻身下马,因为它在疏松的地上挖洞的速度极快,等你姗姗跳下马来时,它的后半身已经消失了。人们似乎都不忍心杀死这么可爱的小动物,有个高乔人边在它背上磨刀边嘟囔:“真老实啊!”

犰狳的骨骼

三带犰狳(懒犰狳)
这里有很多爬行类动物。有一种巨蝮蛇( Trigonocephalus ),也叫比布龙( Cophias [2] ),根据其尖牙里的毒槽尺寸,可以想见毒汁肯定致命。但居维叶跟其他博物学家的意见相左,把它归入响尾蛇的一个亚属,介于响尾蛇与蝮蛇之间。我观察到一个很奇怪但有启发性的事实,或可为他的这个观点提供佐证。我发现生物的每个特征,即使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跟结构没有太大关系的特征,似乎都会发生些微的变异。这种蛇的尾巴末端是尖的,最后一节稍微膨大一些。蛇滑行时不断振动最末端的那一寸尾巴,后者拍打到干草或灌木丛上发出连续的响声,六英尺外也能清楚地听见。一旦蛇被刺激或受惊,它的尾巴就会抖动,这时尾端会振动得飞快。只要身体维持在受惊状态,它就会习惯性地振动不止。因此巨蝮蛇有蝮蛇一样的身体结构,却有响尾蛇的习性,只是它制造声响的机理更简单。这种蛇的面目表情狰狞丑恶。铜色斑驳的虹膜上,瞳孔眯成一垂直狭缝,下巴底部很宽,鼻子呈三角形。我还没见过比它更丑恶的东西,大概有的吸血蝙蝠除外。我想令人厌恶的原因源于它的这些脸部特征的相对位置,多少与人脸各个部位的位置成比例,我们因此有了衡量厌恶感的标准。
至于无尾的两栖动物,我只发现一种小蟾蜍( Phryniscus nigrican ),它的肤色非常奇异。想象一下,先把它浸在最黑的墨水里,捞起来晾干后,再让它在刚用最亮丽的朱红色刷过的宽板上爬过去,使其脚底和腹部有的地方蘸上红色,就知道小蟾蜍的大致外观了。如果它是一个尚未命名的物种的话,应该叫它毒蟆( Diabolicus ),因为它就像那个往夏娃的耳朵里灌输异端邪说的家伙。它不像别的癞蛤蟆那样在潮湿阴暗的地方昼伏夜出,而是大白天里在一滴水都找不到的干旱沙丘或平原上爬来爬去。它大概是靠皮肤吸收露水来保持湿润的,已知这些爬行动物的皮肤具有很强的吸收水分的能力。我在马尔多纳多的一个跟布兰卡港几乎一样干燥的地方抓到了一只。我把它放到一个水池里,想让它好好享受一番。结果这个小家伙根本不会游泳,我不帮一把的话,转眼就要被淹死了。蜥蜴有许多种,但只有一种( Proctotretus multimaculatus )的习性值得一提。它生活在海岸边光秃秃的沙滩上,皮肤斑驳,褐色的鳞片上有白、橙红和暗蓝色的斑点,趴在地上很难被注意到。受到惊吓时,它会装死,腿一蹬,眼睛一闭,全身松塌下来。如果再逗它,它会极快地把自己埋进松软的沙土中。这种蜥蜴身体扁平,腿短跑不快。
在这里简单说几句南美洲这片地区动物的冬眠情况。我们于1832年9月7日第一次来到布兰卡港时,还以为大自然没有给这个多沙干燥的地方赐予生灵。后来从土里挖出了几种昆虫、大蜘蛛和蜥蜴,它们都处于半昏迷状态。9月15日,一些动物开始出现,到了18日(离春分差三天),万物纷至沓来,春天到了。平原上鲜花盛开,有粉红色的木酢浆草、野豌豆、月见草和天竺葵。鸟儿也开始下蛋。众多的金龟子类( Lamellicorn )和异跗节类( Heteromerous )的昆虫,从容地爬来爬去,后者深度雕纹的身体引人注目。蜥蜴亚科是沙质土壤的常住居民,无处不在、四处冲撞。大地仍处于休眠状态的头十一天内,小猎犬号上的观察站每两个小时测一次的平均气温为51度,一天中温度很少超过55度;在随后万物复苏的十一天中平均为58度,中午在60到70度之间。就是说平均气温只增加了7度,最高气温涨幅略大一些,就足以唤醒生命功能。在此之前,从蒙得维的亚启航前,从7月26日至8月19日之间的二十三天内,根据276个数据点算出的平均气温为58.4度;最热的一天平均气温65.5度,最冷的一天46度;温度降到过41.5度,偶尔中午可以上升到69或70度。然而即使这么热,几乎所有的甲虫、好几个属的蜘蛛、蜗牛和陆地贝类以及蟾蜍和蜥蜴都躺在石头下滞伏不动。但我们已经看到,再往南4纬度,来到气候稍微寒冷一些的布兰卡港,气温升到类似的平均温度时(白天的最高温度甚至更低),几乎所有的生物都苏醒了。这说明冬眠动物所需要的刺激是由每个地区的通常气候,而不是绝对温度决定的。众所周知,热带地区内的动物冬眠,或更恰当地说夏眠,不是由温度,而是由旱季决定的。在里约热内卢附近,我最初很惊讶地看到,一些小洼地有水后没过几天,就被无数已经是成虫的贝壳和甲虫填满了,说明它们此前肯定是处于休眠状态。洪堡曾提到一个奇怪的事件,一家客栈建在已经变硬的泥地上,却意外发现下面埋了一条小鳄鱼。他补充说:“印第安人经常会发现巨大的蟒蛇,他们称之为水蛇(Uji),处在昏睡状态。想唤醒它们的话,必须用水去激怒或把它们淋湿。”

《动物美图博物馆》里的一页(1850年左右),画的是各种蛇,包括巨蝮蛇
最后再提一种动物:植虫类(zoophyte)的海鳃(sea-pen),我相信学名是巴塔哥尼亚海箸(
Virgularia Patagonica
)。它由细而直的肉质茎构成,茎两侧是交替成排的水螅体,茎内是有弹性的石质轴。轴的长度八英寸到两英尺不等。茎的一端如齐齐断掉一般,而另一端是一个肉质的蠕虫状突起。支持茎的石质轴靠近这末端时变成一只小管,里面装满颗粒状物质。退潮时可以看见成百上千个这样的海箸,从泥滩里伸出几英寸长,断茎那端向上,如同谷地收割后的残茬。碰一下或拉一下,它就会使劲一缩,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肯定是靠弹性很强的中轴埋在地里的末端收缩造成的,那里本来就有点弯曲。我相信海箸也是靠这个弹力从泥里再钻出来。一片片海螅体,虽然彼此紧密相连,却都有自己的口、身体和触手。一个大的海箸标本恐怕有上千个海螅体,但看起来它们总是步调一致。海螅体也有一个中心轴,与微小的循环系统相通,但卵子产自一个单独的器官,独立于水螅体的个体
 。让人不由得要问,在这里“个体”指的是什么?搞清楚老航海家那些稀奇古怪故事的来源是很有趣的事。我毫不怀疑这种海箸的习性可以提供一个解释。兰开斯特(Lancaster)船长记述他在1601年的那次航海中
。让人不由得要问,在这里“个体”指的是什么?搞清楚老航海家那些稀奇古怪故事的来源是很有趣的事。我毫不怀疑这种海箸的习性可以提供一个解释。兰开斯特(Lancaster)船长记述他在1601年的那次航海中
 ,在东印度群岛的松布雷罗岛(Sombrero)沙滩上,“发现了一种长得像树的小枝,正要拔,它却一下子就缩回地面。再不使劲抓住的话,就陷入地下了。拔起来后,却发现它的根竟然是个大蠕虫。树开始长时,蠕虫就变小,直到完全转化成树。根植于地,枝繁叶茂。这是在我所有的旅行中看到的最神奇的事。另外,如果把树拔出来,趁着新鲜,把树叶和树皮都剥掉晒干后,它就变成坚硬的石头,像白珊瑚一般。如此,该蠕虫可以转化成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采集了许多带回家”。
,在东印度群岛的松布雷罗岛(Sombrero)沙滩上,“发现了一种长得像树的小枝,正要拔,它却一下子就缩回地面。再不使劲抓住的话,就陷入地下了。拔起来后,却发现它的根竟然是个大蠕虫。树开始长时,蠕虫就变小,直到完全转化成树。根植于地,枝繁叶茂。这是在我所有的旅行中看到的最神奇的事。另外,如果把树拔出来,趁着新鲜,把树叶和树皮都剥掉晒干后,它就变成坚硬的石头,像白珊瑚一般。如此,该蠕虫可以转化成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采集了许多带回家”。
我在布兰卡港等候小猎犬号期间,这个地方一直处于骚动状态,关于罗萨斯军队和未开化的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和胜利的流言不断。有一天,消息传来,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哨所的小队士兵全部被杀了。第二天,米兰达军官指挥的三百人从科罗拉多河到达这里。相当一部分士兵是“归顺的”印第安人,来自酋长贝南蒂奥(Bernantio)的部落。他们在这里待了一晚上。难以想象有比他们的营地更疯狂野蛮的了。有的人喝得烂醉如泥,还有人直接喝为晚餐杀的牛喷出的热血。大醉后又吐,满身都是脏物和淤血。正是:
酒足饭饱困,
独眼大力神;
体长窑洞小,
秽物梦里喷。

第二天早上,他们前往凶杀现场,受命跟踪“拉斯特罗”(足迹),哪怕一直追到智利。我们随后听说印第安人已经逃进了潘帕斯大草原,不知为什么足迹在那里也消失了。这些人只要看一眼拉斯特罗,就能知晓一切。比如研究一下千匹马走过的轨迹,他们很快就会知道多少马有人骑,因为这些马的步子会小一些;足迹的深浅可确定多少马载有货物;脚步的不规则可以判断它们有多累;用炊方式决定是否在匆忙赶路;足迹的整体状态则用来估计人们走了有多久。十天或两周以内的拉斯特罗都算新鲜足迹,可以追杀。我们还听说,米兰达从文塔那山脉的西端一直杀到了内格罗河以北七十哩格的乔列切耳(Cholechel)岛。这可是两三百英里长的完全没有人烟的地区。世界上还有什么军队能如此独立自足?太阳导航,马肉为食,马鞍当床,只要可以找到一点点水喝,这些人能跑到世界尽头。
几天之后,我又碰到这帮强盗般的士兵的另一支部队出发去征讨小盐田的印第安人部落,他们被一个沦为囚犯的酋长出卖了。传达远征命令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西班牙人。他给我回顾了他参加的上一次战斗。几个印第安人囚犯供出了一个居住在科罗拉多河北部的部落所在。两百名士兵被派遣到那里。那个印第安人部落当时正好在迁移,马蹄掀起的尘土把自己暴露了。那里是山区野径,在内陆深处,已经看得见科迪勒拉山脉了。男人、女人和孩子,加起来大约有一百一十人,每个男人都被砍杀,其余几乎全部被杀或被抓。印第安人现在非常惧怕,不再联合反抗,而是丢妻弃子,四处逃亡。但如果被追杀,则会像野兽一样,敌众我寡也要拼死到最后一刻。一个垂死的印第安人用牙咬住了对手的大拇指,任由自己的眼珠被抠出来,也不松口。另外一个受了伤,佯装死去,却已经把刀准备好,伺机给敌人致命的最后一击。给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说,他追赶的一个印第安人,哭着求饶的同时,却暗中从腰间取下流星索,意欲抡起来袭击追他的人。“但我先用刀把他砍翻在地,然后跳下马来,割断了他的喉咙。”这是一幅多么黑暗的画面,更骇人听闻但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所有二十岁以上的女人也全部被冷血屠杀!我大叫,这简直太不人道了,他回答说:“为什么?还能怎么办?她们会繁殖啊!”
这里的每个人都笃信这是最正义的战争,就因为杀的是野蛮人。谁敢相信,这个年代,在一个基督教的文明国家会发生如此暴行?印第安人的孩子们免遭屠杀,或被卖掉或送给人家当仆人,其实就是奴隶,只要主人能骗他们相信自己是奴隶,能骗多久算多久。但我相信,对他们所受的待遇,已没有太多可抱怨之处了。
战斗中有四个人结伙逃跑,一人被打死,另外三人被活捉。他们原来是科迪勒拉山区联合起来御敌的一大批印第安人的信使或称大使。他们被送往的部落正要召开隆重的议会,马肉盛宴和战舞也准备就绪。那天早上,大使们本该返回科迪勒拉山脉了。他们长得非常精致,肤色很白,身高超过六英尺,都不到三十岁。显然这三名活下来的信使知道很多重要信息。他们被一字排开,前两人先被盘问,他们回答说:“我不知道。”于是一前一后被枪杀。第三个也说“我不知道”,又补充一句:“开枪吧。我是男人,可以去死!”为了家园的共同大业,他们拒绝吐露一个字!上面提到的那个酋长却不同,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命,交代了战斗计划和在科迪勒拉山脉会师的地点。据信,目前已有六七百印第安人汇聚一堂,到夏天人数会再增加一倍。本来还会派大使前往靠近布兰卡港的小盐田的部落,但我已经提到,他们也被同一个酋长背叛了。看来印第安人的联络范围是从科迪勒拉山脉一直到大西洋沿岸。

《南美印第安人》,儒勒·萨科·克勒沃作,19世纪
罗萨斯将军的计划是杀死所有的散兵游勇,再把其余人驱赶到同一个地点,等到夏季时,在智利人的协助下,一举歼灭。这个作战计划会连续三年执行。我猜选夏天作为主攻的季节是因为那时平原会缺水,印第安人只能在某些地区迁移。内格罗河以南地域宽阔人烟稀少,本来可以是理想的藏身之处,但罗萨斯早与那里的退卫尔彻人(Tehuelches)签了一个条约,他付重金令他们杀死每一个南渡的印第安人;如果违约,那么他们自己就会变成被剿灭的对象。这场战争主要是针对科迪勒拉山脉的印第安人,因为山脉东面的很多部落是与罗萨斯并肩作战的。但罗萨斯将军跟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勋爵一样,认定今天的朋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所以总是把印第安人盟友放在队伍的最前面,以削减他们的人数。离开南美后,我们听说这场种族灭绝战争已经彻底失败了。
同一场战斗中被抓获的女孩子里,有两个很漂亮的西班牙人,她们是很小的时候被印第安人抢走的,现在只会讲印第安土话。根据她们的描述,她们应该是从萨尔塔(Salta)来的,离这里直线距离有一千英里。这就给我们一个大致的概念:这些印第安人的活动空间非常广阔。尽管如此,我想,再过半个世纪,内格罗河北面不会有一个印第安土人残存。基督徒要杀死每一个印第安人,印第安人要杀死每一个基督徒,这么血腥的战争不可能持续。追寻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侵略者面前节节退让的历史让人悲哀。席尔德尔(Schirdel)
 指出,153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时,很多村庄都有两三千居民。即使在福尔克纳时代(1750年),印第安人仍能侵入卢克桑(Luxan)、阿烈科(Areco)和阿雷西费(Arrecife)一带。但现在他们已经被驱赶到萨拉多河(Salado)以外了。不仅是一个个部落被灭绝,苟活的印第安人也变得更野蛮:他们不再居住在大村庄里捕鱼或打猎,而是在辽阔的平原上流浪,无家无业。
指出,153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时,很多村庄都有两三千居民。即使在福尔克纳时代(1750年),印第安人仍能侵入卢克桑(Luxan)、阿烈科(Areco)和阿雷西费(Arrecife)一带。但现在他们已经被驱赶到萨拉多河(Salado)以外了。不仅是一个个部落被灭绝,苟活的印第安人也变得更野蛮:他们不再居住在大村庄里捕鱼或打猎,而是在辽阔的平原上流浪,无家无业。
我还听说了另一次冲突的一些细节。它早几个星期发生在乔列切耳岛。那里是大队马匹的必经之路,至为重要,因此曾是一个军团的指挥部。部队才刚到那里,就发现了一个部落的印第安人,杀了二三十个人。但酋长出逃的方式让人目瞪口呆。每个印第安人首领都有一两匹为紧急情况备用的马。酋长抱着小儿子跳上了其中一匹老白马,那马既无马鞍,也没有缰绳。为了躲避枪击,酋长用的是他那个地区独有的骑术,一只胳膊搂住马的脖子,一条腿搭在马背上。有人看见他这样挂在马的一边,还拍着马头跟它说话。追兵竭尽全力,指挥官就换了三次马,竟然追不上。老印第安人和儿子终于逃出虎口,重获自由。这是一幅多么壮美的图画:赤身露体、古铜般肤色的老人抱着小儿子,像马泽帕(Mazeppa)
 一样骑在白马上,把他的追兵们抛在远远的尘埃之中!
一样骑在白马上,把他的追兵们抛在远远的尘埃之中!
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士兵用一块火石引火,一眼认出那块火石是一个箭头的碎片。他告诉我,是在乔列切耳岛附近找到的,那里经常都能捡到这种箭。箭头长度比现在火地岛人使用的长一倍,在两到三英寸之间,用不透明的奶油色火石制作而成,但箭头尖和倒钩都被有意地折掉了。众所周知,潘帕斯草原的印第安人现在并不使用弓箭,除了东班达亚的一个小部落。但后者与潘帕斯草原的印第安人相离很远,而与那些居住在森林里步行的部落相邻。因此,这些箭头应该是旧时代印第安人的遗物,是在马被引进南美、造成生活栖居发生巨大变化之前
 。
。
[1] 这种理论最早出现在《小猎犬号航海之动物学》里,后见于欧文教授撰写的《论磨齿兽》( Memoir on Mylodon robustus )的论文中。
[2] 比布隆先生称之为 T. crepit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