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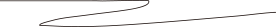
诚然,在人的自然感情里,和谁越近也就和谁越亲;和谁越亲,对谁承担的义务也就越大。我们不妨来看这样一个问题:《穀梁传·定公元年》记载周王室为天子办丧事,鲁国也在为本国国君办丧事,那么鲁国该不该派人去周王室吊唁呢?
依照惯常的理解,诸侯的丧事当然比不上天子的丧事重要,但实际情况是,周王室派了人来鲁国吊唁,鲁国却不派人去周王室吊唁。《穀梁传》给出的解释是,鲁国去世的国君是周天子的臣子,周王室自当派人吊唁;周天子是天下共主,鲁国当然应该由国君亲自前往吊唁,但鲁国的新君正在为上一任国君办理丧事,抽不开身,若派大夫去吊唁天子则属非礼之行。所以周王室派人来鲁国吊唁,鲁国却没人去吊唁周天子。
当独尊儒术之后,这种伦理精神写入立法,就出现了不少在现代人看来会觉得匪夷所思的法律条文。譬如《宋刑统·名例律》甚至规定,只要不涉及谋反罪,四世以上的亲属都可以合法地包庇罪犯,甚至向犯罪的亲属通风报信也属正当;亲属关系只有在小功以下时,才可以论包庇罪,但仍然享有罪减三等的优待。
这并不意味着对关系越远的祖先就越是恩轻义浅。《礼记·大传》谈及父与祖的关系,认为从“仁”的角度上看,从父母一代代追溯到祖先,对越远的祖先自然感情越浅;从“义”的角度上看,没有祖先就不会有后人,所以越远的祖先就越应该受到尊重。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相关问题都可以在这样的理论框架里得到妥善解决。徒弟不可以射师父,徒孙却可以射师公,当真是亲亲减杀的话,在祖父和父亲的冲突中又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这确曾是儒家一个大费争议的问题。东汉年间,贵族子弟丁鸿从小学习《尚书》,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父亲死后,他想把承袭爵位的资格让给弟弟,于是在留下一封信之后悄无声息地离家出走。丁鸿一路跑到东海,不想遇到了老同学鲍骏。为怕身份暴露,丁鸿便故意装作陌路人,但眼尖的鲍骏还是认出了他,继而责备道:“当年伯夷和季札弃位而走是因为遭逢乱世,而你仅仅因为兄弟之间的友爱之情便放弃了皇帝赐给你父亲的爵位继承资格,你这样做完全错了。《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

鲍骏的理论依据出自《公羊传·哀公三年》,当时卫灵公的太子蒯聩流亡国外,卫灵公想立庶子子南继位,但子南拒不接受;待卫灵公死后,卫国人便立了蒯聩的嫡长子辄,也就是卫灵公的嫡孙。
这个继承顺序合法与否呢?按照“殷道亲亲”的传统,太子蒯聩如果不在,同母弟应该接班;按照“周道尊尊”的传统,则是太子的嫡长子接班。所以辄的接班是符合“周道尊尊”的儒家义理的。
辄即位之后,亲生父亲蒯聩却准备回国夺权,于是问题就出现了:从正义性的角度上讲,辄要不要服从父亲的命令,让出君位?
其时孔子刚好就在卫国,《论语·述而》里的一段对话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冉有和子贡聊天,冉有问道:“你说咱们老师会支持卫君吗?”(冉有所谓的卫君,是指蒯聩的儿子辄,辄此时已经即位为君了。)子贡没有直接回答,很稳妥地说:“且等我去问问老师。”
子贡见了孔子,问了一个和时局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老师,您觉得伯夷和叔齐是怎么样的人?”孔子回答说:“他们是古代的贤人。”子贡又问:“那他们互相推让君位而双双逃跑之后可有什么怨悔之情吗?”孔子话:“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贡找到冉有,对他说:“咱们老师是不会支持卫君的。”(《论语·述而》)
子贡是借着伯夷和叔齐的问题探知了孔子对卫君辄的态度。伯夷和叔齐是兄弟相让,蒯聩与辄却是父子相争,孔子既然认同前者,自然就不会认同后者。

但是,孔子不支持卫君辄,难道会支持蒯聩吗?当然也不会,最大的可能就是孔子两边都不支持。但是,当下的问题是:作为父亲的蒯聩不会罢手不争,作为儿子的卫君辄也不会甘心让位,如果一定要解决其中的正义性问题,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实在是经学史上的一大辩题,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各执一词,前者认为卫君辄子拒父命,大逆不道,后者认为这时候拒绝父命是一点都不错的。

子拒父命,大逆不道,这个说法容易理解,那么公羊家的意见又有什么根据呢?
《公羊传》给出了这样一条原则:当父亲和祖父有了矛盾冲突,应该听从祖父的,因为这顺乎父子之道;当家事与王事发生了冲突,应该让王事优先,因为这顺乎尊卑之道。(《公羊传·哀公三年》)——此即前述鲍骏所援引的“《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的经典出处。
《穀梁传》也站在辄的一边,认为顺从父亲之命而拒绝祖父之命是不对的。(《穀梁传·哀公二年》)至此,儒家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阵营各执一词,谁也说不服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