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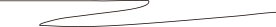
这样的道德观,看上去完全是穆勒式的功利主义,处处致力于一个更大的、更长远的“善”。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的建设尤其注重人之常情。很多时候,无论是礼还是法,只不过是将人之常情做了条文化的处理而已。
这种自动自发的人之常情当然不可能仅仅限于血缘关系,譬如《左传·襄公十四年》中,卫国孙文子叛乱,追杀卫献公。公孙丁为卫献公驾车跑在前面,尹公佗和庚公差在后面追。公孙丁曾是庚公差的箭术老师,庚公差又是尹公佗的箭术老师,也就是说,当下的状况是徒弟和徒孙在一道追击师父。眼看已经追到了弓箭的射程之内,射,还是不射?什么才是尹公佗和庚公差各自的符合道义的选择呢?
孟子讲过这段故事的另一个版本:郑国派出子濯孺子进犯卫国,卫国派出庾公之斯追击。这两人都是著名的神箭手,庾公之斯的箭术老师恰恰就是子濯孺子的学生。眼看已经追到了弓箭的射程之内,跑在前面的子濯孺子偏偏疾病发作,拿不了弓。在这个紧要关头,庾公之斯该不该射向自己的师公呢?
对于事情的结果,《左传》的后文是这样交代的:庚公差非常为难,说道:“射的话是背弃老师,不射的话自己回去会被论罪处死,射应该是合乎礼的吧?”
《左传》评论是非对错,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礼”,褒奖之辞常用“礼也”,批判之语常用“非礼也”。古人注重师道,尤其此刻要以老师教授的箭术射杀老师,可谓极大的道德重负。但师恩是私情,交战则是公义,若徇私情则无法向主君交代。一番权衡之下,庚公差还是选择了射,但他手下留情,发两箭射中车轭而回。
尹公佗说:“他是你的老师,和我的关系就远了。”于是回车再追,看来对师公不准备手下留情。公孙丁驾车载着卫献公跑在前面,见情形危殆,便把缰绳交给卫献公,回身向尹公佗发箭,一箭贯穿了尹公佗的手臂。
依儒家的伦理标准来看,尹公佗欲射师公也自有一番道理。儒家宣扬等差之爱,关系远则亲爱之情浅,责任与义务亦相应减少。所以庚公差不忍“欺师”,尹公佗却甘愿“灭祖”。但尹公佗的手段仍然显得决绝而不近人情,爱做道德训诫的《左传》作者便也乐得记载他追击不成却反被师公射中的窘态。
在孟子的版本里,故事被放到了两国相争的背景之下,两难之情便益发凸显出来。
子濯孺子疾病发作,拿不了弓,眼看就要被庾公之斯追上。但当他得知后面追来的是庾公之斯时,却庆幸自己这回能逃一死了。驾车者很不理解,问道:“庾公之斯是卫国著名的神箭手,您怎么反而说自己死不了呢?”子濯孺子答道:“庾公之斯的箭术是跟尹公之他学的,尹公之他的箭术则是跟我学的。我了解尹公之他,他是个正直的人,他挑的学生一定也是正直的人。”
不久,庾公之斯追了上来,当他看到以箭术闻名的子濯孺子并不拿弓,便没有急于射击,而是先去问明情况。在得知师公今天因为疾病而无法射箭之后,庾公之斯说道:“我的箭术是跟尹公之他学的,尹公之他的箭术是跟您学的,我不忍用您传下来的箭术伤害您。但今天的事情是国家的公事,我也不敢完全废弃。”说罢,庾公之斯抽出箭矢,在车轮上将箭镞敲掉,射了四箭就回去了。(《孟子·离娄下》第二十四章)
孟子的这番讲述,与回答桃应问题的用心一般无二。也就是说,大舜与庾公之斯在不同的两件事情当中有着同样的道德根据,不要说在国事与亲情的权衡中,就算是在国事与并无血缘纽带的“人情”的权衡中,后者都毋庸置疑地优先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