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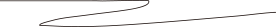
君子奉行中道,通晓过犹不及的道理,不会做出那种义愤感激的极端行为。
君子伦理源于周代,周人以礼立国,讲究规范和节制,要求君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总而言之,一切超乎常规的极端感情都是不好的。
平民社会一般不喜欢君子的礼仪风范,认为这纯属忸怩作态——为什么要用那么多规矩来束缚自己的天然情感呢?笑就该大声去笑,哭就该大声去哭,高兴时就该大呼小叫,难过时不妨呼朋唤友,尽情发泄。正如贵族社会所推崇的节制在平民社会看来纯属装腔作势一样,平民社会所推崇的真挚在贵族社会看来简直粗俗野蛮得如同野兽。所以当我们抛开贵族或平民的立场之后,就会发现极端的情感表达其实未必都蕴藏着恶意。
比如爱情,许多为爱疯狂而不顾一切的人在我们看来并不那么面目可憎,甚至值得同情和感动。晋人荀奉倩和妻子的感情极笃,有一次妻子患病,身体发热,体温总是降不下来,当时正值隆冬,荀奉倩情急之下,脱掉衣服,赤身跑到庭院里,让风雪冻冷自己的身体,再回来贴到妻子的身上给她降温。如是者多次,但这般深情并没有感动上天,妻子还是死了,荀奉倩也被折磨得病重不起,很快也随妻子而去。
这一悲剧在今天看来分外感人,而《世说新语》却将之记入“惑溺”一章,反而认为荀奉倩是违背正常人情的,如吸毒一般在一段不该投入太多感情的人际关系里一发不可收拾。深爱妻子的纳兰性德在悼亡诗词里常常引述荀奉倩这则掌故,诸如“不辞冰雪为卿热”云云。今日年轻人心目中的这个爱情楷模倘若生在晋代,一定也会被《世说新语》记入“惑溺”一章加以讥讽的。
但究竟怎样才算惑溺,倘若荀奉倩将“不辞冰雪为卿热”的行为用在父母身上,哪怕是用在继母身上,非但不会被讥为惑溺,反而会受到官府的表彰和世人的景仰。明清之际,理学大家张履祥撰《辨惑》,讲到有孝子不惜割自己的肝脏给继母治病,乡人为之嗟叹,前去探访的先后有上千人,或者敬拜,或者以钱米相赠。事情传到官府那里,官府给以隆重表彰。(《杨园先生全集》卷十九)
如果从人类的天然情感来讲,儿女对父母刳肝疗疾倒也是一往情深所致,儿女对继母显然没有这样的天伦之情。换言之,在一般意义上,一个人对继母的天然感情一定远远小于对恋人的天然感情,然而荀奉倩被讥为惑溺,为继母刳肝疗疾的孝子却受到景仰与表彰,显然其评价标准不是由人性天伦,而是由风俗道德所决定的,人们实在没理由断言后者之真而讥讽前者之伪。
再者,正因为有些牺牲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出来的,当某人真的做出来之后才显得格外感人。也许乐羊真的太爱他的国君或他的职责,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激情无时无刻不充满他那颗火热的心。这样的感情当然有可能是真挚的——必须承认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至少我们没有确凿的理由怀疑其中一定存在着什么心机与诈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