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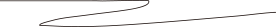
但这并不是问题最终的答案。在石碏的例子里,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细节,即处决者的人选:卫国派出右宰丑到陈国诛杀州吁,石碏派出家臣獳羊肩到陈国诛杀石厚。我们的问题是,如果石碏的行为确乎出于天下公义,或者出于国家利益,那么他为何不将儿子交付有司以国法制裁(正如右宰丑代表卫国处决州吁一样),却派自己的家宰动用私刑呢?
州吁和石厚明明被关押在一起,完全没必要派两个人分别行刑。之所以做出这种似乎画蛇添足的事情,是因为右宰丑处决州吁,办的是国事;獳羊肩处决石厚,办的是家事。石碏灭亲之“大义”是家法之义,而非国法之义,这实是基于周代特殊的社会结构。
若以秦汉以后的普通眼光来看,石碏的所作所为无论大义灭亲与否,首先便该算是赤裸裸的弑君。州吁一则是卫桓公的异母兄弟,二则已经做了卫国的君主,如果因为君主有过错,臣下便可以弑杀之,这显然不是政治哲学的主流所能认同的。但在春秋的特定社会结构下,石碏的杀子与弑君却有着十足的习惯法的依据,所以《左传》对他才有“纯臣”之誉。
若我们站在社群主义的角度为石碏的所作所为寻找道德动机的话,就会把问题追溯到周代的开国时期。周人以宗法建国,以血统维系政统,政治结构建筑在家族结构的基础之上,所以才有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周初分封诸侯,卫国的始封君是周武王的同母兄弟康叔封,上文提及周文王共有十位嫡子,康叔封在其中排行第九。在宗法制度里,周天子是天下大宗,百世不迁,诸侯国君于周天子为小宗,于本国为大宗。诸侯在本国分封亲族,是为卿大夫之分封,卿大夫也像诸侯一样世代相传,这便是周代的世卿世禄制度。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即便数代相传,卿大夫和国君仍然保有血缘关系。卫国是姬姓诸侯,传统上,历代周天子会对卫国国君以叔伯相称;石碏其时为卫国上卿
 ,姓姬,石为其氏。
,姓姬,石为其氏。
 也就是说,石碏与卫桓公、州吁都是同一个家族里的亲人,或者说,石碏并不是一个被国君“聘用”或“雇用”的大臣,而是一位在卫国握有相当股权的股东。
也就是说,石碏与卫桓公、州吁都是同一个家族里的亲人,或者说,石碏并不是一个被国君“聘用”或“雇用”的大臣,而是一位在卫国握有相当股权的股东。
《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子产刚刚在郑国执政,有事情安排伯石去办,为此授伯石以采邑。子大叔很有意见,对子产说:“国是大家的国,为什么独独分采邑给伯石?”——这里出现的三个人物都是郑穆公之后,也同为郑的世卿,所以子大叔口中的“大家”指的是“我们所有贵族”。这并不像霍韬给嘉靖帝的上疏中仅仅在理论上成立的所谓“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而是国家确乎属于贵族共同体所有。既然政治结构有别,臣子对国事所能行使的权利自然也就不同。
正如孟子对齐宣王言及,公卿分为两种,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如果国君犯下大错,贵戚之卿有废立之权,异姓之卿则仅能尽规劝之力。
 孟子说这话的时候已是战国之际,各国政治都是中央集权之势日盛,西周乃至春秋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度已经在悄然瓦解了,所以齐宣王对孟子所谓贵戚之卿的说法便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诧异。石碏在卫国恰恰属于贵戚之卿,行废立之事自是顺理成章。而从宗法制度上讲,石碏于卫君为小宗,在自家则是大宗宗主,有维护宗族利益的义务。所以对于石碏来说,杀石厚自然属于家务,杀州吁则既属国事,相当程度上亦属家务。
孟子说这话的时候已是战国之际,各国政治都是中央集权之势日盛,西周乃至春秋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度已经在悄然瓦解了,所以齐宣王对孟子所谓贵戚之卿的说法便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诧异。石碏在卫国恰恰属于贵戚之卿,行废立之事自是顺理成章。而从宗法制度上讲,石碏于卫君为小宗,在自家则是大宗宗主,有维护宗族利益的义务。所以对于石碏来说,杀石厚自然属于家务,杀州吁则既属国事,相当程度上亦属家务。
孔子也讲过类似的道理。《左传·宣公九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一同和当时著名的美女夏姬私通,这一君二臣简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对私通行为非但不加掩饰,甚至还穿着夏姬的内衣在朝堂上戏谑。大臣泄冶规劝陈灵公说:“国君与卿宣扬淫乱,人民无法效法,何况这名声实在太坏,君王还是收敛一下的好。”泄冶的意见义正而词严,陈灵公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开脱。对泄冶虚与委蛇一番之后,陈灵公找来孔宁和仪行父商议对策。后者于此时此刻表现出了完美意义上的讳疾忌医与怙恶不悛,提议杀掉泄冶。于是,在陈灵公的默许之下,直言进谏的泄冶死于非命。
按照一般的想法,我们在谴责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之余,对泄冶应当大加褒奖才是。然而孔子的看法是:“《诗》说‘人民多有邪僻之事,你就不要再自立法度’,说的就是泄冶这样的人吧。”

泄冶无疑是个直言敢谏的忠臣,即便比之前述“大礼议”事件中的殉道者们亦不遑多让,但孔子居然对此不以为然,道理何在呢?在《孔子家语》里,子贡就问过老师这个问题,说泄冶堪比殷商的忠臣比干,可以当得起一个“仁”字吧?孔子答道:“比干之于纣王,论血缘是诸父,论官职是少师,忠报之心在于宗庙,希望能以自己的死令纣王幡然悔悟,用心确实称得上仁;但泄冶之于陈灵公就不同了,论官他只是一名普通大夫,论亲他和陈灵公也不存在骨肉之情,只不过眷恋于国君的恩宠,出仕于昏乱的朝廷,妄想以区区一己之力扭转一国的淫乱风气,这样的人当不得仁人之称,只当得起一个‘狷’字。”(《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篇》)
《孔子家语》的这段记载也许是从《左传》敷衍而来的,但它的确合乎先秦儒家的一贯宗旨。后来世道嬗变,专制日深,便常有学者怀疑孔子这番议论的真实性,因为如此这般的一种臣子之道已经随着宗法制度的瓦解而不再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