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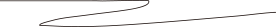
上述对天伦的支持难免会令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天子的突然离职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动荡,野心家自然蠢蠢欲动,下一任天子会不会非桀即纣呢,如此重大的社会责任该不该由那位弃天下若敝屣的高尚天子来承担呢?
这个问题确实不易回答,但幸好也可以避而不答。儒者们并不希望看到理想天子大舜面临如此这般的两难抉择,所以张璁的《大礼或问》说大舜在背着父亲瞽瞍潜逃的时候,心里只有父亲而没有天下,所以明代学者马明衡说其时“皋陶但知有法,舜但知有父”。也就是说,做事只要符合道义原则就足够了,完全不必考虑结果如何。“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仅此而已。
可惜现实总是比理论残酷。大舜将要和犯了罪的父亲一同以逃犯的身份度过漫长的后半生,就算潜逃的时候心里只有父亲而没有天下,但总会有重新想起天下的时候;设若大舜在几年之后听说国内因为自己的突然离职而致使野心家篡位,国家板荡,民不聊生,会不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呢?
既然亲情重于天下,无论如何大舜都应该是无怨无悔的。毕竟人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无法逆睹结局,不能以结果来证明手段的合理性。譬如医生救治婴儿,那个时候难道会因为顾虑到这个婴儿有可能成长为一名杀人魔头而放弃救治吗——这个例子虽然不是一个十分恰当的类比,但或多或少总是与上述情形有几分相通之处吧。
只不过当我们从如此角度来排疑解惑的时候,依旧避不开两难的局面:儒家所推崇的古圣先贤,素来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连称,其中又以舜与周公最为突出;舜是天子的理想型,周公是辅臣的理想型;所谓“周公制礼”,周公被认为是儒家礼制的创始人,但是,周公在处理亲情与国事的矛盾时,却偏偏选取了与大舜截然相反的大义灭亲的解决方案,而且千古传为楷模。
那是在周武王灭掉殷商之后,殷商的王畿被重新划分为几个部分,北部作为纣王之子武庚的封国,中部和东南部作为“三监”的封国。顾名思义,设置“三监”的意义就是监视武庚治下的殷商遗民。大略而言,“三监”即管叔、蔡叔和霍叔。周武王的同母兄弟共有十人。当时,周文王长子伯邑考已经去世,次子便是周武王,三子管叔鲜,四子周公旦,五子蔡叔度,六子曹叔振铎,七子成叔武,八子霍叔处,九子康叔封,十子冉季载。这就是说,周武王、周公与“三监”都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其中管叔还是周公的兄长。
后来武王去世,其子成王年纪尚幼,便由周公主持政局。而管叔等人散布流言,说周公将要趁着这个主少国疑的时候篡夺王位。在做足了舆论铺垫之后,管叔和蔡叔发动叛乱,开中国历史上“清君侧”之先河,武庚也联合殷商遗民企图趁乱复辟(周公指责武庚与管叔、蔡叔有勾结)。此情此景之下,周公应当如何呢?
今天的民族主义者和主权论者很自然地会把正义的旗帜派给武庚,因为周人灭商属于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藩国征服宗主国,与明清易代堪有一比;再者,侵略战争总归是非正义的,而周人显然就是侵略者,就算商纣暴政真实不虚,而不是周人作为敌对方对征服者的肆意污蔑,但这毕竟属于殷商内政,轮不到周人横加干涉。
若换到功利主义立场,正义性取决于谁能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那么我们将会无从判别——也许武庚或管叔的统治会带给万民更大的福祉,谁知道呢?
仅在周人内部而言,武庚的叛乱当然一定要彻底敉平,这是革命(就“革命”一词的原始意义而言)与反革命阵营之间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但周公和管叔、蔡叔的矛盾不过是同一革命阵营的内部纠纷罢了,接受管叔、蔡叔未必就比接受周公的情况更坏。何况管叔是周公的同母兄长,也是周文王在世的嫡子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周人服膺管叔甚至比服膺周公更加顺理成章。
倘若我们援引舜的成例,重申亲情重于国事这一原则,那么为了避免手足相残的悲剧,周公分明应当避让管叔、蔡叔才对;一旦由后者主持政局,分明也可以辅弼成王,安定武庚,国事就算不会更好,想来也不会更坏到哪里去。退一步说,即便管叔废黜成王而自立,即便管叔、蔡叔没有能力阻止武庚的复辟,那又如何呢?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问心无愧也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