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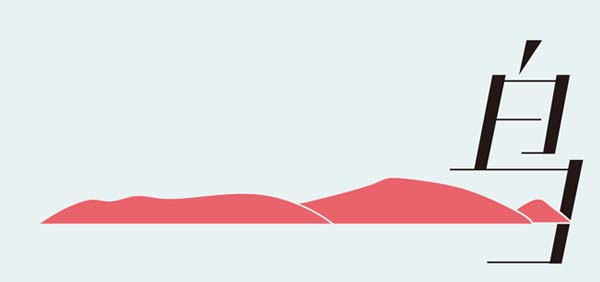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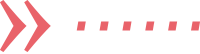
汤姆·克里希那和玛莉·沙拉金妮同邻居园丁家的孩子一道去睡午觉了。在黑暗的起居室里,苏茜拉·麦克费尔夫人独自坐在那儿,回忆着过去的幸福时光,忍受着而今失去丈夫的悲痛。厨房里的钟声响过半点,她出发的时间到了。她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穿上凉鞋,走进了热带地区下午那极其耀眼的阳光中。她抬头看了看天。在火山上空,厚厚的巨大云层正向穹顶聚集,一个小时后就会下雨。她沿着树木林立的道路行走,享受着一片又一片树荫的清凉。突然一阵“扑棱棱”的翅膀扇动的声音传来,一群鸽子从一棵十分高大的菩提树上起飞,向远处森林的方向飞去。绿色的翅膀,珊瑚色的喙,它们的前胸在阳光下如珍珠蚌般变幻着颜色。它们多么漂亮!可爱得无以言说!苏茜拉正要扭头看看杜加德仰面微笑的愉快表情,但是突然发现自己看到的只是地面而已。杜加德不在了,只留下痛苦,就像是一只幽灵的手臂在想象中萦绕,萦绕在一个仿佛经历了截肢的人的感知中。“截肢,”她对自己低语道,“截肢……”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她痛哭起来。截肢的感受不是自哀自怜的借口,既然杜加德已经死了,鸟儿依旧美丽,她自己的孩子们,还有其他的孩子也正迫切需要被爱护、帮助和教育。如果他已经不在的事实如此挥之不去,那就是在提醒她,从今以后,她必须为两个人去爱、去活、去思考,必须用她自己的眼睛和思想,也同时要用他的眼睛和思想,去感知和理解。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前,两人的所见所思一直是愉悦和智慧的交融。
这就是医生的小屋了。她登上台阶,穿过门廊,走进了起居室。她的公公正坐在窗边,呷着陶缸里的凉茶,阅读法文的《真菌学评论》。当她走近的时候,他抬起头微笑着表示欢迎。
“苏茜拉,我的孩子!你能来我真高兴。”
她弯下腰吻了一下他胡子拉碴的脸颊。
“玛莉·沙拉金妮说的是怎么回事?”她问道,“她真的发现了一个乘船遇难的人?”
“嗯,英格兰人,从中国经由壬当来的,还有遇难的船只。是一名记者。”
“他长得什么样子?”
“弥赛亚
 的身形,但是很聪明,不相信上帝,也不确信他自己的使命。即使是深信自己的使命并执行时,也太过敏感。他的身体想行动,他的情感想相信,但是他的神经末梢和他的聪明阻止他那样做。”
的身形,但是很聪明,不相信上帝,也不确信他自己的使命。即使是深信自己的使命并执行时,也太过敏感。他的身体想行动,他的情感想相信,但是他的神经末梢和他的聪明阻止他那样做。”
“那么我想他很不开心了。”
“是很不开心,因此笑起来像一只土狼一样。”
“他知道自己笑起来像土狼一样吗?”
“知道并且引以为荣。甚至还编了一句隽语:我不是一个轻易赞同别人的人。”
“他伤得严重吗?”她问道。
“不严重,但是他正在发烧。我已经给他用了抗生素。现在你来决定是否提高他的肌体抵抗力,给自然的痊愈力量一个机会。”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她沉默了一段时间说,“我去看了拉克西米,在我从学校回来的路上。”
“你觉得她情况如何?”
“还是老样子。不对,可能比昨天虚弱了点。”
“我今天早晨看到她也是这种感觉。”
“所幸的是疼痛不会再加重了。我们仍旧可以从心理方面来想办法。今早我们诊治了恶心的症状。现在她可以喝东西了。我认为没有再进行静脉输液的必要了。”
“谢天谢地!”他说道,“静脉输液就是一种折磨。面对每一个真正的危险时需要巨大的勇气。但是每当涉及皮下注射或是静脉针刺的时候,她都会表现出极其可怜和极不理智的恐惧。”
他回忆起了过去的岁月,在他们刚结婚的日子里,每当她对此大惊小怪的时候,他都会大发雷霆称她是个胆小鬼。拉克西米哭了,样子很可怜,乞求他原谅,这就如同把炭火放在了他头上一样
 。“拉克西米,拉克西米……”现在她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三十七年了。“你们谈了些什么?”他大声问道。
。“拉克西米,拉克西米……”现在她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三十七年了。“你们谈了些什么?”他大声问道。
“没什么特别的。”苏茜拉回答道。事实上,她和拉克西米谈论了杜加德,但她现在真是无法让自己再重复一遍她们谈话的内容。“我的第一个孩子,”拉克西米低声说道,“我不知道孩子还能长得如此漂亮。”在她深陷发黑的眼窝中,双眼突然亮了起来,苍白的嘴唇也绽开了笑容。“这么小小的手,”微弱、嘶哑的声音继续说道,“那么贪吃的小嘴。”她用一只骨瘦如柴、颤抖的手摸了一下自己乳房的位置,由于去年的手术,现在已经是扁平的了。“我真的想不到。”她不断重复着。是的,在事故发生前,她怎么能知道呢?这是一种启示,一种爱和紧连着的灾难。“你懂我的意思吗?”苏茜拉点了点头。她当然是懂得的——从与她自己两个孩子的关系中她懂得,从其他爱和紧连着的悲剧中她懂得,同有着这小手和贪吃小嘴的杜加德长大成人后的相处中她懂得。“我那时常常为他担心,”这位病中的夫人低语道,“他那么强壮,像暴君一样,他本可能会去伤害、去欺凌、去毁坏,如果他娶了别的女人……谢天谢地,他娶了你!”她的手从乳房的位置移到了苏茜拉的手臂上。苏茜拉低下头亲吻了她的手。她们两个都哭了。
麦克费尔医生叹了口气,向上看了一下,就像是一个刚从水中爬出来的人一样,战栗了一下。“那位遇险的人名字叫法纳比,”他说,“威尔·法纳比。”
“威尔·法纳比,”苏茜拉重复道,“嗯,我去看看可以为他做点什么。” 于是她转身走开了。
麦克费尔医生目送她离开后,向后仰靠着椅子闭上了眼睛。他想到了他的儿子,他的妻子——杜加德像是一束熊熊燃烧的明亮火炬突然被熄灭了,拉克西米则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无常和无法预知的变化组成了人生,所有的美丽、恐惧和荒诞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人类命运也无法解释而同时又具有上天意旨的模样。“可怜的女孩。”他自言自语道,他清楚地记得当他把杜加德的噩耗告诉苏茜拉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可怜的女孩!”那时,也是这篇在《真菌学评论》上刊登的有关产生幻觉蘑菇的文章发表的时候。这是另一件发生在上天安排的模式里不相关的事情。一首老拉贾古怪的诗歌此时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造化万端,致敬凡此种种,
无动于衷
其间冲突不谐
为了一种善,超越了好坏的善
为了一种存在,永恒于短暂无常中
其衰减耗散,比天堂中的上帝更加永恒
门嘎吱的响了一下,随后威尔听到了轻轻的脚步声和衣裙窸窣的声音。一只手放在了他的肩上,同时他听到一个低沉并悦耳的女声问他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很糟糕。”他回答道,却没有睁开眼睛。
他的语气中并没有自怜自艾,也没有恳求同情——只是像一位苦修的斯多葛派人物,最终厌倦了长期不动声色的闹剧,愤恨地将内心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
“我感觉很糟糕。”
那只手又触碰了一下他。“我是苏茜拉·麦克费尔,”这个声音告诉他,“玛莉·沙拉金妮的妈妈。”
威尔勉强地把头转过来,睁开了眼睛。一个成年版的、肤色更暗的玛莉·沙拉金妮正坐在他的床旁边,向他微笑,充满了友善的关怀。向她回以微笑需要做出太多的努力,所以他满足于对她说声“你好”,然后向上拉了一下床单就又闭上了眼睛。
苏茜拉默默地看着他——骨瘦如柴的肩膀,清晰可见的胸廓肋骨,典型北欧人的苍白皮肤,以她——帕拉岛居民的眼光看来,这肤色显得虚弱和不堪一击。再看看他被太阳晒伤的脸,五官分明,就像是一座只适合远观的雕塑品——俊秀而又敏感。是他的颤抖,而不是这张裸露的脸,让她不禁想到一个被剥了皮并被独自撇下承受痛苦的人。
“我听说你来自英格兰。”她隔了半天才开口说道。
“我不在乎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威尔暴躁地咕哝道,“也不在乎将要去哪儿。不过是,从地狱到地狱而已。”
“战争刚过,我就到了英格兰,”她接着说,“当时还是个学生。”
他试图不听她讲话,但是耳朵不像眼睛有眼皮,根本不可能屏蔽这闯入的声音。
“我们心理学班上有个女孩,”声音在继续,“她的父母住在威尔斯。她邀请我暑假一开始就去那里和他们待上一个月。你知道有三口泉水的威尔斯小城吧?”
他当然知道威尔斯。她为什么用这些愚蠢的回忆在这里烦扰自己呢?
“我那时喜欢在水边散步,”苏茜拉说,“看运河对面的大教堂,”——这时她想到,当她看大教堂的时候,杜加德在海滩边的棕榈树下,给她上了攀岩第一课。“你身上系着绳索,是非常安全的,不可能掉下来……”不可能掉下来,她苦涩地重复道——然后她想起,此时此地,还有任务要完成,她又看了一下这张像被剥了皮一样英俊的脸,想起来这儿还有一个疼痛的人需要她。“大教堂多么漂亮”,她接着说道,“多么宏伟宁静!”
声音,对于威尔·法纳比来说,变得越来越悦耳,并且不可思议地更加遥远。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他不再厌恶其侵扰的原因。
“如此非凡的平静。香提
 ,香提,香提。传递理解的宁静。”
,香提,香提。传递理解的宁静。”
现在,声音几乎变得如唱诵一般了——似乎来自于另外某个世界的唱诵。
“我可以闭上眼睛,”她继续念诵道,“可以闭上眼睛并把全部景色看得很清晰。可以看到教堂——它宏伟壮观,比在主教宫殿旁边的参天大树还要高得多。可以看到绿草、水,还有照在石头上的金色阳光,投射在扶壁之间斜斜的长影。听啊!我可以听见钟声,钟声和寒鸦的声音,在塔里的寒鸦——你可以听见寒鸦的叫声吗?”
是的,他可以听到寒鸦的声音,同他现在听到窗外树上那些鹦鹉的叫声几乎一样清晰。他在此地,同时他又在彼地——此地即是在赤道附近地区这间黑暗、闷热的房间里,彼地是在门迪普斯边上凉爽山谷的室外,寒鸦在大教堂的塔楼顶上鸣叫,教堂钟声远播,渐远渐弱消失在绿色的沉寂中。
“还有白色的云朵,”这个声音又说道,“白色云朵之间的蓝天显得如此浅淡、雅致、精美、轻柔。”
轻柔,他重复道,四月里的一个周末,蓝天也是那么轻柔,在他和莫莉婚姻触礁之前,他俩在那里待过。草丛里开着雏菊和蒲公英,河水对面矗立着恢宏的教堂,建筑朴素的几何线条挑战着旷野四月轻柔的云朵,和旷野互相抗衡,同时也互相映衬,完美地调和在一起。这应该是他和莫莉之间的关系——那时确实也是这样的关系。
“还有天鹅,”他听到那个声音如梦般地在念诵着,“天鹅……”
是的,天鹅。白色的天鹅在碧绿又略带墨黑色的湖面上划过——一面起伏抖动的镜子,因此天鹅银白色的倒影总是在破碎和重聚之中,分裂而又合为一体。
“就像纹章一般,浪漫的、难以置信的美。然而它们就存在于此——真实场景中真实的禽类,和我离得很近,我几乎都可以触摸到它们——同时又那么遥远,在数千英里以外,遥远的平静的水面上,像是被某种神奇的力量所推动,轻柔、庄严……”
庄严地、庄严地划动,当它们富有曲线的白色胸脯在水中前行,沉黑色的水涌起而后拨散——涌起,拨散,波纹向后散去,然后如闪着微光的箭头在它们身后展开。他可以看到天鹅划过黑色的镜面,可以听到寒鸦在塔楼里鸣叫,可以闻到传来的消毒剂和栀子花混合的味道,以及远处绿色山谷中冷森森的哥特式护城河淡淡的野草味道。
“轻而易举地漂浮。”
“轻而易举地漂浮。”这几个词让他内心深处感到十分满足。
“我会坐在那里,”她说,“我会坐在那里一直观看、观看,一会儿我也会漂浮起来。我会和平静湖面上的天鹅一起,飞舞在墨黑色的河流与轻柔的淡蓝色天空之间。同时飞舞在此地与遥远的空间之中,彼时与此时之间的另一处所在。”同时,她的思绪也徘徊在过去的幸福回忆和现在持续的丧偶之痛中间。“漂浮,”她高声说道,“在现实和想象的世界之间的平面,在外界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和我们内心最深处升腾的事物之间漂浮。”
她把手放在他的前额上,突然,这些话开始变成了它们所指示的景物和事件,意象变成了事实,他确实正处在漂浮之中。
“漂浮,”那个声音继续轻轻地说道,“漂浮,就像是一只水上的白鸟。漂浮在生命的伟大长河上——宽广、平缓、宁静的河流,如此的宁静、宁静,你几乎可能认为它已经睡着了。沉睡的河流。但它仍旧不可阻挡地向前流淌。 ”
“生命静静地、不可阻挡地流向更充实的人生,流向更深刻、更丰富、更坚强,也更完满的宁静,因为它知晓你的痛苦和不幸,知晓并且将其吸纳进生命之流并使之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现在你正漂浮进入那片宁静,漂浮在这条平滑宁静的沉睡着的河流上,也是不可阻挡的,不可阻挡恰恰因为它在沉睡。我在和它一起漂浮。”她为这个陌生人言说,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是在为自己言说,“不费气力地漂浮,根本不必做任何事。仅仅需要放手让自己被河流推动,就让这条不可阻挡的沉睡的生命之河把我带到它流淌的目的地——知道河流去往的地方也是我想去往的地方,我必须去往的地方:去往更多生命力、更多宁静的所在。沿着沉睡的河流,不可阻挡地,流向完全的和解。”
威尔·法纳比不由自主地、下意识地深深叹了一口气。世界变得多么安静!像水晶一样透彻的沉沉的安静。纵使鹦鹉们仍旧在百叶窗外跳来跳去,纵使声音仍旧在他旁边念诵!宁静空寂,在宁静空寂中流淌着一条沉睡的、不可阻挡的河流。
苏茜拉低头看了看枕头上的这张脸:突然这张脸看起来非常年轻,在静谧安详中显得像孩童一般。前额上紧锁的皱纹消失了。由于痛苦而紧闭着的嘴唇也分开了,气息变得缓慢、轻柔,几乎不易察觉。一个月夜,她想起来,当她低头看着杜加德变得纯净无邪的脸庞时,这句话突然闪现在脑际:“她让她深爱着的人安眠了。”
“睡吧。”她大声说道,“睡吧。”
宁静似乎变得愈加深沉,空寂变得愈加无边。
“在沉睡的河上睡着,”这个声音说道,“在河面之上,淡蓝色的天空,飘浮着巨大的白色云朵。当你看着它们的时候,你开始向它们飘去。是的,你开始向它们飘去。而河流现在是空中的河流,一条看不见的河流载着你向前,载着你向上,越来越高。”
一直向上、向上,穿过宁静的空无。意象变成了现实,语言成了体验。
“穿越炽热的平原,”这个声音继续说道,“轻松地进入大山之间的清新和凉爽。”
是的,这里是少女峰
 ,在蓝天下发出耀眼的银白色光芒。还有蒙特罗萨峰
,在蓝天下发出耀眼的银白色光芒。还有蒙特罗萨峰
 ……
……
“当你呼吸的时候,你觉得空气是多么的新鲜!新鲜、纯净,充满了生命力!”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仿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现在横跨雪地,吹来了一阵微风,使肌肤倍感凉爽,诱人的凉爽。仿佛回应着他的想法,描绘着他的感受。这个声音说道:“清凉。清凉,安睡。清凉带来了更多的生命力。通过睡眠,获得了和解、完整与生活的平静。”
半个小时之后,苏茜拉再次进入了起居室。
“怎么样?”她的公公问道,“成功了吗?”
她点了点头。
“我和他谈论了英格兰的一个地方,”她说道,“他进入角色的速度比我期望得更快。在那之后,我给了他一些关于体温的暗示。”
“还有膝盖吧,我希望。”
“当然。”
“直接的引导?”
“不,间接的。间接的效果通常好些。我让他意识到了自己身体的意象。然后让他想象自己的体形要比现实生活中更大——这样膝盖就更小。糟糕的小东西反抗巨大辉煌的事物,哪个会胜出毫无疑问。”她看了看墙上的钟,“天啊,我得走了。要不我在学校给孩子们上课就会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