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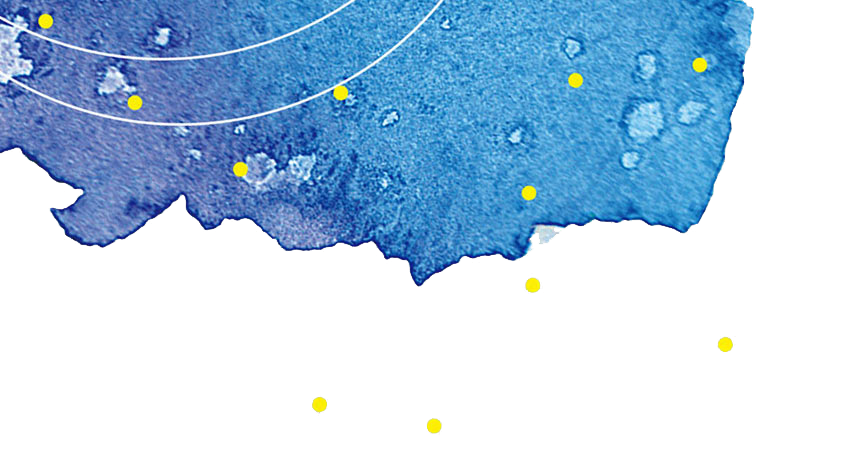
这年冬天,天空连着下了好几场大雪。雪花把房屋覆盖起来,一直埋到了窗户底下,最后将门都封住了。
我的卧室在枣梨园的后院,阁楼的窗户正好对着桔麓山的山脊。白天的时候,我能够从窗缝中看到桔麓山顶堆着的皑皑白雪,以及断裂的山崖上裸露出来的棕红色的山石。到了晚上,蓝幽幽的雪光就会渗到屋子里面来。这天深夜,雪还在下着,我被人叫醒了。小扣走进房门给我穿衣服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她背着我走到屋外,我意识到家里也许出了一件什么事,不过,我没有显出过分的惊慌。天气格外地寒冷。雪片一落到地上,马上就被冻住了似的,脚踩上去,发出一阵阵咔嚓咔嚓的响声。
我们没有沿着回廊朝前院走,而是抄了一条竹林里的近路。小扣显得非常慌乱,她不住地喘息着,竹枝上的积雪劈头盖脸地打在我们的身上,小扣走得太快,所以我们不得不时常停下来歇息一两次。
我看见了父亲书房的灯光。飞舞的雪花将它包裹着,我还听到了那边传来的可怕的呕吐的声音和一声接着一声的喊叫,那一定是父亲在叫,像是要把整个村庄里的人都弄醒。
父亲蹲在一只陶制的缸盆前,突出的眼珠像蜗牛一样睁得溜圆。他双手按着肚子朝缸盆里大口大口地吐着血。九斤和尚——我们家新来的仆人,不时地将一团团草木灰朝他的嘴里塞。那些草木灰刚刚塞进去,父亲就将它吐了出来,带着黑黑的血喷到对面的墙上。我看到让烟炭熏黑的墙边、炉膛的箱壁上,鲜血已经凝结住了。
“杂种,”父亲吼了一句,将九斤和尚递过来的手挡开,“你想把我噎死吗?”
父亲看上去威风凛凛的,浑身都是劲儿,一点也不像生了病的样子。看到我进来,父亲突然抬起头,怔怔地瞪着我,好像在回忆一件过去的什么事,又像是一时还没有认出我来似的,我看见他笑了一下,示意我过去。我本能地往后退了几步,心怦怦直跳。我没有朝他走过去,而是小心翼翼地绕开他,朝母亲走去。满地都是血迹,我再小心,也没法不让它弄脏我的鞋子。
母亲静静地站在一边,手指不停地抚弄着桌上的一根砚墨。父亲又吐了一口血。他大声地叫喊着什么人的名字,喉管里发出一连串流水般呼噜呼噜的声音。不一会儿,他的身体渐渐软下来,靠在了那只没有生火的炉子上。
九斤和尚神色慌张地瞥了母亲一眼:“他已经开始说胡话了,太太,老爷眼看快要不行了。”
母亲紧抿着双唇,转过身来看着父亲:“忍着点吧,人人都有这么一天,别把孩子给吓着了。”
父亲的眼泪滚滚而出,他缓缓地抬起头,朝我们摆了摆手,示意母亲将我领开。
父亲第一次流泪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一刻,我似乎感觉到他有些什么话要对我说,但一时仿佛又拿不定主意。我看见他的腰像弓一样高高耸起,然后“嘭”的一声摔在地上。
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北风鼓荡着窗纸,噗噗直响。一绺绺雪从门缝中挤进来,闪动着晶莹的光亮。我紧紧地揪住母亲的衣襟,又一次避开了父亲投过来的虚弱的目光。我当时是那样害怕他悲怜的目光,我不知不觉地扭过头去,装作没有看见。
等到天色微明,母亲领着我离开书房的时候,我依然能够听到父亲渐渐沙哑的叫喊声。他在叫什么?我问母亲。他在叫妈妈。是在叫你吗?母亲说:不,他是在叫他自己的妈妈,不是在叫我。我说他现在大概害怕了吧?母亲说:他害怕。我想了想,又说,我们为什么要让他一个人留在书房里?因为……母亲犹豫了一下,我们在那儿也没有什么用处。他会死吗?
“会的。”母亲果断地说道。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蚕房的边上。我又闻到了隔年的桑叶和蚕粪的气息,我们在那处背风的山墙边站了很久。母亲一言不发,像是在盘算着一件什么事。过了一会儿,母亲拉起我的手,朝父亲的书房踅回去,这时,我们已经听不到那边的一丝声音。母亲一边加快了步子,一边说出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没准这样更好。”
父亲是在第二天午后死去的。等到天晴的日子,我们将他埋在了桔麓山南坡的一块麦田里。
在枣梨园,有一种植物叫作荨麻,它有着山雀花一样的香味,像松针一样苍翠,可是它细细的针刺在人的皮肤上留下的伤痕要过很久才会显现出来。对母亲来说,父亲的死给她带来的伤痛一直在她的静穆的脸上深藏着,很多年以后,它才清晰地表露出来。
一个夏日的早晨,母亲将我叫到堂前,让我背一段《幼学琼林》给她听。我背了不一会儿就哽住了。“张丽华……”母亲打了个哈欠,“接着往下背。”我说张丽华发光可鉴。“吴绛仙呢?”母亲又提了我一句。我说吴绛仙秀色可餐。“我问你,”母亲说,“张丽华是谁?”我摇了摇头。“秀色可餐是什么意思?”我再一次摇了摇头。母亲立即勃然大怒:“那个徐复观就是这么给你上课的吗?”
徐复观是我的私塾先生,也是麦村一带有名的中医。他身材魁梧,满脸胡须,一身斯文的长袍使他的模样看上去有几分滑稽。他开办的私塾学堂在运河的南岸,一条年久失修的木桥将它与麦村连在一起。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我站在枣梨园的前院,就能看见学堂雪白的石灰墙,在河面上停泊着的一艘艘装满棉花的船只。父亲死后,我就很少去那儿上课了。这年夏天,徐复观先生常常在傍晚时分捏着一把纸扇,一摇一摆地来枣梨园喝茶。夜深人静的晚上,我偶尔能够听到他和母亲在楼下的树荫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时间久了,徐复观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在第二年桑叶繁盛、蚕虫吐丝结茧的时节,枣梨园发生了一件事。我在一生中从未向人提及这件事,即便是在回想之中,也常常伴随着耻辱的印象使我惊悸不安。这类事情的性质在我当时的年龄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它一览无余的真实却使它在日后的岁月中成了我翩翩幻觉的一个部分。
那年春天,蚕房的灯整夜整夜地亮着。它在夜色中显得模糊而潮湿,常常使我从梦中醒过来。这天晚上,我又一次被那种莫名其妙的念头搅得一夜没有睡着。在晚上天最黑的那段时间,我悄悄地溜下了床,赤着脚往外走。我轻轻地拉开了房门,它发出的奇怪的叫声吓了我一跳。我轻手轻脚地走下楼梯,来到院中。草丛中蛤蟆呱呱地叫着,我顺着两道墙壁中的一条狭窄的甬道,神思恍惚地来到了蚕房外的围栏边上,来到了梨花芳香的深处。蚕房的门前灰蒙蒙的,刚刚做好的几条草龙堆在篱笆的旁边,门前的一棵树上吊着一盏蛾灯。我看见成群的小虫子在它的四周翩然飞旋。蚕虫咬噬桑叶的声音连成了一片。接着,我看到对面的墙上有一团黑影闪了一下,我转过身来,看见母亲正拎着一铅桶水朝这边走过来,她的身体微微倾斜着,铅桶的挂钩发着一声声单调刺耳的声响。我想,母亲一定在很远的地方就发现了我。由于她加快了步伐,桶里的水不断地泼了出来。
母亲走到我身边,把铅桶放下,将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
“你在看什么?”她说。
“我要拉屎。”我赶紧回答她。
“昨天晚上你是不是来过这里?”母亲显得有些微微气喘。我的迟疑不决使她立刻知道了答案。她的敏感和警觉促使她换了一种问法:“昨天晚上打雷的时候你是不是感到害怕?”
“昨天晚上下了一会儿雨,没有打雷。”我纠正道。
“这么说你是来过的。”母亲肯定地说,“那么你都看到了什么?”
“没有。”
“说实话。”
“没看到什么。”
“别说谎,告诉妈妈,你看到了什么?”母亲紧紧地搂着我,几乎使我喘不过气来。
“我看见了父亲。”我说。
母亲放开了我。
我的确看见了父亲。他穿着一件金黄色的衣裳,站在一棵枣树下,满脸都是雨水。我朝他走过去,他突然冲着我笑了一下,然后就在树丛里消失了。
母亲朝那株黑黢黢的枣树瞥了一眼,再一次搂紧了我,她滚烫的泪水流过我的脖颈,弄湿了她胸前的衣衫。
我看到了昨晚的那场滂沱大雨,看见了徐复观先生,他和母亲在蚕房里扭打在一起,我看到母亲赤裸的背上粘满了蚕粪。在一声接着一声的呻吟中,我听到母亲在叫: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母亲吼道。
我还看到了一个无法说明的秘密。它是一棵枣树,阳光灿烂的中午,母亲在树下晾晒着衣服;有时,它是倒映在水杯中的一轮弯月,我的母亲长久地注视着它,默默无言,在无声无息的夜色中守候着黎明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