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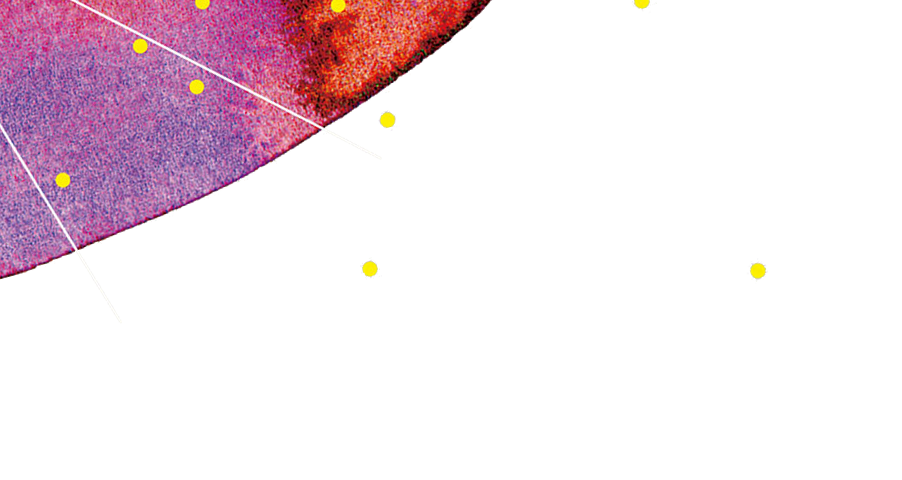
到了后半夜,赵龙微微觉得有些困意,在半明半暗的酒坊里,蜡烛烧化的油脂凝结成珊瑚状在桌上堆得很高。门缝中漏进来的冷风使他腹部隐隐有些疼痛。空气中飘浮着浓烈的酒香,除了牌桌,一切都浸没在黑暗之中。墙上挂着的皇历牌被风卷起,扑刺扑刺地发出响声。王胡子满脸酒气坐在他对面,他眯缝着一对小眼珠,每次摸起一张牌都要凑到烛光下去看个究竟。赵龙觉得今晚的运气不太好。坐在他上家的赵立本虽说从辈分上排下来还和他略沾一点亲,可是这个早已沦落潦倒的秀才老是不让他吃牌。
赵龙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在睡意朦胧之中打出一张中间牌,王胡子叫了一声“和了”,呼啦一下推倒了面前的牌,赵龙探过身,察看了一下对方的牌局,从口袋里摸出四枚铜板扔到桌上。
“怎么,困了吧?”坐在赵龙下首的老板娘柔声细气地说了一句。坐在她旁边看牌的更生已经伏在桌上睡着了,口涎流了一摊。老板娘站起身从酒柜里拿出一瓶花雕酒,给赵龙斟了一杯。这个性情无常的女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经年的酒气。赵立本一口接一口地吸着旱烟,在散淡的烟雾之中,那只瘦骨嶙峋的手时隐时现。那是一只赌棍的手,在年深日久的一次次博戏之中,仿佛具有了一种神秘的灵性,它像钳子一样夹起骨牌,拇指在牌面上轻轻一滑,便已明白了是张什么牌。摸过十四五手之后,赵龙已经砌成了一副清一色的万字牌,他的内心感到一阵狂喜。他只要再摸进一张万字,便可以听牌。桌面上的码牌渐渐地少了,赵龙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摸牌的手忍不住地颤抖,赵立本瞥了他一眼,顺手丢出一张“六万”,赵龙叫了一声“吃”,然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把手中的最后一张闲牌“二饼”打了出去。赵立本哈哈一笑,依次摊开了面前的牌。他一边往烟锅里装着烟丝,一边漫不经心地说:“清一色一条龙一般高二八将……”赵龙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站起身。
“你去哪儿?”秀才警觉地问道。
“撒尿。”
赵龙走到屋外,赵立本随后跟了出来。门外树影婆娑,在幽暗的星光下,大地正在降霜,远处河面上船只的轮廓影影绰绰的,不时传来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赵龙重新回到牌桌前,看见赵立本将两手拢在袖子里一动不动。“砌牌砌牌。”老板娘不耐烦地催促着。赵立本依旧没有动,赵龙知道他是在等着自己付钱。
“我该付多少?”赵龙说。
“十二块铜板。”
“欠着。”
“不欠。”
“我真的没钱了……”
赵立本瞟了一眼他的手腕:“把那副镯子脱下来押着。”
“那是我老婆的。”赵龙说。话一出口,他便感到有些后悔,其实那副手镯是从妹妹的梳妆盒中偷来的,他担心柳柳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跟他要。
“老婆?”赵秀才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你的老婆在哪儿呀?”赵龙怔了一下,他内心深处的那根弦又被触动了。他仿佛又闻到夏季飘浮在墨河上空的桉叶的清香。那年,他在墨河岸边的滩头上种了几亩西瓜,过了端午节,他便早早地在河边搭了一个草棚,睡在里面看瓜。一天黄昏,一条从外地来的装蚕茧的大船停泊在子午镇上,等待着蚕房的茧壳长硬。每天清晨他从草棚中醒来,都能看见船上的外乡人从墨河里吊水,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在间断的几场暴雨过后,墨河水位上涨了几尺,可是他对于身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那天,大雨下到子夜才停,阵雨斜斜地灌进草棚,把他的被褥打得濡湿。拂晓的时候,他提着马灯准备回家去睡。他走到大院前,在一道闪电的光亮之中,他看见院门敞开着,感到有些奇怪。他朝自己的卧房走去,和卧房毗邻的羊圈里传来山羊咩咩的叫声。他推开房门,看见妻子和那条大船上押送蚕茧的一个小白脸躺在床上,床边摇篮里他的不到两岁的儿子正在熟睡。赵龙的嘴边滑过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他的老婆在惊慌之中赤条条地从床上跳下来,扑通一声在他面前跪倒,抱住了他的双腿,她嘤嘤地啜泣,他的小腿被女人的泪水弄得热乎乎的。他感到有些手足无措,推开了自己的女人,走到屋外,女人“砰”的一声把门关严。在黑暗之中他看见一个人影在不远的地方晃动了一下。
“是谁啊?”那个人影问了一句,赵龙听见是父亲赵少忠的声音,便松了一口气。
“是我。”
“我刚才听见这边有人在哭,就起来看看,”少忠说,“你们又吵架啦?”
“没有,没什么事。”赵龙说。他听见屋里那个小白脸正在慌慌忙忙地穿衣服,皮带上的搭扣发出“窸窸”的声响。赵少忠在夜色中静立了一会儿,便转身走了。几天后的一个晴朗的中午,满载着白花花蚕茧的大船离开了子午镇,赵龙的女人撇下了刚刚断奶的儿子也随船一去不返。村里的几个老人告诉他,他的女人拎着一个蓝布包在午后炽烈的阳光中上了船。一连好几个黄昏或早晨,赵龙像一块礁石一样矗立在墨河岸边,对着迤逦远去的河水独自发愣。这件意外的事很快传遍了子午镇的每一个角落。七月初九这一天,村里的媒婆趁着天黑来到了赵家大院,这个前来提亲的老人面对着一言不发的赵少忠简直有些不知所措,她小心翼翼地绕开了可能引起这个家庭种种不愉快的所有话题,委婉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赵少忠淡淡一笑:“我家大媳妇随船到娘家去了,过不了十天半个月就会回来。”媒婆瞥了一眼像座钟一样闲坐在旁边的赵龙,悻悻地走了。在这一点上,赵龙始终弄不清父亲的用意,赵家也曾暗里出钱雇过几个人到外地去找过她,也一直杳无音讯,时间一长,人们就把这事渐渐地淡忘了。
“你的老婆才不稀罕这副镯子呢,”赵秀才说,“你一个男人家套上女人这些玩艺也不怕别人笑话。”
“你就赊他一回嘛。”王胡子在一边劝道。
赵龙没有吭声,他依然沉浸在往昔的回忆之中。他正想得出神,感到桌下有人捏了一下他的大腿,老板娘脸上红扑扑的,额头深深的皱纹上搽着亮晶晶的油脂。女人从桌下伸过手来,把一枚银元塞在赵龙的手里,那枚银元湿漉漉的,像冰一样冷,女人的手像水蛇一样光滑,赵龙觉得身上的热气顷刻之间都被那块银元吸走了。他在凉飕飕的空气中打了个寒噤,把那枚银元抛到桌上。赵秀才眼睛一亮:“我说你是哭穷,有钱不肯拿出来。”
天亮的时候,赵龙最后一个离开了酒坊。女人绿袄的侧襟敞得很开,她踮着小脚把他送到门外,在她身后,她的丈夫更生依旧趴在桌上酣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