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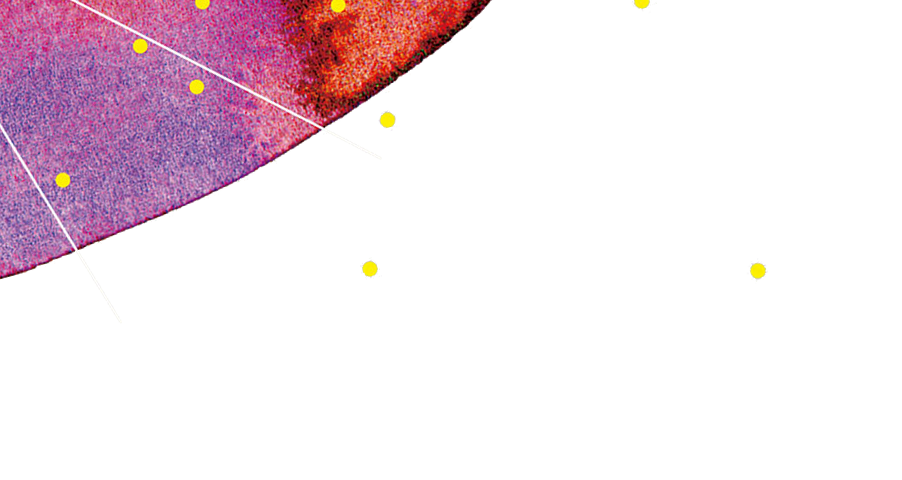
村中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几十年前的那场大火。那是清明节的一天。天黑下来的时候,村里的人都忙着焚香祭祖。在村头的河边、小树林里到处都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火光。村里的老和尚日复一日地来到河边挑水,当他看见村中黑压压的瓦楞上空蹿出一丈多高的火苗,还对着正在水码头上洗衣服的女人说了一句:“你瞧那是谁家在化钱?那么大的火。”女人连头都没有抬:“除了赵伯衡还有谁啦?”一丝凉飕飕的风贴着水皮飘过来,混杂着一股焦黄的硫磺气息。女人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在衣裙上搓了搓手,直起腰来朝村里张望:“和尚,你看那火……”
村口黑乎乎的弄堂里跌跌撞撞跑出一个人影,他敲着铜盆狂呼着朝河边奔过来,在他身后,西北方的半个天都被火光映红了,仿佛落日时的情景。蒸腾的紫绛色浓烟在东渐的北风中疾速浮动,在破碎的铜盆敲击时发出的瘆人声响中,偶尔夹杂着一两声火药引燃的爆炸声,到处都是硫磺的气味。村中高大的山榆树、东奔西突的人群在火花中时隐时现。村里所有阁楼的窗子都打开了,露出一张张半明半暗的脸。几个年轻人从祠堂里抬来了水龙,那个像黄牛一样笨重的土制灭火器发出呜呜的叫声。这个村已经多年没有发生火灾了,废弃不用的水龙的喷水管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怎么也压不出水来。人们叹息着隐伏在河边的树丛中,无奈地看着火焰卷起一片片店铺的屋顶,大火从傍晚时分一直烧到第二天拂晓。当太阳再一次从村后的桑树丛中露出脸来,一些围观的人已经在河滩上的草地里睡着了。在暖烘烘的阳光之中,一切都重新变得安详起来。邻村或更远地方的人得到火灾的讯号赶到这里的时候,天已大亮。那些面容倦怠的外乡人抬着水龙,拎着盛水的木桶围着那片焦黑的废墟转了几圈,就沿着蜿蜒的水路稀稀落落地往回走。
黄昏时分,一个瘦弱高大的老人拄着拐杖走到了这片瓦砾遍地的焦土之中。他吃力地绕过一座座倒坍的墙壁,不时地停住脚步靠在断墙上喘息。没有烧尽的椽子、棉絮和桌椅依然冒着一股一股的青烟,纸烬和布灰在地上随风拂动。西斜的夕阳映衬着他身后绿色——黄色的背景,他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老人在一块赭红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水烟锅,望着宁静的天边一言不发。他的眼前不远处是一片竹篱,篱中的油菜花开得正黄,几只白色的蝴蝶夹在金色的蜂群中翩然而飞。再远处就是静静流淌的墨河,河上拱形的石桥像弓一样横卧在水面上。他隐约能看见地平线上模糊的山峦,风在开阔的田野上吹起一道一道波纹。
天色渐渐暗下来,老人一直那样坐着。他整肃而宁静的外表在这片苍凉的废墟中显得很不协调。这个村里的人们在岁月的更迭中早已滤掉了多余的情感,但他们一旦看到赵伯衡那张由于痛苦而扭曲的脸都忍不住要掉下泪来。仆人第三次来到赵伯衡面前。他依旧摆了摆手。没有人知道此刻他究竟在想什么,他也许在估算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使那些被烧毁的作坊、店铺和阁楼在废墟中重新生长起来,这个刚毅的老人和他那受人尊敬的先辈一样,依靠勤劳和智慧建立了家业,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他一夜之间变得更加苍老。他的身影在晚风中像田野上矗立的稻草人一样显得不真实。在火灾后的最初几天里,赵伯衡依旧孤身一人在门前的白果树下打拳,他想积攒起残存生命的最后一丝光亮,但是那丝光亮仿佛是耗尽了油的灯心草尖上的火星,在风中扑闪了几下,旋即就熄灭了。半个月之后,赵伯衡终于卧床不起。炎热的夏季刚刚来临,他的身体就开始溃烂,褥子上浸湿的脓血和地上的痰迹招来了无数的苍蝇和蚊子,床上和潮湿的墙根下爬满了白蛆,他独自一人呆在那间阴暗的房间里,除了几个端茶送水的仆人之外,在他弥留之际,唯一能够和他常常呆在一起的就是他的长孙赵少忠。那一年赵少忠只有四岁。一天晌午,赵少忠看见祖父勉强支撑着身体在床上坐了起来,在一张张宣纸上写着什么。赵少忠走到床前趴在茶几上帮他研墨,老人脸上吓人的表情慢慢消散开,冲着他凄然一笑。
“你在写信吧,老爷?”端茶进来的仆人顺便问了一句。
“写个屁!”赵伯衡含糊地吭了一声,重新陷入了冥想之中。
在飘飘扬扬的第一场冬雪中,赵伯衡终于命归黄泉,一名跟随他多年的家佣替他合上了眼帘。葬礼结束以后,没有人愿意清扫那间不透风的房间,即使在冬天,屋子里也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
赵景轩是赵伯衡的第二个儿子。起火那天,他正在漫长的运河上押送一只装棉花的船。他的兄弟姑嫂将残剩的财宝席卷而走,他却独自一个人回到了子午镇上,在那间空空落落的大宅里住了下来。这个忧郁的中年人承袭了先辈沉默寡言的秉性,同时染上了一种颓唐、散漫的习性,他整天衣冠不整,蓬头垢面,慵懒的身影像幽灵一样在村中四处晃荡。
一天早晨,赵景轩突然打开了父亲那间尘封的屋子。他在床下的一只木箱中翻出了赵伯衡写过的那些宣纸。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他不知道父亲在临终前为何要将村里几乎每个人的名字写一遍,那时赵少忠已经识得几个字,他朝那几张散发着霉味的宣纸瞥了一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虽然无法知道祖父抄录这些人名的用心,但几年来一直悬挂在心的谜团总算有了满意的解答。原先,他还以为祖父是在交待藏有财宝的地方呢。赵景轩小心翼翼地翻看那些宣纸,他的脸上渐渐呈现出和父亲垂暮之年一样的神色。当他从外地赶回村里时,村庄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流传着那次火灾的各种传说。一个年老的家佣告诉他,大火从铁匠铺、木器铺、鞋店里同时蹿出来,根本来不及救,“如果不是上天有意要灭掉这一族,一定是有人故意放火。另外,好好的水龙怎么也压不出水来,也许有人用木塞将水龙头的喷水管堵住了。”
赵景轩整天坐在阁楼的窗前,仔细察看宣纸上的人名,他似乎突然明白了父亲写下这些名字的缘由。那些歪歪扭扭的文字仿佛刻下了赵伯衡临终前孤独深邃的内心。赵景轩把他一生中剩余的几年光阴完全耗费在父亲遗留下来的宣纸上,白天他在村中四处打听那次火灾的每一个枝节,到了晚上他就对着那些人名发愣。赵少忠常常看见他坐在天井中的一株文竹旁,把那些人名一个个划掉。
十年之后,赵少忠在村中的祠堂和一个外乡女子结婚,那场火灾的阴影已经变得模糊而遥远了,但是他的脑中一旦掠过那些宣纸上的人名,就感到浑身无力,新婚的喜悦和内心潜藏的恐惧纠合在一起形成了记忆深处的一个巨大的纽结。
赵景轩五十五岁时死于痢疾。在葬礼的当天,赵少忠最后一次看了看那几张发黄的宣纸,他发现父亲在一个个名字上划了横杠,只剩下三个名字没有划去。他看着走远的送葬的人群,顺手将它揉皱,丢进了燃烧的火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