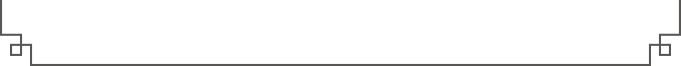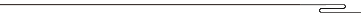
当一夫一妻制家庭成为个体经济单位,它便从母系氏族公社中分裂出来,男女结合由从妻居逐渐变为从夫居,家长由女性变为男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而从夫居与从妻居的转变过程显得特别激烈。

在母系氏族社会,男子习惯于从女方居住,女方是家长,男子是伴宿的过客。到了一夫一妻制时期,丈夫成了家长,妻子从夫居,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便出现了女子抵制出嫁,新婚之夜,新娘不与新郎同房,而由送亲的妇女与新娘伴宿的风俗。
新娘在第二天给夫家挑几挑水,又回到娘家,仍过自由的生活。有了身孕后,丈夫才把她接回去“坐家”,不准再有外遇。
南方有的少数民族女子有三回九转的婚俗,说明结婚次数很多。只有在第四次结婚时才算数。因此,新娘从第一次结婚到夫家去“坐家”,少则两三年,多则十几年。还有的少数民族女子要举行两次婚礼。第一次在新娘家中举行,新娘仍住在娘家。过了三年,新娘去男家举行第二次婚礼,才算正式夫妻。
赘婚也是夫从妻居的一种婚姻形式。它是在有子无财的贫户与有女无儿的富户之间发生的婚姻关系。贫困之家缺乏给子弟娶媳妇的聘财,只得让子弟到女家从事一定期限的无偿劳动,以达到娶到妻子的目的。这就是古书中说的“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的意思。

入赘的男子在女家劳动,要受女子和女家的监督,并经受各种艰苦的考验,以证明自己有养家糊口的能力,才能成为赘婿。否则,就会被女家撵走。《诗经·小雅·我行其野》中,便描写了一个赘婿被女家驱逐后,在野外奔波的心情。
抢婚与逃婚的斗争也是一夫一妻制时期的一个习俗。抢婚一般发生在男女相爱之后,因结婚受到女方家长的阻挠,他们为了达到结婚的目的,便与所爱之人私下约定抢婚的时间和地点。
届时,男子邀约伙伴前来抢亲,女子假装哭叫,表示拒绝,引起女家亲属和邻居赶到出事地点,男方一行人便挟持女子设法逃走。然后由男方家长派媒人到女家求亲。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后,女子到男家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
有些少数民族规定,在娶第一个妻子时,可以在联婚中给中意女子的家长送财礼,然后把她抢走。有些少数民族中保存着女子在婚前哭嫁的习俗。反映出她们留恋母家,对陌生的夫家心怀恐惧的矛盾心情。如汉魏乐府民歌《白头吟》: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有心人,白头不相离。
女子之所以伤心啼哭,就是因她所嫁的不一定是“有心人”。此外,在原始社会的婚姻中,还存在着女子血缘是从父系还是从母系的不同观念。
比如在子女命名的问题上,由父子连名代替原先的母子连名,我国的基诺族、布朗族尚保留着这种遗俗。再如产翁制,子女本是母亲生育的,做父亲的为了夺取子女的所有权,便在妻子分娩后,装作生育的样子在床上“坐褥”,接受亲友的祝贺,而让产妇下地干活,哺乳婴儿。据史书记载,我国的仡佬族、壮族、傣族和苗族,都长期盛行产翁制婚。

“审”新娘是普米族特有的一种婚俗,普米族实行父权制下的一夫一妻制。在“审”新娘的活动中,便体现出夫权意识。
当新娘来到夫家,先由村里的老人向新娘交代规矩,然后把新娘带到无男人的地方谈心,劝新娘交代出她从13岁成年后,在娘家交过多少朋友,有什么隐情,都要在这个时候讲清楚,告诉新娘这样做对本人、对新郎、对全家都有好处。
新娘如实讲出来,表示与过去划清了界限。通过这种方式,妻子迁到自己的氏族来居住,变从妻居为从夫居。从此以后,世系便依父系计算,财产按父系继承。
在父系制的早期阶段,往往还保留着妻方居住婚的残余。随着一夫一妻婚个体婚制的确立,夫方居住婚即成为主要的婚姻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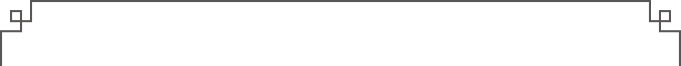
生活在海南岛黎族的对偶婚称“放寮”,异姓青年男女可以到对方的寮房自由地结交伴侣。纳西族称对偶婚为“阿柱婚”,对内称“主子主米”,即最亲密的伴侣。该婚俗也称“走访婚”。从对偶同居,发展为一夫一妻制婚,夫妻不再称“阿柱”,称丈夫为“寨叔巴”,称妻子为“楚米”。在称谓上反映出婚制的改变。
对偶婚虽然是男女双方自愿选择结合,但在同居期间,双方仍享有交结新欢的权利,互不干涉。由于它是介乎群婚与一夫一妻制之间的过渡性婚姻形态,随着母系氏族社会日趋衰落,原来不是很固定的对偶婚,逐渐转变为一夫一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