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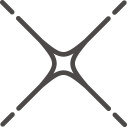
我第一次产生写《日本第一》的想法是在一九七五年。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五年这十五年期间,我几乎每年至少去一次日本,最长会待两个月。一九七五年,我获得一次学术休假,因此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苏珊娜和我在日本度过了一学年。当时戴维已经上大学了,我们带上了两个年幼的孩子,斯蒂文和伊娃。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再次拜访朋友,重游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间住在日本时去过的旧地。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那会儿,我们有时间仔细观察事物,在过去十五年间事情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一九六〇年离开日本的时候,路上车子很少,可选择的食物和服务也非常有限。当新鲜的外来食物第一次出现在市场上时,通常很昂贵。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人们热衷于通过储蓄来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努力工作,提前规划。我还记得当日本首次引进拖拉机时,一个电视节目中有个农民被问到是否打算购买一辆新拖拉机,这位农民回答称:“拖拉机太贵了,而且现在还在试验中。”他预测大概两年内,等一些问题被解决后,价格应该会下降。他决定等到价格降下来、质量也有所提升时再买,并准备从现在开始攒钱。
我觉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远远落后于美国。我在《日本第一》的序言中写道:“我仍未怀疑美国社会和制度总体上的优越性。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比日本先进。无论是研究水平,还是创造发明,日本都望尘莫及。至于天然资源和人口,美国更是丰富得多了。”
一九五八年,我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据我所知,我们是极少数拥有电视机的家庭之一。一九六〇年我准备回美国时,把电视机便宜卖给了土居健郎。这是他拥有的第一台电视机,因为一台全新的电视机那时还非常昂贵。为了学习日语,我们买了索尼最新出的转盘式磁带录音机,回美国之前也将它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六户人家中的一家。这也成了这户家庭拥有的第一台磁带录音机。这户家庭就像土居家一样,他们不得不存一段时间的钱,才能买得起崭新的电子产品。
但当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访问日本时,日本实力的发展让我改变了看法。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前夕,我短暂地回到日本,住在一家小旅馆。屋外都是夜以继日工作的建筑工人。他们正在为这座城市预计将接待成千上万来此观看奥运会的游客做准备。我走到涩谷附近一个我们曾居住过的社区,非常惊讶—为了拓宽道路,建筑工人们拆掉了长达整整七英里的房子。我在美国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景。
一开始,我以为这一系列的建设是特殊情况,因为日本要为奥运会做准备。然而,奥运会结束后,日本仍在继续建造并扩大经济规模。
我在第二版《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九七一)中记录了对这十年进步的最初印象。一九七一年,有两点变化特别引人注目。
我们在一九五九年时认识的日本家庭非常渴望学习美国。就像之前提到的,我们邀请六家人来我家小聚,他们却一门心思地想了解美国人的生活,就像我们想了解他们那样。十年后,他们依旧对此感兴趣,但那种迫切感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西方生活的精髓”。这些家庭已经结束了学徒期:“他们保留日本习俗并不是因为尚未学会西方模式,而是因为他们更爱日本模式。”
一九五九年我第一次见到这六个家庭时,他们非常担心日本的经济止步不前,“感到日常生活岌岌可危”。十年后,“银行存款变多了,物质财富更丰富了。另一个全国性的共识是,日本经济前景(如果有的话)一片光明,对物质福利的焦虑感几乎消失殆尽”。
一九七五年,我用整整一年时间来检视日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变化,我被这些变化震惊了,其速度比美国快得多。我开始思考其中的含义。如果说日本已经经历了戏剧性的高速成长,那未来还能持续这样的发展速度吗?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在《日本第一》里,我提出日本能够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能力和意愿。
我在书中给出的事实是,日本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成功地解决了后工业化社会的基本问题,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从日本学到了经验。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有其他作者写了日本经济奇迹的著作。一九六二年,《经济学人》记者诺曼·麦克莱恩(Norman McClane)用金融数据展现日本未来的发展,他的调研结果和课题项目最终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这一时期,我仍在做心理卫生研究,也没有继续写作关于日本的商业和经济发展的著作。麦克莱恩的文章是我在《日本第一》出版后读到的唯一一篇。
一九七〇年,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的书《新兴的超级大国日本:挑战与回应》出版。卡恩从日本的相关数据中推断并证明日本的经济增长有可能追赶甚至超越西方,他还预测日本很快会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
不过,我的角度有所不同。我思考的是日本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相比经济增长率,我更关注其别具一格的社会结构,比如教育系统,从而来回答“是什么使日本自成一体”这个问题。自从第一次来到日本,我就一直在琢磨所有这些社会结构以及它们的变化。
我刚开始考虑论述日本这十五年的进步时,还只是想写一篇长论文。起初,打算用一年时间做准备,写一本关于日本财团的书,因为当时对美国学者而言,这几乎是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有很多人写了日本政府和政治家,还有一些人写了日本官僚机构,所以我决定将兴趣聚焦在日本的商界。
作为一名社会学者,我通常会在正式写作前对所有制度进行系统性思考。随着时间推移,我总结了日本十五年来的进展,并构想了不同章节的标题。对财团研究愈多,我就愈加意识到商界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而已,真正的故事是日本在各方面取得的进步。于是,我停止撰写关于财团的文章,转身投入写日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我试图通盘考虑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帮助日本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五年间创造了比世界所知的其他地方更快的发展速度。正如我在《日本第一》的序言
 中写到的那样:“一九五二年日本结束了美军占领时代,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英国或法国的三分之一。到了七十年代后半期,迅速增加,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约为美国生产总值的一半。”我相信美国可以从日本即将发起的真正挑战中获取很多经验。
中写到的那样:“一九五二年日本结束了美军占领时代,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英国或法国的三分之一。到了七十年代后半期,迅速增加,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约为美国生产总值的一半。”我相信美国可以从日本即将发起的真正挑战中获取很多经验。
我开始着手写《日本第一》时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很多研究时必须参考的话题还没有被写过。我意识到大学不会一直是我了解日本的最佳场所,因为很多教授讲的日本课程笼统且充斥理论,却没有进行过系统性的实地调查。因此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间,在读过一些著作后,我决定最重要的还是得依靠自己的实地调查,去采访和参观日本的政府机关、工厂和农场。
一九五九年,为了洞察日本主流家庭的样态,我访问了大约二十至二十五位准备结婚的日本人,设计的问题诸如:新娘家希望能得到什么东西,新郎家又希望获得什么,以及新郎新娘在有能力结婚前都会碰到哪些问题,等等。我把自己的调研结果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比起以往跟教授对话或采访,实地调查让我对真实的日本家庭状况有了更好的切身感受。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间,我进行了几次实地考察旅行,经常会遭遇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我曾受阿部德三郎教授邀请,花了两周时间在山形县观察当地的农村家庭。阿部教授是我在一次社会学会议上认识的,他是山形县三河村一位富有的地主家的儿子,二战前曾在德国学习社会学。
可能因为我的名字中有“Vogel”,他就以为我会讲德语,其实我只会一点点德语。不过他仍和我讲德语,我则用日语回答他。事实证明,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向我讲授乡村生活,把我介绍给其他人,以及帮助分发调查问卷,让答卷人放心回答。因为有他的帮助,我了解了很多乡村生活的情况。很多年来他一直用德语给我写信。
另一位日本社会学界的友人佐佐木彻郎(Tetsuro Sasaki)带我去了仙台附近的渔村,这是他实地调查中的一处。他带我去拜访了村里的其他家庭,还去了其他村子。由于他的协助,我得以一窥渔民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
这是我着手了解农民和渔民日常生活的途径。这两位朋友都受过社会学训练。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从事一线实地调查工作,对不同社区中的日本家庭日常生活有实际了解。我也花了几天时间跟着另两位教授逐个走访村庄,一位是福武直(Tadashi Fukutake),日本农村社会研究的著名专家,另一位是川岛武宜(Takeyoshi Kawashima),著名的民法学教授。
直到一九六九年,在日本研究领域,我的注意力基本集中在家庭研究。那几年中,鲍勃·贝拉(Bob Bellah)
 教授离开哈佛大学后,我便接手了他的日本社会研究课程。“日本社会”是一个涉猎宽泛的论题,我想要呈现一个宽阔而系统的思考社会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我的教授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教授离开哈佛大学后,我便接手了他的日本社会研究课程。“日本社会”是一个涉猎宽泛的论题,我想要呈现一个宽阔而系统的思考社会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从我的教授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那里学到的。他经常鼓励我们去思考整个制度体系的所有重要层面。
那里学到的。他经常鼓励我们去思考整个制度体系的所有重要层面。
政治和经济都是体系的一部分,家庭和价值观也是体系的一部分。在读过关于日本社会的基本著作后,我想要依靠采访和田野调查来完成自己的著作。
自从我准备开日本社会的课程后,我决定在一九六九年夏天去日本实地了解政治和经济现状。这也让我和一位日本老朋友野田一夫(Kazuo Noda)再次联系上。我和他第一次碰面是一九五九年,在我们共同的朋友富永健一(Tominaga Kenichi)的婚礼上,当时就一拍即合。他对日本的商业、政治和官僚系统非常了解,富有批判性思维和宽阔视野。他后来成为玉川大学(Tamagawa University)和宫城县立大学的校长。野田毕业于东京大学,取得社会学学士学位,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当过吉姆·阿贝格伦(Jim Abegglen)教授的助理研究员,阿贝格伦教授在野田的帮助下对日本企业管理做了开创性研究。野田是一个非常自信、开放的人,完全不像典型的日本人那样拘谨严肃。
野田成为我接触日本商业领袖最佳且唯一的渠道。一九六九年,他做了一系列的电视节目,由此采访了很多知名日本企业总裁,在商界和官僚机构有非常多的熟人和关系网络。野田也是索尼总裁盛田昭夫、丰田汽车集团总裁丰田章男、IBM日本公司总裁椎名武雄等商界高层的高尔夫球友。
经他介绍,我得以见到商界人士和高级官僚。我自己的方式是,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对商人或官员进行采访,集中了解我想要知道的内容。野田教我的方法则是,和这些人一起出去吃饭喝酒,结成自然的人际关系后就可以谈论任何事情。他认为这样我才可以学到更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会更加坦诚。如果我能从社交场合得到十五分钟有用、有价值的材料,那就很幸运了;这十五分钟对我而言就是一笔宝贵财富。
通过和哈佛大学日本同事的友谊,我也建立了与日本高级官员间的人脉网络。
我能以自己的方式写出《日本第一》的原因之一,和我在这个课题上所学到的知识一样,是通过我能建立起来的个人友谊而获得的。
哈佛大学可能是最受亚洲人欢迎的美国教育机构。很多日本官僚机构中的人员会来哈佛学习进修。他们在哈佛时,我通常会去结识他们,并在某种程度上给他们提供帮助。所以,后来我在日本碰到他们时,我们的关系就会很亲近。
特别棒的是,我认识了很多日本外务省的精英官员。外务省的一个计划是,每年都会将一位四十岁左右、最有前途的人送到哈佛学习。这些人在哈佛求学期间,我和其中很多位都见过面并成为了朋友,比如曾担任驻美大使的大河原良雄,曾任驻英大使的北村洋司,曾担任多个国家大使、现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总裁的藤井弘昭,后来担任驻俄大使的渡边幸治以及现任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我还和现在的主要政治领导人加藤紘一(Kato Koichi)、小和田恒在哈佛时结识。当藤井弘昭担任外务省在首相官邸代表时,他引荐我和前首相大平正芳谈过几次话。在三木武夫任首相时,村上和夫担任外务省代表。村上是另一个我此前在哈佛认识的日本人,他为我安排了对首相三木武夫的采访。类似的经历是,我还见过前首相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竹下登、宫泽喜一等人士。
野田和我合作得非常好。他有社会学思维,因此能帮我认清制度体系的社会学背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野田和我应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委托,为该委员会组织一次关于日本组织的会议。我们决定邀请商界高层人士和政府官员与学者一道出席会议。我们请他们提交一篇基于自己经验写成的会议论文,讨论自己所在的组织及组织成员。其中一位参会高级官员是日本通产省前次长大滋弥嘉久,他谈论了通产省的复杂架构和决策程序。
我们将论文收集起来后出版成书,由我担任主编,论文集名为《日本的组织和决策》( Japanese Organizations and Decision Making ,一九七五)。我们的目的是扩大英语研究圈内对日本商界和政府机构的理解。
一九七六年,也就是在日本待了一年后,我开始着手考虑写《日本第一》,我觉得自己已经收集了足够的信息和数据来为日本的成功提供背景和分析;相信自己能够为这段特殊时期的日本作出精确和详细的诠释。甚至时至今日,我仍认为这本书的前提和论证是基于一个坚实的基础,如果回头再看这本书,尽管日本经历了更困难的时期,但这些描述和分析仍然有效。
我写《日本第一》的时候,就知道一定会在美国引发论战。那时在美国国内出现了对日本在国际市场中取得成功越来越不满的情绪。正如我在书中写的那样:“五十年代早期,日本制造的收音机、录音机、立体音响等产品质量还不如美国,一转眼如今却席卷了整个市场。”“一九七七年日本出口汽车达四百五十万辆,而同年美国的汽车出口量仅为其几分之一。”“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已达一百亿美元,尽管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实行美元贬值,但逆差仍不见好转。”
我知道自己的书和我本人也会遭受情绪化的攻击。“傅高义戴着玫瑰色的眼镜打量日本。”“傅高义在日本的时间太长了。他失去了自己的客观性。”有时甚至会出现更恶毒的话语。
这也是我花了很长时间考虑如何来回应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我希望能引起深思熟虑的美国人的注意。我原本认为“日本是第一”,但后来决定更换这个标题,这个标题太过观点明确。我担心人们可能误会,认为我是在说日本已经成为最大的经济体,或者日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最后,我决定用《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作为完整的标题。我知道即便如此,也会冒犯到某些美国评论人士。但是我觉得这更加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本书的基本论点:鉴于自身局限性和体量,日本解决了自身问题,成功应对挑战,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但无论如何,有些美国人误会了。他们对我赞扬日本进行批判,并要我对日本人变得傲慢自大而负责。
显然,这些人只是读了标题,没有注意到我在文中指出了日本的局限性,并认为将日本模式进行“批发”“同化”是不恰当的。他们也同样没有意识到在这本书的日语版中,我写了一个非常强硬的序言,警告日本人要小心自大骄傲的危险。
我认为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者,一个世界主义的爱国者。在日本和美国,当人们简单地满足于阿谀奉承时,我常常批评这种心胸狭隘和自以为是。我在写书时,内心关切的是美国利益,我希望美国能做得更好,对来自日本的挑战能作出建设性的回应。
《日本第一》并不是我唯一的畅销书,但可能是最能反映“我”作为一个人的状况的著作。我看到自己人生中最基本的角色是帮助美国人树立起对亚洲文化的一种既抱有同理心又有现实主义的理解。我试着和外国人建立良好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去理解他们和他们的社会。然后我回到家就会说:“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帮助我们提高自身、改善社会。”
无论如何,执着地向人们说教要对外国人更有同理心、要改善我们的社会,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过去相信、现在也依然强烈地相信美国人能从日本人身上学到很多经验教训。我想,美国人可能难以接受要向一个曾在战场上被自己打败并在一九四五年后帮助重建的国家学习。但我觉得,美国人如能像日本强烈渴望学习西方那样向东方取经,一定会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