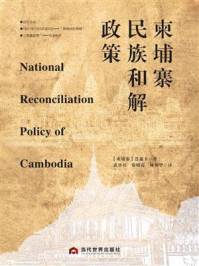摘要 :原生澳大利亚桉属尤加利(桉树)于晚清时期引入慈禧宫廷,后因速生、易栽、多用而在中国南方得以推广。随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高速发展人工桉林,环境问题逐渐显露,倒逼公众的生态意识,因“倒桉”“挺桉”引发的报道、口述、描述、数据等与超然的桉树文学书写构成一种“复调”的话语现象。本文拟通过爬梳澳桉引种史料和劝种话语,综述当代媒体的倾向性观点,分析公众对于单一桉林的感知,比较抗战期间旅居云南的学者和作家的桉树书写,试图呈现晚清以来中国如何接轨世界造林体系来应对自己的环境难题,如何因单一的桉树种植而卷入全球性生态同质世和文化后效之中,以及作为全球史实践一部分的桉树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甚至文学想象。
关键词 :物种交换 造林 桉树 生态争议 公众感知 林景 昆明
原生于澳洲的桃金娘科桉属植物(eucalyptus),音译为尤加利,是近900多个亚种、变种的总称。广为人知的桉树包括蓝桉、赤桉、细叶桉、大叶桉等,桉树最先是作为观赏植物由意大利公使于1890年引入晚清宫廷,
 后因“生长迅速、干材挺直,材质坚硬、利用价值宏大”
后因“生长迅速、干材挺直,材质坚硬、利用价值宏大”
 逐渐扩种到接近原种生境的广州(1890年)、福州(1894年)、昆明(1896年)、西昌(1910年)、合浦(1920年)等南方地区。
逐渐扩种到接近原种生境的广州(1890年)、福州(1894年)、昆明(1896年)、西昌(1910年)、合浦(1920年)等南方地区。
 桉树与另外两种更有气候普适性的优良行道树种(美国洋槐和英国悬铃木)构成清末民初中国城市植景的“异域”情调——北平五月槐荫绿海、沪上租界梧桐大道、昆明海埂桉堤。桉树见证了晚清以降,卷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如何在风景层面一步步全球化自己的都市植被(vegetation cover)。
桉树与另外两种更有气候普适性的优良行道树种(美国洋槐和英国悬铃木)构成清末民初中国城市植景的“异域”情调——北平五月槐荫绿海、沪上租界梧桐大道、昆明海埂桉堤。桉树见证了晚清以降,卷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如何在风景层面一步步全球化自己的都市植被(vegetation cover)。
作为世界三大最优速生树种之一,桉树的用途范围和经济价值远超杨树、松树,备受中国政治家、经济决策者以及林农学家的青睐。经由晚清外交家吴宗濂(1856—1933)引介、
 广东军阀陈济棠(1890—1954)倡导,
广东军阀陈济棠(1890—1954)倡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朱德委员长(1886—1976)等人力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朱德委员长(1886—1976)等人力推,
 加上侯宽昭、祁述雄、谢耀坚等几代林学家的努力,桉树渐由观赏植物、道路绿化树跃升为中国现代林业的主力树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基本国策、木材和纸浆巨大需求及延伸利益的驱动下,中国的桉林、桉园、防风桉林带等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到2015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桉树种植面积已达440万公顷,
[1]
分布于19个省600多个县市,超过印度,仅次于巴西。经过120年的引种、归化和推广,原为澳洲本土植物的桉树重塑了中国南方诸省甚至一些北方地区(如陕西汉中)的植物群落,在提升乡村经济水平,造福于国计民生的同时,永久性地改变了这些地区的生态系统,也留下了激发公众焦虑的环境问题。
加上侯宽昭、祁述雄、谢耀坚等几代林学家的努力,桉树渐由观赏植物、道路绿化树跃升为中国现代林业的主力树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基本国策、木材和纸浆巨大需求及延伸利益的驱动下,中国的桉林、桉园、防风桉林带等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到2015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桉树种植面积已达440万公顷,
[1]
分布于19个省600多个县市,超过印度,仅次于巴西。经过120年的引种、归化和推广,原为澳洲本土植物的桉树重塑了中国南方诸省甚至一些北方地区(如陕西汉中)的植物群落,在提升乡村经济水平,造福于国计民生的同时,永久性地改变了这些地区的生态系统,也留下了激发公众焦虑的环境问题。
一如公元前2世纪张骞等引入中国的伊朗苜蓿和葡萄,“哥伦布大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
[2]
转给我们的美洲作物烟草、玉米、甘薯、土豆、澳桉已经成为中国大地上的巨大存在,并入植物交换引动的文化汇流(transculturation),嵌入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潜入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想象——沈从文、林徽因、冯至、于坚、李浔等人笔下的尤加利或桉树书写佐证:一个群体从另外一个群体引入一种事物或植物,“人们会通过适应、改造记忆混合的方式让其本地化,从而适应自己的需求和境况”
 ,进而内化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进而内化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近20年来,澳桉引发的争议和舆情却是那些自汉朝以来源源不断输入中国的外来植物所未遭遇过的。其中部分争议是拜密集、交互、广泛的新媒体传播方式所赐,围绕“挺桉”“限桉”“禁桉”“复种”所展开的多方博弈和争议已经脱出林业、经济、环保范畴,变为公共话题甚至演进出社会事件,
 由此引发的公众口述、描述、评论、权威部门的政策背书、利益方的专业修辞或广告、生态学家的数据、环保主义者的抗议等与相对超然的文学书写构成了一种“复调”话语现象,各个声部互相搏斗、追逐、缠绕、分异、汇聚,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由此引发的公众口述、描述、评论、权威部门的政策背书、利益方的专业修辞或广告、生态学家的数据、环保主义者的抗议等与相对超然的文学书写构成了一种“复调”话语现象,各个声部互相搏斗、追逐、缠绕、分异、汇聚,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受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查尔斯·曼恩(Charles C.Mann)基于物种(植物)大交换的全球环境史和迈克尔·马德尔(Michael Marder)以植物为中心的跨学科批评(critical plant studies)启发,结合近年风景类型研究的新进展
 ,笔者开始:关注被誉为“造林嘉木”“未来之树”“绿色黄金”“奇迹树”的澳桉如何逐渐取代中国乡土树种,撑起1/4的中国森林工业;观察不断扩散北移的人造桉林如何削减东南沿海、西南山区、中南丘陵不同地区原生植物群落,将西方曾经垂涎的植物多样性天堂,从云南楚雄到广西十万大山再到四川金沙江河谷同质化(homogenize)为单调高产的全球性林业景观;
,笔者开始:关注被誉为“造林嘉木”“未来之树”“绿色黄金”“奇迹树”的澳桉如何逐渐取代中国乡土树种,撑起1/4的中国森林工业;观察不断扩散北移的人造桉林如何削减东南沿海、西南山区、中南丘陵不同地区原生植物群落,将西方曾经垂涎的植物多样性天堂,从云南楚雄到广西十万大山再到四川金沙江河谷同质化(homogenize)为单调高产的全球性林业景观;
 追踪澳桉如何被各种传媒拽进公共话语空间,渐渐被描述为“抽水机”“吸肥器”“霸王树”“灾难树”“亡国树”,这在唤醒公众的生态意识同时,又引发桉树学家的集体“焦虑”,担心媒体与公众共谋的“社会偏见”将会危及中国的木材安全;思考中国文学家对外来桉树的想象与澳大利亚的本土桉树崇拜是否有共通之处?抑或大相径庭?各自的想象和表述在一部全球视野的桉树文化史里具有何种意义?
追踪澳桉如何被各种传媒拽进公共话语空间,渐渐被描述为“抽水机”“吸肥器”“霸王树”“灾难树”“亡国树”,这在唤醒公众的生态意识同时,又引发桉树学家的集体“焦虑”,担心媒体与公众共谋的“社会偏见”将会危及中国的木材安全;思考中国文学家对外来桉树的想象与澳大利亚的本土桉树崇拜是否有共通之处?抑或大相径庭?各自的想象和表述在一部全球视野的桉树文化史里具有何种意义?
在有限篇幅里,本文暂且锁定四个方面:爬梳澳桉引种史料和劝种话语;综述当代媒体的倾向性观点,分析公众对于单一桉林的感知;比较抗战期间旅居云南的学者和作家的桉树书写,试图呈现晚清以来中国如何接轨世界造林体系来应对自己的环境难题,如何因单一的桉树种植而卷入全球性生态同质世和文化后效之中;以及作为全球史一部分的桉树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甚至文学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