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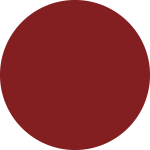
(ix)初版于1957年、如今整整40周年后再版的《国王的两个身体》,面世时的反响可谓即时而强烈。两篇书评一,篇由彼得·雷森伯格(Peter Riesenberg)撰写,另一篇由威廉·邓纳姆(William Dunham)撰写,都在开篇直抒胸臆——坎托洛维奇教授“写就了一部伟大著作”。
[1]
邓纳姆接着继续就坎托洛维奇的方法(主张从都铎王朝时期国王两个身体的已知学说,回溯至其幽晦未明的中世纪先声),与弗里德里希·威廉·梅特兰在《末日审判书及其他:英格兰早期历史中的三篇论文》中所运用的方法进行比较。
 梅特兰的这部著作,作为曾出版过的六七部历史撰述和概念诠释方面的佳作之一,是《国王的两个身体》恰当的参照对象;邓纳姆企盼其读者能够欣赏坎托洛维奇那同样大胆的探索。
梅特兰的这部著作,作为曾出版过的六七部历史撰述和概念诠释方面的佳作之一,是《国王的两个身体》恰当的参照对象;邓纳姆企盼其读者能够欣赏坎托洛维奇那同样大胆的探索。
 在雷森伯格看来,《国王的两个身体》“可能是有关中世纪政治思想史最重要的著作,无疑是过去几代人相关著述里最为瞩目之作”。
在雷森伯格看来,《国王的两个身体》“可能是有关中世纪政治思想史最重要的著作,无疑是过去几代人相关著述里最为瞩目之作”。

(x)这样的溢美之词几乎成为共识:“这部杰作”(celivremagistral);“自近一个世纪前弗里兹·科恩(Fritz Kern)的《神恩与反抗权利》( Gottesgnadentum und Widerstandsrecht )问世以来对中世纪王权历史研究最重要的贡献”“;这项伟大的研究”。 [2] 德国评论者中最受青睐的一个词是“钦佩”( Bewunderung );坎托洛维奇写下了一部“奇迹”。 [3] 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反响。雅各布(E.F.Jacob)在1958年8月19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中赞叹不已:“他写下了一部多么了不起的著作啊!”虽不是盛誉却也不乏褒扬之情的杰弗里·巴拉克劳(Geoffrey Barraclough)在《观察家》( Spectator )上发表文章,对该书副标题“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的精当性作了深入思考。在他看来,其他学者甚至其他评论家都引人误解、过于理性化地称作“中世纪政治思想”的东西里,这一副标题抓住了它虔敬至诚的且归根结底乃形而上的方面(神学)。 [4]
当然,也有一些诫防之言。并非所有评论家都喜欢坎托洛维奇“政治神学”这一用语, [5] 有人把这一用语与德国具有纳粹倾向的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对独裁主义的描述和支持联系了起来。 [6] 英国某些关注日常问题的历史学家想要更多了解,国王两个身体的学说是如何直接影响了都铎王朝法官接手的法院案件。法官们把国王设想成既是自然身体、有朽身体,同时又是政治身体、不朽身体,这对于日常生活来说重要吗?对这些批评者而言,坎托洛维奇这部著作的内容,有点过于沉湎去恢复高度思辨的修辞笔法,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有所转圜,热情称颂这部著作。 [7]
评论者们的另一同感是,该书整体上看有不少可谓冗繁之处(用一位评论者的词来说,“过度”[nimiety])。 [8] 细读《国王的两个身体》,其中包括了十余项研究,均生动有趣但又彼此联系松散,总体来看说服力不足。读这本书就像是要去破解一个“万花筒”,一位同时也持褒赞态度的评论家抱怨道。 [9] 一本“丰富而混乱的书”,贝里尔·斯莫利(Beryl Smalley)埋怨说,读到最后,“我感觉就像用了一顿没有面包光是果酱的餐之后那般反胃”。 [10] 或用理查德·索森(Richard Southern)很容易引起共鸣的话来说,“与坎托洛维奇教授一起漫游中世纪探寻国王的两个身体,就像夜幕下沿着未知道路行走在一个陌生的乡村:光亮断断续续,虽有时也照得通明,乡村轮廓却仍只是依稀可辨”。但他又补充说,“这种经历给人留下的印象,比许多次白天行走在偏远道路上的旅行要更加深刻”。 [11]
本书在讨论实践政治方面有所欠缺(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种批评
 ),书中内容过于冗赘,但在教皇制度的论述上却略显单薄,一位研究中世纪教会的专家如是评述;
[12]
除此之外,多是对作者学识渊博的由衷赞扬和叹服,赞叹他从都铎法学家那里一路长途跋涉,溯源之旅横贯了整个中世纪和古代后期。
[13]
坎托洛维奇是如何写就了这样一部既专精又广博的著作?
),书中内容过于冗赘,但在教皇制度的论述上却略显单薄,一位研究中世纪教会的专家如是评述;
[12]
除此之外,多是对作者学识渊博的由衷赞扬和叹服,赞叹他从都铎法学家那里一路长途跋涉,溯源之旅横贯了整个中世纪和古代后期。
[13]
坎托洛维奇是如何写就了这样一部既专精又广博的著作?
(xii)近来,一些有学识的崇拜者们,其中不乏奇思异想者,一再为这位恩斯特·H.坎托洛维奇(Ernst H.Kantorowicz)的生平故事著书立说。
[14]
他的故事有时还不免让人惋叹。按旧时欧洲所理解的“极端保守派”一词来看,坎托洛维奇算得上一位,他也是一个不信教的犹太人,可能还是个无神论者,沉浸于名噪一时的中世纪宗教和社会的有机统一体论。
[15]
身为施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圈子的一员和1933年这位大师葬礼上的扶柩人,坎托洛维奇在许多方面表现得是位唯美主义者,带有当时看来稀松平常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实为不幸的一些种族偏见。
 1895年,他出身于波森(Posen)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在德国军队服役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战后,他倾力于对德国“共产主义者”的镇压并再次负伤。
1895年,他出身于波森(Posen)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在德国军队服役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战后,他倾力于对德国“共产主义者”的镇压并再次负伤。
尽管他曾经试着研究东部地中海的经济史,不过后来还是决定专注于中世纪史。他第一部重要著作是皇帝腓特烈二世的传记。传记于1927年出版,没有注释,强烈表现出了近于小说的演义风格。它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之后受到纳粹追捧,但却引起了学界传统卫道士疾风骤雨式的批评。坎托洛维奇以几种方式作了回应,其中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出版了一部对史料进行补充的续卷,即使这样做并未回答完对手提出的所有批评,但至少证实了他对史料确如其自己所言是了然于胸的。

(xiii)坎托洛维奇于1930年在法兰克福接受教职之后,似乎要就此从事较为传统的大学教授工作了,但此时的德国已是政治堪忧、形势日蹙。这位有着贵族气质的激进保守主义者,既憎恶“国家社会主义”及其追随者强烈的反犹主义,也憎恶他们不得要领而且庸俗下作的粗暴不羁,所有这些情绪侵蚀了他对德国政治文化的本有尊重。1934年,他拒绝宣誓效忠阿道夫·希特勒,放弃了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学术生涯,选择退隐。之后他陷溺于忧郁,并在此期间汇编和翻译了大量英国诗歌,以“死亡、痛苦和变形”为主题(这是他自己为诗集拟定的题目)。不过,直至1938年他才动身离开德国,再未踏足这片土地。 [16]
幸运的是他在美国找到了一块安全避难处,伯克利提供给了他一个职位,使他得以安顿下来撰他的第二部书《君王颂:礼拜呼颂和中世纪统治者崇拜》( Laudes Regiae:A Studyin Liturgical Acclamations and Mediaeval Ruler Worship ,Berkeley,1946)。但几年之后坎托洛维奇离开了西海岸,当时他和其他加州大学的几位教员拒绝向麦卡锡主义宣誓效忠。麦卡锡反共立场那时在国家机构中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校务委员们要求坎托洛维奇发表的声明,其实质内容并不是真正令他反感的;他的反共产主义倾向至少可追溯到接踵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自己那段街头巷斗的日子。但他认为反共宣誓的要求是对学术自由的侵犯,他奋起抵制,竭尽所能寻求支持,尽管最终效果平平。
坎托洛维奇很幸运地又找到了一块自己的立足之地,因为他不久便收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给他的一个永久职位,还享有工作时间方面的特权,何时在大学开设研究生课程班由他自己决定。从1951年一直到1963年9月9日去世,他从事研究工作的地方正是普林斯顿。《国王的两个身体》这部著作,与《君王颂》一样,重建了中世纪思想家关于有机体整体所阐发的一些构想。不过,坎托洛维奇逐渐将他的颂扬对象指向了那些在有机体社会形态中体现出宗教理想的人物。尽管腓特烈二世仍然令他着迷,但坎托洛维奇极为欣赏的人物形象——比如,在《君王颂》中——已不是那位神话般的英雄皇帝腓特烈二世,而是腓特烈二世那位圣人般的同时代人兼“对手”:法兰西的路易九世。 [17]
(xiv)1962年秋,坎托洛维奇在他最后一次研究生课程班上研讨了但丁的《帝制论》(
De
Monarchia
)。在研究生课程班一位成员的简短叙述中,作者回忆了坎托洛维奇的方法,尤其是他对学生所提学术性较强问题的回答。他会准备一张便签卡片,不管他被问到的是什么问题,卡片会将提问者引导至相关的文本和学术讨论现状。“几本参考书目里肯定会提到《国王的两个身体》,不过很少会直接引文本内容。……坎托洛维奇的研究是依据脚注进行的,那是他学识的储藏库。他一次又一次把我们送到那里,我们很快都对他使用的史料心生敬意,因为那是学问的宝藏,而且至今仍然是。”

如果要对这段引文内容加上着重号,人们理所当然可能会加在“仍然”这个词上。对《国王的两个身体》最初的极大热忱,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延续着。
[18]
弗里德里希·贝特根(Friedrich Baethgen)在他纪念坎托洛维奇的著作中的公允评价,如今仍然广受认可:对所有“”国家理论(
Staatstheorie
)和政治神学方面的研究而言,《国王的两个身体》一直是而且会继续是不可或缺的。
 这并不是说这本书已经达到了无可挑剔的状态。
[19]
对于初学者甚至往往包括高级研究学者来说,弄清其中的一些论证总归是有难度的事情,更不用说把它们编入一个连贯的整体中,纵然有先前学者在这方面所做努力的便利条件。
这并不是说这本书已经达到了无可挑剔的状态。
[19]
对于初学者甚至往往包括高级研究学者来说,弄清其中的一些论证总归是有难度的事情,更不用说把它们编入一个连贯的整体中,纵然有先前学者在这方面所做努力的便利条件。
(xv)然而,对大多数读者而言,《国王的两个身体》精彩讨论过的各种各样的主题,它们的奇绝魅力,以及注释所带给人的喜悦,依然如故。当社会史学在20世纪60—70年代臻至鼎盛时,这样一部总体来说高度思辨的历史,或者至少是端赖于传统观念史资料的著作,似乎本不可避免地会被搁置在略远离中心舞台的位置。但是由于坎托洛维奇为自己的主题加入了艺术的、辐散式的和象征的取向,读者们便决不会认为《国王的两个身体》“仅仅”是一部观念史。因此,该书仍然占据了很多学者的历史想象。 [20]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社会史因其他学科、特别是文化人类学而变得愈加丰富的时候,甚至出现了对《国王的两个身体》一波更大的兴趣浪潮,这似乎可从译本新增之数得到合理说明:1985年的西班牙语译本;1989年的意大利语和法语译本;1990年的德语译本;1997年的葡萄牙语和波兰语译本。
1957年,恩斯特·坎托洛维奇出版了一部著作,这部著作一直引导着几代学人索解中世纪政治神学那些晦涩难解之谜。《国王的两个身体》不愧为一位伟大学者的珍贵遗产。它也依然是一部激荡人心、不断令人获益的著作。
威廉·切斯特·乔丹(William Chester Jordan)
新泽西,普林斯顿
1997年3月
[1] 邓纳姆的书评可见于 Speculum 33(1958):550 553;雷森伯格的书评可见于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2(1958):11391140。
[2] 按引用的先后顺序,所引评论者及其文章收录情况如下:Robert Folz in Revue d'histoire et philosophie religieuses 38(1958):374378;NormanCantor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4(1958):8183;R.E.Mc Nallyin Journalof Religion 38(1958):205。
[3] WiebkeFesefeldtin Göttingische Gelehrte Anzeigen 212(1958):67;Rudolf Kloos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88(1959):364;还有Friedrich Kempf,“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Einwirken der Theologie auf die Staatslehre des Mittelalters(Bericht über ein neues Buch)” Römische Quartalschrift 54(1959):233。尽管费瑟菲尔德(Fesefeldt)希望该书的德译本尽快面世,但是据我所知,至1990年尚无德译本出现。
[4] Spectator ,1 August1958,p.171.为 Review of Metaphysics 撰文的评论者——有可能是罗伯特·特雷德韦尔(Robert Tredwell)(但也可能是位助理编辑),认为本书在讨论对他而言也算一个形而上学主题的研究上是“引人入胜的”。
[5] 可参见恩斯特·鲁宾斯坦(Ernst Reibstein)的评论,载于 Zeitschrift der Savigny 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GermanistischeAbteilung)76(1959):379。鲁宾斯坦的冷言评论在弗雷德里希·贝特根(Friedirch Baethgen)看来没那么重要,见后者的“Ernst Kantorowicz 3.5.1895 9.9.1963,” Deutsches Archiv 21(1965):12 n.19,“wird,auch wenn die darin erhobenen kritischen Einwände sich mehr oder minder als stichhaltig erweisen sollten,der Bedeutung des Buches im Ganzen keineswegs gerecht”(“尽管其中提出的批评反对意见多多少少会有一定道理,但他没有公正看待这部著作整体的意义”)。
[6] 参见阿兰·布若(AlainBoureau)在 Histoire d'un historien:Kantorowicz (Paris,1990),pp.162 167中的讨论。
[7] 持这种批评观点的人当中有邓纳姆和诺曼·坎托尔(Norman Cantor)(见注1和5),前者态度温和,后者语气尖刻;另外还有埃瓦尔特·路易斯(Ewart Lewis)的观点,录在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73(1985),453455,以及科斯坦佐(J.F.Costanzo)的观点,录在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321(1959):203 204。
[8] “有点过度”的说法,参见奥夫勒(H.S.Offler)的评论,载于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75(1960):295298。
[9] Cecil Grayson, Romance Philology 15(1961 1962):179 184。格雷森激赏《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书中论但丁的章节;克罗斯(Kloos)(见上面注6)也称那一章是“一篇精湛的但丁诠注”(“ein meisterlicher Danteexkurs”)(第363页)。
[10] Past and Present ,No.20(1961),pp.30 35.
[11] Journal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10(1959):105108.
15雷森伯格(上面注1)和佛尔兹(Folz)(上面注5)在这一点上就不会觉得有问题。
[12] Michael Wilks in Journalof Theological Studies 10(1959):185 188.参较Kempf,“Untersuchungen,”pp.213 214,文中谈到了坎托洛维奇对教会学的论述。
[13] 除已经援引的评论外,另外还有R.J.Schoekinthe Review of Politics 22(1960):281 284,以及Hubert Dauphin in the Revue d'histoire ecclésaistique 55(1960):176 179。
[14] 后面的故事梗概,既包括细节也包括总体阐释,来自以下材料(以出版先后为序):Yakov Malkiel,“Ernst H.Kantorowicz,”in On Four Modern Humanists:Hofmannsthal , Gundolf , Curtius , Kantorowicz ,ed.ArthurEvans,Jr.(Princeton,1970),pp.146 219;David Abulafia,“Kantorowicz and Fredriek II,” History 62(1977):193 210(重刊于作者的《意大利、西西里和地中海:11001400》[ Italy , Sicily andthe Mediterranean1100 1400 ],[London,1987],No.II,在“Addenda et Corrigenda,”p.1中有一份重要的文献补录);Boureau, Histoire d'un historien ;以及NormanCantor, Inventing the Middle Ages:The Lives , Works , and Ideas of the Great Medievali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1991),pp.79 117。
[15] 有关他身上可能的无神论,我采信了Boureau, Histoires d'unhistorien ,p.137。
[16] Boureau, Histoire d'unhistorien ,p.124.
[17] Laudes Regiae ,pp.3 4,“正是圣路易,在各方面丰富了那恩典的宝藏,所有他的继任者会在此恩典宝藏的基础上繁盛起来。正是在他那里,王权被他那个时代的圣灵派和象征派抬升到了超验层面;反过来他将天国的氤氲渺渺施布于自己国土之上……可以说,他已将自己的王政交付给了作为凯旋者和君王的基督,相比于其他任何国王,他自己在地上可能更为完美地代表了基督。”
[18] 渡边守道(Morimichi Watanabe)评论了1983年再版的平装本,其中一段对最初及后来的一些反响作了综述; Church History 52(1983),pp.258 259。
[19] Malkiel,“Ernst H.Kantorowicz”,pp.214 215中有一些苛刻的评述。在马尔基尔看来,《国王的两个身体》由于缺乏总体的内在连贯性,所以他相信书中不会有什么见地,就像是一次“stubborn retreat from monumentality”(“从鸿篇巨作中执意的撤退”);我不知道他此言何意。安东尼·布莱克(Anthony Black)一篇不逊和反传统的文章,题为“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Rousseau:Philosophy,Jurisprudence and Constitutional Theory”,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1(1980):147 n.13,当布莱克称坎托洛维奇的著作是“博学之混乱的杰作”时,不过是在重复上一代人的保留意见。
[20] 给该书做一次引证索引检索,比如在《艺术人文引证索引》( 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Philadelphia,1976])上做,尽管可能不是最好的证据,却可显示出对本书连续性的而且相对高频率的援引率。看过引用记录,我发现本书似乎“胜过”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权威之作《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15581641,Oxford),其初版时间是1965年;而且本书的引用记录紧随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综论性著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àl'époque de Philippe II,Paris),其初版时间是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