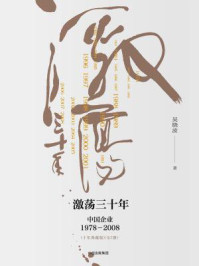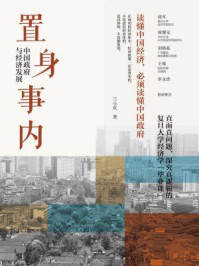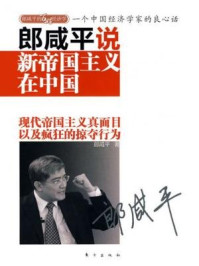中国农家将“农”作为自己关注的中心,将农看作一切行当和职业的基础部门和国家的基础,认为工、商会妨碍农业,由此建构起了自己的重农思想体系。重农意识是中国农家的又一个基本特征。《吕氏春秋》第一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农本商末的问题。
中国的传统看法是农业为本、工商为末,采取的基本做法是重本抑末。那么,农家究竞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管子》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重本抑末的。《管子》的作者进一步重申了重农的意义,认为要想国库充盈,其根本的出路在于“务五谷”“养桑麻”“畜六畜”。“务五谷”就是致力于发展种植业(狭义的农业),这样,人们的吃饭问题才能解决;“养桑麻”就是致力于发展家庭手工业,“畜六畜”就是致力于发展养殖业,而这些都是广义农业的构成部分,这样,人们才可以解决其他生活问题。总之,《管子》的作者将“耕农树艺”看成“财用足”的基本前提和保证。
《吕氏春秋》则与之不同。《吕氏春秋》的作者将劝民道德教化作为农本商末的根本目的。他们指出,古时候圣王引导他的百姓的做法,首先是致力于农业。使百姓致力于农业,不仅仅是为了地里的出产,关键的问题是务农可以陶冶百姓的心志。使百姓致力于农业,他们的思想就会淳朴,就容易为统治者役使;百姓容易役使,国家就会安定,君主的地位就会尊贵。因而,重农有两大好处:一是使百姓致力于农业,他们的举止就会持重,举止持重就能减少私人交谊,少了私人交谊就能不为私,这样,公法就能够得以确立,民力也能够专一。二是使百姓致力于农业,他们的家产就会增多,家产多了就会害怕迁徙,害怕迁徙就会老死故乡而没有别的考虑,这样就可以把百姓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与此相适应,假如采取轻农的政策和措施的话,百姓就会舍弃作为根本的农业而从事其他行当;百姓从事其他行当,就会不听从统治者的命令;百姓不听从命令,就不能依靠他们防守,不能依靠他们攻战,这样,国家社稷就有了危险。因而,轻农有两大害处:一是,如果百姓舍弃农业而从事其他行业,他们的家产就很简单,家产简单就会随意迁徙;百姓随意迁徙,国家有难时,百姓就会远走高飞,没有安居之心。二是,如果百姓舍弃农业而从事其他行当,他们就会玩弄计谋;喜好玩弄计谋,他们的行为就会诡诈多变;行为诡诈多变,他们就会巧妙地钻法令的空子,从而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样,《吕氏春秋》的作者不但肯定了重农的意义和价值,而且认定了工、商为末事;不但将农本和商末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从理论上对重农抑末的问题进行了说明。这样,《吕氏春秋》就使重农本商末的主张上升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高度,成为后来一切农本商末理论、主张和政策的基础。
农家主张重农抑商,但并不是要否定工商活动存在的价值,他们只是要求从国家意志的高度来缩小和控制工商活动的范围,使工商活动不得成为农事活动的障碍。
《吕氏春秋》的作者提出了社会分工协调说。许行并不否认社会分工,他看到了社会分工在商品互通有无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他没有谈及分工如何协调的问题,只强调农本商末。《吕氏春秋》则进一步肯定了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认为凡是成年以上的百姓,就应分别归属于农、工、商三种行当。农、工、商三种社会分工各有所司,“农攻粟”(生产粮食),“工攻器”(制作器物),“商攻货”(经营货物)。这三种行当不能互相僭越。假如百姓不尽力于耕桑,不养殖家畜,农、工、商三者的互相僭越就会达到顶峰,这就叫作背离了根本,违反了社会分工准则,国家就难以为治,甚至会毁灭丧亡。因此,这三种行当必须协调一致才行。如何才能协调好社会分工的关系呢?关键的问题是要做到行事与农时相适应,也就是说其他行当不能妨碍农时。在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农事紧要关头,不得进行工商活动,工商活动必须在农闲时节进行;假如行事与农时不相适应,就称作“大凶”。这样,《吕氏春秋》的社会分工说就在农本的基础上通过协调时令活动的方式将各种行当统一起来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不失为明智之举。
许行主张等物交换说来避免商业投机,这种空想的绝对平均主义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吕氏春秋》的作者则更明智和务实,在肯定商业活动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同时,他们主张通过统一度量衡的做法来避免商业投机。具体做法是:在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两个月由国家来统一组织进行,主要内容是划齐度量单位、统一衡称、平整量器、修整溉具。这可能与吕不韦出身商人有关,也开了秦“车同轨、书同文”的先河。因此,与许行的主张比较起来,这是一个进步。
农家所提出的这些抑商的具体措施,大都变成了现实。
《吕氏春秋》的作者在两处引用了“后稷”,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场,肯定自己是属于重农学派的。一处是在《上农》篇中引用“后稷”的话,声称让大家耕田织布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道德教化;另一处是在《任地》篇中引用“后稷”的话,提出了利用和改造土地的十个技术问题(例如:你能把洼地改造成高地吗?你能把干燥的土壤除掉而代之以湿润的土壤吗?等等)。这样,我们就可以肯定:农家并没有绝灭,而是在《吕氏春秋》中得到了记录,而且发扬光大了。《吕氏春秋》第一处引用“后稷”的话,肯定了重农学说的社会政治目的,这是中国历史上采用重农政策的基本依据;第二处引用“后稷”的话,使农家开始了一个转型过程,也就是说,农家通过对农业技术问题的探讨而使自己保留了下来。这样,通过这两方面的工作,农家既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申明自己是属于后稷学派的(神农学派、重农学派);同时,又获得了为统治者所认可的形式,推动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样,《吕氏春秋》就在中国农家的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而悲壮的一页。说它辉煌,因为它终于使农家思想构成了一个系统;说它悲壮,因为从此以后,中国农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文化流派隐退到了农学家之中。因而,《吕氏春秋》在中国农家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吕不韦本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家,“真的,吕氏本人很有意思,他的出身虽是阳翟大贾,而他却是一位重农主义者,这是值得注意的事”
 。当然,这只是从思想集成意义上讲的。
。当然,这只是从思想集成意义上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