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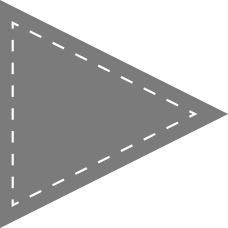 第一节
第一节
1949年至1978年,是中国法制史学学术史上的一段低潮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波动,中国法制史学也经历了许多跌宕浮沉。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与1966年至1978年的两个阶段。
1949年至1966年这一阶段,随着和平的来临,社会经济恢复发展,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政策的提出,中国法制史学发展得到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在研究成果方面,这一阶段出现了数量较多的成果;在教育方面,中国人民大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法制史研究生,充实了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科研实力,各大院校都编著了中国法制史教材和讲义,推动了中国法制史学知识普及。然而,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阶段的中国法制史学,在时局变化的影响下,发生了许多变化。
在新中国成立前夜的1949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指示,在解放区内全面废除国民党的旧法律制度,要求各级司法机关要以“蔑视和批判”的态度,去批判国民党政权颁布的“一切反动法律、法令”。
 于是,一场批判旧法的运动迅速展开。这场运动使包括学术界在内的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对旧法的态度产生巨大变化,批判旧法成为中国法制史的主流观点。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了不少批判旧法律制度的文章。它们批判旧法律制度是“反人民的反动法律”,认为这些法律“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
于是,一场批判旧法的运动迅速展开。这场运动使包括学术界在内的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对旧法的态度产生巨大变化,批判旧法成为中国法制史的主流观点。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了不少批判旧法律制度的文章。它们批判旧法律制度是“反人民的反动法律”,认为这些法律“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
 这种批判尤其表现在对近代法制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南京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研究上。在这批判浪潮下,当时的中国法制史学没有辩证地看待旧法,把旧法律制度中一些进步的、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法律制度和原则同它们的本质区别开来。在批判旧法律的同时,主张法律的继承性的言论也被当作“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进行批判,它们认为,法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不能继承的”。
这种批判尤其表现在对近代法制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南京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研究上。在这批判浪潮下,当时的中国法制史学没有辩证地看待旧法,把旧法律制度中一些进步的、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法律制度和原则同它们的本质区别开来。在批判旧法律的同时,主张法律的继承性的言论也被当作“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进行批判,它们认为,法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不能继承的”。
 这些观点对以后的中国法制史学研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这些观点对以后的中国法制史学研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批判旧法的同时,建立在旧法基础上的旧法学也遭到了弃置,旧法学著作遭到批判,传播受到限制。民国时期的法学家或是失业,或是被迫改行从事其他研究,部分民国时期从事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学者转投中国法制史研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有戴克光、吴恩裕等。
旧法学被批判打倒后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这为苏联法学的进军提供了大片的空间。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苏友好的大环境下,苏联派出大量专家援助中国建设,其中也包括为数不少的法学专家。这些苏联专家当时主要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当时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工作母机”,不少中国法制史研究人员在校时都上过苏联专家讲授的课程,其中的个别人还得以进一步赴苏联留学深造。在当时,中国法制史的学科定名也曾引起一场争论,学者对中国法制史学科名称是采用清末以来一直使用的旧称“中国法制史”还是采用苏联式的“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在最后,苏联式的学科名称——“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明显占了上风。当时中国法制史的教材也是按照苏联法制史教科书模式编写的。
依靠自力更生和部分苏联法学的影响,新中国逐步在旧法学的废墟上建立了新中国的法学。新中国的法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法学,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和生产力决定论成为中国法制史学界的指导思想。从这时候开始,中国法制史学不再把法律视为一种独立的、永恒的存在,而是把它看作阶级统治的工具,一种上层建筑。法律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社会的消亡而逐步消亡。法律被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也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
在研究方法上,阶级分析成为当时中国法制史学的主导研究方法,在这种研究方法影响下,确定历史上法律制度的性质,成了当时中国法制史研究最热衷的问题,质量并不佳:这些作品的论证模式都是以论带史,经常大段引述领导人的讲话或是马列经典著作的论述,史料只是处于一个从属的位置,其结论往往也是千篇一律,成果质量不能算高。
这一阶段的中国法制史研究的这些变化,与其说是中国法制史自身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社会政治因素影响下的产物。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中国法制史学抛弃了过去的研究基础,走上了一条与此前截然不同的道路,这种转变对后一个阶段乃至更往后时期的中国法制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阶段爆发“文化大革命”,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事业造成巨大冲击。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间,随着国家机构的瘫痪,立法、执法、司法工作全都陷入停顿,法学教学与研究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在这种环境下,中国法制史学学术遭受严重打击。这种打击表现在教学与研究两个方面。在教学方面,法制史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被迫停止。“文革”期间,除了西南政法学院和吉林大学的法律系没有被撤销之外,全国其他所有的政法院校都被解散,未解散的院校的教学秩序也受到严重的干扰。中国法制史教育全面陷入停顿。
在研究方面,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也陷入了停滞。在1966年至1971年这5年间,没有一篇有关中国法制史的论文发表,也没有一部中国法制史的著作、教材编成出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上海市法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等研究机构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人员被调离本职,改做其他研究工作。1972年之后,随着国家的部分整顿,历史学研究得以部分恢复,中国法制史研究在部分领域得以重新开展。但是,由于受到“批儒评法”运动的影响,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受到严重的干扰。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下,法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遭到严重夸大,儒家思想则受到错误批判,所有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都被解读为“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
总的来说,由于扭曲的现实的影响,1966年至1976年这10年间的中国法制史学基本上是一片萧条,并无建树。中国法制史研究这种萧条局面的逐步改观,要到“文革”结束之后。
1976年,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寒冬过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迎来局部复苏。许多中国法制史科研人员回到了自己的研究岗位,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新的科研人员也加入中国法制史的研究队伍,壮大了中国法制史研究人员的阵容。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部分研究人员开始反思批判“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恶劣影响,“批儒评法”等“左”倾错误思想的负面影响逐步被清除。随着国家的法制建设重新开展,研究中国法制史,为中国法制建设事业服务成为中国法制史学界的共识,因此1976年之后的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重心重新回到中国法制史的本体问题——法律制度研究上来。相较于以前的研究成果,1976年以后的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成果中,研究法制史的具体问题的成果逐步多了,其问题意识更加明确。
随着法学院校的恢复,法学教育得以重新开展,中国法制史的课程又重新回到大学的课堂,成为法学院学生的必修课程。中国法制史的教材讲义也得以重新编写出版,这些“文革”后出版的中国法制史教材讲义和参考资料的名称基本上都改变了50年代以来沿用的“国家与法的历史”这一称呼,重新称为“法制史”或“法律制度史”,其写作范式也一改过去苏联式的“国家与法的历史”模式,回到以法律制度为主的模式上来。此外,1978年,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法律史研究生,其中的一些研究生成为了八九十年代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主力军。
但是,在“文革”结束后的两年中,“左”倾错误的影响还没完全清除,整个国家还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受制于社会政治环境,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制史学的复苏是有限的,中国法制史学真正迎来春天,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