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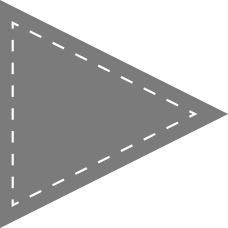 第六节
第六节
前面已经对1949年至1978年中国法制史学的成果、重大事件、重大争鸣和研究人员群体进行梳理,已勾勒出这个时期中国法制史学的基本面貌。本节将探讨这一时期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特点,同时对这一时期研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反思。
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和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在年代上相去不远,而且两者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把两个时期的中国法制史学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可以发现,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法制史学有以下两个突出的特点。
与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相比,我们可以发现1949年至1978年中国法制史学的另一个特点: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马列主义著作和领导人论述占有重要地位,常常被引用为自己观点的例证。
这种特征在1949年之后就已经出现。最初引用较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的论述。以经君健的《明清两代“雇工人”的法律地位问题》为例,该文39个引注中,引用马列主义经典的注释就有6个,占到了近六分之一。这些引注多数分布在论文的首尾两端,该文的前四个引注主要引用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引用的目的主要是说明资本主义自由雇佣的关系,特别是“自由”一词的含义。该文最后两个引注是列宁的著作,主要是阐明“阶级”这一词的含义,由上可见,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这里变成了问题的来源,文中引用的一切论证都是为了证明这些经典著作里面的论述而存在。
到了“文革”时期,这种引用扩展到了领导人的语录。在“文革”时期的一些有关中国法制史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成果在开篇和结尾必定引用一段领导人的语录,并且这些语录常常使用黑体字,被加粗,有时候还加上了着重号,显得十分显眼。这些领导人的语录常常作为整篇文章的中心论点的出处,论证都是围绕其展开。
这种马列主义著作和领导人语录在论文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现象,体现了当时法制史研究中一种“以论带史”的倾向,先抛出观点,再以史料作为佐证,而非从史料中引出论点。“以论带史”正是那个时代社会政治现实的反映。不论日常生活,还是学术研究,都特别强调观念、立场、路线的重要性。而最正确的理论莫过于马列主义著作和最高领导人的语录,所以马列主义著作和领导人的语录常常成为论之所出,史料成为证明其正确的依据。这种现象正是在“左”倾的大环境下,当时学术活动政治化的产物。
与20世纪80年代比较,我们可以发现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法制史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在学科关系上,1949年至1978年中国法制史学表现出一种与历史学特别密切的关系。
在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法制史学与历史学的这种联系紧密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如前文所述,研究人员群体中,历史学专业出身、研究领域在历史学的学者从事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有不少,而且他们研究的成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比法学专业出身的学者差,最典型的例子是王永兴,他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唐史专家,他曾在五六十年代发表过多篇有关唐律的论文,对唐律的性质和唐律“同居相为隐”原则有一定的研究。第二,在这一时期中国法制史也常常参与到史学问题的讨论中。新中国成立之初,史学界曾有关于“五朵金花”问题的争论,一些研究人员试图从法制史的角度去探讨这些问题,其中的典型代表有侯外庐和经君健,侯外庐试图从法制史的角度去讨论中国古史分期和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经君健试图从法制史的角度去探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三,在一些非常时期,法学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中国法制史依靠着历史学得以存续和发展。在“文革”时期,整个法学研究处于瘫痪状态,许多专门从事法制史研究学者被调往历史学研究机构,在那里得以部分继续从事中国法制史研究,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法学》和《政法研究》等法学专门学术刊物停办,大部分的中国法制史论文都是通过《历史研究》《历史教学》等历史学的期刊发表的。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法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国法制史学应该与法学和历史学之间有紧密的联系。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法制史学与历史学这种特别紧密的联系,有着特殊的意义。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使法学研究举步维艰,在“文化大革命”中,法学研究更是一度停摆。虽然历史学也受到了“左”的冲击,但是历史学的研究尚未全部停顿,还可以进行部分研究,与历史学保持紧密的联系,保留下了将来中国法制史学发展的种子。也正是因为与历史学的这层紧密关系,使得中国法制史能够在“文革”结束后较早得以恢复,成为“文革”结束后最早恢复的法学学科之一。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到,尽管1949年至1978年和20世纪80年代在时间上相去不远,但是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法制史研究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法制史研究相比,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处于一个比较低潮的阶段。
纵观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法制史研究,可以发现它在对待传统法律的态度以及研究方法这两个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有一些值得我们反思,作为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镜鉴。
纵观1949年至1978年的中国法制史学,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制史学在研究中充满了“革命史观”支配下的政治化叙事。在“革命史观”的支配下,当时的法制史学把中国传统法律视为剥削阶级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工具,应该予以彻底批判。
这种全面否定、批判的态度既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同时也是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失去自信的产物。这种思潮挫伤了研究人员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积极性,对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法学众多学科中,中国法制史是唯一与传统法律挂钩的学科,如果传统法律一文不值,那么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价值又从何谈起。
钱穆先生曾说,一个国家在“知识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的历史应该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会认为本国历史是一种“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的东西,也不会认为“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也不会把现在的种种罪恶与弱点,全部“诿卸于古人”。
 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法律已经式微。研究中国法制史并不意味着是要事事以古为美,在今天复活那些早已走进历史的制度;也不是要证明某些现行制度古已有之,今天只是前人的翻版。而是客观地去审视这些传统法律在它们的时代的实施情况和效果优劣。这种“审视”不应是站在一个“历史的终结”去俯视过往的历史;而是用“温情与敬意”去理解历史,像演员一样,把自己融入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场景中,去品味社会的架构和人们的行动。从前人的一个个具体行动中逐步抽象出前人在处理类似问题时的智慧,与我们今天的行动形成观照。
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法律已经式微。研究中国法制史并不意味着是要事事以古为美,在今天复活那些早已走进历史的制度;也不是要证明某些现行制度古已有之,今天只是前人的翻版。而是客观地去审视这些传统法律在它们的时代的实施情况和效果优劣。这种“审视”不应是站在一个“历史的终结”去俯视过往的历史;而是用“温情与敬意”去理解历史,像演员一样,把自己融入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场景中,去品味社会的架构和人们的行动。从前人的一个个具体行动中逐步抽象出前人在处理类似问题时的智慧,与我们今天的行动形成观照。
尽管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法制史学还处于初生期,但是在那时的中国法制史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学科研究方法并存,并且相互影响、交织使用的场景。既有用西方法律分类体系去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陈顾远、杨鸿烈,也有运用传统史学方法去考据古律的沈家本、杨鸿烈,还有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从法律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法律的瞿同祖。
 正因为众多学者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从多学科角度去研究中国法制史,才造就了这一时期中国法制史研究繁盛的局面。
正因为众多学者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从多学科角度去研究中国法制史,才造就了这一时期中国法制史研究繁盛的局面。
即使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出冰期的中国法制史学也出现了多种学科方法并用的场景。除去基于规范分析和权利义务关系出发的法学方法与从史料分析和考据着手的传统史学方法之外,还有以田野调查为主要形式的人类学方法,着重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的比较法等方法。
然而在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中国法制史研究却呈现出成果十分有限的局面。除了在“文革”前有少数历史学和考古学学者运用过二重证据法等史学方法,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方法就只有阶级分析法一种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会有不同的思维定向、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制史著述机械地套用阶级分析法,因此,尽管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制史研究人员群体中有着来自各个学科的知识精英,但是这一时期中国法制史学研究成果的内容很不足。它们在选题时多数都是以分析某传统法典的阶级性质为主,论证过程常常是先大段引述马列经典著作和领导人的论断,然后中间引述一两段史料,它们得出的结果也是大同小异:认为这些法律是剥削阶级维护统治、镇压人民的工具。这一时期对法律性质的分析,超过了对法制史具体问题的探讨。这种机械地套用阶级分析法的做法,使得当时的中国法制史学俨然成了政治学的附庸,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开展。
中国法制史作为一门法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研究人员不仅有法学的专业素养,同时也要求研究者有一定的历史学功底。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法律都不只是纸上的文献,还是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简单描述一种纸上的规范,还应该深入地去分析这种规范与它背后社会的互动。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可以把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运用在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社会学中定性研究的方法,特别是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在法制史研究中已经被广泛应用,但是定量研究似乎方兴未艾。法律史研究中有大量的司法判例、案卷档案等法律史史料。这些史料数量较多,作为样本有一定代表性,在整理这些史料的时候,可以将这些“概念化”“可操作化”,为其中的某些特定项进行编码和赋值,然后通过统计分析,去估量数据的规模、核心趋势和特征离散程度等,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得出明确、量化的而非笼统、抽象的结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中,除了田野考察可资利用之外,“深描”的方法也可以作为法制史研究的有益借鉴。正如莎翁所言,“寰宇皆舞台,世人为优伶”,人的行为不是无端的,其实都是按照一定的“剧本”的“表演”,“剧本”这么安排,其实是有它一定的意涵。“深描”的方法,可以说就是像戏剧鉴赏一样,去分析角色“表演”与在剧中的意义。简而言之,“深描”就是把文化符号放在一定的历史、社会和意义结构中进行综合考察,层层深入地揭示这些符号背后的真正意涵。法律制度其实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现象,“深描”可以运用到法制史研究中。法制史研究中的文化符号可大可小,一条法律条文,判词中的一个典故、一个仪式,都能成为“深描”的对象。这种“深描”不是没有意义的,对这些符号的深描,可以从小见大解释这种行为在当时为什么是犯罪,为什么要判刑。由于“深描”是立足于当时的结构进行研究,通过“深描”,还可以提高研究的客观程度,避免“以今非古”的偏见。总而言之,中国法制史不是一个封闭的学科,不断地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才能使它的视野更加开阔,成果更加丰富多彩。
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虽然中国法制史学成果并不算少,但是它们的内容和研究方法都较为单调。然而,这一段学术史又有着它独特的意义。它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史的开端,它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