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六月份的天空,飘满了柳树和杨树的带毛种子,水面上,也形成了厚厚一层浮渣。柳树和杨树的花为雌雄异株,雄花和雌花多半长在不同的植株上。那些长在本地堤道上的外来白柳,碰巧多为雄株。雌性的柳树,当果实成熟爆开,你能凭着一片灰白,轻易地从远处认出。据说垂柳的雄株从未引进美国,我们只拥有这种树的一半,因此在这里找不到完美的种子。此外,那些常见于本地河岸的原生柳树,我只看到两性中的其中一性,至于我们的美国白杨,大多数都是雌株。
柳树雌花序长约一英寸,貌似绿色毛虫,在黄色的雄花序掉落或枯萎之后,雌花序开始快速发育果实。一串雌花序会发育出二十五到一百个小果实,这些果实略呈卵形且状似鸟喙,里头紧紧塞满棉絮,包藏无数肉眼难见的微小种子。一待成熟,鸟喙状果实打开嘴巴,开裂的两半各自往后卷,将毛茸茸的种子释放出来,就像马利筋一样。如果实际大小差很多的话,一串柳树果实,看起来就像上百个马利筋果实聚集在一根棒子上。
柳树种子比桦树种子更小、更轻——据我测量,只能算是微粒,长度仅为十六分之一英寸,宽度仅为长度的四分之一——基部包围着一簇棉絮般的绒毛,这些绒毛约四分之一英寸长,不规则地分布在种子的四周和上方。这些绒毛使柳树种子成为最容易飘浮的树木种子,能被微风水平吹送至极远的地方。柳树种子落下极缓,即便在室内的无风状态之中也是这样,却能在炉子上方的热气里迅速上升。它就像游丝般飘浮,蜿蜒行进,而在这簇蛛网般绒毛的包覆之下,你很难看见种子。需要一部最精巧的轧棉机,才能把这些种子和绒毛分开。
到了五月十三日,本地柳树里开花最早的水杨柳,就在温暖的草地边缘伸展一两英尺长的绿色嫩枝,上头长满三英寸长、弯曲有如毛虫的串串果实。如同榆树果实,这些果实也在叶子出现前在树上形成醒目的一片绿。不过,现在有些果实已开始迸裂、露出绒毛,使得水杨柳在本地的乔木和灌木之中,是紧接榆树之后开始散播种子的树。
三四天后,在林间和林缘干燥洼地的草原柳,以及位于地势高且极干的林间小径的本地最小的矮毛柳,都开始露出绒毛。后者的细枝很快就覆满柳絮,有如灰白的棍杖,里面包含着有如毛虫粪便的绿色小种子。
此外,约略同时,早熟的颤杨也开始吐露绒毛,晚些则是大齿白杨。这些杨树的果实形状特异,长得很大,而后又会转为鲜黄,看起来很像漂亮的成熟水果。

在六月的前半个月,各种柳树的柳絮和种子飘遍各处堤道和草地。
一八六〇年六月九日,我们碰上六场夏日骤雨——西边和东北边突然飘来乌云,还有一些雷鸣和冰雹。就在这些骤雨过后,我在午后站上磨坊水坝,看见约在屋顶高度的空中,充满某种绒毛,我起初以为那是来自某个房间的羽毛或棉絮。那种绒毛就像一群蜉蝣那样起起落落,或者像是一大团跳动的白色尘埃,间或降至地面。后来,我又以为那是某种轻薄易飘的昆虫。那些绒毛受到建筑之间和之上的微弱气流驱动,沿着街道飘过,衬着还悬在西边的乌云,在潮湿的空气里看起来非常明显。店主们站在自家门口,好奇这是什么。这是白柳的柳絮,大雨将它们从果实中释放出来,接着而来的微风则使它们飞离,带走微小的黑色种子。土地刚刚变得湿润,正是播撒这种子的好时机。我追溯出那些柳絮来自二十竿外的一棵大柳树,距离那条街有十二竿,就在打铁铺后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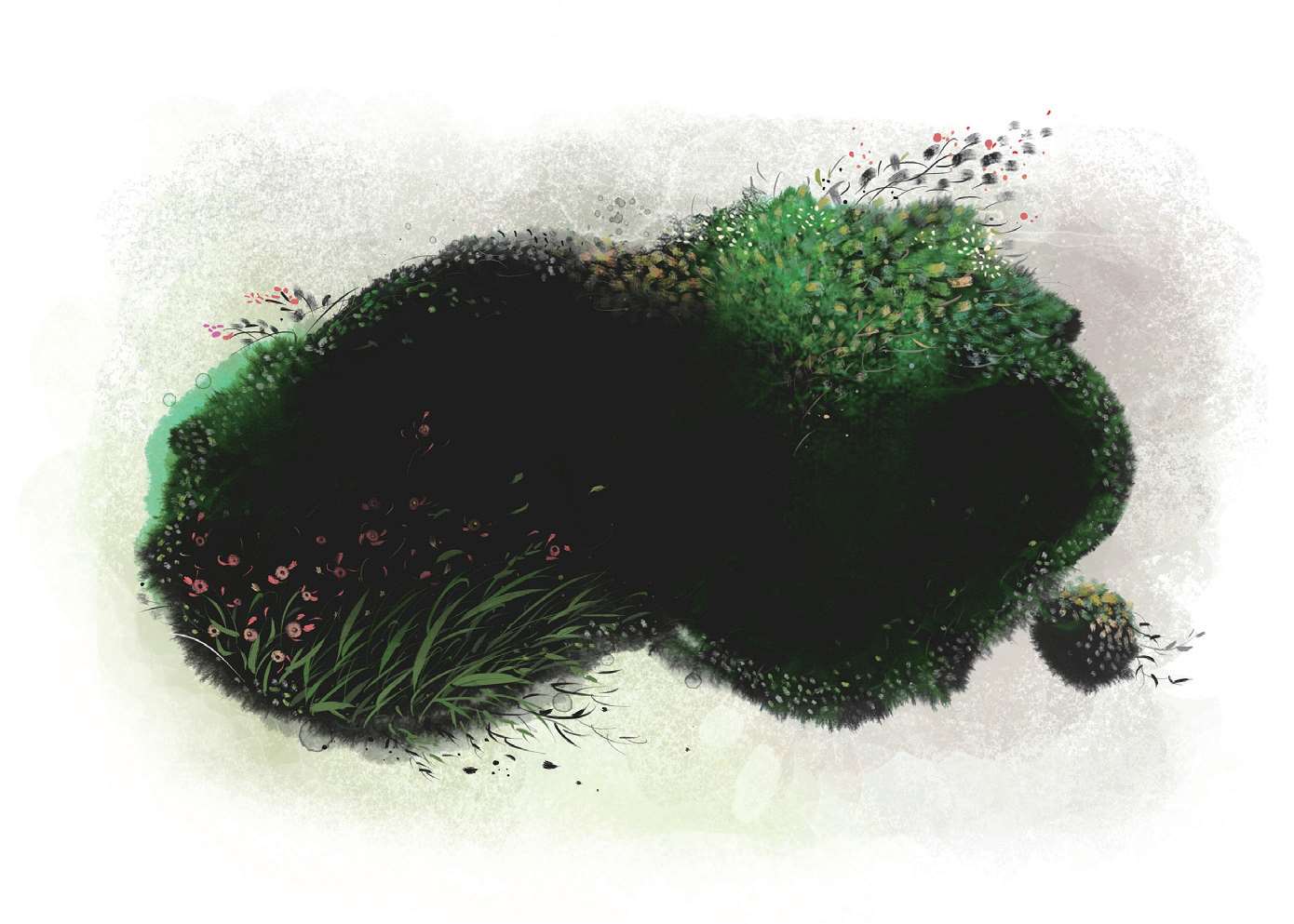
柳树就是以这种方式播撒种子,这些带着绒毛的细小微粒,就算擦过你的脸颊你也不会察觉,以后却可长成直径五英尺的大树。
一周过后,到了六月十五日,当时我在康科德河上,看到某种东西染白了下风处的河岸,那里有个小湾,就坐落在黑柳和风箱树丛之间。这明显的一片白色延伸了两三竿,让我想到有次看到从失事船只冲上海岸的那些白色破布,也让我想到羽毛。我靠近一看,发现那是白柳的柳絮,一如往常充满着细小种子,被风吹聚一处,看来有如水边的浓密白色泡沫,宽达一两英尺,像毛毯或棉垫那样覆盖着水面,而且也和泡沫一样会在外缘堆高或隆起。我原本没想到那是柳絮,因为河边并无白柳,而现在也不是那一带黑柳吐絮的时节。此时吹着西南风,那些柳絮就是来自西南方二十竿外某条堤道上的一些白柳,它们已先被吹越了十五竿的陆地,才来到此处。
这些毛絮是柳树和杨树最广为人知的一项特点。美国白杨为人诟病的缺点就是毛絮会掉得整个院子都是。有种目前并未长在康科德的杨树,甚至被叫作棉花树。
普林尼认为,柳树在种子成熟前就丢失它,使其变成蛛网:“in araneam abit”。希腊诗人荷马曾在《奥德赛》里描述柳树,普林尼等人将他的描述解释为“失去种子的”,不过其他人则解作“不孕的”。在《奥德赛》中,女神喀耳刻在指引尤利西斯前往冥界时说:
不久你将抵达旧海末端,倾斜海岸在那沉降入海;
女神普洛塞庇涅那黑树林的不孕树,杨树和柳树在洪水里颤动。
我由此推论荷马笔下冥河河岸的样子,必定近似美国西北大草原的河流,如萨斯喀彻温河和阿西尼博因河等。诗人借由天界最偏远、最为不毛之处,来设想冥界的模样。那些曾走过美国广袤西北平原的探险家,从麦肯锡到欣德,都谈到当地最常见的树木,在河谷、近河处的就是小型的白杨和柳树;而有些人认为,那些大草原若非每年都被印第安人焚烧,最终或能长出更高贵的树林。

我经常在缅因州的荒野,甚至这附近,发现杨树在以火烧般的速度迅速冒出。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种子最小最轻的树,竟然传播得最广——可说是所有树种的先锋,在较偏北方和更为不毛的地区更是如此。杨树那微小的种子在空气里飘浮、远扬,迅速覆满英属北美地区和我们北部那些火烧地,为河狸和野兔提供食物和庇护之处;水流也协助运送它们。而种子较大、较重的树木,虽然走在杨树铺好的道路上,却传播得比较慢。
没有哪种土壤因为太过干燥、多沙、潮湿,抑或处于太高或太冷的地方,而不能作为某种柳树特有的生育地。一八五八年七月,我看到白山山脉的高山区域,有好几大片地方被那矮小的熊果柳的柳絮染成灰白,这是一种茂密丛生的蔓生灌木,踩踏过去的感觉就像苔藓。其种子以不可抑止的弹力和浮力迸发,将自身族类传遍白山山脉的一座座山峰。另一种亦可于当地发现的柳树是矮柳——它即便不是最小的灌木,也是最小的柳树——这种柳树据说与北极柳同为所有木本植物中分布最北的。
虽然我们不常观察到这些种子飘过空中,但只要做个适当的测试,几乎能在任何地方发现它们。到我们森林里的任何一处观察——无论那里如何多沙,例如铁道沿线,或因霜害而无树木长出之地——除柳树(草原柳或矮毛柳)和杨树之外,没有其他哪种灌木或乔木有可能会在那里立足生长。
如同马利筋种子,杨树种子似乎也多在风止息的洼地落脚。或者,这些种子之所以碰巧在那里成长,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结了霜,较不耐寒的植物难以占领。在这附近有许多这样的杨树洼地。
在任何开阔草地上建造一条堤道后,如果人类不加干涉,那条堤道的两侧总是很快就会冒出一整排的柳树(还有赤杨之类的植物),即便先前或许没有任何柳树长在附近,也没有任何植株或种子被人类带到那里。由此,人类学会借由种植最大型的柳树来为堤道抵挡洪水。
本地的铁路约于一八四四年兴建,当时有一大片多为草地的开阔地带,位于村庄西端以南,坐落在村庄和树林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灌木丛生长。铁路堤道穿越这里,建起了一座高度超过十五英尺的沙堤,以南北向与河流直交。大约十年过后,我惊见柳树在此形成绵延的天然树篱,尤其是沿着这条沙堤东侧的基底,那边有道栅栏始于距河大约半英里处,并延伸半英里直到树林。那座柳树篱当然就像那条铁路或其栅栏一样笔直。
事实上,那座篱笆就像一座天然的柳树园,很方便我做研究,里头有八种柳树,约为我在康科德所见种类的一半:喙状柳、草原柳、水杨柳、白柳、密苏里河柳、绢毛柳、沼泽柳以及亮叶柳,其中只有白柳非本地原产。你可能会以为,那些种子或枝条是在兴建堤道时,跟着沙子一起从附近树林里的深谷带来的;然而,这些柳树至多只有前三种长在那里,后四种仅见于半英里以北、村庄彼端的河边草地——的确,它们在镇上通常都只长在河边和毗邻的草地。要是我发现后两种出现在远离河边草地的地方,必会特别惊讶,因为它们在本地的分布非常局限。白柳是其中唯一一种,就我所知曾长在上述堤道附近的区域。

因此,我认为这些柳树至少有一半的种子——或许另一半的大部分也是——从远方被吹到这里,被沙堤拦下,落脚在其底部,有点像飘雪那样积在那里。因为我在它们之间看到数棵梣树,它们源自十竿以东草原上的那棵梣树,而其他地方并没有梣树萌芽生长。这里还有一些赤杨、榆树、桦树、杨树和某种接骨木。于是,如果其他条件合适,你必能看到柳树冒出,因为空气中总是飘浮着许多它们的种子。
这片空旷草地上,可能好几年里都不曾有过一棵柳树扎根,但当草地上建起一道这样的屏障后,沿途很快就会长满柳树,因为这道屏障除了聚积种子,也能为柳树抵挡人类和其他敌人。柳树只会沿着屏障的基部生长,就像它们只会沿着河流的岸边生长那样。沙堤之于柳树,就如同湖岸一样,而整片草地就像湖泊;柳树享受着沙子的温暖和庇护,而其根部沉醉于草地的湿润。如果我们思考树木和野草的来源,那么我们会发现,它们就像雪一样飘向栅栏和山坡,在那里获得成长的支持和保护。
这些柳树多么急切、多么繁茂、多么早熟。它们拉丁文学名中的 Salix ,来自 salire 这个单词,为“跳跃”之意,它们跃起得如此迅速、如此活跃。它们在两年内才抽出两条幼枝,枝上就立刻发出银白的花序,接着就是盛开的金黄色的花和带毛的种子,它们以惊人的速度来传播族群。如此,它们繁衍不息并群聚一处,就连对其他树种来说是侵入领域、干扰生长的铁路,它们也能善加利用。
然而,虽说柳树种子年年都在空中撒满柳絮,被风吹遍树林和草地,但显然只有百万分之一能长成灌木或乔木。不过那就够了,大自然的目的已获得满足。许多白柳长在本地的堤道两旁,但少有白柳在别处自然萌发并维持领地,我猜想这些白柳来自意外落下的柳条而非种子。就连少数跟着黑柳一块长在溪边的白柳,也可能是来自从堤道漂去的枝条。最老且最大的白柳就长在房屋周围,如果我们相信传说的话,那么它们都有共同的历史,几乎每棵柳树都有相同的故事。某位胖老爹坐在屋里回忆儿时,当年在院子玩骑马,他最后将柳枝插在地上,然后忘了这回事,而柳枝现已长成那边的大树,所有过客都为之赞叹。当然,让太多柳树种子长成也行不通,因为要是每颗白柳种子都长成这样的大树,那么几年内,整个地球就会变成一座柳树林,这并非大自然会做的计划。
另一种外来柳树——杞柳,是在几年前偶然来到本镇,那时有一枝柳条被用来捆绑其他树木。有位好奇的园丁将那枝柳条插在地里,而今它已有了后裔。
约莫六月中旬,沿河而生的黑柳结起籽,其柳絮开始飘落水面,并持续飘落一个多月。黑柳柳絮在树上最显眼的时候是在六月末周,带来一种斑驳的绿白样貌,相当有趣,就像果实一样。那些柳絮也在此时大量布满水面。
六月七日,一些黑柳种子被我放进窗边的圆杯里,不到两天就发了芽,长出圆圆的小绿叶。这让我既惊讶又好奇,因为植物学家经常抱怨,要让柳树种子发芽有多么困难。
我想我知道黑柳如何繁殖。它那微小的棕色种子,在绒毛里隐约可见,随之飘至水面——尤以六月二十五日最多——这些绒毛在水面漂流,还跟其他东西一块形成厚厚的白色浮渣,经常在水流较小之处,碰到河边的赤杨或其他低垂的灌木。这些浮渣通常呈现窄窄的新月形,长十到十五英尺,并与河岸形成直角,月弯则朝向下游,看来又厚又白,让我想到白霜。在两三天内,大量种子发芽,在一片白色之中露出圆圆的小绿叶,将浮渣表面略微染绿,就像在浮着棉花的水杯里撒上草籽。这些种子有许多漂进河岸的风箱树、柳树等灌木和莎草之间;或许就在细根长出时,水位下降了,它们便轻轻沉积在树荫底下刚露出的淤泥上,许多种子也许就这样有了机会长大成树。但是,它们如果未掉进够浅的水面,并适时地留在淤泥里,可能就消亡了。我在许多这样的地方,看过淤泥点缀着绿色,而那些种子或许是被风直接吹到那里的。
然而,它们借着这个方法若是无法成功,还有其他办法。比方说,像是长在本地河岸的另一种柳树,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枝条的基部长得很脆,一碰就断,好似被切下一般——不过基部以上反倒极为坚韧,可以绞成强韧的绳索,能用于泊船,此即柳枝在某些国家的用途之一。然而,这些枝条就像种子那般撒落、漂流,然后扎根在第一个停靠的河岸。

某年六月,我在阿萨伯特河的沙岸上看到一团湿湿的东西,混杂着细屑、叶子和沙子,我注意到里头倒卧着一小株正在开花的黑柳。我将它拔起,发现那是一根十六英寸长的柳条,它有三分之二都埋在那团湿物里。这根柳条或许是被雪弄断、顺流而下、被冲上岸,然后被埋在那里,就像园艺的压条技法一样;如今,埋着的那三分之二,已生出了许多一两英寸长的幼根,而在地面上的部分也抽出叶子和花序——这样就有了一棵树,或许它将来还能高高站立在岸边摇曳呢。黑柳的生命力如此旺盛,它把握住每次机遇,沿河散布蔓延。降雪折断它的柳条,却反而让它传播得更远。
每次,当我把船驶入一片黑柳之中,船上总是撒满了柳枝,因为这些柳树低垂、伸展,甚至依着水面。从前我曾无知地怜悯黑柳的苦命,感叹它们的枝条如此脆而易断,不像芦苇那样柔韧易曲。然而,如今我却钦佩黑柳的坚强。我很乐意将我的竖琴挂在这样的一株柳树上,仿佛这么做就能获得灵感。我在康科德河岸旁边坐了下来,几乎要为了这个发现喜极而泣。
柳树啊,柳树,
愿我总能拥有像你那般的好精神,
那般柔韧,那般迅速地从伤痛中复原。
我不晓得人们为何将柳树称作无望之爱的象征,他们说:
“被抛弃的情人穿戴着柳树!”
毋宁说,柳树是大自然里胜利之爱和同情的象征。它会垂下,也极易弯折,但绝不哭泣。垂柳在此也开得一样有生气,即便它的另一半(雄株)并不在新大陆,而且也从未到来。柳树之所以低垂,并不是要纪念大卫的眼泪,而是要提醒我们,当年在幼发拉底河,它们如何从亚历山大头上摘走皇冠。
难怪柳木在古代会被用来制造圆盾,因为柳木和整棵柳树上下一样,不仅柔软易弯,还坚韧而易复原,不会一击即裂,而且能立刻愈合伤口,不让创伤扩大。这种树的命运就是每两三年会被砍断一次,但它们却不会因而死去或哭泣,只会抽出更健壮、更有生气的嫩枝,而且活得跟大多树种一样久。富勒在其《英格兰名人传》中谈道:“柳树喜爱潮湿的地方,而且遍布伊利岛,根部可巩固岸边,剪下的柳条可做生火的燃料,生长速度惊人。这里有句俗语说,柳树的利润已为主人买来一匹马,但其他树木的收益却还连马鞍也买不起。”
希罗多德说,斯基泰人借助柳杖来占卜,他们要上哪去找更适合用来占卜的树枝呢?连我初见柳杖,我也成了占卜师呢。
无论我是在十二月初某处干燥洼地的莎草丛里,还是在仲冬的雪地里,只要看到一根柳枝冒出,即便是最细的那种,都让我精神振奋,仿佛那是沙漠中的绿洲。柳树家族的学名Salix,来自凯尔特语的sal(近)和is(水),意味着它们附近流着某种天然的汁液或生命泉源。柳树是不曾失灵的占卜杖,总是扎根在水源处。

哎,柳树绝非自尽之树,它从不绝望。大自然里总是会有水汽,让它能化作生命的汁液。柳树是青春、喜悦和永生的象征。何处可见柳树失意的冬天?它的生长几乎不受任何季节的阻碍,白色的柳絮总会在一月最暖的日子里开始吐露。
杨树也不像某些人所称,是法厄同那些哭泣的姊妹,因为没有什么比太阳马车的出现更让杨树欢喜,而它们也丝毫不为那位驾驶员感到悲痛。
想要叙述柳树如何未能传播,或许要比描写它们如何传播来得省事。我不晓得除了那些在巢里用上种子绒毛的鸟,还有哪些动物会帮忙传播柳树。贾汀在写给威尔森的笔记里谈道,他经常在英国北部的年轻冷杉林里,发现于季末所筑的小朱顶雀的鸟巢,“总是铺上柳树的毛絮”。这种做法有时亦可见于我们这里的金翅雀鸟巢。穆迪说,英格兰地区的金翅雀有时会在巢里铺上柳絮。威尔森说,紫红朱雀会以杨树种子为食。
至于悬铃木——据米肖所述,是这个纬度上最大的落叶树——它的种子虽然远大于桦树和柳树的种子,却小于大多数园艺植物的种子。球形的果实直径约为八分之七英寸,系由三四百个长约四分之一英寸的棒状种子组成,那些种子尖端朝下,像针一样密集插在球形针插中;种子的基部围了一圈茶色硬毛,适合作为降落伞。果球连着长而韧的纤维质果柄,高高悬荡在大树上——因此每当树梢长了一些果球,我就会注意到。果球会在冬季和春季的暴风雨中猛烈摇晃,因而逐渐崩解,而种子或许就在一阵强劲的暴风雪里松落。在这种情况下,悬铃木种子虽然不是特别会飘,但仍有机会被风运送一段距离。我注意到这些种子能轻易散布于距离母树十到二十竿的范围。我曾读到书上说“杨树和悬铃木在冲积地和大草原上的内陆森林里占了一大部分”。威尔森说,果园拟黄鹂常用悬铃木的绒毛或羊毛来铺巢,还说紫红朱雀会在冬天食用悬铃木种子。
吉罗也说,紫红朱雀似乎很爱那些种子。
这般细小的起始——可说仅是一粒微尘——却是巨木之所由生。正如普林尼对柏树的描述:“有件事不但惊人,而且不该被忽略,那就是树木竟然是由如此细微的起源产生,而小麦和大麦的谷粒却远远大得多,更别提豆类了。”他又说,蚂蚁非常喜欢柏树的微小种子,让他惊讶的是,“如此微小的昆虫竟能摧毁这般巨树的起源”。
或者,如似乎受了普林尼启发的伊夫林所写的:
凡人之中哪有如此完美的原子论者,愿意分析研究这般飘逸种子的千分之一?这种子可是无法感知的雏形,或像气息般的精神,却能产生高耸的冷杉和展开的橡树。(或者,谁愿相信)如此高耸而巨大的树木,像是榆树、悬铃木和柏树,有些甚至坚硬如铁,扎实如大理石,竟能被裹在这么小的范围里(如果一个点也能说是有范围的话),而没有丝毫脱位、混淆和错乱,放进如此微弱的物质。那在最初不过是某种黏液或腐物,但在埋进大地湿润的孕育处之后,竟能轻易分解、侵蚀那些远远硬得多的物质。而这种子虽然柔弱而有弹性,最终竟能推开或扯碎整块岩石,有时更以超过铁楔的力量将其劈开,甚至能够移山?没有任何重量可以压抑一棵胜利的棕榈,而我们的树木虽是种在腐败里,却能一步步长成坚硬、挺立的壮观大树,变成坚牢的巨塔。不久前才能让一只蚂蚁轻易搬回它那小洞的种子,如今已能抵挡最猛烈的暴风雨。
普林尼和伊夫林会如何谈论世界第八大奇观——加州巨大的“世界爷”呢?这种树起自这般细小的种子(其球果据称形似白松球果,但长仅两英寸半),却见证了世上诸多王国的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