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大类植物(林奈称之为粘着植物)的种子或果实附有微小的带刺长矛、钩子或其他机关,借以粘上任何碰到它们的动物,以便被运送到其他地方。这类植物在本地最常见的,就是各种鬼针草和山蚂蟥,还有牛蒡、龙牙草、露珠草和猪殃殃等等。
作物枯萎,
牛蒡和矢车菊丛生;
有害的黑穗病和不孕的橡树
主宰了耕地。
鬼针草——本地共计有五种——种子的形状略似扁平的褐色箭袋,从里面伸出二到六枝带有倒钩的箭。它们最早的是在十月二日左右成熟,如果你在十月里得走过或经过某个半干涸的水塘,这些种子往往就会粘上你的衣服,而且数量惊人。这就好比你无意间走过一片数不尽又看不见的小人国军队,他们一怒之下将所有的箭矢和标枪都射向你,只是无一射中腿部以上。这些双箭、三箭和四箭种子全都射向你,直到你的衣服全被插满,由于它们很难用手拂去,因此就连那些最爱整洁的人,也只得带着它们前进。有时到了一月中旬,这些种子还有很多。
特别的是,本地有种水生鬼针草,分布于河流,只在水里生长,往往连绵整个河面,所以鲜少不会被经过它们附近的动物碰到。然而,也许是某只麝田鼠、貂、涉禽、麋鹿或牛,或者甚至是某位不怕弄湿衣服的老派梭鱼钓手涉水而过(大自然预期他来,就像预期麋鹿到来那样),它们皆为传送这种鬼针草的媒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鬼针草的箭袋,拥有最多支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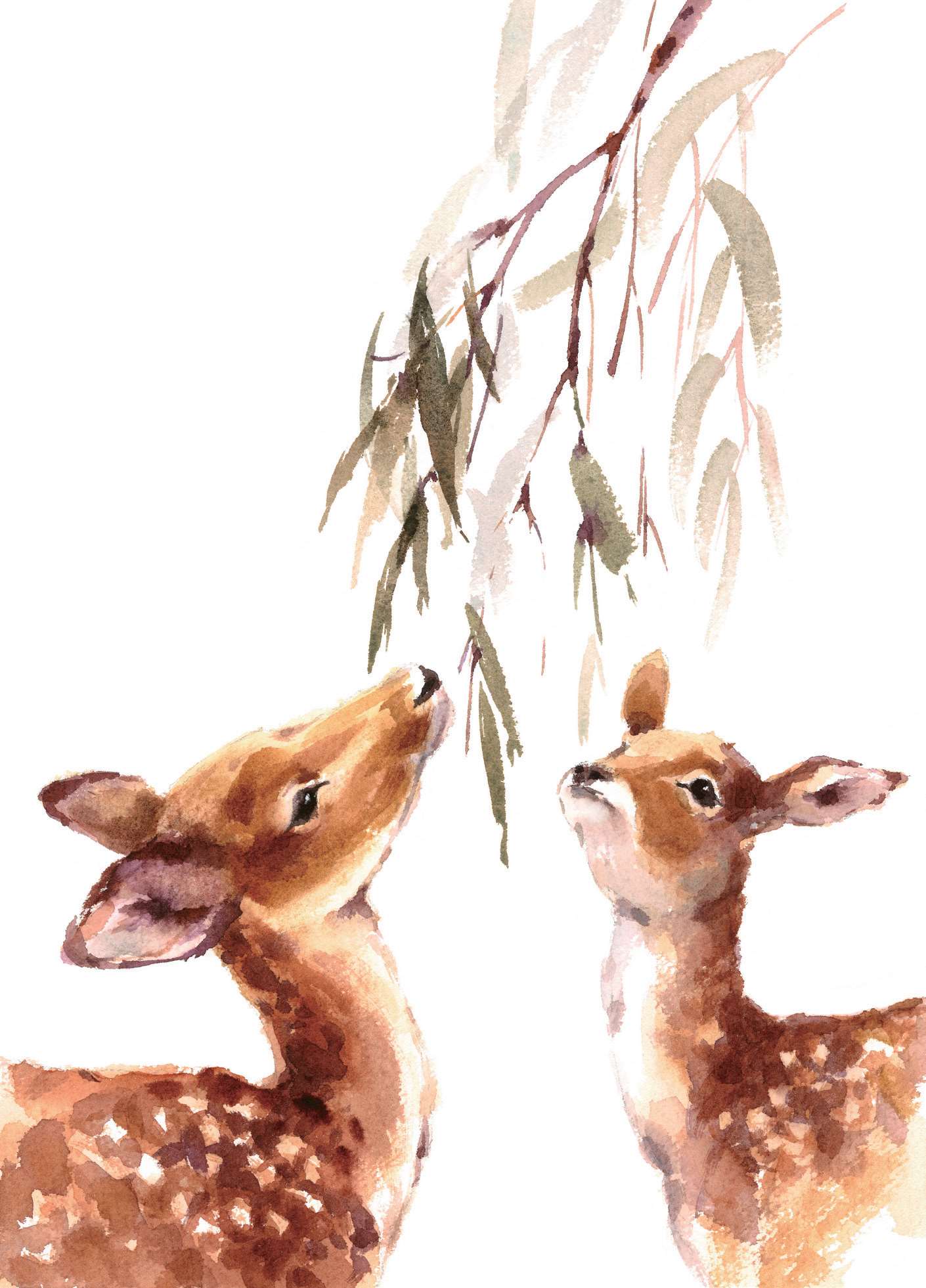
我在本镇找到八种山蚂蟥,它们的种子被包在节状的果荚里,看起来好像短链条,各节的形状呈菱形、圆形或三角形,上头覆满细微的钩状绒毛。山蚂蟥最早的是在八月三十日左右成熟。
池畔的鬼针草和长在峭壁的山蚂蟥,知道必有野兽或人类前来,以其皮毛或外套为它们运送种子!每当我在九月里爬上峭壁去找寻葡萄,几乎没有一次不把衣服弄得都是山蚂蟥的种子(尤其是圆叶山蚂蟥和圆锥山蚂蟥)。就算你拼命地逃,它们还是赶得及抓住你、粘上你——而且往往是粘上整排果荚,有如一把有着四五个锯齿的窄锯子。它们甚至会粘上你的手。它们凭着有如婴儿寻找妈妈乳房般的直觉粘上你,渴求一片处女地,急于发现新的土地,到外地去寻求它们的未来。它们偷偷搭上你这艘船,知道你不会回到原来的港口。我们不愿被绊住或耽搁行程,于是被迫带着这些种子和我们一起走。这些几乎看不见的网已撒向我们,一群群的山蚂蟥和鬼针草种子,就这么巧妙地利用我们偷搭便车来运送种子。
你得花上好些时间才能把它们去除干净,它们粘上你却只需要一下子。我常发现自己好像覆盖着一件由山蚂蟥种子叠覆成的褐色大衣,或是一座多刺的拒马,必须在某个方便的地方(或许对它们来说更为方便),花上至少一刻钟摘掉它们,从而它们可以得偿所愿——被运到另一个地点。
因此,即使是最肮脏、最懒散的闲汉或乞丐,也能对大自然的运作有点贡献,只要他一直不断移动的话。
某天下午,我和一位同伴在河流下游靠岸,漫步走过岸边那一大片山蚂蟥(马利兰山蚂蟥,果荚各节为圆形),发现裤子沾了满满的山蚂蟥种子,数量多到令人感到惊奇又有趣。这些绿色的鳞状种子紧密覆盖着,把我们的腿都变绿了,让我想到水沟里的浮萍,又像某种锁子铠甲。这成了我们散步时的一大趣事,我们也很自豪能穿上这身勋章,时而有些嫉妒地相互打量,好像谁的衣服上粘得多,谁就比较杰出似的。我的同伴对此事流露出某种信念,因为他指责我说,他认为不该故意走近山蚂蟥以求粘上更多种子,也不该拔掉身上的种子,应让种子在无意间磨搓而落。结果一两天后,他为了和我散步再次出现在我面前,他的衣服几乎仍像起初那样粘了满满的种子。我发现大自然的计划,被他的迷信大幅往前推进。
我们常说某人的衣服老旧且褴褛,这可能是指衣服穿久了,破烂得就像有些结了种子的、破败的植物,也或者意指衣服粘着许多种子而变得凌乱不堪。
牛蒡果实的状况也是一样。孩童经常将其拿来盖房子和谷仓,而不需用上任何灰泥,而人类和动物只要有毛茸茸的外衣或皮毛,都可以被用来运送它们。我曾帮过一只猫,去除满身它自己弄不掉的牛蒡种子,而我也常看到牛只甩动着的尾巴末端,粘了一堆,它或许会为了挥掉那些想象中的苍蝇而刺到自己。
某年一月,我散完步走过厚厚积雪回来,发现一些干掉的种子粘在我的大衣衬里,但我不晓得那个季节里何处找得到牛蒡。由此看来,甚至在大雪期间,大自然也没忘了它的植物生计。借由这些方式,牛蒡从欧洲传入美洲。
那些在工厂里拣羊毛的人或许能告诉我们,他们在羊毛里发现了什么。无疑,会有许多新品种的野草,它们经由作为肥料的羊毛废料——至少暂时地——引进我们的土地。鸟类学家威尔森谈道,苍耳在他那年代长满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的岸边,“那些在苍耳最盛处吃草的羊只,身上嵌满整片芒刺果实,使得这些羊毛几乎不值得清理”。而据康多尔所述,“从东边冲来的羊毛曾导致蒙特皮利尔附近某处出现一大堆来自柏柏里、叙利亚和比萨拉比亚的植物品种,不过,那些植物大多未能在这里成功生存下来”。
几年前,我知道镇上仅有一处长有琉璃草。我用手帕包了一把这种植物的小果实放在口袋,回家后,花了很长时间才将它们从手帕上一一扯下,还在这过程中拉断许多棉线。接着,我又花了二十分钟来清理自己,因为我也碰到那些植物。不过,我并不介意这种事;所以,到了来年春天,我好意将一些前一年八月采到的种子,送给某位照顾花园的年轻女士和我的姊妹,希望能够传播这种稀少的植物。她们对这种植物的期望被激起,而且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琉璃草要到第二年才会开花。开花时,花朵及其特殊香气很受喜爱;但忽然之间,抗议声大声地传到我耳里,因为琉璃草的种子粘到了那些花园常客的衣服上。我得知那位年轻女士的母亲,在某次出门旅行前,到花园摘取了一朵香花,后来,她发现自己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衣服上夹带了数量惊人的种子去波士顿,而铁路公司也未对这些货物收取费用——那些邀你前去欣赏、摘采的花儿,对你都是别有用心的。因此,这种种子就这样被传播了,而我的目的也已达到,我不需要再为它烦恼了。
文明人要比野蛮人夹带更多种子。皮克林在其人种研究中谈道:“澳洲原住民几乎不着衣物,而且拥有极少人为制品,他们在传播种子和植物的贡献上,或许少于任何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