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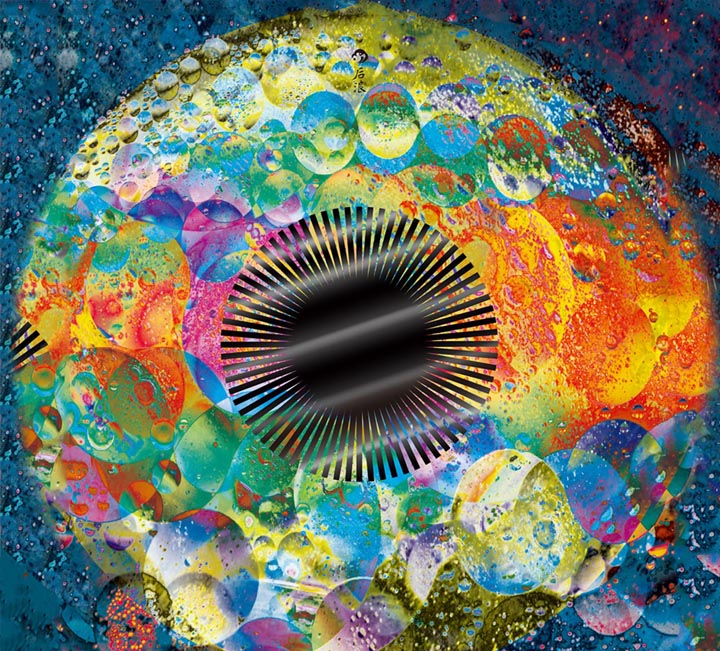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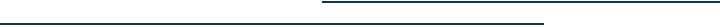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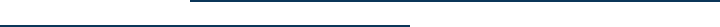
1924年,马歇尔·赫蒂希(Marshall Hertig)和希米恩·伯特·沃尔巴克(Simeon Burt Wolbach)在波士顿和明尼阿波利斯附近收集淡色库蚊(
Culex pipens
),他们从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微生物。
 它看起来有点像立克次体(
Rickettsia
,沃尔巴克曾把立克次体鉴定为导致洛基山地区斑疹发烧和斑疹伤寒的元凶),但是这种新的微生物似乎并不对任何疾病负责,因此基本遭到了忽略。赫蒂希花了12年时间才正式以拉丁名
Wolbachia pipientis
命名沃尔巴克氏体,以纪念发现这种细菌的朋友,以及记录携带它的蚊子。之后,生物学家花了好几十年时间,才意识到这种细菌是多么特别。
它看起来有点像立克次体(
Rickettsia
,沃尔巴克曾把立克次体鉴定为导致洛基山地区斑疹发烧和斑疹伤寒的元凶),但是这种新的微生物似乎并不对任何疾病负责,因此基本遭到了忽略。赫蒂希花了12年时间才正式以拉丁名
Wolbachia pipientis
命名沃尔巴克氏体,以纪念发现这种细菌的朋友,以及记录携带它的蚊子。之后,生物学家花了好几十年时间,才意识到这种细菌是多么特别。
对于经常写作微生物专题的科学作者来说,内心有一种最喜欢的细菌并不奇怪,就像人们有各自心仪的电影或乐队一样。沃尔巴克氏体就是我最喜欢的细菌。它的行为和传播范围都令人惊叹。它还完美地佐证了所有微生物都拥有双重身份的事实:既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又是寄生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卡尔·乌斯向全世界展示了如何通过基因测序来鉴定微生物,自那之后,生物学家开始发现,沃尔巴克氏体无处不在。而许多独立研究这种细菌的科学工作者逐渐意识到,他们的研究都导向了同一个发现:这种细菌能够操纵其宿主的性生活。理查德·斯陶特海默(Richard Stouthamer)发现了一组进行无性生殖、实际上全为雌性的黄蜂,它们完全通过克隆来繁殖。这种特性正是拜细菌沃尔巴克氏体所赐:当斯陶特海默给黄蜂用抗生素杀死细菌后,雄性又突然出现,不同性别的个体再次开始交配。蒂埃里·里戈(Thierry Rigaud)在木虱中发现了一种细菌,它会干扰雄激素的产生,从而把雄性转化为雌性——而这种细菌,也是沃尔巴克氏体。在斐济和萨摩亚,格雷格·赫斯特(Greg Hurst)发现,美丽的幻紫斑蛱蝶的雄性胚胎总是被一种细菌杀死,从而使得雌雄比超过了100∶1。这里的罪魁祸首,还是沃尔巴克氏体。也许具体种类不完全一致,但这些与赫蒂希和沃尔巴克在他们抓到的蚊子中找到的微生物大致相同,只是版本不同罢了。

这种细菌所采用的全部策略都不利于雄性,因为沃尔巴克氏体只能通过动物的卵把自己传递到下一代宿主,而精子太小,容纳不下它们。雌性给了它们通向未来的车票,雄性只会带着它们走入演化的死胡同。所以,沃尔巴克氏体演化出了许多方法,欺骗雄性宿主,扩大雌性群体占有的地盘。它像赫斯特的蝴蝶一样杀死雄性,或者像里高的木虱一样使雄性变成雌性,甚至可以像斯陶特海默的黄蜂一样允许雌性无性繁殖,完全排除雄性存在的必要。这些手段都不是沃尔巴克氏体独有的,但它是唯一能够用全这些策略的细菌。
在一些地方,沃尔巴克氏体允许雄性生存,但仍然操纵它们。它经常改变宿主的精子,使它们不能成功地让卵子受精,除非卵子也感染了同一种沃尔巴克氏体。从雌性的角度来看,这种不相容意味着:与未感染的雌性(只能与未感染的雄性交配)相比,受感染的雌性会获得更多竞争优势。这样一代代地繁衍下去,受感染的雌性越来越多,它们携带的沃尔巴克氏体也会传播开去。这就是细胞质不亲和,是沃尔巴克氏体最常采用,也最为成功的策略。使用这一策略的菌种,通常能够迅速地在一个群落中传播,感染100%的潜在宿主。
除了这些“厌男”手段,沃尔巴克氏体还擅长入侵卵巢、进入卵细胞,所以很快可以成为昆虫留给后代的“传家之宝”。它也极其擅长感染新宿主。因此,即使它与任何一个物种“分手”,也会找到好几十个可以“安家”的新物种。研究这种细菌的杰克·韦伦(Jack Werren)猜测:“或许能够在澳大利亚的甲虫和欧洲的苍蝇中发现同一种沃尔巴克氏体。”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沃尔巴克氏体已经变得非常普遍。最近一项研究估计,每10种节肢动物中,至少有4种会感染沃尔巴克氏体。这个比例听起来十分荒诞。要知道,节肢动物包括各种昆虫、蜘蛛、蝎子、螨虫、木虱等,动物界中现存的大约780万种物种都属于节肢动物。如果沃尔巴克氏体感染了其中的40%,
 那么几乎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细菌,至少是陆地上的王者。
[1]
不过,令人悲伤的是,沃尔巴克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被用于命名了生命史上最重大的一种传染病,死于1954年的他对此毫不知情。
那么几乎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细菌,至少是陆地上的王者。
[1]
不过,令人悲伤的是,沃尔巴克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被用于命名了生命史上最重大的一种传染病,死于1954年的他对此毫不知情。
对于许多动物而言,沃尔巴克氏体是一种生殖寄生虫:它操纵宿主的性生活,进而实现自身的目的。宿主会因此受苦,有些会死亡,其他一些会失去生育能力;即使是没有受到影响的个体,也必须生活在一个畸形的世界中,几乎找不到潜在的伴侣。这么说来,沃尔巴克氏体可能像是典型的“坏微生物”,但它也有有利于宿主的一面。它能给某些线虫提供一些人类未知的益处;没有它,这些线虫便无法生存。它还能保护一些苍蝇和蚊子,使它们免受病毒和其他病原体的侵扰。缩基反颚茧蜂(
Asobara tabida
)离了沃尔巴克氏体就不能产卵。对床虱而言,沃尔巴克氏体是一种营养补充剂。因为床虱吸食的血液中不含 B 族维生素,沃尔巴克氏体正好能补充这种缺失;没有它,床虱便会发育不良,也无法生育。

到了秋天,如果你有机会去到欧洲的苹果园,便能见证沃尔巴克氏体最惊人的用处。在苹果树黄橙相间的叶片上,你可能会发现一些绿色的斑点,仿佛在对抗季节性的枯萎。这是斑幕潜叶蛾制造的结果,它的幼虫住在苹果树的叶片里,且几乎都携带着沃尔巴克氏体。微生物在这种昆虫体内释放激素,阻止叶片变黄枯萎。它们让幼虫拖慢秋天的脚步,给自己足够的时间蜕化成蛾。如果消灭了沃尔巴克氏体,叶片便会凋零,里面的毛虫也会随之死去。
因此,沃尔巴克氏体是一种多面的微生物。它们可以是自私的寄生虫,无所不用其极,搭载宿主的翅膀和腿脚散布到世界各地;它们杀死动物,破坏其生理功能,并对宿主的择偶施加限制。但它们中的另一些则是互助主义者,给予恩惠,是动物不可或缺的盟友。还有一些二者均沾。而在微生物的世界里,沃尔巴克氏体也不是唯一如此多面的存在。
虽然本书意在介绍与微生物一同生活的益处,但这里涉及了一种微妙但又很关键的认知:没有所谓的“好微生物”或“坏微生物”。只有童话故事才会这样定性,这种简单的标签并不足以描述自然界中各种复杂的爱恨情仇。

事实上,在“坏”寄生虫到“好”共生体之间有一段连续的性质分布范围,细菌分布其间。如沃尔巴克氏菌这样的微生物,能从连续范围的一端滑到另一端,变好变坏取决于菌种和它们所在的宿主。但许多细菌同时存在于连续范围的两端,同样的菌种却能同时导致好坏两种结果
 :比如胃里的幽门螺杆菌(
Helicobacter pylori
)能引起胃溃疡和胃癌,但也能防止食管癌。其他一些菌种可以根据具体环境而在同一宿主体内更换角色。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诸如互助、共生、共栖、病原体或寄生虫等标签,并不完全指一种固定的身份,更像是代表了当下的一种状态,与饥饿、清醒、活着类似;抑或是一种行为,比如合作或战斗。它们是形容词和动词,而不是名词:它们描述的是两个伙伴在何时何地如何彼此关联。
:比如胃里的幽门螺杆菌(
Helicobacter pylori
)能引起胃溃疡和胃癌,但也能防止食管癌。其他一些菌种可以根据具体环境而在同一宿主体内更换角色。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诸如互助、共生、共栖、病原体或寄生虫等标签,并不完全指一种固定的身份,更像是代表了当下的一种状态,与饥饿、清醒、活着类似;抑或是一种行为,比如合作或战斗。它们是形容词和动词,而不是名词:它们描述的是两个伙伴在何时何地如何彼此关联。
妮科尔·布罗德里克(Nichole Broderick)在研究一种名为苏云金芽孢杆菌( Bacillus thuringiensis ,简称 Bt)的土壤微生物时,发现了一个展现以上互动模式的绝佳例子。Bt 产生毒素,在昆虫肠道上蚀出孔,从而杀死昆虫。20世纪20年代,农民开始利用微生物的这种能力,把 Bt 作为活性杀虫剂喷洒到作物上。甚至连有机农业也采用了这种做法。这种微生物的有效性毋庸置疑,但关于它是如何杀死昆虫的,科学家几十年来都想错了。他们一直认为,该微生物的毒素对昆虫的肠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进而导致后者饿死。但这不能解释整个故事。毛虫不吃不喝一个多星期才会饿死,但 Bt 只消一半时间便可以置它们于死地。
布罗德里克几乎是在完全偶然的状况下发现了真相。
 她怀疑毛虫肠道中的微生物会保护它们免受 Bt 侵害,所以她先给毛虫使用了抗生素,再喷洒 Bt。她想,肠道微生物消失后,毛虫可能死得更快。可是它们最后却都幸存了下来。事实证明,肠道细菌不仅没有保护毛虫,反而被 Bt 借来杀死毛虫。它们留在肠道中时是无害的,但却可以通过由 Bt 毒素在肠道上蚀出的孔而侵入昆虫血液。毛虫的免疫系统一感受到这些微生物的存在,便会陷入狂暴状态,制造一大波炎症,并传播至毛虫身体各处,损害各种器官、阻断血液流动。这便是败血症,也是昆虫死得如此快的原因。
她怀疑毛虫肠道中的微生物会保护它们免受 Bt 侵害,所以她先给毛虫使用了抗生素,再喷洒 Bt。她想,肠道微生物消失后,毛虫可能死得更快。可是它们最后却都幸存了下来。事实证明,肠道细菌不仅没有保护毛虫,反而被 Bt 借来杀死毛虫。它们留在肠道中时是无害的,但却可以通过由 Bt 毒素在肠道上蚀出的孔而侵入昆虫血液。毛虫的免疫系统一感受到这些微生物的存在,便会陷入狂暴状态,制造一大波炎症,并传播至毛虫身体各处,损害各种器官、阻断血液流动。这便是败血症,也是昆虫死得如此快的原因。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人体内,每年可能有数百万人遭受影响。这类能在肠道中蚀出孔洞的病原体同样会感染人类,而当肠道中常见的微生物进入血液时,我们也会得败血症。就像在毛虫体内,相同的微生物可以在肠道中扮演“好菌”,也可以在血液中变身为危险分子。只有待对了地方,它们才会成为互助主义者。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生活在我们身体中的所谓“机会主义细菌”。它们通常是无害的,但也可以感染免疫系统变弱的人群,甚至危及生命,
[2]
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即使对于长期存在于人类体内的最基本的共生体线粒体而言,情况也是如此。所有动物细胞都含有线粒体,它们是提供能量的动力工厂;而一旦出现在错误的地方,它们也可以造成严重的破坏。一些细胞会因为伤口或擦破了皮而裂开,其中的线粒体片段便会溅入你的血液。要知道,这些片段仍然保留了它们自古以来的细菌特性。你的免疫系统发现它们后,会错误地认为体内发生了感染,于是会建立起强大的防御机制。如果损伤严重而释放出足够多的线粒体,那就可能导致全身性炎症,而这种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甚至会危及生命。
 SIRS 比最初的伤口更糟糕。荒唐的是,线粒体已经历经了20多亿年的驯化,而人体再面对它时依然会错误地过度反应。正如长错了地方的鲜花与杂草无异,我们的微生物在一个器官中可能极其宝贵,但在另一个器官中却可以变得危险异常;在细胞内是必需品,在细胞外却成了致命物质。“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受到一点抑制,它们就会杀了你;你死后它们会吃了你,”珊瑚生物学家福瑞斯特·罗威尔(Forest Rohwer)说道,“它们才不在乎。你和它们之间不是一段美妙的姻缘,只是一幕纯粹的生物学戏剧。”
SIRS 比最初的伤口更糟糕。荒唐的是,线粒体已经历经了20多亿年的驯化,而人体再面对它时依然会错误地过度反应。正如长错了地方的鲜花与杂草无异,我们的微生物在一个器官中可能极其宝贵,但在另一个器官中却可以变得危险异常;在细胞内是必需品,在细胞外却成了致命物质。“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受到一点抑制,它们就会杀了你;你死后它们会吃了你,”珊瑚生物学家福瑞斯特·罗威尔(Forest Rohwer)说道,“它们才不在乎。你和它们之间不是一段美妙的姻缘,只是一幕纯粹的生物学戏剧。”
所以,在共生的世界里,盟友随时可能背弃,敌人却可以与我们结盟。从共生到毁灭,只有区区几毫米之隔。
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此脆弱?为什么微生物能轻易地在病原体和共生体之间切换?首先,这些角色不像你想象得那么矛盾。试想象,“友好”的肠道微生物需要与宿主建立稳定的关系。它必须在肠道中存活、扎根、不被扫地出门,并与宿主细胞相互作用。这些也是病原体必须做的。因此,无论是共生体还是病原体,无论是英雄还是恶棍,通常都会使用相同的分子,服务于相同的目的。其中一些分子拥有比较负面的名称,比如“毒力因子”(virulence factors),只有当人们生病时,它们才会被发现;但本质上它们是中性的,就如电脑、钢笔和刀这样的工具:可以用来创造美妙的作品,也可以唤醒可怕的妄念。
即使是能给人类带来益处的微生物,也可以间接地伤害我们:先让身体变得脆弱,让其他寄生虫和病原体有机可乘。它们的存在本身导致了纰漏。蚜虫体内某种必需的微生物会释放出一种随空气传播的分子,可以吸引细扁食蚜蝇的注意。这种看起来像黄蜂的黑白昆虫,对蚜虫而言意味着死亡。它的幼虫在其生命史内可以吃掉数百只蚜虫,成虫则通过嗅得这种蚜虫没法不散发的“微生物之香”(Eau de Microbiome)来为后代瞄准猎物。自然界充满了这些不经意的诱惑,就连你,现在也散发着某种气味。某些细菌可以把它们的宿主变成吸引疟蚊的磁体,其他细菌则能把这种小吸血鬼拒之门外。你是不是也曾好奇,为什么二人同时穿过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一个被叮成筛子,另一个则毫发无伤、轻松一笑?其中一部分答案就藏在你的微生物中。

病原体也可以利用我们的微生物发起入侵。比如导致小儿麻痹症的病毒,它会攫住肠道细菌表面的分子,就像抓住绳子一般,随着这些细菌荡入宿主细胞。这种病毒能更好地附着在哺乳动物的细胞上,并且在接触肠道微生物之后,能更稳定地适应人体温暖的体温环境。这些微生物无意间把这种病毒变得更强。

所以,共生并非毫无代价。它们既能帮助宿主,也会捅出娄子。它们需要喂养、寄住和传播,一切都在耗费能量。最重要的是,与所有其他有机体一样,它们有自己的利益目标,但也经常与宿主发生冲突。像沃尔巴克氏体这样依靠母系遗传的共生体,若彻底驱逐其中的雄性,短期内会得到更多的宿主,但长此以往却有令宿主灭绝的风险。如果短尾乌贼体内的细菌停止发光,它们当然可以节省能量,但如果不发光的细菌太多,乌贼就会失去“保护光”,捕食者就会注意到它们并将其双双吞噬。如果肠道微生物抑制了我们的免疫系统,它们当然更容易生长,但我们却会罹患疾病。
自然界中的伙伴关系都是如此。欺骗永存,背叛四伏。伙伴们可能一起工作,但如果其中一方不用太努力或花费太多精力便可搭上便车、获得同样的好处,它肯定会这样做,除非会面对惩罚或被施加管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曾于1930年写道:“每段共生关系背后都多多少少暗藏敌意,只有通过适当的规则加以约束以及精心地调节,才能保持互利状态。尽管人类拥有智慧、能够掌握互利关系的意义,但在人类事务中,互利的伙伴关系也不容易维持。低等生物更是没有这样的理解能力来帮助它们保持关系。相互成立的伙伴关系在建立之初多是盲目的,是他者无意间造就的一种适应。”
曾于1930年写道:“每段共生关系背后都多多少少暗藏敌意,只有通过适当的规则加以约束以及精心地调节,才能保持互利状态。尽管人类拥有智慧、能够掌握互利关系的意义,但在人类事务中,互利的伙伴关系也不容易维持。低等生物更是没有这样的理解能力来帮助它们保持关系。相互成立的伙伴关系在建立之初多是盲目的,是他者无意间造就的一种适应。”

这些原则很容易被遗忘。我们喜欢非黑即白的叙事,英雄与恶棍泾渭分明。过去几年,我见证了从“所有细菌必须被消灭”到“细菌是我们的朋友,希望它们帮助我们”的转向。但是后者与前者是同一种错误的一体两面。我们并不能因为某种特定的微生物生存在我们体内,就简单地假设它是“好”的。甚至连科学家有时也会忘记这点。“共生”这一术语原有的意义已经扭曲,其原本的中立含义“共同生活”被注入了积极色彩,浅薄地暗示着合作与和谐的内涵。但这不是演化的真实面貌,它不一定利于合作,即使结果符合双方利益;它甚至会为最和谐的关系绑上导致冲突的定时炸弹。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暂时移离微生物世界,转而去更宏观的世界看看。以牛椋鸟为例。你可以在非洲大陆找到这些棕色的鸟,它们通常都紧抓在长颈鹿和羚羊的腹侧。人们过去总视它们为清洁工,认为它们会吃掉动物身上的蜱虫和吸血的寄生虫等。但其实它们也会啄向没有闭合的伤口,这就比较不利于动物,会阻碍伤口的愈合,增加感染的风险。牛椋鸟渴望鲜血,而它们满足这种渴望的方式既可以给宿主带去好处,也可能制造危机。珊瑚礁中也上演着如此悲喜交加的闹剧。一种名为清洁工濑鱼的小鱼,在珊瑚礁中经营着“健康水疗中心”。大鱼经过时,濑鱼会食取它们下巴、鳃和其他难以触及之处的寄生虫。清洁工可以饱餐一顿,“客户”也获得了医疗服务。但清洁工有时也会作弊,例如吸取客户身上的黏液和健康组织。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客户便会另觅别地以示警告,而清洁工内部也会惩罚惹恼潜在客户、搞砸生意的同事。还有一例。南美洲的金合欢树依靠蚂蚁防御杂草的侵袭,以及害虫和食草动物的啃食。作为回报,金合欢树会送一些甜味“零食”给它们的“保镖”,让后者住在树上的空心刺中。这看起来像是公平的互助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树会用一种酶阻止蚂蚁消化来源于其他地方的含糖食物。蚂蚁和金合欢树签订了主仆契约。以上这些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合作实例,常常能在教科书和野生动物纪录片中找到。每个参与者都难免卷入冲突、操纵和欺骗之中。

“我们需要区分
重要
与
和谐
这两个概念。微生物组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关系是和谐的。”演化生物学家托比·凯尔斯(Toby Kiers)说道。
 运作良好的伙伴关系其实是一种互惠的剥削,这很容易理解。“两个合作伙伴都可能从中受益,但是其内部固有一种紧张关系。共生是冲突,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冲突。”
运作良好的伙伴关系其实是一种互惠的剥削,这很容易理解。“两个合作伙伴都可能从中受益,但是其内部固有一种紧张关系。共生是冲突,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冲突。”
然而,这种关系可以经由管理保持稳定。夏威夷周围的海域中没有因此而充斥着不发光的乌贼,
 许多感染沃尔巴克氏体的昆虫仍有雄性个体,我们的免疫系统工作正常,所有人都会找到各自的方法与体内微生物保持稳定的关系:促进发挥彼此的功能,且不会轻易背叛。我们演化出各种方式,以此来选择与哪些物种共生,以及学会如何在体内限制和控制它们的行为,使其更倾向于与我们共生,而不是致病。就如经营好每一段关系,这些方式都很耗费精力。生命史上的每一次重大转型——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个体到共生体——都不得不解决同样的问题:如何克服个体的私利,形成合作的团体?
许多感染沃尔巴克氏体的昆虫仍有雄性个体,我们的免疫系统工作正常,所有人都会找到各自的方法与体内微生物保持稳定的关系:促进发挥彼此的功能,且不会轻易背叛。我们演化出各种方式,以此来选择与哪些物种共生,以及学会如何在体内限制和控制它们的行为,使其更倾向于与我们共生,而不是致病。就如经营好每一段关系,这些方式都很耗费精力。生命史上的每一次重大转型——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个体到共生体——都不得不解决同样的问题:如何克服个体的私利,形成合作的团体?
换言之,我如何“包罗”我的“万象”?
包罗万象的方式很像农耕作业。我们用栅栏和围墙标记菜园的边界,为作物施肥,把杂草斩草除根,甚至直接扼杀在萌芽初期。我们为园子选址在一个温度、土壤条件和阳光适宜的地方,为任何我们想要种植的作物提供养分。动物也会采取类似的措施来制定它们和微生物伙伴合作的条款和条件。
 所有与微生物有关的共生细节,待我们细细数来。
所有与微生物有关的共生细节,待我们细细数来。
首先,每个物种的每个身体部位,各自都有动物学意义上的“水土条件”:特定的温度、酸碱度、含氧量,以及其他决定特定微生物可以在那里生长的条件。人体的肠道可能看起来像是微生物的天堂,因为会定期供应食物和水。但是,这样的环境也具有挑战。食物仿佛汹涌的洪流倾泻而入,微生物必须快速生长或携带分子锚而立足。肠道也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依赖阳光制造食物的微生物无法在此处生长。这里还缺氧,所以也解释了为什么绝大多数肠道微生物是厌氧菌,即通过发酵食物生存,在没有氧气的环境下也能生长。其中一些细菌太过依赖厌氧环境,以至于一旦置身有氧环境之中便会死去。
皮肤则完全不同:有的地方像凉爽、干燥的沙漠,比如前臂;有的地方像湿润的丛林,比如腹股沟和腋窝。人体可以照到充足的阳光,但这也会带来潜在的问题,因为阳光通常会带来紫外线辐射。人体周围不缺氧气,并且由于大部分皮肤都暴露在新鲜空气中,所以需氧菌会茁壮成长。然而皮肤上也有隐蔽的一隅,比如汗腺可以庇护痤疮丙酸杆菌( Propionibacterium acnes )这类厌氧菌生长,导致皮肤上长出痤疮。在人体内外,物理和化学规律形塑着生命体。
动物也可以主动改造自己的体内环境,为不同的微生物铺上红地毯,或者设置封锁区。我们的胃会分泌强劲的胃酸,把大多数细菌拒之于外,只有幽门螺杆菌等极能忍受酸性环境的特殊细菌才能驻扎其中。木蚂蚁没有分泌酸的胃,但其身体后端的腺体可以分泌蚁酸。通常情况下,它们喷洒酸性物质是用来防御的,但木蚂蚁也可以从自己的后端吸进蚁酸,酸化消化道,防止不需要的微生物入侵。

这些身体条件制定了准入标准,决定了哪些微生物能够进入人体的某处并生存下来。它们是粗略的过滤器,大致决定了可以与我们共存的微生物类型,同时标出了它们可以落脚的地方。但我们还需要更具体的微调微生物菌群的方法,以及建构起保证它们处在正确位置的坚实围栏。请牢记,自始至终,“位置”都非常重要:微生物可以很容易地从有益的盟友转换为致命的威胁,一切都取决于它们身处何方。所以许多动物体内设置了屏障,把微生物团团围住。我们演化出一套围栏,让微生物相安无事。短尾乌贼用隐窝暗藏它们的发光伙伴。可再生的扁虫把身体的大部分都用于存放微生物。椿象的消化道中间有一条非常狭窄的通廊,可以阻止食物和液体流动,并把肠道的后半部分打造成一间宽敞的微生物公寓。全世界1/5的昆虫,都把它们的微生物共生体包裹在一种特殊的含菌细胞(bacteriocytes)中。

含菌细胞在昆虫的不同谱系中重复演化。一些昆虫把它们安插在其他细胞之间,另一些则把它们捆绑在一起,形成一种名为怀菌体(bacteriome)的器官,像一串串葡萄似的增生到肠道旁。无论它们起源于何处,发挥的功能都大抵相同:储存并控制细菌共生体,阻止它们扩散到其他组织,并保护它们不被免疫系统发现。含菌细胞不是豪华公寓,一个含菌细胞可以包含数以十万计的细菌。它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即使拿沙丁鱼罐头做比,后者所在的空间都可算得上十分宽敞了。它们是以不同形式存在的细胞。
它们也是控制工具。尽管许多昆虫与其共生体之间的依存关系存在已久,但仍然可能爆发大量冲突。如果你觉得这很奇怪,不妨想一想,每年都有数百万人被诊断患有癌症,这是细胞“造反”所导致的疾病,即让细胞抵抗其所在身体的调节作用,不受控制地生长、分裂,形成可能危及宿主生命的肿瘤。癌症细胞其实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既然连身体细胞都可以如此肆无忌惮,那么不难想象,作为一个单独的生命体,弓背蚁体内的布赫曼菌也会像癌细胞一样增殖、扩散。而这种扩增可以演变成一种共生癌症,不经身体控制而疯狂地复制自己,吸收蚂蚁自身所需的能量,并侵入本不应该侵入的细胞。

利用含菌细胞,昆虫可以阻止此类情况发生。昆虫可以控制营养物质穿过含菌细胞的过程,阻止“骗子”共生体出现:它们既违背合作条件,也不为对方提供既定的必需利益;它们会用有害的酶和抗菌的化学物质攻击捕获到的微生物,严格管控群体数量。米象是一种以米和其他谷物为生的长触角甲虫,它们就用这种手段对付自己含菌细胞中的一种伴虫菌(
Sodalis
)
[3]
。这种细菌会产生某种化学物质,在米象体外形成一层硬保护壳。米象在成虫阶段第一次形成这层壳时,会放松对细菌的控制,而后者的数量会翻两番。壳一旦形成,米象便不再需要它的共生伴侣——它们会杀死这些微生物。含菌细胞内的伴虫菌和其他所有内容物都会被米象循环成原材料。接着,细胞自毁。如果是迫于生存形势,米象还会再次使用体内的“细胞监狱”培养足量的细菌,并在伙伴关系不再具有利用价值时销毁它们。

对于脊椎动物而言,内含微生物更加困难。与昆虫的内含细菌相比,人类必须控制一个规模更大的微生物菌群,而且我们体内也没有含菌细胞,大多数微生物都生活在细胞周围,而不是内部。试想象你的肠道。那是一条层层叠叠地堆在一起的极长的管子,如果完全展开,其完整的表面能够覆盖一整片足球场。肠道里云集了数以万亿计的细菌,只有一层上皮细胞(也是隔开其他器官的细胞)阻止它们穿透肠道壁,不然它们就能到达血管,并被带往其他身体部位。肠道的上皮细胞是我们与微生物伙伴的主要接触点,也是最脆弱的防线。如珊瑚和海绵这样的简单水生动物,甚至更脆弱,因为它们整个身体的外部就好比完全浸没在微生物的上皮层中。但即使如此,它们仍能控制这些共生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它们会使用黏液,这种黏糊糊的东西和感冒时堵住鼻子的鼻涕差不多。“黏液太酷了,几乎不会让你失望。”福瑞斯特·罗威尔说道。
 他对此非常了解。多年来,他已经从动物王国中收集了许多不同的黏液样本。几乎所有动物都使用黏液来覆盖暴露在外的身体组织。对人体而言,这些组织包括肠道、肺、鼻子和生殖器;对珊瑚而言,黏液几乎覆盖了所有地方。这些黏性物质是一道物理屏障。黏液由黏蛋白大分子构成:每个分子都由蛋白质构成一条主链,然后分出千万个糖分子分支。这些糖允许多个黏蛋白缠结在一起,形成一片密集、几乎不可渗透的荆棘丛,这一道黏液长城能够阻止有害微生物穿透并进入身体。如果这道防线还不足以构成威慑,那么身体会派出病毒严加看守。
他对此非常了解。多年来,他已经从动物王国中收集了许多不同的黏液样本。几乎所有动物都使用黏液来覆盖暴露在外的身体组织。对人体而言,这些组织包括肠道、肺、鼻子和生殖器;对珊瑚而言,黏液几乎覆盖了所有地方。这些黏性物质是一道物理屏障。黏液由黏蛋白大分子构成:每个分子都由蛋白质构成一条主链,然后分出千万个糖分子分支。这些糖允许多个黏蛋白缠结在一起,形成一片密集、几乎不可渗透的荆棘丛,这一道黏液长城能够阻止有害微生物穿透并进入身体。如果这道防线还不足以构成威慑,那么身体会派出病毒严加看守。
看到病毒二字,你可能会想到埃博拉、艾滋病毒或流感病毒:它们导致疾病,是臭名昭著的恶棍。但大多数病毒主要感染和杀死微生物。它们便是噬菌体,顾名思义,就是细菌吞噬者。它们长有犄角的头部由细长的腿支撑着,好似搭载阿姆斯特朗的“阿波罗”号登月探测器。一旦接触细菌,它们便会把自己的 DNA 注入其中,把该微生物变成制造更多噬菌体的工厂。最终,它们会以致命的方式从微生物宿主中释放出来。噬菌体并不感染动物,其数量也远大于感染动物的病毒。人类肠道中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能支持数以千万亿计的噬菌体。
几年前,罗威尔团队的成员杰里米·巴尔(Jeremy Barr)注意到,噬菌体特别喜欢黏液。在一般环境下,细菌细胞和噬菌体的比例大致是1∶10。
 而在黏液中,这个比例达到了1∶40。在人类的牙龈、小鼠的肠道、鱼皮、海生蠕虫、海葵和珊瑚中,噬菌体也差不多以4倍于宿主的比例存在着。试想象,成群结队的噬菌体,伸长腿、探出头,等待给路过的微生物一个致命的拥抱。并且,这些与黏液相结合的噬菌体,可能不仅仅是用于杀死微生物的粗糙工具。罗威尔怀疑,动物可能可以通过改变黏液的化学成分而招徕特定的噬菌体、杀死某些细菌,同时为别的细菌提供安全通道。也许,这是我们为自己所偏爱的微生物合作伙伴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
而在黏液中,这个比例达到了1∶40。在人类的牙龈、小鼠的肠道、鱼皮、海生蠕虫、海葵和珊瑚中,噬菌体也差不多以4倍于宿主的比例存在着。试想象,成群结队的噬菌体,伸长腿、探出头,等待给路过的微生物一个致命的拥抱。并且,这些与黏液相结合的噬菌体,可能不仅仅是用于杀死微生物的粗糙工具。罗威尔怀疑,动物可能可以通过改变黏液的化学成分而招徕特定的噬菌体、杀死某些细菌,同时为别的细菌提供安全通道。也许,这是我们为自己所偏爱的微生物合作伙伴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
这一畅想可谓影响深远。它表明,噬菌体(记住,噬菌体是病毒)能与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形成互惠关系。它们保证把我们的微生物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作为回报,我们为它们提供一个充满细菌的环境,供它们寄生。就找到寄生对象的概率而言,附着在黏液上的噬菌体比一般条件下高出15倍。并且,由于黏液普遍存在于动物中,噬菌体也随之广泛分布,这种伙伴关系可能在动物王国形成之初就已开始。实际上,罗威尔推测,噬菌体是我们最原始的免疫系统,即动物守住微生物进入体内的最简单手段。
 周围有不少这样的病毒,因此,给它们提供一个可以集中停靠的黏液层并不困难。随着这种基本合作关系的成形,更多更复杂的控制手段也陆续涌现。
周围有不少这样的病毒,因此,给它们提供一个可以集中停靠的黏液层并不困难。随着这种基本合作关系的成形,更多更复杂的控制手段也陆续涌现。
以哺乳动物的肠道为例。其上覆盖了两层黏液:内层非常致密,直接覆盖在上皮细胞上;外层则相对松散。外层的黏液中充满了噬菌体,但也能令微生物在此立足、建立繁荣的菌落,形成一片丰饶之地。相比之下,致密的内层只含有非常少的微生物,这是因为上皮细胞会向这个区域喷射充足的抗菌肽(AMPs)——这种小分子“子弹”能够驱逐侵入其中的微生物。它们创造了罗拉·霍珀口中的“非军事区”:一个紧靠肠道内衬的区域,微生物不能在此定居。

如果有任何微生物能成功地穿过黏液、噬菌体和抗菌肽的重重防守,并偷偷地穿过上皮细胞——不必高兴得太早,因为另一边还有一个营的免疫细胞等着吞噬并销毁它们。这些免疫细胞不只停驻在一边,而是会十分主动地穿过上皮细胞去检查另一侧的微生物,仿佛透过栅栏的板条向另一边窥探。它们一旦在“非军事区”发现细菌,就会马上开始实施抓捕,再把它们带到另一边吃掉。吃多了这些不守规矩的“犯罪分子”,免疫系统也就愈发清楚哪些细菌会在黏液中逗留,从而可以提前制备抗体,准备其他合适的对策。

黏液、抗菌肽和抗体也会左右人体决定哪些微生物可以留在肠道中。
 科学家培育了一种或多种缺失这些成分的突变小鼠,它们体内的微生物会变得不正常,通常会患上某种炎症性疾病。所以,肠道的免疫系统并不是一道不加鉴别的屏障,它不会随意击倒任何正在接近的微生物,而是有选择地施加控制。它的反应很活跃:例如,许多细菌分子刺激肠细胞产生更多黏液;细菌越多,肠道就变得越坚固。同样地,肠细胞接收到细菌出没的信号时会释放抗菌肽,它们并不会持续朝“非军事区”扫射,而是等目标靠太近时才开火。
科学家培育了一种或多种缺失这些成分的突变小鼠,它们体内的微生物会变得不正常,通常会患上某种炎症性疾病。所以,肠道的免疫系统并不是一道不加鉴别的屏障,它不会随意击倒任何正在接近的微生物,而是有选择地施加控制。它的反应很活跃:例如,许多细菌分子刺激肠细胞产生更多黏液;细菌越多,肠道就变得越坚固。同样地,肠细胞接收到细菌出没的信号时会释放抗菌肽,它们并不会持续朝“非军事区”扫射,而是等目标靠太近时才开火。

你可以把这个过程视为免疫系统对微生物组的校准:微生物越多,免疫系统就阻击得越猛烈。或者你也可以说,微生物也在校准免疫系统:触发免疫系统的反应,为自己创造一个合适的生态位,同时置竞争对手于不利之境。如果你认为我们最常见的肠道微生物在不断地适应、力争与免疫系统共存的话,那么后一种看法更能解释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免疫系统就是要摧毁那些致病微生物,然而上述种种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见解。当我写作本书时,维基百科仍然把免疫系统定义为“由一系列生物体结构和生理机制组成的疾病防御系统”。
 免疫系统的激活是因为它探测到了病原体的存在:视其为威胁,然后清除。然而对许多科学家而言,防止病原体入侵只是一项额外技能。免疫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管理我们与体内常驻微生物的关系:更关乎平衡和良好的管理,而不是防御和破坏。
免疫系统的激活是因为它探测到了病原体的存在:视其为威胁,然后清除。然而对许多科学家而言,防止病原体入侵只是一项额外技能。免疫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管理我们与体内常驻微生物的关系:更关乎平衡和良好的管理,而不是防御和破坏。
脊椎动物拥有特别复杂的免疫系统,可以针对特定的威胁定制长期的防御机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得过麻疹或接种过疫苗后,就产生了相应的免疫力。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动物更容易受到感染,相反,乌贼专家麦克福尔-恩盖认为,这是一种历经演化而形成的更复杂的免疫系统,能控制更复杂的微生物组,允许脊椎动物更准确地选择生活在自己体内的微生物物种,并长期保持一种精妙的平衡关系。我们的免疫系统并不会限制微生物,而是会支持更多的微生物共存。

回想前文,我把免疫系统描述为一支管理国家公园的护林员队伍。如果微生物侵袭公园的黏液“栅栏”,护林员会驱逐它们,并加固屏障。护林员会控制任何在公园中占据过于主导地位的物种,也会消灭从外部世界侵入的任何病原体;它们会保持领域内的势力平衡,并不断地抵御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威胁。
护林员只有在我们生命伊始时才不那么忙碌,借用微生物学的术语形容,彼时的我们正处在“白板状态”。为了让第一种微生物定植于新生儿体内,一种特殊的免疫细胞会抑制身体的防御系统——这就是为什么婴儿新生后的六个月内极易受到感染。
 人们通常认为婴儿此时的免疫系统尚不成熟,但事实并非如此,是它故意给微生物敞开了一扇可以自由进入的窗口,让后者得以生存生长。但是,没有免疫系统的选择能力,哺乳动物的婴儿如何确保获得正确的微生物菌群呢?
人们通常认为婴儿此时的免疫系统尚不成熟,但事实并非如此,是它故意给微生物敞开了一扇可以自由进入的窗口,让后者得以生存生长。但是,没有免疫系统的选择能力,哺乳动物的婴儿如何确保获得正确的微生物菌群呢?
母亲会帮助他们。母乳中富含控制成年人微生物菌群的抗体,婴儿通过母乳摄取这些抗体。免疫学家夏洛特·凯泽尔(Charlotte Kaetzel)改造了一种基因突变的小鼠,它们的母乳中不包含其中的一种抗体。然后她发现,这些小鼠的幼体长大后,其肠道微生物组成十分奇怪。
 这些组成与典型的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相仿,其中很多细菌会穿透肠壁,进而导致淋巴结炎症。正如前文所述,许多无害的细菌,只有待在本应该待的地方才无害。母乳可以约束这些细菌。当然,母乳的功用远不止于此。哺乳动物正是通过母乳实现了最令人惊讶的微生物控制手段。
这些组成与典型的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相仿,其中很多细菌会穿透肠壁,进而导致淋巴结炎症。正如前文所述,许多无害的细菌,只有待在本应该待的地方才无害。母乳可以约束这些细菌。当然,母乳的功用远不止于此。哺乳动物正是通过母乳实现了最令人惊讶的微生物控制手段。
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一座陶土砖墙砌起的建筑物俯瞰着一大片葡萄园,旁边还有种满夏季蔬菜的菜园。它像一座托斯卡纳别墅,但不知为何穿越到了美国西部。这其实是一家研究所,在其中工作的科学家十分着迷于研究动物的母乳。研究所的领头人布鲁斯·杰曼,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小个子男人。如果举办一场赞美母乳的比赛,他一定是世界冠军。我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他,与他握了握手,问道:“你为什么对母乳感兴趣?”半小时后,他仍然坐在一颗健身球上,一边捏着破破烂烂的气泡包装垫,一边自言自语般地回答着我的问题。
他说,母乳是完美的营养来源,当之无愧的“超级食品”。这种观点并不常见。到目前为止,与血液、唾液,甚至尿液等其他体液相比,关于母乳的科学出版物少之又少。乳品业投入大量资金从奶牛那儿挤出更多牛奶,但却很少去了解这种白色液体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发挥功用的。医疗资助机构认为它无关紧要,正如杰曼所说,“丝毫无助于缓解中年白人的疾病”。营养学家认为它不过是脂肪和乳糖的简单混合液,很容易被成分差不多的奶粉替代。“人们认为这只是一袋化学物质,”杰曼说道,“它却偏偏不止如此。”
母乳是哺乳动物的演化创新。每一种哺乳动物的母亲,无论是鸭嘴兽还是穿山甲,无论是人类还是河马,都通过“溶解”自身的一部分来制造一种白色的液体,然后通过乳头分泌。这种液体的成分是哺乳动物经过2亿年演化的结果,它们不断调整和完善,以提供婴儿所需的全部营养。这些成分包括名为低聚糖的复合糖。每种哺乳动物都会分泌乳汁,但出于某种原因,人类的母亲混合出了一种特殊的母乳——截至目前,科学家已经识别出了200多种人乳低聚糖,简称 HMO 。
 这是人乳中继乳糖和脂肪后的第三大组成部分,它们理应是婴儿成长过程中丰富的能量来源之一。
这是人乳中继乳糖和脂肪后的第三大组成部分,它们理应是婴儿成长过程中丰富的能量来源之一。
但是,婴儿并不能消化它们。
杰曼第一次听说人乳低聚糖时,简直目瞪口呆。为什么母亲要耗上大量能量制造这些复杂的物质,但没办法为婴儿消化,也因而无助于其成长?为什么自然选择没有淘汰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做法?线索在这里:这些低聚糖能够完好无损地通过胃和小肠,最后抵达大肠——那里生活着大多数细菌。那么,低聚糖也许并不是给婴儿的食物,而是给微生物的食物?
该想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团队做出了类似的发现(双方互不知晓对方的存在)。
 其中一个团队的儿科医生发现,与用奶粉喂养的婴儿相比,一种名为双歧杆菌(
Bifidobacteria
)的微生物更常出现在通过母乳喂养的婴儿的粪便中。他们认为,人乳中必定含有滋养这些细菌的物质,即后世科学家口中的“双歧因子”。同时,另一组化学家发现,人乳中含有牛乳所不具有的碳水化合物,并且会逐渐把这种神秘的化合物分解成更小的物质,其中就包括几种低聚糖。原本平行的两条线最终于1954年相交,理查德·库恩(Richard Kuhn,奥地利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和保罗·吉尔吉(Paul Gyorgy,出生于匈牙利的美国儿科医生,母乳喂养倡导者)开启了一段合作。他们共同证实,神秘的双歧因子与母乳中的低聚糖一样,滋养了肠道微生物。(不同科学分支通常会开展合作,以此来了解不同生命领域间的伙伴关系。)
其中一个团队的儿科医生发现,与用奶粉喂养的婴儿相比,一种名为双歧杆菌(
Bifidobacteria
)的微生物更常出现在通过母乳喂养的婴儿的粪便中。他们认为,人乳中必定含有滋养这些细菌的物质,即后世科学家口中的“双歧因子”。同时,另一组化学家发现,人乳中含有牛乳所不具有的碳水化合物,并且会逐渐把这种神秘的化合物分解成更小的物质,其中就包括几种低聚糖。原本平行的两条线最终于1954年相交,理查德·库恩(Richard Kuhn,奥地利化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和保罗·吉尔吉(Paul Gyorgy,出生于匈牙利的美国儿科医生,母乳喂养倡导者)开启了一段合作。他们共同证实,神秘的双歧因子与母乳中的低聚糖一样,滋养了肠道微生物。(不同科学分支通常会开展合作,以此来了解不同生命领域间的伙伴关系。)
到了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们已经知道母乳中含有超过100种 HMO,但经过详细描述的只有少数几种。没有人知道它们中的大多数是什么样子,或它们喂养了哪种细菌。但众所周知的是,它们公平地喂养着所有的双歧杆菌。杰曼对此并不满意,他想知道谁是食客,它们又点了什么菜。为了得到答案,他从历史研究中寻得一条线索,并组建了一支由化学家、微生物学家和食品科学家组成的多元团队。
 他们一起识别了所有的 HMO,提取并喂给细菌。但是令他们苦恼的是,细菌并没有生长起来。
他们一起识别了所有的 HMO,提取并喂给细菌。但是令他们苦恼的是,细菌并没有生长起来。
这个问题很快变得清晰:HMO 不是双歧杆菌的通用食物。2006年,该团队发现这些糖类有选择地滋养着某种细菌的特定亚种,婴儿双歧杆菌(
Bifidobacterium longum infantis
,长双歧杆菌的亚种)。只要为它们提供 HMO,它们将胜过任何其他肠道细菌,占据肠道优势菌种的位置。另一个与它们关系很密切的亚种是
B. longum longum
,但是为其提供相同的 HMO 后,生长得却很缓慢。讽刺的是,在益生菌酸奶中常见的乳酸乳杆菌(
B. lactis
)根本不能生长。另一种主流益生菌双歧杆菌
B. bifidum
的情况稍微好些,但它是很麻烦的贪食者,会分解几个 HMO,只挑喜欢的部分吃。相比之下,婴儿双歧杆菌会把 HMO 吞得一点不剩,它的30个基因仿佛是为了食用 HMO 而定制的餐具套装。
 其他双歧杆菌并没有这个基因群,那是婴儿双歧杆菌所特有的。人乳已经演化成了专门滋养这种微生物的物质,而这种微生物也演化成了完美的 HMO 食客。不出意外,这也是通常在接受母乳喂养的婴儿肠道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微生物。
其他双歧杆菌并没有这个基因群,那是婴儿双歧杆菌所特有的。人乳已经演化成了专门滋养这种微生物的物质,而这种微生物也演化成了完美的 HMO 食客。不出意外,这也是通常在接受母乳喂养的婴儿肠道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微生物。
婴儿双歧杆菌占据地盘,也赚取相应的回报。它消化 HMO 时,会释放短链脂肪酸(SCFAs)喂养婴儿的肠道细胞。因此,当母亲用母乳滋养这种微生物时,后者也会反过来养育婴儿。通过直接接触肠道细胞,婴儿双歧杆菌还刺激它们制造黏附蛋白,密封肠道细胞间的间隙,另外也会制造调整免疫系统的抗炎分子。这些变化,只在婴儿双歧杆菌食用 HMO 而生长时才会发生。如果它得到的是其他乳糖,那么也能生存下来,但不会参与和婴儿细胞相关的任何互动。它只有在接受母乳喂养时才能释放出全部的有益潜能。同样,对一个孩子而言,母乳可以提供的所有好处也必须经由婴儿双歧杆菌才能实现。
 因此,与杰曼合作的微生物学家大卫·米尔斯(David Mills),实际上是把婴儿双歧杆菌视为母乳的一部分,尽管这一部分并不由乳房分泌。
因此,与杰曼合作的微生物学家大卫·米尔斯(David Mills),实际上是把婴儿双歧杆菌视为母乳的一部分,尽管这一部分并不由乳房分泌。

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人类的母乳脱颖而出:它含有的 HMO 种类是牛奶的5倍,数量更是后者的几百倍之多,就连黑猩猩的母乳也远不及人乳丰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异,不过米尔斯提供了几种可靠的猜想,其中一项与我们的大脑有关。以人类这样的灵长类动物而言,与我们的身长相比,大脑的尺寸可以说非常惊人,而且其快速生长阶段主要集中在我们出生后的第一年内。这种快速生长,部分取决于一种名为唾液酸的营养物质,而它恰巧也是婴儿双歧杆菌食用 HMO 时所释放出来的。如果好好喂养这种细菌,母亲的确可能喂养出更聪明的宝宝。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与独来独往的猿猴相比,社会性强的猿猴,其母乳中的低聚糖含量更高,所含种类也更多样。如果生活在更大的群体中,个体需要记住更多的社会关系、管理更多的伙伴关系、与更多的对手过招。许多科学家认为,这些需求驱动了灵长类动物的智力演化,也许也促进了 HMO 的多样发展。
另一种猜想与疾病有关。病原体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宿主跳到另一个宿主身上,所以群居动物需要保护自己免受传染病感染。HMO 提供了这样一道防御机制。当病原体感染我们的肠道时,它们几乎总是第一时间缠住附着在肠道细胞表面的多糖。但是,HMO 与这些肠道中的多糖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病原体有时会转而缠住它们。它们可以作为诱饵,转移攻击婴儿自身细胞的火力。它们可以阻止一连串在肠道内为非作歹的“坏菌”:沙门氏菌(
Salmonella
)、李斯特菌(
Listeria
)、霍乱弧菌(
Vibrio cholerae
,导致霍乱的罪魁祸首)、空肠弯曲菌(
Campylobacter jejuni
,细菌性腹泻的最常见诱因)、痢疾内变形虫(
Entamoeba histolytica
,一种凶残的变形虫,会引起痢疾,每年致死10万人),以及许多大肠杆菌强毒株。它们甚至可能阻止艾滋病毒——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携带 HIV 病毒的母亲用母乳喂养时不会感染婴儿,尽管母乳本身携带病毒。每当有 HMO 存在时,即使科学家散播了病原体,培养出来的细胞也总是毫发无损。这有助于解释,与用奶粉喂养的婴儿相比,为什么用母乳喂养的婴儿更少发生肠道感染,以及其体内为什么存在这么多种 HMO。“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只有足够多样的 HMO 才能针对包括病毒和细菌在内的不同病原体,”米尔斯表示,“我认为,这种惊人的多样性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保护措施。”

该团队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他们在那座仿托斯卡纳风格的研究所内设立了一座非常厉害的母乳加工设备,希望借此从这种最为人类熟悉的液体中,发现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主实验室由米尔斯与食品科学家丹妮埃拉·巴丽勒(Daniela Barile)共同负责,里面有两个储存母乳的巨型钢桶,还有一台看起来像卡布奇诺咖啡机的巴氏灭菌器,以及其他一些用于过滤液体和分解成分的设备。附近的机架上摆放着数百个白色空桶。巴丽勒告诉我:“它们通常都是装满的。”
装满母乳的白色巨桶保存在一个巨大的步入式冰柜中,里面的温度维持在零下32摄氏度,人根本待不住。一旁的长凳上摆着一排长筒雨靴(“我们加工母乳时会洒得到处都是。”巴丽勒解释道)、一把用来锤冰的锤子(“门总是关不严”),另外还莫名其妙地放着一台火腿切片机(我没问为什么)。我们把头探进去,看到白色巨桶依次排列在托盘和架子上,里面大约有2,728升母乳,其中很多是乳制品商捐赠的牛奶,但取自人类的母乳也储量庞大。“很多妈妈会吸一些母乳储存起来,但她们的孩子断奶后,这些母乳能有什么用呢?她们打听到我们,把母乳捐给我们,”米尔斯解释道,“我们从斯坦福大学的某个人手里收集到了80升母乳,一共花了两年时间。那人问我们:‘我有这么些母乳,你们要不要?’”当然要。他们需要很多很多母乳。
他们计划研究母乳的组成部分,包括 HMO 和其他物质,比如附着多糖的脂肪和蛋白质(它们又是如何影响婴儿双歧杆菌和其他的双歧杆菌?),还有噬菌体。杰曼与杰里米·巴尔(Jeremy Barr)共同合作,探究母亲是否通过母乳把一系列共生病毒传递给婴儿。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现象:噬菌体本来就很擅长附着在黏液上,但如果有母乳的帮助,它们的附着效率能提高十倍。母乳中的某些成分能够帮助它们固定在合适的地方。而促成此事的,似乎是一小块包裹在黏液般的蛋白质中的脂肪。静置一杯乳汁,浮在表面的脂肪层里就充满了这些小球。它们为婴儿提供营养,但也可能在婴儿肠道中为他们遭遇的第一个病毒提供立足之处。
当巴尔告诉我这一机制时,我十分惊讶。这意味着,我们塑造和控制微生物组(噬菌体也好,黏液也罢,甚至还包括免疫系统的各种装备与母乳中的成分)的手段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先前把它们作为分离的工具单独讨论,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一个纵横交织的庞大系统中的一部分,而正是这个系统在维持我们与微生物的稳定关系。在这种违反直觉的现实中,病毒可以是盟友,免疫系统可以支持微生物的生存,哺乳期的母亲不仅通过母乳喂养婴儿,还为下一代建立起了一整个微生物世界。母乳到底是什么?杰曼是对的:它远不止是一袋化学成分;它同时滋养着婴儿和婴儿双歧杆菌。这是一个初步的免疫系统,可以防止更邪恶的微生物入侵。母亲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从第一天开始就确保宝宝能交上正确的伙伴。
 母乳帮助宝宝为迎战未来的生活挑战做好准备。
母乳帮助宝宝为迎战未来的生活挑战做好准备。
一旦断奶,我们就必须自力更生地滋养微生物。我们会通过膳食为肠道输送一股股多糖,以替代失去的 HMO。另外,我们也会制造多糖,比如肠道黏液中就充满了这些多糖,仿佛一片为肠道微生物准备好的丰美牧场。如果我们继续为它们提供正确的食物,便能培育出可能有益于健康的细菌,并把更容易带来健康隐患的细菌排除在外。喂养微生物太必要了,即使我们自己停止进食,这项工作也在继续。动物生病时常常会失去食欲,这其实是一项明智的生存策略,能够省下觅食的能量,专注于恢复。这也意味着,肠道微生物会经历暂时的饥荒。生病的小鼠会通过释放应急“存粮”——一种名为岩藻糖的单糖——来处理这个问题。肠道微生物可以切断并消化这种单糖,存活下来,等待宿主恢复正常,再给它们喂食。

拟杆菌属(
Bacteroides
)擅长消化这些多糖,它们很快便成了肠道中最常见的微生物。但关键是,多糖如此多样,没有哪种细菌拥有消化所有多糖的工具。这意味着,吃下种类丰富的多糖,可以支持多样细菌的生存。有些是像鸽子或浣熊那样随和的杂食者,还有一些则像熊猫或食蚁兽一样特别挑食。这些微生物共同形成了一张食物网,其中一些攻克最大、最难分解的分子,并释放较小的碎片,供其他微生物享用。两种微生物同时出没时会缔结盟约,互相喂食,各自消化不同的食物,同时产生对方可以利用的化学物质;它们调节代谢动作,彼此和平相处,避免与邻居发生冲突。

这些相互作用十分重要,因为可以维持整个系统的稳定。如果单个细菌的多糖消化效率太高,它可能会消耗黏液屏障,产生空隙,使其他微生物得以进入。但是,如果有数百种彼此竞争的物种,它们就可以防止彼此变成垄断食物供应的贪食鬼。我们为肠道提供多样的营养,也饲养了种类繁多的微生物,保持这个巨大、多样的菌群的稳定性。而这些菌群也会反过来使病原体的侵入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在餐桌上摆上正确的食物,能够确保邀请到正确的客人,把不速之客拒之门外。母亲在我们的生命之初为我们设定了正确的方向,我们延续着她们的工作。
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让宿主减少与微生物发生冲突,但是比较极端:它们可以彼此依赖,直到变成一个真正的单一实体。
 细菌在宿主细胞内落脚,并通过父母忠实地传递给后代,让双方的命运因此而紧紧相连。它们仍然有各自的利益,但又有一定重叠,能让剩余的任何分歧都变得可以忽略不计。
细菌在宿主细胞内落脚,并通过父母忠实地传递给后代,让双方的命运因此而紧紧相连。它们仍然有各自的利益,但又有一定重叠,能让剩余的任何分歧都变得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安排在昆虫中特别常见。它们倾向于把捕获到的微生物纳入一种可预测的简化螺旋中。在宿主的细胞中,它们的群体大小受到限制,并与其他细菌分离。这种隔离让它们的 DNA 出现了有害的突变。任何不必要的基因都会出现缺陷且无法发挥作用,乃至彻底消失。
 如果把一个新的共生体塞入一只昆虫体内,并且快进播放演化过程,你便能看到一场剧烈的动荡:它的基因组不断被扭曲、碾碎、收缩。最终,基因组皱缩成一团,趋近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典型的自由生活的微生物,例如大肠杆菌,其基因组由大约460万个碱基对组成。而已知最小的共生体
Nasuia
,只有11.2万个碱基对。如果大肠杆菌的基因组和本书一样厚,那么
Nasuia
只有前言那几页。这些共生体已经完全被驯化,不能独立生存,必须永远寄住在昆虫体内。
如果把一个新的共生体塞入一只昆虫体内,并且快进播放演化过程,你便能看到一场剧烈的动荡:它的基因组不断被扭曲、碾碎、收缩。最终,基因组皱缩成一团,趋近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典型的自由生活的微生物,例如大肠杆菌,其基因组由大约460万个碱基对组成。而已知最小的共生体
Nasuia
,只有11.2万个碱基对。如果大肠杆菌的基因组和本书一样厚,那么
Nasuia
只有前言那几页。这些共生体已经完全被驯化,不能独立生存,必须永远寄住在昆虫体内。
 宿主常常依赖于这些被驯化的共生体,以获得营养或其他重要益处。这个过程与古老的细菌转化为线粒体相仿,而我们离了线粒体就不能生存。
宿主常常依赖于这些被驯化的共生体,以获得营养或其他重要益处。这个过程与古老的细菌转化为线粒体相仿,而我们离了线粒体就不能生存。
这些融合是减轻宿主和微生物之间冲突的有效方法,但也有其阴暗的一面。约翰·麦卡琴(John McCutcheon)是一个高大的光头生物学家,戴着眼镜,笑容灿烂。他在研究一种生命周期为13年的周期蝉时注意到了这一点。这种黑体红眼的虫子,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以若虫形态藏在地下,从植物根部吸取营养。13年暗无天日的日子过去之后,这些蝉会同时蜕化,然后把粗腔横调的合唱注入空气。经过一波疯狂的交配,它们会在同一时间死去,腐败的躯壳覆满大地。这些蝉的生活方式太过奇怪,麦卡琴怀疑它们可能含有同样奇怪的共生体。他猜对了,只是目前尚不清楚它们究竟有多奇怪。
这种蝉的共生体 DNA 序列一团糟。它们看起来好像应该都属于同一个基因组,但又好像是有人从同一幅拼图的几个不完整的副本中找出了一些混乱的碎片塞给麦卡琴。他带着困惑转而研究另一种蝉:一种来自南美洲的寿命更短、更多毛的物种。他发现了同样的问题:DNA 片段无法拼合成一个单一的基因组——不过,倒是能拼出两个。
这两个基因组从属的细菌,是一种名为霍奇金氏菌(
Hodgkinia
)的共生体的后代。这种微生物一旦进入多毛的蝉,便会以一定程度在其体内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物种”。
 这些后续物种都丢失了霍奇金氏菌的部分原始基因,但丢弃的部分各有不同。即使能模糊地从中看出各自从前的样貌,它们目前的基因组则完全互补。它们就像一个整体的两半:霍奇金氏菌原先能做的,没有什么是这两种后续细菌不能一起做的。
这些后续物种都丢失了霍奇金氏菌的部分原始基因,但丢弃的部分各有不同。即使能模糊地从中看出各自从前的样貌,它们目前的基因组则完全互补。它们就像一个整体的两半:霍奇金氏菌原先能做的,没有什么是这两种后续细菌不能一起做的。
麦卡琴花了近一年时间来研究其中的原理,当他最终发现其中的奥秘时,那种13年周期蝉的混乱共生之谜就变得格外清晰。这种昆虫也含有霍奇金氏菌,并不是只分成了两种,而是分裂成了许多种,具体数量谁也不知道。它的 DNA 最终能拼合成至少17个不同的环,最多甚至可达50个。是不是每个霍奇金氏菌都是不同的物种?或者有没有某个谱系,可以涵盖这些基因组在不同环之间的分裂?没人知道。无论如何,该团队现在研究了很多其他的蝉,经常发现相同的模式。在一种智利蝉体内,霍奇金氏菌已经分裂成了6个互补的基因组。

在所有这些研究案例中,制造重要维生素的基因都分散在蝉的基因组和它们的霍奇金氏菌共生体中,整个集合只有在每个成员都不缺席的情况下才能存活。从短期来看,它们相安无事;但从长期来看……谁知道呢?如果霍奇金氏菌继续分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而且所有碎片都至关重要,那么整个菌群将陷入难以置信的危险境地,一处细微的损失就可能令整体走向灭亡。“这就像眼睁睁地看着火车撞得粉碎,或是目睹一起放慢镜头的灭绝事件,”麦卡琴说道,“它让我对共生有了不同的看法。”他之前总是把共生视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认为共生能为合作伙伴提供好处与机会,但现在却发现它也可以是一个陷阱,合作伙伴在依赖共生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脆弱。麦卡琴的前导师南希·莫兰(Nancy Moran)称这是一个“演化的兔子洞”(《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隐喻),意思是,这是“踏上了一场不可逆转的旅程,进入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世界,普通的规则均不再适用”。
 一旦合作双方不慎跌入兔子洞,二者都很难再度逃离。洞的底部没有奇迹,等待它们的只有灭绝。
一旦合作双方不慎跌入兔子洞,二者都很难再度逃离。洞的底部没有奇迹,等待它们的只有灭绝。
这是共生的代价。即使不像蝉的共生体那样对其宿主至关重要,微生物仍然能对我们的生活和健康造成巨大的影响。它们一旦离群失去控制,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和其他动物已经演化出了许多方式来保持菌群的稳定。我们通过体内的生化机制限制它们,给它们围起物理屏障。我们可以选择“胡萝卜”,精选食物喂养它们;也可以采用“大棒”策略, [4] 命令噬菌体、抗体和免疫系统中的其他部分击溃它们。面对宿主与微生物之间永恒的冲突,我们有许多解决方案;为了执行与微生物缔结的契约,我们同样有许多办法。
不幸的是,我们人类也无意间发展出了许多破坏契约的方式。
[1] 有可能是更常见的海洋细菌。其中原绿球藻( Prochlorococcus )非常常见,从海洋表面汲取一毫升水,其中就可能含有十万个原绿球藻。这些原绿球藻贡献了空气中大约20%的氧气。每吸进五口气,就有一口氧气来自这些细菌。但要讲完它们的故事就得重写另一本书了。
[2] 西奥多·罗斯伯里憎恨“机会主义”这个术语。“这个名词再次暗示了这种隐喻,即微生物也有人类的恶习,”他写道,“所有微生物、所有生物,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应身边环境的变化。可能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种种机会,都会把无害的微生物转化成有害的微生物。”他创造了另一个术语:双重性( amphibiosis ),用于描述在某些情况下有所帮助,但在其他情况下却会加害对方的自然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一个拥有积极意义的术语,甚至是美丽的,但也许是不必要的,因为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合作伙伴关系都是如此。
[3] Sodalis 源于拉丁语中的“伙伴”(sodalis),由于与特定昆虫物种构成的共生关系,本书采用“伴虫菌”这一译名。——译者注
[4] “胡萝卜加大棒”是一种奖励与惩罚并行的策略,其中“胡萝卜”对应奖励,“大棒”对应惩罚。——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