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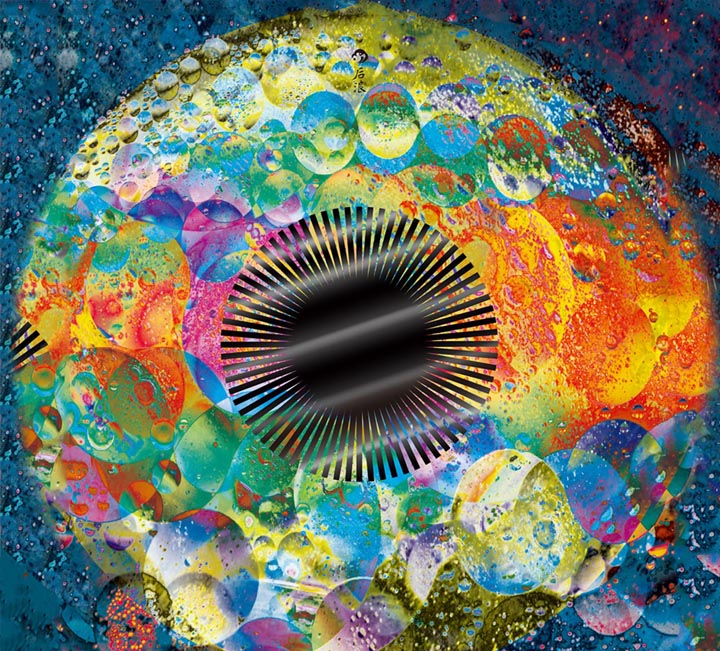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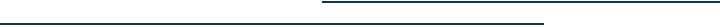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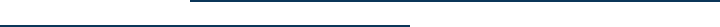
“你要找的东西大概有高尔夫球那么大。”妮尔·贝基亚雷斯(Nell Bekiares)向我说明道。

这里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间实验室,我正在窥视一个小鱼缸的内部。它看起来是空的,没有什么高尔夫球大小的东西。实际上,除了一层沙子,我什么都没看到。贝基亚雷斯把手轻轻探入水中,忽然有什么东西往外喷射出一团黏稠的、墨水般的黑云,我这才注意到缸里有一只大约只有我拇指大小的雌性夏威夷短尾乌贼(Hawaiian bobtail squid)。贝基亚雷斯用勺子把乌贼舀到碗里,只见它慌张地四处喷射,身体透白如幽灵,触腕伸展,侧鳍疯狂摆动。过了一会儿,它慢慢平静下来,把触腕卷进身体下方,悬浮在水中漫游,从飞镖变成一颗豆豆糖的形状。它的皮肤也变了样,有色小点从针眼大小迅速扩大成圆斑,遍布身体各处:深褐色、红色、黄色,其间还点缀着闪亮的微粒。乌贼不再透白,它此刻的颜色宛若修拉 [1] 笔下的秋天。
“变成这种褐色时,说明它们很高兴,”贝基亚雷斯解释道,“褐色代表状态不错。通常雄性更容易被激怒,它们会不停地喷啊喷,喷得到处是墨。它们往你脸上或胸口射水时,很可能就是故意的。”
我被迷住了。这种乌贼真有性格,而且美得惊人。
碗里没有其他动物,但这只乌贼并不孤单。它的身体底部有两个腔体(也是发光器官),里面充盈着一种名为费氏弧菌( Vibrio fischeri )的发光细菌,它们会向下投射微光。这些微光暗弱得连在实验室的荧光灯下都看不到。不过,这种乌贼的真实生境是夏威夷周围较浅的礁坪,而这些微光会让它们在那种环境中显得更加醒目。但是到了夜晚,微光恰似洒在海面上的柔和月光,正好模糊了乌贼的身影,使海洋中的捕食者无法发现它们。可以说,这种动物没有影子。
从下往上看,短尾乌贼可能是隐身的,但从上往下看就很容易发现它们。所以你只需飞到夏威夷,等夜幕降临后,戴上头灯、拿着网兜,涉进齐膝深的海水;只要反应足够迅速,日出前就可以抓到半打。之后的饲养也很容易,喂食、繁殖都不难。这间实验室的负责人是动物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福尔-恩盖,她说道:“如果它们能在威斯康星州的中部存活,那么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问题。”这位泰然自若、举止优雅又热情洋溢的科学家,近30年来一直在研究这种乌贼和它的发光细菌。她把该项目打造成了共生领域的标志性研究,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磨砺成了一位传奇人物。她在同事眼中有着很多面:直言不讳的反叛者、热情的滑板爱好者(希望没让读者朋友太意外),并且早在微生物组成为时髦流行语之前,就开始不懈地倡导微生物研究。一位生物学家告诉我:“当她谈到‘新生物学’时,这个词条全部都是大写加粗的。”可她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想的,正是这种乌贼让她改变了主意。

麦克福尔-恩盖在研究生阶段研究了一种同样携带发光细菌的鱼类。她深深地为其吸引,但却遇到了令她十分沮丧的研究困境。因为她发现不可能在实验室里繁殖这种鱼类,所以之前抓到的每一条鱼实际上均已被细菌定植。她不能回答真正引发她深度好奇的问题:发光细菌和鱼第一次相遇时发生了什么?它们如何建立起联结?是什么让别的微生物不再占领宿主?直到有一天一位同事问她:“嗨,你有没有听说过这种乌贼?”
夏威夷短尾乌贼对于胚胎学家而言已经十分熟悉,它们携带的发光细菌也早已为微生物学家关注,但二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却完全遭到了忽略。可正是这种伙伴关系激发了麦克福尔-恩盖的研究热情。不过,她首先要为自己招募一名伙伴,一个十分了解细菌的人,其知识水平可以与她自己在动物学研究方面的专业素养相辅相成,这个人便是内德·鲁比(Ned Ruby)。“我想,我是她问过的第三个微生物学家,不过是第一个答应的。”鲁比说道。二人成了专业上的伙伴,随后又成了生命中的伴侣。鲁比有像冲浪男孩一样的悠闲气质,麦克福尔-恩盖则如政治家一般好强,两人刚好阴阳互补,只不过他为阴、她为阳。他们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俩“构成了真正的共生关系”。如今,他们的实验室相互紧挨,甚至会用同一只乌贼做实验。
这些动物被安置在一道水槽中。这一装置沿着狭窄的走廊直线排放,一次可容纳24只乌贼。每当新一批乌贼运抵实验室后,贝基亚雷斯会随机挑选一个字母,让所有学生用相应的字母开头组词,为这些乌贼命名。我在那儿见到的雌性乌贼分别是耀西(Yoshi)、雅虎(Yahoo)、伊索德(Ysolde)、亚德利(Yardley)、亚拉(Yara)、伊芙(Yves)、优素福(Yusuf)、优克尔(Yokel),还有一位雅克(Yuk)先生,它们共同生活在附近的水槽中。雌乌贼每两周会共赴一场“约会之夜”;完成交配后,她们被安置在布满聚氯乙烯(PVC)管子的育儿室中。她们通常会产下几百枚卵,而这些卵一般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孵化。我们参观育苗室时发现,架子上放了一口小碗,里面上下浮游着几十只乌贼宝宝,每只都只有几毫米长。10只雌性乌贼一年能产下并孵化6万只小乌贼,这也是它们能作为理想的实验室动物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幼体出生时是无菌的。在野外环境下,它们出生几小时后就会被费氏弧菌定植;而在实验室,麦克福尔-恩盖和鲁比可以控制幼体接触共生体的过程。他们可以用发光的蛋白质标识费氏弧菌,跟踪它们进入乌贼的发光器官,从而目睹完整的伙伴关系形成过程。
一开始是物理过程。发光器官的表面覆盖着黏液以及舞动的纤毛。纤毛会制造一股湍流,从而吸进细菌大小的颗粒,但更大的颗粒会滞留在外。这些微生物积聚在黏液中,其中就有费氏弧菌。接着,物理过程让位于化学过程。一个费氏弧菌接触乌贼不会发生什么;两个呢?依然没动静。但是如果达到五个,乌贼基因中的计数器就会启动。这些基因会让乌贼生成一种含有多种抗菌化学物质的混合物,令费氏弧菌免受伤害,但同时又让周围环境变得不适合其他微生物生存。其他基因会指导合成并释放一种酶,这种酶能分解黏液,并产生一种吸引更多费氏弧菌的物质。这些变化解释了:尽管一开始其他细菌的数量是费氏弧菌的几千倍,最终为什么却是后者迅速占据了黏液层。是费氏弧菌,也只有它拥有转变乌贼体表环境的能力、吸引更多同类,并阻止竞争对手落脚。它们就像科幻故事的主角,把荒凉的星球改造成宜居的家园。只不过,这次的场景从星球换到了动物的身体。
改变乌贼的体表后,费氏弧菌开始向体内移动。它滑进几个小孔,向下穿过一条很长的管道,挤过一个瓶颈部位,最终到达封闭的隐窝。它的入驻进一步改变了乌贼的身体。隐窝周围排列着的柱状细胞此时变得更大、更密集,把刚刚到达的微生物紧紧围住。等细菌适应经过改变的体内环境,它们身后的大门就会关闭。隐窝入口变窄、管道收缩,纤毛覆盖的地方也逐渐退化。这时候,发光器官已经成熟。被正确的细菌定植后(再次强调,费氏弧菌是唯一能够完成这趟旅程的微生物),乌贼不会再被其他微生物定植。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种不起眼的小动物所经历的特殊成长过程,似乎充满了神秘的细节。但拨开迷雾,这种乌贼个例其实暗含了深远的意义,并很快得到了麦克福尔-恩盖的重视。1994年,她完成了乌贼的第一阶段研究,写道:“我们通过这些研究首次得到了证明以下结果的实验数据,即特定的细菌共生可以诱导动物的发育。”
换句话说,微生物形塑了动物的身体。
那么,究竟是怎样塑造的呢?2004年,麦克福尔-恩盖的研究小组发现,费氏弧菌表面的两种分子是主导转变的左右手,它们分别是肽聚糖(PGN)和脂多糖(LPS)。这令人十分惊喜。当时只有与疾病相关的用语才会涉及这些化学物质,人们把它们描述为与病原体相关的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简称 PAMPs),即唤醒动物免疫系统对抗感染扩散的警报器。但费氏弧菌并不是致病菌,它和导致霍乱的细菌有关联,但并不会伤害乌贼。所以,麦克福尔-恩盖更正了缩写,把代表致病性的第一个 P 换成了更包容,同时也代表了微生物的 M,把这种分子模式重新命名为 MAMPs。这个新名词象征着微生物研究统合成了一门专业学科,并告诉世人:这些分子不只是疾病的表征。它们的确可以引发有损健康的炎症,但也可以与动物开启一段美好的友谊。没有它们,乌贼的发光器官不会正常发育;没有它们,乌贼尽管可以生存下去,但却不会走向完整的成熟状态。
现在我们都很清楚,从鱼到老鼠再到其他许多动物,它们的生长都伴随着细菌伙伴的影响,就像塑造乌贼发光器官的 MAMPs 一样,支持着动物的成长。
 多亏了这些发现,我们可以用全新的视角看待从受精卵到一个功能齐全的成熟个体的发育过程。
多亏了这些发现,我们可以用全新的视角看待从受精卵到一个功能齐全的成熟个体的发育过程。
如果你小心地把受精卵分离出来,人类的可以,乌贼的也行,任何动物的都没问题,然后放到显微镜下观察,你最终会看到它们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细胞逐渐变大,长出褶皱和隆起,形状开始扭曲。细胞间交换信号分子,相互告知各自需要在哪里形成什么组织或器官。身体各部位就这样陆续形成。一个胚胎只要得到足够的营养,就会不断地生长,整个过程看似完全由自身调控完成,仿佛一个单靠自己就可以有条不紊地快速运行的复杂计算机程序。但是,夏威夷短尾乌贼和其他动物的例子告诉我们,个体的发育并不这么简单。该过程不仅在动物的基因指令下进行,也受微生物基因的影响。个体的发育裹挟在微生物与动物的持续协调之中——多个物种共同互作,但具体影响的是其中一种物种的发育过程。而这正是整个生态系统的运作方式。
如何判断某个动物是否需要微生物才能正常发育呢?最简单的方法是剥离它们身上的微生物。有些物种会直接死去:例如,如果没有微生物,携带登革热的埃及伊蚊(
Aedes aegypti
)发育到幼虫状态后就不能再继续发育。
 有些物种可以稍稍应付无菌状态:例如,失去微生物的夏威夷短尾乌贼只是失去了发光能力,若继续生活在麦克福尔-恩盖的实验室里,那么问题不大;但失去伪装的它们,一到野外就很容易被捕食者锁定目标。就最常见的实验动物而言,科学家几乎饲养过所有动物的无菌版本,斑马鱼、苍蝇、小白鼠,等等。这些动物也能继续生存,但已大不同于原来。“总的来说,无菌动物非常可怜,它们生命历程中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几乎都需要人工替代品来补充所缺乏的细菌,”西奥多·罗斯伯里写道,“它就像一个脆弱的孩子,我们只能把它放在玻璃后面,隔绝外界所有的侵害。”
有些物种可以稍稍应付无菌状态:例如,失去微生物的夏威夷短尾乌贼只是失去了发光能力,若继续生活在麦克福尔-恩盖的实验室里,那么问题不大;但失去伪装的它们,一到野外就很容易被捕食者锁定目标。就最常见的实验动物而言,科学家几乎饲养过所有动物的无菌版本,斑马鱼、苍蝇、小白鼠,等等。这些动物也能继续生存,但已大不同于原来。“总的来说,无菌动物非常可怜,它们生命历程中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几乎都需要人工替代品来补充所缺乏的细菌,”西奥多·罗斯伯里写道,“它就像一个脆弱的孩子,我们只能把它放在玻璃后面,隔绝外界所有的侵害。”

无菌动物的怪异生物学在肠道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一条运作良好的肠道需要巨大的表面来吸收营养,这也是为什么肠壁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手指状的突起。流经肠道的食物会严重地磨损表皮细胞,所以需要不断地再生更新。表层下面必须分布丰富的血管网络,因为需要运载和输送营养物质。肠壁应该密而不漏——细胞间必须紧紧相连,防止外来分子(和微生物)渗漏到血管中。如果没有微生物的参与,所有这些基本属性都会大打折扣。在无菌环境下长大的斑马鱼或小鼠,其肠道无法充分发育,指状突起较短,肠壁容易渗漏,血管看起来更像是稀疏的乡间小路,而不是密集的城市电网;与此同时,细胞本身也缺乏再生的驱动力。如果适当地给这些动物施予微生物或单独的微生物分子,就可以简单地矫正许多小缺陷。

这些细菌并不直接重塑肠道本身。相反,它们通过与宿主合作而达成目标,这使得它们更像是管理者而不是劳工。罗拉·胡珀(Lora Hooper)给无菌小鼠注射一种常见的肠道菌——多形拟杆菌(
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
,或 B-theta)后证明了这一点。
 她发现,微生物激活了小鼠体内多方面的基因,涉及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建立不渗透的屏障、分解毒素、建造血管,以及创建成熟细胞等。换言之,该微生物教会了小鼠如何使用小鼠自己的基因,进而打造出一个健康的肠道环境。
她发现,微生物激活了小鼠体内多方面的基因,涉及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建立不渗透的屏障、分解毒素、建造血管,以及创建成熟细胞等。换言之,该微生物教会了小鼠如何使用小鼠自己的基因,进而打造出一个健康的肠道环境。
 发育生物学家斯科特·吉尔伯特(Scott Gilbert)把这个模式称为共同发育(co-development)。这与你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微生物只会威胁人体健康的印象相去甚远,相反,微生物真的在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模样。
发育生物学家斯科特·吉尔伯特(Scott Gilbert)把这个模式称为共同发育(co-development)。这与你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微生物只会威胁人体健康的印象相去甚远,相反,微生物真的在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模样。

怀疑论者可能会争辩,小鼠、斑马鱼和短尾乌贼并不需要微生物才能发育:一只无菌小鼠看起来仍然像小鼠,走路像小鼠,叫声也像小鼠,因此,除掉细菌后并不会突然得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动物。但是无菌动物只能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中:一个恒温、有充足的食物和饮水、没有捕食者和任何形式的传染源的安全气泡之中。在残酷的野外,它们无法生存很长时间。它们可以存在,但可能无法存续。它们可以单独发育,但与微生物伙伴一起显然可以过得更好。
为什么呢?为什么动物会把自身的发育阶段外包给其他物种?为什么不自己完成一切?“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曾与无菌小鼠和乌贼一起工作过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解释道,“微生物是动物生命的必要组成部分,不可能摆脱它们。”请记住,动物出现在地球上时,微生物已经挤满地球长达数十亿年之久。在人类出现以前,它们才是这个星球长久以来的统治者。我们出现后当然会与周围的微生物相互作用,一同演化。如果你捂着双眼、塞住双耳、堵上嘴巴地搬进一座新城市,不得不说,这看起来很荒唐。除此之外,微生物不仅仅是不可避免的,还十分有用。它们为最早出现在地球上的动物提供食物。而它们的存在也为动物提供了寻找营养丰富地带的宝贵线索,指示适合生存的气温或者适宜定居的平坦表面。通过感知这些线索,那些最早出现的动物获取了关于周围世界的重要信息。正如我们接下去会看到的,那些古老的互动痕迹,今天仍然比比皆是。
妮科尔·金(Nicole King)现在离家正远。她平时负责运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实验室,不过目前正在伦敦休假。她马上要带8岁的儿子内特(Nate)去看音乐剧《舞动人生》( Billy Elliot )的日场演出,只要他能在公园长椅上耐心地坐上半个小时,等我们在一旁谈论完一种鲜为人知的生物:领鞭毛虫(choanoflagellates)。金是全世界少数专门研究这种生物的科学家之一,她亲切地称其为“领鞭”(choanos),我也干脆跟着她这样称呼。
它们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的水域,从热带的河流到南极冰面下的海洋。我们正说着,一旁正在笔记簿上安安静静涂鸦的内特,忽然兴奋地凑了过来,并画下了一条领鞭毛虫。他勾勒出一个长着蜿蜒尾巴的椭圆,还缀上了细丝一般的“领口”(collar),活像一颗穿着短裙的精子。摇动的尾部会驱动细菌和其他碎屑朝“领口”游动,然后领鞭会围住、吞食和消化它们。领鞭是一种活跃的捕食者。内特的涂鸦漂亮地抓住了这种动物的精髓,尤其是领鞭作为单细胞生物的特征。它们是与你我一样的真核生物,功能强大,拥有线粒体和细胞核(细菌则不具备)。但是,和细菌一样,它们仅仅由一个自由游动的细胞构成。 [2]
这些细胞有时会表现出具有社会性的一面。金特别喜欢玫瑰领鞭毛虫(
Salpingoeca rosetta
)
 ,它们往往会形成一团花簇样的菌落。内特依旧可以把它们画下来:几十个领鞭头部朝内地聚在一起,尾部不断向外挥舞,像某种毛茸茸的覆盆子。从外观上看,这像是一组游到一起的领鞭毛虫凑成了一团,但这种形状实际是分裂所致,而非各条领鞭个体碰撞在一起的结果。领鞭的繁殖方式是一分为二,但有时两个子细胞不能完全分裂,而是通过短桥相连。这种情况一再发生,直到这些联结在一起的细胞裹上了一层鞘,形成了一个球。这就是所谓的“玫瑰丛”(rosette)。这团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微小生物,其实是与地球上所有动物关系最近的物种,
,它们往往会形成一团花簇样的菌落。内特依旧可以把它们画下来:几十个领鞭头部朝内地聚在一起,尾部不断向外挥舞,像某种毛茸茸的覆盆子。从外观上看,这像是一组游到一起的领鞭毛虫凑成了一团,但这种形状实际是分裂所致,而非各条领鞭个体碰撞在一起的结果。领鞭的繁殖方式是一分为二,但有时两个子细胞不能完全分裂,而是通过短桥相连。这种情况一再发生,直到这些联结在一起的细胞裹上了一层鞘,形成了一个球。这就是所谓的“玫瑰丛”(rosette)。这团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微小生物,其实是与地球上所有动物关系最近的物种,
 是每一只青蛙、蝎子、蚯蚓、鹪鹩和海星的远房亲戚。对于想要解开动物王国最初演化之谜的金而言,领鞭毛虫十分迷人。“玫瑰丛”的形成过程——从单个细胞变成聚成一簇的多个细胞——尤其引人入胜。
是每一只青蛙、蝎子、蚯蚓、鹪鹩和海星的远房亲戚。对于想要解开动物王国最初演化之谜的金而言,领鞭毛虫十分迷人。“玫瑰丛”的形成过程——从单个细胞变成聚成一簇的多个细胞——尤其引人入胜。
我们对世界上第一种动物的样貌所知甚少,因为它们躯体柔软,没有形成化石。它们像冬日的寒风,悄无声息地来了又走,不留下一丝印记。但我们可以适当地推断。所有现代动物都是多细胞生物,其生命运作都始于一个中空的球型细胞,以吃其他东西为生,所以可以合理地猜测,我们的共同祖先拥有相同的特质。 [3] 这些“玫瑰丛”可能呈现了地球上第一种动物当下的面貌。它们在形成过程中由单个细胞分裂成一个紧密结合的群体,这个过程也折射出了更宏观的演化历程,即从某种动物原型到松鼠、鸽子、鸭子和小孩,以及我和金所在的这座公园里的一切动物。研究这些人畜无害、看似无关紧要的单细胞生物,能让金尽可能地揭示整个动物王国的神秘起源。
她与“玫瑰丛”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她知道这种细菌在野外能形成菌落,但无法在实验室再现这一过程:在她和其他科学家的研究中,这些社会性动物不知为何变得独来独往。她改变温度、营养水平、环境酸度……均毫无起色。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沮丧的她转向了另一个目标:测序“玫瑰丛”的基因组。但这么做还是有问题。金已经用细菌喂养了“玫瑰丛”,但她现在需要摆脱这些细菌,使它们的基因不会污染测序结果。于是,她给领鞭喂了一管抗生素,结果令她大吃一惊:没有了细菌之后,领鞭形成菌落的能力严重受损。如果说它们以前只是不愿形成菌落,现在则是彻底拒绝。与细菌相关的某些因素赋予了它们社交性。
金的研究生罗茜·阿列加多(Rosie Alegado)取了原始水样,分离了其中的微生物,一种种地单独喂给领鞭。在64种不同的微生物中,只有一种细菌让“玫瑰丛”恢复形成了菌落。这解释了为什么金之前的实验从未成功过:因为只有遇到正确的微生物,它们才会形成“玫瑰丛”菌落。阿列加多确定了这种细菌的身份,并将其命名为马岛噬冷菌(
Algoriphagus machipongonensis
)
[4]
:这是一种新的微生物,与我们肠道中的主要菌类同属拟杆菌。
 她还确定了细菌诱导“玫瑰丛”菌落形成的过程:通过释放名为 RIF-1的类脂肪分子。阿列加多解释道:“我把它称为 RIF,代表 rosetta-inducing factor(‘玫瑰丛’诱导因子),然后标上数字1,因为我敢肯定这个过程中还有其他细菌参与。”她说对了。自那以后,他们的团队还识别出了其他一些微生物。它们聚拢领鞭,使后者以菌落形式存在。
她还确定了细菌诱导“玫瑰丛”菌落形成的过程:通过释放名为 RIF-1的类脂肪分子。阿列加多解释道:“我把它称为 RIF,代表 rosetta-inducing factor(‘玫瑰丛’诱导因子),然后标上数字1,因为我敢肯定这个过程中还有其他细菌参与。”她说对了。自那以后,他们的团队还识别出了其他一些微生物。它们聚拢领鞭,使后者以菌落形式存在。
阿列加多怀疑,这种现象的形成很可能意味着附近有食物。领鞭作为一个群体,比单个个体更擅长捕捉细菌,所以它们一感到细菌靠近便会联合起来。“我觉得领鞭就像聚在一起窃听,”阿列加多说道,“它们缓慢地游动着,拟杆菌则指示它们进入一个富含食物资源的区域,之后便开始形成‘玫瑰丛’。”
后来这一切导致了什么?细菌是否为我们的单细胞祖先提供了食物线索,从而使这些单细胞形成多细胞菌落,从而促成了动物的起源?金觉得我们应该谨慎地下结论。今天的领鞭毛虫只是我们的远亲,并不是我们的祖先。如果能从它们的行为中推断出其祖先的行为,这将是一步巨大的飞跃,更别说了解它们对古老微生物的反应了。金还没准备好。她现在想知道,现代动物对微生物的反应是否和以前一样。如果是,即同样的细菌直接通过相同的分子引导了领鞭以及其他动物的发育,那将极大地支持这个古老现象促使动物起源的猜想。“演化出第一个动物的海洋中含有众多细菌,我觉得这点没有争议,”金说道,“它们十分多样,主宰着那时候的世界,动物必须适应它们。我们不难拓展一下思维,想象细菌产生的一些分子可能影响了第一种动物的发育。”不,这不仅仅是发散思维,尤其是想到珍珠港至今还面临着的微生物困境。
1941年12月7日上午,日本战机中队偷袭了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美国海军的“亚利桑那”号(USS Arizona)很快被击沉,随船的1,000名军官和船员也长眠海底。7艘战列舰在港口被摧毁或遭到严重损坏,其他18艘船和300架飞机也惨遭不测。如今,珍珠港已恢复平静。不过,虽然仍是重要的海军基地,且部署着多艘重要的舰艇与潜艇,但珍珠港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天上的战机,而是来自大海。
这些舰船出了什么问题呢?你可以随意丢一块金属到水里,看看会发生什么。不到几小时,细菌就开始附着在金属上生长,藻类可能随之而来,蛤蜊或藤壶也可能出现。但不消几天工夫,金属上就会出现白色的管子:它们很小,每个只有几厘米长、几毫米宽,很快会增至数百个、成千上万个,乃至数百万个;最终,金属的整个表面都会像盖上了一层冻过的粗毛地毯。这些白管子无处不在:岩石上、木桩上、渔笼上、船上,等等。一艘航母在海港停泊数月,船体上就会积起好几厘米厚的白管。有一个专业术语可以描述这种现象,那就是生物污染(biofouling),更形象的描述也许是“芒刺在背”(a pain in the ass)。海军有时需要派潜水员下海,用塑料袋覆盖螺旋桨和其他敏感结构,避免遭到白管的堵塞。

这些白色的管状物本身就由动物组成,其内部还充斥着动物。海军称其为“弯扭虫”(squiggly worm)。在夏威夷大学海洋生物学家迈克尔·哈德菲尔德(Michael Hadfield)的眼中,这种管状物的真实身份是华美盘管虫( Hydroides elegans )。人们第一次发现它们是在悉尼港,并详细地描述了它们,随后在地中海、加勒比海、日本和夏威夷海岸等地均有发现。只要是有船只停泊的温水港,就能见到它们的身影。这种附着在船体上搭便车偷渡的生物,已经随船航行占领了世界。
在海军的请求下,哈德菲尔德于1990年开始研究这种弯弯扭扭的虫子。当时的他已经是海洋幼虫方面的专家,海军希望请他来测试一系列的防侵蚀涂料,看看哪一种可以抵抗这些虫子。但是他认为真正的解决方案,是找出促使这些虫子定居于此的因素。到底是什么让它们突然出现在船体上的呢?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阿尔芒·玛丽·勒鲁瓦(Armand Marie Leroi)在那本精彩的亚里士多德传记中写道:“(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支海军中队停靠在罗德斯岛,大量陶器被扔到海里。陶器中聚起了泥沙,引来活牡蛎。由于牡蛎不能移动到陶器或任何其他地方,所以它们一定是从泥里长出来的。”
 从泥里自发生长的想法流行了几个世纪,但实则错得离谱。导致牡蛎和管虫突然出现的原因其实非常普通。珊瑚、海胆、贻贝、龙虾等动物都会经历幼虫阶段,可以乘着洋流进入开放海域,直到找到落脚地。这些幼虫非常微小,数量极其庞大(一滴海水里可能就有上百个),形态与成体完全不同。海胆的幼体看起来像个毽子,之后才会长成圆乎乎的球状针垫。华美盘管虫的幼体并不呈长长的、外覆管子的蠕虫状,而更像是长了眼睛的插头。很难相信这是同一种动物的两种形态。
从泥里自发生长的想法流行了几个世纪,但实则错得离谱。导致牡蛎和管虫突然出现的原因其实非常普通。珊瑚、海胆、贻贝、龙虾等动物都会经历幼虫阶段,可以乘着洋流进入开放海域,直到找到落脚地。这些幼虫非常微小,数量极其庞大(一滴海水里可能就有上百个),形态与成体完全不同。海胆的幼体看起来像个毽子,之后才会长成圆乎乎的球状针垫。华美盘管虫的幼体并不呈长长的、外覆管子的蠕虫状,而更像是长了眼睛的插头。很难相信这是同一种动物的两种形态。
到了一定时候,幼虫会定居于某处。它们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四处游荡,而是重塑自己的身体,转变成定栖的成体。这个过程即为变态(metamorphosis),是它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科学家一度怀疑该过程是随机发生的,与此同时,幼虫随波逐流地寻找任何地方定居,如果足够幸运地占据了一个很好的位置,它们便能生存下来。事实上,它们是带有目的和选择性的。它们会追随一些线索,比如化学物质的痕迹、渐变的温度,甚至是声音,然后找到最适宜变态的地点。
哈德菲尔德很快了解到,华美盘管虫会被细菌吸引,特别是菌膜(biofilm),即水下一层黏黏的薄垫子:细菌在上面快速繁殖,不久便密布其上。幼虫发现菌膜后会沿着细菌游动,正面压向它们。几分钟后,幼虫从尾巴处挤出一股黏液,向下锚定,然后继续分泌,形成一个透明的套子,接着把整个身体藏入其中。着苗后,它的身体开始变化:先脱落曾经在水中摆动并帮助自己往前游动的纤毛;再拉长身体,头部周围长出一圈触须,帮它小口小口地捕捉周围的食物;其体外坚硬的管状物开始形成并往下固定;现在它成了一个成体,不会再移动。这种转变完全有赖于细菌。对华美盘管虫来说,一个干净、无菌的烧杯就是彼得潘的梦幻岛。在那里,它永远不会长大、成熟。
面对任何来来往往的微生物,这种成虫都不会产生反应。哈德菲尔德发现,夏威夷水域中的许多菌株,只有少数几种能诱导盘管虫变态,仅有一种会起到强烈作用。这种细菌有一个特别绕口的名字:藤黄紫假交替单胞菌(
Pseudoalteromonas luteoviolacea
)。还好,哈德菲尔德以 P-luteo 称呼它就行。这种微生物比其他任何微生物都更擅长把幼虫转变为成虫。如果没有这种细菌,幼虫就永远不会成熟。

它们并不是例外。海绵的幼体也会降落到菌膜表面,遇到细菌后便转变为成体。贻贝、藤壶、海鞘和珊瑚也是如此。要对亚里士多德说声抱歉:牡蛎也在这份名单上。长着触手的贝螅(
Hydractinia
)是水母和海葵的近亲,必须接触到寄居蟹壳里的一种细菌后才开始成熟。海洋里充满了这些动物的幼体,它们只有接触细菌后才会完成完整的生命周期。对 P-luteo 来说,成长过程尤其如此。

如果这些微生物突然消失,那会发生什么呢?这些动物是否都会灭绝、无法发育成熟或繁殖?如果没有这些细菌测量师先行侦察适宜停栖的菌膜表面,海洋中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珊瑚礁是否就无法形成?“我可没设想过这么宏大的图景,”哈德菲尔德回应道,带着科学家特有的谨慎,不过他补充了一句令我惊讶的话,“但这么说也很有道理。当然,不是海洋里的每个幼体都需要细菌的刺激,更何况茫茫多的幼体都未经过实验检测。只是,管虫、珊瑚、海葵、藤壶、苔藓虫、海绵……我还可以继续举出很多例子,对这些物种而言,细菌的作用十分关键。”
同样,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以细菌为线索?有可能是微生物提高了幼体在某个表面的附着力,或者提供了把病原体阻拦在外的分子。但是,哈德菲尔德认为可以更简单地解释细菌的价值。菌膜的存在为动物的幼体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生存信息:(1)有一个提供可附着表面的固体底物;(2)细菌已经在这里存在了一段时间;(3)周围环境中没有太多毒素;(4)有足够的营养来维持微生物的生存。这些都是促使它们定居下来的充分条件。更有价值的问题也许是,为什么不以细菌为线索呢?或者说,你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当第一个海洋动物的幼体准备找地方落脚的时候,没有一处表面是干净的,”哈德菲尔德的这番话也呼应了罗尔斯和金的看法,“所有地方都覆盖着细菌。这并不奇怪,这些细菌群落的差异,将成为寻找定居点的最初线索。”
金的领鞭毛虫和哈德菲尔德的华美盘管虫,自身都经过精确的调谐以适应微生物的存在,也因为微生物而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没有细菌的话,原本善于抱团的领鞭将永远孑然一身,盘管虫的幼虫也永远无法成熟。这些都是微生物彻底形塑动物(或动物近亲)身体的绝佳实例。然而,这些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生。盘管虫其实没有把 P-luteo 包含在体内,而且它们长为成体后似乎也不再与细菌互动。这种关系很短暂,就像游客向路人打听方向后又继续前行。不过,其他动物和微生物会形成更持久的相互依存关系。
扁形虫下有一个半链涡虫属(
Paracatenula
),属内都是这样的生物。这种微小的动物生活在全世界温暖的海洋沉积物中,它们把共生发挥到了极致。在它们长约一厘米的身体内,共生细菌占了一半:这些共生细菌挤在一个名为营养体的部位,而这个营养体又占了这种扁形虫身体的90%,相当于大脑背后差不多住满了微生物。研究扁形虫的哈拉尔德·格鲁伯-福迪卡(Harald Gruber-Vodicka)把细菌描述为扁形虫的发动机和电池,因为它们为扁形虫提供能量,并以脂肪和硫化物的形式把能量储存在体内。这些储存物给了扁形虫明亮的白色身体,并且为扁形虫极不寻常的生存技能提供能量。
 半链涡虫是再生高手,把它一剪为二,两端都能变成功能齐全的活体,后半部分甚至会重新长出头和大脑。“把它们砍成一截一截后,最终会变出10条,”格鲁伯-福迪卡说道,“它们在自然条件下也很可能这样。越长越长后,一端脱落,然后形成两条虫。”这样的能力完全取决于营养体中的细菌和细菌锁住的能量。只要扁形虫的一段包含足够多的共生细菌,它便可以再生出一个完整的活体;如果共生菌太少,那么这一段就会死去。与我们的直觉相反,这意味着扁形虫唯一不能再生的部位,是不含细菌的头部。它们的尾巴上可以重新长出一个脑袋,但单靠脑袋却长不出一条尾巴。
半链涡虫是再生高手,把它一剪为二,两端都能变成功能齐全的活体,后半部分甚至会重新长出头和大脑。“把它们砍成一截一截后,最终会变出10条,”格鲁伯-福迪卡说道,“它们在自然条件下也很可能这样。越长越长后,一端脱落,然后形成两条虫。”这样的能力完全取决于营养体中的细菌和细菌锁住的能量。只要扁形虫的一段包含足够多的共生细菌,它便可以再生出一个完整的活体;如果共生菌太少,那么这一段就会死去。与我们的直觉相反,这意味着扁形虫唯一不能再生的部位,是不含细菌的头部。它们的尾巴上可以重新长出一个脑袋,但单靠脑袋却长不出一条尾巴。
纵观包括你我在内的动物王国,半链涡虫属与微生物的合作算是典型。我们可能不会有扁形虫那样奇妙的自愈能力,但我们体内确实寄宿着不少微生物,并且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与它们互动。哈德菲尔德的盘管虫是身体在单个时间点受环境中的细菌影响而实现转变的,与之不同的是,我们的身体不断地由体内的细菌建造和重塑。我们与它们的关系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持续的协商和周旋。
目前已知微生物会影响肠道等器官的发育,但完成这项任务后,它们不能休息,仍要继续工作,以保持动物机体的正常运转。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
 曾说过:“对有机体的独立存续而言,没什么比维护一个恒定的内部环境更重要——无论是大象还是原生动物,都是如此。”
曾说过:“对有机体的独立存续而言,没什么比维护一个恒定的内部环境更重要——无论是大象还是原生动物,都是如此。”
 而微生物在这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影响脂肪的储存,有助于修复肠道和皮肤的表皮,用新的细胞更换受损和死亡的细胞。它们确保血脑屏障的不可侵犯:那里的细胞紧密衔接,允许营养物质和小分子从血液传递到大脑,但把较大的物质和活体细胞挡在外面。它们甚至会影响骨骼的重塑,新骨一刻不停地形成,旧骨又被重新吸收。
而微生物在这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影响脂肪的储存,有助于修复肠道和皮肤的表皮,用新的细胞更换受损和死亡的细胞。它们确保血脑屏障的不可侵犯:那里的细胞紧密衔接,允许营养物质和小分子从血液传递到大脑,但把较大的物质和活体细胞挡在外面。它们甚至会影响骨骼的重塑,新骨一刻不停地形成,旧骨又被重新吸收。

没有什么比免疫系统能更清楚地体现微生物对稳定性的影响:免疫细胞与分子共同保护我们的身体,使其免遭感染或其他的外来威胁。该系统复杂到令人生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台巨大的、鲁布·戈德堡式的机器
 ,由一系列数不清的零部件组成;它们产生信号,触发彼此,一个接一个地传递下去。现在请想象一台同样的机器,但却是摇摇欲坠的混乱半成品,每一个零部件要么不完整,要么数量过少,要么连接出错。这就是无菌啮齿动物体内的免疫系统。就像西奥多·罗斯伯里解释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动物“总的来说极易受到感染,因为它们一直以婴儿般的不完整状态面对外部世界的威胁”。
,由一系列数不清的零部件组成;它们产生信号,触发彼此,一个接一个地传递下去。现在请想象一台同样的机器,但却是摇摇欲坠的混乱半成品,每一个零部件要么不完整,要么数量过少,要么连接出错。这就是无菌啮齿动物体内的免疫系统。就像西奥多·罗斯伯里解释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动物“总的来说极易受到感染,因为它们一直以婴儿般的不完整状态面对外部世界的威胁”。

这告诉我们,动物的基因组并没有为一个成熟免疫系统的建立提供所需的一切。该过程还需要微生物的贡献。
 数百篇关于小鼠、舌蝇、斑马鱼等一系列物种的科学论文表明,微生物有助于以某种方式帮助免疫系统的形成。它们影响免疫系统创建完整的免疫细胞类别,也能帮助储存这些细胞的免疫器官发育。这些微生物在生命早期发育过程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影响。那时,机体的免疫机器被首次建造出来,它开始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庞大且充满危险的世界。机器开始轰鸣后,微生物继续工作,帮助它校准面对外部威胁的反应。
数百篇关于小鼠、舌蝇、斑马鱼等一系列物种的科学论文表明,微生物有助于以某种方式帮助免疫系统的形成。它们影响免疫系统创建完整的免疫细胞类别,也能帮助储存这些细胞的免疫器官发育。这些微生物在生命早期发育过程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影响。那时,机体的免疫机器被首次建造出来,它开始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庞大且充满危险的世界。机器开始轰鸣后,微生物继续工作,帮助它校准面对外部威胁的反应。

以炎症为例。炎症是一种防御反应,免疫细胞冲向损伤或受到感染的部位,造成肿胀、发红、发热的症状。这对保护人体免受威胁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炎症,我们会持续遭受感染。但有时候,免疫本身也会成为问题。如果免疫反应遍及全身、持续时间过长,或者轻易就能触发,那么就会导致哮喘、关节炎,以及其他炎性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所以,炎症必须在正确的时间点被触发,并适当地加以控制。抑制和激活它同样重要。而这两方面的工作,微生物都能胜任。有些微生物会刺激“鹰派”免疫细胞的反应、触发炎症,另一些则会诱发“鸽派”抗炎细胞。
 它们把人体状态平衡在二者之间,使我们能够应对威胁做出反应,但又不至于过度反应。没有它们,这种平衡会消失,这就是为什么无菌小鼠既容易发生感染,又容易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因为它们既不能在威胁入侵时让免疫系统做出合适的应答,也不能在相对安全时阻止不恰当的反应发生。
它们把人体状态平衡在二者之间,使我们能够应对威胁做出反应,但又不至于过度反应。没有它们,这种平衡会消失,这就是为什么无菌小鼠既容易发生感染,又容易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因为它们既不能在威胁入侵时让免疫系统做出合适的应答,也不能在相对安全时阻止不恰当的反应发生。
现在让我们暂停一会儿,看看这整件事有多奇特。人们对免疫系统的传统描述,充斥着敌对意味的军事术语。我们把它视为一种防御系统:判定“自我”(我们自己的细胞)和“非我”(微生物和其他一切);保护自我,抵御非我。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微生物从一开始就打造和调整了我们的免疫系统!
请看以下这个例子。脆弱拟杆菌(
Bacteroides fragilis
)或 B-frag 是一种常见的肠道细菌,2002年,萨尔基斯·马兹马尼亚(Sarkis Mazmanian)通过研究表明,这种特殊的微生物可以修复无菌小鼠免疫系统的一些问题。具体而言,这种细菌的存在能够恢复辅助性 T 细胞,这是一类关键的免疫细胞,负责聚集、协调其余的免疫细胞。
 马兹马尼亚的研究显示,甚至不需要整个微生物出马,其表面的多聚糖 A(PSA)就能提高辅助性 T 细胞的数量。这是第一次有人表明,一个单一的微生物——甚至一个单一的微生物分子——就能纠正一个特异的免疫问题。马兹马尼亚的团队后来又发现,PSA 可以防治炎症性疾病,比如影响肠道的结肠炎和影响神经细胞的多发性硬化症,至少在小鼠研究中都表现出一定的效果。
马兹马尼亚的研究显示,甚至不需要整个微生物出马,其表面的多聚糖 A(PSA)就能提高辅助性 T 细胞的数量。这是第一次有人表明,一个单一的微生物——甚至一个单一的微生物分子——就能纠正一个特异的免疫问题。马兹马尼亚的团队后来又发现,PSA 可以防治炎症性疾病,比如影响肠道的结肠炎和影响神经细胞的多发性硬化症,至少在小鼠研究中都表现出一定的效果。
 这些都是免疫系统过度反应所导致的疾病,而 PSA 能通过镇静作用保持机体健康。
这些都是免疫系统过度反应所导致的疾病,而 PSA 能通过镇静作用保持机体健康。
但是请记住,PSA 是一种细菌分子:根据常识,免疫系统应该视其为威胁才对,PSA 应该引发炎症。但事实正相反:PSA 能够消炎,镇静免疫系统。马兹马尼亚称其为“共生因子”,即一种微生物发给宿主的化学信息,仿佛在说“我为和平而来”。
 这清楚地表明,免疫系统天生并没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不一定能区分无害的共生体和充满威胁的病原体。正如以上例子所示,在这种情况下,微生物会帮助它区分。
这清楚地表明,免疫系统天生并没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不一定能区分无害的共生体和充满威胁的病原体。正如以上例子所示,在这种情况下,微生物会帮助它区分。
既然如此,我们是否能把免疫系统视为一支誓将微生物杀得丢盔弃甲的军队?实际情况显然更微妙。它有时能把身体内部搅得如同大锅快煮,特别是在患有 I 型糖尿病或多发性硬化症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体内。而在 B-frag 等原生微生物存在时,它也可以表现得如同温火慢炖。我认为,把免疫系统视为负责国家公园的护林员队伍可能更准确:它们就是生态系统的管理者,必须小心地控制本地物种的数量,并驱逐侵略者。
但有一处转折:公园里的生物首先聘请了这些护林员。它们教护林员区分需要照料的物种与应该驱逐的侵略者,而且还在不断地生成像 PSA 这样的化学物质,影响护林员对警报的反应程度。这样看来,免疫系统并不只是控制微生物的手段,它至少部分地由微生物控制。这是我们体内“万物”保护我们的另一种方式。
如果按种类列出一个特定微生物组中的所有微生物,便可以知道“谁”在“哪里”。一旦列出了这些微生物的所有基因,你就可以知道“谁”有“什么能力”。
 如果列出所有微生物产生的化学物质,即它们的代谢产物,便可以知道这些微生物“实际做了什么”。前述几章已经提及了很多这类化学物质,例如共生因子 PSA、麦克福尔-恩盖识别的两种操纵乌贼的 MAMPs。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这些化学物质都发挥了什么功用,还有数十万种等着我们去破译。
如果列出所有微生物产生的化学物质,即它们的代谢产物,便可以知道这些微生物“实际做了什么”。前述几章已经提及了很多这类化学物质,例如共生因子 PSA、麦克福尔-恩盖识别的两种操纵乌贼的 MAMPs。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这些化学物质都发挥了什么功用,还有数十万种等着我们去破译。
 动物正是通过这些物质与其共生体“对话”。现在,许多科学家都在试图“窃听”这些交流。不只是对话,这些微生物分子还可能走出宿主的身体,在空气中飘荡一定距离,再传递信息。如果你取道非洲大草原,随处都可以闻到这些生物信息公告。
动物正是通过这些物质与其共生体“对话”。现在,许多科学家都在试图“窃听”这些交流。不只是对话,这些微生物分子还可能走出宿主的身体,在空气中飘荡一定距离,再传递信息。如果你取道非洲大草原,随处都可以闻到这些生物信息公告。
在非洲所有的大型食肉动物中,斑鬣狗最善于社交。狮群一般由十几个个体组成,但一支斑鬣狗族群大约由40到80个个体组成。它们不会每时每刻都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很多小群体会在一天之内不断地形成又解散。这种群体组成的动态变化,是新兴生物学领域中的极佳研究对象。“你可以实地观察狮子,但它们只会躺在那儿;你可以追随狼群多年,但只能看到狼爪的抓痕或者听到狼嚎,”鬣狗迷凯文·泰斯(Kevin Theis)说道,“但鬣狗不一样……它们之间会问候,会重复融入,还会发出占据优势和表示顺从的信号。你可以看到幼崽努力地学着在族群内争夺地盘,从别群移居过来的雄性鬣狗会为了结实伙伴而跑遍整个部落。它们的社交生活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
它们使用一整套信号来应付这些复杂的社交活动,其中包括化学信号。一只斑鬣狗会跨坐在一根长草秆上,挤压尾部的臭腺。它在秆上来回地蹭,留下一些膏状物,黑色到橙色均有,有可能黏稠如白垩粉,也有可能稀如液体。气味呢?“对我来说,它闻起来像发了酵的护根覆盖物,但也有人觉得像切达干酪或廉价肥皂。”泰斯描述道。
他一直在研究这些膏状物。有一次一位同事问他,细菌是否参与了气味的形成。泰斯被问住了。然后他发现,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科学家提出过类似的猜想,即认为许多哺乳动物的臭腺中含有细菌,它们会通过发酵脂肪和蛋白质来产生异味分子,并利用空气传播。这些微生物的不同,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味道——你是否还记得,圣迭戈动物园里散发着爆米花香味的熊狸?
 这些味道还可能提供身份信息,透露宿主的健康状况。而当动物互相玩闹、挤攘、交配时,它们还会彼此交换、共享微生物,从而形成一个群体的特别气味。
这些味道还可能提供身份信息,透露宿主的健康状况。而当动物互相玩闹、挤攘、交配时,它们还会彼此交换、共享微生物,从而形成一个群体的特别气味。
这些假设都说得通,但一直很难验证。过了几十年,有了基因工具的帮助,泰斯得以轻松地开展研究。在肯尼亚工作时,他从被麻醉的鬣狗身上收集了73个臭腺中的膏状物,并为样本中含有的微生物测序了 DNA。这次他发现了许多种细菌,比从前所有调查加起来的还要多。他的研究还显示,在斑鬣狗和黑纹灰鬣狗之间,这些细菌和它们产生的化学物质均有所不同,不同族群的斑鬣狗之间也有所不同,雌性和雄性、生育和不育者之间也有所区别。
 基于这些差异,研究者可以把这些膏状物作为化学笔记,循迹找到真正的信号发布者:它们年龄几何,是否已经做好交配的准备。通过把带有气味的微生物涂满秸秆,鬣狗把自己的个人名片洒满大草原。
基于这些差异,研究者可以把这些膏状物作为化学笔记,循迹找到真正的信号发布者:它们年龄几何,是否已经做好交配的准备。通过把带有气味的微生物涂满秸秆,鬣狗把自己的个人名片洒满大草原。
不过,这目前仍然是一个假设。“我们需要操作、改变产生气味的微生物,看看其传递的信息是否也有所改变,”泰斯说道,“我们需要证明,当气味发生变化后,鬣狗也会关注和回应这些变化。”与此同时,其他科学家也发现,在包括大象、猫鼬、獾、老鼠、蝙蝠等在内的其他哺乳动物中,其臭腺和尿液也表现出类似的规律。一只老猫鼬的气味和小猫鼬不同,雌雄大象的气味也各不一样。
接着便轮到观察我们自己了。人的腋下和一只鬣狗的臭腺并无太大区别:温暖,湿润,富含细菌。每一个物种都会制造自己的“芳香”。棒状杆菌(
Corynebacterium
)把汗水转换成闻起来像洋葱的东西,把睾酮转换成闻起来像香草、尿液或者什么都不像的物质,这些完全取决于闻者的基因。这些气味都在传递有用的信号吗?当然!腋下的微生物构成出奇地稳定,腋窝的气味也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气味。在几例相关研究实验中,志愿者能通过各自 T 恤上的气味辨别出不同的人,甚至还成功匹配了同卵双胞胎的气味。也许,像鬣狗一样,我们还可以嗅探到自己身上的微生物所发出的信号,以此来收集对方发出的消息。这也不仅限于哺乳动物。荒地蚱蜢(desert locust)的肠道细菌会分泌聚集信息素,刺激这些平日里独来独往的昆虫聚成铺天盖地的集群。德国小蠊总是绕着对方的粪便转圈,这种恶心的习惯也拜肠道细菌所赐。大型豆科灌木会依靠自己的共生体产生一种信息素,彼此警告周围的危险。

动物为什么要依靠微生物产生的化学信号?泰斯和罗尔斯、金、哈德菲尔德给出了同样的答案:这不可避免。微生物占据着地球的每一处表面,释放出具有挥发性的化学物质。如果这些化学线索有助于判断性别、强壮与否或生育能力等,那么宿主动物可能演化出产生气味的器官,藏匿并滋养特定的微生物。最终,无意中生成的线索变成了成熟的信号。因此,通过制造随空气传播的信息,微生物可以超越宿主,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影响其他动物的行为。如果的确如此,它们会影响宿主本身的行为也就毫不奇怪了。
2001年,神经学家保罗·帕特森(Paul Patterson)给怀孕的小鼠注射了一种物质,可以模仿病毒感染并触发免疫应答。这些小鼠会诞下健康的幼崽,但帕特森注意到,在幼鼠的成熟过程中,它们会表现出一些有趣的怪癖。小鼠天生不愿进入开放空间,但这些新生儿尤为拒斥。它们很容易受到巨大噪声的惊吓,会一遍遍地舔舐自己的毛,或反复尝试埋一颗玻璃球。它们比同龄的小鼠更少社交,也会回避社会联系。焦虑、重复动作、社会问题,帕特森从这些小鼠身上看到两种人类病症的表现: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这些相似性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帕特森读到过,曾严重感染流感或麻疹的孕妇更可能诞下患有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孩子。他认为,母亲的免疫反应可能会影响宝宝的大脑发育,但只是不知道究竟是如何产生影响的。

几年后,谜题才终于解开。帕特森与同事萨尔基斯·马兹马尼亚共进午餐,后者正是发现肠道细菌 B-frag 具有抗炎作用的学者。二位科学家发现,他们一直在通过两个不同的视角研究同一个问题。马兹马尼亚表明,肠道微生物会影响免疫系统;帕特森发现,免疫系统会影响大脑发育。他们意识到,帕特森实验中那些患有肠道问题的小鼠,与真实世界中的自闭症儿童有共同点:都更容易产生腹泻等胃肠功能紊乱问题,并且肠道内的微生物很不寻常。二人推测,这些微生物以某种方式影响了小鼠和儿童的行为表征。他们甚至更进一步地推测:解决肠道问题可能改变行为。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他们二人给帕特森的小鼠喂了一些 B-frag。
 效果显著。这些小鼠变得更热衷于探索,更难受到惊吓,也不容易重复动作,而且更善于沟通。他们仍然不太愿意接近其他小鼠,除此之外,B-frag 已经扭转了母亲免疫反应引发的变化。
效果显著。这些小鼠变得更热衷于探索,更难受到惊吓,也不容易重复动作,而且更善于沟通。他们仍然不太愿意接近其他小鼠,除此之外,B-frag 已经扭转了母亲免疫反应引发的变化。
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以下恐怕是最佳猜想:在怀孕小鼠身上模拟病毒感染会触发免疫反应,后果是,它们产下的后代,其肠道特别容易渗漏,肠道中的微生物群落也很不寻常。这些微生物产生化学物质透入血液,再进入大脑,从而引发不正常行为。其中的罪魁祸首是一种名为4-乙基苯基硫酸盐(4-ethylphenylsulfate ,缩写为4EPS)的毒素,它能使健康的动物产生焦虑症状。小鼠吞下 B-frag 后,这种微生物会帮助封死它们的肠道,把4EPS(和其他物质)挡在血管外,防止其影响大脑,从而扭转异常症状。
帕特森于2014年去世,马兹马尼亚仍在继续这位朋友的研究。他的长期目标是开发一种细菌,人们吞服后便可以控制一些难以治疗的自闭症症状。开发备选可能是 B-frag:它在小鼠身上的实验效果不错,而且恰好是自闭症患者肠道内最缺乏的微生物。自闭症孩子的父母了解到他的研究后经常发来电子邮件,询问可以去哪里获得这种细菌。很多这样的父母已经给他们的孩子服用了益生菌,帮助解决肠道问题。一些父母表示,孩子的行为已经有所改善。除了这些个别反馈,马兹马尼亚还想收集更坚实的临床证据。他对前景充满信心。
一些人则持怀疑态度。最显著的批评来自科学作家埃米莉·威林厄姆(Emily Willingham):“老鼠不会得自闭症。自闭症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社会和文化观念建构出来的。”
 小鼠反复掩埋玻璃珠,与自闭症孩子来回摇摆身体是一回事吗?发出比一般小鼠更低频的吱吱声,真的能与自闭症患者无法正常交流的状况相提并论吗?简单一瞥,你可能会发现相似之处;再仔细一看,可能还会注意到其他的相似症状。事实上,帕特森的小鼠最初是用来模拟精神分裂症,而不是自闭症的。不过话说回来,马兹马尼亚的研究团队最近通过实验表明,这些小鼠的行为可能与自闭症患者的行为有相关性。他们把自闭症儿童的肠道微生物移植到小鼠体内后发现,这些小型啮齿动物发展出的怪异行为,其中有不少与帕特森发现的相似,比如机械地重复行为,厌恶社交。
小鼠反复掩埋玻璃珠,与自闭症孩子来回摇摆身体是一回事吗?发出比一般小鼠更低频的吱吱声,真的能与自闭症患者无法正常交流的状况相提并论吗?简单一瞥,你可能会发现相似之处;再仔细一看,可能还会注意到其他的相似症状。事实上,帕特森的小鼠最初是用来模拟精神分裂症,而不是自闭症的。不过话说回来,马兹马尼亚的研究团队最近通过实验表明,这些小鼠的行为可能与自闭症患者的行为有相关性。他们把自闭症儿童的肠道微生物移植到小鼠体内后发现,这些小型啮齿动物发展出的怪异行为,其中有不少与帕特森发现的相似,比如机械地重复行为,厌恶社交。
 这表明,微生物至少部分地导致了这些行为。“我不认为有人会声称能在小鼠身上重现人类的自闭症,”马兹马尼亚乐观地说道,“因为有生理遗传上的限制,但实验结果就是那样。”
这表明,微生物至少部分地导致了这些行为。“我不认为有人会声称能在小鼠身上重现人类的自闭症,”马兹马尼亚乐观地说道,“因为有生理遗传上的限制,但实验结果就是那样。”
最起码,帕特森和马兹马尼亚通过研究表明,调整小鼠的肠道微生物——哪怕只是一个单一的微生物分子4EPS——就可以改变它的行为。我们此前已经知道,微生物可以影响肠道、骨骼、血管和 T 细胞的发育。而现在我们又看到,它们甚至可以改变大脑,而大脑比任何其他器官都能说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这个想法有些令人不安。我们如此珍视自由意志,害怕被看不见的力量剥夺独立性,这无疑是深藏在人类社会中的恐惧之一。就像一部最黑暗的小说,充满了奥威尔反乌托邦式的隐喻、藏在暗处的阴谋,以及控制我们心灵的超级反派。但事实证明,这种没有大脑的微观单细胞生物一直存在于我们体内,并在幕后操纵着我们的命运。
1822年6月6日,五大湖地区的一座小岛上,一个名为亚历克西斯·圣马丁(Alexis St. Martin)的20岁毛皮商,不小心被距离很近的步枪误射。岛上唯一的医生是一位名叫威廉·博蒙特(William Beaumont)的军队外科医生,当他赶到现场时,圣马丁已经出了半个多小时的血。圣马丁的肋骨被击碎,肌肉破损,一块烧焦的肺暴露在外。他的胃开了一个手指宽的口子,食物从里面倾泻而出。博蒙特后来写道:“我当时认为,都到这种地步了,再怎么试图挽救他的生命都回天乏术。”

不过他还是试了一把。他把圣马丁带到家中,克服种种困难,经过多次手术和几个月的护理,好不容易才稳定了伤情。但圣马丁的伤口一直没有完全愈合。他的胃附着在皮肤的创口上,形成了一个连通体内与外界的洞。用博蒙特的话说,这是一个“意外之孔”。圣马丁不能再打猎,也无法继续经营毛皮生意。于是,他干脆成了博蒙特的杂役及仆人,而博蒙特把他当成了一只实验豚鼠。当时的人们对消化系统的具体运作一无所知,而通过圣马丁的伤口,博蒙特仿佛看到了一扇机会之窗。他收集了许多胃酸样本,有时还直接把食物送进这个开口,用肉眼观看消化过程。实验一直持续到1833年,在此之后,二人分道扬镳。圣马丁回到加拿大魁北克省,余生一直务农,直到78岁离开人世。同处一个时代的博蒙特则摇身一变,成了“胃生理学之父”。

博蒙特通过多次观察注意到,圣马丁的情绪会影响他的胃。当他生气或变得易怒时——当你的外科医生往你身上的开孔里塞食物时,你很难不暴躁吧——他的消化速度会改变。这是大脑影响肠道运作的第一个明确信号。近两个世纪过去了,这一关联对于我们而言已太过熟悉。情绪变化时,我们会没胃口;当我们感到饥饿时,情绪也会变化。精神状况和消化问题往往紧密相连。生物学家用“肠—脑轴”(gut-brain axis)来描述连通肠道和大脑之间的双向线路。
我们现在知道,肠道微生物是这条“轴”的一部分,而且于两个方向而言都很重要。20世纪70年代以降,断断续续的小规模研究已经表明,任何一种压力,例如饥饿、失眠、与母亲分离、突然碰到一个好斗之人、不舒服的温度、身处人满为患的地方,甚至周围噪声太大等,都可以改变小鼠的肠道微生物。反向亦然:微生物组会影响宿主的行为,包括其社交态度和应对压力的能力。

2011年之前,这类研究只能算是一股涓涓细流,但一到2011年,诸多细流忽然汇成洪流。几个月之内,多位科学家发表了一系列令人着迷的研究,表明微生物可以影响大脑和行为。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斯文·彼得森(Sven Petterson)发现,无菌小鼠不太容易焦虑,与拥有正常微生物的鼠兄鼠弟相比,它们更愿意冒险。但是,如果这些小鼠幼年时就被微生物定植,它们长大后所表现出的谨慎与其他成年个体并无不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斯蒂芬·柯林斯(Stephen Collins)也很巧合地发现了类似的现象。胃肠病学专业出身的他,当时正在研究益生菌对无菌小鼠肠道的影响。他回忆道:“一位技术员对我说: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劲,益生菌让小鼠跳来跳去的。它们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随后,柯林斯研究了两种实验室常用的小鼠,其中一种一生下来就比另一种更胆小,更容易焦虑。他发现,如果在胆大的“无菌版”小鼠体内种上胆小鼠体内的微生物,前者也会变得胆小。反之亦然:“无菌版”的胆小鼠若能获得强悍表亲身上的微生物,就会变得底气十足。实验结果如柯林斯期望的一样充满戏剧性:交换动物肠道内部细菌的同时,也交换了它们的一部分个性。
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斯文·彼得森(Sven Petterson)发现,无菌小鼠不太容易焦虑,与拥有正常微生物的鼠兄鼠弟相比,它们更愿意冒险。但是,如果这些小鼠幼年时就被微生物定植,它们长大后所表现出的谨慎与其他成年个体并无不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斯蒂芬·柯林斯(Stephen Collins)也很巧合地发现了类似的现象。胃肠病学专业出身的他,当时正在研究益生菌对无菌小鼠肠道的影响。他回忆道:“一位技术员对我说: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对劲,益生菌让小鼠跳来跳去的。它们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随后,柯林斯研究了两种实验室常用的小鼠,其中一种一生下来就比另一种更胆小,更容易焦虑。他发现,如果在胆大的“无菌版”小鼠体内种上胆小鼠体内的微生物,前者也会变得胆小。反之亦然:“无菌版”的胆小鼠若能获得强悍表亲身上的微生物,就会变得底气十足。实验结果如柯林斯期望的一样充满戏剧性:交换动物肠道内部细菌的同时,也交换了它们的一部分个性。
正如我们所见,无菌小鼠是一种奇怪的生物,其生理变化可能导致行为差异。所以,当爱尔兰大学的约翰·克赖恩(John Cryan)和特德·迪南(Ted Dinan)在拥有完整微生物组的正常小鼠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时,这一结果就显得更有指导价值。他们实验用的小鼠与柯林斯用的“胆小鼠”一样。他们给小鼠喂鼠李糖乳杆菌(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又名 JB-1,一株在酸奶和乳制品中常用的细菌),并成功地改变了它们的行为。小鼠摄入细菌后,能更好地克服焦虑:身处一个迷宫时,在暴露于外的部分或开放的中央地带,它们不急于躲藏,能在其中活动更长时间。它们也更善于抵抗消极情绪:被投入水中后,它们会花更多时间划水前进,而不是漫无目的地随意漂浮。
 类似的实验通常用于测试精神病药物的有效性,而 JB-1的效果类似于抗焦虑、抗抑郁药物中的成分。“这就像给小鼠注射了低剂量的百优解或安定。”克赖恩解释道。
类似的实验通常用于测试精神病药物的有效性,而 JB-1的效果类似于抗焦虑、抗抑郁药物中的成分。“这就像给小鼠注射了低剂量的百优解或安定。”克赖恩解释道。
为了了解哪些细菌在做什么,该团队观察了小鼠的大脑。他们看到,JB-1改变了大脑不同部位对 GABA(一种镇静、平息兴奋神经元的化学物质)的应对方式,包括那些参与学习、记忆和控制情绪的部位。同样,这和人类的精神障碍惊人的相似:焦虑和抑郁的征兆之一就是大脑对 GABA 的应答出现了问题,而苯二氮䓬类药物正是通过增强 GABA 应答来对抗焦虑的。该团队还研究出微生物对大脑的影响。他们认为,迷走神经是关键媒介。这是一种细长、有许多分岔的神经,在大脑和肠道等内脏之间传递信号,也是“肠—脑轴”的一种物理形式。该研究团队切断这种神经后发现,可以改变意识的 JB-1失去了所有影响。

这些研究以及后续的许多研究均显示,改变小鼠体内的微生物可以改变其行为乃至大脑中的化学物质,让它们更容易患上小鼠意义上的焦虑和抑郁。但这些研究也有很多不一致之处。一些研究发现,细菌仅影响小鼠幼体的大脑;另一些研究则显示,性成熟期和成年的小鼠也会受到影响。有人发现,细菌能使小鼠减少焦虑;另一些人则发现细菌会促进焦虑。一些研究表明,迷走神经至关重要;另一些研究则强调,微生物可以产生像多巴胺和血清素这样的神经递质,携带信息,在神经元中传递。
 出现这些矛盾并不令人意外。大脑和微生物都极为复杂,不可能很快就把二者的碰撞与交互研究透彻。
出现这些矛盾并不令人意外。大脑和微生物都极为复杂,不可能很快就把二者的碰撞与交互研究透彻。
现在的大问题是,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也同样重要。微生物产生的细微影响可以在受控的环境条件下、在实验室用的啮齿动物身上得到体现,但在真实世界中所能发挥的影响是否同样显著?克赖恩明白,对这个问题持有怀疑是有道理的,而打消怀疑只有一种方法,即选用比啮齿动物更复杂的实验材料。他展望道:“我们必须进入真实的人体。”
现在有一些研究主要是给人注射一定剂量的抗生素或益生菌,然后观察其行为变化。但这些研究方法存在严重的问题,结果也模棱两可。另有一些更有前途的研究,其中,(虽然研究规模还很小)柯尔斯滕·蒂利希(Kirsten Tillisch)发现,与食用不含微生物的奶制品的女性相比,每天食用两次富含微生物的酸奶的女性,其大脑中参与情绪处理的部位较少活动。这些实验所体现的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它们至少表明,细菌可以影响人类的大脑活动。

在判断细菌是否可以帮助人们应对压力、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时,这些研究将面临真正的考验。不过,目前已有一些成功的迹象。斯蒂芬·柯林斯刚刚完成了一个小型的临床试验:他用某食品公司专有的一种益生菌,一种双歧杆菌菌株,来减少患有肠易激综合征的抑郁症患者的症状。
 他表示:“我认为,这个试验首次证明,益生菌能用来减少特定患者群体的异常行为。”同时,约翰·克赖恩和特德·迪南的实验也接近完成:他们研究的是益生菌〔或用他们的话说是“精神益生素”(psychobiotics)〕,看其是否可以帮助人们应对压力。迪南是一名心理医生,负责一家诊疗抑郁症的诊所。随着实验的推进,他的期望有了明显的变化:“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我深信不疑,给动物植入微生物不能改变它们的行为。”但现在他改变了想法,虽然仍然认为:“不可能通过某种‘益生菌鸡尾酒疗法’
[5]
治疗严重的抑郁症。但有可能开发出温和、有效的治疗方案。对于很多不希望采取抗抑郁药物治疗或者觉得当前疗法太昂贵的人,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有效的益生菌疗法,那将是精神病学方面的一大进步。”
他表示:“我认为,这个试验首次证明,益生菌能用来减少特定患者群体的异常行为。”同时,约翰·克赖恩和特德·迪南的实验也接近完成:他们研究的是益生菌〔或用他们的话说是“精神益生素”(psychobiotics)〕,看其是否可以帮助人们应对压力。迪南是一名心理医生,负责一家诊疗抑郁症的诊所。随着实验的推进,他的期望有了明显的变化:“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我深信不疑,给动物植入微生物不能改变它们的行为。”但现在他改变了想法,虽然仍然认为:“不可能通过某种‘益生菌鸡尾酒疗法’
[5]
治疗严重的抑郁症。但有可能开发出温和、有效的治疗方案。对于很多不希望采取抗抑郁药物治疗或者觉得当前疗法太昂贵的人,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有效的益生菌疗法,那将是精神病学方面的一大进步。”
这些研究的出现,已经使科学家不得不通过微生物这面透镜来窥探人类行为的不同方面。饮酒过度会使肠道更容易渗漏,使细菌更容易影响大脑——这是否有助于解释:酗酒者为什么常常会患上抑郁症或焦虑症?我们的饮食会重塑肠道中的微生物——这些变化是否也可能波及大脑?
 中老年人肠道中的微生物不太稳定——这是否能帮助解释:为什么中老年人更容易罹患脑部疾病?我们体内的微生物是否在操控我们对食物的渴望?比如,你面前放着一个汉堡或一块巧克力,究竟是什么让你伸出手去的呢?
中老年人肠道中的微生物不太稳定——这是否能帮助解释:为什么中老年人更容易罹患脑部疾病?我们体内的微生物是否在操控我们对食物的渴望?比如,你面前放着一个汉堡或一块巧克力,究竟是什么让你伸出手去的呢?
从你的角度出发,有没有从菜单上点到正确的菜肴所导致的区别,仅仅在于吃了一顿好的还是坏的。但是对于肠道细菌而言,这个选择异常重要。在不同的饮食条件下,不同微生物的生存、生长状况也不同。比如,有些十分善于消化植物纤维,有些则能在脂肪的供给下茁壮成长。选择用餐的同时,你也选择了喂饱哪种细菌,并且使某种细菌获得优于其他细菌的地位。但细菌也不会耐心地等待你的决定。正如我们所见,细菌能想办法侵入你的神经系统。如果它们能在你吃到“正确”的食物时释放多巴胺(一种与愉悦和奖励相关的化学物质),这是不是在潜在地“训练”你对食物的偏好?你点菜时,它们有发言权吗?

现在这只是一个假设,但并不牵强。自然环境中充斥着控制宿主头脑的寄生虫;
 狂犬病病毒会感染神经系统,使携带者变得暴力且极具侵略性;如果感染者向同类发起攻击,并咬伤或抓伤同类,那么病毒会趁机传染到新宿主上。弓形虫(
Toxoplasma gondii
)是一种大脑寄生虫,是另一种如傀儡师一般的存在。它只能在猫的体内进行有性生殖,一旦进入老鼠体内,就会抑制啮齿动物对猫的气味的自然恐惧,甚至能把这种恐惧转换为性引诱。老鼠会屁颠屁颠地跑向附近的猫,直接送上小命。弓形虫因此得以重新进入猫的体内,完成生命周期。
狂犬病病毒会感染神经系统,使携带者变得暴力且极具侵略性;如果感染者向同类发起攻击,并咬伤或抓伤同类,那么病毒会趁机传染到新宿主上。弓形虫(
Toxoplasma gondii
)是一种大脑寄生虫,是另一种如傀儡师一般的存在。它只能在猫的体内进行有性生殖,一旦进入老鼠体内,就会抑制啮齿动物对猫的气味的自然恐惧,甚至能把这种恐惧转换为性引诱。老鼠会屁颠屁颠地跑向附近的猫,直接送上小命。弓形虫因此得以重新进入猫的体内,完成生命周期。

狂犬病毒和弓形虫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它们以宿主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自私地达成自己的繁殖目的,常常导致有害且致命的结果。我们的肠道微生物则不同,它们是我们生命中的自然组成。它们帮助塑造了肠道、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等身体部位,造福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陷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共生的微生物仍然自成一体,它们也需要拓展自己的利益,在演化的战场上拼杀。它们可以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但不是我们的朋友。即使在最和谐的共生关系中,也总有冲突、自私和背叛。
[1] 乔治—皮埃尔·修拉(Georges-Pierre Seurat),法国画家,点彩画派代表人物,代表作《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 A Sunday Afternoon on the Island of La Grande Jatte )。——译者注
[2] 大部分细菌都是单细胞生物,但是生物学中总有例外。在一些条件下,上百万个黄色粘球菌( Myxococcus xanthus )会形成相互合作地进行捕食的整体,一起移动、发育、猎食。
[3] 伟大的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曾经想象过,最早的动物是一些由细胞组成的、以细菌为食的中空球体。他将这种想象出来的群体称为囊胚( Blastaea ),并按他的习惯画了出来。他的草图看起来和金的儿子在笔记本上画的“玫瑰丛”惊人地相似。
[4] 属名 Algoriphagus 中的 Algori 意为寒冷,而 phagus 是吞噬的意思。 Machipongonensis 意为“属于 Machipongo 之地”, Machipongo 是阿岗昆族(北美原住民)对霍格岛(Hog Island)的称呼。——译者注
[5] 鸡尾酒疗法:一般指一种治疗艾滋病的方法,通过使用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来治疗;这里泛指用“调配”一套益生菌的方法来治疗抑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