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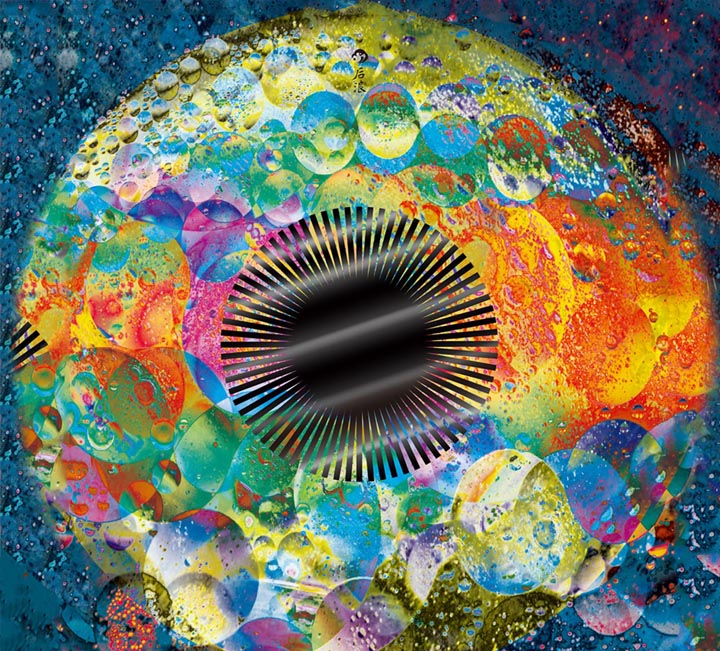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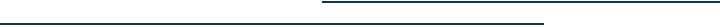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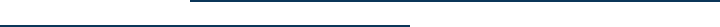
细菌无处不在,但若只用肉眼观察,那么在哪儿都看不到它们。不过有少数几个例外:比如费氏刺骨鱼菌( Epulopiscium fishelsoni ),这是一种只生活在褐斑刺尾鲷内脏里的细菌,大概有一个句号那么大。但如果不借助相关工具,对人类的肉眼而言,其他绝大多数细菌都是不可见的。这也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本没人看到过它们。根据第一章中设置的虚拟日历(即将地球历史浓缩在一年之内),细菌最早出现在3月中旬。事实上,它们统治地球期间,任何东西都很难说是具有意识的,更谈不上注意到微生物的存在。在一年即将结束的几秒前,有人打破了它们的“隐身”状态。一名好奇的荷兰人异想天开地想透过手中那个全世界质量最好的手造镜头,观察眼前的一滴水珠。
1632年,安东尼·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出生在荷兰的代尔夫特市(Delft)。那是一个热闹的外贸枢纽城市,布满了运河、树木以及鹅卵石小道。 [1] 白天,列文虎克在政府担任官员,同时经营着一间小杂货铺;晚上则在家中磨制镜片。在当时的代尔夫特,镜片制作可是一门好生意,因为荷兰人不久前刚发明了复式显微镜和望远镜。透过镜头上的那块小圆玻璃,科学家能够通过肉眼观察以前对他们来说太远或者太小的对象。英国的通才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便是其中之一,他热衷于观察一切微小的事物:跳蚤、黏在毛发上的虱子、针头、孔雀羽毛,还有罂粟籽。1665年,他梳理了自己的发现,并配上了非常华丽且十分详尽的插图,最终结集出版了一部名为《显微图谱》( Micrographia )的著作。此书甫一出版便在英国畅销,可谓小物件赶上了大时代。
不同于胡克,列文虎克从没上过大学,算不上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而且只会讲荷兰语,也不会使用学术界通用的拉丁文。即便如此,他还是通过自学习得了制造镜片的技术,水平之精湛无人可比。关于他所掌握的技术,具体细节尚不清楚,但简单而言,他把一块玲珑的小玻璃磨成了平滑、完美的对称透镜,直径不足2毫米,然后把它夹在一对矩形的黄铜片之间。随后,他把标本钉在透镜前的一颗针头上,并用几颗螺丝微调透镜的位置。这台显微镜看起来像一块漂亮的门铰链,实际上不比一个可调节距离的放大镜强多少。列文虎克只有把它凑到自己眼前,保持几乎碰上脸的距离,才能眯缝着眼睛、透过微小的镜头进行观察,而且最好还得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与胡克极力推崇并亲自使用的多透镜复合显微镜相比,这个单镜头显微镜真的非常难用。但是在更高的放大倍率下,列文虎克的这台显微镜能生成更清晰的图像。胡克使用的显微镜能够放大20至50倍,列文虎克的则能达到270倍。毫无疑问,这是那个年代全世界最棒的显微镜。
但是列文虎克不仅仅是一名“出色的显微镜制造者”,我们可以在阿尔玛·史密斯·佩恩(Alma Smith Payne)的著作《克利尔的观察者》( The Cleere Observer )中看到,“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显微镜专家(microscopist),也就是使用显微镜的能人”。他记录下一切,一遍遍地反复观察,系统地开展实验。虽然他只是一名业余的科学家,但以科学方法探究问题对他来说几乎是本能——就像一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任由自己的好奇心在大千世界中驰骋。透过显微镜,他观察了动物的皮毛、苍蝇的头、木材、种子、鲸的肌肉、脱落的死皮、牛的眼睛,等等。他看到有如神迹一般的东西,并把它们展示给朋友、家人,以及代尔夫特的学者。
其中有一位名叫雷尼尔·德·格拉夫(Regnier de Graaf)的医师,他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皇家学会的总部设在伦敦,是一个新近成立的颇有名望的科学公会。在他眼中,列文虎克的显微镜“水平远超迄今面世的所有显微镜”,并把列文虎克引荐给其他博学的同事,并恳求他们与列文虎克取得联系。学会秘书兼学界领头期刊的编辑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真的照格拉夫说的去做了,最终还翻译出版了列文虎克这个外行人的几封非正式信件,其中涉及对红细胞、植物组织和虱子内部结构的描述。列文虎克的行文杂乱得扰人,但却以极其严谨的态度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细节。
之后,列文虎克用显微镜观察了一些水,更准确地说,是取自代尔夫特附近的博克尔瑟湖(Berkelse Mere)的湖水。他用玻璃细管从湖中吸取了一些浑浊的液体,放在自己的显微镜前。他看到了一个充满生命的世界:宛如“绿色小云彩”的水藻,成千上万的微小生物在镜头下舞动。
 “大部分微型动物(animalcules)都在水中迅速地移动,上上下下、不停转圈,真是奇妙极了,”他写道,“根据我的判断,其中一些微小生物,甚至可能不及我在奶酪外皮上看到的最小霉点的千分之一。”
“大部分微型动物(animalcules)都在水中迅速地移动,上上下下、不停转圈,真是奇妙极了,”他写道,“根据我的判断,其中一些微小生物,甚至可能不及我在奶酪外皮上看到的最小霉点的千分之一。”
 这些便是原生动物,其中所包含的生物体十分多样,囊括了阿米巴原虫(又称变形虫)等单细胞真核生物。列文虎克成了第一个看到它们的人。
这些便是原生动物,其中所包含的生物体十分多样,囊括了阿米巴原虫(又称变形虫)等单细胞真核生物。列文虎克成了第一个看到它们的人。

1675年,列文虎克在自己的房子外面放了一把蓝色的小壶,用来收集供显微镜观察的雨水。取到雨水进行观察后,映入眼帘的是又一个可爱的动物园。他看到蛇形的东西不断蜷曲、伸展,还有“长着不同形状的小脚”的椭圆状东西——这些都是原生动物。他还看到一类更小的生物,比虱子眼睛的千分之一还小,它们的“转身速度迅疾无比”——细菌!他接着观察了收集自不同地方的水:书房、楼顶、代尔夫特的运河、附近的海水,还有花园里的井水。这些微型动物无处不在。原来,大量生命存在于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远远超出人类的感知范围,只有这一个人通过最精妙的镜头才得以目睹它们的真面目。正如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安德森(Douglas Anderson)写到的:“他透过镜头看到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人类首次目击到的。”但为什么他最先选择观察水呢?究竟是什么迷住了他、让他用小壶收集雨水并仔细观察?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提给整部微生物研究史中的许多人——这些人,是想到要去看一看的人。
1676年10月,列文虎克把他观察到的东西报告给了英国皇家学会。
 他送出的所有公函,都截然不同于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古板科学论述。列文虎克递交的材料中充斥着邻里八卦,甚至还有他自己的健康报告。(安德森笑称:“他需要建一个博客。”)比如,10月的信件记录了代尔夫特那年夏天的天气。不过除此之外,里面也详尽地描述了微型动物的各种细节,着实令人着迷。它们“小得令人难以置信;不,不仅如此,据我亲眼观察,即使把100个这样极小的动物首尾相连地排成一列,可能都没有一颗谷粒或一粒粗沙子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小活物,每个的体积大小可能大约只有一颗谷粒或者粗沙粒的一百万分之一那么大。”(他后来指出,沙粒大概长0.3毫米,那么这些“极小的动物”大约只有3微米长。这个数字已经很接近细菌真实的平均长度了,可见列文虎克的计算结果惊人地准确。)
他送出的所有公函,都截然不同于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古板科学论述。列文虎克递交的材料中充斥着邻里八卦,甚至还有他自己的健康报告。(安德森笑称:“他需要建一个博客。”)比如,10月的信件记录了代尔夫特那年夏天的天气。不过除此之外,里面也详尽地描述了微型动物的各种细节,着实令人着迷。它们“小得令人难以置信;不,不仅如此,据我亲眼观察,即使把100个这样极小的动物首尾相连地排成一列,可能都没有一颗谷粒或一粒粗沙子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小活物,每个的体积大小可能大约只有一颗谷粒或者粗沙粒的一百万分之一那么大。”(他后来指出,沙粒大概长0.3毫米,那么这些“极小的动物”大约只有3微米长。这个数字已经很接近细菌真实的平均长度了,可见列文虎克的计算结果惊人地准确。)
如果有人突然声称他看到了你看不到的奇妙生物,而且此前从没有人亲眼看到过,你会相信他吗?奥尔登堡当然有他的疑虑,他对列文虎克早先关于微型动物的描述也持有类似的怀疑。但是,他依然于1677年出版了列文虎克的信件。在尼克·莱恩看来,此举堪称“体现科学开明怀疑精神的非凡里程碑”。不过,奥尔登堡还是谨慎地加上了一条注释:皇家学会希望获取列文虎克实验方法的详细信息,以便让其他人能够重复实验、确认这些意外发现。列文虎克并没有完全照做。他对自己的镜头制作技术讳莫如深。他并不希望透露制作机密,因此只向一名公证人、一名律师、一名医生,以及其他颇具声誉的绅士展示了这些微型动物,再由这些人向英国皇家学会保证:列文虎克的发现是可靠的。与此同时,也有其他显微镜制造者试图重复他的工作,然而均告失败。即使强大如胡克也挣扎着尝试过,最后还是不得不采用他手里那台讨厌的单镜头显微镜,才终告成功。由此,他证明了列文虎克的正确性,也最终夯实了这位荷兰人的声誉。1680年,这个从未接受过科学训练的布商当选了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因为他还是不会读拉丁文和英文,所以皇家学会只好同意用荷兰语撰写他的院士聘书。
继成为第一个看到微生物的人之后,列文虎克又成了第一个看到自身携带的微生物的人。1683年,他注意到自己的牙齿间卡着某种白色的糊状斑块。出于习惯,他取下这些斑块,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他看到了更多移动的生物,“极漂亮的移动”!修长的、如鱼雷般的棒状物“像梭子一样”在水中穿梭,还有一些小一点的生物,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他记录道:“今天我嘴巴里的生物数量,可比我们荷兰共和国的所有居民还多。”他把这些微生物画了下来,为它们创建了简单明快的形象。这些图像后来成了微生物界的“蒙娜丽莎”。他研究了代尔夫特当地居民嘴巴里的微生物:两个女人,一个8岁大的孩子,还有一个以从不刷牙而远近闻名的老男人。列文虎克还往自己的口腔碎屑中添加酒醋,然后看到微型动物纷纷死去——这是史上第一次抗菌消毒。
列文虎克于1723年去世,享年90岁。当时,他已是英国皇家学会最负盛名的成员。他把一个黑色的漆柜赠予皇家学会,里面放置的正是那26台不可思议的显微镜,剩下的则是整整一柜子标本。奇怪的是,这个柜子后来不见了,而且再没找到过。这是一项十分惨痛的损失,因为列文虎克从未把自己制作显微镜的具体方法告诉过其他任何人。他在一封信中抱怨道,学生更感兴趣的是金钱或名声,而不是“寻找隐藏在视野以外的事物”。“一千个人中很少有一个人能够胜任这项研究,因为它既占用很多时间,也需要花费大量金钱,”他感叹道,“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份好奇心。不,有些人甚至都没有勇气明说:知道这些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呢?不知道又能怎样?”

他的态度几乎粉碎了自己留下的所有遗产。透过其他的劣质显微镜,别人什么也看不见,或者最多只能臆想出一些碎片。人们对微生物的兴趣日益减退。18世纪30年代,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开始分类命名所有的生命体,他把所有的微生物集中分入了“混沌属”( Chaos )和“蠕虫门”(Vermes)。直到一个半世纪后,人们才发现了微生物世界,并开始认真地探索。
如今,人们普遍把微生物与污垢、疾病联系在一起:如果你向某人揭示其口腔中的“万象”,对方大概会恶心反胃吧。列文虎克对微生物却毫不反感。成千上万的小东西?在他的饮用水里?在他的嘴里?在大家的嘴里?这多么激动人心!他似乎从未怀疑微生物可能会引发疾病,至少他没有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确,他的著作有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很少粗略地加以推断。其他学者就没有这么克制。1762年,维也纳一位名叫马库斯·普兰西兹(Marcus Plenciz)的医生声称,微小的生命体可以在体内繁殖倍增,再通过空气传播,进而引发疾病。他很有预见性地总结道:“每种疾病的致病源都是一种微生物。”但很可惜,他拿不出证据,没能说服他人相信: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生物其实拥有显著的影响力。甚至有批评家说:“我不会再花力气去驳斥这些荒谬的假设了,实在是浪费时间。”

19世纪中叶,微生物研究出现了一些改变。这要归功于一位名叫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人。 [2] 这个极度自信、不惮与他人辩论的法国化学家,接连证明了细菌会令酒变味、让肉腐烂。他辩称,既然细菌可以促进发酵和腐烂,那么它们也很有可能导致疾病。之前早有普兰西兹等人倡导类似的“细菌论”,但仍饱受争议。当时更普遍的看法是,疾病是由不洁的空气或者腐烂物质释放的某种“瘴气”所致。1865年,巴斯德证明了“细菌论”的正确性。当时,蚕身上的两种疾病深深地困扰着法国丝绸业,而巴斯德发现,这两种疾病均由微生物所致。巴斯德隔离了受到感染的卵,成功地阻止了疾病的传播,挽救了整个丝绸产业。
与此同时,一场炭疽病席卷了德国当地的某处农场,感染了不少动物。一位名叫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的医师正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科学家已经在感染者的身体组织内发现了一种名为炭疽杆菌的细菌。1876年,科赫把这种细菌注入小鼠体内,结果小鼠死了。接着他又从小鼠尸体中提取细菌,再注入另一只小鼠体内——这只小鼠也死了。他执着地在20多代小鼠的身上重复这个残酷的过程,每次结果都一样。科赫的实验明确表明,炭疽病是由细菌引起的。疾病的“细菌论”是正确的。
这一次对微生物的重新发现影响很大,而且被立即等同于死亡的化身。它们是细菌,是病原体,是会带来瘟疫的东西。在科赫研究炭疽病后不到20年,他和其他许多人都陆续发现导致麻风病、淋病、伤寒、肺结核、霍乱、白喉、破伤风和鼠疫的细菌。与列文虎克成功地发现微生物一样,新工具为新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更好的镜片,在凝胶状的琼脂上培养微生物,以及新的着色技术,都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使用显微镜发现和识别细菌。刚识别出细菌不久,人们就长驱直入,直奔消灭它们而去。受巴斯德的启发,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利斯特(Joseph Lister)开始把灭菌技术应用到医疗实践中,强制诊所职员用化学试剂彻底清洁和消毒双手、仪器,以及手术室,保证无数患者不受肆虐的细菌感染。另外也有人在探求阻挡细菌的手段,旨在更好地治疗疾病、改善卫生条件、保存食物。细菌学成了一门应用科学,而研究微生物就是为了驱除或消灭它们。
这一波微生物大发现的浪潮,恰好发生在达尔文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之后。微生物学家勒内·杜博(René Dubos)写道:“这是一次历史的巧合,细菌理论刚好在盛行达尔文主义的伟大时代得到发展。根据达尔文主义的解读,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生存斗争,因此必须敌我分明,不允许存在模糊地带……之后所有试图控制微生物疾病的努力,一开始就被这种认识主导,并激发了人类对微生物的敌意,使前者对后者发起进攻,力图从患病个体与群体中彻底消灭微生物。”

这种认识持续至今。随便走进一家图书馆,取下一本微生物教材扔出窗外,依然很容易吓到路人。如果我把本书中与有益微生物有关的书页全部撕下来递给别人,在他们眼中,这依旧是一叠令人心生厌恶的纸张。疾病与死亡的叙事,仍然主导着我们今日对微生物的看法。
在这个领域中,一些细菌理论家一个接一个地识别出致命病菌,在聚光灯下大出风头;但还有一些生物学家在学术边缘地带辛勤工作,最终用另一种方式揭示了微生物的又一面真相。
荷兰人马丁努斯·贝杰林克(Martinus Beijerinck)是第一位展现这些“次要部分”之重要性的生物学家。他平日深居简出,性情粗暴,很不受他人待见。他不爱和人打交道,只与少数几位同事关系较近;他对当时风头正劲的医学微生物学兴趣寥寥。
 他对疾病不感兴趣,更想研究在自然条件下生存的微生物:土壤、水环境、植物的根部。1888年,他发现细菌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氮,然后把它们转化成能为植物所用的氨;之后,他分离出一个菌种,该菌种有助于促进土壤和大气间的硫循环。这项工作使微生物研究得以在贝杰林克所在的城市——代尔夫特重生。两个世纪前,正是在同一座城市,列文虎克第一次亲眼确证了细菌的存在。贝杰林克与其他几位科研界的知音,如俄罗斯的谢尔盖·维诺格拉茨基(Sergei Winogradsky)等一起创立了新的代尔夫特学派,并自称“微生物生态学家”(microbial ecologists)。他们发现,虽然微生物会对人类构成威胁,但它们也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对疾病不感兴趣,更想研究在自然条件下生存的微生物:土壤、水环境、植物的根部。1888年,他发现细菌可以固定空气中的氮,然后把它们转化成能为植物所用的氨;之后,他分离出一个菌种,该菌种有助于促进土壤和大气间的硫循环。这项工作使微生物研究得以在贝杰林克所在的城市——代尔夫特重生。两个世纪前,正是在同一座城市,列文虎克第一次亲眼确证了细菌的存在。贝杰林克与其他几位科研界的知音,如俄罗斯的谢尔盖·维诺格拉茨基(Sergei Winogradsky)等一起创立了新的代尔夫特学派,并自称“微生物生态学家”(microbial ecologists)。他们发现,虽然微生物会对人类构成威胁,但它们也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彼时的报纸上开始涌现关于“好细菌”的报道。这些好细菌滋养土壤,催化酒与乳制品发酵。一部1910年的教科书这样写道:“每个人都关注的‘坏细菌’,实际上它们只是细菌界的一个特殊分支,仅占一小部分,而且从广义上而言,它们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
 这本教科书还表示,大多数细菌会帮助分解腐烂的有机物,让营养元素重新进入循环、重返自然。“这并不是在耸人听闻,如果没有(它们)……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必定会消失”。
这本教科书还表示,大多数细菌会帮助分解腐烂的有机物,让营养元素重新进入循环、重返自然。“这并不是在耸人听闻,如果没有(它们)……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必定会消失”。
20世纪初,其他微生物学家也意识到,许多微生物会同时寄宿在动植物与其他肉眼可见的有机体上。人们逐渐发现,地衣(附着生长在墙壁、石头、树皮和树干上的彩色斑点)是一种复合有机体,由寄宿在真菌上的微藻组成,其中微藻为宿主提供营养,以此来交换矿物质和水分。 [3] 海葵和扁形虫等动物细胞也含有藻类,木蚁身上也寄宿着细菌。人们长期以来都认为,附着在树根上的真菌是寄生虫,但后来却发现它们与树互相合作:真菌为树供氮,树为真菌提供碳水化合物。
这种伙伴关系得到了一个新的专有名词:共生(其词源由希腊语的“共同”和“生存”构成)。
 这个词本身是中性的,可以用来描述任何形式的共存。如果一方受益、另一方付出代价,二者就构成寄生关系(parasite)
这个词本身是中性的,可以用来描述任何形式的共存。如果一方受益、另一方付出代价,二者就构成寄生关系(parasite)
〔如果会引起疾病,那么其中一方就是病原体(pathogen)〕。如果一方受益,且不影响宿主,那就是共栖关系(commensal)。如果寄宿者反过来有益于宿主,二者就构成互助关系(mutualist)。所有这些共存类型,都归属在共生范畴内。
不过,这些概念出现的时间不太合适。在达尔文主义的强势影响下,生物学家讨论的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还有大自然中鲜血淋漓的各路爪牙。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把动物世界比作一场“角斗士的表演”。因此,在满是冲突和竞争的解释框架内,强调合作与团队协作的共生观念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而且也不契合微生物留给人们的邪恶印象。后巴斯德时代,微生物已成为疾病的标志,它们的缺席与否则成为衡量机体健康程度的标准。1884年,弗雷德里希·布洛赫曼(Friedrich Blochmann)第一次看到弓背蚁身上的细菌。那时盛行一种非常反直觉的想法,即认为寄居于人体的微生物无害于健康。布洛赫曼不得不在文字上下功夫,避免透露它们的真实身份。
 “细胞质小棒(plasma rodlets)”,他这样称呼它们,或者是“非常可疑的纤维状卵质”。他历经数年的严格研究,终于在1887年明确表态:“我们不得不宣布,这些小棒其实是细菌,除此之外很难再有别的解释。”
“细胞质小棒(plasma rodlets)”,他这样称呼它们,或者是“非常可疑的纤维状卵质”。他历经数年的严格研究,终于在1887年明确表态:“我们不得不宣布,这些小棒其实是细菌,除此之外很难再有别的解释。”
与此同时,其他科学家也已经注意到,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内脏中也含有众多共生菌,它们并没有导致显著的疾病或腐败,只是作为所谓的“正常菌群”栖居在人体内。“随着动物的出现……不可避免地,细菌会时不时地被动物摄入体内。”内脏研究先驱亚瑟·艾萨克·肯德尔(Arthur Isaac Kendall)写道。
 人体只是细菌的另一处栖息地,而肯德尔认为,应该好好地研究人体的微生物,而不只是单纯地消灭或抑制它们。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即使是那时的研究者,也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我们体内存在着大量微生物,数量多到令人沮丧。发现大肠杆菌(
E. coli
,后来成了重要的实验材料)的西奥多·埃希里希(Theodor Escherich)曾表示:“研究、分辨各种随机出现在正常粪便和肠道中的细菌,这项工作看起来毫无意义,也令人心生怀疑,因为肠道环境仿佛受着一千个巧合的调控。”
人体只是细菌的另一处栖息地,而肯德尔认为,应该好好地研究人体的微生物,而不只是单纯地消灭或抑制它们。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即使是那时的研究者,也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我们体内存在着大量微生物,数量多到令人沮丧。发现大肠杆菌(
E. coli
,后来成了重要的实验材料)的西奥多·埃希里希(Theodor Escherich)曾表示:“研究、分辨各种随机出现在正常粪便和肠道中的细菌,这项工作看起来毫无意义,也令人心生怀疑,因为肠道环境仿佛受着一千个巧合的调控。”

尽管如此,埃希里希和他的同辈人已经尽己所能。他们分别确定了猫、狗、狼、老虎、狮子、马、牛、绵羊、山羊、大象、骆驼以及人类等动物各自的细菌特征,此时距离微生物组成为流行语还有一个世纪之遥。
 他们勾勒出了人类微生物生态系统的基础,甚至比1935年提出的生态系统(ecosystem)还早了几十年。他们让人们认识到: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微生物就开始在我们体内积累,并且在各个器官中占据优势的微生物各有不同。他们也了解到,肠道中的微生物特别丰富,而且会随动物摄食的不同而变化。1909年,肯德尔把肠道形容为“完美的细菌孵化器”,而这些细菌“不会主动破坏人类的正常生理活动”。
他们勾勒出了人类微生物生态系统的基础,甚至比1935年提出的生态系统(ecosystem)还早了几十年。他们让人们认识到: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微生物就开始在我们体内积累,并且在各个器官中占据优势的微生物各有不同。他们也了解到,肠道中的微生物特别丰富,而且会随动物摄食的不同而变化。1909年,肯德尔把肠道形容为“完美的细菌孵化器”,而这些细菌“不会主动破坏人类的正常生理活动”。
 当宿主抵抗力下降,它们可能会伺机引发疾病;但在一般情况下,它们大多无害。
当宿主抵抗力下降,它们可能会伺机引发疾病;但在一般情况下,它们大多无害。
它们可能有益于宿主吗?讽刺的是,在与微生物漫长战斗中打头阵的巴斯德,竟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他认为,细菌可能有益于宿主,甚至可能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人们都知道牛胃能够消化植物纤维素,然后转化成营养丰富、易于牛吸收的氨基酸。肯德尔提出,人体肠道中的微生物可能帮助宿主与外来细菌战斗,防止它们占领人体的肠道(虽然他怀疑细菌的消化作用)。
 俄罗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利·梅奇尼科夫(Élie Metchnikoff)把这种看法发挥到了极致。他曾被形容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一个歇斯底里的角色”,
俄罗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利·梅奇尼科夫(Élie Metchnikoff)把这种看法发挥到了极致。他曾被形容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一个歇斯底里的角色”,
 他的身上体现出了极强的自我矛盾:作为一个深度的悲观主义者,他曾至少两次试图自杀,但却写下了一部名为《延寿:关于乐观主义的研究》(
The
Prolongation of Life: Optimistic Studies
)的著作。在这本出版于1908年的书里,他把自己的矛盾投射进了微生物的世界。
他的身上体现出了极强的自我矛盾:作为一个深度的悲观主义者,他曾至少两次试图自杀,但却写下了一部名为《延寿:关于乐观主义的研究》(
The
Prolongation of Life: Optimistic Studies
)的著作。在这本出版于1908年的书里,他把自己的矛盾投射进了微生物的世界。
一方面,梅奇尼科夫认为肠道细菌会产生引发疾病和促进衰老的毒素,这是“导致人类短命的主要原因”;而另一方面,他又相信一些微生物可以延长寿命。就后者而言,他曾受到保加利亚农民的启发。这些农民经常饮用发酵变酸的牛奶,都能轻松活过100岁。梅奇尼科夫把这两个特点联系起来。发酵乳中含有细菌,其中包括由他命名的保加利亚杆菌( Bulgarian bacillus )。这些细菌产生乳酸,杀死那些农民肠道中“致人短命”的有害细菌。梅奇尼科夫坚信这个想法的正确性,并开始定期大量饮用酸牛奶。其他很多人因为十分相信梅奇尼科夫,也纷纷开始效仿。〔他的此番断言,让结肠造口术风靡一时。著名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也经梅奇尼科夫的启发,在《夏来夏去》( After Many a Summer )中描写了一位好莱坞大亨:他给自己灌入鲤鱼肠子来改变肠道中的微生物,试图实现永生。〕当然,人类饮用发酵乳制品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现在,人们一边喝一边还惦记着微生物。梅奇尼科夫71岁时死于心脏衰竭,而这股潮流却在他死后延续了很长时间。
尽管有肯德尔、梅奇尼科夫等人的努力,但有关人体和动物体内共生细菌的研究,却被越来越重视病原体的趋势压垮。公共卫生部门开始鼓励人们用抗菌产品给身体和周边的物品彻底消毒,创造一个极其卫生的环境。与此同时,科学家发现了抗生素(可以将病菌和其附带物全部消灭干净),并开始大规模制造生产。终于,我们有了打败这些微小敌人的机会。可是,共生菌的研究也由此陷入了长时间的停滞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半叶。1938年,一本关于细菌学的详细历史记录出版,但其中没有一句提到寄生在我们体内的微生物。
 该领域当时的顶尖教科书把一个单独的章节分配给了该主题,但讲的主要是如何区分它们与病原体——只有在必须与“更有趣”的同类加以区分时,生命体内的共生细菌才会受到人们的关注。即使有科学家研究细菌,也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其他有机体。基因的表达是如何开启的、能量是如何存储的等诸多生物化学问题,在原理上都是相通的,因此适用于整棵生命树上的任何生物。科学家希望通过研究大肠杆菌来更好地了解大象。细菌成了“普世生命的极简替身”,历史学家芬克·桑戈德伊(Funke Sangodeyi)曾这样写道:“微生物学成了科学的侍女。”
该领域当时的顶尖教科书把一个单独的章节分配给了该主题,但讲的主要是如何区分它们与病原体——只有在必须与“更有趣”的同类加以区分时,生命体内的共生细菌才会受到人们的关注。即使有科学家研究细菌,也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其他有机体。基因的表达是如何开启的、能量是如何存储的等诸多生物化学问题,在原理上都是相通的,因此适用于整棵生命树上的任何生物。科学家希望通过研究大肠杆菌来更好地了解大象。细菌成了“普世生命的极简替身”,历史学家芬克·桑戈德伊(Funke Sangodeyi)曾这样写道:“微生物学成了科学的侍女。”

微生物学走向显学的道路十分漫长。新技术提供了一些帮助,包括培养厌氧菌的手段。在动物内脏中占绝大部分的厌氧菌是非常重要的微生物,但在此之前,科学家很难获得它们,当然也不可能开展大规模研究。
 人们对于微生物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这得感谢代尔夫特学派的微生物生态学家。他们意识到,不应该把细菌看作单个的个体而孤零零地放进试管研究,而应该把它们视为生活在各个栖息地(即宿主动物)中的群落来研究。当时,在例如牙科和皮肤科等边缘医学分支,人们开始研究相应器官中的微生物生态学。
人们对于微生物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这得感谢代尔夫特学派的微生物生态学家。他们意识到,不应该把细菌看作单个的个体而孤零零地放进试管研究,而应该把它们视为生活在各个栖息地(即宿主动物)中的群落来研究。当时,在例如牙科和皮肤科等边缘医学分支,人们开始研究相应器官中的微生物生态学。
 桑戈德伊写道: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置于当时的主流微生物研究的对立面”。但是,这些学者都是在相互孤立的不同领域中开展研究的。例如,植物学家研究植物微生物,动物学家攻克动物微生物。微生物学分裂成多个小领域,因此各领域的点滴努力很容易被忽视。没有一个紧密联系的科学家共同体去研究微生物的共生现象,也没有一个领域能给他们机会发话。本着共生精神,必须有人把这个领域的零碎部件组装成一个更大的整体。
桑戈德伊写道: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置于当时的主流微生物研究的对立面”。但是,这些学者都是在相互孤立的不同领域中开展研究的。例如,植物学家研究植物微生物,动物学家攻克动物微生物。微生物学分裂成多个小领域,因此各领域的点滴努力很容易被忽视。没有一个紧密联系的科学家共同体去研究微生物的共生现象,也没有一个领域能给他们机会发话。本着共生精神,必须有人把这个领域的零碎部件组装成一个更大的整体。
西奥多·罗斯伯里(Theodor Rosebury)是一名口腔微生物学家,他于1928年开始统合人类微生物群系的研究工作。历时30余年,他收集自己能找到的每一项相关研究,最终于1962年把这些细碎的丝线织成了一张结实的挂毯:他撰写了一本具有开创性的大部头专著,《人类原生微生物》(
Microorganisms Indigenous to Man
)。
 “据我所知,还没有别人尝试过写这样一本书,”他写道,“事实上,这似乎是第一次……把这个课题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他写得很对。这本书细节丰富,涉猎广泛,是该领域的先行者。
[4]
他十分详细地描写了每个身体部位的常见细菌,还论述了婴儿出生后被微生物定植的过程:他认为,微生物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维生素和抗生素,防止病原体在婴儿体内引起感染。他表示,使用抗生素后,微生物会恢复到正常比例,但长期使用可能导致体内产生永久不可逆的变化。他说的大部分都正确。“我们忽视了许多曾经受到过关注的微生物,人类从未正眼瞧过它们中的大多数,”他写道,“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还原它们本来的面目。”
“据我所知,还没有别人尝试过写这样一本书,”他写道,“事实上,这似乎是第一次……把这个课题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他写得很对。这本书细节丰富,涉猎广泛,是该领域的先行者。
[4]
他十分详细地描写了每个身体部位的常见细菌,还论述了婴儿出生后被微生物定植的过程:他认为,微生物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维生素和抗生素,防止病原体在婴儿体内引起感染。他表示,使用抗生素后,微生物会恢复到正常比例,但长期使用可能导致体内产生永久不可逆的变化。他说的大部分都正确。“我们忽视了许多曾经受到过关注的微生物,人类从未正眼瞧过它们中的大多数,”他写道,“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还原它们本来的面目。”
罗斯伯里的书大获成功,而他的统合工作也为原本步履蹒跚的研究领域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许多新研究随之喷涌而出。
 后来者纷纷用自己的贡献扩大该领域的影响力,其中就有一位充满魅力的美国人。他出生在法国,名为勒内·杜博,早早地就为自己挣得了名声。他效仿代尔夫特学派,用生态学方法研究土壤中的微生物,并从这些微生物中分离出了一种引领抗生素时代的药物。不过,在杜博看来,他的药物不是杀掉微生物的武器,而是“驯化”微生物的工具。即使后来转向肺结核和肺炎研究,他也尽量不用敌对眼光看待微生物,还尽量避免任何对立于细菌的隐喻式表述。在杜博的内心深处,自己是一名纯然的自然爱好者,而微生物正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传记作者苏珊·莫伯格(Susan Moberg)写道:“面对一个具有生命的有机体,只有通过研究它与其他一切事物的关系,才能彻底理解它。这是他一生的信条。”
后来者纷纷用自己的贡献扩大该领域的影响力,其中就有一位充满魅力的美国人。他出生在法国,名为勒内·杜博,早早地就为自己挣得了名声。他效仿代尔夫特学派,用生态学方法研究土壤中的微生物,并从这些微生物中分离出了一种引领抗生素时代的药物。不过,在杜博看来,他的药物不是杀掉微生物的武器,而是“驯化”微生物的工具。即使后来转向肺结核和肺炎研究,他也尽量不用敌对眼光看待微生物,还尽量避免任何对立于细菌的隐喻式表述。在杜博的内心深处,自己是一名纯然的自然爱好者,而微生物正是自然的一部分。他的传记作者苏珊·莫伯格(Susan Moberg)写道:“面对一个具有生命的有机体,只有通过研究它与其他一切事物的关系,才能彻底理解它。这是他一生的信条。”

他看到微生物的共生价值,为人们忽视它们的益处而深感失望。“微生物可以帮助人类,对公众而言,这种认识有着前所未有的吸引力。人们曾经先入为主地相信,微生物十分危险,甚至会威胁我们的生命;而他们现在意识到,微生物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力军,”他写道,“战争的历史总是比合作的历史更吸引人。鼠疫、霍乱、黄热病都被写成了故事,排成了戏剧,拍成了电影,但却没有人漂亮地讲出肠道和胃部微生物发挥有益作用的故事。”
 他与同事德韦恩·萨维奇(Dwayne Savage)和拉塞尔·夏德乐(Russell Schaedler)一起讲出了他们的研究故事。他们指出,用抗生素消灭原生菌种后,有害的菌种变成了霸主。他们研究了在无菌条件下培养起来的小鼠,发现这些小鼠更短命,成长速度也更缓慢,内脏和免疫系统都发育异常,且更容易因为压力或病菌而受到感染。他写道:“在动物和人类的发育和生理活动中,有几种微生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与同事德韦恩·萨维奇(Dwayne Savage)和拉塞尔·夏德乐(Russell Schaedler)一起讲出了他们的研究故事。他们指出,用抗生素消灭原生菌种后,有害的菌种变成了霸主。他们研究了在无菌条件下培养起来的小鼠,发现这些小鼠更短命,成长速度也更缓慢,内脏和免疫系统都发育异常,且更容易因为压力或病菌而受到感染。他写道:“在动物和人类的发育和生理活动中,有几种微生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杜博知道,他只窥见了冰山一角。他写道:“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目前识别出的细菌)只是全部微生物中很小的一部分,也不是最重要的。”剩下的——也许有99%之多——没法在实验室条件下生长。“没办法培育”成了当时阻碍微生物研究发展的巨大障碍。自列文虎克起,人们虽然有诸多新发现,但微生物学家对大部分有待研究的微生物仍一无所知。强大的显微镜解决不了当时面临的问题,微生物培育技术也解决不了。研究者亟须找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
20世纪60年代末,年轻的美国科学家卡尔·乌斯(Carl Woese)开始了一项古怪但非常精专的小研究:他收集了不同种的细菌,分析了一种存在于所有收集到的细菌中的核糖体分子——16S rRNA。所有科学家都觉得这项工作没有任何价值,也就没人与乌斯竞争。他之后回忆道:“这是一场只有一匹马的赛马比赛。” [5] 这场比赛昂贵、缓慢又危险,其中涉及的放射性液体多到令人心惊。但是,该研究起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
当时的生物学家完全依靠体表特征来推断物种间的关系:比如体型大小、身材形状,以及细微的解剖特征差异。乌斯认为,他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他的方法就是检测所有生物都携带的生命分子:DNA、RNA 和蛋白质。这些分子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分化,亲缘关系越近的相似度就越高。乌斯相信,如果能找到那个对的分子,再比较足够多物种的亲缘关系远近,生命之树的演化枝干就将清晰显现。

他确定以16S rRNA 核糖体(由同名基因指导合成)为研究对象。这种核糖体参与了所有有机体中基础蛋白质的制造过程,所以,它正是乌斯渴望寻找到的、适用于广泛比较多样物种的基本单元。截至1976年,他已经为大约30多种微生物的16S rRNA 建立起档案。同年6月,他开始研究某一物种。之后,这一物种不仅改变了他的生活,还改变了人们已经熟知的生物学。
这种不起眼的微生物由拉尔夫·沃尔夫(Ralph Wolfe)提供,他是产甲烷菌(methanogens)方面的权威专家。这些小东西可以仅靠二氧化碳和氢气生存,并将其转化成甲烷。它们生活在沼泽、海洋和人类的肠道中,首次发现于灼热的下水道污泥中,被命名为嗜热自养甲烷杆菌( Methanobacterium thermoautotrophicum )。与其他人一样,乌斯一开始也认为,虽然这种小东西有奇怪的癖好,但终究只是另一种细菌。但是,分析了它的16S rRNA 后,他意识到这绝对不是细菌。对该发现的解释可能要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比如他是否充分理解了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当时的他是精力旺盛还是小心谨慎,他是否要求重复这次实验等。但到了12月,他的团队测序了更多产甲烷菌基因,结果都呈现出相同的模式。至此,结论已经显而易见。沃尔夫还记得乌斯是这么告诉他的:“这些东西甚至都不是细菌。”
乌斯于1977年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他在论文中把产甲烷菌重新归至古菌之下(当时古菌还被称为 archaebacteria,后来去掉了当中的“细菌”部分,直接记作 archaea)。
 乌斯坚信,它们并不是怪异的细菌,而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这是一项惊人的发现。乌斯从淤泥中挑选出这些不起眼的微生物,并把它们视为与无所不在的细菌和强大的真核生物同等重要的存在。这就如同每个人都盯着世界地图看,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只有乌斯悄悄展开了折叠着的另外1/3的地图。
乌斯坚信,它们并不是怪异的细菌,而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这是一项惊人的发现。乌斯从淤泥中挑选出这些不起眼的微生物,并把它们视为与无所不在的细菌和强大的真核生物同等重要的存在。这就如同每个人都盯着世界地图看,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只有乌斯悄悄展开了折叠着的另外1/3的地图。
不难预料,他的说法招致了猛烈的批评,甚至连一些同样志在打破传统的叛逆者,都觉得他走得太远了。后来,《科学》评价他“为微生物学的研究发展烙下了一道伤疤”,甚至到他2012年去世时,这道伤疤仍未消除。
 今日,他留下的知识遗产不可否认,他关于古菌完全不同于细菌的断言也非常正确。而在他所有的研究中,更重要的也许是他倡导的“通过比较基因来研究物种间关系”的方法——这成了现代生物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
今日,他留下的知识遗产不可否认,他关于古菌完全不同于细菌的断言也非常正确。而在他所有的研究中,更重要的也许是他倡导的“通过比较基因来研究物种间关系”的方法——这成了现代生物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
 他的方法为其他科学家,比如他的老朋友诺曼·佩斯(Norman Pace)的研究铺平了道路,生物学家得以真正迈出探索微生物世界的脚步。
他的方法为其他科学家,比如他的老朋友诺曼·佩斯(Norman Pace)的研究铺平了道路,生物学家得以真正迈出探索微生物世界的脚步。
20世纪80年代,佩斯开始研究生存在极热环境下的古菌,主要检测它们的 rRNA。他对黄石国家公园的章鱼泉(Octopus Spring)特别感兴趣:在这口深蓝色的大汽锅里,水温高达91℃,里面翻滚着众多人类还未识别的喜热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大量积聚,在泉水中形成人们肉眼可见的粉红色游丝。佩斯还记得,他读到关于章鱼泉的描述后,兴奋不已地冲进实验室大喊:“嘿,伙计们,瞧瞧这个!好几千克的微生物!赶紧拿桶去捞啊。”组里的另一个人说:“喂,你连它们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佩斯回答道:“没关系。我们可以给它们测个序。”
其实,他当时应该大喊“尤里卡(Eureka)”
 !佩斯已经意识到,如果采用乌斯的方法,那么无须培养就可以识别某种微生物。他甚至无须看到它们,只需从周边环境中抽取 DNA 或 RNA,然后为它们测序。这可以一步回答“泉水中生活着哪些微生物”,以及“它们处于微生物生命树的哪个位置”等问题——既涵盖了生物地理学,又探讨了演化生物学,可谓一举两得。佩斯介绍道:“我们带着水桶来到黄石公园,立刻着手干了这些活。”佩斯的研究小组为两种细菌和一种古菌测了序,它们取自“寂静、美丽又布满危险”的水域,没有一个微生物是从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所见之物都是科学新发现。他们最终于1984年发表了该项研究结果,
!佩斯已经意识到,如果采用乌斯的方法,那么无须培养就可以识别某种微生物。他甚至无须看到它们,只需从周边环境中抽取 DNA 或 RNA,然后为它们测序。这可以一步回答“泉水中生活着哪些微生物”,以及“它们处于微生物生命树的哪个位置”等问题——既涵盖了生物地理学,又探讨了演化生物学,可谓一举两得。佩斯介绍道:“我们带着水桶来到黄石公园,立刻着手干了这些活。”佩斯的研究小组为两种细菌和一种古菌测了序,它们取自“寂静、美丽又布满危险”的水域,没有一个微生物是从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所见之物都是科学新发现。他们最终于1984年发表了该项研究结果,
 这也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只凭基因就能够发现新物种,而这绝不是最后一次。
这也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只凭基因就能够发现新物种,而这绝不是最后一次。
1991年,佩斯和他的学生埃德·德隆(Ed DeLong)分析了一些捞自太平洋的浮游生物。他们发现了一个比黄石公园热泉中更复杂的微生物群落:共计15个细菌新种,其中两种不同于任何已知的细菌。那棵原本十分疏落的细菌生命树慢慢长出了新叶,有时甚至直接长出了整根全新的枝条。20世纪80年代,所有已知的细菌都被妥当地分置在十几个大类别(门)中。到了1998年,这一数字已涨到40。佩斯与我聊天时告诉我,现在已经接近100个门了,其中大约有80个门从来没有在实验室培养过。一个月后,吉尔·班菲尔德(Jill Banfield)宣布,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含水层中新发现了35个门。

从培养皿和显微镜中解放出来后,现在的微生物学家可以更全面地普查地球上的微生物。“这一直是我们的目标,”佩斯说道,“微生物生态学曾一度停滞不前。一个人走出去,翻开一块岩石,发现一种细菌,并认为它能代表该地区的微生物组成——现在看来,这种方法愚蠢极了。从采用新方法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像是轰开了自然微生物世界的大门。我想把这句话写进我的墓志铭。这种美妙的感觉延续至今,一直没有褪色。”
他们并没有局限在16S rRNA 的研究上。佩斯、德隆等人很快发展出了新方法,能够测序一团土壤或者一勺水中每种微生物的基因。
 他们提取了所有本地微生物的 DNA,切成小碎片,然后一同测序。佩斯说:“我们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基因。”通过16S rRNA,他们可以确定某个地方有哪些微生物;但通过搜索合成维生素、消化纤维素或者抵抗抗生素的基因,他们能发现当地微生物所拥有的具体能力。
他们提取了所有本地微生物的 DNA,切成小碎片,然后一同测序。佩斯说:“我们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基因。”通过16S rRNA,他们可以确定某个地方有哪些微生物;但通过搜索合成维生素、消化纤维素或者抵抗抗生素的基因,他们能发现当地微生物所拥有的具体能力。
这项技术将毫无疑问地彻底改变微生物学,现在只缺一个让人过眼难忘的名字。1998年,乔·汉德尔斯曼(Jo Handelsman)想出了一个名字:宏基因组学(metagenomics),旨在研究一个群落的基因组。
 汉德尔斯曼曾说过:“自显微镜问世以来,宏基因组学可能是微生物研究中最重要的事件。”终于,我们有了一套完整理解地球生命的研究方法。汉德尔斯曼等人开始研究生活在各种环境中的微生物:阿拉斯加的土壤、威斯康星州的草原、从加利福尼亚州矿山上冲下来的酸性物质,还有马尾藻海的海水、深海蠕虫的尸体、昆虫的内脏,等等。当然,也有微生物学家像列文虎克一样,把研究对象转向了自己。
汉德尔斯曼曾说过:“自显微镜问世以来,宏基因组学可能是微生物研究中最重要的事件。”终于,我们有了一套完整理解地球生命的研究方法。汉德尔斯曼等人开始研究生活在各种环境中的微生物:阿拉斯加的土壤、威斯康星州的草原、从加利福尼亚州矿山上冲下来的酸性物质,还有马尾藻海的海水、深海蠕虫的尸体、昆虫的内脏,等等。当然,也有微生物学家像列文虎克一样,把研究对象转向了自己。
上文提到的杜博以及许多其他人,一开始都打算消灭微生物,最后却爱上了它们。戴维·雷尔曼也是其中一员。他最早是一名临床医生,主攻传染性疾病方向。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用佩斯的新技术识别了一些导致疑难杂症的未知微生物。他起初深感沮丧,因为待检测的组织样本中总是充斥着人体内的正常菌群,因而难以分辨病原体。但后来雷尔曼意识到,这些菌群本身就很有趣:与其专攻少数致病菌,为什么不转而去研究这些微生物呢?
所以,雷尔曼继承了微生物学家的光辉传统,开始测序自己的微生物组基因。他让牙医从他的牙龈缝隙里刮下一些碎屑,收集在一根消过毒的试管中。他把这一管黏糊糊的东西带回实验室,然后测序它的 DNA。他很可能研究不出什么新东西,毕竟口腔可算是人体中被研究得最透彻的微生物栖息地了。列文虎克研究过它,罗斯伯里仔细调查过它,微生物学家已经培养了近500种来自不同生态位的细菌。如果说哪个身体部位与新发现无缘,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嘴。然而,雷尔曼在他的牙龈中发现了一系列远超出当前认知范围的细菌;若采用同样的口腔样本,那么只能在培养皿中培养出很少一部分。
 即使在人类最熟悉的栖息地,依然有数量惊人的未知物种等待我们去发现。2005年,雷尔曼在肠道中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他从三名志愿者肠道中的不同部位收集了一些样本,鉴别出了近400种细菌和一种古菌——其中80%都是新发现。
即使在人类最熟悉的栖息地,依然有数量惊人的未知物种等待我们去发现。2005年,雷尔曼在肠道中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他从三名志愿者肠道中的不同部位收集了一些样本,鉴别出了近400种细菌和一种古菌——其中80%都是新发现。
 换句话说,杜博的预感是对的:在他的时代,微生物学家才刚刚触及了人类正常菌群的皮毛。
换句话说,杜博的预感是对的:在他的时代,微生物学家才刚刚触及了人类正常菌群的皮毛。
一切改变都发端于21世纪早期,研究人员开始调查和测序人体各个部位的微生物。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见到微生物领域的领军人物杰夫·戈登(Jeff Gordon)。戈登通过研究发现,人体内的微生物能控制脂肪的储存与血管的生成,胖子和瘦子的肠道微生物各不相同。
 雷尔曼开始把人体微生物群称为“必不可少的器官”。这些先驱吸引了生物学各领域的研究者前来合作,也吸引了大众媒体的关注,还招募到了上百万美元的国际大项目资金。
雷尔曼开始把人体微生物群称为“必不可少的器官”。这些先驱吸引了生物学各领域的研究者前来合作,也吸引了大众媒体的关注,还招募到了上百万美元的国际大项目资金。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微生物组一直潜伏在生物学的外场,只受到一些反叛者的推崇。而现在,它已经成为生物学研究的重要组成。这既是微生物的故事,也记述了人类关于身体和科学研究的新想法从边缘渐渐走向中心的历程。
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微生物组一直潜伏在生物学的外场,只受到一些反叛者的推崇。而现在,它已经成为生物学研究的重要组成。这既是微生物的故事,也记述了人类关于身体和科学研究的新想法从边缘渐渐走向中心的历程。
走进荷兰阿姆斯特丹阿提斯皇家动物园(Artis Royal Zoo)的大门,你会看到一幢两层楼高的建筑,其侧面的墙上有一幅大步行走的巨大人像。这个人像由毛茸茸的小球拼成:橘色的、米色的、黄色的,还有蓝色的,它们代表了人体内的微生物。他向路过的游客挥手,仿佛在友好地邀请他们进来参观这座微生物博物馆(Micropia)。这是全世界第一座以微生物为主题的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历时12年才策划修建完成,总造价约为1,000万欧元(约合7,800万人民币),于2014年9月正式开放。选址荷兰再合适不过了。正是在距离此地约64千米的小城代尔夫特,列文虎克第一次为人类打开了神秘的细菌世界大门。而现在当我穿过微生物博物馆的检票口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列文虎克的显微镜复制品:低调地摆在一个玻璃罐里,大头朝上,结构简陋得有些不协调。放置在显微镜旁的是列文虎克曾用它观察到的简单物体,其中包括一撮混合胡椒粉、捞自当地池塘的浮萍,以及一块牙菌斑。
我与朋友以及另外一家人一起走入一架电梯。一抬头,我们就能从电梯天花板上的屏幕中看见自己的脸。随着电梯渐渐上升,屏幕中的视频镜头忽然急速拉近,我们的脸被放大再放大,可以陆续看到自己眼睫毛上的螨虫、皮肤细胞、细菌,最后是病毒。当电梯到达二楼打开大门时,一块由无数针眼大小的光点组成的标志牌出现在我们眼前。它们明灭闪烁,仿佛一簇活体菌群,上面写着:“靠得很近很近时,你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美丽、震撼,超乎你想象。”
“欢迎来到 Micropia。”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显微镜,我们可以通过它们立即亲眼观察到美妙的微生物世界:蚊卵、水蚤、线虫、黏菌、海藻以及绿藻,等等。显微镜下的绿藻被放大了200倍,而一想到楼下陈列的那支列文虎克自制的显微镜也能观察到同样的奇景,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列文虎克一定亲眼看过这些奇妙之物,虽然可能不如我们今天观察得这么自在:他必须斜视,让视线透过那块小小的镜片;我则能把眼睛舒服地靠在目镜上,畅览眼前清晰明亮的电子影像。
走过显微镜,再往前便是一个全尺寸展示人体内微生物分布状况的装置。游客可以站在一台相机前,待相机扫描全身;接着,一人高的屏幕上会生成一幅由微生物构成的影像:白色部分勾勒出了皮肤的轮廓,明亮的颜色突出表现了器官,并模拟它们在体内的活动。这幅影像会随着游客的移动而移动。游客可以挥手,选择不同的器官,了解皮肤、肠、胃、头皮、嘴、鼻子等不同部位的微生物状况。游客可以由此知道哪些微生物生活在哪些特定部位,以及它们在那儿会怎样活动。这个展示装置所呈现的内容,浓缩了微生物学家几十年来的发现:从肯德尔到罗斯伯里,再到雷尔曼——可以说,整座博物馆都在向这一段微生物发现史致敬。馆内还展示了一排地衣,它们的结构反映了19世纪的微生物学家关于共生现象的重要发现;还有一台显微镜下摆着乳酸菌,梅奇尼科夫曾经醉心于此。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乳酸菌被放大了630倍,移动的样子十分可爱。
这一切信息直白得令我猝不及防,游客们却很快接受了这个充斥着微生物的世界,没有人畏惧、紧缩眉头或者皱起鼻子,这着实令我惊讶。一对夫妇站在一个红色的心形平台上,面前的“0米亲吻”(Kiss-0-Meter)告诉他们刚才接吻时交换了多少细菌。一位年轻的女士凝视着面前摆满粪便样本的墙壁,它们分别来自大猩猩、水豚、小熊猫、小袋鼠、狮子、食蚁兽、大象、树懒、苏拉威西黑冠猴等,均直接收集自隔壁的动物园;粪便放在密封的真空罐子里,外面还封着一层有机玻璃柜。一群十几岁的少年在细细地参观一堵放着琼脂培养皿的墙,背光灯照亮了正在琼脂中生长的霉菌和细菌,其中一些收集自我们的日常用品,可以通过这些微生物勾勒出的形状辨别它们的来源:钥匙、电话、电脑鼠标、遥控器、牙刷、门把手和长方形的欧元纸币。他们呆呆地盯着克雷伯氏菌( Klebsiella )形成的橘色小点,肠球菌( Enterococcus )铺开的一块蓝色小垫子,以及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留下的铅笔涂鸦般的灰色印迹。
与我一同乘坐电梯上楼的那家人,此刻正在仔细地欣赏一幅覆满整面墙壁的漂亮图画,这是卡尔·乌斯“生命之树”的另一种呈现。动植物退居画面的一角,细菌和古菌占据主干和枝条。那一家人中的父亲出生时,可能还没有任何人发现古菌的存在,而他的孩子们现在已经在这个著名的景点学习它们。
微生物博物馆展现了人类350年来不断增长的微生物知识,同时也反映了人类面对它们不断改变的态度。在这里,微生物不再是遭受忽视的次等生物,也不再是预示凶兆的坏东西。在这里,它们看起来奇妙、美丽,非常引人关注。在这里,它们就是明星。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写道:“确实,那些伟大的创始者要等升到天上,成为明星,左右着我们的命运以后,才会引起我们大多数人的重视。”
 她笔下所写的,可以是那些为我们揭开微生物奇妙世界的科学家,也可以是微生物本身。
她笔下所写的,可以是那些为我们揭开微生物奇妙世界的科学家,也可以是微生物本身。
[1] 列文虎克的生平详细资料可以在道格拉斯·安德森的网站“Lens on Leeuwenhoek”上找到:http://lensonleeuwenhoek.net/,另外还有两部人物传记 Antony Van Leeuwenhoek and His ‘Little Animals’ (Dobell,1932),以及 The Cleere Observer (Payne,1970)。道格拉斯·安德森(Anderson,2014)和尼克·莱恩(Lane,2015b)也在论文中讨论过列文虎克,本书均有引用。列文虎克的名字没有标准拼法,本书选用的是 Dobell 版本的拼法。
[2] 关于巴斯德、科赫以及他们同时代人的故事,在《微生物猎人》( Microbe Hunters )一书中有非常清楚的讲述(Kruif,2002)。
[3] Sapp,1994,pp. 3–14。他的《联合演化》( Evolution by Association )是目前关于共生关系研究历史的最详尽记录,堪称一部历史经典。
[4] 罗斯伯里写了第一本关于人类微生物的科普读物《人类身上的生命》( Life on Man ),是出版于1976年的畅销书。
[5] 这段话摘自《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Blakeslee,1996)。关于乌斯这次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的详细解释,请参见约翰·阿奇巴尔德(John Archibald)的《一加一等于》( One Plus One Equals One ,Archibald,2014)以及简·萨普(Jan Sapp)的《演化的新基础》( The New Foundations of Evolution ,Sapp,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