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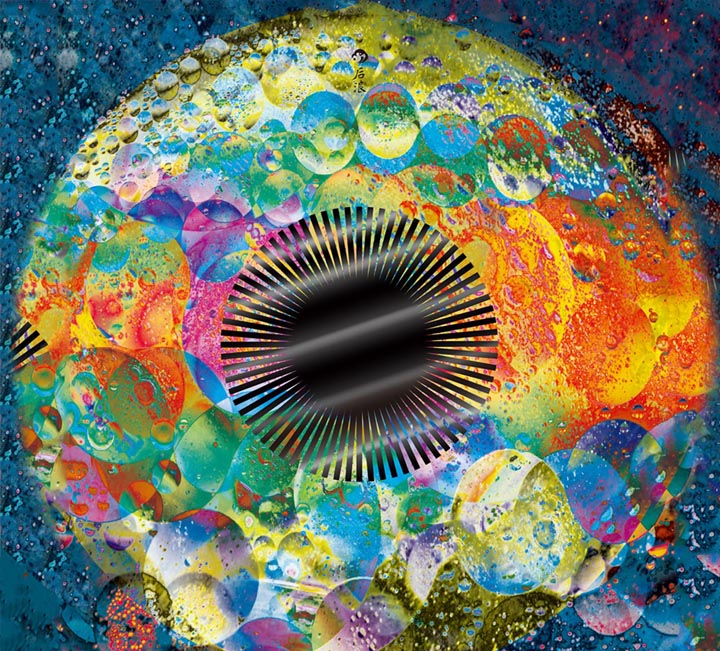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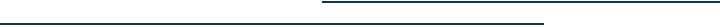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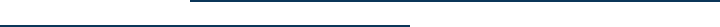
我站在一个花园棚屋大小的房间里,刚好能把猫举起来转一圈,不过多半会在墙上留下猫抓痕。门又厚又大,房间四壁全白,一尘不染。里面一台巨大的风扇有节奏地搅动和控制着空气,听起来就像《星球大战》里的大反派达斯·维德在用扩音器说话。房间里种满了植物,小罐子里冒着豌豆苗、蚕豆和苜蓿的幼苗,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架子上的托盘中。这里仿佛一个奇怪的温室,更奇怪的是一切都被覆盖着。一些幼苗被透明的塑料杯罩着,另一些放置在塑料立方体中,只通过胳膊粗的舷窗与外界相连,舷窗上则覆盖着细棉布。有一个特别大的盒子,里面放着一大簇肆意生长的幼芽。
“我们刚刚开始培育它们,所以我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否已经在这儿了。”生物学家南希·莫兰说道。这个房间位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房间本身以及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她的。
我盯着这些幼芽。很显然,莫兰看不到的,我也没法看到。
“噢,已经有了,”她指着一个地方说,“在那条茎上。”
隔了好一阵,就在我快忍不住开口问到底在哪条茎上之前,我发现了它们。黑色、楔形状的小东西,不超过一厘米,像微型门挡一样挂在芽上。它们是玻璃翅叶蝉(glassy-winged sharpshooters)。英文名字的前半部分透着晶莹剔透的精致感,后半部分又带着几分西部牛仔的粗犷与苍凉
 ,而它实际上与二者都不搭。这些细小的昆虫把口器刺入植物,然后从枝叶里吸取液体,过滤吸收微量的营养物质,再从背后喷出一簇细小的水柱,排出剩余的水分,后半部分的名字正由此而来。这种昆虫会吸取几十种不同植物的汁液,能对农业产生不小的威胁,所以要用又大又重的门隔离,再用细布密封,以防逃逸。
,而它实际上与二者都不搭。这些细小的昆虫把口器刺入植物,然后从枝叶里吸取液体,过滤吸收微量的营养物质,再从背后喷出一簇细小的水柱,排出剩余的水分,后半部分的名字正由此而来。这种昆虫会吸取几十种不同植物的汁液,能对农业产生不小的威胁,所以要用又大又重的门隔离,再用细布密封,以防逃逸。
这个房间里满是这样的威胁。另一种植物正在被一种叶蝉吞噬。满满几架子蚕豆芽正在被豌豆蚜蚕食。这种绿色的昆虫待在绿色的茎表面并不显眼,但我最终还是发现了它们:绿色的锭状小虫,细长腿,触须向后,腹部的两根触角向后突出。每只蚜虫都有自己的私领域,都独占一根正在生长的幼苗。与玻璃翅叶蝉一样,蚜虫也会带来灾害。它们只要简单地占据植物就可以使后者枯萎、死亡,这还不算上它们携带的病毒。这些蚜虫堪称农业之害,在任何人类耕耘和栽种植物的地方都不受欢迎。但在这个房间除外。在这里,它们才是重点,栽培植物的目的只是喂养它们。像这样专门为了培育蚜虫和其他害虫而建的园子,全世界罕见。
这些不起眼的昆虫都属于半翅目(Hemiptera)。这个目包含了丰富的物种,比如床虱、猎蝽、介壳虫和叶蝉等,它们的特点是都拥有能够穿刺和吸吮的口器。大多数人说“虫子”(bug)的时候,指的基本是到处爬的小东西。而昆虫学家口中的“bug”指的是半翅目昆虫。大多数半翅目昆虫一辈子都在吸食植物汁液,它们也是唯一只凭这种方式度日的动物。蝴蝶或蜂鸟只是偶尔吸食,但只有半翅目专门以此为生。其实,这种生存方式是它们的共生细菌造就的。如果所有这些细菌突然死亡,那么这间房里的所有昆虫都只有死路一条。“这些虫子的命基本上是它们的共生体给的。”莫兰说道。有了这些共生体,虫子不仅活了下来,生命力亦十分旺盛:人类已经描述了大约82,000种半翅目昆虫,还有数千种等待我们去发现。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在许多动物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微生物不可或缺,它们甚至打造了生命的基础,例如构造器官、校准免疫系统。我们还简单地了解到,一些微生物可以赋予动物不寻常的能力,比如短尾乌贼用于伪装的发光功能,扁形虫的再生技能等。而现在我们即将见证,一些拥有超强能力的微生物,可以如何让一些动物成为演化中的赢家。它们可以消化无法消化的食物,抵御不适宜生存的环境,吃下威胁生命的食物后还能活下去,或者在其他物种失败的时候获得成功。半翅目正是讲述这一切的完美开端。
1910年,德国动物学家保罗·布赫纳(Paul Buchner)便开始研究昆虫的共生体,而这也是他探寻整个昆虫世界的一部分旅程。
 他解剖、观察了无数物种,发现动物与微生物之间的共生现象并不罕见。当时的人们认为共生是偶然的,但布赫纳坚持认为这是规律而非例外:“这是一计广泛的策略,虽然总是被作为补充策略。它以多种方式扩展宿主动物的生存可能。”他把几十年的工作所得写成一部巨著,《动物与植物微生物的内共生》(
Endosymbiosis of Animals with Plant Microorganisms
),
他解剖、观察了无数物种,发现动物与微生物之间的共生现象并不罕见。当时的人们认为共生是偶然的,但布赫纳坚持认为这是规律而非例外:“这是一计广泛的策略,虽然总是被作为补充策略。它以多种方式扩展宿主动物的生存可能。”他把几十年的工作所得写成一部巨著,《动物与植物微生物的内共生》(
Endosymbiosis of Animals with Plant Microorganisms
),
 该书后来还译成了英文,并在他80岁生日之际面世。莫兰从她办公室的书架上抽出这本书,虔诚地翻阅泛黄的书页。她说:“这是我们这个领域的圣经。”
该书后来还译成了英文,并在他80岁生日之际面世。莫兰从她办公室的书架上抽出这本书,虔诚地翻阅泛黄的书页。她说:“这是我们这个领域的圣经。”
几十年来,莫兰一直为半翅目昆虫着迷。她曾经也是用罐子收集昆虫的小孩,现在则成了共生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蚜虫正是她职业生涯的基石。1991年,她参与了11种蚜虫共生菌的基因测序。当时,基因测序技术仍处于初期阶段,所以那项研究无疑是个庞大的任务。为了交换数据,她和她的同事需要“来来回回地寄软盘”。他们发现,所有的蚜虫共生体都属于同一个未经命名的物种。微生物领域的传统,是用大名鼎鼎的微生物学家的名字来命名新发现的微生物,就像亲笔签名。比如西米恩·伯特·沃尔巴克(Simeon Burt Wolbach)把自己的名字永远地刻在了沃尔巴克氏体上,路易·巴斯德则出现在巴氏杆菌( Pasteurella )中。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默默无闻的美国兽医丹尼尔·埃尔默·沙门(Daniel Elmer Salmon),但很可能耳闻过沙门氏菌的鼎鼎大名。那么把哪个名字赋予蚜虫的共生体呢?好像自始至终,布赫纳氏菌都是不二的选择。 [1]
这是一种古老的蚜虫伴侣。布赫纳氏菌菌株的系谱,也完全和宿主蚜虫的系谱相符,画出一个就会立即得出另一个。
 这意味着,布赫纳氏菌只定植了一次蚜虫(或者至少可以说,只有一次定植成功了)。这个开创性的事件发生在2.5亿至2亿年前,彼时恐龙刚出现,哺乳动物和开花植物都不存在。布赫纳氏菌在那么一长段时间里做了什么呢?布赫纳猜测,昆虫共生体大多是为了获取营养而帮助宿主消化食物。他研究过的许多昆虫都是类似的情况,但布赫纳氏菌略有不同,它不是消化蚜虫的食物,而是为这些食物提供额外的营养。
这意味着,布赫纳氏菌只定植了一次蚜虫(或者至少可以说,只有一次定植成功了)。这个开创性的事件发生在2.5亿至2亿年前,彼时恐龙刚出现,哺乳动物和开花植物都不存在。布赫纳氏菌在那么一长段时间里做了什么呢?布赫纳猜测,昆虫共生体大多是为了获取营养而帮助宿主消化食物。他研究过的许多昆虫都是类似的情况,但布赫纳氏菌略有不同,它不是消化蚜虫的食物,而是为这些食物提供额外的营养。
蚜虫以植物韧皮部的汁液为食,这是一种流经植物各个部位的甜蜜液体,从许多方面而言都是一种极好的食物来源:高糖,低毒,很大程度上也不被其他动物觊觎。但它却严重缺乏几种营养素,包括10种动物生存所需的氨基酸。动物缺乏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将面临毁灭性的冲击。10种氨基酸都缺,更是没有动物能忍受,除非有别的东西可以补偿。现在有无数证据表明,布赫纳氏菌就能提供这样的帮助。
 科学家用能杀死布赫纳氏菌的抗生素处理蚜虫,然后发现昆虫需要人工补充氨基酸才能生存。他们用放射性化学物质追踪营养物质的流向,证明氨基酸正是从微生物流向宿主的。研究表明,布赫纳氏菌的基因组尽管非常小且极度退化,但仍保留了许多合成必需氨基酸的基因。
科学家用能杀死布赫纳氏菌的抗生素处理蚜虫,然后发现昆虫需要人工补充氨基酸才能生存。他们用放射性化学物质追踪营养物质的流向,证明氨基酸正是从微生物流向宿主的。研究表明,布赫纳氏菌的基因组尽管非常小且极度退化,但仍保留了许多合成必需氨基酸的基因。
许多,但不是全部。合成氨基酸很复杂,涉及一系列化学反应,每一次反应都需要不同的酶催化。试想象汽车工厂的流水线,一条履带经过一系列机器,有的固定座位,有的加上底盘,还有的安装车轮……履带尽头,一辆汽车出现。合成氨基酸的生物化学途径,其作用方式差不多,但是蚜虫和布赫纳氏菌都没法自己修建全套的制酶机。不过,它们选择合作建立生产线,使其贯穿进出两个工厂,一个嵌套在另一个之内。只有合作,它们才能靠韧皮的汁液生存。

吸食汁液与补充共生体之间的联系,在一些同时放弃了二者的半翅目昆虫身上体现得更清楚。一些物种会摄取整个植物细胞,自然不缺乏氨基酸,于是便丢弃了它们的共生体伙伴。这段关系中容不下念旧或者多情的念头,自然选择的残酷契约让一个不再必要的合作伙伴惨遭抛弃。这种苛刻的命令也适用于基因,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半翅目会让自己步入一个并不能稳定供应营养的处境。它们是动物,所有的动物都演化自摄食其他东西的单细胞捕食者。它们所摄取的食物提供了许多必需的营养,所以会失去自行合成这些营养素的基因。蚜虫、穿山甲、人类和其他动物都背负着这一历史遗存。我们之中没有谁能自行合成这10种必需氨基酸,而通过饮食可以填补这一缺口。如果我们想靠一种特定但缺乏必要营养的食物而活,比如韧皮部的汁液,那就需要帮助。
这时候就轮到细菌登场了。面对束缚整个动物王国的限制时,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半翅目挣脱,把其他动物无法利用的食物制作成美味盛宴。
 随着植物的迁移,这种吸食植物汁液的昆虫也随之占领了整个世界。今天,全世界大约有5,000余种蚜虫、1,600余种粉虱、3,000余种木虱、8,000余种介壳虫、2,500种蝉、3,000余种沫蝉、13,000多种蚱蜢和超过20,000种叶蝉——这些还仅仅是我们已知的。多亏了共生关系,半翅目得以成为动物界成功的演化典范。
随着植物的迁移,这种吸食植物汁液的昆虫也随之占领了整个世界。今天,全世界大约有5,000余种蚜虫、1,600余种粉虱、3,000余种木虱、8,000余种介壳虫、2,500种蝉、3,000余种沫蝉、13,000多种蚱蜢和超过20,000种叶蝉——这些还仅仅是我们已知的。多亏了共生关系,半翅目得以成为动物界成功的演化典范。
除了半翅目,还有很多其他动物也拥有营养共生体。大约10%至20%的昆虫都依赖这种微生物:它们为昆虫提供维生素、制备蛋白质所需的氨基酸,以及合成激素所需的固醇。
 所有这些活性补充剂,都能让宿主在只能食用缺乏营养的食物(比如植物汁液和血液等)的条件下存活。弓背蚁(又名木匠蚁)是一个包含了大约1,000个物种的属,它们均携带一种名为布洛赫曼氏菌(
Blochmannia
)的共生细菌。这种细菌能让它们主要依靠素食生存,并主宰热带雨林的树冠层。
所有这些活性补充剂,都能让宿主在只能食用缺乏营养的食物(比如植物汁液和血液等)的条件下存活。弓背蚁(又名木匠蚁)是一个包含了大约1,000个物种的属,它们均携带一种名为布洛赫曼氏菌(
Blochmannia
)的共生细菌。这种细菌能让它们主要依靠素食生存,并主宰热带雨林的树冠层。
 例如虱子和床虱(以及不是昆虫的蜱和水蛭等),这些小吸血鬼都依靠细菌提供无法通过血液摄取的 B 族维生素。
例如虱子和床虱(以及不是昆虫的蜱和水蛭等),这些小吸血鬼都依靠细菌提供无法通过血液摄取的 B 族维生素。
细菌和其他微生物一次又一次地让动物超越自身的“动物性”,引诱它们闯入并占据生态环境中的犄角旮旯处,而这些地方原本并不可达;让它们获得原本不能承受的生活方式,吃下原本无法消化的食物;让它们突破天性、获得成功。可以在深海中找到这种携手成功的最极端例子:在那里,一些微生物能够让它们的宿主活在几乎不存在食物的环境中。
1977年2月,就在《星球大战》虚拟世界中的“千年隼”号(Millennium Falcon)奔向太空的几个月前,一艘同样灌注着冒险精神的潜水器“阿尔文”号(Alvin)潜入了深海。这艘潜水器足够容纳三位科学家,其中的空间局促到他们无法展臂,但整个载体又坚固到能够抵达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度。它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以北约402千米的水域开始下潜。在那里,地球上的两个构造板块开裂,就如恋人分手后撕裂的照片。地壳因此生成了一条大裂缝,第一个热液喷口也可能就在这里。人们相信,火山喷发的温度极高的过热水将从海床上滚滚地喷涌而出。
载着工作小队的“阿尔文”号开始下潜。海水从表面的蔚蓝渐渐变成深海的墨黑,而且越来越黑,比任何东西都黑。只有偶尔发着生物光的海底生物打破了这一片黢黑。最终,潜水器的灯光照亮了一切,这里是海平面以下2,400米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之前预测过的海底热液喷口,但也看到了一些不曾预见到的现象,那就是这里活跃着极其丰富的生命。一大簇一大簇的蛤蜊和贝类紧贴着热液烟囱的石壁,鬼魅般雪白的虾和螃蟹依覆其上。规模庞大的鱼群游来游去。最奇怪的是,岩石被坚硬的白色管状物覆盖,其一端仿佛是长着绯红色羽毛的巨型蠕虫。它们看起来就像拧过头的口红,或者像一些更让人不忍直视的东西。其实,它们的确是巨型蠕虫。
人们曾以为,深海是不存在生命的海底荒漠;没有阳光照射,高压下的热水可以达到400 ℃,还必须承受深海的巨大压力。但就在这里,“阿尔文”号的团队发现了一个隐蔽的生态系统,其中的生物多样性丝毫不输热带雨林。正如罗伯特·孔齐希(Robert Kunzig)在《测绘深海》(
Mapping the Deep
)中写到的:“就像一个在加拿大拉布拉多出生长大的人,之前完全不了解外面的世界,突然有一天空降到了时代广场。”该团队没想到能在这里找到生命的迹象,他们之中没有一人是生物学家,全是地质学家。当他们收集好标本并带回地面后,唯一可用的防腐剂是伏特加。

其中一条巨型蠕虫辗转到了史密森尼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梅雷迪斯·琼斯(Meredith Jones)手中,随后被命名为 Riftia pachyptila (巨型管虫)。他发现这种生物非常有意思,甚至于1979年亲自去加拉帕戈斯裂谷收集了更多蠕虫。那里布满了管虫的红色羽状触手,并因此得名“玫瑰园”(Rose Garden)。在一张黑白老照片中,琼斯一头白发,留着小胡子,手里拿着一个管虫标本。照片里的他既温柔又亲切,而管虫看起来像是一坨没包装好的香肠。它的体型很大,比目前发现的其他深海蠕虫都大,抻直了甚至可能有琼斯本人那么高。奇怪的是,它没有嘴,没有内脏,也没有肛门。
既然没办法吃东西,它又是如何生存的呢?最直接的假设是,它像绦虫一样通过皮肤吸收营养。但是这个想法很快被推翻,因为采用这种方式的话,它吸收营养的速度不可能这么快。然后,琼斯注意到一条重要线索。这种管虫有一种名为营养体(trophosome)的神秘器官,占了体重的一半,里面充满了纯硫晶体。琼斯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讲座中提到了这一点。当时,一位年轻的动物学家科琳·卡瓦诺(Colleen Cavanaugh)坐在观众席间,听完琼斯这席话,她的脑中立即产生了一个想法。听琼斯描述营养体时,她的“尤里卡时刻”忽然到来。根据她的说法,自己当即就跳了起来,并且宣布:管虫体内一定有一种细菌,而且这些细菌会用硫来产生能量。琼斯一再请求她坐下,后来干脆给了她一条虫子研究。
经证明,卡瓦诺的顿悟是正确的,也具有革命性。
 她通过显微镜发现,管虫的营养体内充满了细菌,每克组织中大约有十亿个细菌。另一个科学家也发现营养体内富含能够处理硫化物的酶,硫化物则包括常见于海底热液喷口环境的硫化氢。卡瓦诺把两个结论结合在一起,推测这些酶来自细菌,管虫利用细菌合成自身所需的食物,其采用的途径完全不同于当时已知的任何形式。
她通过显微镜发现,管虫的营养体内充满了细菌,每克组织中大约有十亿个细菌。另一个科学家也发现营养体内富含能够处理硫化物的酶,硫化物则包括常见于海底热液喷口环境的硫化氢。卡瓦诺把两个结论结合在一起,推测这些酶来自细菌,管虫利用细菌合成自身所需的食物,其采用的途径完全不同于当时已知的任何形式。
陆地生命由阳光驱动。植物、藻类和一些细菌可以利用太阳能来制作自己的食物,把二氧化碳和水加工成糖类。这种把碳从无机物转化成供能物质的过程即为固碳,利用太阳能的过程便是光合作用。这是我们熟悉的食物链的基础。每棵树、每朵花、每只田鼠和鹰,最终都依赖太阳给予的能量。但在深海,生命无法选择依靠阳光生存。它们可以选择过滤海水,捞得那么一点点从海上像落雪一般沉下的有机物碎屑,但若想旺盛地生存,那就需要一个不同的能量来源。对于管虫体内的细菌来说,这种能量来源便是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热液喷口喷出的硫化物。细菌氧化这些化学物质,用氧化所释放的能量固碳,这就是化学合成(chemosynthesis),即使用化学能而不是光或太阳能来合成食物。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会把氧气作为一种废弃产物排出体外,进行化学合成的细菌则会排出纯硫,并在管虫的营养体内留下黄色的结晶。
这种化学合成过程解释了为什么这种管虫既没有消化系统,也没有嘴:它们的共生细菌为它们提供了所需的所有食物。不像只依赖细菌产生的氨基酸的蚜虫或玻璃翅叶蝉,这些管虫把一切都寄托在它们的共生体之上。
科学家很快在深海发现了类似的共生现象。事实证明,很多动物体内都有进行化学合成的细菌,均使用硫化物或甲烷来固碳。
 能再生的扁形虫旁链虫(
Paracatenula
)
[2]
便是其中之一。一些蛤蛎、蠕虫和带壳蜗牛的体内也有参与化学合成的共生体,虾的鳃和嘴上也聚集了类似的菌群。某些线虫身上布满了此类微生物,看起来仿佛穿着毛皮大衣;有些雪蟹的钳子上就养着一个细菌乐园,随着滑稽的舞步挥动。
能再生的扁形虫旁链虫(
Paracatenula
)
[2]
便是其中之一。一些蛤蛎、蠕虫和带壳蜗牛的体内也有参与化学合成的共生体,虾的鳃和嘴上也聚集了类似的菌群。某些线虫身上布满了此类微生物,看起来仿佛穿着毛皮大衣;有些雪蟹的钳子上就养着一个细菌乐园,随着滑稽的舞步挥动。
许多这样的生物都生活在热液喷口附近,还有一些聚集在冷泉附近,后者会释放相同的化学物质,不过是在较低的温度下以更慢的速度释放。失事船只和沉到海底的木头上定居着与巨型管虫关系很近的管状蠕虫,这些腐烂的木材会产生硫化物供它们使用。死去的鲸会像天赐吗哪
 一般,缓缓地沉入海底,也随之创造出富含硫化物的环境,支撑起一个临时但充满生命力的化学合成生物群落。其中一些生物,例如没有肠子、鼻涕状、靠“啃骨头”生存的食骨蠕虫(
Osedax mucofloris
)
一般,缓缓地沉入海底,也随之创造出富含硫化物的环境,支撑起一个临时但充满生命力的化学合成生物群落。其中一些生物,例如没有肠子、鼻涕状、靠“啃骨头”生存的食骨蠕虫(
Osedax mucofloris
)
 ,专门生存并活跃在鲸落中。
,专门生存并活跃在鲸落中。
对于这些动物而言,走过数十亿年的演化之路后,深海中的生命又仿佛回到了原点。地球上的生命起源于深海热液喷口,一开始的存在形式便是能进行化学合成的微生物。(加拉帕戈斯裂谷的一处地点名为“伊甸园”,真是起得恰如其分。)最终,这些微生物先祖精彩地演化成了数不尽的美丽生命,它们从深海发迹,来到浅海。其中一些演化出了更复杂的生命形式,例如动物;还有一些则通过与进行化学合成的细菌合作,又找回了落回深海、抵达另一个世界的演化之路——如果不这么做,深海极其贫瘠的营养氛围根本没办法支持它们的生存。今天包括管虫在内的所有生活在热液喷口处的动物,都是从浅海物种演化而来的,而它们最终成了深海微生物的宿主。通过内化这些细菌,这些动物拿到了返回冥古的车票。那里既是冥古,也是所有生命的源头。
化学合成可能起源于深海,但不仅限于此。卡瓦诺在新英格兰海岸富含硫化物的泥沙中发现了一种蛤蜊,其体内有一种进行化学合成的细菌。另有人在红树林、沼泽、被污水污染的泥土,甚至珊瑚礁周围的沉积物中发现了类似的共生关系——这些生态系统几乎与浅水同义。卡瓦诺团队的前成员妮科尔·杜比利埃(Nicole Dubilier)在一个远离炽热热液喷口的地方研究化学合成。这地方远到什么程度呢?也许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景色美如明信片的托斯卡纳小岛厄尔巴。
厄尔巴岛阳光灿烂,而这些太阳能也没有白白浪费。离岸的海湾里生长着大片海草。光合作用显然在这里占据着很主要的地位,但即使如此,化学合成也不罕见。杜比利埃潜水到海草处,搅起一些沉积物后便会看到明亮的白色线虫在里面扭来扭去。这是一种名为阿氏厄尔巴线虫( Olavius algarvensis ) [3] 的海洋蠕虫,它们是蚯蚓的近亲,长几厘米,宽半毫米,没有嘴和消化道。“我觉得它们美极了,”杜比利埃说道,“它们是白色的,因为其皮肤下的共生细菌里充满了小球状的硫黄。你可以很容易地把它们挑出来。”这些细菌进行化学合成,类似许多本地的线虫、蛤蛎和扁虫。在这片地中海的泥沙中,通过硫化物制造能量的生物极其丰富多样,甚至能与深海媲美。“居然在意大利!”杜比利埃惊叹道,“我们去了遥远的深海、到了热液喷口后才反过来留意到自家后院里的化学合成共生现象。每次奔赴实地考察,我们都会发现新的物种和新的共生物。”
厄尔巴岛看起来是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但对化学合成的生命而言,这个地方也提出了挑战。还记得管虫的细菌通过氧化硫化物释放能量吧。在厄尔巴岛的泥沙层沉积物中,硫化物含量非常低,按照原理推测,化学合成过程应该不会在那里起作用。那么,厄尔巴线虫是如何生存的呢?2001年,杜比利埃发现了答案。她发现,它们有两个不同的共生体:一大一小,在皮肤下混在一起。
 小的细菌捕获了厄尔巴岛沉积物中十分丰富的硫酸盐,并把它们转化为硫化物;大的细菌会氧化硫化物,为化学合成提供动力,与管虫中的微生物发挥相似的作用。该过程会持续地产生硫酸盐,供身边的小细菌重复使用。这两种微生物在硫循环中为彼此提供原料,然后向蠕虫提供能量和营养,仿佛共生“三人组”。这个环境对于常规参与化学合成过程的伙伴而言非常贫瘠,但厄尔巴线虫在原有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加入了捕获硫酸盐的细菌,成功地在泥沙中存活下来。
小的细菌捕获了厄尔巴岛沉积物中十分丰富的硫酸盐,并把它们转化为硫化物;大的细菌会氧化硫化物,为化学合成提供动力,与管虫中的微生物发挥相似的作用。该过程会持续地产生硫酸盐,供身边的小细菌重复使用。这两种微生物在硫循环中为彼此提供原料,然后向蠕虫提供能量和营养,仿佛共生“三人组”。这个环境对于常规参与化学合成过程的伙伴而言非常贫瘠,但厄尔巴线虫在原有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加入了捕获硫酸盐的细菌,成功地在泥沙中存活下来。
杜比利埃后来又发现,该联盟甚至更复杂。厄尔巴线虫实际上有五个共生体:两个处理硫酸盐,两个处理硫化物,还有一个螺旋状的细菌现在还不知道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可能还需要三十年才能完全理解它。”杜比利埃笑着说道。在浅水中研究共生的她很幸运,不用搭载笨重的潜水器抵达深海也能收集研究对象。她可以在阳光明媚的厄尔巴岛或在加勒比和大堡礁等地点浮潜。总之,这类科研课题很艰难,但必须有人来做。
对于露丝·莱(Ruth Ley)而言,收集微生物就更难了。问题不在于她要从粪便样本中找出微生物,因为在微生物研究中,处理便便根本不是什么事;问题也不在于要从动物园的动物身上收集微生物,因为总有笼子、围墙,或者拿着棍子的管理员守着,可以避免被利爪尖牙伤到。问题在于,做事情之前得先和各类人员过招,忍受各种各样的繁文缛节。
莱是一名微生物生态学家,她想比较不同哺乳动物之间的肠道细菌,看看它们的饮食以及演化史如何塑造各自的微生物组。她需要接触许多动物,收集大量粪便,而她附近的圣路易斯动物园刚好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实验间隙,莱会戴上手套,拎着袋子和一桶干冰,跳上动物园管理员的车,跟着这个非常友好的工作人员驶遍动物园。管理员负责分散动物的注意力,她则偷偷铲走粪便。“我一直往动物园跑,结果有一天有人注意到我原来是在捡大便,于是把我的情况上报给了动物园管理处,要求我必须‘走程序’。”她说道。不能再随便跟着管理员捡粪便,必须和园方沟通,填好收粪便的表格,签一大堆注意条款。例如一个冬日,莱发现动物园里的河马趴在围场的地上,它们已经悠闲地睡着了,“那里恰好有一大坨便便!”莱说道,“但园方却坚持表格上没有河马。随后,铲屎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些粪便十分钟后会转到巷子里,你去那儿取吧。”她只能照做。
她还收集了许多其他动物的粪便:熊(黑熊、北极熊和眼镜熊),大象(非洲象和亚洲象),犀牛(印度犀牛和黑犀牛),狐猴(黑狐猴、獴狐猴和环尾狐猴),以及熊猫(大熊猫和小熊猫)。她花了4年时间收集了60个物种、106个个体的粪便,每份样本都在烘箱中干燥,在混合器中搅成浆,并用研钵和研杵粉碎。那些气味令人难忘,而付出这一切都是为了拿到 DNA 数据,让她能够为这些动物的肠道细菌编目。
莱发现,每种哺乳动物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肠道微生物组,但根据其所有者的祖先,特别是它们的饮食结构,这些菌群能够再次被分成小群体。
 食草动物的肠道菌群通常具有最高的多样性;食肉动物的最低;杂食动物的饮食种类丰富,肠道菌群多样性居中。不过也有例外:小熊猫和大熊猫的肠道微生物更像它们的肉食亲戚,例如熊、猫和狗,但它们本身却是纯食草动物。
食草动物的肠道菌群通常具有最高的多样性;食肉动物的最低;杂食动物的饮食种类丰富,肠道菌群多样性居中。不过也有例外:小熊猫和大熊猫的肠道微生物更像它们的肉食亲戚,例如熊、猫和狗,但它们本身却是纯食草动物。
 不过这依然存在着某种一般模式,可以为此提供一个简单的解释,以及另一个深刻的暗示。
不过这依然存在着某种一般模式,可以为此提供一个简单的解释,以及另一个深刻的暗示。
首先是解释。植物是陆地上迄今为止最丰富的食物来源,但这要求动物配备更多酶来消化它们。与肉类相比,植物组织中含有更复杂的碳水化合物,例如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和抗性淀粉。脊椎动物不具有切碎这些化合物的分子刀,但细菌有。常见的肠道细菌 B-theta 便拥有超过250个切断碳链的酶,而我们虽然拥有比其复杂500倍的基因组,体内的这种酶却只有不到100种。我们使用类似于 B-theta 的各种细菌工具,切断植物组织中的碳水化合物,并释放直接滋养我们自身细胞的物质。它们为我们提供的能量占总摄入能量的10%,而这个比例在牛羊中高达70%。如果选择吃素,动物就需要种类多样、数量丰富的微生物。

其次是暗示。地球上出现的第一种哺乳动物是食肉动物,它们体型较小,动起来一溜小跑,吃昆虫管饱。从肉食到植食的转变,是整个哺乳动物纲在演化上的突破。植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得食草动物的多样性增加得比食肉动物更快,并且散布各处,填补了大型恐龙灭亡后腾出的生态位。今天地球上的大多数哺乳动物是植食性的,大多数目下都至少包括一些食草的物种。即使是包括猫、狗、熊和鬣狗在内的食肉目,其中也有吃竹子的大熊猫。所以,哺乳动物的生存成功建立在植食基础上,而植食又建立在微生物的基础上。不同的哺乳动物一次又一次地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取能够针对植物的微生物,用微生物的酶充分地磨碎和消化枝枝叶叶。
拥有合适的微生物还不够,它们也需要适当的空间和时间才能发挥作用,而植食性的哺乳动物恰好提供了这些条件。它们扩大了一部分肠胃,把它变成发酵室,一是为了容纳这些消化植物的细菌伙伴,二是为了减缓食物通过的速度,让细菌可以充分工作。在大象、马、犀牛、兔子、大猩猩、猪和部分啮齿动物体内,这些发酵室一般都位于肠道的尽头。这些“后肠发酵室”可以令动物在随粪便排出微生物前,让后者通过酶从食物中提取尽可能多的营养。例如牛、鹿、绵羊、袋鼠、长颈鹿、河马和骆驼等另一些哺乳动物,用的则是“前肠发酵室”:它们把微生物放在胃前,或者几个胃中的第一个。为了细菌,它们会牺牲一些营养,但是随后也会消化这些消化助手。“之所以把装细菌的袋子放在前面,是因为你自己也吃这些细菌,”莱说道,“这很聪明。如此一来,单吃秸秆就可以获取所需的全部营养。”比如牛的前肠发酵室会通过反刍来给微生物留下更多时间,虽然把吃下去的东西再呕回嘴里有些恶心,但这种循环反流、重新咀嚼和吞咽的过程十分有效。
发酵室的位置还会影响哺乳动物已有的微生物种类。莱发现,前肠发酵动物的微生物组彼此相似,与后肠发酵动物的微生物组差别较大,反之亦然。这些相似之处,甚至超越了物种祖先之间的边界。袋鼠是一种蹦跳在澳大利亚土地上的有袋动物,身穿“条纹裤”、长相与长颈鹿相仿的㺢㹢狓则来自非洲——但这二者都是前肠发酵动物,从广义上而言,它们的微生物组非常相似。后肠发酵动物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换言之,微生物左右了哺乳动物肠道的演化,哺乳动物肠道的形态也影响了微生物的演化。

莱的下一项研究更加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现象。她与罗布·奈特一起,比较了动物园动物和生活在泥土、海洋、热泉和湖泊等其他地方的动物的微生物基因组。他们发现,就微生物的多样性而言,脊椎动物的肠道菌群十分独特。动物个体之间的肠道菌群差异,甚至大于湖泊、热泉和其他环境之间的微生物差异。正如该研究团队描述的:“肠道与非肠道环境分属两种情况。”
 “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奈特说道,“第一次有人着手这项分析时,我还认为他们搞错了。”形成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不过奈特认为,肠道是微生物的独特栖息地:黑暗、缺氧、时刻经受液体的冲刷,还布满了四处巡逻的免疫细胞,而且极富营养。不是所有细菌都可以在这里生存,但对那些抓住这种生态机遇的细菌来说,这一切都十分合适。它们打入肠道环境,疯狂地生长,继而发展出极富多样性的不同菌株和微生物物种。这株演化树朝一个方向深入,叶片宽大且薄薄的一层,与其说像树冠硕大的橡树,倒不如说更像高挑的棕榈。
“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奈特说道,“第一次有人着手这项分析时,我还认为他们搞错了。”形成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不过奈特认为,肠道是微生物的独特栖息地:黑暗、缺氧、时刻经受液体的冲刷,还布满了四处巡逻的免疫细胞,而且极富营养。不是所有细菌都可以在这里生存,但对那些抓住这种生态机遇的细菌来说,这一切都十分合适。它们打入肠道环境,疯狂地生长,继而发展出极富多样性的不同菌株和微生物物种。这株演化树朝一个方向深入,叶片宽大且薄薄的一层,与其说像树冠硕大的橡树,倒不如说更像高挑的棕榈。
你会在海岛上看到相似的生态系统。岛屿是动物演化的先遣据点,它们或是被暴风雨吹来,或许乘着树干漂来,抑或搭船而来。这些动物或飞行或四处窜行,抑或是蜿蜒滑行着来到岛上各处。它们的后裔开始慢慢地占据岛上的各种栖息地,演化出新的物种。于是便有了夏威夷的蜜旋木雀、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达尔文雀、法属波利尼西亚的蜗牛、加勒比的变色蜥……也许还应该算上我们肠道内的微生物。
研究小组表明,植食性脊椎动物的肠道微生物与其他任何环境中的微生物相比都有很大区别,不论是食肉动物、其他身体部位,还是无脊椎动物的肠道微生物。肠道本身可能就非常特殊,但脊椎动物的肠道更特殊,而灌满植物的脊椎动物肠道更是特殊到无可比拟。大量的枝条和叶片,还有多种多样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就像一座岛屿,为微生物提供了大量的食物来源。肠道为定植其中的细菌提供了无数种谋生方式,并鼓励它们发展出新的生存形式。
 以微生物为动力的消化系统不断让吃素的动物成为自然界的赢家,并且不仅限于哺乳动物。
以微生物为动力的消化系统不断让吃素的动物成为自然界的赢家,并且不仅限于哺乳动物。
昆虫中的素食冠军是白蚁。1889年,一名卓越的美国自然主义者约瑟夫·莱迪(Joseph Leidy)切开了白蚁的肠道,发现了它们吃的东西。他在显微镜下观察解剖后的昆虫,震惊地看到小小的斑点正在逃离白蚁的尸体,就像“一大群人挤出爆满的会议室大门”。他认为它们是“寄生虫”,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些逃掉的小不点儿是一种原生生物:比细菌更复杂的真核微生物,仍由单个细胞组成。原生生物的重量可达白蚁宿主体重的一半,造成其数量极其丰富的原因是,它们有一种能够消化白蚁所吃木材中坚韧纤维素的酶。

这些原生生物大多数都发现于较原始的白蚁种群的肠道内,该白蚁被略带贬义地命名为低等白蚁(lower termites)。“高端”的高等白蚁(higher termites)之后才演化出来,它们更多地依赖细菌,好几个胃中都有各种细菌,这种结构几乎与牛一样。
 有一种听起来更进阶的大白蚁是最新演化出来的物种,它们采用了最复杂的策略来捣碎木质素:该策略就是“农业”。它们会在蚁穴内“种上”一种真菌,并用木屑和碎木片“喂养”这些真菌。真菌把其中的大分子纤维素分裂成更小的分子,做成白蚁能吃的“肥料”。在白蚁的肠道内,肠道细菌会更进一步地消化这些纤维碎片。在解决纤维素的消化问题上,白蚁本身并没有付出太多,它们主要为细菌提供寄宿场所,并培养那些能消化纤维的真菌。如果没有这些微生物伙伴,白蚁就会饿死。大白蚁的蚁后在这条路上甚至走得更远。它的体型巨大,头、胸加起来大约有人类指甲那么长,腹部却有手掌那么大,是一个不断颤动、不停产卵的巨大的囊,大到无法移动。它的肠道中也明显缺乏微生物。不过,它可以依靠工蚁(和它们的微生物)喂养。它的整个领地,包括巨大的巢穴、成千上万的工蚁、数以十亿计的微生物,以及能消化木屑的真菌,都是它的肠道。
有一种听起来更进阶的大白蚁是最新演化出来的物种,它们采用了最复杂的策略来捣碎木质素:该策略就是“农业”。它们会在蚁穴内“种上”一种真菌,并用木屑和碎木片“喂养”这些真菌。真菌把其中的大分子纤维素分裂成更小的分子,做成白蚁能吃的“肥料”。在白蚁的肠道内,肠道细菌会更进一步地消化这些纤维碎片。在解决纤维素的消化问题上,白蚁本身并没有付出太多,它们主要为细菌提供寄宿场所,并培养那些能消化纤维的真菌。如果没有这些微生物伙伴,白蚁就会饿死。大白蚁的蚁后在这条路上甚至走得更远。它的体型巨大,头、胸加起来大约有人类指甲那么长,腹部却有手掌那么大,是一个不断颤动、不停产卵的巨大的囊,大到无法移动。它的肠道中也明显缺乏微生物。不过,它可以依靠工蚁(和它们的微生物)喂养。它的整个领地,包括巨大的巢穴、成千上万的工蚁、数以十亿计的微生物,以及能消化木屑的真菌,都是它的肠道。

大家去非洲旅游时,可以看看这一整条策略有多成功。大白蚁修建了巨大的蚁穴,有些甚至高达9米,仿若哥特式的尖塔和支柱直冲天空。据记载,最古老的蚁穴(现在已经废弃)已有2,200年之久。而蚁穴也为许多其他动物提供了栖息地,白蚁自己也是其他动物的食物。它们消耗枯萎、腐烂的植物,以此驱动营养物和水分在环境中循环流动。它们堪称生态系统的工程师。在非洲的萨瓦那草原上,它们,或者说它们的微生物,秘密地开展着整项工作。如果这些消化植物的肠道细菌不复存在,非洲的自然景观将彻底改变。不仅白蚁会消失,那些巨大的兽群、食草者和巡游者也会消失:羚羊、水牛、斑马、长颈鹿和大象,这些可都是非洲野生动物的代名词。
我曾经在角马大迁徙期间去过肯尼亚。那是一场一年一度的马拉松,数以百万计的角马长途跋涉,寻找更丰美的草场。有一次,我们不得不停下吉普车,让一列长到不可思议的角马队伍从我们面前穿过,足足花了半小时。如果没有微生物尽可能多地从一口口难以消化的植物中提取营养,这些食草动物将不复存在。我们人类也不会。的确难以想象:如果没有驯化这些反刍动物,人类可能走不出狩猎时代,也发展不出聚落和农业,更不用说发明出我们搭载的国际航班,以及这趟野生动物园之旅。再没有游客目瞪口呆地观看一群揣着发酵室的动物跑过,蹄声如雷;非洲可能就只剩下一条空无一物的地平线,伴随着长久的沉寂。
30周内,凯瑟琳·阿马托(Katherine Amato)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她于黎明前醒来,开车到墨西哥的帕伦克国家公园(Palenque National Park),竖耳倾听。当清晨的阳光穿过树林,树枝沙沙作响的声音伴随着一阵阵深沉而嘹亮的喉声。这些叫声来自墨西哥吼猴,它们栖息在树上,硕大且黝黑,长着善于抓握的卷尾,还会发出非常响亮的叫声。整个白天,阿马托都追随着吼叫声,在地面上紧跟着它们穿行于树梢之上的脚步奔跑。她对它们的肠道微生物组感兴趣,需要收集粪便。吼猴都会在同一时间排便,所以很方便收集:“当一只猴子去‘方便’时,你就知道其他猴子都会跟过来。”阿马托解释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吼猴全年不同时期会吃非常不同的食物。它们有半年时间吃的大多是无花果和其他水果:高热量,易消化。吃光果子后,它们大多靠叶和花生存:热量低,纤维更强韧,难以分解。一些科学家提出,为了度过食物短缺时期,这些吼猴会减少活动,进入“待机状态”。但阿马托观察到了截然不同的情形:这些吼猴一年到头都同样活跃。不过,它们的肠道微生物会变化。具体而言,在没有果实的季节,它们会产生更多的短链脂肪酸。由于这些物质能为猴子的细胞提供营养,当吼猴通过食物摄入的热量有所减少时,微生物会有效地为它们提供更多的能量。任凭季节变幻无常,微生物还是为吼猴保证了稳定的营养供给。

如果我们讨论动物时都认为它们一年到头只吃一种东西,其实简化了问题,我之前也曾这样认为。而真实情况是,我们的饮食因季节而异,甚至每天都不同。一只吼猴上个月可能还在吃无花果,下个月却只能闷闷不乐地嚼叶子;松鼠可能整整一个秋天都在吃坚果,冬天则什么都不吃。我可能今天狼吞虎咽地吃着羊角面包,明天只能戳戳沙拉。每吃下一顿饭或一口菜,我们都会选择最适合消化它们的微生物。微生物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对我们的食物做出反馈。有一项研究找了十位志愿者,给了他们两种食谱,让他们按照每种食谱严格坚持吃五天:一种富含水果、蔬菜和谷物,另一种则包括大量的肉、鸡蛋和奶酪。随着饮食结构的改变,他们的肠道也非常迅速地召唤了新的微生物菌群。一天之内,肠道菌群可以从分解碳水化合物和消化植物的模式,转变成分解蛋白质和消化肉类的模式,反之亦然。
 事实上,这两种菌群看起来分别与食草和食肉动物的肠道微生物菌群相符。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它们就重现了别处经历数百万年的演化。
事实上,这两种菌群看起来分别与食草和食肉动物的肠道微生物菌群相符。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它们就重现了别处经历数百万年的演化。
就这一意义而言,肠道微生物使我们成了更灵活的食客。这对于发达国家的居民或动物园中的动物来说可能并不重要,因为他们进食规律,食源丰富。但对于从事狩猎—采集活动的人类祖先,或者吼猴那样的野生动物而言,肠道微生物就非常关键了。他们必须应对跟随季节变化的食物结构,有丰也有荒,或者被迫尝试不熟悉的食物。具有快速适应能力的微生物组,有助于我们应对所有挑战。在不断变化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它们为我们提供了灵活性和稳定性。
这种灵活性可能是动物的福音,但对我们而言可能是诅咒。玉米根萤叶甲是一种产自北美的甲虫,会导致严重的危害。其成虫在玉米地里产卵,来年孵化的幼虫会大口啃食植物的根。这样的生命周期也有脆弱的一环:如果农民交替种植玉米和大豆,成虫在玉米地里产卵,但幼虫孵化后身边都变成了大豆,那就没法存活。这种耕作方式便是轮作,在阻止根虫方面已经卓有成效。但一些抗轮作的叶甲逐渐发展出了利用微生物的对策。它们的肠道细菌变得能够更好地消化大豆的根,让成虫能够打破对玉米长久以来的依赖,从而也能在大豆田中产卵。现在,幼虫孵化后再次如鱼得水。也正是由于这些快速适应变化的微生物组,害虫还在继续为难人类。

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是,有机体不会坐以待毙,它们会保卫自己。动物选择战斗或逃跑,植物则更加被动,更多地依赖化学防御。它们用一些化学物质填充自身的组织,阻止植食者取食;它们能让动物中毒、杀灭细菌、导致体重减轻、引发肿瘤、导致流产、造成神经紊乱,或者干脆杀死对方。
石炭酸灌木(creosote bush)是美国西南部沙漠中最常见的植物之一。它的生存秘诀就是拥有很强的抗性:抗干旱、抗老化,还抗动物啃食。它用含有数百种化学物质的树脂填充枝叶,这占了干重(除去水分的重量)的1/4。这种混合物质赋予了它独特的刺激性气味,雨滴冲刷叶子时,这种气味变得尤为明显。有人说石炭酸灌木闻起来像下雨的味道,但或许是它让雨闻起来像它自己。总之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靠嗅觉都可以捕捉到这种树脂的气味。但是,吞下它就是另一回事了。这种树脂对肝和肾都具有很强的毒性,实验室小鼠一旦摄入过量就会死亡。但是,荒漠林鼠(desert woodrat)吃这种叶子就什么事都没有。它会吃很多很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西南的莫哈韦沙漠(Mojave Desert),石炭酸灌木为它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食物来源,以至于荒漠林鼠冬春两季几乎不吃别的东西。它们每天会吞下大量的有毒树脂,所含剂量足够让实验室小鼠丧命多次。那么,它们是如何应对这种毒性的呢?
动物有许多方法绕开植物毒素,但每个解决方案都要求一定的付出。它们可以吃含毒素较少的部分,但过分挑剔会大大限制觅食机会。它们可以摄入能够中和毒素的物质,比如黏土,但寻找解毒剂会另外耗费时间和精力。它们也可以自己分泌解毒酶,但这会损耗能量。细菌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它们是生化大师,可以降解从重金属到原油的任何物质,区区几种植物毒素根本不在话下。早在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就提出,动物消化道中的微生物,应该能在肠道吸收毒素前对毒素进行“预解毒”。
 若能依靠这些微生物为食物解毒,动物可以省去自己寻找对策而遇到的麻烦。生态学家凯文·科尔(Kevin Kohl)猜想,细菌可能可以解释荒漠林鼠的百毒不侵,而几千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十分明显地为他揭示了证实其猜想的重要线索。
若能依靠这些微生物为食物解毒,动物可以省去自己寻找对策而遇到的麻烦。生态学家凯文·科尔(Kevin Kohl)猜想,细菌可能可以解释荒漠林鼠的百毒不侵,而几千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十分明显地为他揭示了证实其猜想的重要线索。
在大约17,000年前,美国南部的气候开始变暖,起源于南美洲的石炭酸灌木开始在这个地区扎根。它在温暖的莫哈韦沙漠安家,也就进入了荒漠林鼠的领地。但它从来没能迁移到更北、更偏冷的大盆地沙漠(Great Basin Desert),所以生活在那里的主要以杜松为食的林鼠,从来没有尝过石炭酸灌木。如果科尔的猜想正确,那么莫哈韦沙漠的林鼠肠道中应该充满了解毒菌,大盆地里的同类则缺少该细菌。科尔分别从两个沙漠捕获了一些林鼠个体,发现情况正是如此。摄入大量毒素后,大盆地的林鼠的肠道菌群会萎缩,而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的莫哈韦林鼠则会激活相应的解毒基因,大量肠道细菌活跃繁殖。为了证实莫哈韦林鼠是依赖微生物解毒的,科尔在它们的食物中加入了抗生素。然后他用正常的实验室食物喂养这些啮齿动物,在此之前,它们都很健康,但喂食带有少量石炭酸灌木树脂的食物时,它们就受不了了。随着肠道微生物的死亡,它们越来越不耐受这种有毒树脂,甚至不如大盆地的同类。它们的体重掉得很快,科尔不得不提前让它们退出实验。短短几星期,历经17,000年的演化遭到扭转,耐毒经验丰富的荒漠林鼠变成了彻底的“新手”。

科尔做了相反的实验。他收集了一些正常的莫哈韦林鼠的粪便颗粒,搅拌制浆后再喂给大盆地林鼠,即相当于给它们注入了解毒微生物。很快,这些林鼠便可以愉快地享用石炭酸灌木。它们的尿液十分明显地体现出这种新能力:石炭酸灌木毒素会使林鼠的尿液变色、变暗,但这些之前毫无食毒经验的啮齿动物却能分解这么多毒素,它们的尿液呈金黄色,十分清透。仅几顿饭的工夫,它们就获得了历经几千年才演化出来的耐毒经验。
莫哈韦沙漠上首次出现石炭酸灌木时,可能发生了类似的事:一只林鼠窜入灌丛并决定啃上一口,结果这一口东西让它很不好受;但是冬天食物稀缺,没得挑,于是只好再咬一口。咬下去的每一口中都含有一些微生物,它们存在于石炭酸灌木的表面,也许这些微生物已经演化出分解这些树脂毒素的方法。林鼠吃下这些微生物后,也具有了分解毒素的能力。然后,它在身后留下了充满这种微生物的便便,再被另一只林鼠发现并吃下。分解毒素的能力自此得到传播。石炭酸灌木很快成了莫哈韦沙漠中最常见的植物,而林鼠也获得了食用这种植物的能力。林鼠随时都能从彼此身上获得新的微生物,这也许解释了它们为何能适应得如此成功。

在微生物的帮助下,原本不耐毒的宿主能吃下原本致命的食物,类似的案例还有许多。
 共生关系的代表生物地衣,携带着一种名为地衣酸(usnic acid)的毒素。但是驯鹿主要靠食用地衣生存,它们能很好地分解这种酸,排泄物中几乎没有残留这种物质的痕迹。肠道微生物也许可以解释这种能力。从考拉到林鼠的许多植食性哺乳动物都携带降解单宁(一种带有苦味的化合物)的微生物,它赋予红葡萄酒特殊的口感,但会对肝脏和肾脏造成损害。咖啡果小蠹携带的肠道微生物可以分解咖啡因,这种物质虽然能给咖啡爱好者带去愉悦的兴奋感,但也会毒害任何试图寄生在咖啡豆里的害虫。不过这伤害不到咖啡果小蠹本身,因为它携带分解咖啡因的细菌,从而成了唯一以咖啡豆为食的动物,并且也成了全球咖啡业最大的威胁之一。
共生关系的代表生物地衣,携带着一种名为地衣酸(usnic acid)的毒素。但是驯鹿主要靠食用地衣生存,它们能很好地分解这种酸,排泄物中几乎没有残留这种物质的痕迹。肠道微生物也许可以解释这种能力。从考拉到林鼠的许多植食性哺乳动物都携带降解单宁(一种带有苦味的化合物)的微生物,它赋予红葡萄酒特殊的口感,但会对肝脏和肾脏造成损害。咖啡果小蠹携带的肠道微生物可以分解咖啡因,这种物质虽然能给咖啡爱好者带去愉悦的兴奋感,但也会毒害任何试图寄生在咖啡豆里的害虫。不过这伤害不到咖啡果小蠹本身,因为它携带分解咖啡因的细菌,从而成了唯一以咖啡豆为食的动物,并且也成了全球咖啡业最大的威胁之一。
这些技巧都是草食动物生存所必需的:消化食物,同时也分解毒物;不仅因为吃下食物而活着,还因为吃下这些也能活。植食者把微生物的各种能力与动物自身拥有的任何策略相结合后,可以充分利用环境中丰富的绿色植物。同时,植物会受到一定损害,但一般不会太严重。石炭酸灌木虽然遭到林鼠啃食,但它们依然是莫哈韦沙漠的主人。地衣遭到驯鹿啃食,却仍然覆盖着茫茫苔原。考拉吃掉桉树树叶,但在澳大利亚依然随处可见它们的树影。谢天谢地,即使有咖啡果小蠹的侵害,咖啡产量总体上还过得去。但有时微生物分解毒素的能力实在太强,反而会让植物遭受重大损失。
如果你坐飞机飞过北美的西部森林,很可能会发现大片红色或者裸露着枝干的树林。这看起来像是一派如画的秋天景色,但实际上却是一场灾难。这些树是松树,作为常绿树,它们的针叶不应该是红色的,至少还未濒死时应该全年常绿。杀害它们的凶手是谁呢?山松甲虫是一种身长不超过一粒米饭的炭黑色昆虫。它钻透松树的表皮,在树皮下蚀出一道长长的沟,一边移动一边产卵。孵化后,幼虫会钻入树皮,吸食韧皮部的汁液。一只甲虫吸食的汁液可能很少,但是成千上万只甲虫就可以侵蚀一整棵松树。剥下一块树皮,你会看到它们的“杰作”:迷宫般的隧道沿着树干向下延伸。甲虫吸取了松树大部分的营养,从而导致松树死亡,并把死讯散播给旁边的一棵棵同类,松树林一亩又一亩地变红,大片大片地死亡。

这种甲虫有一些更小的同谋者:类似于之前写到的蚜虫,两种真菌作为膳食补充剂,如影随形地陪伴着它们。虽然甲虫的活动范围仅仅是树皮下方一层(而那一部位通常都无法获得充足的营养),但这两种真菌却可以更深入地侵入树体,打入存储着氮和其他必需营养物质的部位。而这些地方在其他情况下一般都难以企及。之后,这两种真菌再把这些营养物质抽取到表面,也就是幼虫可达的范围。“这些甲虫靠‘垃圾食品’过活,而真菌为它们提供全面的营养。”昆虫学家戴安娜·西克斯(Diana Six)说道,多年来她一直在研究甲虫。幼虫最终成蛹后,真菌会产生一种结实而强大的繁殖体——孢子。成虫羽化后会把孢子装入口中一个类似旅行箱的结构,然后带着它们去往下一棵倒霉的松树。
甲虫疫情忽来忽去,但目前这场因为全球气候变暖而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剧烈十倍。自1999年以来,甲虫及其附带的真菌杀死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超过一半的成年松树,影响了美国1,500万平方千米的树林。它们甚至越过了寒冷的加拿大落基山脉,离开长期止步于此的西海岸,开始向东扩散。而绵延在它们前面的,恰好是一条茂密但脆弱的森林带。
然而,树木不会温和地走进那良夜。遭到甲虫攻击后,它们会大规模地分泌一种名为萜烯(terpenes)的化合物,浓度很高,足以杀死甲虫和真菌。甲虫应该以纯暴力来对抗树木的防御:以巨大的数量盘踞树上,多到树木制造的萜烯都不足以杀光它们。但在昆虫学家肯·拉法(Ken Raffa)看来,这一解释说不通。如果真是这样,树木应该会集中产生一定数量的萜烯,那么在面对甲虫的猛攻时会很快耗尽。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树木实际上能保持至少一个月的高水平化学防御,而甲虫的幼虫必须比它们的父母面对更多的毒素。
甲虫会怎么办呢?拉法的团队发现,除了真菌,甲虫也与一些细菌合作,比如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和拉恩氏菌(
Rahnella
)。它们出现在所有分布着甲虫的地区和有甲虫寄生的树上,几乎无处不在:附在昆虫的外骨骼上、挖出的虫道里、嘴和肠道中。它们是一组特定的菌种,多样性远小于白蚁等动物的肠道菌群,不适合承担任何消化功能。然而,它们具有大量用于降解萜烯的基因。研究表明,在实验室条件下,它们能有效地分解这些化学物质。不同的菌种处理不同的化合物,合在一起便能基本清除这些有毒物质。

到了这一步,似乎可以宣布问题已经解决:细菌解除松树的毒素防御,甲虫把它们从一棵树传播到另一棵。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共生世界很复杂,简单的叙事虽然看起来自洽,但往往都是错误的。一开始,健康、未经感染的松树上也存在相同的细菌,它们可能是树本身的微生物组的一部分。松树遭到甲虫攻击时,萜烯分泌量飙升,这些细菌仿佛迎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盛宴”。它们得到了丰富的食物,却无意中伤害了宿主、帮助了入侵的甲虫。甲虫自身也有一套作用有限的分解萜烯的酶,所以如何计算细菌本身的贡献呢?是承担了大量的解毒工作,或是与昆虫各自分工,就像蚜虫和布赫纳氏菌合作制造氨基酸那样?以及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们真的提高了甲虫的生存概率吗?
现在我们很清楚:由动物、真菌和细菌组成的大型联盟降临森林,虽然树木具有非常强的化学防御机制,但在这个联盟的攻击下,它们依旧陆续地开始死亡。它们的消亡证明了共生的力量,即一种允许本来最无害的生物变成最可怕生物的力量。你可能需要眯缝起眼睛才能看到这些微小的甲虫,只有通过显微镜才能看到相应的微生物,而它们相互合作形成的后果,却能从遥远的天空中俯瞰到。
微生物赋予半翅目昆虫能力,帮助它们演化到能吸食全世界植物汁液的地步;白蚁和食草哺乳动物也因为有了微生物而可以消化植物的茎和叶。管虫能在最深的海洋中定植,林鼠可以在美国的沙漠中扩散,山松甲虫可以摧毁绵延大陆的常绿森林。

与这些招摇瞩目的例子相反,二斑叶螨制造的破坏场景精细且微妙。与甲虫一样,这种微小的红色蛛形纲生物与句号一般大小,却凭借庞大的数量杀死了它们附着的许多植物。它是一种全球性害虫,其厉害程度也得益于它的抗药性,以及来者不拒的食性:它能吃掉超过1,100种植物,从番茄到草莓、玉米和大豆。如此宽泛的口味意味着它拥有很不错的解毒技能:每种植物都有各自的化学防御物质,二斑叶螨需要一种万能的解毒方法。幸运的是,它装备了一个塞满解毒基因的武器库,一旦决定吸食某种植物,便会激活相应的基因。
微生物似乎不太像是这个特殊故事中的英雄。与荒漠林鼠或山松甲虫不同,二斑叶螨不依赖有助于消化食物的肠道细菌。它自己的基因组里就包含所需的一切。但即使细菌缺席这一场景,这些微生物对二斑叶螨也依旧很重要。
二斑叶螨食用的许多植物,其组织受到破坏后会释放氰化氢。这种物质对生命体极不友好。人们用它毒灭老鼠,捕鲸者把它抹在鱼叉上,纳粹把它用在集中营中。但二斑叶螨坚不可摧。它的其中一个基因可以产生一种把氰化氢转化为无害化学物质的酶。相同的基因存在于各种蝴蝶和蛾的毛虫中,所以它们能安之若素地爬过布满氰化物的植物。二斑叶螨和毛虫破坏氰化物的基因都不是自己原生的,也并非遗传自共同的祖先。
这种基因来自细菌。

[1] 莫兰对布赫纳菌的第一项研究,与细菌学家保罗·鲍曼一同完成(Baumann et al.,1995)。两位都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共生体。鲍曼菌( Baumannia )发现自玻璃翅叶蝉体内,莫兰菌在更晚些时候发现自柑橘粉蚧体内。
[2] 拉丁名 Paracatenula , para- 为拉丁词根中的“旁、伴”, catenula 意为“小链子”。该译名系译者自拟。——译者注
[3] 拉丁名 Olavius algarvensis 中涉及地名,其中 Olavius 来自 Ilva,是厄尔巴岛的罗马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