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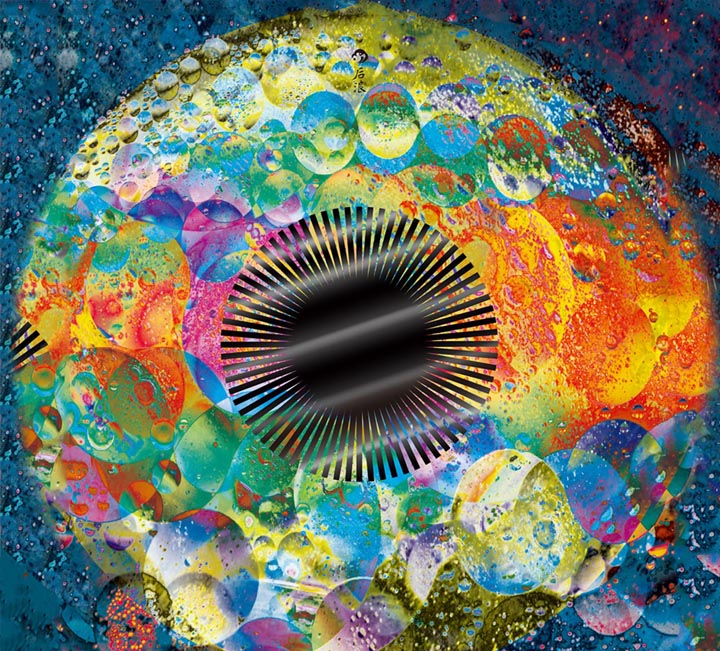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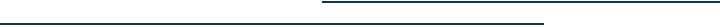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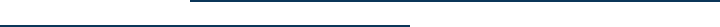
2010年10月15日,印第安纳州埃文斯维尔一位名叫托马斯·弗里茨(Thomas Fritz)的退休工程师,开始砍自家院子里一棵枯败的欧洲野苹果树。他轻松地把树砍倒,但拖走枝干时,他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虎口被一根铅笔粗细的枝条直接穿透。弗里茨是一名消防志愿者,接受过急救训练,他知道如何包扎伤口。尽管这样,他的手还是受到了感染。两天后他去找医生,那时候他的手上已经长出了一个囊肿。弗里茨用了一个疗程的抗生素,但无济于事。过了漫长的五周后,一名外科医生摘出了几块顽固嵌在他肉里的树皮,弗里茨的手才开始恢复正常。
这件倒霉事本该就此画上句号,但弗里茨的医生当时从他的伤口中收集了一些体液。这些样本被送到犹他大学的一个实验室,那里有条件识别其中的神秘微生物。经过实验室自动化仪器的鉴定,弗里茨伤口中的细菌显示为大肠杆菌,但医学主任马克·费希尔(Mark Fischer)并不买账。二者的 DNA 匹配度并不高。他更仔细地检查基因序列后发现,这些细菌的基因几乎与一种名为伴虫菌的细菌相同,后者发现于1999年。幸运的是,伴虫菌的发现者、英国科学家科林·戴尔(Colin Dale)也在犹他大学工作。
戴尔对此持怀疑态度。费希尔与他确认,说实验室的琼脂培养皿中正在培养这种微生物。戴尔反驳了他,认为这一定是个错误。根据已知的发现,伴虫菌只存在于昆虫体内。戴尔最开始在一只吸血的舌蝇体内发现了该细菌,之后又在象鼻虫、椿象、蚜虫和虱子中找到了相应的踪迹。它寄居在这些动物的细胞内,因为在演化过程中失去了太多基因,所以没有办法在其他地方生存。它不可能在一个培养皿中生长,更不用说在受到感染的手部伤口或枯死的树枝上。然而 DNA 不会说谎。来自弗里茨手上的细菌与伴虫菌存在许多相同的基因。戴尔称这种新菌株为 HS,意为“人类伴虫菌”(human sodalis)。他表示:“我推测 HS 普遍存在,但我们从未检查过枯死的树枝。”
细想这个故事,其中存在着颇多巧合。野外的微生物寄居在正确的树枝上,刺穿了正确的人,并最终在正确的实验室碰见了正确的人,而这个人恰好发现了这种细菌被昆虫“驯化”的“表亲”。这看起来像是集合了一系列荒诞的“不可能”事件。但此类事件又发生了一次。这一次的受害者是一个爬树的孩子。与弗里茨的遭遇很相似,这个孩子爬树时受了伤。但与弗里茨不同,他没有立即受到感染。他的第一个症状出现在十年后,一个神秘的囊肿在旧伤口处形成。医生取出囊肿,并把样本送到犹他大学。实验人员从中发现了两种 HS 菌株。

我们暂且不谈弗里茨或者那个爬树的孩子:截至目前,他们都很健康,只是下次面对树木时或许会更加小心谨慎。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 HS 上。一讨论到这种微生物,共生问题的研究者总会两眼放光,因为它们通过一个罕见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动物与细菌的伙伴关系中最根本,但又不确定的面向:这种关系的形成开端。通常,当我们发现自然界还存在这些关系时,它们已经共舞了数百万年。但是,它们第一次携手时,各自是什么模样呢?是什么让它们走到一起?它们是如何一起共舞的,又是如何分别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改变的?这些问题令人摸不着头脑。这曲漫长华尔兹的第一步,几乎迷散在了时间长河中,留下的足迹少之又少,让我们很难追根溯源。
HS 却是个例外。它显示了与昆虫“签订契约”成为其身体的一部分之前,伴虫菌看起来可能是什么模样的。那时候,它还是自由生存在动物体外的微生物,只在时机合适时感染宿主。但其发展过程中缺少一处关键连接,即潜在的共生体。科学家早就预言,世界上存在着这样的原始微生物,但人们普遍认为很难找到哪怕一个这样的生物。戴尔一人就发现了两个。他已经为 HS 赋予了正式的学名:
Sodalis praecaptivus
。该拉丁名的字面意思是“被囚禁前的伴虫菌”。

试想象 HS 的生活。它原本好好地待在植物上,自生自灭。但是如果一不小心闯入了一位粗心大意的园丁或者摔了一跤的孩子的皮肤,它就开始增长、繁殖。还有一种更可能成立的情况,即它进入了一种生活在植物上的昆虫体内。事实上,戴尔根据基因推测它是一种病原体,会让树木患病,并利用昆虫的口器传播。它们早先就已经依靠这些动物抵达新的宿主。它逐渐演化,为动物提供营养或防止其他寄生虫侵入,从而助益宿主的生长。它最终可能从宿主的肠道或唾液腺转移到细胞内部,也无须通过树木,只要从一只昆虫转移到另一只昆虫上,再从母本转移到后代,代代相传,永久地成为宿主的一部分。HS 作为昆虫的共生体,因为所处环境的舒适度而逐渐失去了不再需要的基因,继而成为“伴虫菌”。这些事件可能发生了好几次,最终演化出了存在于各种昆虫体内的不同版本的伴虫菌。

许多共生关系很可能都以这种方式开始。环境中的任意一种微生物——寄生虫或无害的细菌——都会以某种方式侵入动物宿主。这种侵入很常见,且不可避免。细菌的普遍存在,意味着我们做任何事情几乎都会接触到新的细菌物种。
你不需要用树枝刺穿自己。可以通过交配接触微生物:蚜虫交配时可以通过微生物来帮助彼此防御寄生虫或忍受高温。吃东西也可以:木虱可以通过捕食同类来获取微生物。小鼠可以通过吃掉其他小鼠的粪便来获取对方的细菌。如果两只臭虫恰好在吸食同一株植物,那么它们可以通过回流的消化物传递微生物。每个人每吞下一克食物,平均会吞下约100万个微生物。正因为微生物无处不在,无论是水、植物的茎或是另一种动物的肉,几乎所有食物都是新共生体的潜在来源。

寄生虫为进入动物宿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传播路径。许多黄蜂通过尾部尖尖的蜂针把卵产在其他昆虫体内,就这样从一个受害者插向另一个受害者。这些黄蜂就像活的飞版“脏针头”,把对它们自己有益的微生物从一个宿主传给另一个宿主,就像蚊虫叮咬可能传播疟疾或登革热一样。我们对已有事态的掌握,仰赖于科学家实地目睹到,并在实验室中复制出的这些过程。
 受到污染的食物和水、不采取防护措施的性行为、脏针头:这些传播路径都会让我们联想到疾病。但是,任何病原体能走通的道路,有益的共生体也可以加以利用。
受到污染的食物和水、不采取防护措施的性行为、脏针头:这些传播路径都会让我们联想到疾病。但是,任何病原体能走通的道路,有益的共生体也可以加以利用。
当然,传播路径并不是故事的全部。细菌一到达某个新的目的地,首先要让自己在那里“安家”,但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它必须对付免疫系统、微生物竞争对手和其他各种威胁。也许每一百次传递,只有一次能发展出稳定的合作关系,甚至更可能是一百万次才有一次。但我们没办法知道。不过,单就任何一个领域而言,可能有一百万只蚜虫吸食了同一株植物,有一百万只黄蜂飞来飞去、把被细菌污染的蜂针插入蚜虫体内。在这样的基数下,本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也会变得普遍,看起来不合理的事情也能说得通,比如因为树枝刺穿皮肤而获得了一个新的共生体。
如果新来的微生物是战斗力尚可的寄生虫,或许能逗留一阵;但其中有些寄生虫会通过给宿主提供一点好处而保证自己有地方住。它们甚至不需要任何特别的适应过程。这种微生物随处可见。它们通过自然而然的行为来适应共生。植食动物摄取的微生物可以分解复杂的植物纤维,通过这一过程释放出一些难以获取的化学副产物,供给细胞产能。毫无疑问,这样的微生物能够马上适应这种共生关系。只要采取纯粹自利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还能顺便让宿主获益。这里的“副产物互惠”,可以算是微生物和动物的第一次完美携手。
 合作双方都能从共生关系中得到好处,且不必另外投资。随后,宿主可以演化出巩固合作关系的特征,从容纳伙伴的细胞到提供分子锚点、供微生物们锁定自身。而这其中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用于保证关系稳定性的最重要特质:遗传。
合作双方都能从共生关系中得到好处,且不必另外投资。随后,宿主可以演化出巩固合作关系的特征,从容纳伙伴的细胞到提供分子锚点、供微生物们锁定自身。而这其中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用于保证关系稳定性的最重要特质:遗传。
夏日炎炎,欧洲的蜜蜂嗡嗡地穿梭在花丛中。突然,一只黑黄色的昆虫闯了进来,一把抓住蜜蜂,用螫针麻痹了它。这个攻击者是欧洲狼蜂,势如其名,凶猛、大块头。这只雌蜂把受害者拖回地下洞穴,把它与她产下的卵以及其他几只蜜蜂埋在一起。这些蜜蜂还都活着,但动弹不得。雌蜂会把食物小心地储存在卵边,小狼蜂一孵化便可以大快朵颐。
蜜蜂只是雌蜂亲子食单中的一道佳肴。马丁·卡尔滕波特(Martin Kaltenpoth)在研究狼蜂的行为时,注意到有白色的液体从一个标本的触角中流出来。他以前看到过这种物质。为了产卵,雌蜂会挖一个洞穴,而在往里产卵之前,它会把触角按压在泥土上,像挤牙膏一样从中挤出一些白色物质,然后摇晃头部,把分泌物涂抹在洞穴顶部。经过涂抹的位置标志着出口,可以告诉新孵化的狼蜂,离开这个洞穴时应该从哪儿开始挖掘。卡尔滕波特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分泌物时,惊讶地发现里面充满了细菌。狼蜂是用触角分泌微生物的蜂类?此前还没人听说过这样的奇闻。更神奇的是,每只狼蜂分泌的都是同一种细菌:链霉菌( Streptomyces )菌株。
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链霉菌十分擅长杀死其他微生物,我们使用的抗生素有2/3都来源于这种细菌。一只幼小的狼蜂肯定需要抗生素。它吃完母亲为它储备的蜜蜂后,会织茧过冬。整整九个月,它都困在一个温暖、潮湿的房间内,而这恰恰是滋养病原真菌和细菌的完美环境。卡尔腾波特认为,母亲的抗生素分泌物,可能可以帮助幼虫免遭致命的感染。实际上,当他仔细观察幼虫时,他发现它们能把这种含有细菌的分泌物掺入茧的纤维中,就相当于给自己织了一床抗生素棉被。卡尔滕波特移除这种白色分泌物后,几乎所有狼蜂都在一个月内死于真菌感染。
 如果有白色分泌物,它们通常都能存活下来。春天一到,成年狼蜂破茧而出,之后再次通过触角分泌的链霉菌,守卫自己过冬。它们自己挖洞、捕捉蜜蜂,并把这些救命的微生物传给后代。
如果有白色分泌物,它们通常都能存活下来。春天一到,成年狼蜂破茧而出,之后再次通过触角分泌的链霉菌,守卫自己过冬。它们自己挖洞、捕捉蜜蜂,并把这些救命的微生物传给后代。
动物把微生物传给后代,这是共生世界中最重要的传播行为,宿主和共生物的命运也因此捆绑在一起。
 传播行为确保动物与微生物共舞的这曲华尔兹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无论时间的推移;与上一代相比,下一代也会与微生物维持同样的关系。这种传播行为营造了演化的压力,让舞者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微生物面临巨大的演化压力,进而发展出帮助宿主的能力,因为这会为它们搭建起一个更浩大的合作伙伴储备库。动物也受到这种压力的驱使,从而演化出更有效的传播方式,像传递传家宝一样,把自己体内的微生物原封不动地传给后代。
传播行为确保动物与微生物共舞的这曲华尔兹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无论时间的推移;与上一代相比,下一代也会与微生物维持同样的关系。这种传播行为营造了演化的压力,让舞者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微生物面临巨大的演化压力,进而发展出帮助宿主的能力,因为这会为它们搭建起一个更浩大的合作伙伴储备库。动物也受到这种压力的驱使,从而演化出更有效的传播方式,像传递传家宝一样,把自己体内的微生物原封不动地传给后代。
最可靠且能打造出最亲密共生关系的传播途径,是直接向卵细胞中添加微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的线粒体,其前身也是一种细菌;它已经存在于动物的卵细胞中,所以母亲不需要采取额外的手段就能把它们传递给孩子。而深海蛤、海扁虫和无数昆虫等都采用“进口”策略引入其他微生物。从成为受精卵的那一刻起,微生物就伴随着动物的成长发育。动物从不孤独。
即使不能通过卵细胞传播,也有其他方法确保合适的微生物定植你的后代。许多昆虫会采用类似狼蜂的策略:它们在卵的附近储备微生物,供幼虫食用。椿象科的昆虫也十分擅长这种策略。没什么人比深津武马(Takema Fukatsu)更了解椿象,这位对昆虫充满热情且本人极富感染力的昆虫学家,志在研究世界上的每一种昆虫。
 他发现,有一种椿象能把微生物裹在一个耐寒、防水的“胶囊”中,然后把卵产在其中,新孵化的幼虫便能食用这些微生物。另一种椿象则直接把卵包裹在充满微生物的胶状物中。日本的一种椿象有着红黑色的英俊外表,十分漂亮,但对农作物有害。这种椿象采取的策略最为极端。大多数昆虫会放任卵和幼虫不管,但这种椿象十分执着于自己产下的卵,会像母鸡孵蛋一样守在卵上,甚至孵化后还会收集果实来喂养幼虫。它们可以以某种方式感知开始传递微生物的时刻。为了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它们会预先从背部分泌大量充满细菌的黏液。它们把这种白色的液体覆在卵上。裹完后的卵看起来像一个果冻球,上面涂着世界上最恶心的“糖霜”。幼虫孵化后会咽下这些黏液,这也意味着,最新鲜的肠道微生物定植在了它们体内。这种时候就不要想象这件事情有多恶心啦,想想这一刻多么重要啊!每一只幼小的虫子吞下第一口黏液后,便从一个个体转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群体,它们的身体从无菌环境变成了一个繁荣的生态系统。
他发现,有一种椿象能把微生物裹在一个耐寒、防水的“胶囊”中,然后把卵产在其中,新孵化的幼虫便能食用这些微生物。另一种椿象则直接把卵包裹在充满微生物的胶状物中。日本的一种椿象有着红黑色的英俊外表,十分漂亮,但对农作物有害。这种椿象采取的策略最为极端。大多数昆虫会放任卵和幼虫不管,但这种椿象十分执着于自己产下的卵,会像母鸡孵蛋一样守在卵上,甚至孵化后还会收集果实来喂养幼虫。它们可以以某种方式感知开始传递微生物的时刻。为了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它们会预先从背部分泌大量充满细菌的黏液。它们把这种白色的液体覆在卵上。裹完后的卵看起来像一个果冻球,上面涂着世界上最恶心的“糖霜”。幼虫孵化后会咽下这些黏液,这也意味着,最新鲜的肠道微生物定植在了它们体内。这种时候就不要想象这件事情有多恶心啦,想想这一刻多么重要啊!每一只幼小的虫子吞下第一口黏液后,便从一个个体转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群体,它们的身体从无菌环境变成了一个繁荣的生态系统。
吸血的舌蝇在人类之间传播非洲昏睡病(也称非洲锥虫病)。这种昆虫也为它们的幼虫提供微生物,但却是在自己体内完成这一过程的。这种昆虫尝试着把自己变成哺乳动物。它们不产卵,而是“分娩”幼虫,所采取的生存策略也不是通过繁衍大量后代来对赌成活概率,而是把能量投给单一幼虫。它们把幼虫养在“子宫”里,用类似母乳的液体喂养。液体中充满了营养物质和微生物(包括伴虫菌),所以当可怜的母亲生出奇怪、巨大的幼虫时——相信我,人类婴儿的诞生完全不能与之相比——它已经拥有了生存所需的全部细菌伙伴。

其他动物都等幼体孵化或出生后才喂食微生物。小考拉六个月大时断奶,接着开始吃桉树叶。但它先会把鼻子和嘴巴紧贴着母亲的后背摩擦。作为回应,母亲会分泌一种半流质体(pap)让小考拉吞下。半流质体里充满了细菌,能帮助小考拉消化坚韧的桉树叶,而其中所包含的微生物数量是正常粪便中的40倍之多。如果没有吃下这“第一餐”,接下去无论吃多少餐,小考拉都很难消化桉树叶。

幸好我们人类不用先吃半流质体。人类的卵细胞中没有细菌(线粒体不算),我们的母亲也不会给我们涂满黏液。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与第一批微生物汇合。1900年,法国儿科医师亨利·蒂西耶(Henry Tissier)推断,子宫是隔开婴儿和细菌的无菌环境,当我们通过阴道挤压、与阴道中的细菌接触后,这种隔离就结束了。这些细菌是我们身上的第一批“殖民者”,是打入人体内空白生态系统的先驱。这很像日本的椿象,从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刻起,全身就被母亲的微生物包围。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显示,在羊水、脐带血和胎盘等所谓的无菌组织中,都发现过微生物 DNA 的痕迹。这大大挑战了“无菌子宫”这一概念(但这些研究还极具争议)。
 目前尚不清楚微生物是如何到达这些地方的,以及它们的存在是否重要,甚至是否真的存在。因为这些 DNA 可能来自死去的细胞,或是某些污染了实验的细菌。蒂西耶的“无菌子宫”假说可能是错的,但肯定还没有被彻底推翻。
目前尚不清楚微生物是如何到达这些地方的,以及它们的存在是否重要,甚至是否真的存在。因为这些 DNA 可能来自死去的细胞,或是某些污染了实验的细菌。蒂西耶的“无菌子宫”假说可能是错的,但肯定还没有被彻底推翻。
即使动物不从亲本身上垂直地遗传微生物,它们仍有办法在水平方向上“捕捉”合适的共生体。许多动物通过排出微生物而把周围打造成充满微生物的环境,使后代可以拾取它们。
 其他动物甚至会采取更直接的方式。比如白蚁,用格雷格·赫斯特(Greg Hurst)的话来说,“(幼虫)直接舔舐肛门,或者换用较为专业的术语,它们进行‘直肠交哺’(proctodeal trophollaxis)。”考拉这样的动物需要微生物来消化食物(即木质纤维素),它们通过吸收母体分泌的半流质体达成目标。但是白蚁不像考拉,它每次蜕皮都会失去肠道内衬和其上的所有微生物,所以经常需要舔舐兄弟姐妹的“后门”来补充微生物。我们可能觉得这种习惯令人生理不适,但放眼动物世界,我们对粪便的厌恶反而显得很不寻常。牛、大象、熊猫、大猩猩、老鼠、兔子、狗、鬣蜥、葬甲、蟑螂和苍蝇等许多我们熟知的动物都具有粪食性(coprophagy),即经常吃彼此的粪便。
其他动物甚至会采取更直接的方式。比如白蚁,用格雷格·赫斯特(Greg Hurst)的话来说,“(幼虫)直接舔舐肛门,或者换用较为专业的术语,它们进行‘直肠交哺’(proctodeal trophollaxis)。”考拉这样的动物需要微生物来消化食物(即木质纤维素),它们通过吸收母体分泌的半流质体达成目标。但是白蚁不像考拉,它每次蜕皮都会失去肠道内衬和其上的所有微生物,所以经常需要舔舐兄弟姐妹的“后门”来补充微生物。我们可能觉得这种习惯令人生理不适,但放眼动物世界,我们对粪便的厌恶反而显得很不寻常。牛、大象、熊猫、大猩猩、老鼠、兔子、狗、鬣蜥、葬甲、蟑螂和苍蝇等许多我们熟知的动物都具有粪食性(coprophagy),即经常吃彼此的粪便。
对于表皮上的微生物而言,简单的接触就已足够。从蝾螈、蓝鸲再到人类,比邻而居的不同动物往往拥有类似的菌群。与分开居住的朋友相比,住在同一栋房子里的人,其皮肤微生物会更类似。同样,在同一个狒狒群内部(会互相梳毛),其肠道微生物彼此相似;即使有两个住在同一地方、吃同样食物的狒狒群,群体间(而非群体内)也存在差异。以美国一群轮滑对抗赛(Roller Derby,一种有大量身体接触的轮滑比赛)球员为对象开展的研究,为这种趋同现象提供了一例最好的说明。球员与队友分享皮肤细菌,不同的队伍有自己独特的菌群。但在比赛中,两队会在赛道上发生冲撞,所以他们的皮肤微生物会暂时趋同。“接触”孕育了“相同”。在这曲漫长的华尔兹中,不同的人也会撞到彼此。

细菌的传递路径取决于不同的社会接触形式。只有当亲本和后代待在一起,或者不同世代混合在一个大群体中时,传递才会发生。日本椿象会照顾幼虫,并在这个过程中给后代注入合适的细菌。白蚁非常密集地群居在一起,新的工蚁可以从姐妹那里舔舐到合适的微生物。迈克尔·隆巴尔多(Michael Lombardo)认为,这种聚居模式的形成是有原因的。一些动物逐渐以大群体群居,因为它们可以更容易地从左邻右舍那里获取对自己有益的共生微生物。当然,这不是社会模式演变背后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社会性动物可以进行团队猎食,更大的群体可以保障安全,或者更便于它们在野外寻路。隆巴尔多想说的是,微生物的传递可能是动物可以通过群居获得的益处,但这一直以来都遭到了忽视。一谈到传染性微生物,人们首先想到的很可能是病原体。畜群、鸟群和人类的聚居地使疾病更容易传播,但它们也创造了机会,使得有益的微生物共生体找到新宿主。

动物获取彼此微生物的途径多种多样,似乎无法穷尽。但这些传播途径必须满足相同的必要条件:需要把微生物从一代宿主移动到下一代宿主身上。无论是椿象或是考拉,无论是狼蜂或是狒狒,动物都需要使用某种方法,来确保与或多或少相同的伙伴延续这段漫长的华尔兹。有时,这意味着严格地从父母到后代的垂直遗传,保证宿主和后代与同一微生物相连。另一种方式则是更宽松的水平传输,微生物来自同代或共享同一环境的个体;这种方法确保了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同时允许动物更自由地交换共生体或者获取新的共生体。但即使在这种更宽松的路径中,动物仍然会进行一定的挑选。周围的世界充满了潜在的可供选择的合作伙伴,但它们并不会随便找一个当“舞伴”。
很多人家附近的池塘里就住着一种迷人、拥有奇怪魅力的生物,但你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它们。想发现它们很简单:舀起一些浮萍或其他浮水植物,放入一个装有少量水的罐子,然后等着……仔细地观察这些植物,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绿色或棕色斑点,只有几毫米宽,粘在茎的下面或叶片的背面。给它一些时间和一点阳光,这块小斑会慢慢伸展成一根小管,顶端会长出触手;完全伸展开后,它看起来像是一条轻薄的胶状手臂,顶端仿佛张开的手指。
这是一个水螅,是海葵、珊瑚和水母的近亲。它的英文名 hydra 来源于希腊神话,原型是一条居住在沼泽中的可怕九头蛇,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曾经与它战斗。考虑到这种生物的微小尺寸,这个名字让它显得有点“名不副实”,但从某种奇怪的角度看,又很合适它。村民惧怕怪物九头蛇喷出的有毒气息和血液,水螅则通过触手上的细胞分泌毒素,像鱼叉一样射死水蚤和虾。九头蛇每被切断一个头,就会再长出两个头,而水螅也是再生专家。切断肢体?没问题。从里到外翻个个儿?还是能应对自如。
对想要了解动物生长发育过程的生物学家来说,水螅极具吸引力。它很容易收集、培养和繁殖;大多是透明的,一个光学显微镜就能揭示其内部的运作状态。发育生物学家托马斯·博施(Thomas Bosch)于2000年与它相遇,彼时的科学界已经研究了好几个世纪的水螅。列文虎克本人就在他的笔记本上画过这种动物,其他人还研究并说明了它如何从单个细胞成长为成熟个体,以及如何从切断的部位重新生长。博施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被这种动物“俘虏”。“我一直禁止我的学生用‘原始’(primitive)一词描述它,”他说道,“水螅已经以这种精妙的方式在地球上成功地生存了5亿年。”
但博施自己也一直很奇怪,水螅竟然已经存在了这么长时间,特别是考虑到它们简单的结构,这一切就更不可思议了。人体如此复杂,大部分从来没有暴露在外,唯一的接触点是你的肠、肺和皮肤的表层细胞。这些上皮细胞的诸多功能中,最重要的就是阻止微生物穿透并进入身体内部。但是对于水螅而言,并没有“深入身体”这回事。它仅由两层细胞组成,中间是胶状填充物,外部和内部都与水保持接触。它没有分离组织与环境的屏障,没有皮肤或壳,没有角质层或其他覆盖物。对动物来说,水螅的暴露程度可能已经到达极限。“这种动物全身就只是一层黏糊糊的上皮组织,身处一个布满威胁的环境之中。”博施说道。所以,为什么这样的动物不会持续不断地受到感染?它如何保持健康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博施首先要研究清楚,水螅的内部或周围都有什么微生物。他的学生塞巴斯蒂安·弗劳恩(Sebastian Fraune)把它们的身体捣成浆,提取并测序其中所有细菌的 DNA。他分析了两种关系密切的物种,惊奇地发现它们拥有不同的微生物菌群,就仿佛两种来自不同大陆的野生动物。
这一发现令人惊讶,因为这些水螅是实验室的存货,已经在塑料容器中培养了三十多年。它们一直被浸养在同样经过精心调制的水中,用同样的饲料喂食,并保持相同的温度。如果在如此严格的标准条件下关押人类罪犯,记住他们的身份会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对于这种没有大脑的动物来说,每个个体都仍然以某种方式适配到了恰当的微生物菌群,这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实现。博施最初也不相信实验结果,但弗劳恩重复了实验,并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他测序了更多水螅,发现其中每个水螅都有自己独特的微生物组,这与从当地湖泊中收集来的野生个体中观察到的微生物组情况一致。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博施说道,“我一直用传统的眼光看待微生物,认为动物体内的组织一定是对抗‘坏人’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的实验清楚地表明,每个水螅会主动地形塑自己的微生物组。
这是遍及整个动物王国的发展趋势:我们不只与过去恰巧出现的细菌朋友共舞。新的微生物会不断地侵入我们的生活,而每个物种都会从大杂烩般的候选人中选择具体的合作伙伴。例如,人类肠道中主要有四种细菌,而野生环境中大概存在着数百种细菌。即使是水螅这样简单且大部分暴露在外的动物,也有自己的方法:它们会允许一些特定的菌种在体表定植,同时排除别的微生物。我们的身体,无论大小,也无论结构复杂或简单,都能够创造条件,让一些特定的微生物繁荣生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且由于继承的连续性,随着宿主与共生体逐渐适应彼此,这种选择会变得更加严格。我们很挑剔。

因此,每个物种最终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菌群。你可以从小鼠、斑马鱼,甚至黑猩猩或大猩猩的微生物组中分辨出人类的微生物组。即使是共享相同海洋环境的鲸和海豚,虽然游动时不断受到洋流对皮肤的冲刷,但各自也能维持特定的皮肤菌群。前文提到的欧洲狼蜂,其触角中的细菌也经历了严格的选择,如果其中包含错误的菌株,狼蜂就无法分泌把微生物传递给下一代的白色黏液。它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感知触角中来错了伙伴,一经察觉就切断继承链,结束这曲漫长的华尔兹。

微生物也有自己首选的合作伙伴,并且许多微生物也已适应在特定的宿主上定植。斯诺德格拉斯菌属(
Snodgrassella
[1]
)中的一些菌株适应了蜜蜂,其他菌株则适应了大黄蜂,而这些微生物均无法在非原生宿主上定植。类似地,肠道微生物罗伊氏乳杆菌(
Lactobacillus reuteri
)的不同菌株,分别适应于人、小鼠、大鼠、猪和鸡。如果把它们全部放入一只小鼠体内,那么适应啮齿动物的菌株会生长得更旺盛,盖过其他菌株。这类微生物实验予人不少启发,其中,约翰·罗尔斯的一个实验可称得上是最具影响力的。他在实验中交换了实验室的两种常客——小鼠和斑马鱼身上的微生物组。首先,他培育了两种动物的无菌版本,然后从常规培养体上收集微生物,植入对方体内。斑马鱼会接受小鼠的肠道微生物吗?小鼠呢?答案是肯定的。但罗尔斯发现,动物不是被动地接过给它们的东西,而是重塑自己的新菌群,从而更贴近原有微生物的需求。小鼠部分地“小鼠化”了斑马鱼的微生物组,斑马鱼那边亦然。

这并不是说一个特定物种中的每个个体都会有相同的微生物组,其中还存在着很多变体。我们可以这样思考:动物的基因就像剧院的舞台设计师,它们为特定的微生物创造可以表演的舞台。
 我们的环境——从伙伴到伙食,从门板到灰尘——都会影响舞台上的演员。随机事件会慢慢叠加,进而作用于整个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基因相同、住在同一个笼子里的小鼠,其微生物组会略有不同。我们微生物组的组成有些像身高、智力、气质,或患上癌症的风险:这些性状都很复杂,由数百个基因一同决定,甚至更多时候为环境因素所左右。这里最大的区别在于,基因直接决定我们的身高或者大脑的大小,但它们不创造微生物。基因设定条件,而这些条件会对某些微生物有利,从而选择某些物种,摒弃另一些。
我们的环境——从伙伴到伙食,从门板到灰尘——都会影响舞台上的演员。随机事件会慢慢叠加,进而作用于整个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基因相同、住在同一个笼子里的小鼠,其微生物组会略有不同。我们微生物组的组成有些像身高、智力、气质,或患上癌症的风险:这些性状都很复杂,由数百个基因一同决定,甚至更多时候为环境因素所左右。这里最大的区别在于,基因直接决定我们的身高或者大脑的大小,但它们不创造微生物。基因设定条件,而这些条件会对某些微生物有利,从而选择某些物种,摒弃另一些。
《延伸的表现型》( Extended Phenotype )是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代表作之一,他在那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想法,即动物的基因(基因型)不仅仅塑造了它的身体(表现型),也间接地塑造了动物的生境。河狸的基因构建了河狸的身体,而河狸会筑造水坝,因此可以说是这些基因改径了河道。鸟的基因造就了一只鸟,鸟又会筑巢;我的基因塑造了我的眼睛、手和大脑,我写出了这本书。水坝、鸟巢和书,这些都是道金斯所说的“延伸的表现型”。它们是一种生物的基因延伸出其身体之外的产物。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我们的微生物组也是如此。基因塑造了促进特定微生物生长的环境,因此可以说它们也受到动物基因的形塑。虽然微生物在宿主体内,但它们也是一个延伸的表现型,与河狸筑的水坝没什么不同。
但这种比较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不似河狸坝或者本书,微生物本身是鲜活的生命。它们有自己的基因,其中一些对它们自身而言很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是宿主基因组的延伸,反过来,宿主也是微生物基因组的延伸!所以一些科学家认为,从概念上分离它们没有意义。动物挑选微生物,微生物也挑选宿主,二者世世代代都组成伙伴关系,彼此紧密联结,可能把它们视为统一的实体更能说明问题。也许,我们应该把它们想象成整体。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细菌与它们的宿主高度合一,很难分清彼此之间的界限。许多昆虫共生体就是如此,包括蝉体内的霍奇金菌的许多谱系分支。线粒体肯定也包含在内:我们已经知道,这些“细胞电池”曾经是自由生活的细菌,之后被更大的细胞永久地封存。这个过程为内共生(endosymbiosis),20世纪初就已有人提出,但几十年后才为世人接受。这得感谢大胆直言的美国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她把内共生发展成了一个自洽的理论。她在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文中阐述了这个理论,运用了来自细胞生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和生态学等领域的证据。这是一项大胆的学术成果,在1967年最终发表前,大约被退了15次稿。

同行们否定、嘲笑马古利斯,但她一一给出了有力的回击。反叛、对教条的不屑一顾,使她堪称完美的科学反偶像者。“我不认为我的想法是‘有争议的’,”她说,“我认为它们是正确的。”在线粒体和叶绿体方面,她肯定是对的,但其他领域过分地鼓吹该理论,使她受到了毁誉参半的评价:她获得了至高的尊重,也饱受最谨慎的怀疑。一位生物学家告诉我,他听她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了他的名字。太好了,他心想,林恩·马古利斯知道我的名字!接着,只听她补充道:“……是完全错误的。”唷,他想,如果林恩·马古利斯认为我错了,那我一定做对了什么。
内共生贯穿了马古利斯的职业生涯,也影响了她对世界的看法。她为生物之间的联系所吸引。她意识到,每个生物都生活在一个群落中,与其他许多生物相关联。1991年,她创造了一个词来描述这种关系:全功能体(holobiont)
[2]
。该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整个生命单位”。
 它指的是一个有机体的集合,它们于生命中的重要阶段集中在一起生活。狼蜂的“全功能体”是狼蜂自己加上触角中所有的细菌;本人的“全功能体”是我,埃德·扬,再加上我身上的细菌、真菌、病毒,等等。
它指的是一个有机体的集合,它们于生命中的重要阶段集中在一起生活。狼蜂的“全功能体”是狼蜂自己加上触角中所有的细菌;本人的“全功能体”是我,埃德·扬,再加上我身上的细菌、真菌、病毒,等等。
以色列夫妇尤金·罗森伯格(Eugene Rosenberg)和伊拉娜·齐尔伯-罗森伯格(Ilana Zilber-Rosenberg)听到这个词时就被迷住了。他们一直在研究珊瑚,把这些动物视为一个集合体,认为它们的命运取决于细胞中的藻类,以及周围的其他微生物。视它们为统一的集群是有意义的。他们意识到,只有解释清楚整个珊瑚全功能体的运作,才能彻底理解珊瑚礁的健康状况。
罗森伯格把全功能体的概念推广到基因界。演化生物学家已经开始把动物和其他生物体视为它们各自的基因载体(vehicles)。创造最优载体的基因,比如最快的猎豹、最硬的珊瑚或最美丽的天堂鸟,更有可能传递给下一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基因变得更加常见。虽然相应的动物载体也变得常见,但基因才是自然选择的核心,或者用专业术语来说,基因是“选择的单位”。但是我们说的是谁的基因呢?动物不仅依赖于自身的基因,还依赖于微生物的基因,而微生物的基因数量通常是动物自身基因数量的好几倍。同样,微生物也依赖宿主的基因:创建合适的机体,并把相应的性状遗传给自己的后代。对于罗森伯格而言,单独考虑这些 DNA 的集合没有意义。他认为,这些基因也作为单一的实体运作,可以称其为“全基因体”(hologenome),应该被视为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

这意味着什么呢?请记住,经由自然选择的演化取决于三个条件:个体间必须存在差异(variation);差异必须是可遗传的(heritable);各差异必须具有影响其适应性(fitness)——生存和繁殖能力——的潜力。“差异”“遗传”“适应性”,如果满足这三个条件,演化的引擎便会开启,选择出能够连续且更好地适应环境的下一代。动物的基因肯定符合这三个标准。但罗森伯格指出,动物的微生物也是如此。不同的个体可以携带不同的菌群、菌种或菌株,所以存在差异。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动物可以通过许多方法把微生物传给后代,所以,可遗传的条件也满足了。另外我们也将在下文中看到,微生物具有让宿主生存得更好的重要能力,因此,它们也可以影响宿主的适应性。第一个条件满足,第二个满足,第三个也满足,演化引擎启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最能满足生存挑战的全功能体,将把它们的全基因体,即动物加上微生物的基因总和,传递给下一代。动物与微生物以一个整体而演化。这是看待演化的更整体化(holistic)的视角,重新定义了“个体”,并强调了微生物对于动物生命而言的不可分割性。
任何试图重写演化理论基础的尝试,都必然会引起一些麻烦,全基因体也不例外。这个概念可能使温和的共生研究人员彼此攻讦、互相嘲笑。与之相比,本书涉及的其他概念没有能引起更大争议的了。我觉得挺讽刺的,该理论着眼的是“合作”与“团结”,这么多人几乎花了所有时间来思考这两个关键方面,可是全基因体却在他们之中制造了如此深的隔阂。
另外也有许多人因为该声明的大胆而对其抱有好感。它把遭到忽视的微生物提升到了与宿主相同的地位,并在四周绘制了一个巨大的概念圆圈,添加了大量指向圆圈的闪烁箭头,让人们多加注意。它不断强调:微生物很重要,不要忘记它。“每个动物都自成一个长脚的生态系统,”约翰·罗尔斯说道,“我们可以使用全功能体或其他词,但确实需要合适的术语去捕捉这个概念。在我看来,还没有比全基因体更好的术语。”
福瑞斯特·罗威尔则更谨慎。他在马古利斯之后重新引介了“全功能体”一词,并加以推广,但只是用来描述生活在一起的生物。“那只是普通的共生,”他说道,“它会根据外部的环境压力混合、匹配彼此,可以表现出积极的性状,也可以是消极的。”他不是很热衷于全基因体这一概念。他觉得这个词所强调的意味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仿佛宿主和微生物会携手走进更光明的未来。演化并不是这样发生的。我们知道,即使是最和谐的共生,其中也夹杂着冲突与对抗。罗威尔认为,罗森伯格把全基因体作为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可能正好掩盖了其中的冲突。罗森伯格似乎在说,演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成整体的成功生存。但这并不是真实状况。演化也作用于整体中的某些部分,而这些部分也经常出岔子。研究蚜虫及其共生体的演化生物学家南希·莫兰也同意这一观点。“共生体非常重要,我比任何人都更深信这一点,”她说道,“但是,全基因体的概念,却被用来掩盖了很多论证中极为模棱两可的部分。”
全基因体的性质尚不清楚。诸如伴虫菌这样的共生体,住在舌蝇的细胞内,进行垂直遗传,是宿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基因很容易被看作是舌蝇全基因体的一部分。狼蜂拥有自己独特的链霉菌菌株,水螅的菌群都经过精挑细选。在这两个例子中,全基因体的概念也很适用。但不是所有动物都这么挑剔。如牛鹂、红雀等鸣鸟,其中的每个个体都有完全不同的肠道微生物;就哺乳动物而言,每个物种内部个体的微生物组差异,可能远甚于所有不同哺乳动物之间的差异。
 动物基因虽然会发挥作用,但似乎会被环境影响掩盖。既然一个动物的微生物合作伙伴可能处于如此不稳定的状态,这时候再提全基因体这个概念,即把它们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研究,真的有意义吗?那么临时出现在我们体内、仅待片刻的微生物,是否也该全部算入其中?当托马斯·弗里茨的手被树枝刺穿,侵入他手内的 HS 菌株,其基因是否也该算入弗里茨的全基因体?我的全基因体是否应该包括我吃下的三明治中的微生物?
动物基因虽然会发挥作用,但似乎会被环境影响掩盖。既然一个动物的微生物合作伙伴可能处于如此不稳定的状态,这时候再提全基因体这个概念,即把它们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研究,真的有意义吗?那么临时出现在我们体内、仅待片刻的微生物,是否也该全部算入其中?当托马斯·弗里茨的手被树枝刺穿,侵入他手内的 HS 菌株,其基因是否也该算入弗里茨的全基因体?我的全基因体是否应该包括我吃下的三明治中的微生物?
来自范德堡大学的塞思·博登施坦因(Seth Bordenstein)可谓全基因体学说的“首席传道者”,他认为这些反对意见都没有击中关键之处。他强调,全基因体的解释框架并不是说动物体内的每一个微生物都很重要。其中一些可能是随机出现的居民,一些是临时经过的路人,但是这其中应该有一小部分总是非常重要的。他解释道:“可能是这样的情况:95%的微生物是中性的,只有几种关键的微生物稳定地陪伴你一生,以某种程度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3]
前者会被自然选择忽略,后者则会受到青睐。一些微生物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经过你体内的霍乱弧菌,自然选择会把这些有害的细菌从全基因体中清除出去,就如同把有害的突变清除出基因组。这样一来,该学说也能把冲突的因素纳入解释框架。就如一些批评者(以及一些支持者)所言,全基因体的概念不一定只关乎团结和合作,它表示的只是微生物及其基因是整幅图景中的一部分。它们对宿主的影响会左右后者经历自然选择的结果,而这其中的作用方式是我们在考虑动物演化时所不能轻易忽略的。“它还不具备完美的理论框架,但在思考微生物群如何与人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全基因体是我们迄今为止所掌握的最适用于解释这个问题的概念。”博登施坦因说道。不过,他的批评者也许会争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共生”概念已经在发挥这样的作用。

如果还有一件事是每个人都同意的话,那就是利用“隐喻”的时代已经结束,数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以基因为中心的演化图景已经如此成功,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演化生物学家可以通过公式为基因的兴衰建模,计算出某个突变的消耗和收益。他们可以用精确的数字来表达抽象的概念。然而,全基因体学说的支持者无法使用定量的数学方法,这也让他们的论点处于不利位置。博登施坦因表示:“我们现在还处在早期阶段,人们认为这还是一个偏感性的主题,缺乏严谨的计算。”他也承认,这样的指责是合理的,也希望后来人能弥补这一缺陷。
面对批评,罗森伯格不为所动。他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老派的演化生物学家一直都在以“宿主中心主义”的视角来认识微生物的重要性。(“我的朋友却指责我太‘细菌中心’了。”他说道。)他最近刚退休,乐于让其他人在这场论战中接过他的智识武器。他说:“我关闭了我的实验室,开放了我的思维。”但在交接之前,他还必须付出最后一份贡献。
几年前,一篇发表于1989年的旧论文让罗森伯格夫妇陷入了困境。一位名为黛安娜·多德(Diane Dodd)的生物学家在该论文中提出,果蝇的饮食可能会影响其性生活。她分别在淀粉和麦芽糖上饲养了同一种果蝇,经过25代,“淀粉果蝇”更倾向于与其他淀粉果蝇配对,“麦芽糖果蝇”也更偏好自己的同类。这个结果很奇怪,不知为何,通过改变果蝇的饮食结构,多德也改变了它们的性偏好。
罗森伯格立即想到,影响它们的肯定是细菌。动物的饮食影响它们的微生物组,微生物影响宿主的气味,气味影响其性吸引力。这一切都说通了,也很好地契合了全基因体的概念。如果这个结论正确,那么果蝇不仅通过改变自己的基因,也通过改变微生物进行演化——就像抵抗地中海周围环境的珊瑚。他们重复了多德的实验,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只经过2代,果蝇便更容易吸引食源相同的个体。如果昆虫摄入一定剂量的抗生素后失去了体内的微生物,那么它们相应的性偏好也会消失。

这个实验很古怪,但意义深远。如果这两组昆虫忽略彼此的存在,只在各自的社交圈内交配,那么它们最终会分离成不同的物种。这种分离一直存在于自然界之中,推动其产生的因素很多样:可以是物理阻隔,比如山或河流;可以是时间差异,比如动物活跃于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或一年中的不同季节;也可以是防止两种动物杂交的不相容的基因。任何阻止动物交配、杀死或削弱杂交后代的因素,都可以导致所谓的生殖隔离。这是驱使两个物种最终分道扬镳的鸿沟。正如罗森伯格所说,细菌也可以引起生殖隔离。微生物构成了一道阻止两个个体交配的活的屏障,潜在地推动了新物种的诞生。
这个理念并不新奇。早在1927年,美国人伊万·沃林(Ivan Wallin)便形容共生现象为创新引擎(engine of novelty)。他认为,是共生细菌把现有的物种转化成了新物种,而这正是新物种的基本形成途径。林恩·马古利斯于2002年回应了伊万的观点,她认为长久以来,不同生物不断形成,它们之间所创造的新的共生现象〔她称之为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一直都是新物种起源的主要推动力。在她看来,本书提及的各种关系,不仅仅是演化的支柱,更是演化的基础。但她没能证明自己的理论。她列举了许多共生微生物,它们促生了事关演化导向的关键适应,但问题在于,她几乎没有提出直接证据证明是这些共生现象促进了新物种的诞生,更没法证明它们就是这些物种起源背后的主要推动力。

而现在,一些证据正在浮出水面。2001年,塞思·博登施坦因和他的导师杰克·韦伦研究了两种关系密切的寄生蜂,即金小蜂属下的两个种,吉氏金小蜂(
Nasonia giraulti
)和长角丽金小蜂(
Nasonia longicornis
)。它们作为单独的物种才存在了40万年;在未经专业训练的人眼中,它俩看起来一模一样:小小的,黑色的身体,橙色的腿。但它们之间存在生殖隔离。两种金小蜂携带不同的沃尔巴克氏菌株:当它们交配时,这些处在竞争关系中的菌株会产生冲突,杀死大多数杂交后代。当博登施坦因用抗生素除去其中的沃尔巴克氏菌后,杂交后代活了下来。他的研究表明,这两种蜂之间的生殖隔离可以弥合,因为有清楚的证据表明,是微生物分隔了这些新形成的物种。2013年,他在用两种亲缘关系更远的蜂类做实验时,发现了更令人信服的结果。这两种蜂本来也不可能繁殖出可育的后代。而这一次,他发现杂交后代的肠道微生物最终非常不同于它们的父母。他认为,因为与自身的基因组不兼容,所以这种杂合的微生物组最终令这些后代毙命。这正好说明,扭曲的全基因体也会导致死亡。

博登施坦因的这些研究给出了明确的证据,正如沃林和马古利斯所认为的,共生可以推动新物种的起源。但批评者认为,他们可以用更简单的原理解释:不匹配的微生物与杂交种的存亡无关。
 杂交种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让它们极易受到各种细菌的影响。无论提供什么微生物组,它们的结局都是死亡。但是不管哪种才是正确的论断,至少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杂交种的微生物组的确存在问题,而这加剧了两种蜂之间的隔阂。这个现象本身就很有趣。“我们在金小蜂身上看到了这两个故事,我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偶然发现,”博登施坦因说,“那是因为我们恰好问了微生物是否会导致生殖隔离。有多少人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还错过了多少其他物种身上的故事?我不认为我们发现了唯一的两个例子,我们只是撞了瞎运。”
杂交种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让它们极易受到各种细菌的影响。无论提供什么微生物组,它们的结局都是死亡。但是不管哪种才是正确的论断,至少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杂交种的微生物组的确存在问题,而这加剧了两种蜂之间的隔阂。这个现象本身就很有趣。“我们在金小蜂身上看到了这两个故事,我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偶然发现,”博登施坦因说,“那是因为我们恰好问了微生物是否会导致生殖隔离。有多少人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还错过了多少其他物种身上的故事?我不认为我们发现了唯一的两个例子,我们只是撞了瞎运。”
现在看来,“共生创造了新物种”仍是一个可能性很高且令人兴奋的想法,但还是需要证明其正确性。已经发现的少数案例本身就拥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如果你发现了一块金子,那你不用通过证明你占领了整个诺克斯堡(美国联邦黄金储备地)来证明这块金子是真的。同样,不重新定义演化理论也能体会到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微生物的命运可以深深地纠缠在动物的命运之中。
不可否认,微生物有助于构造宿主的身体,它们也参与了我们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免疫到嗅觉,再到行为;它们的存在与否,也可以决定动物是否健康。在我看来,这非同寻常。从一开始被视为寄生虫或游荡在大环境中的幽灵,到人们发现它们长久地存在于动物体内,并创建起了强大甚至必要的联系,再世代相传。无论你使用全基因体、共生还是别的什么词汇,微生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都是事实。现在,是时候看看这些亲密伙伴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了:不仅仅是动物个体的生长或健康,更是整个物种和种群的命运。本书接下来会呈现:动物充分利用微生物伙伴的力量时,能够达成怎样惊人的成就。
[1] Snodgrassella 属名来自20世纪初著名昆虫学家罗伯特·埃文斯·斯诺德格拉斯(Robert Evans Snodgrass),译者依此翻译为中文名。——译者注
[2] 也译作“共生功能体”。——编者注
[3] 例如,露丝·莱表明,基因并不能决定我们的微生物组成,只是强烈地影响了特定种群的存在。我们体内最容易遗传的细菌是最近发现的鲜为人知的物种,克里斯滕森菌( Christensenella ,Goodrich et al,2014)。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大约40%的多样性都源自基因的多样性。这个神秘的物种在儿童期很常见,在体重健康的人中更普遍,并且经常与其他大量的微生物共存并形成网络。它可能是一个关键的物种:一个相对罕见,但能在生态系统中表现得十分强大的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