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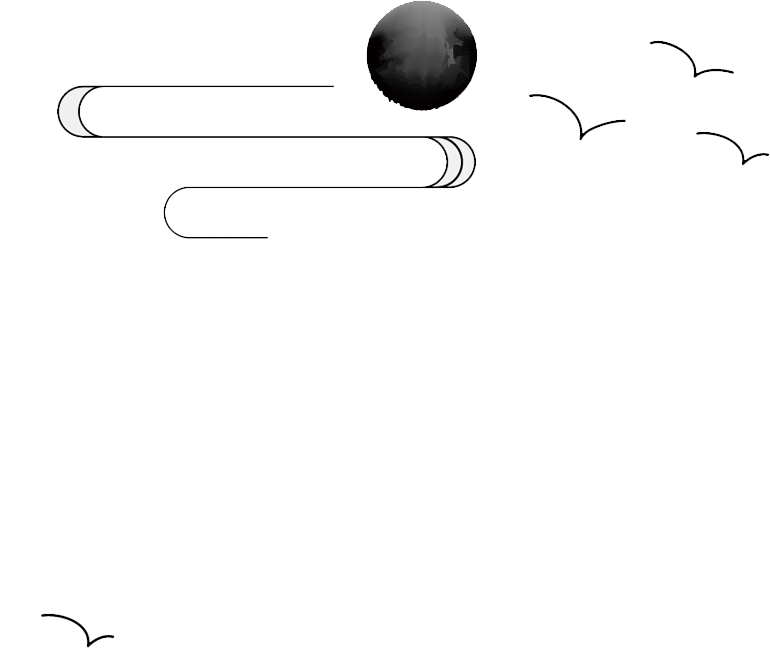

由基什尼奥夫寄莫斯科
1822年9月1日
你可以想见,你那熟悉的龙飞凤舞的笔迹带给我多大的欢乐。将近三年以来我只是从旁人那里得到一点你的似是而非的消息——内中听不到有关欧洲方面的确切的议论。请原谅,如果我要与你来谈谈托尔斯泰
 的话,你的意见对我十分珍贵。你说我的诗
的话,你的意见对我十分珍贵。你说我的诗
 很不得体。我明白,但我的意图并不是要挑起一场好玩的文学战争,我是要趁着这个机会以气势猛烈的侮辱来报答那个人含沙射影的讽刺,我曾与他朋友式地分手,每一次都曾满腔热情地维护他,而他却很随意地就把我引为仇敌,拿牵涉到我的信件供沙霍夫斯科依公爵的阁楼
很不得体。我明白,但我的意图并不是要挑起一场好玩的文学战争,我是要趁着这个机会以气势猛烈的侮辱来报答那个人含沙射影的讽刺,我曾与他朋友式地分手,每一次都曾满腔热情地维护他,而他却很随意地就把我引为仇敌,拿牵涉到我的信件供沙霍夫斯科依公爵的阁楼
 取乐,觉得很好玩。当我被流放时知道了这一切,我认为复仇乃是起码的基督式的品德之一,所以我便在狂怒而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用报刊的污水从远方泼向托尔斯泰。照你说,刑事诉讼超出了诗的范畴,我不敢苟同。法律之剑所不能达者,讽刺之鞭必可达。贺拉斯的讽刺巧妙、轻松而有趣,面对阴险毒辣的诽谤而泰然自若。伏尔泰也有这种感受。你指责我发表骂那个住在莫斯科的人的话是靠着远在基什尼奥夫,在流放的庇护之下。但那时我并不怀疑我会返回的。我的意思是去莫斯科,只有在那里我才能彻底洗雪清楚
取乐,觉得很好玩。当我被流放时知道了这一切,我认为复仇乃是起码的基督式的品德之一,所以我便在狂怒而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用报刊的污水从远方泼向托尔斯泰。照你说,刑事诉讼超出了诗的范畴,我不敢苟同。法律之剑所不能达者,讽刺之鞭必可达。贺拉斯的讽刺巧妙、轻松而有趣,面对阴险毒辣的诽谤而泰然自若。伏尔泰也有这种感受。你指责我发表骂那个住在莫斯科的人的话是靠着远在基什尼奥夫,在流放的庇护之下。但那时我并不怀疑我会返回的。我的意思是去莫斯科,只有在那里我才能彻底洗雪清楚
 。对托尔斯泰伯爵这样公然的进攻并不是出于畏怯。有人说,他给我写了些非常恶毒的东西
。对托尔斯泰伯爵这样公然的进攻并不是出于畏怯。有人说,他给我写了些非常恶毒的东西
 。报刊家们本应该接受那个在他们的报刊上提出严厉批评的人
。报刊家们本应该接受那个在他们的报刊上提出严厉批评的人
 的意见。想想看,我与他们同样见识,这简直气煞我也。然而,该做的我都做了,我再不想跟托尔斯泰打笔墨官司。我会对你有力而明确地证明我是对的,但我尊重你与那个同你极少相同之处的人的关系。
的意见。想想看,我与他们同样见识,这简直气煞我也。然而,该做的我都做了,我再不想跟托尔斯泰打笔墨官司。我会对你有力而明确地证明我是对的,但我尊重你与那个同你极少相同之处的人的关系。
卡切诺夫斯基
 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意见啊!瞧这些彼此相近、大呼小叫的话吧
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意见啊!瞧这些彼此相近、大呼小叫的话吧
 。我很遗憾,你并不十分看重巴拉丁斯基
。我很遗憾,你并不十分看重巴拉丁斯基
 的杰出的天才。他比那些模仿者的模仿者更甚,他是那种真正多愁善感的哀诗的俘虏。《希隆的囚徒》
的杰出的天才。他比那些模仿者的模仿者更甚,他是那种真正多愁善感的哀诗的俘虏。《希隆的囚徒》
 还没读。在《祖国之子》上见到的很优美:
还没读。在《祖国之子》上见到的很优美:
他在柱子上,像春天的花,
高高地悬吊着昂首怒放。
你太让我伤心了——你竟断言你的生气勃勃的诗情已经死去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荣誉而言它已活得够了,而对祖国而言它活得太短了。好在我虽不完全相信你,但却理解你。年岁使人趋向于散文,如果你迷恋于它不是开玩笑的话,那就不能不向欧洲的俄国道贺了。不过,你还期待什么?难道你还醉心于普拉德
 们每月一次的荣耀吗?请坚持不懈地劳动,在专制下的沉默中写吧,来改进我们的那种在你书信中仍在延续的脱离现实的语言吧——这样上帝会赐福的。那些能读善写的人在俄国将很快会有用武之地,那时我愿与你更加亲密;先衷心地拥抱你。
们每月一次的荣耀吗?请坚持不懈地劳动,在专制下的沉默中写吧,来改进我们的那种在你书信中仍在延续的脱离现实的语言吧——这样上帝会赐福的。那些能读善写的人在俄国将很快会有用武之地,那时我愿与你更加亲密;先衷心地拥抱你。
普
寄给你一篇神学的长诗
 ——我成了一个御前诗人了
——我成了一个御前诗人了
 。
。

19世纪俄罗斯贵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