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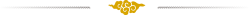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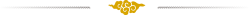
几年前,我曾经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在讨论本雅明(WalterBenjamin, 1892—1940)在“论历史的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这篇文章中的一句话的翻译问题。我查阅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Die Geschichte ist Gegenstand einer Konstruktion, 相应的英文是History is object of construction。有人曾把它翻译成“历史是建构的客体”,另有人认为这译错了,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历史是建构的主体”。实际上,德文的原意很简单,说的只是“历史是一种建构的东西”,Gegenstand指的就是一种东西,并没有所谓“主体”和“客体”的区分。按照本雅明的说法,历史或都是人为地建构出来的东西,没有纯粹客观的、不受任何观念影响的历史。这样的说法后来就成为了后现代史学的一个主题思想,虽或被认为有点矫枉过正,但确实对史学家们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也对今世的史学研究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不但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历史研究很难达到百分之百的精准、客观和科学,就是历史书写、叙事的范式、模式、框架等等,它们也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学术工具,而是通常都连带着某种基本的历史观,它常常可以设定历史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基本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解释。
多年前,我曾经读到过美国芝加哥大学宗教史教授Christian Wedemeyer先生的一篇讨论密乘佛教历史书写的文章,当时读来真的是振聋发聩,印象非常深刻,故以后常常会提到和用到它。这篇文章指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一种历史叙事模式是黑格尔最早提出的所谓“有机的历史发展模式”,即认为任何一部历史就像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anorganic process),它必须经历出生、成长、鼎盛到衰落、灭亡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所以,不管是研究希腊、罗马史,还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城市史、宗教史等等,大家都必须遵循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于是,开国君主无一例外都是英明伟大、雄才大略的,而末代皇帝必然是荒淫无度、腐朽堕落的,所以这个国家才会由兴盛走向灭亡,完成它从出生到死亡的一个完整的自然过程。在这种有机历史发展观的影响下,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目的无非就是要从我们手中所掌握的文献资料中找出这种具体而又有规律性的东西,以帮助我们来描述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所经历的生、老、病、死这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譬如说,我们讲述印度佛教的历史,那么释迦牟尼出生是佛教的诞生,小乘佛教是成长,大乘佛教是鼎盛,到了密乘佛教则一定是腐朽衰落,要走向灭亡了。可是,密乘佛教最晚至少也应该在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它的起源实际上远比人们所设想的要早得多。虽然它常常被人与佛教的腐朽、堕落挂上钩,但它实际上是一种十分精致、复杂的宗教信仰和修习形式,而且即使到了今天它依然方兴未艾,丝毫没有要消亡的迹象。显然,这个有机发展的历史叙事模式在佛教史的构建和叙事中是不合适和无法令人信服的。但很不幸的是,长期以来研究佛教历史的学者们很少有人能够完全摆脱这种历史叙事模式的约束,所以即使是最好的语文学家也都难免不自觉地受到了这种叙事模式的影响和限制,而有意无意地要把密乘佛教的仪轨,如男女双修等,设想和规定为佛教进入腐朽、堕落之末路的象征。
Wedemeyer先生这篇文章中批评了很多当今很有名气的佛教语文学家,包括我在京都大学工作时的合作导师、杰出的印藏佛学语文学家御牧克己先生。Wedemeyer先生想借此说明的是,即使是像御牧先生这么优秀的语文学家,因为受到了这种有机历史观叙事模式的影响,严重影响了他的判断力,以致错误地判定了某部密教经典出现的年代。因为密教必须要到佛教衰落、灭亡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它不可能出现得很早,如果这部经典出现早了就和这种既定的历史叙事不相吻合了。 [1] 我想在其他任何历史研究领域里,我们也都会见到这类历史研究因受叙事模式的影响而出现种种类似的错误和问题的现象。
这种有机发展的历史叙事模式对于当代历史书写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在蒙元史研究中找到一个非常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它就是迄今为止中国古代历史书写传统中对藏传佛教于元朝蒙古宫廷传播历史的叙述。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西番僧于元朝宫廷中所传的“秘密大喜乐禅定”“演揲儿法”和“十六天魔舞”等藏传密教的修习仪轨,当成是导致元朝急速败亡的罪魁祸首,认为正是西番僧所传的这些实际上不过就是淫戏、房中术的藏传密法,彻底蛊惑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及其亲信大臣们的心,导致了元末宫廷的极端腐朽、堕落,最终使得蒙古人很快败亡漠北,失去了江山。显然,这样的历史叙事完全符合有机发展史观的叙事套路,与所有其他皇朝的末代君主一样,元顺帝的宫廷必然应该是腐朽、堕落的,而那些听起来很有异域情调的藏传密教修法不过是为历朝末代宫廷腐朽叙事提供了更让人觉得新奇、刺激的新作料。而把藏传密教修法巫化和色情化为淫戏、房中术,又完全符合这种有机发展史观下建构起来的佛教历史叙事,在这种叙事结构中,密教必然是腐朽、堕落的,它的出现即预示着佛教走向衰亡的开始。可是,我们近年对这段历史所作的文本研究却明确地告诉我们,上述“秘密大喜乐禅定”“演揲儿法”和“十六天魔舞”等密教修法,根本不是在元朝末年才开始出现的,它们早在忽必烈汗建立元朝以前就已经由八思巴帝师亲传而在蒙古人中间传播开了,它们甚至早在蒙古帝国兴起以前就曾经在西夏王国内传播过,所以,这些密法的传播不应该是导致元朝骤亡的直接原因。而且,我们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还告诉我们,上述这些密教修法事实上大部分不涉及密教双修或者多修的内容,即是说,它们中的大部分与密教的双修法并无直接的关联,故不能将它们说成是腐朽、堕落的代名词,并把它们视为佛教或者元朝走向衰亡的必然的原因。
显然,当我们表述和再现蒙元史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会受到各种历史叙事模式/范式的影响和限制,而当我们面对来自日本和西方的“大元史”历史叙事的冲击和影响时,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选择怎样的一种历史叙事框架来叙述蒙元王朝的历史,或者说我们应该从哪个视角、哪个立场出发来叙述和理解这个由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的历史以及它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迄今为止,更多人主张的是从中国王朝更迭史的视角来叙述蒙元史,也有人主张要从蒙古族历史这个视角来叙述蒙元史,而眼下则有很多人更倾向于从世界史、全球史的视角,或者从欧亚史、帝国史的视角来叙述蒙元史,他们各有各的一套说法,使得蒙元史的研究和再现变得十分丰富多彩。但是,这些角度不同的叙事和说法每每各有侧重、各有利弊,以致相互间形成了很多的意见分歧、冲突和争论,甚至牵涉到了当今蒙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牵涉到中国古代历史的定位和当代中国的边疆归属等等敏感和难解的问题。

图1-6 “十六天魔舞”(实为吉祥胜乐坛城修法仪轨的一部分)唐卡
于蒙元史研究领域,我自己长期从事的是元代西藏历史的研究,对蒙元与西藏关系史的研究有比较多的了解,也因此而深刻地体会到如何来叙述蒙元史,如何给蒙元史一个合适的历史定位,对于研究和解释元代西藏历史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对于蒙元时期西藏历史的研究,中外学界都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如意大利著名藏学家Luciano Petech先生对这段历史的精湛研究,理清了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其成果绝对堪称世界一流。
[2]
中国学者中,也有像我的业师陈得芝先生这样世界一流的蒙元史大家,对这段历史从对蒙元制度史的整体把握出发做过一系列非常出色的研究。
 他们的研究明确表明,蒙元王朝有效地统治了西藏百有余年,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并非从此所有人都会服从上述中外学术权威们所得出的这一结论,能够自然地接受从元朝开始西藏成为中国领土之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说法。相反,依然还常听到有人会说元史、蒙古史,跟“中国史”、“中国”有什么关系呀?二者难道就是一回事吗?因为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曾经统治了西藏,今天的西藏就应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吗?这些都是研究西藏历史的人在海外经常会被人问到的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与它们相类似的问题也经常出现于最近对清史的讨论中,清代对西藏、蒙古和新疆等所谓内亚地区的统治也是一个学界所公认的历史事实,可是“清帝国史”、“大清帝国”与“中国史”、“中国”又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清等同于中国吗?这大概也是有关“新清史”的讨论和争议中,最让人纠结和难以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说到底,掩藏在这些争议背后的更关键和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义“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如何来界定历史上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中国,如何来认识今日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形成历史的问题。目前,中国学界对“何谓/何为中国?”这样的问题的讨论层出不穷,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大元史”或者“新清史”等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由非汉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的历史所建构的一套新的历史叙事的回应和批评。
他们的研究明确表明,蒙元王朝有效地统治了西藏百有余年,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并非从此所有人都会服从上述中外学术权威们所得出的这一结论,能够自然地接受从元朝开始西藏成为中国领土之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说法。相反,依然还常听到有人会说元史、蒙古史,跟“中国史”、“中国”有什么关系呀?二者难道就是一回事吗?因为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曾经统治了西藏,今天的西藏就应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吗?这些都是研究西藏历史的人在海外经常会被人问到的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与它们相类似的问题也经常出现于最近对清史的讨论中,清代对西藏、蒙古和新疆等所谓内亚地区的统治也是一个学界所公认的历史事实,可是“清帝国史”、“大清帝国”与“中国史”、“中国”又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清等同于中国吗?这大概也是有关“新清史”的讨论和争议中,最让人纠结和难以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说到底,掩藏在这些争议背后的更关键和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义“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如何来界定历史上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中国,如何来认识今日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中国的形成历史的问题。目前,中国学界对“何谓/何为中国?”这样的问题的讨论层出不穷,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大元史”或者“新清史”等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由非汉民族所建立的“征服王朝”的历史所建构的一套新的历史叙事的回应和批评。
不难发现,杉山先生率先提出的对蒙元史的新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把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从传统的“中国古代王朝历史”的叙事框架中分离出来,转而把它放入全球史、欧亚史的叙事框架中来叙述,形成一种可称为“大元史”的叙事模式,这和近年来于中国学界引起了广泛讨论的“新清史”的观念大同小异,异曲同工。“新清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把清朝的历史从传统的基于汉族中心主义史观的中国古代王朝史的建构中解放出来,然后从同时包括了一个“中国的帝国(汉人的帝国)”和一个“内亚的帝国”的跨越欧亚的大帝国的视角来叙述它的历史,由此而超越了中国古代历史的传统叙事方式。所以,同样从不同的视角、层面来看待蒙元王朝的历史,或者换一种方式来重新讲述蒙元史、建立中国历史学家们自己的关于蒙元史的历史叙事,是一个因海外“大元史”和“新清史”的出现而给中国的蒙元史研究者带来的必须认真对待的学术挑战。毫无疑问,中国的蒙元史学家们现在或许也应该从研究具体史实、具体问题的学术路径中暂时游走出来,一起来讨论一下应该如何来回应“大元史”和“新清史”的挑战、如何来重新讲述蒙元史、如何来重新建构我们自己对蒙元王朝的历史叙事。
 但是,历史研究虽然需要、也难以摆脱今人的视角和关心,但它绝不能完全被今人的立场和观念所左右和支配,我们依然必须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放回到它们原来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语境中去观察、分析和解释,而不能严格按照当下人们之政治、思想和利益的趋向和关注,把它们统统写成一部当代史,否则,历史学就必将失去其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存在的基础和必要。
但是,历史研究虽然需要、也难以摆脱今人的视角和关心,但它绝不能完全被今人的立场和观念所左右和支配,我们依然必须把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放回到它们原来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语境中去观察、分析和解释,而不能严格按照当下人们之政治、思想和利益的趋向和关注,把它们统统写成一部当代史,否则,历史学就必将失去其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存在的基础和必要。
[1] 参见Christian K. Wedemeyer, “Tropes, Typologies, and Turnarounds:A Brief Genealogy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Tantric Buddhism”, History of Religions , vol. 40, no. 3, 2001, pp. 223—259;此文的汉译文《修辞、分类学与转向:简论佛教密宗历史编纂源流》,见沈卫荣主编:《何谓密教?关于密教的定义、修习、符号和历史的诠释与争论》,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
[2] Luciano Petech, 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 The Yüan-Sa-skya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 , Serie Orientale Roma, Roma: Instituto Italiano per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