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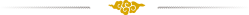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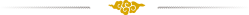
上述杉山先生于学术上的这种华丽转身,除了让中国的同行们觉得惊讶外,同样也应该给人以启发,或许我们今天也应该把眼光放宽一些,或者也像杉山先生一样变换一下视角来重新审视和思考蒙元史,来考虑一下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应当如何来讲述蒙元史,探讨一下蒙元史对于我们当今这个全球化了的世界的现实意义。
历史研究的进步与历史叙事的建构并不是同一回事,二者常常不是同步的。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或者话语的出现多半与一个时代、社会的特殊的兴趣和关注相关,而并不见得一定要依靠优秀的历史学家的努力,也不见得一定是建立在优秀历史学家们所作出的扎实可靠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在蒙元历史研究和蒙元历史叙事、话语建构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条直接的通道。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的蒙元史家或已经把蒙元历史研究得很好,很专深了,可是,他们好像没有像别人一样尝试去把蒙元史这个故事讲得更好,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努力去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为一种可以让非专业读者也能听得进去的历史叙事。与此同时,别人却正在讲述这个故事,而且已经建立起了有关这个故事的一套有影响力的叙事和话语。尽管别人讲的这个故事不见得一定正确,它与我们的研究成果也不一定相符合,但是,他们说的故事讲得多了,流传广了,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权威意义,并演变成为一套固定的历史叙事,随之而产生巨大的话语霸权。这样,我们自己不但失去了有关蒙元史的“话语权”,而且还会时刻受到这套既定叙事和话语的强烈的压迫和限制。所以,任何蒙元史学者在认真研究蒙元历史的同时,也应该对目前全球化、或者全球史背景下出现的种种有关蒙元历史的叙事予以更多的关注,也有必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讲述这个故事,参与到全世界层面的有关蒙元史的叙事和话语的建构过程之中,从而建立起我们自己对蒙元史的历史叙事和话语。
如前所述,中国老一代的蒙元史学者都相信“史学就是史料学”,觉得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兰克(Leopold vonRanke, 1795—1886)所说的,“就像它实际发生的那样”(Wie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来重构历史。我们曾经充分相信,只要我们把史料都找齐了、穷尽了,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弄清楚了,那么,这个我们所寻求的“历史的真实”就自然而然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尽可能地去寻找别人还没有利用过的新的文献资料,然后对这些资料进行仔细的整理和研究,从而对已经十分成熟了的蒙元史研究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当我初学蒙元史的时候,我就知道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对蒙元史研究起了多大的推动作用,明白是大量域外的、非汉语文献资料的发现给元史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但是,于今天看来,这个层次的历史研究固然十分重要,应该说它依然还是蒙元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工作,但它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内容。史料总有一天会被穷尽的,但历史研究是不会停止的,对历史事实的重构不但本身永远难以达到十分理想和完美的境界,而且它也不足以完全满足一个历史学家所有的好奇心,并圆满地实现其从事历史研究这个职业的价值和意义。怎样从对历史事实的探求当中同时求得历史对于我们眼下所处的这个时代和文明的意义?怎样构建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表述和再现,并通过这种叙述建立起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和解释,这或许应该是历史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步骤。至少具备了这两个步骤,我们的历史研究或方可达到司马迁所追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
毋庸讳言,能够从前述历史研究的第一个步骤跳跃到第二个步骤,或者说能够同时兼擅这两个步骤的历史学家并不多见,而杉山正明教授则是蒙元史研究领域内一个非常少有和典型的例子。他同时重视蒙元史研究的两个不同层面,从学术生涯前期对多种语文能力之训练的执着和成就,到后来对建构蒙元历史叙事所作出的创造性的发明,可以说他在语文学和理论两个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并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这对于一位蒙元史学家来说,无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我于京都大学访学三年期间(2002—2005),我和杉山先生曾经非常熟悉,常有来往。记得有一次晚上和他一起酒喝得多了一点,几近半夜时被他拉到家里去喝茶。我很惊讶地发现他家里的藏书和他办公室的藏书完全不一样,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世界。他在京都大学的办公室以前为羽田亨先生所有,据说京大著名的学术前辈如佐藤长先生等即使在晚年到了杉山先生这间办公室门口依然会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而它到了杉山先生这里则成了日本关于蒙元史或者说欧亚史研究的最好的图书馆之一,因为它收藏了波斯文《史集》的所有版本。有几次,我在京大图书馆没找到的书,也在他的办公室全找到了,可见其名不虚传。可是,在他家里我看到他也有一间很大的书房,其中堆满的却全是“岩波文库”一类的普及性读物,以及各种各样的理论类书籍。看起来,杉山先生在学校和在家里从事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研究,他同时驰骋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世界之中,而且皆得心应手、收放自如。

图1-5 杉山正明(摄于1998年,网络照片)
我曾经很冒昧地问杉山先生为什么现在他不专心做《史集》的研究了,他颇带自嘲和无奈的解释是,他目前已经和出版商签下了很多的出书合同,故暂时没法停下来做别的,他还必须继续写这一类面向大众读者的学术作品。但我猜想,杉山先生在学术取向上的这种巨大变化,很可能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即他对我们以前信奉的学术理念——研究历史就是要把历史像它过去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呈现出来——产生了动摇。据说杉山先生给学生上课时,常常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像伯希和先生这样的一众超级学术权威,尖锐地指出这些权威们所犯的各种各样的错误。他大概觉得语文学的、实证性的历史研究最终还是很难达到十分精确和完美的理想境界的。即使是像伯希和这样不世出的伟大的语文学家、历史学家也难免会犯各种各样的低级的错误,所以,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是很难得到完全的保证的。事实上,语文学研究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前赴后继、不断进步的过程,后代学者依靠新的学术手段、凭借新发现的资料,可以不断地对其前代学者的研究和成果进行持续的更新和改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前一代人的学术正是后一代人学术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但是,历史研究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种再现和构建,它必须要建立在一种叙述和解释的框架和范式之上,每一段历史必须借助这些框架和范式才能被讲述、重现出来。所以,哪怕你能做最好的考据,当你要把它讲述出来的时候,依然还会受到某一种观念或者历史叙事模式的影响,更不用说它也可能会受到政治、权力和利益等等世俗因素的严重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后现代史学对杉山先生或许曾经有过一定的影响,促使他实践了这种学术研究方向上的大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