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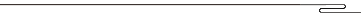
在日本建设律令制国家的过程中,不仅法律政治制度日趋完备,文化也欣欣向荣,形成了在日本文化史上与飞鸟文化时期构成双璧、亦以佛教文化为轴心的文化繁荣时期——白凤文化时期。
白凤文化因白雉年号(650—654年)而得名,但狭义的白凤文化时期以天武朝为中心,即672年至686年前后。广义的白凤文化时期则指自大化改新至迁都平城京,即645年至708年。白凤文化前期受大陆六朝文化影响,后期受唐朝文化影响。在这一时期,各朝天皇实施佛教国教化,建造了大官大寺、药师寺等多所官寺,各寺多次举行法会讲解护国经典。同时,各地贵族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氏寺。《扶桑略记》记载,据持统六年(692年)调查,当时日本全国共建有寺院545所。近年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有白凤样式古瓦的寺院遗迹,其数和《扶桑略记》记载数大致相符,说明其无甚夸张。以《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的传说为线索,可知佛教向全国各地急速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救援百济的地方豪族直接见闻了百济佛教,或从百济偕僧尼请佛像回国,不管采取哪一说,均说明系受百济佛教影响。
遗留下来的白凤文化的代表性佛教建筑有药师寺东塔、山田寺回廊等,雕刻有药师寺金堂药师三尊像等,绘画有法隆寺金堂壁画、高松塚古坟壁画等。另外还有一些王公贵族如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创作的汉诗作品,以及额田王、柿本人麻吕创作的长短歌、和歌等,其作品被收入奈良时代编撰的《怀风藻》和《万叶集》。白凤期的佛教因与朝廷关系密切而映照出日本律令制国家建设时期的时代川流。
大化元年(645年),登基甫定,孝德天皇即颁发《正教崇启》之诏,阐述了自佛教传入至苏我稻目、苏我马子显扬佛教、恭敬僧尼的事迹,以及朝廷设置十师教导众僧、捐助氏寺任命寺司寺主的宗旨,最后以“朕更复思崇正教光启大猷”结尾。
 该诏书不仅是继推古二年(594年)的《三宝隆兴》之诏颁布的第二个兴隆佛教的诏书,而且其颁布先于国家政治制度改革。朝廷“兴隆三宝”之决意,昭然若揭。
该诏书不仅是继推古二年(594年)的《三宝隆兴》之诏颁布的第二个兴隆佛教的诏书,而且其颁布先于国家政治制度改革。朝廷“兴隆三宝”之决意,昭然若揭。
之后,佛教因素不断渗入朝廷,成为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例如,迁都难波的孝德天皇首先在宫廷礼仪中吸收了佛教因素,规定在一些重大法事中着大化三年制定的7色13阶冠位。特别在白雉二年(651年)年末,不仅白天在味经宫邀集2000多僧尼一起诵经,而且夜晚在庭内点燃2700余盏灯,令其诵读《安宅神咒经》和《侧土经》;为征讨虾夷和救援百济等内忧外患问题所困的齐明六年(660年)5月,官僚奉敕造上百高座和上百袈裟,并举行仁王般若会,诵读祈祷驱除灾害护佑国土的《仁王般若经》。之后,如此场面在宫廷一再重现。
佛教虽进入宫廷,但在天武朝之前还没有超越宫廷范围。作为佛教跨出宫廷向更广阔的领域伸展的标志,是根据天皇的意愿建造大寺。虽则佛教传来后,历代天皇都致意兴隆佛法,尤其推古朝后,朝廷下诏兴隆三宝,佛教日益兴隆,创建了法兴寺、法隆学问寺、四天王寺等大寺,但其中法兴寺是由苏我氏建立的,后来改为元兴寺,或称为飞鸟大寺,由朝廷任命寺司,几乎成了朝廷的祈祷寺。真正由天皇发愿建造的大寺,始于舒明朝。舒明十一年(639年),天皇将圣德太子的熊凝寺移到百济河边,称为百济大寺,但据称因招惹了大寺附近的子部社引起,使大寺堂塔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天武二年(673年)朝廷任命了负责复建该寺的造寺司,并将该寺从百济川畔移至高市郡夜部村,该寺因此获名高市大寺。天武六年(677年)改名大官大寺,意为培养僧尼的“国家的寺院”。同时因其“大”字原非“小”的反义,而是附于天皇的事物表达尊敬之意,故又意为“天皇的寺院”。
之后建造的是川原寺(弘福寺)。川原寺系日本最古老的抄经寺院。据《日本书纪》天武二年(674年)二月条记载,是年,天武天皇敕令有学问的僧侣聚集该寺,抄写数千卷《大藏经》。后1960年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文献记载的川原寺遗址下层系川原宫,因而推断川原寺建于天智天皇为其母齐明天皇追善举行殡葬仪式的飞鸟川原宫。2005年2月20日,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发表调查报告,称在飞鸟时代的国家寺院的代表、奈良县明日香村的川原寺迹(国史迹),找到了7世纪末的六座巨大基石,由采自当地的花岗岩所制成,最大的基石为1.4米×1.6米,以「一」形间隔2.1米排列,从而证实了上述推断。值得一提的是,佛寺伽蓝配置主要是塔与佛殿位置的变化,这种是了解佛教传播和崇佛思想演变的主要根据。川原寺伽蓝配置呈“塔与佛殿东西并立”,具有当时中国大陆佛寺伽蓝的明显特征,因而再次印证了日本佛教的发展演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佛教发展演变的投影。
与川原寺具有同样伽蓝配置的崇福寺,因1941年发表的第10号《滋贺县史籍调查报告》即考古发掘公布的结果,同《扶桑略记》天智六年二月三日条、翌年正月十七日条所载情况基本吻合,亦当为天智天皇所建。
与在飞鸟京的川原寺形成对偶、位于模仿中国都城规划建造的“新益之京”藤原京的药师寺,亦是白凤文化的时代杰作。据收入《宁乐遗文》的“药师寺东塔擦铭”记载,天武八年(680年)皇后病笃,为了祈愿皇后(以后的持统天皇)病体早愈,天武天皇于是年11月发愿造1寺供奉药师如来,始建药师寺。然未等竣工,天武即驾鹤西行。皇后登基成为持统天皇后,即秉承夫君遗志,创建堂宇,并于持统二年(688年)在寺内举行无遮大会(佛教举行的一种广结善缘,不分贵贱、僧俗、智愚、善恶都一律平等对待的大斋会)。文武二年(698年)10月,寺宇建成,诏众僧入住。如果说大官大寺实质上是天武天皇的“大寺”,则药师寺堪称持统天皇的“大寺”。大官大寺、药师寺、法兴寺、川原寺,并称藤原京“四大寺”。此外,各地贵族亦竞相造寺,以致天武九年(681年)4月朝廷不得不颁布敕令,确立分层管理的“官寺制度”,并另设立“造寺司”。
在汲取中国佛教的营养方面,遣唐留学僧的作用当不可忽略。以白雉四年(653年)入唐、齐明天皇七年(661年)回国的道昭为例,据《续日本纪》记载:“文武天皇四年三月己未,道昭和尚物化。天皇甚悼惜之。”
 与寺院建设并立的,是佛事法会不仅在宫廷举行,而且在都城和地方诸寺举行。如天武五年(677年)十一月,朝廷遣使各国要求诵读《金光明经》和《仁王经》;天武九年(681年)五月,敕令宫中和诸寺诵读《金光明经》,等等。《金光明经》的诵读和大忌祭、风神祭、新尝祭等祭祀一起,作为国家祭祀而恒例化。
与寺院建设并立的,是佛事法会不仅在宫廷举行,而且在都城和地方诸寺举行。如天武五年(677年)十一月,朝廷遣使各国要求诵读《金光明经》和《仁王经》;天武九年(681年)五月,敕令宫中和诸寺诵读《金光明经》,等等。《金光明经》的诵读和大忌祭、风神祭、新尝祭等祭祀一起,作为国家祭祀而恒例化。
“大寺制度”和“护国法会”作为新生的律令制国家宗教意识形态的支柱,占有“国家佛教”的地位。同时,大化的“十师”不久即被废除,天智朝末年“僧正”、“僧都”的名称得以复活,天武十二年(684年)朝廷任命了僧正、僧都、律师,敕令“统领僧尼”。
白凤文化代表性建筑,当首推药师寺东塔。虽药师寺内有东西两塔,但唯东塔在日本建筑史和美术史上均占有突出地位,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东塔实为三层,但因每层都附有“裳层”(飞檐),因此看似六层,塔顶耸立的相轮有天女起舞的透雕水烟,给人以明快的感觉,和擦柱的铭文一起称誉于世。
雕塑领域的代表性作品,明确标识年代的有大阪野中寺的弥勒像(黄铜造半跏思维像),在该像铭文上,不仅明确记有天智天皇五年(公元666年),而且记有其缘起:栢寺的智识等118人为了使中宫天皇的病体早日康复发愿而建。此像衣襟边缘雕着的连珠花纹图案,这种图案原为隋代由西方传到中国,日本佛像自始也出现这种图案,再次无声地叙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列岛的影响。雕塑领域另一代表性作品是记有□戌年(686年或698年)的长谷寺“《法华经》说相图”。顾名思义,该图描绘了宣讲《法华经》的情景。该寺铜版铭文还记载了寺内三重塔之缘起:依天武天皇敕愿,道明上人率众80余人,为在飞鸟净御原大宫内日理万机治天下的天皇建千佛多宝塔(三重塔)。另外,壬辰年(692年)的岛根县鳄渊寺的金铜立像观音菩萨像,亦是该时期雕塑的逸品。据铭文记载,系由出云国的若倭部臣德太理为其父母所建。之后,显示受唐朝初年佛教文化影响的作品开始出现,如药师寺东院堂的圣观音立像。该立像镀金铜,等身大,贴身衣纹的手法和清秀圣洁的表情,一洗前代生硬的皱纹和古拙的面貌。然而,此作虽然精妙绝伦,但作为雕刻黄金时代即将来临的真正路标,则是药师寺金堂的药师三尊像。这三尊像同样镀金铜,等身大,其中药师如来坐像端庄威严,分侍左右的日、月光菩萨立像则表情悠然,姿态轻盈。三尊像目前安置于1972年甫复原完工的金堂内,不仅是药师寺的镇宝,也是日本美术史屈指可数的国宝。三位尊师守在白凤美术的关口,既保住初唐雕刻的洗练,又透露着盛唐样式的圆熟,作为理想完美的典型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可能因为其精妙绝伦,鬼斧神工,又不见确切的历史记载,以致和东塔何时建造一样,其创作年代目前尚无定论:一说是藤原京药师寺本尊的迁移,即随药师寺迁建而移座;一说是药师寺平城京的新铸,即药师寺迁建之后重新铸造。前者以白凤谕者坚持的697年开眼供养说为据;后者则因为奈良谕者不相信前代会有如此精美的佳作。
绘画方面,无疑数法隆寺金堂壁画最美轮美奂:在法隆寺金堂大壁四面,绘有四个天界景象或曰四方净土的菩萨群像:北面墙壁上是弥勒佛和药师佛,东面墙壁上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佛,西面墙壁上是阿弥陀佛。四个天界中央的主佛法座,绘有被俗称“四大天王”的护法天神和众菩萨围绕。上面的宝盖两边各有飞天,下面有—张祭桌,两头狮子。八角壁面上的八尊菩萨像两两相对,或坐或立。整个墙壁上部空白处是隐士们在山中修行。画面大小不一,但布局对称整齐,手法多样,风格独异。整个壁画采用线描与晕染法画出,立体感和真实感很强,研究者认为与印度阿旅陀石窟的壁画相似,可见其创作手法亦源自印度经中国传至日本。1949年1月26日拂晓,法隆寺金堂失火,这一烧使金堂彩色壁画严重受损。然而,俗界事物祸福相倚,佛界亦然。这场火虽然使旷世奇宝原形不再,但却逼出了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案》,尽管所付代价过于高昂,但所幸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隆寺大修进度缓慢,解体部分和寺藏宝物都疏散各处,因此躲过了灭顶之灾。

在日本文化不断以新的姿态呈现于世时,新陈代谢也就势所必然。4世纪以来历经300年风霜雨雪、曾为日本古代社会注入极大能量的前方后圆古坟的营造者,在白凤文化时期开始印证“异己”的哲学意义:自己创造的古坟,最终埋葬自己。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东传,前方后圆古坟的地位逐渐被以中国帝王陵为模板的方陵取代。
据考古发掘,畿内目前最终末的大型前方后圆古坟,是大和的见濑丸山古坟。该古坟长轴为315米,后圆有直径为26米的巨大横穴式石室构成,放有家形石棺两个。这种构造的古坟盛行于6世纪后半叶至7世纪初,被认为是苏我马子的墓的飞鸟石舞台古坟是这种古坟的代表,但见濑丸山古坟更出其右。虽目前尚无法断定被葬者身份,但古坟很可能是钦明陵。
 与之相比,用明陵、推古陵均是边长为70米的方陵。据《日本书纪》九月条记载,用明天皇于推古元年(593年)被改葬于现在的矶长陵。也就是说,大王陵改为方陵,和推古朝画时代的政治变革是相辅相成的;是和以小帝国面对隋帝国、最终创始天皇号的历史背景相一致的;也是大王陵殊别于地方豪族陵墓的显著标志。虽然在关东地区北部和东部,至7世纪初前方后圆古坟依然放出光芒,如高崎市八幡观音塚古坟、绵冠观音山古坟、木更津市金铃塚古坟等,但那无疑已如夕阳残照。至7世纪末,这种古坟在日本东部也踏上归途。
与之相比,用明陵、推古陵均是边长为70米的方陵。据《日本书纪》九月条记载,用明天皇于推古元年(593年)被改葬于现在的矶长陵。也就是说,大王陵改为方陵,和推古朝画时代的政治变革是相辅相成的;是和以小帝国面对隋帝国、最终创始天皇号的历史背景相一致的;也是大王陵殊别于地方豪族陵墓的显著标志。虽然在关东地区北部和东部,至7世纪初前方后圆古坟依然放出光芒,如高崎市八幡观音塚古坟、绵冠观音山古坟、木更津市金铃塚古坟等,但那无疑已如夕阳残照。至7世纪末,这种古坟在日本东部也踏上归途。
按照哲学原理,内容当比形式更加重要。在古坟外形发生变化的同时,其内容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正当美术史家担忧法隆寺壁画遭劫使飞鸟白凤期的壁画再也无处寻觅时,同年,即1972年3月21日,考古学家惊喜地发现了高松塚古坟壁画。高松塚古坟本身是横穴式小圆坟,位于奈良县明日香村。壁画绘于石室三面墙上,有四神像,日、月、云纹,以及青龙、白虎、男女人物,天井中央有星宿图。此外,还出土有海兽葡萄镜。虽然和法隆寺金堂壁画相比,高松塚古坟壁画只能算一组小品,但它以高度的写实和绚丽的色彩,弥补了法隆寺金堂壁画烧损的遗憾,更弥补了日本绘画史的一段空白。虽然壁画剥落之处甚多,可是残存的西壁女子像仍最受瞩目,被认为价值不可估量。从技法判断,高松塚壁画精确的描法,动感的层次显然受中国唐代文化的影响,因此其创作年代被推定为7世纪末、8世纪初,即白凤文化时代。
虽然白凤文化时期上述成就的价值不可估量,但是更不可估量的,无疑是“日文”自始真正开始形成。日文的形成,使日本真正拥有了自己的“语文”;使日本文化获得了不可或缺的载体;使日本文化在由历史积淀构成纵轴和各民族文化构成横轴的世界文化的坐标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
在远古时代,“日本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早在江户时代,已有学者通过日语和周边民族语言的比较,调查了解日语语系,探究日语的源流。例如,新井白石和藤井贞干就曾指出,日本语和朝鲜语相类似。明治以后,语言比较进一步展开,并形成了4种较有说服力的观点:1.日语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特别是属于阿尔泰语。2.日语和同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朝鲜语关系密切。3.日语和南方语系关系密切。4.日语是从阿伊努语分离出来,即源于阿伊努的语言。
上述第4种论说,即认为日语和阿伊努语存在亲缘关系的论说的主要倡导者,是被称为“阿伊努之父”的J.巴切拉。但是阿伊努语研究大家金田一京助和知里真志保均指出,上述两种语言虽然文法方面存在相似点,但是也存在很多相异点,并且不存在数词和其他基本单词的对应性。因此上述第4种论说现已被排除,而第1种和第2种论说则可以归并为“乌拉尔·阿尔泰语说”。因此,在此只需探讨两种论说。
认为日语和乌拉尔·阿尔泰语关系密切的论说,早已有欧洲学者进行了论述。在日本学者中,东京大学语言学教授藤冈胜二在1908年列出了14项阿尔泰语的特征,其中13项特征日语同样存在。他的论说,受到很多学者支持。但是,阿尔泰语和日语对应的单词非常少,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存在亲缘关系,则日语当很早就从阿尔泰语中分离出来。
关于日语和南方语言的关系,近年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所谓南方语言,是指从包括夏威夷和新西兰在内的南太平洋,到东南亚、印度洋诸岛的岛民使用的语言,总称波利尼西亚语。很早就关注日本语和南方语关系的,是前苏联语言学家Е·Д·波利瓦诺夫。Е·Д·波利瓦诺夫1914年到达日本,他通过对长崎县西彼杵郡三重村的实地调查和其他各项研究后声称:“我可以证明,日语和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同根同源。”他的这一着眼点为比较神话学者松本信广所承袭,语言学者泉井久之助则提出,自西南日本至朝鲜南部,可能存在使用南方语的时期。国语学者大野晋更是进一步推进了这项研究。他在1957年撰写的《日本语的起源》中,列举了几个颇为关键的波利尼西亚语和日语的类似点,并据此推断:波利尼西亚语为日语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相对语言的混沌,看一下今天的日文就不难明白,日本文字的“血脉”显得非常清晰。可以认为,大陆魏国使者登上日本列岛时,已将文字传入。但当时的倭人仅是“观赏”,并未仿效。也就是说,在4世纪,即公元300年,日本尚未使用文字。至5世纪,有两件证据证明日本人已开始使用文字,一是在中国478年的史籍中,有倭王武,即雄略天皇呈出上表文的记载。另外,在九州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了一把大刀。刀上有银的象眼铭文,计74个字。据推断,当属反正天皇时的器物。反正天皇时被称为倭王珍,即位略早于雄武天皇。之后,在近畿地区的和歌山县隅田八幡宫的人物画像镜上,有48个字组成的铭文,其中有“癸未年”3个字。据推算,443年和503年是癸未年。也就是说,在5世纪中或6世纪初,已有极少数人开始使用文字。不仅如此,当时还有人临摹那些从中国传入的镜子上的文字。所以称为临摹,是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与其说是文字,倒毋宁说是图案。另据《记纪》记载,在应神朝,来自百济的归化人王仁将千字文和儒教典籍带入日本并开始教习。虽然这仅是传说,但汉字经朝鲜传入,则是事实。而最先使用文字的,无疑是归化人。当时有归化人为皇室撰写文书,上述倭王武的上表文,即被认为系归化人所写。之后,对文字发生兴趣的人不断增加,文字的书写很快在达官显贵中传播,8世纪也因此被称为“文书的世纪”。确实,8世纪获此美名,当之无愧,因为和前此累计仅区区20件文书的相比,8世纪的文书达到1.2万件。现在,这些文书大都被收藏于东大寺正仓院。
在日本的书写文字当中,现存最古的是隅田八幡宫所藏的、有“癸未年八月”纪年的《人物画像镜铭文》。关于“癸未”年,有383年、443年、503年各种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443年(倭王济时)之说最有说服力。其次,是1978年秋在埼玉县稻荷山大坟出土的《铁剑铭文》,其中有“辛亥年”、“获加多支卤大王”的字样,由此可以推断为是雄略天皇时代。另外,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铭文》,也有“蝮□□□齿大王”等字样。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是反正天皇时代的产物。然而,自从出现了稻荷山古坟出土的“获加多支齿大王”铭文之后,被认定为是雄略天皇时期文物的理由则更为充分些。以上这3种文字,皆为铸造或施以雕刻之后而镶嵌的文字,并非用笔直接书写上去。其结体古拙,近似于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只不过中国的青铜器铭文是钟鼎文字,而日本的则是具有典型的中国六朝时代风格的魏碑体。其中,《隅田八幡宫人物画像镜铭》和《稻荷山古坟铁剑铭》的共同特征为:楷法中时而出现隶书或章草书的笔意,方圆兼用,让人联想到中国北魏时代龙门造像记的书风来。尤其是《稻荷山古坟铁剑铭》和《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均为5世纪之后的雄略天皇时代,两者制作年代和书风也相差无几,文字有凿刻的味道。
在其后的一个世纪,日本均未看到有书写文字的遗品。到了推古天皇时代,才出现了确切的金石文字的遗例。7世纪以降,其数量才急剧地增加起来。这一时期,年代最古且书写在纸上的代表性遗墨,当属圣德太子自撰自书的《法华义疏》。不久前藤枝晃氏提出质疑,认为《法华义疏》并非圣德太子书写,恐怕是职业的写经生所为。但无论怎么说,它仍能显示出那个年代的书风面貌。同时,《法华义疏》也揭示出典型的六朝书风的样式。
由于文字的普及,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意识可以显现个性,和歌的表现形式也自此发生飞跃性变化。关于和歌究竟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当源于天智朝。但是,和歌创作手法的明确变化,以及正式用汉字表记和歌,当始自天武朝。最初的日文——“万叶假名”日本文字赖以“孵化”的《万叶集》即产生于这一背景,尽管“万叶假名”的现身,还有待时日。由于《万叶集》在日本文化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以致人们将以《万叶集》为代表的时代称为“万叶的世纪”或“万叶的时代”,即大化改新自奈良中期(645—759年)。这一时代又以不同文化背景和都城分为白凤(藤原京)文化和天平(平城京)文化两个时期,这里考察前一个时期。与之相应,《万叶集》里的和歌可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考察,本节考察属于前一个时期的两个阶段。

自舒明朝(629—641年)至壬申之乱(672年),为第一阶段,即“初期万叶”阶段。毫无疑问,进入“初期万叶”阶段,和大化改新、壬申之乱和近江朝灭亡等内政剧变的国内政治背景,以及受大陆文化强烈影响的国际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就与文字纪录的关系而言,这一阶段创作的和歌基本上是口诵作品,作者有舒明、齐明、天智、天武四位天皇,以及倭太后、额田王、镜女王、藤原镰足、大伴安麻吕等皇族和贵族的作品。不过,其中有些显然是托名之作,因此究竟作者是谁颇有争议。这一阶段的特点概括而言,是集团性、意欲性、咒术性、与自然的交融,以及同歌谣、民谣的血脉相通。所谓集团性,不难发现“初期万叶”的许多和歌所描述的,是“年中行事”即每年按惯例举行的庆典活动或其他礼仪活动时的作品,如舒明朝的“国见歌”、宇智野狩猎歌、天智天皇千秋后的殡宫的歌,等等。即便一代才女额田王的《下近江国时作歌》:“三轮山,岂可被遮掩;云但能体谅,怎再频遮掩?”也是在迁都奈良时,抒发别离作为大和之国魂的三轮山时的心情,使读者仿佛看到一种礼仪场景。所谓意欲性,如《额田王歌》:“乘舟熟田津,待月把帆扬;潮水涌,操棹桨”,描述了齐明七年(661年)驶向九州的船队,在印南野附近的海上或从伊予的熟田津西行时,向海神的祈祷,具有在以后的和歌中难以寻觅的充实的意欲感。所谓咒术性,则是古代灵魂观和自然观的反映,如有间皇子的《自伤结松枝歌》:“磐代岸边松,结枝祈幸免;得幸免,归来重见。”再如倭太后的作品《天皇圣躬不豫之时,太后奉御歌》:“仰首高天凝眸,吾皇御寿,定然,天长地久。”所有上述作品,均具有和自然交融的特征。同歌谣、民谣的结合亦为“初期万叶”的特征,即便如在蒲生野的药猎时额田王和大海人皇子的唱和,也不同于个人的恋歌。额田王:“往来紫野围禁场,守吏岂不见,君又举袖扬。”皇太子:“妹妍如紫茜,焉能憎厌;况知已是人妻,犹使我生恋。”
《万叶集》最初阶段的和歌所反映的各种特征,有一点同《记纪》中的歌谣颇为相似,即由艺术的自觉和个性的贫乏构成表里。但是由于大陆文化的浸润,该阶段后期的和歌开始告别过于浓厚的主观表现而向客观即事的方向发展,以简洁的语言表现事物存在核心的初期万叶和歌固有的诗情美,开始从歌谣向抒情诗转变。
第二阶段自壬申之乱以后至迁都平城京(710年),文化的繁荣,往往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对文化事业的推动密切相关。这一观点为天武天皇统治时期的日本所印证。不难认为,这一时期和歌的繁荣与朝廷的政策密切相关。
顺应当时社会对语言文字一体化的强烈关心,天武天皇当政时颁布了许多推进日本语文事业发展的诏敕,这些诏敕在《日本书纪》中多有记载。例如,天武天皇四年(675年)2月,“敕令大倭、河内、摄津……美浓、尾张等国,挑选能歌男女及侏儒、伎人贡上”。天武十一年(682年)3月,“命境部连石积等造《新字》一部四十四卷”。必须强调,《新字》是日本最初的一部辞典。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涌现出了日本和歌史上的一代宗师柿本人麻吕。在日本和歌史上,柿本人麻吕堪称“三朝元老”,因为他的活跃期跨天武、持统、文武三朝。这一阶段正是律令制国家确立时期和口诵文学向记载文学转换时期。与第一阶段艺术的自觉和个性的贫乏构成当是和歌的表里类似,转型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同柿本人麻吕的作品构成表里。换言之,时代规定了柿本人麻吕作品的特征,时代也通过他的作品反映自身。这种表里构成是该时代创作的和歌的一大特征,其中尤以柿本人麻吕的作品为最。
柿本人麻吕的作品以“枕词”和“对仗”的精美著称,写作手法和前代相比迥异其趣。枕词虽是以往口诵词章的一种形式,起源于咒术,但柿本人麻吕作品中的比喻性枕句,不是口诵的惯用句,而是具有通过文字纪录取得自立的倾向,其多样性及从中透示出的柿本人麻吕把握事物的敏感,通过文字这一媒体表现得淋漓尽致,宛如古希腊叙事诗中定型句(formulae)的变质。而一般被称为“对仗”的写作技巧,则从《记纪》歌谣和初期万叶和歌具有的反复性,向对偶地描写事物的方向转型,留有受中国诗作影响的明显痕迹。虽然在天武朝之前,如额田王的歌所显示的,已经有了“对仗”的萌芽,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引入“对仗”与其说是在近江朝时期,毋宁说自柿本人麻吕以后。柿本人麻吕留下的很多与“初期万叶”的长歌明显有别的长歌,以及他在天武朝时创作的七夕歌,均显示出中国文化影响的清晰痕迹。更重要的是,不仅是形式和素材,而且文学意识和诗的灵魂,均受到来自大海彼岸的文学浪潮的推动和冲刷。尝试将长歌、短歌、旋头歌等不同的体裁作为装盛新的情怀的容器,也主要完成于这一时期。特别是由柿本人麻吕定型的长歌“五七”形,既有天皇赞歌、皇族挽歌、悲叹都城荒废的哀歌啊:“志贺海湾,水纵回环,昔日之人,岂能再见”,又有感伤离别的情歌,悼念妻子的悲歌。这些和歌在经过雕琢的文字背后,栖息着朴实无华的精神思想。短歌数首一组的连作形式,也创始这一时期。旋头歌虽然发源于歌垣中的片歌问答,但是柿本人麻吕将其作为六句体歌活用,开辟了和歌的一个新的领域。之所以视柿本人麻吕为和歌史上最初具有作诗意识的自觉者,主要就是基于上述原因。
和柿本人麻吕基本同时代的歌人,还有持统天皇的皇子皇女,天智天皇和天武天皇的皇子皇女,以及石川郎女、志斐妪、高市黑人、长意吉麻吕等。他们的作品,如感叹大津皇子谋反事件的悲歌、称颂穗积皇子和但马皇女恋情的欢歌,均和新的抒情时代互相吻合,而高市黑人吟诵“恋物”旅情的佳作,与柿本人麻吕将古代和开化的自然观融为一体相比,则通过和歌咏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并以触景生情的感伤,开拓了和歌一块新的境地。总之,第二期的和歌比第一期的和歌更增添了技巧性和华丽感,且有时给人以做文字游戏的感觉,但是,这个时期的歌仍不耽形式之浮薄,仍不失线条之明快,仍不陷律令制之矛盾,仍反映充满建设活力之时代。同时,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显示,前代氏族制的精神仍作为支撑这种歌风的一根重要支柱保存于个人和集团之间。
本章与前章的衔接之处就是继续为日本和日本人“寻根”,故开宗明义地指出,“日本”不是地名,而是包含特定时间和地点、由特定的人类集团组成的国家。在“日本”成立之前,“日本”和“日本人”都是不存在的。因此,为了澄清“日本”从何而来,本章引证诸多史籍记载和学者观点,对最原初的“日本”如何发展壮大,进行了考察。
同时本章对日本语言文字、宗教和世俗文化在古代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在阐述中尤其注重揭示了一项史实:不仅日本语言文字、宗教和世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归因于统治阶级的推动,而且在战前占统治地位、作为“日本是神国”之意识基础的“记纪”史观,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遭到有力批判,但在战前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凡此,主要为了验证恩格斯的观点:“统治阶级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
和诸多日本史专家对“大化改新”偏重于论述其意义、对“律令制”偏重于阐释其对古代中国政治体制之仿效不同,包括本章在内,我在拙著中绝不敢“怠慢”日本在政治变革中“刀光剑影”、“同室操戈”、“血雨腥风”的史实。所以如此,不仅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展现日本历史的风云激荡,更为了揭示一个令我等三思的普遍真理:任何一种成功的政治变革,都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中国对此真理有深刻认识并明确表述的仁人志士,首推谭嗣同。谭嗣同在“百日维新”失败时,曾留下一句掷地有声、余音绕梁的豪言壮语:“自古未尝有为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