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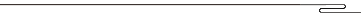
公元6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即自佛教传入至推古朝改革,特别是制定宪法十七条这段历史,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因为前者使儒、释、道(神道)三足鼎立的“传统”文化开始形成,后者则使律令制基础得以奠定。按醍醐天皇当政的弘仁年代编纂的法律法令集《弘仁格·弘仁式》序言中的说法:“国家制法自滋始焉。”
佛教传入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略作叙述,以使读者了解日本佛教产生的历史背景。
据信,佛教发源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现印度东北部恒河流域。作为一种宗教而创生的佛教,在“释尊入寂”后,由其弟子向印度南方,以及沿恒河上游传布。公元前3世纪,向南传布的佛教在锡兰岛建立了根据地,并继续前行。公元3世纪“南传佛教”沿海路到达缅甸、暹罗、柬埔寨、越南,最终形成了小乘佛教。另一方面,沿着恒河向其上游区域传布的“北传佛教”,于公元前3世纪到达了中游区域。当地的国王皈依佛门并对传教进行保护。公元前2世纪,“北传佛教”巩固了其作为大乘佛教的基础,并以印度西北部的恒河流域为中心,进一步向周边地区传布。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经中国西域,即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传入“前秦”和中国东部的“前汉”,并进一步传至扬子江流域的“东晋”,再经“东晋”于公元384年传入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4世纪后半叶传入高句丽,582年传入新罗。
进入6世纪后,大和朝廷的内政外交进入了“继体天皇”和“钦明天皇”当政时期(事实上,当时“天皇”名号尚未问世,但拙作从俗沿用此说)。由于倭五王后列岛和大陆直接交流中断,因此列岛只能通过百济吸收大陆南朝梁文化。百济则不仅和高句丽处于战争状态,而且同新罗也势不两立,亟需倭的军事援助。因此两国进行着持续的交流。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日本,古籍有四处、两个年份记载:
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志癸嶋天皇御世戊午年十月十二日,百济国主明王始奉度佛像经教并僧等,敕授苏我稻目宿禰大臣,令兴隆也。”
元兴寺缘起说:“大倭国佛法,创自志归嶋宫治天下天国案春岐广庭天皇御世。苏我大臣稻目宿禰仕奉时,治天下七年岁次戊午十二月度来。百济国圣明王时,太子像并灌佛之器一具,及说佛起书卷一篋度而言。”
《扶桑略记》钦明十三年(552年)条:“延历寺僧禅岑记云,第廿七代继体天皇即位十六年壬寅,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正,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大尊,皈依礼拜,举世皆云,是大唐神之。”
《日本书纪》钦明十三年(552年)十月条:“百济圣明王(更名圣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利斯致契等,先释迦佛金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
此前,亦有佛教进入列岛的记载。据《叡岳要记》中的“三津首百枝本缘起”记载,显宗天皇三年丁卯(487年),百枝在志贺的草屋中用泥土塑造了一具长3尺的比丘像,人们见之畏惮。但一般不被用作佛教传入凭信。
以往学界一直强调初传日本列岛的佛教,与日本的古神道即氏族信仰相悖,是与之性质迥异的信仰。确实,佛教是具有高度体系化的教义和成文化的经典的宗教,和日本固有宗教神道不同,但这绝不意味着两者自始不可兼容。事实上,将初创时的日本佛教和奈良、平安时代作为一种发达的思想体系的佛教等量齐观,是不甚恰当的。因为,当时的神佛在与原始信仰的邻接点上颇为相通。更值得关注的是,很多论著称,初传日本的佛教被称为“蕃神”。但我认为“蕃神”一词似有误译之嫌。因为,被译为蕃神的日文单词是“ トナリクニノカミ ”,不难认为,该词当译“邻国之神”为妥。毋庸置疑,“蕃神”和“邻国之神”,前者属“上下关系”,后者属“左右关系”,语义显然不同。即便两者无甚差别,“蕃神”一词本身也并不能体现排斥佛教之意。事实上,在日本与大陆、朝鲜半岛交往仍频的年代,“佛”就是来自邻国的渡来人的“神”。毋庸赘言,在世界文化传播史上,对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的吸收,都必须拥有能接受这种文化的土壤。如不作此理解,当很难解释佛教在飞鸟时代为何迅速普及。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如前所述,6世纪30年代钦明朝时期佛教结缘日本列岛,百济圣明王是“月下红娘”。之后,佛教通过种种路径从朝鲜半岛、特别是百济传入日本。据《元兴寺缘起》钦明十五年(554年)二月条记载,百济在替换五经博士的同时,又派遣僧侣曇慧等9人替换了原先派出的僧侣道深等7人;敏达六年(577年)十一月条记载,百济王向倭晋献了律师、禅师、比丘尼、咒禁师、造佛工、造寺工6人。这些人均被安置于难波的大别王寺(四天王寺的前身);崇峻元年(公元588年)为营造法兴寺(飞鸟寺),百济向倭晋献了寺工、炉盘博士、瓦博士、画工等。但根据《崇峻纪》、《元兴寺露盘铭》纪录的人名判断,白昧淳、阳贵文、凌贵文、白加等人显然不像百济人,而似从大陆去的中国人。
普世性宗教佛教的传入,对列岛社会构成了一大冲击。首先在朝廷内部,以苏我氏等代表渡来系利益的高官为一方,以中臣镰子和物部氏等代表土著者利益的高官为另一方,围绕是否接收佛像佛经,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据《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天皇面对佛像经卷,询问诸臣如何因应,苏我氏的第一人苏我稻目当即回禀,称:“西藩诸国(按:指西邻朝鲜诸国)举国礼拜,倭国不应单独拒绝。”物部尾兴和中臣镰子则主张:“吾王若使邻国之神(有些书里写作蕃神)获得礼拜,必惹怒国神。”结果,钦明天皇恩准“崇佛论者”苏我稻目作为个人接受佛教信仰、收纳佛像。这场论争,揭开了日本历史上几度浮沉的“崇佛废佛论争”的序幕。
苏我稻目从钦明天皇手中接过佛像后,将其供奉于小垦田的邸宅日日崇拜。之后更将其在向原的邸宅用作佛寺。孰料此后不久,当地疫病流行,死者甚众。物部尾兴等称,此番灾祸皆因崇拜蕃神惹怒国神所致,于是征得天皇恩准将佛像投弃于难波的堀江,并将伽蓝付之一炬。这,就是日本最初的“废佛毁释”事件。据《元兴寺缘起》记载,此事件发生于苏我稻目死后的钦明三十年(569年)。
事发之后,佛教在日本的流传受阻,直至敏达十三年(公元584年),鹿深臣(甲贺臣)从百济获得一尊弥勒佛石佛后,苏我稻目之后苏我马子才以此为契机使佛教再兴。据《日本书纪》记载,当时苏我马子拜高句丽僧惠便为师,在邸宅的东面建起佛殿并将弥勒佛石像供奉其中并举行法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时佛殿惊现舍利,显示了匪夷所思的灵异。《日本书纪》对此特记,曰佛法之启蒙自此开始。翌年,即公元585年,苏我马子又在大野丘(今奈良县明日香村)的北面建起佛塔,举行了大规模法事,并将舍利置于塔顶。此后,苏我马子在各地建造佛堂佛塔,经常举行大型法事,使崇佛在列岛不像其先人那样仅是一种个人行为。然而,佛教在日本注定命运多蹇,刚如枯木逢春又再次遭难。在一次法事后,苏我马子因有恙在身,遂向弥勒佛石像求拜,祈延年益寿。然此时,国内再度疫病流行,死者甚众。物部尾兴和中臣镰子之后物部守屋和中臣胜海向敏达天皇奏诉,称疫病流行,祸起佛教信仰。敏达天皇准奏,敕令禁教。于是,物部守屋亲往佛寺,推倒佛塔,烧毁佛殿,将佛像投入难波堀江。佛教僧尼也因此遭到弹压。上述事件,在《日本书纪》和《元兴寺缘起》中均有记述,经专家考证,可为信史。
必须强调,崇佛废佛之争,看似有疫病作祟之偶然因素,实则始终存有作为朝廷政治斗争之延伸的必然因素。在佛教传布草创期,苏我氏和6世纪中叶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的司马氏私交甚笃。司马氏是以司马达为首的一个宗族,因以制作马鞍为业,故后改称“鞍作”,为鞍作氏。该家族虽以“鞍作”为业,但亦曾产生卓著如鞍作鸟(止利)的佛师,并在飞鸟建造了坂田寺作为氏寺,是始终与佛教有深刻关联的“渡来系宗族”。事实上,同草创期的佛教关系密切的人,几乎都是“渡来系”的人。不难理解,从朝鲜半岛迁徙日本列岛的“渡来人”,原本就有接受作为外来宗教佛教的意识形态温床,自始力主容纳佛教的苏我氏早与渡来系氏族有染。特别是苏我氏和倭汉氏长年过从甚密,后者几成其私人武装。另外,苏我氏的“部”不仅存在于大和的飞鸟周边,而且分布于渡来人聚居的河内石川流域(今大阪府富田林市周边)。恐在苏我稻目之前,苏我氏已将许多渡来人收入麾下,以其一技之长护己长期之需,将朝廷的财政部门握入掌中,经营先进的“部”,并借此在朝廷中维持较高的政治地位。同时,渡来人的利益诉求,也是苏我氏具有开明派和改革派性格的源泉。因此,当百济圣明王向倭呈献佛像、经卷时,苏我稻目当即表示崇佛态度,虽不能排除其个人信仰因素的驱动,但必有借此笼络渡来人人心的政治动机。
敏达十四年(585年)敏达天皇驾崩后,苏我马子和物部守屋的对立更趋表面化,甚至在安置敏达天皇遗体的殡宫互相嘲讽。所以如此,是因为继位的是钦明天皇的四子大兄皇子用明天皇。由于用明天皇的母亲系苏我稻目的女儿坚盐太后,因此物部守屋的危机感急剧加深。于是,物部守屋便密谋拥立钦明的妃子小姉君的三儿子穴穗部皇子。一场冲突在所难免。用明二年(公元587年),用明天皇在新尝祭的当天以带病之躯(据说所患疾病为天花)召集重臣,表明欲皈依佛门之意,请重臣商议可否。天皇首次主动表明崇佛之意,与用明有苏我氏血脉似不无关系。席间,崇佛派和废佛派自然再起冲突,对阵双方的立场也可以预料:物部守屋和中臣胜海表示反对,苏我马子表示支持。争论正酣之际,押坂部史毛屎走进会场,暗暗告知物部守屋大祸即将临头,于是物部守屋当即逃往阿都(今大阪府八尾市迹部),召集部众。
时隔不久,用明气绝身亡。苏我马子当即集合兵力,首先将与物部守屋联手的穴穗部皇子斩杀,随后率领泊濑部皇子(崇峻天皇)、竹田皇子等诸王子,以及纪男麻吕、巨势比良夫等举兵讨伐物部守屋,决意斩草除根。面对讨伐,物部守屋集合一族之众及其部民迎战,与苏我马子阵营浴血相搏。据称物部守屋亲自登高射箭,并因此被迹见赤梼射杀。主帅阵亡,物部氏全线崩溃。
据《日本书纪》记述,当时厩户皇子(圣德太子)也在苏我马子阵中。在对阵双方激战正酣之际,厩户皇子正雕琢四天王木像,发誓征战胜利后定为四天王建造寺院佛塔。由于笃信佛教的苏我马子也为求菩萨保佑而在战前发誓将建造寺院佛塔。因此在平定“叛乱”后,厩户皇子在摄津国建立了四天王寺,将物部守屋半数部民和奴隶捐赠给该寺。苏我马子也在飞鸟建造了飞鸟寺(法兴寺)。然而据专家考证,《日本书纪》中四天王寺和飞鸟寺同时建造的记述,显然不符史实。因为,四天王寺的轩丸瓦较若草伽蓝迹(创建时的法隆寺)新,显然建成当在其之后,应建于7世纪初。所以出现这一误记,盖因《日本书纪》所述取材于《四天王寺缘起》。《四天王寺缘起》的作者为了提高该寺地位,刻意使之与厩户皇子扯上关系,使之具有更悠久的历史。与之相应,关于厩户皇子的誓愿和参与平乱的记述当也不足为信。因为厩户皇子生于敏达三年(574年),当时年仅14岁。
尽管上述记述或有讹误,但佛教此后获得厩户皇子(即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的皈依和崇拜,则是不争的史实。正因如此,废佛派被一举横扫,佛教在列岛迎来了璀璨的黎明。佛教在列岛第一个真正的寺院飞鸟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建造的。
崇峻元年(588年),百济遣使倭国,向倭国朝廷进献了舍利、僧侣和寺工、炉盘博士、瓦博士、画工等技术人员。由于获得百济的全面协助,飞鸟寺的建造于是年正式开工,推古四年(596)年竣工,历时8年建成:在选址飞鸟真神原后,崇峻三年(590年)开始采伐寺院建筑用材;崇峻五年(592年)开工建造金堂和回廊;推古元年(593年)将百济晋献的舍利供奉于佛塔心础(支撑佛塔中心之心柱的基石),并树立心柱正式开始建塔。推古四年(596年)佛塔建成;推古十四年(606年)由鞍作鸟(止利佛师)领衔雕琢的金铜如来像问世。佛像高达1.6丈(约4.8米),被供奉于金堂。该佛像即现在飞鸟寺(安居院)的本尊释迦像(飞鸟大佛)。伽蓝的竣工,也当在这个时候。
如前所述,以百济圣明王晋献的一尊佛像和数卷经纶为标志,佛教在钦明天皇时期正式传入日本,之后另经敏达天皇、用明天皇时期的“崇佛废佛之争”,至崇峻天皇时期以飞鸟寺的建造为标志趋向繁荣。这一过程看似历经几代皇帝颇为“漫长”,实则并非如此。因为敏达天皇、用明天皇、崇峻天皇是兄弟关系,即均是钦明天皇的子。从538年佛像和佛经传入至596年飞鸟寺竣工,虽经“几代皇帝”,实则仅历时58年。崇峻天皇登基后,苏我马子作为其岳父,更加飞扬跋扈,令崇峻天皇非常不满。据史料记载,某日,有人向崇峻天皇献猪。崇峻指着那口猪说:“我真想像宰这口猪那样,将那令人讨厌的家伙给宰了!”此话传至苏我马子的耳内,苏我马子勃然大怒,称:“天皇这是自寻死路。好吧,容我在被杀之前先把他给杀了。”公元592年,苏我马子果然不辞“弑君之罪”,诱使崇峻天皇出席一个仪式,并指使刺客东汉驹伺机将其刺杀。
在崇峻被杀后的第二年,众臣拥戴的敏达天皇的皇后登基,成为统御列岛的第一个女王——推古天皇。据《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推古天皇即位前纪”:“天皇为大臣马子宿祢见杀,嗣位即空,群臣请渟中仓太珠敷天皇之皇后额田部皇女,以将令践祚……因以奉天皇之玺印。”
对上述引文有必要作两点说明。第一,所谓“天皇之皇后额田部皇女”,是因为推古既是用明天皇的胞妹,也是敏达天皇的皇后及同父异母妹妹。也就是说,敏达天皇娶了同父异母妹妹为妻并立其为皇后。按现代观点,敏达和推古此举纯属乱伦。但在当时的日本朝廷,不是近亲结婚而是“至亲”结婚的现象,并非绝无仅有。例如,圣德太子的父亲用明天皇和他母亲,也是同父异母兄妹。第二,在推古天皇前后出现的女统治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萨满型即女巫型,如《魏志·倭人传》所记载的“事鬼道、能惑众”的卑弥呼。清宁天皇逝后“临朝秉政”的饭丰皇女,亦属这种类型。另一种类型是先帝的皇后,如舒明天皇的皇后齐明天皇,天武天皇的皇后持统天皇。
推古天皇登基后,用明天皇的皇子、年方19岁的圣德太子摄政。其实,“圣德太子”是其谥号。所谓“圣德”,是称赞其身具佛德、深谙佛法。圣德太子的本名为厩户皇子,在《日本书纪》为丰聪耳厩户皇子。同时,因其居于上宫,故又称上宫王、上宫太子。关于圣德太子的身世,《日本书纪》卷二十一中专有记载:“(用明天皇元年)春正月壬子朔,立穴穗部间人皇女为皇后,是生四男,其一曰厩户皇子,更名丰耳聪圣德,或名丰聪耳法大王,或云法主王。是皇子初居上宫,后移斑鸠,于丰御食炊屋姬天皇世,位居东宫,总摄万机,行天皇事。”
推古天皇在圣德太子摄政下推行的政策的基本路线,和苏我马子的路线可谓一脉相承。如许多史家所言,推古朝最初十年的政治体制,堪称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共治体制。但即便如此,两人之间的矛盾显然存在。如引文所述,推古天皇九年(601年),圣德太子移居在斑鸠之地建造的宫室,“总摄万机,行天皇事”。究其迁移斑鸠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脱离苏我马子的控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圣德太子展开了他的内政外交改革。
在内政改革方面,最重要的、使推古朝彪炳千秋的改革,是制定作为官员秩序之基本的身份制度“冠位十二阶”,以及制定官员必须遵循的国法“宪法十七条”。
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十一年(603年)10月,推古天皇在小垦田宫设立朝廷,12月即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并于翌年正月实施。所谓冠位十二阶,即将官员分为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的一种官位制度。显而易见,冠位十二阶将作为儒教最大道德准则的德置于第1位,然后依次是儒学强调的、必须奉行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共十二阶,充分显示了推古朝对儒学的重视。同时因采用不同颜色的
 制成的“冠”作为官位等级的标志,故称“冠位十二阶”。实际上,各阶官员不仅冠位不同,衣服的质地和颜色也不同。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冠位是天皇授予朝廷和地方豪族、官员作为其身份的标志,但和当时和以后依然存在的氏姓制度相比具有明显特征:姓氏是一定范围的族员的共同标志,强调的是血统,而冠位则是授予个人的、显示个人官职的标志,强调个人的功绩。推古朝制定的冠位十二阶,是使以姓为基础的强调血缘的秩序,向强调功绩的官员秩序转变的开端。之后,随着国家组织的完善,特别是律令法的形成进一步发展,并经过大化改新后的冠位制修改,
制成的“冠”作为官位等级的标志,故称“冠位十二阶”。实际上,各阶官员不仅冠位不同,衣服的质地和颜色也不同。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冠位是天皇授予朝廷和地方豪族、官员作为其身份的标志,但和当时和以后依然存在的氏姓制度相比具有明显特征:姓氏是一定范围的族员的共同标志,强调的是血统,而冠位则是授予个人的、显示个人官职的标志,强调个人的功绩。推古朝制定的冠位十二阶,是使以姓为基础的强调血缘的秩序,向强调功绩的官员秩序转变的开端。之后,随着国家组织的完善,特别是律令法的形成进一步发展,并经过大化改新后的冠位制修改,
 成为以后官员身份制度的起源。
成为以后官员身份制度的起源。
同样据《日本书纪》,推古十二年(604年)条,有“夏四月丙寅朔戊辰、皇太子亲肇作宪法十七条”一句,以及宪法十七条全文:
夏四月丙寅朔戊辰、皇太子亲肇作宪法十七条。
一曰、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人皆有党,亦少达者。是以,或不顺君父,乍违于邻里。然上和下睦,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
二曰、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
三曰、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载,四时顺行,万气得通。地欲天覆,则至怀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诏必愼,不谨自败。
四曰、群卿百寮,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礼乎。上不礼,而下非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群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
五曰、绝飨弃欲,明辨诉讼。其百姓之讼,一百千事。一日尚尔,况乎累岁。顷治讼者,得利为常,见贿厅谳,便有财之讼,如右投水。乏者之诉,似水投石。是以,贫民则不知所由,臣道亦于焉阙。
六曰、惩恶劝善,古之良典。是以无匿人善,见恶必匡。其谄诈者,则为覆国家之利器,为绝人臣之锋剑。亦佞媚者,对上则好说下过、逢下则诽谤上失。其如此人,皆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也。
七曰、人各有任。掌宜不滥。其贤哲任官,颂音则起。奸者有官,祸乱则繁。世少生知,克念作圣。事无大少,得人必治。时无急缓,遇贤自宽。因此国家永久,社禝勿危。故古圣王,为官以求人,为人不求官。
八曰、群卿百寮,早朝晏退。公事靡监,终日难尽。是以,迟朝不逮于急。早退必事不尽。
九曰、信是义本,每事有信。其善恶成败,要在于信。群臣共信,何事不成。群臣无信,万事悉败。
十曰、绝忿弃瞋,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共贤愚,如环无端。是以,彼人虽瞋,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众同举。
十一曰、明察功过,赏罚必当。日者赏不在功,罚不在罪。执事群卿,宜明赏罚。
十二曰、国司国造,勿收敛百姓。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与公,赋敛百姓。
十三曰、诸任官者,同知职掌。或病或使,有阙于事。然得知之日,和如曾识。其以非与闻,勿防公务。
十四曰、群臣百寮,无有嫉妒。我既嫉人,人亦嫉我。嫉妒之患,不知其极。所以,智胜于己则不悦,才优于己则嫉妒。是以,五百之乃今遇贤,千载以难待一圣。其不得贤圣。何以治国。
十五曰、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凡人有私必有恨,有憾必非同,非同则以私妨公,憾起则违制害法。故初章云,上下和谐,其亦是情欤。
十六曰、使民以时,古之良典。故冬月有间,以可使民。从春至秋,农桑之节,不可使民。其不农何食,不桑何服。
十七曰、夫事不可独断,必与众宜论。少事是轻,不可必众。唯逮论大事,若疑有失,故与众相辩,辞则得理。
宪法十七条之“宪法”当然不是现代意义的、作为国家一切法律之基础的宪法(constitution)。现代意义的宪法在日本的问世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但是就功能而言,十七条宪法在规范社会秩序和人类行为方面,有几点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宪法十七条强调国家由君(3次)、臣(4次)、民(6次)三大要素构成,即体现了国家的基本社会结构,尽管在宪法十七条中,“君”也时以“王”出现;广义的“臣”包括“王臣”、“群臣”、“群卿臣百僚”等中央官吏,以及“国司”、“国造”等地方官吏;同时“官”、“官司”等词语也多次出现;“民”则既有“百姓”,也有“人民”。

其次,宪法十七条规定了国家的臣僚——公务员应该具备的道德操守和必须服从的纪律规定。如规定官对君要“承诏必谨”(第三条);官对官要“群卿百寮、以礼为本”(第4条);官对民要“绝飨弃欲、明辨诉讼”(第五条),“国司国造、勿收敛百姓”,“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第十二条)。“明察功过、赏罚必当”(第十一条),则体现了法家的治国原则。
最后,宪法十七条虽然具有浓厚的儒学色彩,但并不排斥其他学说。例如,“笃敬三宝”(第二条)即强调必须尊崇佛教。
总之,虽然宪法十七条是一种训诫,和被称为律令的法律属两个系统。但是,无论是在通过对官吏的训诫来阐述国家的理想方面,还是在遵循儒家和法家的世界观方面,宪法十七条同律令,特别是令的根本思想是一致的。因此,被称为律令时代明法家的法律学者,视宪法十七条为令的起源。例如,弘仁格式序中即写道:“上宫太子亲作宪法十七条,国家制法自滋始焉。”另外,宪法十七条虽无刑罚规定,但是《隋书·东夷传》关于倭国风俗写道的“其诉杀人强盗即奸皆死,盗者计赃酬物,无财者没身为奴,自余轻重,或流或杖”,则明确无误显示了推古时代“笞、杖、徒、流、死”五刑的运用。
推古朝摄政的圣德太子另一项重要政绩是在苏我氏的协助下,自620年开始着手编纂“天皇记”和“国记”。这是日本“国史”编纂的正式开端。在“大化改新”的争斗中,这一珍贵资料焚于战火,现已无法查考。
在外交方面,推古朝推行的基本路线是“亲隋”路线。事实上,遣隋使的派遣,就是圣德太子利用他摄政的权力断然采取的、与苏我马子的外交路线有违的决定。据《隋书·东夷传》记载:“开皇二十年(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斯比孤,号阿辈鸡弥(按:此姓、字、号皆日语读音音译),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王妻号鸡弥,后宫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为利歌弥多弗利……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
值得关注的是,推古朝一次次派遣遣隋使,意欲何为?通过史实,我们或许能获得启示。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隋书·东夷传》对此有明确记载:“大业三年(607年),其王多利斯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教,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另据《日本书纪》卷二十二记载:“(推古天皇十六年)旧约辛未朔辛巳(十一日),唐客裴世清罢归,则复以小野臣为大使,吉士雄成为小使,福利为通事,副于唐客而遣之……是时,遣于唐国学生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圀、学问僧新汉人日文、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慧隐、新汉人广济等,并八人也。”值得关注的是,是年“日本”朝廷首次派遣学问僧随遣隋使前往中国。
另外,从上述两条史料中,我们还可以获得两点启示,第一条史料,“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的原因,是倭致隋的国书中后来传闻于世、广为人知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一句,彰显了倭国欲与隋帝国“平起平坐”的勃勃野心,也因此惹恼了隋炀帝。由此可联系另一史实:608年小野妹子和隋使裴世清一起归国后,隋炀帝本有复函,但小野妹子称复函丢失,无法禀呈。专家分析,很可能所涉内容会引起倭朝廷愤怒,影响两国关系,故小野妹子不敢禀告;再联系以后倭“大王”改称“天皇”,“倭”改称“日本”,我们更不难发现这一野心。第二条史料,“遣于唐国学生……学问僧”显示,推古朝虽欲改变其“属国”形象,提高其国际地位,但其深知这种改变和提高是必须通过与隋亲善、借此吸收隋文化实现的。可以认为,这一日本以后也极力贯彻的外交政策,在推古朝时期已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