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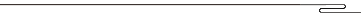
“倭”即日本,“倭人”即日本人,已成为日本和亚洲其他民族的一种常识。然而必须明确的是,“日本”不是地名,而是包含特定时间和地点、由特定的人类集团组成的国家。因此,在“日本”成立之前,“日本”和“日本人”都是不存在的。即使在日本国成立的时候,日本列岛东北中北部和南九州的人们,也仍然不是“日本人”。那么,“倭”即日本,“倭人”即日本人这一认识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澄清“倭”的概念。虽然日本方面与大陆交往的文字记载要迟至7世纪后才出现,但是在中国的史籍中,早在公元前就已有关于日本列岛的记载。《山海经》中的《海内北经》有关于倭的记载:“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这是关于“倭”最初的文字记载。王充的《论衡》也有关于倭的记载:“越裳献上白雉,倭人献上畅草。”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设立乐浪、临屯、玄菟、真藩四郡。此后,中国学者对北九州的倭和倭人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如班固(32—92年)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一记载被引用最繁。但是,如下所述,百余国中最主要的国家“邪马台”究竟在何处,则曾犹如“海市蜃楼”。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设立乐浪、临屯、玄菟、真藩四郡。此后,中国学者对北九州的倭和倭人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如班固(32—92年)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一记载被引用最繁。但是,如下所述,百余国中最主要的国家“邪马台”究竟在何处,则曾犹如“海市蜃楼”。
范晔(398—445年)的《后汉书·东夷传》中,有关于汉光武帝刘秀赐倭奴国王金印的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1784年(天明四年)2月23日,在博多湾志贺岛上,农民甚兵卫发现了一枚金印,其发现过程在3月送交那珂郡役所的口上书(不签字的备忘录)中有明确记载。即中国文献中的记载现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
志贺岛叶崎农民甚兵卫在水渠修缮过程中,发现了一块约需两个人搬动的大石头,用金属杠棒撬起石头后,他发现了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5个字的金印。甚兵卫随即将这枚金印交给了当时的藩校“甘棠馆”馆长龟井南冥。龟井南冥敏锐地判断,这枚金印就是《后汉书·东夷传》里记载的、汉光武帝赐予倭女王的“印绶”。于是,金印立即被送交福冈藩的藩库收藏。
 另有一说是,这枚金印随后经郡宰津田原次郎而交到福冈藩主黑田手里并作为黑田家的收藏品保存至今。
另有一说是,这枚金印随后经郡宰津田原次郎而交到福冈藩主黑田手里并作为黑田家的收藏品保存至今。

陈寿(233—297年)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通称“《魏志·倭人传》”)中,有关记述更为详尽:“倭人在带方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
同时,关于汉朝和倭的交往,该史籍亦多有记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所。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景初二年(238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脂郡,求旨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使,将送旨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离升米、次使都市年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斑布二匹而丈以到,如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如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正始元年(240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诏书印绶,旨倭国,拜假倭王,并宣诏,赐金帛、锦、刀、镜、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诏恩。其四年(243年),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帛衣、帛布、丹、木(木字旁一个付字)、短弓矢、掖邪狗等拜率善中郎将印绶。其六年(245年),诏赐我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
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卑弥呼作为倭的代表和魏交往,俨然是个政治君主。另一方面,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又纯然是个萨满女巫。
关于“倭人”的生活习俗,在《魏志·倭人传》中是如此描述的:“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皆卧息异处,以朱丹,如中国用粉也。食饮用笾豆手食,其死有棺无椁,封土作家,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人性嗜酒,见大人所敬,但搏手以当跪拜。其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妇人不淫,不妒忌,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何有所序,足相臣服……下户与大人相逢大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
从公元前1世纪中叶北九州的许多“国”,经公元1世纪中叶的“奴国”、2世纪初北九州的“倭国”,至3世纪中指称卑弥呼的“亲魏倭王”,中国史籍中已不乏有关“倭”的记载。实际上,那些属于“倭”各小国的国王,在弥生时代中、后期,实际上仅是具有司祭性质的政治首长。
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在经历了公元2世纪末发生的一场大乱后,“倭”形成了以卑弥呼为首的政治联合体。但是,如何认识统率这一联合体的“邪马台国”,自古以来一直存有争议。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日本书纪》的编者。因为,《日本书纪》的编者将卑弥呼和神宫皇后视为同一个人。而正视这一问题的,首先是本居宣长时代的所谓“熊袭”(九州)说。然而,仅关注这一问题的前提,从江户时代的新井白石、本居宣长时代到今天,就发生了很大变化。难以容忍向中国朝贡的女酋是皇室的祖先这一思想,曾是国学者认识这一问题的前提。而明治、大正时期的一些知识分子关注这一问题并作出不懈努力的前提,则是为了通过文献记载复原古代日本的真实形象,打破《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述中的虚妄内容。
关于邪马台国的争议,主要围绕其地理位置进行。邪马台国究竟是在大和,位于畿内即奈良县中部的“大和盆地”,还是在北九州地区?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在邪马台国研究史上,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因为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虎次郎)通过《卑弥呼考》提出的“畿内说”,以及白鸟库吉教授通过《倭女王卑弥呼考》提出的“九州说”,均在这一年问世,并因此将此项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20世纪20年代,京都大学教授喜田贞吉发表了《汉籍中所见的倭人纪事的解释》,折中了双方的意见,并使“九州说”对“畿内说”这场被称为“东大和京大之争”的争论暂告段落。战后,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持“畿内说”,认为邪马台王权的母体就是大和即畿内势力本身的人占据多数;70年代,台状、壶状和楯筑坟丘墓的存在得到关注,认为邪马台服属于畿内政权的主张开始登场;80年代,由于考古新发现,不少学者认为邪马台是和畿内对等的政权。
毋庸赘言,在《魏志·倭人传》中,有关于赴邪马台国所需里程,以及邪马台国所在方位的记载,观察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主要有两个视角,就是注重里程,抑或注重方位。包括内藤湖南和白鸟库吉在内,致力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或注重里程,或注重方位。一般而言,“九州说”注重里程,“畿内说”注重方位。事实上,注重方位对“九州说”不利,而注重里程则对“畿内说”不利。例如,根据《延喜式》记载,从京都到太宰府,海路有30天的旅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按照“里程说”,认为邪马台位于畿内的“大和”显然不合理。但是,考古发现所获得的证据,又对“畿内说”有利。首先,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卑弥呼从魏国获得了很多镜子,而与卑弥呼同时代的中国三国时代的镜子,仅在畿内被发掘出土。其次,卑弥呼死时筑了百余步的塚。按字面理解,那塚当属高塚式古坟,而高塚式古坟发现于“大和”。但是,也有考古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如斋藤忠发表于古代史谈话会编的《邪马台国》的论文指出,首先,镜子存在传世和移动的可能。也就是说,镜子在大陆制成后,未必马上输入列岛,并未经传世和移动即被葬入古坟。因此,三国时代的镜子,很可能在三国时代以后,即邪马台国以后被葬入冢中。其次,现在伴随古坟出土的三国时代的镜子,据推断为公元239年以后的物品,如果将镜子传世、移动的因素考虑在内并综合其他因素,则古坟的发生,当在3世纪后半、4世纪初。换言之,在能够确证邪马台国存在的年代,日本尚未见古坟。按日本古代史权威井上光贞的论述:“根据《魏志》地理记载,自然当位于北九州,考古学也证实在弥生时代后期,北九州处在同近畿地区不同的文化圈内。因此,将邪马台联合体视为北九州的政治统合体的假说,似更加合理。”
 新近的考古发现,特别是1989年北九州佐贺县神埼町吉野里遗址的发现,为“九州说”提供了有力支持。同年2月23日,《朝日新闻》以《邪马台国时代的“国家”》、《佐贺县吉野里、最大规模的环濠集落发掘》等醒目标题,对此作了报道。当天,NHK新闻节目也对此作了报道。这些报道引起极大关注,据统计,在72天时间里,约有106万人踏访吉野里遗址。至此,曾经的“海市蜃楼”似已清晰可辨。但是,20世纪末的一个重大考古发现,使“邪马台论争”重起:1997年8月11日,日本考古学者开始对奈良县天理市黑塚古坟进行发掘。1998年1月10日,日本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称,在黑塚古坟发现了34面镜子,其中画纹带神兽镜1面、三角缘盘龙镜1面、三角缘神兽镜32面。由于黑塚古坟是全长约130米的前方后圆坟,墓主显然应是侍奉卑弥呼的权贵,而三角缘神兽镜当是卑弥呼从大陆魏国获取,故这一发现顿时为“畿内说”注入了活力,使之盛赞有加。1998年1月10日,持“畿内说”的奈良大学校长、考古学家水野正好在日本销量最大的《读卖新闻》上撰文称,这一发现是“本世纪最大的发现之一。邪马台国已清晰可见”。“三角缘神兽镜是卑弥呼受赐于中国皇帝并搜集的镜子,黑塚的被葬者获得的镜子,来自王室的镜仓。”九州大学教授、考古学家西古正更是声称:“这已经不是为‘畿内说’补充证据,而是使研究朝一个方向发展的铁证。”但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卑弥呼仅从魏国获取了百面镜子。如果这些镜子是三角缘神兽镜,那么黑塚古坟的被葬者独占其中33枚,似不太合理。这些三角缘神兽镜完全有可能是国产而非舶来的。最终,以下意见获得了众多专家的认可:“仅仅以关于三角缘神兽镜的看法为依据展开邪马台国争论,似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一意见,使邪马台国重新恢复了“海市蜃楼”的原貌。
新近的考古发现,特别是1989年北九州佐贺县神埼町吉野里遗址的发现,为“九州说”提供了有力支持。同年2月23日,《朝日新闻》以《邪马台国时代的“国家”》、《佐贺县吉野里、最大规模的环濠集落发掘》等醒目标题,对此作了报道。当天,NHK新闻节目也对此作了报道。这些报道引起极大关注,据统计,在72天时间里,约有106万人踏访吉野里遗址。至此,曾经的“海市蜃楼”似已清晰可辨。但是,20世纪末的一个重大考古发现,使“邪马台论争”重起:1997年8月11日,日本考古学者开始对奈良县天理市黑塚古坟进行发掘。1998年1月10日,日本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称,在黑塚古坟发现了34面镜子,其中画纹带神兽镜1面、三角缘盘龙镜1面、三角缘神兽镜32面。由于黑塚古坟是全长约130米的前方后圆坟,墓主显然应是侍奉卑弥呼的权贵,而三角缘神兽镜当是卑弥呼从大陆魏国获取,故这一发现顿时为“畿内说”注入了活力,使之盛赞有加。1998年1月10日,持“畿内说”的奈良大学校长、考古学家水野正好在日本销量最大的《读卖新闻》上撰文称,这一发现是“本世纪最大的发现之一。邪马台国已清晰可见”。“三角缘神兽镜是卑弥呼受赐于中国皇帝并搜集的镜子,黑塚的被葬者获得的镜子,来自王室的镜仓。”九州大学教授、考古学家西古正更是声称:“这已经不是为‘畿内说’补充证据,而是使研究朝一个方向发展的铁证。”但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据《魏志·倭人传》记载,卑弥呼仅从魏国获取了百面镜子。如果这些镜子是三角缘神兽镜,那么黑塚古坟的被葬者独占其中33枚,似不太合理。这些三角缘神兽镜完全有可能是国产而非舶来的。最终,以下意见获得了众多专家的认可:“仅仅以关于三角缘神兽镜的看法为依据展开邪马台国争论,似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一意见,使邪马台国重新恢复了“海市蜃楼”的原貌。
虽则邪马台国究竟所在何处迄今尚未明了,但是对邪马台部落联盟性质的认识,则已然清晰;邪马台是咒术宗教权威在统合中扮演重要角色、各属“国”具有很强独立性的政治集团、处在国家正式形成前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女性无疑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早在弥生时代受大陆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伊都国,公元前后在汉王朝的扶持下,和奴国一起发展成了部落国家。2世纪初,在后汉王朝的庇佑下,伊都国登上了倭国盟主的宝座并在较长时期保持了盟主地位。1965年,在三云遗址群西北1.2公里的平原遗址令人惊叹的国王墓穴的随葬品中,发掘出了约40面已几呈粉状的镜子,以及玛瑙制管玉、玻璃制耳珰(耳饰)、勾玉、小玉。通过这些随葬品考古学家有理由判断,伊都国最后一位躺在这种墓穴中的,无疑是女性祭司王。事实上,《魏志·倭人传》中的记述,也反映了当时女性的政治地位:“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3世纪30年代,卑弥呼和魏国正式开始交往,但不久在和狗奴国的争斗中去世。卑弥呼去世后,“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同样据中国史籍记载,晋亡魏后,壹与继续与之保持联系并多次遣使。但是,自“泰始初年”后,壹与遣使在中国史籍中曾中断近150年。最后一次遣使见于《晋书》记载:“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十一月乙卯,倭人来献方物。”之后,在《晋书》义熙九年(公元413年),才又见记载:“是岁,倭国及西南夷献铜头大饰及方物。”两国交往何以长期中断?林屋辰三郎在论述了当时中国动乱的政治形势后指出:“由于中国当时存在这种政局,因此使魏晋以来一直是中国和倭交涉对象的洛阳,被完全卷入了战争漩涡。再则,前此倭使前往洛阳一直经由朝鲜半岛,而倭本身在这一期间因侵略朝鲜而堵塞了这条路。”
 林屋辰三郎的论述颇给人启发。国交长期中绝,似与中国政局和亚洲政局变化有关。邪马台部落联盟和魏的关系,虽然由其同西晋的关系所取代,但是如“八王之乱”所象征的,4世纪西晋在对外关系方面已难以维持权威。
林屋辰三郎的论述颇给人启发。国交长期中绝,似与中国政局和亚洲政局变化有关。邪马台部落联盟和魏的关系,虽然由其同西晋的关系所取代,但是如“八王之乱”所象征的,4世纪西晋在对外关系方面已难以维持权威。

日本

与此对应,中国周边民族发生了明显的政治变动。自3世纪末至4世纪中,随着中国王朝势力的衰退,东亚的政治地图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朝鲜半岛,高句丽日益向南方扩展势力范围,百济统一了马韩诸国,新罗统一了辰韩诸国。但是,在这一时期,倭似保持着和朝鲜半岛的交往,其主要证据,就是镇坐于奈良县天理市布留的石上神宫和石上的七支刀。石上神宫系《日本书纪》中的“振神宫”,原本和大神神社一样没有本殿(现在的本殿是1911年动工、1912年建成的)。神宫以瑞垣围起的禁足地信仰迄今仍有保持。经考古发掘,石上的禁足地出土了大量宝物,如各种玉器、金铜镮、环头大刀柄头、琴柱形石制品等。据推断,该处自4世纪后半叶当是一个作为祭司场所的圣域。在各种宝物中,尤其珍贵的,是国宝“七支刀”。这把刀长74.9厘米(刀身65厘米),刀身两侧刻有金象嵌铭文60余字。对此铭文,自明治后即有多种解读。1981年通过高倍显微镜·X线摄影,辨认出有“泰和四年五月十六日”字样。一般认为,此“泰和四年”(公元369年)当为东晋年号。关于宝刀来历,认为系百济呈献倭王的“献上说”和认为系倭王下赐给百济的“下赐说”可谓旗鼓相当。“但不管采用何种论说,七支刀在考察古代日朝关系史方面,均堪称不可轻视的传世品”。

以上述历史为背景,在日本列岛,以畿内,即以奈良县中部的“大和盆地”为中心,古坟和古坟文化兴起并迅速波及北九州。自3、4世纪前后,畿内开始成为日本古代统一政权“大和朝廷”的根据地。虽然统一的主体是畿内地方土著势力,还是东迁的原北九州地方势力,目前尚不明了。但是有一点似可以肯定,即大和政权不再是由卑弥呼那样的萨满统治的国家,而是由掌握强大权力的王者统治。王死后,也不像邪马台国那样即刻发生内乱,而是依靠已稳固建立的体制,由新的王者职掌政权继续统治。所有这些均表明,当时畿内地区已进入阶级社会。
与上述大和与邪马台显著有别的情况相对应,从3世纪末到4世纪末约100年间,以大和为中心、在近畿和濑户内海等地区,出现了前方后圆形坟墓,之后这种坟墓逐渐扩展到自九州北部到东北南部的日本列岛大部分地域。象征一个时代的古坟不断向各地扩展,不仅清晰地显示了日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显示了豪强势力以畿内为中心逐步建立起了统一国家,即在列岛各地,整合了附近的共同体并确立起强大而稳固统治权的地方首领,均附属于以大和为中心的畿内首长联合体即大和政权,形成日本古代国家母体的过程。如果说邪马台国如“海市蜃楼”,那么古坟无疑已清晰可辨并于大和政权荣衰与共:经考古发掘,在以畿内为中心,包括濑户内海、九州北部在内的广大区域内,出土了被称为前方后圆坟的高塚坟墓。其中被认为最早的古坟,有京都府椿井大塚山古坟、兵库县吉岛古坟、冈山县汤迫车塚古坟、山口县竹岛古坟、福冈县石塚山古坟、大分县赤塚古坟,等等。这一考古发现说明,在3世纪后半叶至4世纪初,日本迎来了古坟时代并急速扩展,进入5世纪后已达九州南部至东北南部,至6世纪后半叶或7世纪初,前方后圆坟几乎遍布各地。
同时,自5世纪后半叶,除了大型的前方后圆坟以外,中、小古坟也有明显增加。尤其是圆坟的“群集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在6世纪后期达到高峰,现身于列岛各地的山间岛屿。进入7世纪后,其原先生机勃勃的气势陡然衰颓,至律令制国家得以确立的7世纪,古坟的营造基本打上了休止符。这一休止符,宣告又一个新时代——古坟时代的来临。
所谓“古坟”,原本的含义是“用土高高堆起的古墓”。但是在日本,“古坟”特指代表这个时代的高塚坟墓。同时由于高塚坟墓在3世纪后半叶至7世纪,即400年左右的时间里遍布全国,因此这一时期在日本学术界被称为“古坟时代”。古坟时代大致被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前期、中期、后期。前期以镜子、碧玉制腕饰等咒术、宗教色彩较强的随葬品,以及狭长的坚穴式石室和黏土廓等为特征,跨越年代为4世纪前后,是古坟文化的形成期。中期的特征是前方后圆坟的规模达到顶端;将铁器、石制仿造品以及新增添的源自大陆的马具作为随葬品;炫耀权力的古坟祭祀的礼仪化得以推进。跨越年代大致是整个5世纪,是古坟文化的发展期。后期以横穴式石室、须惠器、马具的普及、群集坟的发展等为特征,表现出对大陆文化的全面吸收和咒术、宗教要素的淡化;古坟开始变质并踏上从衰退至消亡的不归路。后期的时间跨度为6、7世纪。
以高塚古坟为象征的古坟之所以能代表一个时代,是因为在该时代初期高塚古坟都建于鸟瞰平地的山丘或山尾上,显示出一种威压四方的气势。而这,显然是炫耀身份的重要手段。虽则古代的达官显贵往往通过建筑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寺院炫耀自身的权力,但对于古坟时代的豪族来说,进入那个阶段还要等待几百年。除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外,这些古坟还显示出充分反映当时生产技术水平的特征:
第一,古坟无论是坟丘的规模还是地形的选择,不仅显示出与一般坟墓不同的风格,而且显示出在营造时经过很好的规划设计。前方后圆坟自出现时,就有长达数十米至二百数十米不等的坟丘,将圆丘和方丘联结起来的大坟丘,无论平面还是立体均具有几何学轮廓,非常整然。整个坟丘的表面均堆有葺石。可以认为,当时的人们在营造这些坟丘时,都进行了很好的规划和计划,并采用了统一的尺度和测量方法。
第二,虽然遗骸以各种方式收入棺中,但埋葬设施的结构相当复杂,即在营造时首先自坟顶处掘出一个很大的方形土圹,在土圹底部铺上砾、黏土,将宽5米长7米的硕大的木棺安放在里面,然后用石板构筑的竖穴式石室将木棺围起,用厚厚的黏土覆盖其顶部,最后将棺木埋葬。这种特殊的埋葬设施,作为同前方后圆坟的坟丘一体化的内部结构而被定形。
第三,墓葬中有大量中国制的镜子、铁制武器、生产用具、铜镞、玉等成套的随葬品。需要强调的是,分布于濑户内海地区和山阴、北陆等地、承袭了方形周沟墓和方形台状墓传统的坟丘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坟丘的发达,但几乎没有随葬品。与之相反,在九州北部弥生时代的瓮棺墓中,虽然有大量中国制的镜子、金属武器、玉器等随葬品,但却看不到坟丘的发达。也就是说巨大的坟丘、复杂的内部结构、定型的成套随葬品整齐划一的组合,是宣告新时代来临的新的墓葬制度的标志。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古坟的随葬品中,有许多三角缘神兽镜的同范镜(按:即用相同的模子铸造的镜子)。根据镜子的分布状况判断,似由畿内首长统一配发。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墓的主人和畿内的首长存在这种授受宝器的亲密关系,对照畿内,特别是大和盆地的前方后圆坟相比其他地区更早显示出显赫规模,不难判断当时以畿内豪族势力为中心的政治联合体已经形成。因为,仅仅为安葬一个人而营造、并以大量贵重器物随葬的巨大的古坟,既是弥生时代最后的栖身之处,同时也是凌驾于共同体其他成员之上、握有权威的首长的摇篮:无声地宣告一个时代的降临。
毋庸赘言,营造一个大则全长二百数十米,小则数十米,一般全长约百米至四五十米的庞大的古坟,需要动员和组织大量劳动力。能做到这一点本身就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事实上根据考古发现,很多古坟所在的区域,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郡或一个郡的二、三分之一——一般均以一个水系的上、中、下游为中心,即显示了古坟的主人生前拥有的“势力范围”。由于这些古坟是渐次营造的,因此先后营造的座座古坟同时也显示了政治权力的代代传承。
在前方后圆坟中,镜、铁制利器、玉成套的随葬品,与其说是墓主身前的财物,毋宁说是显示其权力、具有强烈咒术和宗教色彩的宝物。同时,这些宝物是我们了解墓主身份的重要线索。如铁刀、铁剑、铁镞、铜镞等各种武器,在成套的随葬品中占据中间很大位置,说明墓主身前曾是一位军事首领。由于在古坟时代,墓主往往既是军事统帅者,也是共同体生产的指导和组织者。因此,在随葬品中也有许多铁制农具、工具。在古坟时代前半期,铁制农具和工具始终占有重要位置,并在5世纪表现得最为明显。而掌握铁制生产用具的供应源并集中管理,动员和组织包括治水、灌溉在内的生产活动,也是当时墓主的一大权力。除了掌握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世俗权力外,当时的部落首领同时也是作为该部落最高司祭的宗教权威,并在身前和身后以此姿态君临共同体。在被认为是祭祀位于玄海滩孤岛沖岛上的海神宗像神的遗址,考古学者发掘出了与以镜为中心的古坟的随葬品的种类一致的大量奉献品。依此判断,当时的人们显然将去世的首领作为部落的守护神供奉。特别考虑到作为重要随葬品的大量镜子,是由作为共同体司祭的部落首领管理的神圣祭器,因此首领本身从祭祀者转变为护佑部落安宁的被祭祀者,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探寻一下古坟文化的传播。以畿内、濑户内海沿海区域为中心的西日本古坟分布圈,自4世纪后半叶至5世纪初,迅速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展,西至九州北部和中部,东至东北地方南部。毫无疑问,在扩展过程中,不仅古坟的外观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以圆筒埴轮为主的定形化的埴轮的大量出现,以及台形、壶形、盖形、楯形的出现;而且古坟的内容——随葬品,也随之发生变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大陆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古坟时代初期,作为随葬品的镜子,均是中国制的所谓“舶载镜”,最初日本制的所谓“国产镜”,也只不过是对中国制的三角缘神兽镜的忠实模仿。至古坟时代中期,“在随葬品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马具、金铜制带金具等大陆要素的出现。在随葬品中显示出的大陆要素,在4世纪后半叶的古坟中,已经可以看到其先驱者,如奈良县新山古坟出土的龙文透雕带金具。马具则最初发现于誉田山古坟的陪塚丸山古坟、石津丘古坟(履中陵)的陪塚七观古坟等,在坟丘规模最大化时期的大王陵周边”。
 同时毋庸置疑的是,在5世纪前半叶至中叶,在王权主导下,通过吸收大陆的先进技术及人员,列岛的劳动生产水平和武器生产水平得到了划时代的增长。日本列岛居民骑马的习俗不仅传自大陆,而且是当时受大陆文化影响的典型事例。事实上,当时确实有大批专门负责养马以及传授骑马技术的“马饲部”,以及专门从事马具制作的“鞍作部”的技术者的赴日。而马具的普及,如前面所述,则是古坟时代后期的一大特征。
同时毋庸置疑的是,在5世纪前半叶至中叶,在王权主导下,通过吸收大陆的先进技术及人员,列岛的劳动生产水平和武器生产水平得到了划时代的增长。日本列岛居民骑马的习俗不仅传自大陆,而且是当时受大陆文化影响的典型事例。事实上,当时确实有大批专门负责养马以及传授骑马技术的“马饲部”,以及专门从事马具制作的“鞍作部”的技术者的赴日。而马具的普及,如前面所述,则是古坟时代后期的一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