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许我的任何一个经验主义概念都没有一如集体无意识概念,遭遇到如此多的误解。我将努力在下文中提供:(1)关于这个概念的定义;(2)关于它对心理学的意谓的描述;(3)关于检验方法的解释;(4)例子。
集体无意识是精神的一部分,这部分精神可以通过如下事实将其从否定层面与个人无意识相区隔,即它并非一如后者,将自己的存在归结为个人经验,因此并非是一种个人习得。虽然从本质上讲,构成个人无意识的内容有时属于意识,但是它们已然因为被遗忘或者被压抑而从意识中消失;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从未存在于意识之中,因此从未为个人所习得,而是将其存在完全归结为遗传。不同于个人无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情结 (complexes)构成,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基本上是由 原型 构成。
原型概念是集体无意识概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联物,它表示似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种种确定形式在精神中的存在。神话研究称它们为“主题”;在原始派心理学中,它们相当于列维——布留尔的“集体表象”概念,在比较宗教学领域,它们被于贝尔(Hubert)和莫斯(Mauss)定义为“想象的范畴”。很久以前,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称它们为“初级思想”或者“原始思想”。这些参照物非常清楚地表明,我的原型概念——实际上是一种业已存在的形式——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在其他知识领域中得到了承认与命名的东西。
因此,我的观点如下:除了我们的即刻意识——它是完全个人性的,以及我们认为它是唯一的经验性精神(尽管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补充而接受),还存在着第二种精神系统,这一系统具有在所有个人身上完全相同的集体性、普世性、非个人性本质。这种集体无意识并非是单独发展而来的,而是遗传而得的。它由事先存在的形式、原型组成;原型只能继发性地成为意识,赋予某些精神内容以确定的形式。
因为医学心理学发展自职业实践,它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精神的 个人 性质。我这样讲意指的是弗洛伊德和阿德勒(Adler)的观点。它是一种“ 个 人的心理学 ”(psychology of the person),其病因学或者因果关系的因素几乎被视为是俨然个人性质的。然而,这种心理学的基础是某些普通的生物因素,比如性本能或者自我主张的需求,这些因素绝非仅仅是个人特性。它不得不如此,因为它自诩是一门解释性的科学。这两种观点都不否认在人和动物身上同样存在的种种先验性本能,或者这些本能对个人心理有着重要影响。但是本能是一个有活力的或者具有启发作用的人的非个人的、普世性地分布的、遗传而得的因素,这些因素经常无力到达意识,所以现代精神治疗面临着帮助患者意识到它们的任务。而且,本能在本质上并非模糊或者不确定,而是具体地形成的启发性力量;这些力量无论早在意识出现之前,还是后来意识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始终追求其与生俱来的目标。因此,它们变得与原型极为相似,事实上,相似得让人有充分理由认为原型是本能自身的无意识形象,换言之,它们是本能行为的模式。
因此,集体无意识的假设并不比本能存在的假定更加大胆。人们始终承认,除了有意识的大脑的理性动机以外,人类活动深受本能的影响。因此,如果人们可以断言我们的想象、知觉与思想同样受到与生俱来的、普遍存在的形式因素的影响,那么在我看来,正常运行的智识会发现这种观念中的神秘主义与本能理论中的神秘主义是等量的。虽然对神秘主义的这种非难经常以我的概念为靶子,但是我必须再次强调,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既不是思辨性的,也不是哲学性的,而是经验性的。简单地说,问题如下:究竟是有还是没有这种无意识的、普世性的形式?如果它们存在,一个人们可以称之为无意识的精神领域也就存在。诚然,对集体无意识的诊断并非总是易事。仅仅指出无意识产物的时常显在的原型性质是不够的,因为这些也可能是源自语言与教育的习得产物。潜在记忆(cryptomnesia,又译密码记忆)也应该被消除,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依旧有足够的个人例证在表明神话主题的土著复活,从而使得这一问题不容置疑。但是如果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无意识,那么心理学解释就必须考虑到它们,以及对某些所谓的病因解释进行更为尖锐的批评。
或许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使我的意思更加清楚。或者你们已经阅读过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一幅画所进行的讨论: [1] 即那幅有圣·安妮(St.Anne)、圣母玛利亚及幼年基督(Christ-child)的画。弗洛伊德基于列奥纳多本人有两位母亲这一事实,对这幅名画进行了解读。这种因果关系是个人性的。我们既不会留连于这幅画远非独特这一事实,也不会纠缠于这幅画的小小失误:圣·安妮是基督的祖母,而不是像弗洛伊德的解释所要求的那样,是基督的母亲,而是将仅仅指出与显在个人的心理学交织在一起的,是一个对我们中来自其他领域的人而言十分熟悉的非个人主题。这就是“双重母亲”(dual mother)的主题,它是神话学、比较宗教学中见诸于若干变体的一种原型,构成了无数“集体表象”的基础。比如,我可以论及“双重血统”(dualdescent)的主题,即同时拥有来自人类父辈的血统与来自上帝的血统,一如赫拉克勒斯(Heracles,又译赫拉克里斯——中译者):他因不知情地受到了天后赫拉(Hera)的收养而获得了不朽。在希腊是神话的东西在埃及实际上是一种仪式:法老(Pharaoh)在本质上且人且神。在埃及神庙的身世室(birthchamber)中,四周的墙上刻绘着法老的第二次、圣灵受孕及诞生;他是“重获新生的”。正是思想构成了一切再生神话的基础,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本人是“重获新生的”:通过在约旦河的洗礼,他从水与精神之中获得了再生或者新生。因此,在罗马的礼拜仪式中,洗礼盆被称作“教会之腹”(uterusecclesiae),而且一如人们可以在罗马的弥撒书里可以看到的,即使是时至今日,在复活节前的圣星期六的“洗礼盆的祝福”中,它仍被这样称呼。而且,根据一种早期的基督教——诺斯替教思想,以鸽子形式显形的精神被解释为索菲娅——沙皮恩提亚(Sophia-Sapientia)——智慧与基督之母。由于这一双重诞生的主题,今天的孩子在出生时被赐予了保护人——“教父”与“教母”,而不是拥有魔法般用祝福或者诅咒“收养”他们的精灵。
第二次诞生的思想见诸于任何时间与地点。在医学之初,它是一种神奇的治疗手段;在诸多宗教里,它是核心的神秘经验;在中世纪的神秘哲学中,它是关键性的概念;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它是出现在无数孩子身上的一种童年幻想,他们无论大小,全都认为自己的父母并非生身父母,而仅仅是收养他们的养父母而言。一如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本人在其自传中所叙述的,他也曾有过这一幻想。
现在绝对不容置疑的是,所有相信双重血统的人在现实中总是有两个母亲,或者相反,那些与列奥纳多命运相同的少数人已然使他人感染上了他们的情结。相反,人们无法回避这一假设:双重诞生的主题与两位母亲的幻想的普遍存在,应和了反映在这些主题之中的无所不在的人类需求。然而,如果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确是在以圣·安妮和圣母玛利亚描绘他的两位母亲——对此我深表怀疑——他仅仅是在表达他之前和之后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所信仰的某种东西。秃鹫的象征(弗洛伊德也在上文所提及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讨论)使得这一观点愈加可信。不无道理的是,他把在列奥纳多时代极为流行的一本书,即荷拉波罗(Horapollo)的《象形文字》(
Hieroglyphica
),
 引证为这一象征之源。其间人们会看到,秃鹫全是雌性的,象征着母亲。它们靠风(元气)受孕。这个词有了“精神”的意思,主要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即使是在对圣灵降临节(Pentecost)奇迹的叙述之中,元气仍有风与精神的双重意义。在我看来,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地指向圣母玛利亚,因为就本性而言,她是一个处女,像秃鹫一样靠元气受的孕。另外,根据荷拉波罗,秃鹫也象征雅典娜(Athene);并非生于分娩、而是直接从宙斯(Zeus)的头部跳出来的雅典娜是一个处女,仅仅知道精神之母。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是对圣母玛利亚和再生主题的暗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列奥纳多用这幅画表达了其他什么。即使他把自己等同为童年基督这一假设是正确的,他完全可能是在表征神话学的双重母亲主题,而绝非他自己的个人史前史。所有其他曾经表现过同一主题的艺术家又如何呢?肯定不是他们大家都有两个母亲吧?
引证为这一象征之源。其间人们会看到,秃鹫全是雌性的,象征着母亲。它们靠风(元气)受孕。这个词有了“精神”的意思,主要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即使是在对圣灵降临节(Pentecost)奇迹的叙述之中,元气仍有风与精神的双重意义。在我看来,这一事实毋庸置疑地指向圣母玛利亚,因为就本性而言,她是一个处女,像秃鹫一样靠元气受的孕。另外,根据荷拉波罗,秃鹫也象征雅典娜(Athene);并非生于分娩、而是直接从宙斯(Zeus)的头部跳出来的雅典娜是一个处女,仅仅知道精神之母。所有这一切实际上是对圣母玛利亚和再生主题的暗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列奥纳多用这幅画表达了其他什么。即使他把自己等同为童年基督这一假设是正确的,他完全可能是在表征神话学的双重母亲主题,而绝非他自己的个人史前史。所有其他曾经表现过同一主题的艺术家又如何呢?肯定不是他们大家都有两个母亲吧?
现在让我们把列奥纳多的例子置换为神经病的领域,假定一位有母亲情结的患者正苦于其神经病的根源在于他的确有两个母亲的幻觉。个人的解释必须承认他是对的——但是这将大错特错。因为事实上,他的神经病的根源在于双重母亲原型的重新激活,完全无关乎他是否是有一个母亲或者是有两个母亲,因为一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原型单独地、历史地发挥作用,决不关涉相对稀罕的双重母亲的出现。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事先假定一个如此简单与个人化的原因当然具有吸引力,但是这种假设不仅是不准确的,而且是完全错误的。要理解双重母亲主题——这是仅仅在医学领域受过训练的医生所不知的——怎么可能有如此大的决定能力,以致造成创伤性条件的影响,这诚然很难。但是如果我考虑潜伏于人类神话及宗教领域之中的巨大力量,原型的病因作用就会显得没那么荒谬了。在无数的神经病案例中,失调的原因正是在于患者的精神生活缺乏这些动机力量的配合这一事实。然而,纯粹的个体心理学通过把一切都压缩为个人原因,尽其所能地否定原型主题的存在,甚至试图通过个人分析毁掉原型主题。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方法,无法在医学上被证明具有合法性。今天你们对关涉其中的种种力量的性质的判断,会好过在二十年以前。难道你们不能看到一个民族是在如何复兴一个古老的象征,是的,甚至古老的宗教形式,以及这种大众情绪在如何以一种灾难性的方式影响和革命个人的生活?过去的人今天依旧活在我们身上,其程度之大是战前未曾料想得到的;归根到底,伟大民族的命运如果不是个人精神变化的总和又会是什么呢?
只要神经病真的仅仅是一桩私事,其根源全部在个人原因之中,原型便不会在其间起任何作用。但如果它是一个普遍不兼容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在数量相对较大的个人中引发神经病的别样有害状况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假定聚合原型的存在。因为在多数情况下神经病都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现象,所以我们必须假定原型也聚合在了这些病例之中。与这一情势相应的原型被激活了,潜伏在原型之中的那些猛烈、危险的力量因此开始运作,常常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受制于原型支配的人无不成为精神病的牺牲品。如果三十年前有人胆敢预言我们的心理学会朝着复活对犹太人进行中世纪式迫害方向发展、欧洲将再次战栗于罗马权杖及罗马军团的脚步声面前、人们将一如两千年前那样再次行罗马举手礼、是古老的十字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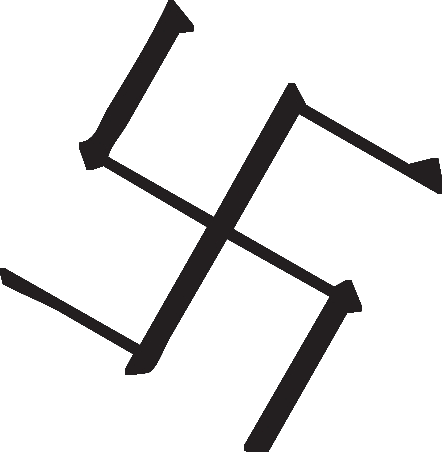 ”(swastika)而不是基督教十字架将引领数百万将士准备战死疆场——这个人一定会被斥骂为神秘主义傻瓜。今天又会怎么样呢?尽管这可能听起来令人吃惊,但是所有这些荒谬之事都已然成为可怕的现实。在当下世间,私人的生活、私人的病因以及私人的神经病几乎已成为虚构之物。生活在古老的“集体表象”世界中的“故人”,重新出现在了非常显在及痛苦的真实的生活之中,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为数不多的神经错乱的人当中,而是存在于数以百万计的人当中。
”(swastika)而不是基督教十字架将引领数百万将士准备战死疆场——这个人一定会被斥骂为神秘主义傻瓜。今天又会怎么样呢?尽管这可能听起来令人吃惊,但是所有这些荒谬之事都已然成为可怕的现实。在当下世间,私人的生活、私人的病因以及私人的神经病几乎已成为虚构之物。生活在古老的“集体表象”世界中的“故人”,重新出现在了非常显在及痛苦的真实的生活之中,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为数不多的神经错乱的人当中,而是存在于数以百万计的人当中。
生活中有多少种典型情势,就会有多少种原型。无止境的重复已经把这些经验铭刻进了我们的精神构成之中,但是并不是以充满内容的形象的形式,而是首先仅为 没有内容的形式 ,仅仅表征某种感知与行为的可能性。当符合某种原型的情势出现时,这种原型便被激活,一种强制性随之出现;这种强制性要么像本能驱使一样,获取反对所有理性与意志的方法,要么引发病理维度的冲突,换言之,引发神经病。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原型的存在可以如何证明的问题。因为人们认为原型引发了某些精神形式,所以我们必须讨论人们能够以何种方式及在何处获得证明这些形式的材料。因此,主意的渠道是梦,因为梦拥有作为无意识心理的不自主、自发产物的优点,因此是纯粹的自然产物,没有为任何意识目的所歪曲。借助对个人的考察,人们可以确定出现在梦中的哪些主题是他所熟悉的。很自然,我们必须把所有可能是熟悉于他的主题从那些他所不熟悉的梦中排除,比如——回到列奥纳多的例子——秃鹫的象征。我们不确定列奥纳多是否是从荷拉波罗那里得到了这一象征,虽然对一个在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言,这完全有可能,因为在那个时代,艺术家以其广博的人文知识而著称。因此,虽然鸟的主题是最为出色的一种原型,但是它在列奥纳多的幻想中的存在依旧证明不了什么。因此,我们必须寻找的主题可能不为梦者所知,但是却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其梦中功能性地运作,以致它正好吻合于从历史渠道获知的原型的运作。
我们所需材料的另一源头将见诸“积极想象”(active imagination)之中。我这样讲,意指的是由蓄意的专注所引发的一系列幻想。我已经发现,种种未被认识的、无意识的幻想的存在会增强梦的频率与强度,以及当这些幻想被变为意识时,梦便会改变其性质,强度减弱、频率降低。我因此得出了梦里经常有“期望”成为意识的种种幻想的结论。梦的源头为受压抑的本能,它们有一种影响意识的自然倾向。在这一类型的病例之中,患者被赋予的任务仅仅是冥思似乎非常有意义于他的幻想的任何片段——也许是一个偶然的念头,或者他在梦中意识到的什么东西——直到其内容即它所根植于其间的有关连带材料变得直观起来。这并非是一个弗洛伊德为释梦目的推荐的“自由联想”(freeassociation)的问题,而是通过考察以自然方式将自身补充到片段之中的深层幻想材料对幻想进行阐释的问题。
这里并非是开始对方法进行技术讨论的地方。仅需说明的是,幻想的综合结果释放了无意识,制造了富有原型形象与联想的材料。很显然,这种方法仅能运用于某些经过精心选择的病例之中。这种方法并非全无危险,因为它可能把患者带离现实太远。因此,对不加思考的应用进行警告是恰当的。
最后,原型材料的非常有趣的源头将见诸于偏执狂患者的幻想之中、迷睡状态的幻想之中,以及三到五岁这一童年初期的梦之中。虽然这样的材料十分丰富,但是它们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引证出令人信服的神话相似物。当然,仅仅把关于蛇的梦与蛇的神话故事联系起来是不够的,因为谁能保证梦中的蛇与神话场景中的蛇的功能意义一致呢?为了使比较有效,我们必须知道个别象征的功能意义,然后探寻表面相似的神话象征是否有相似语境,以及是否因此有相同功能意义。确立这些事实不仅需要繁琐艰辛的研究,而且同时是令人生厌的阐释主题。因为象征不能脱离语境,人们必须进行或个人性质的或象征性质的无遗漏描述;事实上,这在一次演讲的框架内是不可能的。我已经冒着把半数听众送入梦乡的危险,反复对此进行了尝试。
虽然此间被我选作例子的病例业已发表过,但是因为它的简短使它特别适合于说明,所以我依旧要选用它。而且,我还会补充一些上次发表时被略去的评论。 [2]
大约是在1916年,我在一位已经接受过多年治疗的妄想狂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遭遇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幻想。这位患者青年时代伊始一直受此困扰,无法治愈。他曾在一所国立学校接受教育,后来受雇为办公室职员。他并无特殊天赋,而且我本人那时也对神话学或者考古学一无所知,所以该情势并未引起丝毫怀疑。有一天,我发现患者站在窗前,摇头晃脑地对太阳眨巴着眼睛。他让我也这么做,因为我将因此看到趣味横生的东西。当我问他看到了什么时,他对我什么也未能看见惊讶不已;他说:“你肯定看到了太阳的阴茎——我把头前后晃动时,它也跟着动;这就是风的开始。”很自然,我浑然不解这一奇怪的想法,但是我把它记录了下来。大约四年以后,在我进行神话研究期间,我偶然发现了已故著名哲学家阿尔布莱特·狄特里希(Albrecht Dieterich) [3] 的一本著作;它使我对这一幻想有了新的认知。这本出版于1910年的著作讨论了巴黎国立图书馆里的一部希腊手抄本。狄特里希认为,他在一部分抄本里发现了一种密特拉教(Mithraic,又译蜜特拉教)仪式。毋庸置疑,这部手抄本是一个施行某些咒语的宗教规定,密特拉神于其间获得了命名。它源自神秘主义的亚历山大学派,相似于莱顿(Leiden)草纸文稿与《赫姆提卡文集》的某些段落。在狄特里希的著作中,我们可以读到如下指示:
如果你在阳光下呼吸,尽你所能地呼吸三次,你就会感觉到自己被提升起来,朝着高处行走;你将似乎是处于半空之中……有形诸神的道路将通过作为圣父的太阳的圆环显现出来。所谓的管子(tube),即救助之风,也是同样的。因为你会见到太阳的圆环下悬垂着一段看起来像管子的东西。似乎有一股强劲的东风正在朝西部吹。但是如果有另一股风朝东方吹,你同样会见到按此方向旋转的异象。

很显然,作者旨在让读者体验到他曾有过的异象,或者至少是他曾相信的异象。读者要么被引入到作者的内心宗教经验之中,要么——这似乎更加可能——被引入到斐洛·犹大乌斯曾作过当下解释的那些神秘社团之一。此间所召唤的火神或者太阳神这一形象酷似诸多历史形象,比如《启示录》中的基督形象。因此,它也一如所描述的仪式行为,比如对动物声音的模仿等,是一种“集体表象”。这一异象根植于具有显在迷狂性质的宗教语境,描述一种被引入上帝的神秘经验之中的情形。
我们的患者大约比我年长10岁。在他的妄想自大狂之中,他自以为是集上帝与基督于一身。他对我的态度是屈尊俯就的态度;他之所以喜欢我,也许是因为我是唯一对他的深奥难懂的思想有所同情的人。他的幻想主要是宗教性的;当他邀请我像他那样对太阳眨巴眼睛、摇晃脑袋时,他显然是在期望我分享他的异象。他扮演的是一位神秘圣人的角色,而我则是一名新教徒。他觉得他自己就是太阳神,把头前后晃动便可制造出风。进入上帝的仪式性转换通过伊西丝密宗的阿普列乌斯以及赫利奥斯太阳神崇拜的形式得到了证明。也许“救助之风”的意义无异于具有生殖力的灵气;灵气从太阳神那里流入灵魂,使它开花结果。太阳与风的联系时常出现在古代的象征体系之中。
现在必须证明的是,这并非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病例的纯粹巧合。我们因此必须证明,风管与上帝或者太阳相联系的思想自主地存在于这些证据之外,以及它也发生在其他的时间与其他的地点。事实上,现在已发现有描述玛利亚受孕的中世纪油画:一根管子或者水管从上帝的宝座上垂下来、伸进她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一只鸽子或者童年基督翩然飞下。鸽子表征受孕的动因,以及圣灵(Holy Ghost)之风。
现在,绝不可能的是,患者对类似四年之后出版的希腊手抄本之物有任何了解;几乎没有可能性的是,他的异象与圣母受孕的罕见中世纪表征有任何联系,即使是他曾借助难以置信的不可能的机会看到过这样一幅画的复制品。患者在20岁刚出头时便被诊断为精神病人。他从未旅行过。而且在他的家乡苏黎世,公共艺术馆里并没有这类画作。
我提出这个病例,目的并非是要证明这个异象是一种原型,而是仅仅在于以最为简单的方式向大家表明我处理这一程序的方法。如果我们仅有这类病例,调查的任务便会相对容易,但实际的证明要远为复杂得多。首先,必须把某些象征足够清晰地分离出来,以便它们可被识别为典型现象,而非仅仅是偶然事件。这一步的完成依赖于为典型形象而考察一系列梦,估计得有好几百个,以及依赖于观察它们在这一系列中的发展。相同的方法可以施用于积极想象的产物之中。因此建立同一形象的某些连续性或者变化是可能的。人们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在梦或者异象系列中的行为给人以原型的印象。如果可支配的材料得到了细致观察并且足够充分,人们就会发现关于某种类型所经历的变化的有趣事实。无论是这一类型本身还是其变体,都可以借助比较神话学及人种文化学的证据得到证明。我已在其他地方描述过调查的方法,
 并已提供了必要的病例材料。
并已提供了必要的病例材料。
[1] 《列奥纳多·达·芬奇及其童年记忆》( 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第4部分。
[2] 《力比多的转换与象征》( 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 ,首版于1912年)。[英译名《无意识的心理学》( Psychology of Unconscious ,1916年)。参见《转化的象征》(修订本),第223页第149段及其以后段。——英编者]
[3] 《一种密特拉礼拜仪式》( Eine Mithrasliturgie )。[正如作者后来所了解到的,1910年的版本其实是第二版,因为1903年便已有了第一版。然而,患者在1903年以前已患病多年。——英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