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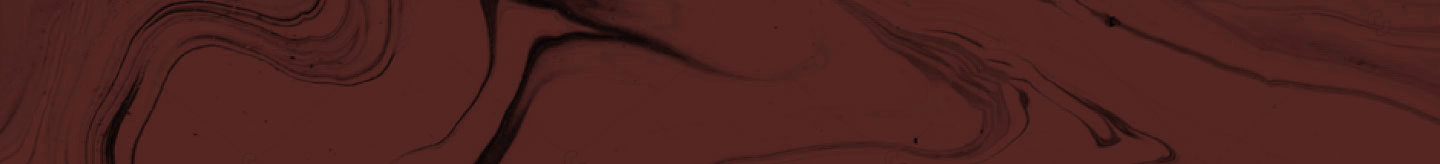
我在美国南方视察的情形,在前几次的《忆语》里已说得差不多了。我由塞尔马回到柏明汉,于六月底经华盛顿回到纽约。离开柏明汉时,最难舍的当然是几位美国男女朋友的深挚的友谊。我临走时向他们问通信处,才知道他们不但开会的地方常常更动,住的地方常常更动,就是通信的地方也是要常常更动的。他们在工作上的技术的细密,于此可见一斑。随后M女士终于给我一个通信地址,这地址就是邮政局,他们叫做General Delivery,由她在邮局留下一个姓名,邮局把她所留下的姓名依字母编列备查,以后便可由她自己到邮局取信,不必由邮差送给她,这样一来,她的地址便不会给任何人知道了。可是如果有人知道了她在邮局所留下的姓名,却尽可以到邮局去冒领她的信,因为邮局只照来者所说的姓名付信,并不认人的。所以就是她在邮局所留下的姓名(当然已不是她的真姓名),也是严守秘密,不轻易告人的。我存着这个通信处,到纽约后屡想写一封信去谢谢他们,但是有许多美国朋友知道南方情形的,都劝我如果没有特殊事件时还是不写的好,因为非常反动的南方,对于纽约来信是检查得很严的。
我临走时,他们都紧握着我的手,许久许久不放,再三叮咛郑重而别。十几天相聚的友谊,竟使我感觉到是几十年患难交似的。。为着环境的关系,他们当然都不能到车站来送别,所以我是一个人到火车站去的。我起先并不知道由柏明汉往华盛顿的火车有两种,一种是装有冷气管的(他们叫做air-conditioned),一种没有,有的要加多几块钱车费。我只注意到华盛顿的时间,糊里糊涂地买了一张“冷气火车”的车票(买的时候并不知道),无意中尝尝美国较近才有的“冷气火车”的滋味。上车的时候,是在夜里,气候还不怎样热,但是进了火车,就觉得格外的凉爽。我“阿木林”似的,最初很觉得诧异,何以气候变得那样快,后来仰头看到车里壁上的广告,才恍然知道这是美国新近的“冷气火车”,才知道是此生第一次坐在有冷气管的火车里,不禁惊叹物质文明的日新月异。同是“冷气火车”,仍然是黑白分明,即白人乘的那几节车,黑人不敢进来,黑人是另有一节车的。我是非黑非白的黄种人,但依例却坐在白人的车里,这是在以前就说过的。我屡次看见黑人上车后跑错了,直闯到白人的车里来,但是当他们的头一钻进之后,知道错误,立即飞快地回头,有的不提防地向里走了几步才觉察,觉察后就三步作两步地向外奔,好像犯了什么罪恶似的,那种踉跄的滑稽态,初看起来令人觉得好笑,但是仔细思量之后,却是很可悲悯的。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在精神上是有着很大的刺激,黑人里面略有觉悟的人没有不对你表示痛心疾首的。黑人所以遭到这样的惨遇,无非因为他们是被克服的民族,我看着这样的情形,想到自己祖国当前所处的境遇,真是百感丛集,在火车里一夜都没有睡着。我买不起卧车票,原来是预备坐着打磕睡的,这样引起了万端的心事,想来想去,连磕睡都打不成了。挨到天亮,等一会儿,由窗口望见炎日当空,烈光四射,可是因为车内有着冷气,还是凉飕飕的,没有想到外面气候已热到什么程度。但是因为一夜没有睡,心绪又不好,也没有想到坐在这冷气里有着怎样的受用。
下午到了华盛顿,一踏出了车门,才感觉到外面气候的奇热,和车内比起来好像是两个世界。我的疲倦的身体,好像在炎夏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什么东西,一冷一热,在刹那间趋于极端,倏然间觉得头昏目眩,胸际难过得厉害,勉强提着一个小提箱,孤零零懒洋洋地走出车站,简直好像就要立刻昏倒似的。我心里想这样死去,未免死得太冤罢,赶紧转一个念头,勉强跑到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去,一踏进房里,就不顾一切地躺在床上,好像昏去似的躺了两三小时,才渐渐地恢复转来。
在华盛顿因为要调查侨胞的生活,又耽搁了两天。在华盛顿的华侨约有六七百人,也有所谓唐人街。其实不过在一条街上有着十几家中国人开的店铺。在唐人街的一般现象是洗衣作,菜饭,中国式的药材铺,和中国式的杂货店。华盛顿也不能例外。这里有一家较大的杂货店,店面有着似乎中国庙宇式的建筑,漆得红红绿绿的。据陪我同去视察的朋友说,这家铺子的老板是华盛顿唐人街的一个重要领袖,娶了一位美国妻子。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已近午时,他才从床上起来。我和他谈谈当地侨胞的状况,提到赌的情形,他说最近赌这件事可说是没有的了。一踏出了他的门口,陪我同去的那位朋友就不禁失笑,因为他是很熟悉当地情形的,并且很知道那位“重要领袖”的生活;据他所知道,那位“重要领袖”到午时才起来,就是因为他前一夜是赌到深夜才睡觉的!我说大概做“重要领袖”的人不得不顾面子,可是欺骗不过熟悉内部情形的人。
赌在唐人街的流行,当然也有它的原因。美国人要想发财,可以在做“大生意”上转念头,中国人因资本微薄的关系,虽有极少数的三两个人也走上这一条路,但是大多数都不过是做小生意的,从小生意里发大财是很难的,于是往往视赌博为发财的唯一捷径。而且他们缺乏相当的娱乐,赌博也是一条出路,所以有许多都在这里面寻觅他们的桃源。但是在那里的赌博却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是有着“堂”的“领袖”们包办的。由这里面引起的纠纷,往往发生所谓“堂斗”。“堂斗”发生的时候,美国的当地官署势必出来干涉,于是在“堂”方面便派出所谓“出番”者(据说就等于“外交家”),和美国的当地官署接洽,用运动费来和美国的当地官署狼狈为奸,他便可从运动费中大赚其“康蜜兄”(佣钱或回扣)。这种“出番”当然是“肥缺”,所以都是由“堂”的“领袖”担任。因此“堂斗”发生,便是“领袖”们发财的机会。既是“斗”当然需要打手。这类打手,他们叫做“斧头仔”;追究这名词的所由来,是因为在数十年前,他们用的武器是斧头;后来物质文明进步,有手枪可用了,但是他们在名词上还是同情于复古运动,所以仍用旧名。这类打手最初多为失业的人,由堂的“领袖”时常借钱给他,债务渐积渐多起来,无法归还,便须听受“领袖”的指挥,遇着有事需要打手的时候,便被使用。打死一人,还可得到酬报一千元或五百元。打死别堂的“领袖”,可得到酬报万元。
据说在华盛顿半年来(就当时说)也有了几个中国妓女,堂的“领袖”们不但包办烟赌,而且也包办妓女,所以堂的“领袖”往往也就是老鸨!“领袖”这个名词竟有机会和老鸨连在一起,这真是“出乎意表之外”的一件奇事。美国因受经济恐慌尖锐化的影响,近年来妓女的数量大增,因人数大增,出卖的价格也不得不特别减低。据说在华盛顿的美国妓女(美国没有公娼制度,所以都是私娼),从前一度春风须四五个金圆的,近年已减低到两个金圆了;但是在那里的中国妓女因为不是“自由”的身体,多受一层剥削,仍须四个金圆,不能和美国妓女竞争,生意也不及以前了。
我和华盛顿相别了,但是我和华盛顿相别的时候,不及对于柏明汉的那样依恋不舍,虽则华盛顿比柏明汉美丽得多。这无他,因为在柏明汉所遇着的几位美国男女朋友的深挚的友谊使我舍不得离开他们。我由华盛顿回到纽约的途中,坐在火车里,种种念头又涌现在脑际。最使我想到的当然是这次在美国南方所看到听到的关于“变相的黑奴”的生活。在美国的劳工大众受着他们资产阶级的榨取和压迫,诚然是很厉害的,关于这方面的种种情形,我以前和诸君也谈过不少了。但是在美国的黑人(最大多数都是属于劳工阶级)所受的榨取和压迫更厉害得千百倍,因为他们在表面上虽称美国为他们的祖国,但是他们的民族实在是整个的处于沦亡的地位,他们在实际上实在无异做了亡国奴。所以他们在法律上,经济上,文化上,以及一切的社会生活,都不能和美国的白种人立于平等的地位。在美国南方贯穿十几州的所谓“黑带”;黑色人口只有比白种人口多,但是因为等于做了亡国奴,人口虽多,还是过着那样惨苦的生活。可见领土和主权不是自己的时候,人数虽多还是无用的。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一点。黑人里面有不少觉悟的前进分子,已在积极主张“黑带”应该自立,成立一个独立的黑国,这件事说来容易,要真能使它实现,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既经没有了的领土和主权,要再得到是很难的。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又一点。想到这种种,已使我们做中国人的感到汗颜无地了。我回想所看见的黑人的惨苦生活,又不禁联想到在中国的黄包车夫(或称洋车夫)的生活。老实说,人形而牛马其实的黄包车夫生活,比美国南方的“变相的黑奴”的生活,实在没有两样!我们只要想想,在炎日逼迫之下,或是在严冬抖战之中,为着一口苦饭,几个铜子,不得不弯着背脊,不顾命地奔跑着,这样的惨状,人们见惯了,也许熟视无睹,但是偶一回想,就是那些在“黑带”做“变相的黑奴”的苦作情形,也不过这样吧!都是把人当牛马用!我坐在火车里独自一人默念到这里,虽然这躯壳是夹坐在“白”的车厢里,望望那“黑”车里的黑人们,却不免感到说不出的惭愧,因为大多数中国苦同胞的“命运”(做苦工过着非人生活的当然还不限于黄包车夫),并不比他们高明些!
回到纽约了,好像回到了临时的家乡,但是再耽搁一星期又要和它离别了。在离别前,除继续搜集研究材料外,对于那里的华侨情形,也做了比较详细的调查。
关于纽约唐人街的情形,我以前已略为谈过了,现在只想再谈谈关于组织方面的大概。我在上面提及“堂”,在纽约有所谓安良堂与协胜堂。推溯这两“堂”之所由来,听说最初到美国去的华侨格外穷苦,加以美国移民律限制的苛刻,各人当然都无力带妻子同去,成为无家可归的人。穷苦和无知又往往结不解缘,他们在偷闲的时候便聚赌,一言两语不合便在赌场里打架。后来有些人积下了一些钱,由不顾一切的穷光棍而变为有些钱的商人了,于是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计,觉得有镇压一班穷光棍的必要,便联合他们的一派组织安良堂,一班穷光棍也组织协胜堂以为抵抗。所以最初协胜堂颇有反抗压迫的意味。但是后来各堂各占一街(在纽约的唐人街就只有两条街),认为各有各的势力范围,包庇烟赌和娼妓,同样地由少数人所操纵而腐化起来。华侨的总组织有所谓中华公所,中华公所的董事会在表面上是由各团体(主要的是各会馆)分派代表,及所选出的主席、书记和通事所组织,在实际上却是由两个主要的团体轮流主持,一个是宁阳会馆,由最占势力的台山人组织的;一个是联成公所,是由台山以外的数十县的广东人和少数他省人组织起来的。所谓主席、书记、通事等等,都由这两团体轮流分配。所谓“堂”却在后面操纵各团体,由此操纵中华公所的一切。就一般说,堂是任何人可以加入,会馆则有的以几县的区域为范围,有的以族姓为标准,有的在一个会馆里还分派。简单说一句,他们的组织还是道地十足的封建的遗物。堂的“领袖”以前称会长,中国“革命”后主席盛行,他们也改称“主席”,各堂内还分有小派。
两个“堂”各据一条街,做各个的势力范围,例如有甲堂的人在乙堂的势力范围内开一家店,乙堂便出来干涉,甲堂同时要出来保镳,先来调解,讲条件,条件讲得不合,便是堂斗的导火线,大家派出打手来打个你死我活。这种“地下”的权力是出乎美国警察势力范围之外的。堂斗厉害的时候,唐人街都不得不罢市,美国人也相戒不要到唐人街的范围里面去。受损失最大的当然是华侨群众;无论谁胜谁负,群众都得不到什么好处,分赃的好处只是归于少数所谓“领袖”。在只求安居乐业的华侨群众是用不着堂斗的,是不需要堂斗的,但是因为组织为少数人所操纵,只得眼巴巴望着他们胡闹;这好像国内的老百姓用不着内战,不需要内战,而军阀们却用内战来为少数人争权夺利一样。大多数的华侨群众都是很勤俭刻苦的老实人,徒然供少数人的榨取剥削罢了。美国的劳工界的组织,如全国总工会及若干分会之类,也在少数官僚化的人们的手里,近数年来美国劳工运动的重要趋势是“群众运动”(rank and file movement),就是要把组织从少数人手里夺回到群众自己的手里来。其实华侨的组织也有这种的必要。华侨的组织不健全,当然不就是大多数华侨的不兴,犹之乎美国劳工组织的官僚化,不就是大多数美国工人的不兴,这是要分别清楚的。据我所知道,纽约华侨的团体中有个新兴的衣馆联合会,已有四千家衣馆加入(纽约一向有华人开的衣馆六千家),还在继续进行,便是一个由群众自己组织的团体。可见“群众运动”在他们里面也略有端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