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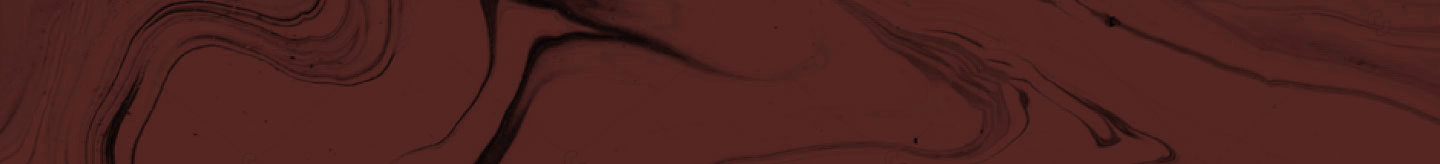
记者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出国,最近于八月廿七日回国,光阴似箭,转瞬间已过了两年。关于海外的观感,曾经略有记述,以告国人;已出版的有《萍踪寄语初集》和《萍踪寄语二集》两种。去夏有美国全国学生同盟(National Students League)所领导的旅行团,赴苏联研究游历,途经伦敦,记者临时加入,同往苏联视察约两个月,回伦敦后,草成《萍踪寄语三集》,全书约十八万字,对于苏联在物质和文化方面的建设,有颇详的评述,不久希望有机会就正于读者。今年五月间由伦敦赴美视察约三个多月,因在苏联和美国旅行团中的旅伴相处了许多时候,在那里面交到了不少思想正确的好友,所以这次在美国视察,很得到他们的有力的介绍和热诚的指导。现在“萍踪”略定,很想就记忆所及,记些“忆语”出来,陆续在本刊上发表,很殷切地盼望读者诸友教正。
在国外研究视察,在私人方面,虽随时随地可遇到诚挚的友谊,但一涉及民族的立场,谈到中国的国事,乃至因为是做了“材纳门”(Chinaman),就一般说来,随时随地可以使你感到蔑视的侮辱的刺激,换句话说,便是种族的成见(racial prejudice),把中国人都看作“劣等民族”的一分子。除了思想正确,不赞成剥削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人外(在这里面我要承认有不少是我要诚恳表示感谢的好友),受惯了帝国主义统治阶层的麻醉的一般人,对于种族成见,根深蒂固,几已普遍化。在这一点,各国对中国人的心理,原都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差异,所不同者,有的摆在面孔上,有的藏在心里罢了。在欧洲各国里,以英国人的种族成见较深。当然,你和他们的知识阶级中人谈谈,你到商店里去买东西,或和你所认识的英国男女朋友来往等等,并不感觉到有这样的刺激。你如遇着他们里面的老滑头,还要对你满口称赞中国五千年的老文明。但你如能冷眼旁观一般的态度,便常能发现种族成见的存在。试举一件我所亲历的小事做个具体的例子。记得在伦敦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和一位中国朋友去看一处开演的苏联的著名影片,跑了很远的路,才到了目的地,不料到时才知道改期,只得打算回家。刚从那处走出几步,看见附近有一处开着跳舞会。这位朋友说,跑了这样远的路,未看着什么,似乎不值得,何妨跑进去看看。我们进门之后,见有一人在一张办公桌旁主持登记和收费的事情;询问之后,才知道这个跳舞会是多半住在附近的职工所组织的,有的是店员,有的是机关里的职员,男女都有。会员没有限制,只须缴纳若干会费,每逢星期六都可来参加,并说我们倘欲参加也可以。我同去的这位朋友建议进去试试看,藉此见识见识。我说我们未带有女朋友来,没有舞伴。那个执事说,来的人有男有女,不全是带有舞伴,尽可临时凑合的。我又对我的朋友说,除非我们带有女友,或是参加所认识的团体或所认识的英国朋友的交际舞,恐怕要感到不愉快罢,因为一般英国人的种族成见特甚,我是早有所闻的。他说,就是有种族成见,我们也不妨乘此机会进去看看他们的成见深到什么程度。我看他那样的好劲儿,便缴了会费(每人似为两个半先令),一同跑进舞厅。参加的男女已有四五十人。我们两人也照例约请舞伴,她们虽没有什么无礼的表示,但总是说句“I am sorry”,婉辞谢绝。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自讨没趣”的勾当,其窘可想。可是我的这位朋友却富有试验的精神,他在美国和英国都有了好几年的经验,比我老练得多,向这个女子约请吃了一鼻子的灰,便改向那个女子约请。试了三四个之后,居然有一个被他请到了。我觉得他那样“迈进”的精神却也不无可取,说来好笑,竟唤起不甘落后的情绪,也鼓起勇气(其实也可以说是厚着脸皮!)依法炮制,结果在硬着头皮碰到几次钉子以后也得到一个舞伴。我们虽都算“排除万难”达到了目的,但是看去对方仍似不很自然。猜想对方的心理,也许自己即觉得不在乎,还不免顾虑到旁人说闲话,以为你怎么肯和“材纳门”——这名词在他们是觉得包含着一切可厌可贱的意义——周旋起来呢!我饱受了一肚子的闷气,不久便溜。出来以后,我的朋友见我好久静默无语,好像受了电击,失却了知觉似的,他说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值得观察的,至少可使你深切地知道“材纳门”在海外所受到的待遇,可使你深切地知道他们对于“材纳门”的种族成见的一斑。
不久以后,有一位从美国经伦敦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某君,彼此原不相识,有一次在一个餐馆里因座位拥挤,偶然同桌,略略接谈,知道他是要乘回国之便,到欧洲玩玩的,在伦敦只有几天耽搁,承他交浅言深(他只问了我的姓,我的名字职业他都不知道),他所最急切关心的是要寻得玩玩英国女人的门径,我深愧对这门学问未曾用过研究工夫,很使他失望;他降格以求,叫我介绍有舞女可雇的英国跳舞场,我说曾在几条马路上看见有跳舞场在门口高悬着招牌,可惜我自己没有工夫,也许是没有心绪,到里面去尝试,只不过把地名和怎样走法告诉他。过两天又无意中碰到他。承他很坦白地告诉我,说他已到过几处有舞女的跳舞场;但是她们都把冰冷的面孔对待;他对她们谈几句话,她们也像要理不理的样子;他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不想再去了。原因当然是因为他是“材纳门”,虽则他的衣服穿得很漂亮。
在欧洲各国中,英人的种族成见比较地厉害,我曾和好几位由欧洲大陆到英国的朋友们谈起,他们都承认。我未往美国以前,正在打算赴美的时候,常听人谈起美国人对于种族的成见比英国人更甚。我在国内读英文的时候,教师多半是美国人,我在国内所曾经肄业过的南洋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不但有不少美国的教授,而且这两个学校的毕业同学大多数都是美国留学生,从他们听到不少关于美国的情形,却不大听见“材纳门”在海外所遭受的不平的待遇;去夏在莫斯科认识了不少美国朋友,除极少数硬死派外,给我的印象都很好:所以我对于美国的印象原来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愉快的意味。但在未渡大西洋以前,在伦敦也就受到两次美国人待遇“材纳门”的刺激。
一件事是这样的:我在伦敦所住的一个英国人家(我曾经迁移过寓所,不是《萍踪寄语初集》里所说的),主妇是一位很慈爱诚恳的六十八岁的老太太(健康如四五十岁),她家里是第一次租给中国人,我也是她家里的唯一的中国房客。我们很谈得来,相处很相得。她和他的丈夫,一个女仆,和她的一对另居的时常来往的儿子媳妇和外孙,对于中国人原来没有机会接触过;他们从我所得的印象,似乎觉得和在惯于糟蹋“材纳门”的报章杂志上所得的不同,所以他们这一伙儿对于“材纳门”很有好感。(在各国除硬死派和曾经久住中国的牧师教士商人以及其他为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张目的人们,其余一般人,只须我们和他们有相当接触的机会,往往可以消除或减少他们对“材纳门”的成见。)有一次有一个美国中年妇人带了一个小女儿到英国旅行,经友人介绍,向我住的这个人家租了一个房间,说明住一星期。她和她的女儿来住以后,我因事忙,早出迟回,并未见过面。当晚房东老太太偶然和她谈起我,承她(房东)满口赞誉,而这位美国妇人听见有一个“材纳门”住在这家里,虽则她从未见过面,谈过话,即毅然决然地对她(房东)说道:“我不能和‘材纳门’住在一个屋子里!”第二天一早就匆匆忙忙地搬走!在当时,房东老太太并不将这件事告诉我,她只是暗中诧异,觉得“材纳门”何以这样使人避若蛇蝎,使人这样地厌恶!痛恨!
过了几时,有两个中年姊妹(英国人),从卜来顿(Brighton)到伦敦来游历,也经友人的介绍,到这家来暂住。来的时候,房东老太太鉴于前次的麻烦,首先声明在她的家里已住有一位“中国的君子人”(这是她这样说,原文是“Chinese gentleman”)。她的意思是:事实如此,你们愿住就住,不愿就拉倒,免得怪麻烦。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那两位姊妹很高兴地回答道:“好极了!我们要约个时候和他谈谈。”原来这两位姊妹是喜欢研究中国艺术的,所以是个例外。有了这件事以后,房东老太太才连带把前次触霉头的一件事告诉我。
还有一件事可以谈谈。由欧洲赴美国游历的中国人,所受的待遇,比别国人也有些不同。别国人只须有本国护照经过美领事的签字,就算了事;中国人还另有专为“材纳门”而设的所谓“第六项”(“Section Six”)的规定:经过伦敦的美领事的严格查问(假使是由英国去),认为无问题后,原带的中国护照不够,要另备单张护照,并要先由他用公文通知纽约(假使你是在纽约登岸)的移民局备案,然后这个“材纳门”到时才准登岸。我到伦敦美领署时,因为有得力的证明书,跑了两次,第二天就领得护照,事后据朋友说,这已算是最迅速而予以便利的了。美副领事问的许多话里面,有一句是问我有没有极端的政治见解和会不会有危害美国政府的行为。
我未往美领事署办护照手续以前,先往通济隆公司定舱位,据说有美国船名叫门赫吞号(Manhattan)于今年五月九日由伦敦开往纽约,有空余舱位,我便定了一个“旅客舱”(依例买有折扣的通票至少须乘“旅客舱”)。到美领署办护照时,照例要说明乘什么船赴美,这船到美的日期等等,美领事在通知美国移民局的公文中都须一一详细注明。不料我的护照手续已经办好,美领署的公文已寄往纽约移民局之后,通济隆忽由电话告诉我,说美国船舱位已满,只得请我改乘五月十一日开行的德国船欧罗巴号走。我定舱位时,该公司很无疑地答应有,何以忽然说已满,我已不懂。但时日已迫,来不及先往该公司办交涉,而且也没有想到这所谓“已满”是另有其特别原因(见后),所以就赶往美领署叫他们再替我向移民局去一道公文,因为倘若船名不符,船到美的日期不符,虽有护照,移民局还是不准登岸,要把你捉到实际等于牢狱的“天使岛”(“Angel Island”)上去吃苦头的。那位美副领事听说我要改乘他船,又须改船期,面孔顿时放下来,大不高兴说:“我们的公文已发寄了,你是太噜囌了!”我说这不是我的噜囌,是通济隆的噜囌。他不相信,立刻拿起电话机,问那个美国船公司,回话说舱位并未满。他听了更不高兴,叫我自己再往通济隆接洽。我以时日已迫,叫他立刻打电话向通济隆一问究竟。后来他在电话里听该公司的职员讲了许久的话,才把态度换过来,对我说门赫吞号的舱位有没有,一时说不定,只得让我乘德国船走,他们只得另去一道公文给美国移民局。这样一来,这件事总算解决了,但却使我如陷入五里雾中:通济隆在先很不踌躇地说一定有舱位,何以忽然说已满?美副领事在先听我要改船及船期,很不高兴,形诸辞色,后来经电话里的一顿叽哩咕噜,忽然又改换态度?我终觉不懂,所以又跑到通济隆去问个明白。该公司的那位职员,因我屡次由英国赴欧洲大陆游历,来往车票的事都由他办理,所以我们两人因渐渐相熟而有了相当的友谊,经我究问原因之后,他竟侷促嗫嚅,现出不便解释的样子,只说“美国船公司对于中国人另有他们的规则,我们虽觉得没有道理,只得照办……”我说我不会怪你,却要听听所谓“规则”究竟是什么,他说:“如你不见怪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经他说明之后,才知道美国船向例把“材纳门”隔离,不许和白种人同舱房;所以要末有单独一人的舱房,不妨住一个“材纳门”,要末有几个“材纳门”一同住入一个几人的舱房。这次门赫吞号的单独一人的舱位已没有余剩,所剩的只有数人同住的舱房,其先他们未注意我是“材纳门”,后来忽而发觉,所以把已答应的舱位临时取消。这个职员大概因为和我有了相当的友谊,说明之后,颇表现替我难过或不平的神情,连说“没有道理”。
以上随意谈到的是帝国主义麻醉下的种族成见的几个例子,诸如此类的事实当然不少,我相信在海外旅行过的我国人,如肯静心默察,当有同感。
平心而论,我们对于这种族成见,如作进一步的分析,明白它的来源,对于有这样成见的一般人的本身,却也用不着怪他们,因为他们只是受了长时期的帝国主义的麻醉作用。帝国主义者利用他们所直接间接控制的教育,书报,电影,以及其他种种方式的宣传机关,把被压迫的民族——尤其是“材纳门”——形容得如何如何的卑鄙,龌龊,野蛮!同时可以反映出他们自己的“文明”,以“证实”他们的“优越民族”确有侵略剥削“劣等民族”的当然权利,使久受他们麻醉的本国民众俯首帖耳做他们的侵略剥削的工具。关于这类事实,举不胜举。像英国的小学里,教师对小学生谈到“材纳门”,还是灌输妇女缠脚,溺女孩,抽大烟的印象。像美国在新闻界占很大势力的赫斯特报纸(Hearst newspaper)就利用他分布全国的数十种日报和刊物,尽量糟蹋“材纳门”,把中国人写成卑劣不堪的该死的民族。又像我国有一部分人所崇拜的希特勒,在他所著的传播很广的《我的奋斗》一书的原文里,就把中国人和“黑奴”连在一起,尽情丑诋。
但是世界向着光明的新运动是一天一天地向前猛进着,已有一部分的人们不再受帝国主义的麻醉作用而醒悟,向着剥削阶层进攻了!民族成见的消除,和光明的新运动成正比例,是必然的趋势。所以我们徒然怀恨或怨怼是无益的,要知道努力奋斗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