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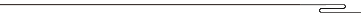
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
——李清照
姚禾和瓣儿、池了了离了范楼,在附近找了家茶坊。
他们坐到最角落一张桌上,瓣儿和姚禾面对面,池了了坐在侧手。
“先说好,茶钱我来付。”瓣儿说。
姚禾听了,想争,但看瓣儿说得认真,知道争也白争,反倒会拂了她的好意,便只笑了笑,心想就先让她一次,后面再争不迟。
池了了却说道:“这事是我请你来帮忙,怎么能让你破费?”
瓣儿笑着道:“既然我接了这件案子,它就是我的事了。你赚钱本来就不容易,为这事又要耽搁不少。你我姐妹之间,不必争这点小事。古人肥马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何况这点小钱?你若连这个都要和我计较,那咱们就各走各的,也不必再查这个案子了。”
池了了忙道:“你和我不一样,哪里来的钱呢?”
“我虽在家里,可也没闲着,平日又没什么花销。你放心吧,我都已安排好了——”瓣儿说着将手边一直提着的小包袱放到桌上,打开包布,里面一个红梅纹样的漆木盒,她揭开盒盖,从里面取出一个锦袋,沉甸甸的,她又解开袋口,露出四锭银子,“今早,我刚卖了四幅绣作,得的这些银子,专用来查这个案子,应该足够了。咱们三个在这里说好了,以后再不许为钱争执,齐心协力找出真凶,才是正事。”
池了了笑了笑,却说不出话,眼中有些暖湿。姚禾心想,她奔走风尘,恐怕很少遇到像瓣儿这般热诚相待的人。再看瓣儿,她重新包好银子,而后握住池了了的手,暖暖笑着。这样一副小小娇躯内,竟藏着侠士襟怀,姚禾心中大为赞叹激赏。
他自幼看父亲摆弄尸体、研视伤口、勘查凶状,习以为常;稍年长一些后,父亲出去验尸,都要带着他;过了几年,他已轻车熟路,自然而然继承父业,做了仵作。
原本他和其他孩童一样,也爱跑跳,坐不住,但因时常研习那些常人惧怕之物,同龄之人都有些避他,渐渐地,连朋友都没了。长到现在,也早已惯于独处,除了应差验尸,回到家中,也经常找些猫狗鼠兔尸体,在家里观察记录。此外,除了读读书,再无他好。人们笑他是一堆死尸中的一具活尸。他听了,只是笑一笑,并不以为意。
那天,听到敲门声,他放下手中的一具兔子尸体,出去开门,见到了瓣儿。
当时天近黄昏,瓣儿一身洁白浅绿,笑吟吟的,如同一朵鲜茉莉,让他眼前一新,心里一动。
等攀谈过后,他更是心仪无比,这样一个女孩家,竟要自己去查凶案,而且话语如铃,心思如杼,他想,世上恐怕再没有比这更赏心悦目的女子了。
他生来就注定是仵作,就像自己的名字,是父母所给,从来没觉得好或不好。但那天茶坊别后,他生平第一次对自己这身份有了自卑之心。他只是一个仵作,而瓣儿则是堂堂皇室宗族贵胄,虽然瓣儿言谈中毫无自高之意,但门第就是门第。
不过,他随即便笑着摇摇头,瓣儿姑娘只是找你帮忙查案子而已,她或许只是一时兴起,兴头过去,便再无相见之理。就算她是真心要查,这案子也迟早会查完。完后,她自她,你自你,你又何必生出非分之想,徒增烦恼?
想明白后,他也就释然了。能和瓣儿多见两次,已是意外福分,那就好好惜这福,珍这时吧。
店家冲点好三盏茶,转身才走,瓣儿就说:“咱们来说正事,我以为,穆柱可能是凶手。”
“穆柱?”姚禾正偷偷瞧着瓣儿小巧的鼻翼,心里正在遐想,她的俏皮天真全在这小鼻头上。听到瓣儿说话,才忙回过神,“哦?说来听听?”
瓣儿望着他们两个,脸上不再玩笑:“这凶案有三处不怕,其一,选在酒楼行凶,却不怕那里人多眼杂;其二,进出那个房间,不怕人起疑;其三,进去行凶,不怕人突然进来。能同时有这三不怕的,只有酒楼端菜的大伯。他们常日都在那酒楼里,熟知形势,而且近便,自然不怕;大伯进出房间,没有人会在意;每个房间的客人他们最知情,若客人全都在房间内,自然知道除了自己,一般不会再有他人来打扰。而那天招待董谦和曹喜的,只有穆柱。”
姚禾听了,不由得赞道:“你这三不怕,很有见地!穆柱做这事也的确最方便。”
池了了却问道:“穆柱为什么要杀董谦?我认识他一年多了,他是个极和善老实的人,从来没有过坏心,没道理这么做。”
瓣儿沉吟道:“至于为什么,的确是首要疑点,人心难测,我只是依理推断,并没有定论,有不妥的地方,你们尽管再说。”
姚禾本来不忍拂了瓣儿的兴头,听她这样讲,才小心说道:“若凶手是穆柱,这里面有个疑点似乎不好解释……”
“什么?”
“他行凶倒有可能,但为何要割下董谦的头颅,而且还要带出去?另外,他们端菜,手中只有托盘,血淋淋头颅怎么带出去?”
“这倒是……”瓣儿握着茶盏,低头沉思起来,“其实还有一点,和曹喜一样,他若是凶手,手上、衣服难免都会沾到血迹,但当天两人身上半点血迹都没有,虽说他的住房就在后院,不过跑去换衣服的途中还是很难不被发觉。另外,照他自己所言,那天临街这面的十间房都客满,是由他一个人照管,必定相当忙碌,并没有多少空闲工夫,若是一刀刺死还好说,再去割下头颅,恐怕耗时太久,难保不令人起疑。最重要的,今天他的神色虽然有些胆怯犹疑,但说起董谦,他似乎并不心虚,更不厌惧,相反,他倒是很敬重董谦,眼里有惋惜之情。这么一看,他应该不是凶手。”
姚禾见瓣儿毫不固执己见,真是难得。又见她如此执着,心想,一定得尽力帮她解开这个谜案。于是他帮着梳理道:“那天进出过那个房间的,所知者,一共有五人,董谦、曹喜、池姑娘、穆柱,还有一位是当天的东道主侯伦。他中途走了,会不会又偷偷潜回?”
“是,目前还不能确定真凶,因此,每个在场者都有嫌疑。也包括了了。”瓣儿向池了了笑着吐了吐小舌头,立即解释道,“我说的嫌疑,不是说凶犯,而是说关联。我听我哥哥说过,这世上没有孤立之事,每件事都由众多小事因果关联而成,所以,这整件事得通体来看,有些疑点和证据说不准就藏在你身上,只是目前我们还未留意和察觉。”
池了了涩然笑了笑:“的确,那天之前,我就已经牵连进去了,而且若不是我多嘴说要去做鱼,董公子恐怕就不会死了。”
“了了,你千万不要自责。目前整件事看来,其实与你无关,若真要说有关,也是凶手利用了你。”
姚禾忙也帮着瓣儿解释道:“我之所以怀疑侯伦,正是为此。那天是侯伦做东道,替董谦、曹喜二人说和,才请了池姑娘你。他真的只是为了劝和才邀请你们三位的?”
池了了道:“开始我也怀疑过侯伦,不过,侯伦应该不是凶手。那件事发生了几天后,我偷偷去打问过他的邻居,那天他中途离开,的确是因为他父亲旧病复发,他邻居看到他跑着进了门,又跑出来找了大夫,而后又去抓药,不久就提着药包回家了,再没出来过。他邻居还去探访过他父亲,说侯伦一直守在父亲病床前服侍。”
瓣儿道:“这么说,侯伦没有太多嫌疑。就算他能借着抓药偷偷溜回范楼,酒楼人不少,大伯们又忙上忙下,难保不被人看到。这件事看来是经过缜密谋划的,他若是凶手,一定不会冒这个风险。”
姚禾道:“看来凶手只能是曹喜。”
池了了也附和道:“对。只有他。”
瓣儿却轻轻摇了摇头:“我始终觉得不是他。”
池了了立即问:“为什么?”
“至少有两点,一、他身上没有半点血迹;二、他没地方藏头颅。不过,眼下不能匆忙下任何结论,我还并未亲眼见过这个人,更不能轻易断定。目前所知还太少,我得去见一见这个人。另外,我还得去拜望一下董谦的父亲,侯伦那里也得去问一问……”
姚禾望着瓣儿,心里偷偷想:真是个执着的女孩儿,她若是中意了什么人,恐怕更是一心到底、百折不回。
池了了执意要陪瓣儿一起去见曹喜。
不管别人怎么说,她始终坚信,曹喜才是真凶。
虽然她和曹喜只见过两面,但只要一想到这个人,她心里不由自主就会腾起一股火。与董谦的敦厚温善正相反,曹喜是她最厌的一类人:傲慢、偏激、冷漠。见到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是——脱下鞋子,狠狠抽他一顿。
因此,她要再当面去看看曹喜,看他如何强作镇定,冷着脸说谎。
两人打问到,曹喜家在南薰门内,离国子监不远,一座中等宅子。
大门开着,池了了和瓣儿走了过去,正好一个年轻妇人出门。
“这位嫂嫂,请问曹公子在家吗?”瓣儿笑着问。
“寻我家大郎啊,你们稍等,我唤他出来。”少妇十分亲切。
不一会儿,曹喜出来了,依然清俊白皙,也依然微皱着眉头,眼露厌意。一看到他,池了了顿时觉得气闷,她狠狠瞪着曹喜。
曹喜先看到她,微有些诧异,连一丝笑意都没有。随即,他又望向瓣儿:“两位找我何事?”
瓣儿笑着说:“是关于董谦的案子,我们有些事想向曹公子请教。”
池了了一直盯着曹喜,见他听到董谦,眼中果然一震,既有厌,又有惧。
但他的脸却始终冷着:“池姑娘我见过,不过你是谁?要请教什么?这案子跟你有什么干联?”
池了了忙道:“她姓赵。董公子于我有恩,他死得不明不白,官府如今也查不出,我就请了赵姑娘帮忙,我们自己来查。”
“你们两个?”曹喜笑起来,令人厌的蔑笑。
“怎么?不成吗?”
“当然可以,不过不要来烦我。”
池了了被冷冷打回,一时顿住。
瓣儿却仍笑着说:“曹公子和董公子是好友,应该也想找出真凶,替董公子雪冤吧。”
曹喜目光又一震,但仍冷着脸并不答言。池了了气得想立即脱下鞋子。
瓣儿继续道:“我们虽是女流,但也看不得这种冤情。哪怕智识短浅,不自量力,也情愿多花些工夫,慢慢解开其中的谜局,就算最终也找不到真凶,也是为公道尽一分心力。何况,这世间并没有藏得住的隐秘,只有没尽心、没尽力的眼睛。”
曹喜的神情缓和下来:“你不怀疑我?”
瓣儿摇摇头,笑着说:“怀疑。真相未揭开之前,所有当事之人都得存疑。”
池了了正在想瓣儿答得太直接,却见曹喜不但没有生气,反倒笑了笑,这笑中没有了厌和蔑。
“好。家里不方便,去那边茶坊吧。”
曹喜知道自己常常令人生厌,而且,他是有意为之。
自小,他就觉得父母有些不对劲,只是年纪太小,还说不清究竟是哪里不对。
母亲从来没有一个准性情,忽冷忽热,忽笑忽怒,从来捉摸不定。对他,也同样如此,有时似冰霜,有时又似火炭,不论冷和热,都让他觉得不对劲。起先他还怕,后来渐渐发觉母亲虽然性情善变,但任何喜怒都是一阵风,既不必理她的怒,也不必感念她的善。总之,根本不必怕。于是他在母亲面前便越来越肆意,即便母亲恼怒大骂,甚至抄起竹条打他,他也毫不在意,不过挨几下疼而已。
至于父亲,对他极是疼爱,甚至可说是溺爱。尽管那时家境还不好,只要他想要的,父亲都会尽力买给他。巷里孩童都羡慕他,他心里却似乎有些怕父亲,只要父亲在,事事都尽力做到最好,从不敢在父亲面前露出丝毫的懈怠。他做得好,父亲便更疼爱他;更疼爱他,他便越怕、越累。
于是,他便渐渐养成两副样子:在父亲面前,恭谨孝顺,在母亲及他人那里,则我行我素,毫不遮掩。
这两个他,他自己其实都不喜欢,但只能如此。
因此他也难得交到朋友,至今也只有董谦和侯伦两个。
在太学时,董谦和侯伦与他在同一斋舍,最先走近他的是侯伦。除了父亲,曹喜从来不会迁就任何人,侯伦又偏巧性情温懦,事事都顺着他,故而他们两个十分投契,一起走路都是他略前半步,侯伦偏后半步,难得有并肩而行的时候。
侯伦和董谦,两家又是世交,孩提时便是玩伴。董谦为人又忠直,事事都爱争个道理。若见到曹喜欺负侯伦,便会过来抱不平。曹喜自幼经过母亲无常性情的历练,向来不在意旁人言语,见董谦义正词严的样子,只觉有些好笑,不过也并不讨厌。故而有时会有意做出些不妥的举动,逗董谦来论理。一来二去,两人反倒成了朋友。
而范楼案,让他吃了从未吃过的苦,受了从未受过的辱。他丝毫都不愿回忆当时的情形。
谁知这个赵瓣儿和池了了竟为这事找上门来。
“首先,我申明,我不是凶手。”
到了茶坊坐下后,他先郑重其事说出这句。
从见面起,池了了就一直盯着他,眼中始终含着怒意,听到他这句话,眼里更像是要射出刀来。曹喜有些纳闷,虽然自己经常激怒别人,但从没让人怒到这个程度。这怒意绝不仅仅由于自己曾蔑视过她,她只是一个唱曲的,被人轻视嘲骂应该是家常便饭,绝不至于怒到这个地步。难道还因为董谦?但她和董谦只见过两次,并没有什么深情厚谊,怎么会因为董谦的死而怒成这样?除非……这姑娘一定是由于董谦维护过她,而对董谦动了情。想到此,他又觉得好笑了。
赵瓣儿也盯着他的双眼,也在探询,不过目光并不逼人。她听后只是笑着微微点了点头,看来也不信。
曹喜撇嘴笑了笑,并不在乎:“你们要问什么,请问吧。”
赵瓣儿道:“能不能讲一讲那天的经过?”
曹喜不由得皱了皱眉,那天的事,他极不愿回想,但看赵瓣儿和池了了都一副绝不罢休的样子,还是讲了一遍——
那天,池了了下去做什么家乡的鱼,曹喜和董谦顿时有些冷场。
曹喜有些看不上董谦和池了了这种态度,董谦对这样的女子竟也要以礼相待,而池了了,虽然东坡词唱得的确不俗,但终究只是个唱曲的,她恐怕也真把自己当作良家才女了。侯伦也是个多事的人,竟搓弄这样一场无聊酒局。
他越想越没情绪,正想起身走人,董谦却端起了酒杯,露出些笑容,道:“那天是我过激了,这杯赔罪。”
曹喜只得笑笑,也举起杯子:“过去就过去了,还提它作甚?”
那天的酒是侯伦从家里带来的老酿,有些烈,喝下去割喉咙,肚里热烘烘,一阵阵冲头。
“对了,你丢了这个——”
董谦从怀里掏出一样物件,是枚玉饰。
曹喜看到那玉饰,不由得愣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