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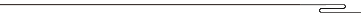
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柔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
——周敦颐
饽哥一边跑一边寻找着灯光,不知道彭嘴儿说的那只船停在哪里。
无论如何,今晚就能离开这里,丢下后母一个人,看她怎么过!
自从后母盲了之后,家里几乎所有事情都是饽哥做,即便这样,后母也从来没有好好朝他笑过一次。这几天,看着后母为孙圆焦虑啼哭,饽哥心里说不出的痛快,当年父亲被推下水后,他在家里连哭都不敢哭,想父亲时,只能远远躲到没人的地方偷偷哭一场。
想到后母那双盲眼,饽哥心里忽然冒出一丝内疚,后母是为了救自己才弄瞎了双眼。但他迅即挥掉这个念头,狠狠问道:父亲一条命和她一双眼睛比,哪个重?
他不再乱想,继续往前跑,天太黑,岸边路又不平,跑得跌跌绊绊,又跑了一阵,眼前亮出一点灯光,是了,就是那只船!他忙加快了速度。
但没跑多久,前面黑暗中忽然传出一阵叫声,女孩子的声音,是小韭!
那叫声十分惊慌,小韭怎么了?
他慌起来,拼命往前奔去,一不留神猛地摔倒在地上,疼得涌出泪来,但前面又传来小韭的惊叫,他忙爬起来,忍着痛,瘸拐着尽力往前赶去,前面小韭哭叫起来,似乎是在和人争扯。
那灯光终于越来越近,渐渐能辨清那只船了。但小韭的声音却在前面漆黑之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又跑了一阵,他终于看到了一团身影,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一个是小韭,另一个似乎是彭嘴儿,两个人扭挣着往船边靠近。
两人身影接近船头的灯光时,饽哥才辨认出来:小韭似乎不肯上船,彭嘴儿硬拽着她,想往船上拉。小韭一直在哭喊。两人争扯了一会儿,小韭忽然挣脱,转身往饽哥这个方向跑来,彭嘴儿忙又追了上去。
饽哥仍不明白究竟是为何,但已没有余力去想,唯有拼命前奔。
终于,他渐渐接近了,依稀能辨出小韭正快步朝自己奔来,但这时彭嘴儿也已经追上小韭,小韭又被拽住,仍在哭叫着挣扎,挣扎了一会儿,忽然停住,也不再喊叫。
饽哥心里涌起一阵惊恐,疯了一样奔过去,走近时,见彭嘴儿喘着粗气呆呆站着,小韭却倒在地上。饽哥扑跪到小韭身旁,小韭一动不动,他伸出手去摇,仍没有回应。
小韭死了?!
他忙抬头望向彭嘴儿,彭嘴儿张着双手,看不清脸,但隐微船灯映照下,神色十分惶恐。
饽哥又低头望向黑影中的小韭,仍一动不动。一年多来,他一直偷偷盼着能牵一牵小韭的手,摸一摸这娇小的身子。然而此刻,他却空张着两只手,不敢再碰小韭的身子。
一股悲怒火一般从心底蹿出,化成一声嘶喊,简直要将心劈裂。他猛地抽出自己带的短刀,又嘶喊了一声,站起身就朝彭嘴儿戳去。彭嘴儿还在发愣,刀尖刺进他的腹部。饽哥却已经疯了一般,拔出刀又继续猛扎,一刀又一刀……
夜太黑,墨儿骑着马不敢跑得太快,也不知道饽哥、彭嘴儿究竟逃往了哪里,只能依着武翔所言,一路往东追。
彭嘴儿拐带了春惜,饽哥又有小韭,几人要想离开,走水路最稳便。于是他便沿着河岸搜寻。五丈河上船只平日就远少于汴河,又多是京东路的粮船,眼下还没到运粮时节,再加上是夜晚,河面上只看到几只夜泊的货船。只亮着微弱灯光,彭嘴儿应该不会藏身在这些船里等人来捉。
墨儿又往下游行了一段,过了官家船坞后,四周越发漆黑寂静,河面上更看不到船影。他想,饽哥从艄公老黄的船舱里爬出来后,带着两锭银铤去和彭嘴儿会合,彭嘴儿自然会选僻静的地方等着。墨儿便继续驱马往下游寻去。
又行了一段,前面亮出了一点灯光,他忙驱马加速,往灯光处奔去。奔了一阵,忽然听到前面有人在嘶喊,又像哭又像骂,似乎是饽哥的声音。
等他奔近时,见一个汉子提着盏灯笼站在小径旁,竟是汴河艄公鲁膀子,他身旁站着两个妇人和一个孩童,其中一个妇人是鲁膀子的媳妇阿葱,另一个面容姣好,用双臂将那孩童揽在怀里,应该正是康潜的妻儿。灯光映照之下,三个人都脸色苍白,一起惊望着地上,墨儿顺着他们的目光望去,见暗影中一个年轻后生弓着背跪在地上,垂头呜咽哭泣,是饽哥。而饽哥身边,似乎躺着两个人,都不动弹。
墨儿忙跳下马,奔了过去,才看清地上躺的是彭嘴儿和小韭。小韭一动不动,彭嘴儿则满胸满腹都是伤口,血水将整个前襟几乎浸遍。饽哥右手边地上掉了把短刀,似乎沾满了血。
见到这惨状,墨儿一阵悲惊,他忙俯身去查看小韭,没有鼻息和脉搏,已经死去。看这情势,他大致明白,恐怕是彭嘴儿先杀了小韭,饽哥急怒之下,又杀了彭嘴儿。彭嘴儿行凶,则恐怕是为小韭不愿跟他走,想要逃回去,他怕小韭走漏风声,惊动官府,或是真的动了杀念,或是惊慌之下捂住小韭口鼻,勒住小韭脖颈,误杀了小韭。
但康游在哪里?他先追了过来,自己一路都没见到人影,难道康游追错方向了?墨儿忙抬起头,却见鲁膀子悄悄捅了捅身旁的妻子,使了个眼色,夫妇两个慢慢往后退,随即一起转身往那只船跑去。
墨儿忙叫道:“你们不要走!得做个证见!”
鲁膀子夫妇听了,反倒加快脚步,慌忙跑到岸边跳上了船。墨儿急忙追了过去,鲁膀子将灯笼交给阿葱,随即掣起船篙插入水中,就要撑船。墨儿觉得纳闷,他们为何这么害怕?等他追到岸边时,船已经撑开,墨儿一眼望见船头趴着个人,灯笼照耀下,那人背上一片血红,似乎是康游。
“不许走!”墨儿大叫着往水里奔去。但鲁膀子却拼命撑着船篙,船很快划到河中央,向下游漂去。墨儿只得回到岸上,急跑回去寻自己的马。
这时,黑暗中传来一阵马蹄声,还有几点火把亮光,从西边飞奔而来,很快到了近前,是万福和四个弓手。
墨儿忙道:“万大哥,快追那只船,不能让他们逃走!”
万福听到,立即扬手号令,率四个弓手一起往前追去。
墨儿便留下来看着饽哥和春惜母子。饽哥已经停止呜咽,但仍跪伏在小韭身旁,不停晃着身子,竟像是得了癔症。春惜则揽着儿子,静静站在那里,漆黑中看不到神情。
墨儿轻声问道:“你可是康大嫂?”
春惜没有答言。
墨儿又问:“康潜大哥已经身亡,你可知道?”
黑暗中,春惜的身子似乎轻轻一颤,但仍不说话。
墨儿忽然明白,并非是彭嘴儿诱骗她逃走,而是两人合谋。看来两人早有旧情,彭嘴儿去年搬到康家隔壁,恐怕正是为此。众人这些天想尽办法要营救的人,其实早就想逃走……
这时,栋儿忽然问道:“娘,身亡是啥?爹怎么了?”
春惜却没有回答,半晌,才轻声道:“你知道他死了,为何不等一等,正正当当向我提亲?”
墨儿一愣,有些摸不着头脑,随即才明白,春惜是在对地上的彭嘴儿说话。
春惜继续道:“你又何必要逃?更何苦做出这些事?我本已是死了心的人,你却把我叫醒,我醒了,你却走了……”
她啜泣起来,再说不下去,黑暗中只听到她极力克制却终难抑止的低低呜咽声。
墨儿心中一阵悲乱,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料到,这件事竟会让四个人丧命,更勾出这些不为人知的凄情悲绪。
正在伤怀,东边传来万福和弓手们的呼喝声:“再不停下就射箭了!”随即嗖嗖两声破空之响,紧接着便是阿葱的惊叫声。墨儿忙望向河中,见两支箭矢射到了船篷上,鲁膀子慌忙停住手,不敢再继续撑船。
万福又喝道:“把船划回来!”
鲁膀子犹疑了半晌,忽然大叫一声,纵身跳进水中。
“快下去追!”万福命令道。
扑通、扑通……连着四声投水声,四个弓手跳进河中,两个去追鲁膀子,两个游到船边,爬了上去,将船撑了回来,押着阿葱下了船。
阿葱不住地哭着:“不关我的事,船上男的和岸上小姑娘都是彭嘴儿杀的,彭嘴儿是饽哥杀的!”
万福驱马过来,举着火把照向阿葱,叫道:“昨天到处找你们夫妇两个找不见,竟然躲在这里!”
阿葱又哭起来:“那个术士也不关我的事,那天术士把我赶下船去了!”
“关不关,等回去再说——”万福指着春惜和饽哥,吩咐那两个弓手,“这对母子和饽哥也一起押回去。”
饽哥听见,慢慢站起身来,悲沉着脸,望着墨儿道:“有件事要拜托你。”
墨儿忙道:“你说。”
“我弟弟孙圆,他在烂柯寺后面那个荒宅子的井里。还有,替我回去告诉我娘,她给我的那些银子我没有拿,放在弟弟枕头下面。”
墨儿独自挑着盏灯笼,骑马来到烂柯寺后的那座荒宅,这时已是后半夜。
月光下,四下里一片死寂,只有一些虫鸣。那宅子的门扇早已被人卸掉,只露出一个黑洞。墨儿下了马,向里望去,门洞内庭院中生满荒草,一片荒败幽深。一阵夜风吹过,那些荒草簌簌颤动,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虽然幼年时曾来过这里,但那是几个人结伴,又是白天,并不觉得如何。这时独自一人,又是黑夜,心底升起一阵惧意。但想着饽哥应该不会说谎,孙圆在这后院的井里,便将马拴在门外一棵柳树上,提着灯笼、壮着胆子小心走了进去。
庭院荒草中间有一道被人踩过的痕迹,应该是饽哥踩的,墨儿便沿着这条路径穿过前庭,又小心走过空荡荡厅堂,来到后院。后院荒草藤蔓越发茂密,那口井就在院子右边墙根下,只能勉强看到井沿。墨儿顺着后廊慢慢走过去,拨开廊外一丛藤草,刚迈出腿,忽然听到扑棱棱一阵刺耳乱响,吓得他猛地一哆嗦,几只鸟飞腾四散,原来是惊到了宿鸟。
墨儿擦掉额头冷汗,定了定神,才小心走到井边。井沿周围也生满野草,不过被人拨开踩踏过。墨儿将灯笼伸到井口,小心探头向下望去,井里黑洞洞,什么都看不到。孙圆是清明那天下午失踪,至今已经这么多天,就算他在井底,恐怕也早已死了。墨儿这才后悔起来,刚才不该谢绝万福,该让个弓手一起来。
他又将灯笼往井下伸去,抻着脖子向下探看,仍是黑洞洞看不到什么。正在尽力探寻,井底忽然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哥!”
墨儿惊了一跳,猛地又打了个冷战,手一颤,灯笼险些掉下去。
井底那声音再次响起:“哥!哥!是你吗?哥?”
似乎是孙圆的声音!
墨儿忙大声问道:“孙圆!孙圆是你吗?”
“是!是!你是谁?快救我出去!”
墨儿忙将灯笼挂在旁边树杈上,取下肩头斜挎的那捆绳子,是方才向武翔家借的。他将绳头用力抛下井中,另一头在手臂上绕了几圈死死攥住。不一会儿,绳子被拉紧,颤动起来,孙圆在井底叫道:“好人!我爬不动,你拉我!”
墨儿忙抓紧绳子拼力往后拉拽,费了不少工夫,终于见一个身影从井口爬了上来,果然是孙圆,头发蓬乱,面色惨白,但看动作,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他爬下井沿,跌坐在地上,忽然呜呜哭起来,边哭边抬头望向墨儿:“墨儿哥?谢谢你!谢谢!”
“你在井底这么多天,竟然还能活着?”
“是我哥,他隔一天就往井里扔几个饼、一袋水,可就是不让我上来!呜呜……”
墨儿把孙圆送回了家,尹氏猛地听到儿子声音,一把抓住,顿时哭起来。
墨儿悄悄离开,骑上马向家里行去。康潜、康游、彭嘴儿和小韭相继送命,饽哥又犯下杀人之罪,让他悲郁莫名。这时见到尹氏母子抱头喜泣,才稍稍有些宽慰。
这时天色已经微亮,远处传来一两声鸡鸣,街上还看不到一个人影。穿出汴河南街,沿着野外那条土路行了一阵,墨儿忽然看见前面隐约有两个人,站在一棵大柳树下,那两人也似乎发觉了他,原本倚在树上,这时一齐站直了身子。墨儿顿时觉得不对。
虽然这里是城郊,但人户密集,监察又严,从来没有过剪径的盗贼,最多只有些泼皮无赖,但也不会在凌晨劫道。墨儿略想了想,不由得伸手摸了摸腰间的香袋。
那香袋里是珠子和耳朵。珠子是从彭嘴儿身上搜出来的,回到小横桥后,万福又带着弓手去搜了彭嘴儿家,从他床下一个坛子里搜出了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一对已经腐烂的耳朵。这两样东西是追查幕后真凶的仅有线索,墨儿便向万福借了来。
前面这两人难道是为这个?
墨儿有些怕,想掉转马头,但这两人若真是为了这两样东西而来,就算今天躲开,明天恐怕仍要来纠缠。他自幼跟着哥哥习武,虽然没有和人真的对斗过,但心想对付两个人应该不成问题。于是,他继续不快不慢向前行去,心下却已做好了防备。快要走近时,前面那两人忽然一起从怀里取出一张帕子,各自蒙在了脸上,其中一人走到了路的另一边。墨儿这时才依稀看到,两人腰间都挂着刀。
他们难道不怕我逃走?墨儿不由得扭头往后一望,身后不远处竟也有两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也都腰间挂刀,用帕子蒙着脸,一起从后面向他逼近。而路两边则是灌田的沟渠,马未必能越得过。就算能越过,两边都是新翻垦的田地,马也跑不快。
墨儿原还想设法制伏前面两人,从他们嘴里掏出些线索,但现在以一敌四,便很危险,不过也越发确信,这四人是为香袋而来。他不由得有些紧张,攥紧了手里的马鞭,这是他唯一的兵器。只能设法脱困,保住香袋不被夺去。
前面两人迎向他,慢慢逼近。微曦之中,墨儿隐约发现,路中间有根绳子一荡一荡,两人竟然扯着根绳索,显然是用来绊马。听脚步,后面两人似乎也加快了脚步。沉住气,莫慌,墨儿不住提醒自己,仍旧不疾不徐向前行去,心里却急急盘算对策,眼下情势,只能攻其不备。
距离前面两人只有一丈多远时,他猛地扬手,向马臀抽了一鞭,那马咆哮一声,顿时加速,向前冲去。前面两人惊了一跳,忙停住脚,扯紧了绳子。
墨儿继续驱马急冲,眼看要到绳索前,他双腿一夹,猛地一勒缰绳,那马扬起前蹄,又咆哮一声,马头应手一偏,马身也随即横转。这时,墨儿已经腾身一旋,双手抓牢马鞍,身子凌空,使出“鞍上横渡”,一脚踢向右边那人,那人根本没有防备,一脚正中颈项,那人惨叫一声,顿时倒地。墨儿双脚落地,随着马疾奔了几步,已经来到左边那人近前。那人正在惊惶,墨儿腾身一脚,脚尖踢中那人前胸,这一脚极重,那人也痛叫一人,倒坐到地上。
这时后面两人已经追了过来,一人举刀劈向马头,一人则向墨儿砍来。墨儿忙用左脚跨蹬,左手抓鞍,驱马在原地嘶鸣着急转了半圈,躲过马头那一刀。随即他前身横斜,头离地只有一尺,避过砍向自己那刀,右手执马鞭反手一抽,正抽中那人大腿,那人怪叫一声,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另一人再次挥刀向墨儿砍来,墨儿陡然翻身,让过那刀,在马上狠狠一抽,抽中那人手臂,钢刀顿时落地。
墨儿才在马上坐稳,前面两人已经爬起,一齐拔刀向他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