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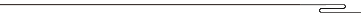
命于人无不正,系其顺与不顺而已,行险以侥幸,不顺命者也。
——张载
彭嘴儿只有一个念头:杀了康游。
若不杀了康游,他这一世便再没有任何可求可盼之机了。
他的父亲是登州坊巷里的教书先生,一生只进过县学,考了许多年都没能考入州学,又不会别的营生,便在家里招了附近的学童来教。
他父亲一生都盼着他们三兄弟能考个功名,替他出一口怨气。可是他们三兄弟承继了父亲的禀赋,于读书一途丝毫没有天分,嘴上倒是都能说,但只要抓起笔,便顿时没了主张。写不出来,怎么去考?
他们的父亲先还尽力鼓舞,后来变成打骂,再后来,就只剩瞪眼空叹。最后大叫着:“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咯血而亡。
好在他们还从父亲那里听来不少历史典故,大哥跟着一位影戏匠学艺,那师傅口技一绝,但肚里没有多少好故事,他大哥彭影儿学了口技之后,又加上父传的古史逸事,说做俱佳,一手影戏全然超过师傅,得了“彭影儿”的名号。
彭嘴儿原也想跟着大哥学,但他只会说,始终学不来口技,手脚又有些笨,所以只能做个说书人,又不想下死功,因此只学了三分艺,哄些过路客的钱。
他家那条街的街口有个竺家饼店,那饼做得不算多好,但店主有个女儿叫春惜,生得像碧桃花一样。
那时彭嘴儿才二十出头,春火正旺的年纪。有次他偶然去买饼,竺家只是个小商户,雇不起佣人,妻子、女儿全都上阵。那回正巧是春惜独自守店,她穿着件翠衫,笑吟吟站在那里,比碧桃花还明眼。
彭嘴儿常日虽然最惯说油话,那天舌头却忽然肿了一样,本想说“一个甜饼,一个咸饼”,张嘴却说成了“一个甜饼,一个甜饼”。
春惜听了,顿时笑起来,笑声又甜又亮,那鲜媚的样儿,让他恨不得咬一口。
春惜说:“听到啦,一个甜饼,何必说两遍?”
他顿时红了脸,却不肯服输,忙道:“我还没说完,我说的是买一个甜饼,再买一个甜饼,再买一个甜饼,还买一个甜饼……”
春惜笑得更加厉害:“你到底是要几个?”
“你家有多少?我全要!”
“五、十、十五……总共三十七个,你真的全要?”
“等等——我数数钱——糟——只够买十二个的钱。”
“那就买十二个吧,刚好,六六成双。我给你包起来?”
自此以后,每天他只吃饼,而且只吃竺家饼。
吃到后来,一见到饼,肠肚就抽筋。但这算得了什么,春惜一笑,抵得上千万个甜饼。
不过,那时他才开始跟人学说书,一个月只赚得到两三贯钱,春惜的爹娘又常在店里,他们两个莫说闲聊两句,就是笑,也只敢偷偷笑一下。
他好不容易攒了三贯钱,买了些酒礼,请了个媒人去竺家说亲,却被春惜的爹娘笑话了一场,把礼退了回来。
这样一来,他连饼都不敢去买了,经过饼店时,只要春惜爹娘在,他连望都不敢望一眼。偶尔瞅见只有春惜一人在店里时,才敢走进去,两人眼对眼,都难过得说不出话。半天,他才狠下心,说了句:“你等着,我赚了钱一定回来娶你。”春惜含着泪点了点头,但那神情其实不太信他说的话。
他开始发狠学说书,要是学到登州第一说书人的地步,每个月至少能赚十贯钱,那就能娶春惜了。
可是,才狠了十来天,他又去看春惜时,饼店的门关着,旗幌子也不在了。他忙向邻居打问,春惜一家竟迁往了京城,投靠亲戚去了。
一瞬间,他的心空得像荒地一样。
他再也没了气力认真学说书,每天只是胡乱说两场混混肚子,有酒就喝两盅,没酒就蒙头睡觉。父母都已亡故,哥哥和弟弟各自忙自己的,也没人管他。
弟弟彭针儿跟着一位京城来的老太丞学了几年医,京城依照三舍法开设了御医学,那老太丞写了封荐书,让彭针儿去京城考太医生。彭影儿知道后,说也想去京城,那里场面大,挣的钱比登州多十倍不止。彭嘴儿见兄弟都要去汴梁,也动了心。
于是三兄弟一起去了京城。
彭嘴儿原以为到了京城就能找见春惜。可真到了那里,十万百万的人涌来涌去,哪里去找?
他哥哥彭影儿功夫扎实,很快便在京城稳稳立住了脚。弟弟彭针儿进了医学院,看着也前程大好。只有他,那点说书技艺,在登州还能进勾栏瓦舍混几场,到了京城,连最破落的瓦舍都看不上他。他只有在街头茶坊里交点租钱,借张桌凳,哄哄路人。每天除了租钱,只能挣个百十文,甚至连在登州都不如。
京城什么都贵,他们三兄弟合起来赁了屋子,不敢分开住。三弟彭针儿进了太医学外舍后,搬到学斋去住。唯有他,只能勉强混饱肚子,独自出去,只能睡街边。
不过,三弟彭针儿和他一样,做事懒得用心用力,学了几年,仍滞留在外舍。去年蔡京致仕,太医学随着三舍法一起罢了,彭针儿也就失了学。他原就没有学到多少真实医技,又没本钱开药店医铺,只能挑根杆子,挂幅医招,背个药箱,满街走卖。
起初,彭影儿还能容让两个弟弟,后来他挣的钱比两个弟弟多出几倍,脸色便渐渐难看起来。之后又娶了亲,嫂嫂曹氏性子冷吝,若不是看在房屋租钱和饭食钱三兄弟均摊,早就撵走了他们。即便这样,她每天也横眉冷眼,骂三喝四。
他们两兄弟只能忍着。忍来忍去,也就惯了,不觉得如何了。
这个处境,就算能找到春惜,仍是旧样,还是娶不到。因此,他也就渐渐死了心,忘了那事。每天说些钱回来,比什么都要紧。
两三年后,他渐渐摸熟了京城,发觉凡事只要做到两个字,到哪里都不怕:一是笑,二是赖。
有手不打笑脸汉,无论什么人、什么态度,你只要一直笑,就能软和掉六分阻难;剩下三分,那就得赖,耐心磨缠,就是铁也能磨掉几寸;至于最后一分,那就看命了,得了是福,不得也不算失。
于是,他慢慢变成个乐呵呵的人,就是见条狗,也以乐相待,恶狗见了他都难得咬。
这么乐呵呵过了几年,直到去年春天,他去城东的观音院闲逛,无意中撞见了一个人:春惜。
春惜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已是一个少妇,手里牵着个孩童,身边还跟着个中年男子。不过他仍旧一眼认出了春惜,脸还是那么中看,仍是一朵碧桃花,且多了些风韵。春惜并没有看到他,他躲在人背后,如饥似渴地望着,怎么看也看不够。
春惜烧完香后,牵着那孩子,跟着那个男子离开了观音院,他便悄悄跟在后面,一直跟到小横桥,看见春惜进了那家古董店。
之后他便不停往那里闲逛,偶尔看到春惜一眼,便会醉半天。没几天,他在那附近的茶坊里歇脚吃饭,听到两个人闲谈,其中一个说自己古董店隔壁那院宅子准备另找人赁出去。他一问,租价比自己三兄弟现住的每月要贵五百文,不过房间也要宽展一些。他立即回去说服兄嫂搬到小横桥,多出的五百文他出三百,彭影儿和彭针儿各出一百。兄嫂被他赖缠不过,就过来看了房,都还中意,就赁了下来。
彭影儿和彭针儿当年虽然也见过春惜,却早已记不清,认不出,都不知道彭嘴儿搬到这里是为了春惜。
搬来之后,他发觉春惜像变了个人,冷冷淡淡的,只有跟自己儿子才会笑一笑,见到外面男子,立即会低下头躲开,因此她也一直没有发觉彭嘴儿。
彭嘴儿留意了两个月,才找到了时机——只有在井边打水时,两人才有可能单独说话。他便赶在春惜打水之前,先躲在井口附近,等春惜刚投下井桶,才走了过去,低声道:“一个甜饼,一个甜饼。”
春惜先惊了一跳,但随即认出了他,脸顿时羞得通红,却没有躲开,直直盯着他。他忙笑了笑,虽然这几年他一直乐呵呵的,其实很少真的笑过。这一笑,才是真的笑,但又最不像笑,心底忽然涌起一阵酸楚,几乎涌出泪来。
春惜也潮红了眼,轻轻叹了口气,弯腰慢慢提起井里的水桶,转身要走时,才轻轻叹了句:“你这又是何苦?”
自那以后,他们两个便时常在井边相会,到处都是眼睛,并不敢说话,连笑也极少,最多只是点点头。但这一瞬,珍贵如当年的甜饼。不同者,甜饼能填饱肚子,这一瞬,却让他越来越饿。
直到今年寒食前两天,他又到井边打水,春惜刚将水桶提起,见到他,眼望着别的地方,低声说:“我丈夫要卖我们母子,隔壁武家二嫂明天要帮我们躲走。”
他忙问:“躲到哪里?”
春惜却没有回答,提着水桶走了。
他顿时慌乱起来,他丢过春惜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不能再丢第二次。
那天他仍得去说书挣饭钱房钱,但坐到香染街口的查老儿杂燠店,嘴和心根本合不到一处,说得三不着调,围听的人纷纷嘲骂着散开了。他正在失魂落魄,却见武家三弟武翘走了过来,并没有留意他,拐向东水门,朝城外走去。
他想起春惜的话,不知道和武翘有没有关联,便偷偷跟了过去,见武翘坐到虹桥口的水饮摊边,和那水饮摊的盲妇说了一阵话,又似乎掏了三陌钱给了那盲妇,水也没喝就走了。
他知道那盲妇是卖饼郎饽哥的娘,看武翘举止有些古怪,怎么会给盲妇这么多钱?不过一时也猜不出,却记在心里。
第二天,他一早起来就出了门,却没走远,站在小横桥头,远远盯着康潜家的店门。盯了很一阵,才见武家的二嫂柳氏走到古董店门口唤春惜,但春惜并没有出来,又过了一阵,康潜才出来跟柳氏说了两句话,柳氏便回家去了。
他心里纳闷,却又不能过去问,心想康潜恐怕不许春惜出门,春惜也就没法逃走了。他稍稍安了些心,仍旧去香染街说书去了。下午回家后,他在康潜家前门、后门张看了几遍,都不见春惜的人影,连那孩子的声音都听不见。春惜真的躲走了?
一夜辗转难安,第二天寒食,上午他又去窥看,仍不见春惜和那孩子,看来春惜真的躲走了。但躲到哪里去了?
他慌乱不宁,却又没有办法,只得照旧去说书。到了香染街,看见卖饼的饽哥扛着饼笼走了过来,忽然想起武翘的事,也许和春惜有关?他便装作买饼,向饽哥套话:“听说你家摊了件好事?”
“我家能有啥好事?”饽哥这后生极少笑,木然望着他。
“什么能瞒得住我?我都见那人给你娘钱了。”
“哦,那事啊。只不过是替人取样东西。”
“什么东西这么精贵,取一下就要三陌钱?”
“我也不知道。”
他听了有些失望,这和春惜可能无关。但看着饽哥要走,他又一动念,不管有关没关,武翘拿这么多钱给饽哥他娘,必定有些古怪。于是他又叫住饽哥,拉到没人处——
“饽哥,跟你商议一件事,你取了那东西,先拿给我看一眼,我给你五十文,如何?”
“别人的东西,你看它做什么?”
“是那人托了你娘,你娘又吩咐你去取?”
“是。”
“我知道你娘是后娘,一向刻薄你。重的累的全是你,甜的好的,全都给她亲儿子,我早就想替你抱不平,只是一直没合适机会。好不容易碰到这种事,咱们来整治整治你那瞎眼娘。若那东西值钱,咱们就把它偷换掉,卖了钱平分。若东西不值钱,也给她换掉,让她尝尝苦头,我另给你五十文。如何?”
饽哥犹豫起来,他又极力说了半天,饽哥终于被说动,答应了。
清明过后第二天一早,饽哥拿了个香袋偷偷塞给彭嘴儿。
彭嘴儿打开一看,吓了一跳,里面除了一些香料和一颗药丸,还有血糊糊一双耳朵,已经隐隐有些发臭。
“这东西值不了什么钱。那就照昨天说的,让你娘吃苦头。”
他取出备好的一百文钱给了饽哥,等饽哥走后,才又仔细查看,发现那颗药丸裂了道缝,剥开一看,里面竟是一粒明珠,萤亮光润,珠围几乎有一寸。他虽然不识货,却也知道这珠子一定极值价,自己说几辈子书恐怕都难挣到。
他喜得手都有些抖,一直以来正因为穷,才一而再地错失春惜,有了这颗珠子,还愁什么?
于是他开始极力寻找春惜的下落,但又不能明问,没有一点头绪,反倒见赵不尤的弟弟赵墨儿接连去找康潜,康潜又一直谎称春惜回娘家去了。一般有讼案,赵不尤才会介入,难道春惜出了什么事?
他忧烦了这许多天,见康潜比他更忧闷憔悴,脸色发青,眼珠发黄。他向弟弟彭针儿询问,彭针儿说康潜是肝气虚弱,沾不得酒,千万不要借酒消愁才好。
他听了之后,忽然生出一个念头。春惜逃走是为了躲避康潜,倘若康潜一死,春惜也就可以安心回来,更可以另行嫁人。
这个念头让他害怕,心底陷出一个漆黑深渊,一旦失足,恐怕再难见天日。但又一想,自己活了这么些年,虽然每天笑呵呵,其实何曾见过什么天日?
——春惜才是天日。
他横下心压住害怕,开始谋划。他曾听人说全京城的酒,唯有前任枢密院邓洵武家酿的私酒酒性最烈。邓洵武去年年底已经病逝,其子邓雍进正在服孝,不能饮酒。他家去年酿的酒恐怕都还藏着。彭嘴儿认得邓家一个姓刘的厨子,他便去邓府后门唤出刘厨子,狠狠心,拿了三贯钱向那厨子偷买了三瓶酒。
等到天黑,前后街都没人时,他另灌了一瓶水,拿了两个大酒盏,连同那三瓶酒用布包兜着,又去找了一根细绳穿在大针上,藏在衣袋里。准备好后,才出去轻轻敲开康潜家的后门。康潜一向不愿理他,冷冷问他做什么,他却不管,笑呵呵强行进去:“我得了几瓶好酒,见大郎这几日闷闷不开心,过来替大郎散散愁闷。”
康潜说不喝酒,他仍不管,提着酒径直走到中间小厅,点亮了油灯,见四条长凳面上都蒙着灰,便说“腰不好,得坐高些”,将一条长凳竖着放稳,坐在凳腿上。取出四个酒瓶、两只酒盏,给康潜斟满了酒,自己斟的则是水。康潜跟着走了进来,一直站在旁边望着,满脸厌烦。他照旧不管,笑呵呵道:“大郎坐啊。”
康潜只得坐下,他把那盏酒强行塞到康潜手中,笑着劝道:“你一向不大吃酒,不知道这酒的好处。尤其是愁闷时,痛快喝他一场,蒙头睡倒,什么烦恼全都去他娘了。”
康潜只饮了一小口,立刻呛得咳嗽起来。他忙继续笑着劝道:“再喝,再喝!多喝几口才能觉出这酒的好。世人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不知道这酒关更难过。好比大郎你的媳妇,算是极标致的美人了,还不是照样被你娶到了手?每日给你端茶煮饭,可见这美人关有什么难过的?但酒就不一样了,大郎你就极少沾它。不知道的人都说大郎你性格懦弱没胆量,但我最清楚,大郎你只是不愿喝,真要喝起来,几条壮汉也喝不过你。你那媳妇那般服服帖帖,一定也是怕你这从不外露的气概。”
康潜听了,果然不再推拒,几杯下肚后,惹起酒兴,再加上彭嘴儿极力劝诱,康潜一盏又一盏,全都一口饮尽,一瓶很快喝完,人也来了兴致,嘴里念念叨叨不知在说什么。彭嘴儿继续哄劝,把第二瓶也哄进了康潜肚中。康潜已趴在桌上,不住晃着脑袋,呜呜咕哝着,像是在哭。
彭嘴儿想差不多了,即便酒量高的人,也受不住这两瓶,便打开第三瓶酒,让康潜自己继续喝,他则起身收起自己那只酒盏和灌水的酒瓶,扶正了自己坐的木凳,摸黑出去。
那天他偷看到墨儿用细绳从外面扣住门闩,康潜后来用黑油泥填抹了门板上的蛀洞,他便也从炉壁上抠了些油泥,而后取出自己带的细绳,照着那个法子,从外面将康潜家的后门闩起,用黑油泥重新填抹了那个蛀洞,这才溜回到自己家中。
第二天,康潜果然醉死了。
彭嘴儿原本以为康潜死后,柳氏就该让春惜母子回来奔丧了。
但直到天黑,都不见春惜母子回来,却见武翘从后门走了过去,神色似乎不对。他忙偷偷跟着武翘,一直来到官府船坞。武翘进到船监屋里,只逗留了一小会儿就出来走了。彭嘴儿仍躲在附近,等四周没有人时,才偷偷趴到窗边向里窥视,竟一眼看到了春惜母子。
他喜得几乎落泪,一直定定看到春惜母子告别了船监夫妇,向船坞里头走去,他忙绕到船坞后墙,幸好墙不高,找了两块石头垫脚,翻了进去。船坞里有只船亮着灯,他悄悄走过去,见船窗半开,春惜正在里面坐着和栋儿玩耍。
他轻轻叩了叩窗,春惜探出头,认出是他,险些惊呼出来。他忙嘘声止住,而后轻步上船,进到船舱之中。
两人四目相对,都说不出话,倒是栋儿,由于彭嘴儿时常买吃食玩物给他,见到彭嘴儿,笑着叫道:“彭二伯!”
春惜忙嘘住栋儿,抬头问道:“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偷偷跟着武翘来的。”
两人四目相对,又说不出话。
半晌,彭嘴儿才问道:“我若有钱了,你愿不愿嫁我?”
春惜先是一愣,怔了片刻,眼睛开始泛潮,轻声道:“你没钱,我也只愿嫁你。”
“真的?”一阵暖热从心底直冲上头顶,彭嘴儿油了十几年的嘴忽然涩住,一个字都说不出,他向前走了半步,忽又顿住,双手想要伸出,却只动了动,便僵在那里。半晌,他才小心问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这时,春惜已平静下来,她轻声问道:“去哪里?”
“离开京城,走远一些,到外路州去。”
“我得带着栋儿。”
“那当然,我也爱这孩子。”
“什么时候走?”
“最好现在就走。”
彭嘴儿带着春惜母子偷偷翻墙逃离了船坞,走到岸边,他才发觉自己太冒失。
这时天已黑了,带着春惜母子去哪里是好?他袋里只有一百多文钱,住店都不够,何况也不敢去住店。客船一定是没有了,雇车马又怕人看到。
饽哥交给他的香袋没有带在身上,那对耳朵已经烂臭,但他不知来历,不敢丢掉,包了几层油纸,藏在自己床下一个小坛子里。那颗珠子怕丢了,也藏在卧房墙角的一个洞里。
要离开京城,至少得有些钱才好,那珠子不是凡常之物,至少半年之内不能拿出去卖。他这几年每天说书挣的钱,除开食费和房费,剩不下几个,只攒了五六贯。有个百十贯钱,才好在他乡安家立业。
他心里烦躁,却不敢露给春惜,心想,至少今晚得找个安稳地方安置春惜母子。
他忽然想到鲁膀子,来京城几年,他并没有交到什么朋友,只有鲁膀子性子有些爽直,又爱听彭嘴儿说些古话,两个人时常喝点酒,交情还算厚,人也大致靠得住。鲁膀子家不敢去,在他船上躲一两天应该不妨碍。
于是他低声对春惜说:“今晚你们母子得委屈一下,我去找个朋友,你们在他船上将就一晚,明天再商量去处。”
“好。”夜色中看不清春惜的脸,但声音里似乎微微带着些欢悦。
彭嘴儿心里又一阵暖,没想到自己竟能和春惜肩并肩站得这么近,更没想到她的心和自己的心能合到一处。
天上飘起细雨,彭嘴儿后悔没带把伞出来,他忙脱下自己的外衣递给春惜:“你们娘俩先在这树下等一等,我去寻那朋友,让他划船来这里接你们。”
“你也要淋湿。”春惜不肯要那外衣。
彭嘴儿执意塞给她,临走时本想告诉她康潜的死讯,但又怕另生枝节,便忍住没说,转身大步望东水门跑去。
许久没有跑过了,他却丝毫不觉得累,反倒觉得畅快无比,地上渐渐湿滑,他连摔了几跤,却都立即爬起来,笑着继续跑。奔了半个多时辰,终于来到虹桥,他先去看鲁膀子的船,那船泊在岸边,一根缆绳拴在柳树根。船里并没有人。他转身又向鲁膀子家快步走去,没走多远,却见前面两个黑影急忙忙走了过来。走近之后,才发现竟是鲁膀子夫妇,他们身上各背着一个大包袱。
“鲁兄弟?”
“彭二哥?”鲁膀子声音有些慌张。
“你们这是?”
“我们……”鲁膀子支吾起来。
“莫不是出了什么事?”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
“跟哥哥我还支吾什么?实话跟你说,我也有桩麻烦,所以才来找你们。”
“哦?那去船上说。”
三人上了船,钻进船篷,鲁膀子却不肯点灯。
“我先说我的——”彭嘴儿见他们迟迟不肯开口,便道,“以前哥哥跟你说过,我相中了一个女子,她父母却嫌我穷,把她嫁给了别人。那女子刚跟我逃了出来,我想求鲁兄弟一件事,用船把我们送离开封府界,我们再搭其他的船走。”
“哥哥啊,我们也惹了桩麻烦,正要逃走呢。”
“哦?什么麻烦?”
“麻烦太大,这一时半时也说不清楚,总归被个闲人捅破了,得尽快逃走。”
“你们就划着这船走?不怕下游锁头关口盘查?”
“走旱路也不稳便,更容易被人看见。”
“这样冒冒失失乱撞不是办法,既然我们都要逃,那就做个难兄难弟,力气使到一处。我有个主意——这汴河盘查严,五丈河却要松得多,既然你们已经被人发觉,这两天一定缉捕得紧,不如来个虚实之计。先躲起来,却不离开京城,让官府的人觉着你们已经逃离了京城,过个两三天,自然会松懈下来,那时我们再一起从五丈河逃走。”
“躲到哪里?”
“五丈河下游有一片河湾,十分僻静,除了过往船只,难得有人去那里。那河湾里有个水道,原是灌田开的沟渠,现今那一片田地被官家占来修艮岳园林,那沟渠被填了,只剩入河的一小段,刚好能停得下你这只船,两边草木又深,藏在那里,决计不会有人发觉。”
鲁膀子夫妇听从了彭嘴儿,将船划到五丈河,接了春惜母子,一起躲到了东边河湾的那个水道里。
他们不敢点灯,黑暗中彭嘴儿看不清春惜,便再三交代了鲁膀子夫妇,让他们好生照看春惜母子,这才告别离开,摸黑赶忙往小横桥家中。
一路上,他都念着春惜,简直做梦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