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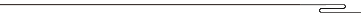
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
——周敦颐
夜里睡不着,康潜又起晚了。
他翻身起来,头有些晕沉,坐在床边,呆望屋中。桌椅箱柜什物,到处铺满灰尘。一扭头,见床头挂的那面昏蒙蒙铜镜里,自己面色灰白,头发凌乱,脸越发瘦削,眉头拧出深褶,一双眼里,阴沉沉的愁郁,简直像孤魂瘦鬼,一阵酸辛漫上心头。
他深叹口气,捶了捶脑袋,蹬好鞋子,拎过那件已经污旧的布袍,胡乱一套,边系衣带,边向外走,去开店门。以他现在这心境,其实早已无心开店,只是多年来已成了早间定式,又还想着不要让邻居起疑。
懒洋洋穿过外间瓶鼎古董间那条窄道,他的衣袖不小心掀落了木架间一只茶盏,哐啷一声,碎了。那是唐贞元年间御制的雪瓷茶器,今年开春才从城外一个员外那里买进,原本一套,几天前,儿子栋儿顽皮,碰碎了一只茶托,被他打了一巴掌,那是他生平第一次动手打儿子,为此和妻子春惜又生了场气。他原还想设法再配出一套来,如今好了,盏和托,全碎了。
他蹲下来捡拾碎片,那天是春惜蹲在这里捡,栋儿则挂着泪珠站在一边。弟弟康游进来,见情势不对,也不敢说话,忙抱着栋儿出去了。
其实那时,他和春惜及弟弟之间,已经不对了。
他一生庸庸,若说算得上大事的,只有三件:一是开了这家古董铺,一是娶了春惜,再一件,就是生了栋儿。
春惜姿色现在倒不觉得如何,但相亲初见那时,却也让他着实心动。收到媒人从女家讨来的草帖后,他去庙里问卜,生辰属相都吉,就回了细帖,上面填了三代名讳、金银、田土、宅舍、财产等事项,女家也回了细贴,虽然陪嫁没有多少,但于康潜算登对,于女方也合意,于是便要相看。
他订了一只汴河画舫,备好二匹锦缎和一只金钗,媒人带着他上了船。大舱里只见到春惜的父母,春惜则躲在隔间里不出来。春惜的父母生得都有些古怪,父亲嘴有些歪,母亲则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康潜于相貌还是有些看重,父母生得如此,女儿自然也不会多好。便想放下压惊用的二匹锦缎,起身走人,媒人看出了他的意思,便使眼色让他稍等,随后进到隔间,将春惜强拉了出来。
帘子掀开那一瞬,康潜如同见到妩媚春光一般。春惜穿着粉衫粉裙,梳着一朵云髻,翠眉秀眼,满腮羞晕,鲜丽如春水岸边的一枝碧桃。他惊了半晌,随即从怀中摸出那支金钗,媒人一把接过,插到了春惜乌黑的鬓边——插钗定亲。
不过娶过来后,康潜发觉,春惜性情有些冷淡。很少见她笑,床笫之间也难得起兴。起初,他以为是新婚害羞,渐渐觉得,或许她生性便是如此。再后来,相处日久,他原本喜静不喜闹,春惜常日里安安静静。本本分分,将家里又操持得井井有序,他反倒觉得是好事了。
直到弟弟康游从边关回来……
第二天,墨儿一早就赶到饽哥家,饽哥已出门卖饼,只有尹氏在家,孙圆昨晚仍未回来。
尹氏越发焦虑,脸色惨白,嘴角起泡,盲眼里冒着黑火一般。一见尹氏这么焦急,他又慌乱起来。忙告诫自己莫慌,莫慌,沉住气好好想想。
偷换香袋的恐怕真是孙圆,那颗珠子应该很值钱,他这两天没回家,也许是去找人变卖珠子,好去会那个吴虫虫。既然孙圆不见人,这事本又起于康潜妻儿被劫,还是先去康潜那边问问详情。
于是他安慰道:“尹婶,你莫焦急,我一定尽力。”说着忙拜别尹氏,赶往了小横桥。
“尽力”他能做到,但“一定”两个字说出来时却十分心虚。
一路上他都急急思虑,如果偷换香袋的真是孙圆,他又是如何不用钥匙就换掉柜子里的香袋?哥哥说要依理往寻常处想,但这件事寻常决计做不到。若往不寻常处想,除了邪魔法术,再没有其他办法,邪魔法术却肯定信不得。寻常与不寻常之间,是否还有其他可行之路?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来,不知不觉间,到了康潜的古董店。
康潜还是那般阴郁模样,见到墨儿进来,他倏地站起身,急急问道:“香袋里的东西找到了?”
墨儿歉然摇了摇头,康潜目光顿时暗下来,一屁股又坐了回去。
墨儿的心也随之黯然,他忙小心解释道:“康先生,香袋的事只找到了些线头,目前还没有确切结果。我今天来,是想再求康先生能讲讲你妻儿被劫的事,当务之急是找到他们母子。若能查出那劫匪的踪迹,就能设法救回你妻儿,那样,香袋的事就算不得什么了。”
康潜听了,似乎略有心动,但眼中随即升起犹豫。
墨儿忙鼓起气劝道:“我想那劫匪这两天一定会在暗中打探,尹婶找我帮忙查找,他恐怕也已经知道,所以,你告诉我实情,他应该不会太在意。”
康潜静默了片刻,忽然站起身,过去把店门关起来,才回身说:“我们到后面去讲。”
墨儿随着他来到后面,这房子是前后三进,外面一大间店面,中间一间小厅,左右两边各一间卧房,门都开着,右边房里一架大床,应该是康潜夫妻居住。左边一间很小,摆着张小竹床,是间小卧房。后面那间房则是厨房,有道后门,关着。
康潜请墨儿到厅中的方桌边,面对面坐下,他搓着自己的手指,清了清嗓子,低声讲起来:“他们母子是忽然间就不见了……”
“忽然间?怎么回事?”
“那是三月初八,寒食前一天,我早上起了床,贱内说跟隔壁二嫂约好,要一起去庙里烧香。我没说什么,自己去开了店门,贱内在厨房里煮了粥,我们一起在这里吃过后,我煎了壶茶,到外间店里坐着吃茶看书,她在厨房里收拾。每回她去烧香前都要洗浴,又烧了一锅水,自己洗好后,叫醒了栋儿,也给他洗澡。栋儿调皮,母子两个一直在厨房里嬉闹。过了一阵,隔壁武家的二嫂柳氏过来唤贱内,我就去厨房叫贱内,进了厨房,地上摆着大木盆,水溅得到处都是,却不见人影,我又回来到两间卧房看,都不见人。重又回到厨房,仍不见人,厨房的后门又闩得死死的。一低头,见门槛边地上有个信封,打开一看,才知道母子两个被人劫走了。”
墨儿听后大惊,门窗紧闭,一对母子却无影无踪。
他忙问:“后门真的关死的?”
“是,门闩插得好好的。”
“窗户呢?”
“后边窗户是死的,打不开。”
“没有外人进来?”
“没有。我一直在外间坐着。”
“隔壁那个二嫂进来没有?”
“没有,她一直候在店外,见我找了半天,才进来。”
“那封信呢?”
康潜眼中又现戒备:“那个你就不必看了。”
墨儿想,那信里写的,定是要挟康潜去割下某人耳朵,拿到珠子,事关凶案,康潜自然不愿拿出。眼下也暂时顾不到那里。只是香袋的古怪还没解开,这里又冒出更大的古怪。
他原想劫匪可能是趁那母子不留意,强行劫走。这么一听,活生生两个人,竟是凭空消失,那劫匪怎么做到的?
“我去看看厨房。”
墨儿起身穿过小厅,小厅和后面厨房之间有扇门,这扇门正对着前面店铺的门。那天康潜妻子洗浴时,应该是关着这扇门的,否则店里来人可以直接望见厨房,不过他还是回头问康潜:“康先生,那天大嫂洗浴时,这扇门关着吧?”
“关着的。这扇门平时难得关,她洗浴时才会关。”
“大嫂洗浴时,你儿子在哪里?”
“在这小厅里,他娘给他穿好衣服后,给他舀了碗粥,让他好生吃,我记得他似乎闹着要吃甜糕,他娘还唬他,若不吃就不带他上庙里,他才没敢再闹。他应该是趴在这桌上吃粥。他们不见后,小粥碗还在这桌上,是吃完了的,只剩了几粒米没吃净。”
“大嫂洗完后,给你儿子洗时,也关上了这门?”
“我想想……是关着的,我当时坐在店里,她母子在里面嬉闹的声音,只能听得到,却听不太清。隔壁武家二嫂来唤她,我先敲门唤了两声,听不见回话,才推开了门,里面虽然没上闩,但这门关起时很紧,用力才推得开。”
墨儿点点头,走进了厨房,厨房挺宽敞,外墙正中间是后门,左角是灶台,灶口上一大一小两只铁锅,都用木盖盖着,上面蒙了薄薄一层灰,灶洞里积着些冷灰,看来几天没动过火了。旁边一个大木筐里有半筐黑炭。
厨房右角靠着外墙则是个木柜,木柜已经陈旧,柜上堆着些厨房杂物。旁边是个水缸,一只大木盆。
左右两边墙上各有一扇小窗户,都勉强可以钻进一个人,但正如康潜所言,窗户是死的,而且贴着窗纸,窗纸可能是去年末才换,还是新的,没有任何破裂。绑匪不可能从这里进入。
右边靠里墙,还有一扇门,门关着。
墨儿问:“这里还有一间屋子?”
“那原是杂物间,因我弟弟从边关回来,就拾掇了一下,改成了间小客房,有时他回家来,就住这间。”
“你还有个弟弟?”
“他叫康游,原在陇西戍守,前年才回来,现在开封县里做县尉。”
“大嫂失踪那天,他在吗?”
“不在,他来得不多,一个月只来住两三天。”
“我能看看房间里吗?”
“请便。”
墨儿轻轻推开门,很小一间屋子,只有一张床,一个柜子。外墙上也有扇窗户。墨儿走过去查看,窗户是菱形格板钉死在窗框,也打不开,窗纸也是新换没几个月,还雪白如新,没有任何破裂。劫匪不可能从这里出入。
他掩上门回到厨房,去查看那扇后门,门已经陈旧发黑,但门板很厚实,板缝间拼合得极紧,又加上多年油垢弥合,除了两三个极小的蛀洞,没有丝毫缝隙。门闩的横木硬实,没有裂痕,两个插口木桩也钉得牢实。康潜妻子洗浴时,应该不会大意,必定会关死这扇门。
墨儿打开门走了出去,门外正对着五丈河,离河只有十几步,河上有几只漕船在缓缓行驶,济郓一带的京东路粮斛是由这条水路入京。墨儿向两边望望,这一排房舍都向河开着后门,方便洗衣泼水。
绑匪劫了康潜妻儿,可以从这里乘船逃走。不过,两边都有邻舍,白天河上都是往来船只,只要康潜妻儿稍作挣扎喊叫,就会被人发觉。绑匪是如何无声无息劫走那母子的?
他回身查看门框、门枢,也都结实完好。他让康潜从里面闩住门,自己从外面推,只微微翕动,绝对推不开。他又弯下腰细看门闩处的门缝,一般窃贼可以用薄刃从这缝里插进去,一点点拨开门闩。不过刀尖若是拨过门闩,必定会在两边木头上留下印痕。他让康潜打开门,凑近细看门板侧面,门闩那个位置并没有印痕。看来绑匪并没有用刀拨开门闩,那么他是如何进去的?
更奇的是,那天康潜进来时,门是从里面闩上的。看来,绑匪挟持着那对母子,并没有从后门出去,那么他是如何离开的?
比起那香袋的隔空取物,这更加难上几倍,是带人穿墙的神迹。
“大郎……”
墨儿正想得出神,旁边响起一个妇人的声音。扭头一看,是个五十来岁的妇人,面容慈和,衣着整洁,双手里端着一个青瓷大碗,上面扣着个白碟,透出些油香气来。
康潜走出后门,硬挤出些笑,问了声:“武家阿嫂。”
“春惜妹子还没回来呢?落下你一个人,这几天恐怕连顿热汤热饭都没吃着吧,有人给你武大哥送了两只兔子,我刚烧好,给你端了碗来,你好下酒。”那妇人将手里的大碗递给康潜。
“这如何使得?”康潜忙连声推辞。
“这有什么呢?咱们两家还分你啊我的?我们也没少吃你家的。”
康潜只得接过来:“多谢阿嫂。”
“这位小哥没见过,他是?”妇人望着墨儿。
“哦,他姓赵——有个古董柜子要卖给我,看看这门够不够宽,能不能搬进来。”
墨儿最不善说谎,正不知该怎么遮掩,听康潜替他掩过,暗暗松了口气。
“哦,那你们忙。”妇人转身走进右边隔壁那扇门。
墨儿随着康潜也走进屋里,关好门,才问道:“我正要问左右邻舍,刚才那位是?”
康潜将碗放到灶台上:“是隔壁武家大嫂朱氏。我们已做了十几年邻居,他家有三兄弟,长兄叫武翔,在礼部任个散职,因喜好古物,常来我这里坐坐;二弟叫武翱,几年前和我家弟弟康游同在西边戍守,前年和西夏作战时阵亡了,他妻子柳氏和我家那位甚是亲密,那天约着烧香的,就是她;三弟叫武翘,是个太学生。”
“左边邻居呢?”
“左边房主姓李,不过房子租给了别人,现住的姓彭,也是三兄弟,老大是影戏社的彭影儿,老二是茶坊里说书的彭嘴儿,老三原是个太医生,不过太医学罢了后,只在街上卖些散药针剂,人都叫他彭针儿。”
“这三人我都见过,竟和你是邻居。你们和他家熟吗?”
“他们搬来才一年多,并非一路人,只是点头之交。”
墨儿听后,又在厨房里四处查看了一圈,并没看出什么来,便向康潜告辞。康潜见他似乎一无所获,虽然未说什么,眼中却露出些不快。
墨儿心中过意不去,勉强笑着安慰康潜:“那绑匪没得到想要的东西,暂时应该不会对大嫂母子怎么样。我一定尽力查寻。”
又说出了“一定”这两个字。
康潜满脸郁郁,勉强点了点头。
墨儿不敢多看他的神情,忙叉手拜别,才转身,险些和一个人撞上,抬头一看,胖大身躯,络腮胡须,是彭嘴儿。
彭嘴儿其实远远就看见赵墨儿了。
他说书的茶坊和赵不尤的讼书摊正好斜对,经常能看到墨儿,却未怎么说过话。他生性爱逗人,越是本分的人,越想逗一逗。
他见墨儿和康潜在说什么,想凑过去听,等走近时,两人却已道别。彭嘴儿凑得太近,墨儿险些撞到自己,他忙伸臂护住,手里提着一尾鲤鱼,一荡,又差点蹭到墨儿身上,彭嘴儿咧嘴笑道:“赵小哥啊,对不住。又来选古董了?难怪这两天都不见你们去书讼摊子。还以为你相亲去了。”
墨儿没有答言,只笑着点了点头,问了声“彭二哥”,而后转身走了。
彭嘴儿转头望向店里,康潜已经坐回到角落那张椅上,昏暗中垂着头,并不看他。彭嘴儿又笑了笑,抬步到自己门前,按照和大嫂约好的,连叩了三声门,停了一下,又扣了两声。
门开了,却只开了一半,大嫂曹氏从里露出头,神色依然紧张,低声道:“二叔啊,快进来!”
彭嘴儿刚侧身挤进门,大嫂立即把门关上了。
“大哥呢?”
“还在下面呢。等饭煮好再叫他上来。”大嫂仍然压低了声音。
彭嘴儿将手里提的半袋米和一尾鱼递给大嫂,大嫂露出些笑脸伸手接住:“又让二叔破费了。”
“该当的。”
彭嘴儿笑了笑,以前除了每月按时交月钱外,他也时常买鱼买菜回来,大嫂从来都是一副欠债收息的模样,哪曾说过这样的话?这几天,大哥彭影儿惹了事,大嫂才忽然变了态度,脸上有了笑,话语少了刺。
大嫂拎着鱼米到后面厨房去了,彭嘴儿朝身后墙上的神龛望去,半扇窗户大小的木框里,一坨干土块,上面插着根枯枝。这枯枝是大嫂从大相国寺抢来的,大相国寺后院有一株古槐,据说已经有几百年,上面坐了几十上百个鸟巢,清晨傍晚百鸟争鸣,比乐坊笙箫琴笛齐奏更震耳。行院会社里的人都说那是株仙树,掌管舌头言语,说书唱曲的拜了它,能保佑唇舌灵妙,生业长旺。那坨土块都是大嫂偷偷从那古槐下挖来的。
大哥彭影儿这时正藏在那神龛底下。
彭嘴儿来相看这房子时,房主偷偷告诉他,这神龛正对着墙后面卧房的一个大木柜,那个木柜底板掀开,是个窄梯,可以通到下面一个暗室。他当时听了不以为然,住进来一年多,也只下去看过一回。
谁知道,大哥现在竟真的用到了这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