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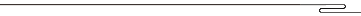
循理者共悦之,不循理者共改之。
——张载
赵不尤别过田况,又去访江渡年。
墨子江渡年终日以笔墨为伴,是个书痴,以摹写名家书法著称。前几十年,有书画大家米芾,善于摹写古时名画,即便行家也难辨真伪,因其性情癫狂,号称“米颠”。现在又有江渡年善仿晋唐以来名家书法,纤毫不差,几如拓写。因此,坊间有句俗语“画伪米发颠,书假江渡年”。
其实米芾摹写,只为爱画,他遍习古今名作,用功极深,名望又极高,从未以假混真,将摹作流布于世。江渡年虽然家境寒素,却也绝不将仿作传之于外。坊间印社书商,却常假托两人之名牟利,即便声称仿作,只要挂了两人名字,也能卖出好价。
而且,江渡年仿写绝不止于临摹法帖。二十岁之前,他的摹写已能逼真,之后,他更深入其间,以字观人,揣摩各名家性情、癖好、胸襟、学养,久而久之,不再是摹字,而是摹人,摹神。挥笔之时,他已不再是自己,而是那些书家本人。
两年前秋分那天,赵不尤和东水八子在城南吹台相聚,琴子乐致和于高台秋风之中,弹奏了新度之曲《秋水》。江渡年当时酒高兴起,因手边无纸,便脱下所穿白布袍,铺在石案上,提笔蘸墨,在布上挥毫狂书,是以东坡笔法写东坡《快哉此风赋》。赵不尤童年时曾亲眼见过一次苏轼,东坡风致洒落,神采豪逸,他虽然年幼,却印象极深。那天江渡年书写时,赵不尤看他形貌神色,竟恍然如同见到东坡本人。而白布之上的墨迹,畅腴豪爽,秋风荡云一般。即便东坡当日亲笔书写,恐怕也不过如此。
众人看了,都连声赞叹,赵不尤记得郑敦当时感叹:“这件旧衣现在拿去典卖,至少得值十贯钱。”江渡年听了,哈哈大笑,随手却将那件旧衣扔进旁边烫酒炙肉的泥炉里,火苗随之噬尽那风云笔墨。众人连叹可惜,他却笑道:“以此衣祭奠东坡先生,东坡泉下有知,亦当大笑,快哉此炬!”
和田况一样,江渡年也曾被召入宫中书院,他不愿做御前书奴,不得自在书写,也托病拒谢了。反倒应召去了集贤阁做抄写书匠。
当今天子继位后,在蔡京协倡之下,大兴文艺,广收民间书画古籍。一些稀有典籍藏于馆阁之中,需要抄写副本。江渡年正是希慕这些典籍,去做了个抄书匠。每月得几贯辛苦费,聊以养家。
去年蔡京致仕,王黼升任宰相,停罢了收书藏书之务,江渡年随之也被清退。他生性狂傲,又不愿卖字营生贱了笔墨,就去了一家经书坊,替书坊抄写经书刻本。照他的讲法,卖字是为身卖心,抄书写刻本,却是播文传道。
赵不尤记得江渡年现在的东家是曹家书坊,当年以违禁盗印苏轼文集起家。这书坊在城南国子监南街,也不算远,便步行前往。
进了东水门,向南才行了小半程,就见前面云骑桥上,一个人飞袍荡袖、行步如风,看那野马一般的行姿,赵不尤一眼就认出,是江渡年。
“不尤兄,我正要去找你!”江渡年一向不修边幅,唇上颌下胡须也如野马乱鬃一般。
“巧,我也是。”
两人相视大笑,一起走进街角一家酒楼,随意点了两样小菜,要了两角酒。
赵不尤又将章美去应天府的事告诉了江渡年,和郑敦、田况一样,江渡年也大吃一惊,连声摇头,不愿相信。
赵不尤劝道:“眼下最要紧的是查明他二人去应天府的缘由,渡年,你再仔细想想,他们两人这一向是否有什么异常?”
“我琢磨了两天,发觉郎繁和章美那天的确有些异样。”江渡年大口饮了一盅酒,用手抹了抹髭须浓遮的嘴。
“哦?说来听听。”
“你也知道,我这些年摹写书法,渐渐摸出一些门道,透过字迹去揣摩人的心性。后来觉得,不但字迹,人的神色语态也可揣摩。这两天,没事时,我就反复回想他们两人寒食那天相聚时的情形。就拿这酒杯来说,喝了酒,两人的手势和平时都有些不同。先说郎繁——”
江渡年端起手边的空酒盅,比划着继续道:“郎繁平日不太说话,心里却藏着抱负,又一直得不到施展,所以有些郁郁寡欢。他平日喝酒,饮过后,放杯时总要顿到桌上,好像是在使气。寒食那天,他喝过酒,放下杯子时,照旧还是顿下去,不过酒杯放下后,手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随即放开,而是捏着杯子,略停半晌才松手。我估计,他恐怕是在留恋什么,或犹豫什么。”
赵不尤照着江渡年说的,拿起酒杯也仿做了一遍,仔细体会其间心绪变化。放下酒杯时,重重顿杯,一般有两种情态,一种是心有郁气,无意间借物宣泄;另一种是性情豪爽,处处使力,显现豪气。郎繁无疑属于前者。
杯子顿下之后,手若随即离开,说明心事不重,手若仍握着杯子,则是心事沉重。据郎繁妻子江氏所言,郎繁先是心事重重,后来似乎已经想明白,作出了决断。但就这握杯手势而言,他所作的决断,必定十分沉重,因此才会握杯不放。
于是他问道:“渡年果然好眼力,你说得不错,握杯不放,应该是留恋和犹豫。那天他顿杯时,和往常有没有不同?”
“我想想……顿的时候,似乎比往常更用力一些。”
“更用力?这么说来,他那天顿杯,不是发泄郁气,而是表诚明志。他是作了一个重大决断。”
“什么决断?”
“赴死。”
“哦?”江渡年睁大了眼睛。
“你们那天说,寒食聚会上,章美和郎繁争论孟子‘不动心’,郎繁说人怎可不动心?一定是有什么让他动了心,即便舍身赴死,也在所不惜。然而,生死事大,再果敢勇决,面对死,也难免踌躇犹疑,他握杯不放,其实是在留恋生。”
“究竟是什么事?”
“目前我也无从得知。这事先放一放,你再说说章美那天的不同。”
“嗯,章美……”江渡年捏着酒杯,低眼回想半晌,才又说道,“章美为人稳重谨慎,平时放杯不轻不重,放得很稳,从来不会碰倒杯子,或洒出酒来。但那天,他似乎随意了一些,放杯子时,时轻时重,还碰翻过一次杯子,杯子翻了之后,他还笑着用中指按住杯沿,让杯子在指下转了几转——”
“据你看,这是什么心情?”
“我觉着似乎有些自暴自弃的意思。”
赵不尤又拿起杯子,反复照着做了几遍,发觉不对,摇摇头道:“恐怕不是自暴自弃,章美一向守礼,转杯,有自嘲的意思,也有些越礼放任的意思。此外,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我估计,他也有什么心事,心不在焉,因此才会碰翻杯子。此外——还有一些心绪,我一时也说不清……”
“对了,平日我们争论时,他从不轻易动怒,更不嘲骂。但那天,他多喝了两杯,语气似乎有些放纵,对简庄兄都略有不恭。”
“哦?”
赵不尤忽然想出刚才难以揣测的另一种心绪:不满。
章美越礼放纵,一定是对什么事,或什么人不满。那天是东水八子寒食聚会,他难道是对座中的某人不满?是谁?难道是对郎繁不满?
他忙问:“章美和郎繁那天争论时,可否动怒?”
“没有,他们两个很少争执,那天也只是各陈己见,说过就完了。”
“那天他还和谁争执过?”
“再没有。”
“宋齐愈呢?那天没有争论新旧法?”赵不尤忽然想起宋齐愈主张新法,其他七子则愿守旧法。其中章、宋两人情谊最深,但也最爱争执。尤其一旦提到新旧法,两人势同冰炭。
“嗯……”江渡年低头捏着酒杯,摇头道,“没有。那天大家兴致都不高,并没说太多,聚了一会儿就散了。”
“为何?”
“各自都有事吧,尤其简庄兄,他的学田要被收回,生计堪忧。”
“这一向,其他人可有什么异常?”
“似乎没有。”
宋齐愈那夜在船上并未睡好,躺在铺上,一直笑着回味与莲观的一番对话。
第二天,他早早起来,走到舱外,想着或许能见莲观一面。然而,他们住的小舱和莲观的大舱中间还隔着个上下船的过道,过道那边又是昨夜那位唐妈的舱室,他站在船尾的艄板上,不时望向过道。那边舱门始终未开,连唐妈都没见到。
他向船工打问,船工却只知道莲观姓张,其他一概不知。
很快,船便到了汴梁,停在力夫店的岸边。章美和郑敦也已经醒来。他们三人从过道处下了船,从岸上绕到船头,前面大舱的窗户都关着,仍没见到莲观。只看到船主站在船头指挥着船工降帆收桅。他们过去向船主道谢,并拿出小包袱里的备用银子,要付船资,船主却说那位小姐吩咐过,不许收。
宋齐愈一听暗喜,正好去向莲观拜谢,谁知道一位锦衣妇人走到船头,冷冷对他们道:“我家小姐说不必言谢。”听声音,正是昨晚那位唐妈。
宋齐愈大为失望,只得向唐妈及船主道别,见到岸边的力夫店,正好腹中饥饿,三人便走了进去。郑敦和章美忙着要尝尝汴京的美味,宋齐愈的眼却始终望着那只客船。
几个男仆先将一些箱笼搬下船,而后几个仆妇提着些包袱什物上了岸,看着东西都搬完后,那位唐妈才下了船。最后,才见一个绿衣婢女扶着一位小姐,踩着踏板,小心下了船,那小姐自然是莲观。
莲观头上戴了顶帷帽,轻纱遮着面庞,看不清。她上身穿着莲叶绿纹的白罗衫儿,下身也是莲白色罗裙,露出秀巧的绿绣鞋。当时是初夏清晨,雾气还未散尽,略有些河风。清风轻轻掀动她的面纱和衫袖,玉颈和皓腕时隐时现,却始终不露真容,只见她身姿纤袅,细步轻盈,如一朵白莲在浅雾间飘移。
岸上已经有一顶轿子候着,绿衣婢女扶着莲观上了岸,坐进轿子,轿帘随即放下,再看不到莲观身影。宋齐愈怅望着轿子走远,心里也起了雾,一阵空惘。
到太学安顿好后,宋齐愈便开始四处打问姓张的员外郎。
但员外郎只是从六品的官阶,京中不知道有几百位,即便姓张的,也有几十位。他一个一个打问过来,都没能找到莲观的父亲。
后来他以为自己听错,又开始打问姓章,甚至姓占、姓展、姓翟的员外郎,却一无所获。渐渐地,他也就断了念,甚至觉得莲观只是梦中一朵白莲,连其有无都开始恍惚。
当他已经淡忘的时候,有天却从太学门吏的手中接过一封信,打开信一看抬头两个字竟是:莲观……
琴子乐致和在老乐清茶坊里,正拿着块帕子擦拭桌凳。
这时天尚早,茶坊里还没有客人,店前的汴河上早雾未散,只听得到三两只早船吱吱呀呀的桨橹声,远处偶尔一两声晚鸡啼鸣。
这老乐清茶坊是他伯父之业,因伯父无子,乐致和自小便被过继给伯父,他虽爱读书,但更爱清静,不愿为利禄而焦心奔忙。长到十五六岁,就帮着伯父料理这间茶坊。这几年,伯父年老,他便独自操持起来。单靠卖茶水,一年只能赚些辛苦衣食钱,故而汴河两岸的茶坊都要兼卖酒饭。他却嫌油污糟乱,只愿卖茶,生意一直清冷。后来因他们东水八子常在这里聚会,这间茶坊渐渐有了雅名,来这里喝茶的大多是文人士子,虽不如其他茶坊火热,却也足以清静度日。
今天虽然四下清静,乐致和却有些烦乱。平日,他最爱擦拭桌凳、清扫店面,一为生性爱洁,二则是由于以前曾听过简庄一席言。有天他们八子聚在这茶坊里论道,简庄见宋齐愈谈得高远,甚至流于庄子玄谈,便转述了其师程颐的一句话:“形而上者,存于洒扫应对之间,理无小大故也。心怀庄敬,无往非道。”
乐致和听到这话,大为受用。少年时,有位潦倒琴师常到他家茶坊来喝茶,那琴师琴技高妙,但性情孤傲,不愿去勾栏瓦肆里卖艺,只在人户里教子弟学琴,他虽寄食于人,却脾性急躁,主人稍有俗态怠慢,抱琴就走;弟子稍有不顺意,便连骂带打,因此没有一家能待得久。乐致和有天到茶坊里玩,琴师见到,一把抓住他的小手,反复揉捏细看,赞叹他天生一双琴手,便向乐致和的伯父说:“我要教他学琴!倒给钱也成!”
果然,乐致和一坐到琴前,便像换了一个人。他原本生得细瘦,背又略有些驼,一向不起眼。然而只要坐到琴前,身子顿时挺拔,眉眼间也散出清秀之气。学琴也极颖悟,三两个月已经上手,一年后已能熟奏十几首古曲。
这时,那琴师却患了不治之症,临终前,琴师将自己那张古琴送给了他,又抓住他的手,喘着气拼力说:“记住!琴比身贵,曲比命重。”
从此,乐致和便一心沉入琴曲之中,对那张古琴也爱之如命。那琴师传给他的琴曲大多清劲孤峭,如绝壁松风、危崖竹声一般,正合他的少年心性,渐渐将他引至孤愤幽怪之境。直到数年后,鼓儿封偶然来到茶坊歇脚。
鼓儿封是个鼓师,常日在酒楼茶肆里给歌妓击鼓伴唱。乐致和虽曾见过,却从未说过话。那天天色已晚,茶客已散,他在后院中弹奏《孤竹》,一曲奏罢,才见到鼓儿封站在门侧茶炉边,目光闪亮,满眼赞叹。那赞叹显然是懂琴之人才会有,再看鼓儿封,衣着虽然俭朴,气宇间却有股清硬不折之气。乐致和还留意到,鼓儿封赞叹之余,眼中似乎另有些疑虑。
他有些纳闷,起身致礼,鼓儿封忙回过礼,赞道:“小兄弟年纪轻轻,琴艺竟已如此精熟,难得!难得!而且这琴音像是水洗过一样干净清明,没有丝毫俗情俗态,我这双老耳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这么清亮过了。”
乐致和忙道:“老伯谬赞。老伯定然也会弹琴?”
“老朽以前也曾胡乱摆弄过,不过在你面前,哪敢说‘会’字?后来手残了,就没再弹过了。”
鼓儿封愧笑着展开双手,两只手的食指都缺了一截。乐致和见到,心里一惊,这残缺虽小,对弹琴之人却是致命之伤。他抬头望向鼓儿封,鼓儿封却笑得爽朗,看来早已不再挂怀。
乐致和便问道:“我看老伯方才眼中似有疑虑,不知为何?”
鼓儿封歉然道:“这话也许不该讲,不过总算是琴道中人,还是说一说吧。方才一曲,在老朽听来,心境似乎过于幽绝险怪了。以老弟年纪,正该三春生气、朝阳焕然才对。论起弹琴的人,当年嵇康是最狂怪的,但他弹琴时,‘手挥五弦,目送飞鸿’,那心境也是超然世外,极广极远,并没有一味往孤僻处走。”
乐致和听了,心里大惊,如一道闪电裂破苍穹。除了那位琴师,他并没有和第二个人论过琴,一直都在一条幽径上独行,自己也隐隐觉得越走越险窄,却难以自拔。鼓儿封正说到了他心底最不安处。
他忙再次叉手致礼:“老伯见多识广,一语中的,还望老伯多多赐教!”
鼓儿封愧笑道:“老朽说浑话,哪里敢教人?何况老弟你这琴艺,我在你这年纪是远远赶不上的。”
乐致和却忙请鼓儿封到前面坐下,点了盏上好的茶,再三求告:“自教我琴的老师亡故后,再没有人指点我,今日有幸能遇到老伯,老伯也说同是琴道中人,就请老伯不要过谦吝惜。”
鼓儿封也就不再推让,诚恳道:“老朽当年也有过一段时间,只好奇险,越怪越爱。后来,我的老师传给我一句话,他说‘琴心即天心’。这句话老朽想了半辈子才渐渐明白——一般人弹琴,心里只有个自己,可自己那颗心再大,也不过方寸,你便是把它角角落落都搜检干净,能收拾出多少东西来?何况其中大半不过是些小愁小恨,弹出来的曲,也只是小腔小调。好琴师却不同,他能把自家那颗小心挣破、丢掉,私心一破,天心就现。这好比一颗水珠在一片江海里,水珠若只会自重自大,就始终只是个小水珠,但它一旦破掉自己,便是江河湖海了……”
乐致和听鼓儿封言语虽质朴,道理却深透,如一只大手拨开了他头顶云雾,现出朗朗晴空。半晌,他才喃喃道:“琴心即天心,伯牙奏《高山》《流水》,其心便是天心。能静能高者为山,能动能远者为水;山之上,水之涯,皆是天……”
从那以后,乐致和便与鼓儿封结成忘年之交,他的琴境也随之大开。
后来他又得遇简庄等人,谈学论道时,更发现鼓儿封所言琴理,和儒学所求乐道,两者竟不谋而合。儒家之乐,用以和心,讲求平和中正,其极处,便是鸢飞鱼跃、万物荣生的天地仁和之境。
尤其听简庄转述师言,洒扫应对皆是道,他不但在弹琴时蓄养和气,即便擦拭桌凳,清扫地面时,也静心诚意,体味其间往复之律、进退之节。
然而这两天,他却心气浮动,再难安宁。他放下手中帕子,望向河面,那只藏有郎繁尸体的新客船已经挪走,只有汤汤河水缓缓而流。偌大京城,人口百万,却只有东水八子能令他情投意合、心静神安,如今却一亡一失……
他长长叹了口气,重又拿起帕子,正要动手擦拭剩下的一小半桌面,却见赵不尤走了进来。
赵不尤这两天心绪也有些烦乱,但他知道心静才能烛理,何况这个案子牵连极广,便随时调息,不让自己乱了心神。
昨晚,顾震派万福送来了两样东西,是从那个服毒自尽的谷二十七身上搜出的,一条纱带,一个瓷瓶。
他先看那瓷瓶,只有拇指大小,却十分精巧,釉质光洁,白底青纹,一枝梅花纹样斜绕瓶身。拔开瓶塞,里面空的,他嗅了嗅,还残余着些气息,略似蒿草气味。
“那个谷二十七就是喝了这瓶子里的毒药自尽的。已经找药剂师查过,是鼠莽草毒,和客船上那二十几人所中的毒一样。”万福道。
赵不尤又看那条白纱,约有二尺长,五寸宽,中间一段光滑平整,有些发硬,他摸了摸,很滑,凑近灯仔细看,似乎是涂了层透明清漆。
万福又道:“府里许多人都看过了,谁也猜不出这是做什么用的。赵将军可想得出?”
赵不尤注视着那条纱带,摇了摇头:“我一时也看不出。船上那些死尸身上可搜出这两样东西?”
“没有,都是些随身常用之物。那案子已经封死,不许再查,这证物也就没用了。顾大人就向管证物的库吏要了来,说赵将军恐怕能从中查出些线索来。另外,顾大人也已经写信给应天府的朋友,让那边帮忙查问那只梅船的来历。”
赵不尤点了点头:“寒食那天下午,郎繁并没有搭乘客船,他也应该不会骑马去应天府,我估计应该是搭乘了官船。有劳你回去转告顾兄,若有空闲,请他再去汴河下锁税关,查问一下那天下午离京的官船。”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