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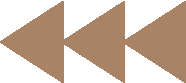
克里斯蒂安·罗伊—斯米特/邓肯·斯尼达尔
这本《手册》究系何类?一本参考书?一本入门书?一本评论性文集?一本研究类著述?它是描述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国际关系还是阐释作为一门研究学科的国际关系?如系后者,它是描述学科的现状还是指明其发展方向?
本书既兼而有之又不属其中任何一类。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成为学习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的一个实用的切入点,加深年轻学者以及资深学者对本学科多种理论视角和分支流派的认识。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既是一本入门书,又是一本参考书。但是,我们对本书的设想远不止如此。我们希望它触及国际关系学科领域内的争论,并带着批评和反思参与其中。鉴于我们的目标在于推动而非陈述争论,因此,本书远非一本评论性文集。作为学者,我们的研究内容及动机决定了我们的成果,因此,我们将本书视为探讨作为政治实践的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的研究类著述。
上述目标在两个层面指导了这本《手册》编写的构思。首先,作为编者的我们更加清楚如何对本书的中心主题和整体结构进行取舍。我们认为这本《手册》不仅仅是一份调查,而且是一种介入,我们试图以一种特别的视角来审视整个学科。正如下文所述,本书内容围绕两大主题展开:一是经验性(和/或实证性)(empirical and/or positive)理论与规范性理论之间的关系;二是不同理论、方法及分支学科之间的动态关联。另外,对本书的目标定位也让我们尝试对这本《手册》的内容进行拓展。在写作过程中,我们除了要求诸位作者对上述主题予以回应,还请求他们超越简单的评论或解释,以求“立新”,并提出启发性的论点和阐释。
本章阐述了这本《手册》设计的大致思路,并就国际关系学科的本质提出了一系列观点。这也是我们通读后续章节后得出的观点。我们尤其关注互相关联的三个问题:国际关系中的理论研究本质是什么?经验性理论与规范性理论的互动如何塑造了各个理论并影响它们之间的争论?最后,国际关系研究是否有所进展,如果有的话,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尽管上述问题没有一个特定答案,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得出许多一般性的结论。首先,本书各章节帮助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一个明晰的理解。本书章节涉及面广泛,足以涵盖盛行于本学科的各种理论化的形式。我们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包含三个组成部分:问题、假定及逻辑论证。其次,可以将国际关系理论理解为相互竞争的实践性话语。尽管理论学派差别明显、相互争鸣,但它们的形成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我们应该如何行为”这一问题所推动。国际关系理论这一不变特征能够解释为什么它们兼有经验性和规范性两方面。最后,本书作者对国际关系中各种理论、方法和问题的探讨,希望能引发人们推动该学科的进步和拓展。他们所著章节的内容包含更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包含跨越范式和传统的更频繁的交流和互动,并且更巧妙地借用了其他学科的思想。然而,推动不同领域内部进展,主要依靠不同理论视角之间的争论。如驾驭得当,这种争论能促进相互间的了解,甚至可以同时解释为什么有时候该学科整体上看起来发展停滞。
关于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的概述和总览的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些著述或将其作为一门学科,或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实践。虽然深度有所参差,但每年都有新的概论出版,本书绝非该领域的第一本《手册》。然而,除个别外,这些书籍的编写均采用共同的方法,差异仅限于形式。作者和编辑们选定值得探讨的若干话题(我们也做了选择),再由各作者紧扣话题精心编写各章节。不过,这些“卷册”很少有自己独特的、超越书内各章节的“声音”。例如,最近要出版的一本手册既没有导入性框架章节,也没有总体结论(Carlsnaes, Risse, and Simmons 2002)。虽然那本书写得很好,但它对其审视的领域并未做出评论或总结。我们的目标在于跨越这一惯常方法以期发出这本《手册》自己的声音。
首先,这本《手册》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其所强调的一些东西。它强调理论、国际关系作为学科的概念、理论进展中的争鸣、不同的理论视角以及世界政治研究的方法论。对上述内容的强调并非因为我们重视理论胜过经验分析,或重视抽象理念胜过“实用的”学术形式;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理论假定(及相关争论)决定了该学科的轮廓,即便对最重视经验分析的研究也有影响。对国际关系学科的探究首先应当探析那些令其充满活力的理念,即那些将国际关系(或全球政治)凸显为一个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理念、决定该政治领域知识构成的理念、决定哪些问题值得回答的理念以及塑造该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理念。否则,国际关系这一学科将失去其身份、发展脉络以及生命力。
鉴于这本《手册》强调这些东西,这就决定了我们不会在特定章节专门探讨经验性问题,如大国竞争、武器扩散、环保、人权、民族主义以及国际贸易和金融等。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并非对这类问题不感兴趣,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恰恰是我们相信本书所提出的这些理念和争论贯穿并支撑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理论和方法论思想决定了对于国际关系学者来说哪些问题是真正的研究重点,而且也提供了学者们在求知过程中所采用的知识工具。当然,特定问题尤其是新问题的复杂性确实充当了理论创新的催化剂,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往往促使国际关系学者们从其他研究领域引入新思想。不过,我们的策略是专注于以国际关系为思想和理论的背景,要求作者们利用其不同的经验知识各抒己见。当下文献资料中考察新、旧问题范畴的篇章如此之多,再多一本此类问题的汇编没有必要,这一考虑也促使我们选择目前的策略。
这本《手册》最突出的特点并不在于我们专注于理论,而在于我们的理论 兼具 经验性和规范性。绝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书籍都专注于经验性(或实证性)理论,即使规范性理论被提及,也仅被放在最后一两个有关“伦理与国际事务”的章节里面。耐人寻味的是,该情况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著述中均出现(见Carlsnaes, Risse, and Simmons 2002; Baylis and Smith 2005; Burchill et al. 2005)。由此得出的假定似乎是经验研究可以与规范研究分割开来,而国际关系理论近乎成为一种排他的经验性(或实证性)研究课题。虽然人们(在有限的程度上)承认,在此之外还存在一套将国际社会视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即规范性理论),但它只是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的专有之物,其默认的观点是国际关系研究是为了进行解释而做出的努力,与之相关的是世界政治的“实然”,而非“应然”。
这种分割性视角不能持续,亦无益处。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政治理论都具有重要的经验性
和
规范性维度,它们在深层次上存在不可割裂的联系。现实主义者批评国家政府的行为不符合国家利益,面对国际秩序的不稳定,其批判的基础是利益和秩序这两种价值,在这方面,只有规范性理论可以支撑。后现代主义者基于解构的学术立场,提出无情批判时,并非是为了进行现实阐释(尽管这是他们的部分动机),而是因为这对权力和统治结构构成了某种对抗。确实,正如这本《手册》各章的作者们所呈现的,每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同时探讨世界的“实然”形态和“应然”形态。该学科多样性的一个核心在于学者们及其因应的理论传统对于理论的规范性和经验性之间的关系所持的不同取向。有些人热衷于二者的交叉,有些人试图抹掉其理论的规范性特质,其他人则相反,重视哲学反思胜于经验知识。然而,所有的理论家都或深或浅地踏足过经验分析与规范分析的交叉地带。对于为何我们的理论同时兼具经验性和规范性,传统的解释是认识论使然。一直以来,批判理论家认为,当我们就这个世界提出问题并决定以哪种方式、做何研究来寻找问题答案时,我们的价值观就融入了我们的探索之中(经典说法见Taylor 1979)。在此,我们不挑战这种观点。但我们的解释与此不同。从最初起,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是一种实践性话语。我们说的“实践”一词不是哈贝马斯所指的深奥含义,也并非为了鼓噪实践胜过理论的简单化思想。相反,我们指的是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论其形式如何,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们应该如何行为”这一问题有关。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概莫能外。它适用于那些寻求用理论解决问题的学者,同样也适用于那些聚集于批判理论旗下的学者。关于这一问题,不同的视角关注的问题领域不同,就采取何种行为达成的结论也不同。因此,不论这些理论关注的是促进和平、秩序、制度建设、经济福祉、社会赋权还是消除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的歧视,不论他们是否主张权力制衡、贸易自由、社会矛盾的激化还是对抗所有社会权力的机构和话语,它们都能被“我们应该如何行为”这一问题所激发和推进。

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实践性话语,这一不变的本质解释了(远远超出认识论的原因)为何所有的理论都 兼具 经验性和规范性。如果对于我们行为(经验性)所处的世界不加审视,对于我们试图实现的目标(规范性)不加了解,我们则无法回答“该如何行为”这一问题。这是爱德华·哈勒特·卡尔(E. H. Carr)所著《二十年危机》的中心观点,即纯粹的现实主义或者理想主义,如果成为一种实践性话语,它们就无法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幸存。没有了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则一片荒芜,毫无目的可言;没有了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则不谙世故,对于行为所处的世界全然无知。对于卡尔来说,国际关系必须成为一门将“实然”与“应然”相结合的政治科学,“由此,乌托邦与现实是政治科学的两个方面,只有在二者并存的地方才会有健全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Carr 1946,10)。
卡尔做出此番言论,试图呼吁国际关系能够往某种特定的形式或趋势发展。我们认为并非他的愿景引导了该领域的发展和走势。但是,他传递的这一信息从未被误读。相反地,我们认为,卡尔发现了一个真相,7即所有话语均带有实践性的抱负。然而,一旦有了这种抱负,不论怎样隐藏或否认,理论家被迫夹在经验性和规范性之间。对部分学者而言,情况就是如此,他们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够以政策建言或者政治对抗的形式直接影响“该如何行为”这一问题。不过,要应对与现实问题有内在关联且无法割离的议题时,即便是那些纯粹的理论派学者们,他们在面对经验性或规范性的理论边界时也会束手束脚。该学科从未落入纯经验研究或纯规范研究的范围内,这一状况注定仍将继续。
本书力求突出并完全展现国际关系理论的这一双重性,而不是将其压制。这并非仅仅因为理论的双重性将成为一种有趣的、启发性的了解该学科的方式,尽管事实也确实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实践性话语的定位及其对政治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的反思。正如本书的很多作者(来自该学科不同分支)所强调的,即便我们的声音不同、视角不同,但我们希望国际关系能成为一门学科,直面当下政治行为所涉及的最严峻的问题。然而,这种期望意味着国际关系学者的探索必须游走于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之间的交叉地带。到目前为止,现实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建构主义者们在这个交叉领域的探索具有一定启迪性。此外,强调所有理论兼具经验性和规范性的双重性,也是对学者们提出挑战,促使他们对该学科已建立的假定和假想进行思考和质疑,以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式重新思忖学科理论。
贯穿本《手册》的第二个主题是不同理论和方法论视角之间的动态互动。这也是本书别具一格之处。绝大部分的总览、概论和纲要都把视角作为单独的思想主体,类似于“这是现实主义”“这是自由主义”“这是建构主义”等。单个章节几乎总是对照“其他”理论来塑造自己的主题理论,通常来说,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突出某个理论的独到之处,其次才将该理论的演进与更大的理论背景联系起来。当然,将该学科的演进作为探讨对象的尝试也屡见不鲜,其中最常被援引的是那些层出不穷的大辩论: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古典主义对科学主义,反思主义对理性主义(Lapid 1989)。但是,不管前一种介绍理论的思路有何种优点(多年来它们帮助很多学生融入该学科),它们都是在宏观层面发挥作用,而模糊了不同视角之间的互动、对话和争论。我们感兴趣的恰恰在于理论之间的互动层面。现有方法的局限性如何引发了新方法的出现?现有视角对新的挑战者做出了何种回应?随之而来的辩论和论争怎样塑造了相互竞争的流派的本质呢?各理论之间如何彼此借鉴,增强自身理论的阐释力,引发对其他理论更多启发性或批评性的思考?该学科最终是各学派相互交流、互相构成,还是各自为政、互不理解?
上述两个编写主题贯穿整本《手册》。这既是本书作者们的组织策略,也启发其思考。本书的编排范围广泛,这反映了我们对相关思想争论的脉络及其发展的判断。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关切是什么,本书就此问题从一系列不同视角的争论作为开篇:国际关系的核心关切是主权国家间的关系(莱克,本书第二章),还是全球层面的更为广泛的政治关系(巴奈特和辛金克,本书第三章)?更加激进地看,“国际关系”或“全球政治”这样的理念本身是否就是一种不恰当地将某些立场置于优先地位的本体论框架(考克斯,本书第四章;达比,本书第五章)?
思考了上述问题后,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本书篇幅最长的一部分,探讨该学科主要的实体理论及其伦理: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英国学派、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以及女性主义。
 我们对于理论的经验性和规范性的关注在此部分体现得最为明显。与每一章探讨一种理论的惯例不同,这本《手册》每两章探讨一种理论:一章概述和探讨相关理论,另一章则致力于挖掘其潜在的伦理立场和观点。我们在第三部分安排的第一篇文章是彼得·卡赞斯坦和鲁德拉·希尔对折中理论优点的论述(本书第六章)。当下人们似乎对于该学科不同理论传统间的沟通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因此,在这部分的开始放置一篇系统性研究范式间对话优势的文章恰逢其时。
我们对于理论的经验性和规范性的关注在此部分体现得最为明显。与每一章探讨一种理论的惯例不同,这本《手册》每两章探讨一种理论:一章概述和探讨相关理论,另一章则致力于挖掘其潜在的伦理立场和观点。我们在第三部分安排的第一篇文章是彼得·卡赞斯坦和鲁德拉·希尔对折中理论优点的论述(本书第六章)。当下人们似乎对于该学科不同理论传统间的沟通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因此,在这部分的开始放置一篇系统性研究范式间对话优势的文章恰逢其时。
下一部分探讨了有关研究方法的一些思想。本书关于方法的概念十分宽泛且包容。对某些人而言,方法是实证主义者的专属品,这只是他们的成见,这些人将国际关系视为建立在自然科学模型基础上的一门社会科学。但是,与理论一样,方法不可回避。目录中的每一章都表明了一种方法,这些方法都是作者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寻求最佳答案而做出的选择。这些选择,有时候是作者进行系统性思考的结果,有时候则是作者的直觉。但是,正如无法绕开方法一样,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因为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方法。要找到问题的最佳答案,有的要通过定量方法,有的要通过定性方法,有的要通过历史学方法,有的则要通过哲学的、解构的以及谱系的方法,而有的则需要巧妙地通过两种或多9种方法的组合。我们的作者探讨了若干主要的方法:理性选择法(基德,本书第二十五章)、社会学方法和诠释法(克拉托奇维尔,本书第二十六章)、心理学方法(戈尔德吉尔和泰特洛克,本书第二十七章)、定量方法(曼斯菲尔德和佩弗豪斯,本书第二十八章)、定性方法(贝内特和埃尔曼,本书第二十九章)以及历史学方法(夸克,本书第三十章),本书前一部分探讨过的众多学派业已彰显了这些方法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认,我们的选择仍未能穷尽所有方法。
之后,本《手册》涉及该学科的边缘领域:国际关系学科分支间的内部边界以及国际关系与其近邻学科间的外部边界。由于令学术界活跃的“国际”问题大量增加(从最初集中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到如今囊括从全球金融到人口迁移等各种问题),学界出现了两个十分明显的趋势。一方面,在“国际关系”大旗下的独立学科骤增。其中有些自成体系,以至于它们与这面大旗的关系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战略研究、对外政策研究或国际伦理学是国际关系的子领域还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呢?另一个趋势是国际关系学者正在走近其他学科,其中最主要的有经济学、法学以及欧陆社会理论。在某些情况下还涉及在国际关系学科形成之初曾被视为一门完整学科的学术领域。国际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本《手册》的第五部分探究了上述边缘领域的动态,尤其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学(雷文希尔,本书第三十一章)、战略研究(艾森,本书第三十二章)、对外政策分析(斯图尔特,本书第三十三章)、国际伦理学(纳尔丁,本书第三十四章)以及国际法(拜尔斯,本书第三十五章)等的发展。围绕国际关系学科的实质性关注点、理论演进的本质、各种“主义”的相关优点、特定方法的妥适性以及各分支的完整性等方面展开争论的同时,人们对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合适关系亦充满了疑虑。对某些人来说,学者的“角色”就是“将真相告知当权者”,罗伯特·基欧汉在本书的一个章节中强调了这一立场(本书第四十二章)。对其他人来说,政策相关性以及与政府互动才是对学术的真正考验。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假装说出真相使得国际关系学者们极易与权力及统治有牵连。这些争论的若干核心问题包括学术研究的身份定位、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本质以及“科学”与客观性的关系等。在这本《手册》的不同部分,许多学者都谈到了这些问题。在第六部分,亨利·诺(本书第三十六章)和约瑟夫·奈(本书第三十七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
第七部分探讨了该学科的多样性问题或者说缺乏多样性的问题。在美国国内,人们往往认为(而且往往是下意识地认为)美国学者关注的理论、方法论以及实际性的问题界定了作为一个政治研究领域的国际关系的本质,且框定了其轮廓“——美国的国际关系就是整个国际关系学科”。在美国之外,人们经常会注意到这种沙文主义并对此表示担忧:美国学界对该学科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该学科对美国学者和出版商青睐有加的问题、他们的分析视角及采用的研究方法特别重视,使得“国际关系成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虽然美国学界对该学科具有不容否认的“向心力”,明确的权力关系便是这一向心力的特征。但是,全球范围内国际关系研究的多样性应该得到认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法国以及德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彼此迥异,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与美国学界的国际关系研究完全相同。我们的作者要探讨的就是该学科同质性或异质性(在霸权内部寻求多样性的可能)的这些问题,他们尤其关注的是“来自南半球”或“第三世界”的国际关系观点(布莱尼和伊纳亚图拉,本书第三十八章)以及前霸主内部的国际关系视角(利特尔,本书第三十九章)。
本《手册》最后部分包括五篇篇幅较短的文章,每一篇对该学科的现状以及(更为重要的)未来方向的理解都不尽相同。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国际关系都是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学科,从某种程度上讲,当前依然如此。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从事该学科的男女比例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女性本科生、研究生以及研究人员急剧增加。女性的声音对于该学科的百家争鸣至关重要,在概念、理论以及分析创新方面她们常常处于领先地位。我们承认并力图反映出这一男女人数比例的变化。因此我们不仅安排了三位杰出男性的成果,他们的观点对该学科的发展颇有影响——罗伯特·基欧汉(本书第四十二章)、理查德·罗斯克兰斯(本书第四十三章)和史蒂夫·史密斯(本书第四十四章),还挑选了两位杰出女性的著述——美国的贾尼丝·彼埃里·马特恩(本书第四十章)和英国的托妮·厄斯金(本书第四十一章),这两位女性的声音在该学科也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
我们对该学科领域的理解体现在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组织上。本《手册》探讨的广泛而又彼此争鸣的理论流派也体现了我们理解的多样性。
其中一些流派彼此紧密相关,而且大多具有互补性(例如,理性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女性主义与批判理论),而其他流派则通常被认为是彼此对立乃至敌视的(例如,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进一步容纳了范围广泛的实质性的主题和议题,其中有一些主题和议题有针对性地与特定的理论流派相关联。理论流派的这一杂音体现了其多样性,对于人们理解该学科的嬗变十分关键。
国际关系学者一向对理论化过程、理论的本质以及特定理论的思想存有分歧。国际关系学科的领域划分较为清晰,因此,界定范畴成了一门看家手艺。但是,本书的作者们鼓励人们以更宽广的思路思考理论,所从事的研究可涉及种类繁多又不同质化的各种理论项目。大部分作者们不仅提倡理论间的交流与互鉴,而且他们的成果和而不同。
有关理论的定义存在争议,而(即便有可能)消除争议将背离人们探究理论间互动、推动该学科发展的初衷。因此,本书关注国际关系的理论化进程,而不是理论的本质。不论其表象如何不同,我们提出国际关系的理论化表现为三个主要方面,而且它们之间存在动态互动。
第一,理论化因应我们所提出的“国际”政治领域的(经验性的和规范性的)问题而发生。一方面,我们构建理论以回答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高度抽象的(比如那些非常活跃的形式理论化),或者是经验性的。它们可能涉及范围宽泛,或者关注点聚焦。不过,国际关系理论总是预先假定一个参照问题,而这个问题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或者我们可能生活的世界有关。另一方面,理论化经常引发问题和思考。例如,假定无政府状态会引发相似的政治活动的理论,同时也促使人们对超越无政府体系的政治变动(political variations)加以思考(Reus-Smit 1999)。第二,理论化依赖于我们对“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问题(经验性的和规范性的)做出的假定:比如“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代理人追求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规范建构了身份和利益”“话语是一种政治性建构”“讲述真理是对权力关系的约束”“人权是普世性的”“共同体是一切价值的来源”等。本体论的、规范性的以及认识论的假定之间常常出现差异(Price and Reus-Smit 1998)。但是,在现实中它们往往紧密交织。后现代主义者不接受国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这一本体论假定以及人权是普世性的这一规范性假定,并非因为它们在经验上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们在认识论上站不住脚(George 1994)。第三,理论化必然涉及逻辑论证。只有通过论证才能将与问题相关的假定组织起来,从而推断出新的结论。论证是一种创造性的媒介,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通过论证对假定进行组合,让其更有趣;对其划分层级,并赋予其意义。
与启发式或演绎式能力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是所有理论流派的共识,也是其引以为傲的标准:女性主义者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者都无法容忍逻辑上的矛盾和不合逻辑的结论。好的理论,其内部逻辑能够很好地引领人们获得新的洞见和结论。就像一个好故事,理论也有一个能够驱动论证的内部逻辑。一旦明确某些因素,人们就能得出结论并拓展出新的论点,而作为该理论逻辑上的备选因素也随之出现。这一内部动态变化促使人们形成关于世界的新理解和新观点。确实,如果某个理论的逻辑特别强大,它不仅能够推动该研究,进而能够重塑问题并形成内向性的理论“世界”。好的理论还能够发掘人们对恒量和变量的假定和理解,其处于理论之中并成为我们的行为指南。
对理论研究的这一设想囊括了国际关系领域内大多数的理论流派。它既适用于所谓的规范理论,也适用于经验理论。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关于普世伦理的经典论断的中心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应该适用何种正义原则,其基本假定是现实中的相互依赖(他从基欧汉和奈那里借用的经验思想,1977)必然导致道德上的相互依赖。它适用于批判理论,也同样适用于解决问题。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 1998)专注于世界政治中包容与排斥的模式,其有关全球范围内道德共同体扩张的观点是基于有关交往行为逻辑的假定。同样,基欧汉(1984)
以相互依赖条件下国家行为理性的假定为基础,对国际制度合作模式进行阐释。最后,理论研究的这一设想既适用于针对“如何”等阐释性问题的理论,也适用于针对“为什么”等解释性问题的理论。学者会质疑化学武器为何受到如此高度的道德认可,同时也质疑国家为什么维持权利政治的平衡,显然他们在逻辑上都以国际政治领域的假定为基础(Kaplan 1957; Waltz 1979; Mearsheimer 2001)。
因为国际关系理论解决的是有关这个世界的问题,它必然包含经验现象。即便是规范性问题,也具有经验现象作为参照物——国家之间使用武力的本质,全球范围内不平等的形式,女性的从属地位,文化等级体系,等等。虽然国际关系的边界是动态的,且存有争议,该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断演变的经验现象以及人们对经验现象的质疑。有关安全和秩序的问题持续存在,但从跨国主义到相互依赖,在全球层面不断变化的互动关系已经拓宽了这一持续性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也包括繁荣与发展问题(Risse-Kappen 1995; Gilpin 2001),以及权利与自由问题(Risse, Ropp, and Sikkink 1999)。在此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如世界大战、去殖民化、石油危机、冷战结束及“9·11”事件等。这些事件塑造并指引了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方向。当然,国际关系学科的不同理论和领域关注的是经验领域的不同方面,甚至是“同一”经验现象的不同方面。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根据彼此不同但又部分重叠的实体性问题来界定自己,导致这两个领域的学者们对世界政治以及未来可能性的理解争执不休。甚至在它们内部,差异也随处可见。人们对于“安全”一词的含义与来源的理解存在争议(Wæver 1995),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问题及理论概念,比如相互依赖、依赖、全球化等,也同样存在争议(雷文希尔,本书第三十一章)。人们甚至对特定的经验性“事实”也有争议——这个世界是单极的吗(Brooks and Wohlforth 2002)?全球化意味着同质化还是碎片化(Scholte 2005)?自由贸易减缓了还是加剧了全球不平等现象(Rodrik 1997)?这些分歧往往提出了需要加以解释的谜题,并促使人们在理论中引入新的要素。
大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化都依赖于经验证据以区分合理的观点和过激的想法。人们多把这种情形认定为实证主义,它推进了绝大部分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下面看一个看似可靠的例子,后现代主义者的标志性论断,即文本具有开放性,可予以多种解读,不存在用于判定某种解读是真实的阿基米德支点。但是,他们对于各种日益复杂化的政治话语的分析,却要立足于假定,即文本和事件接受更好或更差的解读(Price and Reus-Smit 1998; Hansen 2006)。然而,指出各种国际关系理论依赖于经验证据以支撑观点,与将证伪当作最重要任务,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只要实证主义草率地将证伪放在首位,或者仅呈现理论与经验结果相关,这就等于无视理论的重要性,即便理论无法通过经验证据来证实或证伪。它同样适用于实证性的理论化,如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 theorem)(1951)指称,所有的国际性投票或决定都无法满足某些民主愿景。
 它同样适用于规范性的理论化,如人权是普世性的(Donnelly 2003)。上述二者均无法通过经验证据来证实或证伪。概念的理论化同样至关重要,但也无法通过经验证据进行验证。那么,尽管理论化绝不能独立于经验现象,国际关系理论还是有独立于经验分析的自主性,且必须优先于经验分析。
它同样适用于规范性的理论化,如人权是普世性的(Donnelly 2003)。上述二者均无法通过经验证据来证实或证伪。概念的理论化同样至关重要,但也无法通过经验证据进行验证。那么,尽管理论化绝不能独立于经验现象,国际关系理论还是有独立于经验分析的自主性,且必须优先于经验分析。
虽说众多不同派别的国际关系理论能够和平共处,但该学科最突出的特征却是分歧。其中,两个核心分野尤为突出。第一个核心分野存在于批判理论和解决问题理论之间。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即解决问题理论“接受自己所认识的世界现状,以主流社会权力关系、政治权力关系和他们所处的制度作为既定的行为框架”,而批判理论“涉及一个规范性选择,他们支持与现行秩序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但限制了现存秩序向其他秩序转型的选择范围”(Cox 1986, 208, 210)。这样的区分十分重要,一种理论专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和政治复合体”的解放式转型,而另一种理论专注于该复合体在特定方面的技术性管控(technical management)。这二者之间有本质差别。但是,从后面几章看,这种差别也许不能用于区分特定的国际关系理论。正如理查德·沙普科特(本书第十九章)所阐释的,批判理论对该学科的贡献之一在于,关注世界政治的规范化转型不再是那些自称为批判理论家们的专属领地:建构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英国学派学者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这一领域。同样重要的是,传统上与这一批判工作无关联的理论方法却可以带来卓有成效的帮助。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者对于理解当代主权国家体系的来源做出了贡献(Spruyt 1994; 2007)
第二个核心分野存在于言语理论和形式化数学理论(formalmathematical theory)二者之间。形式化方法(the formal approach)的支持者视其为理论的最高形式,而批评者则认为它极具抽象性和不相关性。上述两种立场都有所偏颇。一个能够以数学方法建模的理论涉及强有力的演绎推理形式。这种情况下,即便理论推导基于“建模对话”(Myerson 1992),仍然同时牵涉模型论证和对实体的追求。此外,很多无法通过数学进行有效建模的问题却可以通过言语理论提升对理论的理解力。以技术层面界定研究问题会失去理论发展的意义,理论发展是与人们关注的世界直接相关的。如将该学科降格为一个可以通过数学方法建模的学科,该学科将萎缩为一片荒地。反之,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利用形式演绎,则意味着有可能错失重要的理论见解,而且有可能出现前后矛盾的争辩。

人们经常声称,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根本上是互不兼容的。后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流派常被认为不可调和,而其他流派,比如社会学(克拉托奇维尔,本书第二十六章)和心理学(戈尔德吉尔和泰特洛克,本书第二十七章)则可能没有共同语言。不幸的是,该学科有一种夸大甚至崇尚这些差异的趋势:理论的目的之一在于明确哪些是根本差异,哪些是非根本差异,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求同存异。例如,这一现象一直存在于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反复而又夸张的大辩论中。在理念和战略理性(建构主义者逐渐将这两者整合吸收;Keck and Sikkink 1998)的角色方面,这两派已经渐趋一致(理性主义者更加重视)(Goldstein and Keohane 1993; Snidal 2002)。理性主义的因果理论与建构主义的建构理论之间所谓的差异其实也被夸大了。理性选择中的核心——均衡概念是一个建构性的表述,即一系列因素和谐并存。当某一因素被替代后,和谐被打破,此时审视发展脉络才能让均衡分析具备因果性。相反,有关规范的建构主义理论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因果关系论证和经验检验的理论基础(Checkel 1999; Ruggie 2005)。即便不存在共同之处,不同视角之间经验也可供借鉴,例如批判理论挑战实证主义者关于价值中立的理想。这并不是说,不同理论在深层次上可以兼容,只是想表明,国际关系理论化的最佳状态足以明确哪些是根本性差异,哪些是可以弥合的差异。
一直以来,安全研究的发展都是为了了解战争从而控制和减少战争;人权研究是为了停止种族灭绝、奴隶制度以及虐待等暴行;国际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是为了促进国家、企业及个人之间互利的经济互动;研究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等机构旨在了解如何改善全球卫生或食品状况。尽管很多国际关系理论常常标榜自身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其背后对假定的选择从来不是客观的,推动理论发展的价值观也不是客观的。所有的理论都包含重要的规范因素,它体现在理论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概念、排除或固守的元素以及力图推广的价值观之中。然而,由于担心该派理论思想的进步会受到阻碍,当下不少国际关系理论忽视甚至否认自身的规范性基础。在本部分我们提出相反的立场——只要国际关系学科仍然是一种实践性话语,最终(虽然经常是间接的)涉及“我们应该如何行为”这一问题,学者们就不得不踏上经验与规范之间的这块模糊地带。此外,密切关注该学科伦理基础的多样性能够加深对自身行为的理解,而且在恰当的引导下,这种关注能够促进学术研究进展,因为它提升了个人或集体对当今世界政治中最迫切问题的探究能力。
出于实质问题的、方法论的以及理论方面的原因,在国际关系中,“规范”这一组成部分一直受到错误的压制。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安全是一个看似无可争议的目标,而国家则是无可争议的行为体,彻底排除了将行为目标作为问题本身进行探讨的必要性。早期的英国学派(科克伦,本书第十六章)和美国的自由主义流派(理查森,本书第十二章)分别强调了秩序和效率都是不可置疑的追求目标,二者同等重要。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忽视了对规范的关注。诚然,正如杰克·唐纳利(本书第八章)表示,即使最强硬的、以安全为目标的现实主义也包含某些伦理内容。英国学派重视规范的理论化,自由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以效率作为唯一的规范性概念的不足之处。长久以来,正义战争、外国人待遇以及公平交易等问题一直伴随着我们。目前,国际政治问题变幻不定,而且问题种类不断增加,它们包括像恐怖主义和民族冲突等安全问题的新形势、长期存在的南北问题的新态势、诸如管制等会影响国内职场和家庭的政治经济领域的新问题,以及引发人们深刻担忧的,诸如人权、全球环境等令大国也束手无策的问题。对于所有呈现的新问题,人们对其研究目标都存有争议,也无法达成规范性的共识。
行为主义、实证主义以及要创建一门国际关系“科学”的努力再一次使人们忽视了伦理考量。虽然绝大部分实证主义者都认可,规范考量与提出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效果有关,但“科学”仍被视为看似价值中立的知识生产过程的中间阶段。
 然而,规范考量深深地植根于这一被认为科学性的阶段,只不过其方式往往不太显眼。如今,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十分重视其分析内部的选择偏差。然而,受可测量性和数据可及性的影响,定量分析本身就是选择偏差的一种重要形式(曼斯菲尔德和佩弗豪斯,本书第二十八章)。深层次的价值判断必然嵌入一些颇具争议的概念定义之中,比如权力、自由、和平等概念。这些规范性的假定必定存在,只因概念化过程和衡量方法的不同而有差异。有学者固执地将研究限定于问题本身,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样的研究可以不受价值判断的影响。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做法会限制所提的问题,这本身就隐含着价值判断。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领域的“序数主义革命”对国际关系具有深远的影响。经济学家们发现,在不涉及基数个人效用或人际效用比较(这两种理论都会造成十分棘手的规范性问题)的情况下,能够导出关键的市场结果(Blaug 1985)。这一转向使经济学获得了重大的根本性发展,但付出的代价是基本上放弃了对社会福利问题的考虑;在此之前,社会福利问题在该学科一向具有核心地位。这一方法论的转向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也有所反映,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强调帕累托效率,而不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中的分配,这无形中赋予了规范性以重要地位。自由主义者对这一偏见心知肚明,但由于他们对此的分析工具不如处理其他价值观的那么强大,于是将其轻忽。当然,科学的程序,尤其是努力做到系统性、可比性以及透明性,提供了强调这些规范性因素的途径,并有可能评估它们的影响。但是,他们最多只能阐明而不是消除规范性因素。
然而,规范考量深深地植根于这一被认为科学性的阶段,只不过其方式往往不太显眼。如今,国际关系定量研究十分重视其分析内部的选择偏差。然而,受可测量性和数据可及性的影响,定量分析本身就是选择偏差的一种重要形式(曼斯菲尔德和佩弗豪斯,本书第二十八章)。深层次的价值判断必然嵌入一些颇具争议的概念定义之中,比如权力、自由、和平等概念。这些规范性的假定必定存在,只因概念化过程和衡量方法的不同而有差异。有学者固执地将研究限定于问题本身,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样的研究可以不受价值判断的影响。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做法会限制所提的问题,这本身就隐含着价值判断。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领域的“序数主义革命”对国际关系具有深远的影响。经济学家们发现,在不涉及基数个人效用或人际效用比较(这两种理论都会造成十分棘手的规范性问题)的情况下,能够导出关键的市场结果(Blaug 1985)。这一转向使经济学获得了重大的根本性发展,但付出的代价是基本上放弃了对社会福利问题的考虑;在此之前,社会福利问题在该学科一向具有核心地位。这一方法论的转向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也有所反映,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强调帕累托效率,而不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中的分配,这无形中赋予了规范性以重要地位。自由主义者对这一偏见心知肚明,但由于他们对此的分析工具不如处理其他价值观的那么强大,于是将其轻忽。当然,科学的程序,尤其是努力做到系统性、可比性以及透明性,提供了强调这些规范性因素的途径,并有可能评估它们的影响。但是,他们最多只能阐明而不是消除规范性因素。
人们完全以逻辑替代价值观,这种有误导性的做法更使伦理考量被束之高阁。这一趋势越发明显,体现在理性选择将“应然”和“实然”作为“规范”理论和“实证”理论的区别。实证理论分析一系列行为体的互动之后产生的逻辑结果,假定它们的目标和能力,而对那些目标不做评估或判断。当然,这些关于行为体本身及其目标和能力的假定一部分本身就是规范性的主张,而关于预测的规范性内容则是那些最初激发我们分析兴趣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理性选择否认其规范性传统及可能性,这是自欺欺人的。除了源自明显的功利主义传统外,理性选择可以被视为有关行为体在特定条件下应该如何行为的一个规范性理论(即理性行为是什么)。这与经验主义对于行为体行为的预测一样。重要的是,理性常常会变得薄弱,人们不能认定行为体可以完全达成自己的目标(Levy 1997)。此外,多数的理性选择是为了减轻个人理性产生的不利后果(囚徒困境、集体行为或委托——代理关系等问题就是明证),或者通过例如事先承诺(Martin 2000)和声望(Tomz 2007)等个人救济手段,或者例如军备控制和制度设计(Koremenos, Lipson, and Snidal 2001)等集体救济手段以实现更好的结果。上述解决方案是合理的,因为理性选择中的首要规范性价值在于效率,且效率这一规范性价值被认为是中性的,甚至是“科学的”。但是,对效率这一价值的重视可能会忽视其他价值,比如分配和权利等(Gruber 2000)。安德鲁·基德(本书第二十五章)的说法更加笼统,他认为理性选择以自由主义的规范性价值为前提,包括尊重个体在内,倾向于诸如自由交流和地方分权等具体的实体性成果。可以说,理性选择是一个半规范性理论,而非一个纯逻辑性理论。它是一个以规范性前提为基础的逻辑性理论,为如何进一步推进我们的规范性目标做出指引。有些学者看重规范性因素,以脱身于社会科学流派,这一趋势加剧了经验分析与规范分析的脱钩问题。对此论述最多的当属那些专注于哲学问题的学者,他们从全球范围的对外援助到人道主义干涉等一系列国际形势中判定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关于伦理推理的过程,很多情况下人们对其定义十分狭窄,认为它仅包含伦理准则的逻辑判定。但现实中,伦理推理的范畴要广泛得多,融合了经验性主张与哲学性思考的假定(Reus-Smit 2008)。然而,对伦理推理的狭义定义促使人们更加忽视经验分析及其所需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尽管程度略浅,另一种趋势也很明显。有些研究流派非常重视规范性因素,而规避那些对经验研究来说更为“科学的”方法。这一直是英国学派的一个软肋。该学派在探讨国家间社会和制度关系的本质时采用非系统性方法,这一方法限制了该学派关于秩序与正义的关系的研究(Reus-Smit 2005)。人们没有看到规范性立场与科学性立场之间合理的融合,通常都是充耳不闻,相互漠视或批评。其结果就是导致了分裂,“科学”与“规范”各占一边。
这一分裂严重损害了国际关系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一方面,“科学家”们不愿意触及伦理问题以及看似非科学性的问题,这意味着他们对于当今很多重大问题无话可谈。另一方面,当经验知识不充分时,规范性的国际关系研究无法指导具体行为。例如,面对是否干预下一个卢旺达或达尔富尔问题,我们既需要分析可能的举措(制裁有用吗?军事干涉有效吗?),又需要判断谁有权利或义务采取这样的行为。为了将国际关系理论与相关的现实问题进行重新串联,需要规范和经验两条腿并行。这是批判理论家们长期以来的论调,比如考克斯和林克莱特,对于“现实主义的”、与全球体系的经验性动态一致的国际秩序,他们追求一种规范性导向的强制转型(Cox 1986, 208; Linklater 1998)。这也是基欧汉最近提倡的主张(2001;另见Buchanan and Keohane 2004),他呼吁国际关系学者们努力提出新的国际制度和秩序,而这一尝试需要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的整合。
不过,我们的目的不仅在于鼓励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二者实现更密切的互动和整合,更是为了说明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具备经验和规范的维度。这一点十分必要,原因有二:第一个,也是人们最为熟知的原因,我们作为学者永远无法背离我们的价值观,因为它们浸润在我们所提的问题、我们试图看透的迷局、我们所做的假定以及所采纳的方法之中。不过,这里我们希望强调的还有另一个原因。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解释过的,国际关系一直以来是一种实践性话语,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如何行为”这一问题已经对该学科的学者提供了支持和启迪。现实主义学者关心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有效实现国家利益,后现代主义学者同样关心如何回应支配结构。由于实践性问题的存在对他们就是一种动力,因此不论怎么规避,他们都不得不进入经验和规范之间的模糊地带。要依据我们力图实现的价值观来回答“我们应该如何行为”这一问题,我们就需要依据我们所处行为的情境对“我们能够如何行为”有充分认识。
经验理论与规范理论之间的互动不仅体现在提出问题和理论分析这两个阶段,而且还存在于知识生产这一中间阶段。此前我们讨论过,这一阶段离不开规范性考量。但是,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因为实践性话语的存在,经验和规范更为复杂且紧密地交织。回答“我们应该如何行为”这一问题会产生经验性知识,考察的是因果关系、构成关系、话语结构以及塑造政治行为的过程。同时,这也会产生规范性知识,它考察的是作为行为主体的“我们”是谁、以何原则采取行为以及实现目标准备牺牲什么资源(比如为了拯救陌生人要失去同胞)(Reus-Smit 2008)。因此,实践性话语使得知识生产不能囿于经验理论的“科学”范畴,它需要更为广阔的范畴,包含同样重要的规范性研究。
本《手册》的一个核心目标即是突出国际关系理论中经验的和规范的维度。这一点在我们对主要实体理论的审视中已经做得非常系统。在余下篇幅中,我们将借助众作者们的洞见勾勒出这些理论的经验性和规范性层面,希望以此引领人们了解该学科的特征,并得出与众不同的认识。我们发现,以三条经验性轴线和两条规范性轴线介绍这些理论颇具启发性。当然,选择其他轴线也完全可行。
在经验——理论方面,我们着重探究它们对于能动性——结构、理念——物质性以及权力的本质这三个方面的假定。利用第一个方面的假定,我们可以区分能动性理论(强调个人选择在决定政治结果时的作用)、结构理论(强调社会结构赋予个人选择的机遇与限制)、结构化理论(强调施动者与结构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以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强调通过表意系统和意义系统建构主体性的方式)。利用第二个方面的假定,我们对观念论(将构成性权力归因于主体间的观念和意义)、理性制度主义(强调观念在协调物质或其他利益与政治结果之间关系的作用)和物质主义(强调物质因素的因果力)进行了区分。利用第三个方面的假定,我们可以区分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就“权力”给出的四种不同概念。正如迈克尔·巴奈特和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的类型学理论(2005,3,强调源流)中提到的:
强制性权力 指允许一个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拥有直接控制力的互动关系…… 制度性权力 事实上指行为体对他人实施间接控制…… 结构性权力 关注的是在彼此的直接关系中行为体的社会能力和利益的构成…… 生产性权力 关注的是意义和表意系统中扩散性社会关系对主体性的生成或改造。
至于规范——理论方面,我们着重探究两条变动轴线:价值承诺和变动导向。
 前者指理论试图实现的价值或目标(无论以公开的或隐晦的21方式)。从编者的各章节中,我们发现五种明显的价值承诺:(1)对于国家利益审慎的追求;(2)国际合作(从以主权作为基本规范构建的秩序,到通过国际治理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价值观);(3)个人自由(既包括通过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所体现的积极自由,也包括通过消除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所体现的消极自由);(4)包容性和反身性;以及(5)对他者的责任。我们的第二条轴线即变动导向,指理论家对道德和现实变化问题所持的整体倾向:(隐晦地或明示地)他们持乐观的还是怀疑的态度?国际关系理论的规范方面不仅取决于学者们所持的价值观,还在于他们对于道德可能发生变化的接受程度。我们用此作为勾画理论的一条独立轴线,因为不同理论的变动导向不仅仅源于他们对经验的理解或对实体价值的承诺。例如,现实主义者会因为自己的经验假定对道德变化持怀疑态度吗?或是由于他们是道德的悲观主义者而倾向这些假定?
前者指理论试图实现的价值或目标(无论以公开的或隐晦的21方式)。从编者的各章节中,我们发现五种明显的价值承诺:(1)对于国家利益审慎的追求;(2)国际合作(从以主权作为基本规范构建的秩序,到通过国际治理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价值观);(3)个人自由(既包括通过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所体现的积极自由,也包括通过消除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所体现的消极自由);(4)包容性和反身性;以及(5)对他者的责任。我们的第二条轴线即变动导向,指理论家对道德和现实变化问题所持的整体倾向:(隐晦地或明示地)他们持乐观的还是怀疑的态度?国际关系理论的规范方面不仅取决于学者们所持的价值观,还在于他们对于道德可能发生变化的接受程度。我们用此作为勾画理论的一条独立轴线,因为不同理论的变动导向不仅仅源于他们对经验的理解或对实体价值的承诺。例如,现实主义者会因为自己的经验假定对道德变化持怀疑态度吗?或是由于他们是道德的悲观主义者而倾向这些假定?
表1.1列出的是根据经验和规范的维度划分的国际关系的九种实体理论。在此,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这些理论具体化,使它们的复杂性简化为单一的、同质的形式。
 我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说明我们所选的用于比较的轴线是唯一贴切的、可展现相似性或差异性的维度。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说明:(1)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确实都需要经验的和规范的维度;(2)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审视理论,就会出现大量有趣的模式和重叠。这表明大量被用于划分该学科的传统方法被过于滥用。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科学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之间的截然区分,这种边界划分是因为所谓的可以将经验理论与规范影响相分离。此外,它还说明该学科从根本上被认识论的差异所割裂,具体而言,即对“什么构成真知”的认识差异。尽管这些差异显而易见,但对我们如何开展学术研究却有深刻影响,它们掩盖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之间许多重要的趋同点。
我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说明我们所选的用于比较的轴线是唯一贴切的、可展现相似性或差异性的维度。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说明:(1)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确实都需要经验的和规范的维度;(2)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审视理论,就会出现大量有趣的模式和重叠。这表明大量被用于划分该学科的传统方法被过于滥用。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科学主义者和乌托邦主义者之间的截然区分,这种边界划分是因为所谓的可以将经验理论与规范影响相分离。此外,它还说明该学科从根本上被认识论的差异所割裂,具体而言,即对“什么构成真知”的认识差异。尽管这些差异显而易见,但对我们如何开展学术研究却有深刻影响,它们掩盖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之间许多重要的趋同点。
从比较中我们发现三种值得重视的模式。第一种是看似互相对立的理论之间价值观的共鸣。这一点在批判理论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可能最为明显。正如罗宾·埃克斯利(本书第二十章)在其有关批判理论的伦理章节所阐释的,在“规范伦理”层面,“批判理论的最高伦理目标是为了通过更包容、更直接的对话来促进解放或解除对人类自主的枷锁”。人们很清楚这一规范性立场和新自由主义者赋予个人自由以优先性这二者之间具有相似性。人类个体的福祉在伦理上具有至高地位,而解开个人自由的枷锁也具有优先性。这并非模糊这些理论的伦理立场之间的重要差别,考虑到它们共同起源于启蒙运动,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并不足为奇。英国学派社会连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之间的价值共鸣同样十分明显,二者都明确专注于厘清在何种条件下主权国家能更好地做出让步以促进个人的积极自由,尤其是国际人权形式的积极自由。我们再次声明,重要差异尤其是方法论的差异以及赋予哲学探索以优先性方面的差异,这些都不应该被掩盖,但是不同理论在价值观层面的趋同实在是太明显了。
表1.1 理论的经验性和规范性

(续表)

其二,我们的比较发现,坚持强制性权力概念的理论与信奉生产性权力概念的理论,其变动具有强烈的相关性。其中最主要的例子就是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两种理论对于国际关系中道德变化的可能性都持怀疑态度。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道德政治总是逊色于权力政治;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权力的产生离不开道德话语:所有的道德赋意过程都会产生支配关系。彼得·劳勒(本书第二十二章)注意到,后现代主义者对于道德普世主义的批判并没有使他们走向现实主义者的“道德绝望”,只是使他们倾向于“对伦理方面存有争议的情形做出不全面的、或然的回应”。然而,热衷于强制性或生产性权力观念的理论均认为国际关系中权力无所不在。现实主义者以权力争斗界定政治;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示意过程都生成权力。最终,即便未致绝望,但都促成了二者的道德怀疑论的立场。第三种值得重视的模式是,结构主义理论与怀疑论之间、能动性理论或结构化理论与乐观主义之间一致的相关性。现实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英国学派多元主义者都属于结构主义者,它们或者把无政府状态,或者把资本主义视作结构,为社会行为体提供动力和强加限制。相对而言,它们忽视了行为体在社会结构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也基本否定了国际关系中道德变化的可能性,也有部分例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观点认为结构自身从长期来看是不稳定的(特施克,本书第九章)。反之,能动性理论或结构化理论,如新自由主义、英国学派中的社会连带主义或建构主义,为个人或集体能动性的创造力留下了更多空间,为有关道德和实践变化方面更为乐观的立场提供了社会理论基础。当然,能动性同样也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合作可能针对第三方,而建构主义者也意识到恶性规范可能导致无法控制的后果(Rae 2002)。最后,在结构化理论和怀疑论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属于例外,可能是因为它们对于生产性权力的重视盖过了结构化主义的影响,从而促成怀疑论而不是乐观主义。
上文的比较揭示出,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当下理论化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理论在跨越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时所采取的不同方式。那么,这种多样性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吗?谈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有些老套,但进展的观念对于所有的学术研究确实有所启发。如果我们不认为这一工作对人们理解世界政治做出了贡献、为国关学术共同体创造并收获了知识,那么我们的研究师出何名呢?为此,我们认为国际关系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评估。一方面,是否拓展了人们对于主题的理解(从广义上来讲,包括解释性的、阐释性的、规范性的以及其他理解方法);另一方面,是否提高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简单地说,我们目前在这两个有关方面是否比以前做得更好?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分,即该学科整体的进展与国际关系各分支内部的进展,学科内各分支由实体话题、方法论或理论流派所界定。我们认为,该学科整体上貌似缺乏进展,这与其各分支内部进展的性质紧密相关。
出于各种原因,对进展的评估并不容易。我们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用于衡量我们的所知或其在现实行为中的应用情况(或可以如何应用)。国际关系的动态特征使它成为一个移动标靶,既可以是研究对象,又可以是一个研究领域。虽然某些问题持续存在,但其他问题正随着国际大事和学术潮流的变化而变化。最重要的是,该学科与生俱来就充满了政治性和争议性,因此任何对进展的衡量从来都带有价值取向,而且严重依赖于人们对可能性的认知以及对理想性的信念。
然而,作者们在本书中的论述显然记录了很多理论取得进展的方式。从概念上来说,该学科更具活力;即便在那些缺乏共识的方面,人们对于其差异也有更加清晰的了解。像权力这样的基本概念从根本上来说仍然“充满争议”,但在权力类型的分野(Barnett and Duvall 2005)问题上,我们对其不同方面的理解已经取得重大的进步。同样地,整合了跨国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的相关分析对国家中心主义的假设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莫拉维斯克,本书第十三章),同时,国家中心主义流派及其反对者提出的理论也更加复杂了。沃尔福斯(本书第七章)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之路以及与之同步的争论,比如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之间的论争;伊恩·赫德(本书第十七章)和弗里德里希·克拉托奇维尔(本书第二十六章)指出,建构主义整合了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发展一种新的观念论,做出基于规范的解释。它成为单纯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固执地坚持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的对照。尽管对进展持有怀疑立场,后现代主义同样也发展了更为复杂的解构、话语分析和谱系研究法,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话语建构带来了重要见解(伯克,本书第二十一章)。本学科进展的其他重要方面体现在:新方法与老问题的整合、新研究领域的开放、新问题或再次关注曾经被忽略的问题。上述转变有些萌生于现实中新问题的滋生,有些萌生于不同理论方法的内在逻辑,有些萌生于学术场域的变化,而通常这些转变是以上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冷战后和“9·11”后的安全研究已经转而探讨有关民族冲突和恐怖主义问题,这些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安全保障和威慑的逻辑也相应发生调整。人们对于安全的概念和边界(Buzan, Wæver, and de Wilde1998)一直存有争议,认为它们关涉到个人安全的更深层因素,而不仅仅与军事或国家利益有关。尽管贸易和金钱仍是十分重要的议题,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点已经超越了这些传统问题,扩展到设定标准、跨国经营监管和洗钱等新问题(Abbott and Snidal 2001; Mattli and Büthe 2003; Drezner 2007)。人们对很多制度的概念进行了重组,人们更加重视制度的不同形式和特定属性(Koremenos, Lipson, and Snidal 2001)。同样,全球变暖问题以及全球范围对人权问题的重新关注冲击了许多传统理论,而且激发了人们对新理论更浓厚的兴趣。
该学科,或者说至少该学科的某些部分,面对人们提出的问题时已经不那么自满了。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提出从来不是中性的,其背后总是隐藏着价值和权力的关系。这一现象促使问题和学派的剧增。批判学派和女性主义已经对“主流”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由来已久的偏见发起了挑战,而阐释性研究和更多历史导向型的研究也对实证主义更为普世性的野心提出了挑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实主义因其假定国际政治的本质不变而被批评缺乏进取心;自由主义者注意到有待加以说明的系统内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更为极端的学派对现存国际体系提出质疑以提升对大规模系统变化进行阐释的必要性。
如今,北半球国家和西方国家仍主导着国关学界。一直以来,第三世界受到一定程度的忽视,这说明我们学界的偏见仍在影响国际关系学科,至少在某些领域束缚了该学科的发展。菲利普·达比(本书第五章)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批评,安东尼·伯克(本书第二十一章)对后现代主义的论述以及戴维·布莱尼和纳伊姆·伊纳亚图拉对“自下观点”(view from below)的探讨(本书第三十八章)都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把针对第三世界最相关问题的探讨和分析排除在外,而且仍在以西方话语来定义发展。目前学界普遍关注的是国家、主权,对非西方文化和诸如全球不平等这种问题视而不见,而北半球国家对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而已。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则对上述现象都发起了挑战。布莱尼和伊纳亚图拉(本书第三十八章,另见Gilroy 2006)建议这些学派研究时要“超脱于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bove)以揭示其隐藏的假定和政治目的。
衡量日益复杂化的研究方法是否取得进步,并不困难。研究国际关系实体问题的统计学和形式化的数学方法使用更为广泛,而且设计更为精巧(曼斯菲尔德和佩弗豪斯,本书第二十八章)。针对包括人权(Hathaway 2002; Hafner-Burton 2005)、环境(Sprinz 2004)、国内制度(Howell and Pevehouse 2007; Mansfield, Milner, and Rosendorff 2002)以及民主(Russet and Oneal 2001; Pevehouse and Russett 2006)等越来越多的问题进行的数据采集工作日益完善。形式化模型(Snidal 2004)更为常见,也更加复杂,诸如对抗和合作等领域推动了理论发展。人们更加注意定量研究中的变量选择和变量确定问题(Drezner 2003; Vreeland 2003;von Stein 2005),或者更加重视使用代理模型来解决闭式数理分析所无法处理的问题(Cederman 2003),这反映出这些学派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且应对更为自如。
重要的是,方法论方面的进展并不限于对这些技术性更强的方法的使用。案例研究方法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人们不仅采用历史的和阐释的方法,而且还使用诸如过程追踪这样的技巧,将严谨的因果分析与对底层机制的密切关注相结合(贝内特和埃尔曼,本书第二十九章)。后现代主义在论证方面也得到了发展,这体现在该学派对安全话语和实践的谱系分析(Hansen 2006),以及其更为笼统但更具争议的对历史事件和同时期政策的密切关注(伯克,本书第二十一章)。不同方法的互动让彼此获益。关于变量选择问题的统计学分析使人们特别重视定性研究中的变量选择问题,因而人们对超越单纯的统计学模型的变量选择问题和研究设计的理解更加全面(Signorino 2002)。案例研究与大样本分析相结合得以广泛运用,在某些领域几乎已经成为公式化的套路,这也显示出不同方法之间的互补性。按照这种思路,早期的建构主义研究被实证主义者斥为不可验证,而建构主义者不仅证明自己能够采用更严谨的研究方法开展经验研究(新近案例见Acharya and Johnston 2007),而且实证主义者也能将建构主义者提出的某些因素纳入自己的研究中(Tierney and Weaver 2007)。
不过,因研究方法的进步而取得进展具有较大局限性。对方法的明智使用提升了对国际关系问题的经验和理论分析,但方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对方法论标准的过度重视可能会阻碍特定领域的研究,因为有些研究并不适用技术性较强的研究方法。在人们开发大数据并将其用于定量分析之前,对战争的研究同样很难有价值。即便我们无法对规范性行为进行形式化建模或我们的统计数据有限,我们研究人权这类问题也很有意义。对重大研究课题的研究不能总是等到方法具备时才开始。
如果一项研究要符合经验分析和理论分析的多重标准,那相关问题就产生了。研究工作不必面面俱到也能达到顶级水平。例如,归纳研究能够增进我们对世界形势以及我们关切的重要关系的理解,即使这些关系的理论化程度还不高,归纳研究也是非常有用的。诚然,理论方面的进展必然需要经验事实的支撑,即便这些事实尚未被高度理论化,情况仍然如此。反之,即便该领域的某些假定未经验证,或在某些情况下无法被验证,理论分析也能提高假定的质量:好的理论常常能够引领我们超越当下的经验知识。简而言之,有所侧重也有助益,并非所有的文章都要面面俱到,有些文章应该重理论而轻经验,其他文章应该重归纳而轻理论,还有一些应该重规范甚至重方法论。这一明确分工导致一个必然结果,即没什么研究是完整无缺而且自给自足的。单个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有赖于它们与整体的国关研究的互动联系。
那么,发展又是从何而来呢?将单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与该学科整体的发展进行区别十分有益。尽管《手册》的作者们有时对自己所探讨领域的发展进度或方向有所不满,但是他们在对特定的学派或问题的探讨中都提到各自领域的发展和进步。
 看起来,如果国际关系学科所有领域都取得了发展,我们似乎就可以推断该学科也取得了发展。不过,就该学科是否推进人们对国际政治达成共识的问题,各方看法不一。如今国际关系学科仍然门派分立、争论纷纷,人们认为其不同领域之间往往互不兼容,有时情况可能的确如此。为了协调各领域内部的发展与该学科整体上看似发展不前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对各领域内部发展和跨领域间发展的不同方式进行考察。
看起来,如果国际关系学科所有领域都取得了发展,我们似乎就可以推断该学科也取得了发展。不过,就该学科是否推进人们对国际政治达成共识的问题,各方看法不一。如今国际关系学科仍然门派分立、争论纷纷,人们认为其不同领域之间往往互不兼容,有时情况可能的确如此。为了协调各领域内部的发展与该学科整体上看似发展不前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对各领域内部发展和跨领域间发展的不同方式进行考察。
各领域内部的发展往往源于对某理论假定的内部逻辑的思考,或对该假定指向的经验领域的探索。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关键的理论难题(例如,合作从何而来?)或经验事实(例如,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就会促使人们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重大进展。无名氏定理关于无政府状态下合作可能性的相关论断发展成围绕合作而展开的丰富论述;有关民主和战争关系的一些经验事实(Doyle 1986)引发了多达千篇文章对国内机制与国际格局关系的论述(相关讨论见曼斯菲尔德和佩弗豪斯,本书第二十八章);这些更为内向性的研究逻辑也许能够带来大量研究成果,但单独来看也造成了各领域内部的相对窄化,有时会导致各领域内部的碎片化。典型的例子可见沃尔福斯(本书第七章)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论述,他详细阐述了现实主义理论的演进如何丰富了现实主义学者阵营的多样化。
如果发展以吸纳外部思想为基础,就出现极端反例。国际关系是一个跨学科性极强的领域,该学科发展最为重要的源泉之一就在于借助他山之石。本《手册》的许多章节都记载了从其他学科兼收并蓄的情况:社会学(赫德,本书第十七章;克拉托奇维尔,本书第二十六章)、历史学(夸克,本书第三十章;贝内特和埃尔曼,本书第二十九章;布莱尼和伊纳亚图拉,本书第三十八章)、经济学(基德,本书第二十五章;斯坦,本书第十一章)、哲学(伯克,本书第二十一章)、心理学(戈尔德吉尔和泰特洛克,本书第二十七章)以及政治学(唐纳利,本书第八章;莫拉维斯克,本书第十三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理论吸收了跨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理论范式的思想,如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将国际关系对政治理论的借用重新发扬光大。这一现象其实并不新鲜,正如唐纳利所指出的,很多国关学界的“鼻祖”,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雨果·格劳秀斯(HugoGrotius)和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绝不仅是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家。近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科开始倚重大批更具时代特征的政治理论家,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
向外部借鉴是促进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式,但也带来了自身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必要情况下人们会对国际关系问题进行调整以迎合该理论,而不是相反。在其他背景下所发展的理论可能无法很好地与国际关系问题匹配: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国家交往的方式与个人交往的方式相同,或者理性的国际行为体跟市场竞争中的消费者相似,又或者以个人心理行为模拟领导人和官僚机构面临国际危机时的行为方式。那么,向外部借鉴必须针对国际关系情境进行精心设计才有价值。虽然这种借鉴难以衡量好坏,针对特定情境所做的设计或许也有“削履”之嫌,但从事实上看,通过借鉴外部进行研究已取得较大成效。原因可能是国际关系学者对于自己所借鉴的特定学术领域驾轻就熟。然而,这导致了第二个问题,这种借鉴将导致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的碎片化,因为借鉴学科外的思想,使得国际关系学科各分支与其相对应的外部学术领域密切关联,导致本学科内各分支相对疏离。即使我们不在意国际关系能否黏合成为一个“学科”,但我们所研究问题的共性要求不同学派之间开展富有成效的交流。幸运的是,国际关系内不同的学术共同体之间一直存在广泛的互动。其中一些通过借鉴其他分支学派的思想,让自身学派得以更好地发展,进而形成对其他学派更深刻的理解。在其他情况下,借鉴实质上已经充满竞争和争论。自由制度主义利用了现实主义的前提,提出有关合作的非理想主义论述,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导致两个领域在有关诸如相对收益或制度的重要性等议题上产生竞争乃至冲突,因为它们对“相同”现象做出了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阐释。
论争可能既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在哪些问题重要以及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方面,论争最富有创造性。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能够揭示不足,挑战假设,强化论点,并提出新的问题。理论间的相互论辩还能激发它们的活力,并就研究范式内“自鸣得意”之处提出挑战和质疑。如果论争成为一种自辨性的讨论,妨碍不同理论之间的沟通,论争则无创造性。有关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争论有时确实十分重要,但它们通常落入上述情形。如果人们认为证明理论比理解世界更为重要,论争也会变得具有破坏性。正如在范式竞争中,不同的国际关系研究传统在学术争鸣中更关注自身视角的“脱颖而出”,而不是对世界事务的解释。
 论争是否具有创造性取决于学界如何共同引导学者们的努力。学派分支之间相互批评和借鉴必然给各自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和暂时的停滞,但目的还是为了推动发展而不是阻止发展。针对“权力”相关概念的争论如何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彼埃里·马特恩(本书第四十章)对此进行了有趣的评估。
论争是否具有创造性取决于学界如何共同引导学者们的努力。学派分支之间相互批评和借鉴必然给各自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和暂时的停滞,但目的还是为了推动发展而不是阻止发展。针对“权力”相关概念的争论如何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彼埃里·马特恩(本书第四十章)对此进行了有趣的评估。
一方面,概念的争论使该学科的外延得以拓展;另一方面,争论对各分支学派划分界限,各归各位。正如她指出的,只有争论建立在广泛的、共同的基础之上,(非)/本学科的各种要素相互挑战,争论才会有创造性。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不同的国际关系学派(或哪些学派)之间能否相容以至于它们之间的争鸣能够产生创造性?就相对收益问题,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互动说明,即便两个研究传统均以理性主义为基础,二者的相互兼容性也有限。出人意料的是,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互动情况更加乐观。它们之间的争辩有时聚集在这两个学派(它们自身内部十分多样化)在认识论或本体论方面能否相互兼容以支持两者间的积极正向的沟通。近来的研究显示二者之间有大量的共同基础,包括双方都成功地吸纳了对方的关键理念。前文的表1.1显示出,在非常广义的层面上看似各自独立的理论传统之间具有很多交叉点。从当前研究的具体细节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交叉。建构主义者已经将集体行动和委托——代理关系整合在理论分析中(Keck and Sikkink 1998; Nielson, Tierney, and Weaver 2006);理性主义者更加注意使用规范来深化其对制度的分析。也许某种程度上受早期批评的影响,第二代女性主义学派的成果具有更强的经验导向性,而且与国际政治的其他影响元素更密切关联。这种现象在桑德拉·惠特沃思(本书第二十三章)的著述中充分被体现,该章通过考察从世界银行到军事应用等进而探究各种国际制度的生成方式;雅基·特鲁(本书第二十四章)则探究了女性主义理论与其他国关理论的相互兼容性。当然,更为激进的后现代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们认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明就里”而且也不可能弄明白。然而,即便如此,此类批评仍然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些隐藏的假定和假设,并可能促使它们在其他研究中发生转变。当然,这样的转变可能也不会让批评者满意,这些批评者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满意。琳娜·汉森(Lene Hansen)(2006)呼吁“后结构主义应该从理性主义中找回其方法论”,伯克(本书第二十一章)对此表示赞同,这显然是一个要求在认识论层面实现更多整合的挑战。
国际关系理论就此产生一个悖论:单个领域的进步不会拓展整个学科的发展,至少在针对主题达成统一的、全面的认识方面是如此(Kitcher 1981)。各理论分支间的争论采用了多重逻辑,而不是基于单个研究逻辑的大综合。尽管人们把理论分支间广泛存在的争论视作国际关系领域的败笔,但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成功的一个动因。争论为国际关系学科注入了活力,使其对不断变化的问题保持开放,并为新理念进入该学科提供了入口。本《手册》的宗旨在于以建设性的方式聚合这些不同的争论点,从而使该学科得以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通过强调所有国际关系理论以规范性论据为基础,我们在看似不同的学派之中找到了共同点,并对这些造成我们之间差异的、更为根本性的原因进行阐述。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核心主张是,行为体通过建构极端的他者进而建构自我身份,即通过界定另外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他者来界定我们是谁。可悲的是,在国际关系学术界,身份政治一直是一个过于明显的特征。我们的理论已经成为我们的社会身份,在建构这些理论身份的过程中,为了突出差异、抑制趋同,我们将其他理论立场具体化。我们设计编写这本《手册》的目的,就是为了突破身份政治的藩篱。我们并未忽视真正的差异点,事实上我们使先前未被人们充分承认的差异得到了人们的关注,而且我们也从未淡化这些差异的重要性。我们确实认为差异可能很有创造性。不过,我们强调所有理论之间有两大共同点:各派理论共有的开放形式,它整合了问题、假定和逻辑论证;所有理论都具有经验性和规范性。虽然这些共同点跨越了现有理论之间的差异,它们并未使国际关系理论同质化。相反,它们使之前被掩盖的差异和趋同之处更为凸显。
所有国际关系理论都有经验性和规范性的两面,这一点对于理论作为实践性话语的本质来说是根本,与我们应该如何行为这一问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只有凭借实践性话语,国际关系学者们才能应对当代全球体系中复杂的政治行为问题。而且,如果我们以此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目标,我们就必须认可我们需要穿越经验和规范二者之间的交叉地带,而且要系统地展开这一工作。正是经验与规范二者之间的互动给国际关系带来了活力。这是国际关系学科所研究问题的源头,而且也是该学科对问题的答案从未满意的原因所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发生的变化既源于国际问题的变化,又源于人们关注点的变化。学界对规范问题的屏蔽从根本上来说是有误导性的,而规范性理论化对经验研究的弃置同样如此。这并不意味着,相对于被有关认识论的论争充斥其中,国际关系学科必须专注于有关规范性的论争。这也不意味着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要(都能)不断地对所有的经验性和规范性问题进行研究。国际关系已经得到充分发展并成为一个专业领域,不是每一位学者都要面面俱到,也不是每一项研究都必须将重要考量“囊括”,这并不是说可以忽略它们,或对它们浑然不知。经验导向型的学术研究可能会确定其研究问题和有关行为体的假定,并且对问题结果的评估要相对完整、准确,其研究焦点则会落在对互动的进展进行阐释。反之,规范导向型的研究则可能会确定有关世界运行规则的特定“事实”以及可能的情况,以此作为对实际情况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行为”进行评估的前提。学者重视自己观点的内部逻辑,参与学界争论为自身观点辩护,这种基础研究是促进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国际关系学科极其复杂而且变动不居的问题来说,这种劳动分工既不可避免又极具创造性。
不过,重要的是,个人意识到其研究在本质上是片面的,承认他们的理论化融入了经验性和规范性两种因素,并承认理论的各个部分必须进行互动和沟通,这种劳动分工才不会碎片化而成为单独的生产线。即便单个理论研究者无法始终专注于这种相互关联,后面一项任务也可经作为共同体的国际关系学科加以实施。当然,单个研究者时不时关注理论间互动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正是一个多元的、互动的国际关系共同体能够做到的,也是这本《手册》要强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