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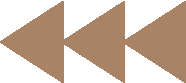
杰克·唐纳利
本章和第七章都将政治现实主义
 界定为一个围绕以下四个议题的松散而明确的国际理论传统。
界定为一个围绕以下四个议题的松散而明确的国际理论传统。
1.无政府状态政府的缺失使国际关系成为定性独特的政治行为领域。
2.自利主义个体和群体趋向于谋求狭义上的自我利益。
3.群体主义政治发生于群体内及群体间。
4.权力政治自利主义群体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互动导致强权与安全政治。“国际政治从来都是权力政治”(Carr 1946, 145)。
对权力追求的优先性使所有其他目标被边缘化。本章着重讨论现实主义的典型观点,即国际政治“是实践行为而非道德行为”(Kennan 1954, 48),“伦理标准不适用于国家间关系”(Carr 1946, 153)。“普遍的道德规范不适用于国家行为”(Morgenthau 1954, 9)。国际政治的“现实”“使政治政策具备了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使纯粹的个人伦理始终倍感尴尬”(Niebuhr 1932, xi)。笔者认为,虽然根源于某些重要的深刻认识,这种对于国际关系领域的道德维度类属的否定描述不够准确而且也不合乎规范。然而,老练的现实主义者都承认权力政治的“现实”只不过是完备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实践的一个方面。最初情况正好相反,绝大多数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者都认为伦理在国际关系中虽然处于从属地位但该地位不可或缺,不过整体来说,他们都无法克服这一说法与他们更为人们所熟知的、与道德无涉的对外政策诉求之间的矛盾。
现实主义与这本《手册》这部分的结构非常吻合。通常来说,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将该理论视为既是一种对实然世界的解释(前一章节的主题),又是一系列基于对政治“现实”这一解读而开出的用于指导各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应当如何开展国际关系实践(本章的主题)的“处方”。不过,由于实质焦点的不同,本章将探讨的相关现实主义文献与前章非常不同。前一章节重点关注社会科学家(主要是美国的)近期的研究成果,而本章基本上关注更早期的研究成果;部分原因在于,现在的社会科学家较其前辈,在其专业研究中对道德问题关注度大为下降。尽管如此,这些现实主义学者的“经典”论述,其无与伦比的说服力与活力毫不逊色。
有现实主义者称,道德与特定共同体有关,而并非各国、各社会或文化所共有之物。例如,爱德华·哈勒特·卡尔(1946,2,8)称“道德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普遍的”。“所谓的绝对普适的原则根本称不上原则,而是对基于特定时期特定国家利益阐释的国家政策的一种无意识反应。”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1954, 103, 47, 36)也认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是我们能够确实知道、理解的所有东西”,反对“我们的道德价值……必然对所有人都有效力”的说法。凯南甚至称“与个人关系中的对错问题相比,大部分国际事务中的对与错于局外人而言难以分辨,当然国际关系是否有对错之分仍不得而知”。
实际上,我们能够而且确实可以了解他人的价值观和利益。许多国际问题的确涉及是非对错。例如,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已经达成的共识有:禁止发动侵略战争;种族灭绝引发合理的国际关切与行动。
此类共同价值观的广度、深度以及政策影响必然会引发激烈的争论。然而,政治价值观仅具有国家性这一说法是虚假的。人们已普遍接受,个人价值观具有普遍性这一观念是错误的。然而,这一错误观念被过度简化,因而产生另一种错误理念,即“不具有普适的共同价值观”。
凯南(1985—1986,206)称国家利益属于“无法绕开的必要问题”,因此“无所谓‘好’与‘坏’之分”;这一说法明显是错误的。任何“必要性”都不是自然而然或无法避免的。除非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否则没有明显的理由一定要遵循。
大部分现实主义者反对道德相对主义尤其是较为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这并不足为奇。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如1932;1941;1953)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如1960;1953)是现实主义者中最为知名的两位基督徒。在无宗教信仰的现实主义者中,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 1979,10)提出“存在客观的且有待发现的道德准则”(参看Morgenthau 1946, 178—180, 195—196; 1962b, 43,237)。就连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970; 1985)这样的激进派也持类似观点。
马基雅维利的“合理作恶”论断认为,“被认为是‘合理’的恶(如果可以这样形容邪恶的话),可以当即实施。‘合理作恶’的目的是多样的,出于自身保护之目的是必要的,为了保存臣民也可以将‘恶’物尽其用”(《君主论》第8章第4段;参看第17章第1段)。尽管道德准则无法直接适用于政治,马基雅维利仍然强调“只要有可能,就不应将善抛于脑后,但在不得已时,也应该知晓如何作恶”(《君主论》第18章第5段)。我们应该注意到马基雅维利对于善与恶的理解非常传统。不道德的方式本质上是坏的,因此应该控制在最低限度——即便是在“保护臣民”、为了广泛的公众利益的不得已之时。
大部分现实主义者不是否认道德与公正的传统属性,而是坚持认为此类标准或是不适用于(国际)政治,或是让步于其他原则或考虑。现实主义者以人性、国际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和领导人的特性为主要依据,主张其他“更加悲观、限制性更强、更实用的标准必须胜出”(Kennan 1954, 49)。
早在修昔底德的《米洛斯对话》(1982,第五册,第85—111章)中,雅典使节就已表明了对国际事务中伦理问题的否定态度。这可谓是现实主义派对国际事务中道德规范最熟知、最彻底的否定。“世界的正义仅存在于力量相当的各方之间。强者依其权力为所欲为,弱者忍气吞声。”(第五册,第89章)“神明在上,治人者在前,统治者遵循其本性施治。”(第五册,第105章)正如一些佚名的雅典人在战争爆发之际宣称,他们建立和保护自己的王国,并应对“三大压力:恐惧、辉煌与利益。这并非我们首开先河,自古以来就是弱者臣服于强者”(第一册,第76章;参看第一册,第72章)。
且将建立“事实”与“法则”的桎梏以及将“是这样”变为“应这样”的种种阻碍置于一旁,此类论述仍存严重错误。如果征服的冲动的确是无法抗拒的本性,那么按照“理应即能够”的道德通则,征服者和暴君则可能会凌驾于公正之上。然而,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人并非因无法抗拒的本性而冲动行事。在强者统治的法则之下,雅典人声称他们已经善待盟友,且程度高于雅典人须恪守的标准(第一册,第76章)。在米洛斯时,雅典人很可能思考过正义的做法。然而,他们选择了不正义的做法,并非被迫为之——由于米洛斯人拒绝投降,雅典人最终屠杀了所有的(米洛斯)男人,将妇孺贬为奴隶。
即便“所有人都渴求权力”(Morgenthau 1962a, 42),大部分现实主义者还是认为,这种内在冲动并非无法抗拒。例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986)在《利维坦》第13章中强调:暴力冲突的根源在于竞争欲、胆怯和荣誉,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利益、安全和名望的追求。然而,霍布斯在该章结尾指出:人类本性也热切渴望和平与理性,因此,人类可以寻求战争以外的其他方式。虽然尼布尔强调“出于利己的堕落具有普遍性”(1953,13),但他同样坚持,我们处于且将一直处于一种道德责任,即与自身堕落的本性抗争。“基督教的原罪教义看似矛盾,一方面认为原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另一方面认为每个人都须为自身的原罪负责。其实,这是真理的辩证性质,也恰恰反映了人类同时具有自爱和自我中心的两面性,但天性使然并不具备辩证的两分法”(1941,263)。人们在“人性为单一性还是两面性”这两种观点间莫衷一是,这种情况反映出现实主义观点中一直存在的争论。一部分现实主义者过度强调关于“制约政治道德的‘事实’”的本质与重要性,这种过度解读有时不免尺水丈波。然而,另一部分现实主义者——通常为更具反思精神的学者——认为此类“事实”至少无法证明权力政治是“无关道德的”,这些“事实”更称不上会对权利政治的道德产生影响。
国际无政府状态是指没有凌驾于国家单元之上的中央政府存在。现实主义者通常认为“个人道德准则与国际社会道德规范间的差别就像社群中与无政府状态下社会关系间的不同”(Schwarzenberger 1951, 231)。然而,国际关系并非都奉行“丛林法则”(Schuman 1941, 9)。一些说法是错误的,比如,“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无法追求道德。道德行为完全依靠有实力阻止并惩戒非法行为的政府”(Art and Waltz 1971, 6)。正如在政府没有强制执行道德准则时,个人可以遵照道德行事,同理,国际关系中也可以存在道德行为。
现实主义者再次别出心裁,提出了该理论学派的典型观点:缺乏规范和协定的中央执行机构将增加不道德或违法行为的发生概率。但一切国家利益和目标都产生在无政府状态下。不会有人建议国家应该放弃经济利益或承诺与敌国永不宣战,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若想实现这些目标,只怕会更加举步维艰。同样,无政府状态并未要求各国政府放弃对外政策的伦理目标。虽然在无政府状态下追求特定的伦理、经济、军事或政治目标不易实现,但这不是政府不作为的理由。
也许,最有力的现实主义论述才会关注国家和治国方略的本质。国家理性学说的学者们认为“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高于其他一切利益与价值观”(Haslam 2002, 12)。国际关系中某一政治群体的自身利益总是高于其他群体的利益,亦优先于其他规范准则。因为任何政府“对其代表国的国内社会利益都负有根本责任”,“相应的道德理念对其不再适用”(Kennan 1985—1986, 206; 1954, 48)。
然而,上述观点涉及伦理性层面。人们关注国际关系中什么是合理的价值观,而非对外政策是否合理地服从于规范性评估。“权力政治是一个由各群体构成的国际关系体系,各群体均将自身定为该群体的最终目标”(Schwarzenberger 1951, 13)。因此,摩根索(1951,33)谈到了“国家154利益的道德价值”,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1916, 54)认为国家“自身是集各种道德规范的整体”。
遗憾的是,现实主义者鲜会为上述价值观辩护,当它们与其他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国家理性学派通常仅关注国家及其他政治群体的道德行为。其他理性行为及规范标准往往被置于一旁。追求国家利益过程中受到的其他价值观的影响及制约往往被忽略。
此外,还有另一种更强有力但更具局限性的现实主义观点:先发制人的价值观,即(国家)生存论。例如,亨利·基辛格(1977,46)认为“政治家操控现实;生存是其首要目标”。罗伯特·塔克尔(Robert Tucker)同样称“政治家的最高道德是保护其所治之国”(Osgood and Tucker 1967, 304 n.71)。一旦生存受到威胁,其他一切均要退居其后;就像国内法律及大部分道德理论都允许公民个体使用致命武力进行自卫。
然而,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形鲜有发生。故“权力争夺完全等同于生存斗争”(Spykman 1942, 18)这种说法有误。“国家只能被动地遵循现实主义的命令行事,否则就会冒被摧毁的风险”(Mearsheimer 1995, 91),这种情形亦较少出现。
而其他的国家利益,无论多么“重要”,都无法与自身的生存相提并论,而必须与政治、法律、道德及其他迫切事项相平衡。利益间的相互平衡产生诸多的现实困境。但现实主义者通常忽略此类问题。而且最糟糕的是,他们还不断推崇极端错误的观念,即国家利益在政治家决策时应当且一直优先于其他一切考量。
从国家再到国家领导人,现实主义者通常认为对国家领导人的公众行为和公民的个体行为应施以不同标准(比如Carr 1946, 151; Kennan 1954, 48; Thompson 1985, 8)。和其他专业人员一样,政治家需优先考虑“客户”的利益。正如辩护律师在道德上需要(在一定限度内)为有罪的客户积极辩护,医生(在一定限度内)应做出对治疗病人最有利的方案而不是考虑整体的社会,因此政治家就其职业性质来说,应对其国家和国家利益做出最有利的决策。“个体以普遍性道德准则评判政治行为,而政治家总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其决策的基础。”(Russell 1990, 51)
这就会导致所做出的决策难以公平对待本国与他国国民的生命与利益。1994年4月,卢旺达发生种族屠杀,西方国家使馆仅组织本国国民撤离。虽然这样的行为有一定的道德争议,但大多数人不仅会欣然接受,通常还会要求(政府做出)此类行为。国家领导人是承担特殊道德责任的代理人,应保护作为被代理人的本国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这样的对外政策可能“与道德无涉”,它既不受普通道德原则的影响,也不以这些原则对其评判。不过,这样的政策既非“价值中立”,亦没有超越伦理或其他规范性界限。就像代理律师不得泄露客户的犯罪计划或是医生不得为病人购买器官,政治家在为公民合理追求利益时也有一定限度。
某些界限源自国际法以及各国社会
 的伦理(及其他)规范。今天,各国仅在出于自卫目的且战争法及人道法允许的范围内,方可正当使用武力。
的伦理(及其他)规范。今天,各国仅在出于自卫目的且战争法及人道法允许的范围内,方可正当使用武力。
然而, 国家 利益与价值观可能会限制一国的对外政策。比如,国家在饥荒灾害救济、民主推进、发展援助或保障人权等问题上做出的承诺。“以本国为整体的利益”才是“国家利益”这一术语指涉的意义,即民族国家所涉及的利益及所持有的价值观。某些现实主义者[如摩根索(Morgenthau 1954, 5, 10)]坚持认为,国家以权势界定利益,这样的观点体现了一种极具争议的、含义不明确的关于对外政策的规范性理论。并无有力的理论依据规定,国家在抵制共产主义、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或消除全球贫困时不能有其价值观。国家理性学说和关于政治家的论述都无法界定该国具有或应该具有何种利益。此类的价值观问题已超出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范围。
“与道德无涉的”对外政策牵涉到一个更具伦理性的争议——“审慎”。马基雅维利将“审慎”定义为“分辨好与次的特性,并将不太次的特性作为好的部分”(《君主论》第21章,第6段)。因为“人们发现善与恶难分开”,马基雅维利建议效仿罗马人,“总是将不太坏的情形作为更好的选择”(《论李维》第三册第37章,第1段;第一册第38章,第2段)。
摩根索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审慎——衡量不同政治行为的后果——[是]政治的最高美德。抽象意义上的伦理评判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法则;政治伦理评判行为的政治后果。”(1954,9)“政治伦理确实是关于各种‘恶行’的伦理……鉴于政治之恶无法避免,就只能从众多‘恶行’中择其善者。”(1946,202;参看Thompson 1985, 13)这是马克斯·韦伯著名的终极目标伦理与责任伦理两分的变体。

然而,一国的公众利益并不是评判政治家行为的唯一合理标准。审慎经常与道德、宗教和其他价值观发生冲突。没有强有力的理由让人相信,审慎总是优先于其他一切价值观和考量。关于如何平衡出现的竞争性规范、需求和价值观,大部分现实主义论述都明显缺乏这方面的讨论。
值得怀疑的是,大部分现实主义著述存在夸张之嫌,因为这些学者尚未理解权力、道德与治国方略之间复杂却又不可避免的互动关系。现实主义者执着于讨论追求道德、法律和人道主义目标过程中(重要性无可否认的)的限度,通常无法对权力政治的限度予以系统性反思。如何平衡现实中各种竞争性的价值观是治国方略的关键性问题。现实主义理论强调负责任的治国方略。然而,该派学者不仅没有解决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他们过度或夸张的陈述反而忽略了对此问题的探讨。这对于现实主义传统而言是莫大的悲哀。
最合理的现实主义伦理观或许是警惕“国际政治行为中道德准则的不当运用”。“现实主义反对的不是道德,而是道德主义,它是对道德的157扭曲。”(Acheson 1958;参看Thompson 1985, 5;Lefever 1998,第9章;Coady 2005, 123)因此,卡尔、尼布尔和凯南等主要学者称自己的研究是在批判“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可理解为理性主义、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的融合。
同样,某种重要的、谨慎的观点在此处被不合理地夸大。比如,卡尔(Carr 1946, 153)称:“关于国际社会中道德适用的思想分为两大类。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间关系仅受制于权力,道德不起任何作用。与此对立的观点认为,同一道德标准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大部分乌托邦主义的学者支持后一种观点。”而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还存在多种其他立场,而且鲜有人真正持上述任一种观点。无论普通民众还是专业人士,人们都清楚,政治家不得不同时兼顾多种价值观。仔细观察后我们发现,大部分重要的现实主义者承认道德伦理,如肯尼思·汤普森(1985,22)所说,“发挥作用但不处于主导性地位”。
卡尔(1946,235)曾以很克制的方式谈道:“虚谈高论的现实主义才会忽略国际秩序中的道德元素。”摩根索谈到了“道德与政治的辩证对立,政治无法逃脱道德评判与规范性指导”(1946,177),并且承认“国家意识到一种道德义务,避免其在特定条件下遭受死亡与痛苦,即便从国家利益考量,(死亡与痛苦)的这些行为可能具有一定正当性”(1948,177)。尼布尔(1932,233,xxiv)不仅坚称“合理的政治道德必须合乎道德主义者与政治现实主义者双方的观点”,并且强调现实主义分析中的“终极目标”“是寻找最有可能达成社会伦理目标的政治途径”。现实主义者恰恰提醒人们不可忽视群体主义与自利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塑造的各种“现实”。争论一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时,“以权力界定国家利益”(Morgenthau 1954, 5, 10)的这一狭小视野当然也有其一席之地。但是,诸如“伦理标准不适用于国家间关系”(Carr 1946, 153)以及“普遍的道德标准不适用于国家行为”(Morgenthau 1954, 9)等观点不仅经不住审视和批判,甚至无法反映出大部分自认的现实主义者的深思熟虑——即便他们倾向于重复和强调站不住脚的、言过其实的论断。
 正如158约翰·赫茨(John Herz 1976, 11)提到的那样,“权力政治中,权力的削弱、施加、平衡和掌控等情形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不可避免”。
正如158约翰·赫茨(John Herz 1976, 11)提到的那样,“权力政治中,权力的削弱、施加、平衡和掌控等情形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不可避免”。
上述评价的意义在于,可将现实主义看成是以政治审慎为中心的小心翼翼伦理观,政治审慎是在对国际政治狭义且深刻的理解中形成的。
 然而,只有认真对待卡尔提出的(Carr 1946, 89)“我们在纯粹的现实主义中终究无法获得安宁”这一观点,我们才能够避免严重扭曲的对外政策的出台。“只有在(现实与乌托邦、权力与道德)两者各安其位时,才能看到明智的政治思想与健康的政治生活。”(Carr 1946, 97;参看Schwarzenberger 1951, xv)
然而,只有认真对待卡尔提出的(Carr 1946, 89)“我们在纯粹的现实主义中终究无法获得安宁”这一观点,我们才能够避免严重扭曲的对外政策的出台。“只有在(现实与乌托邦、权力与道德)两者各安其位时,才能看到明智的政治思想与健康的政治生活。”(Carr 1946, 97;参看Schwarzenberger 1951, xv)

我们也必须警惕另一种夸大。无论是启发性的想法还是实践性的适用,并非所有涉及无政府状态、自利主义或群体主义的观点都属于现实主义学派。实际上,所有研究传统与理论流派的学者们都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只有激进的世界主义者、自由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挑战群体主义假定。大部分伦理传统和道德理论将与自利主义的抗争视为道德行为问题的核心。这类解释性变量不属于现实主义学派特有的,更何况冲突问题。然而,自利主义、群体主义与无政府状态共同作用塑造了引发冲突的权力政治,这种演变的确使得现实主义学派的分析具有辨识性的风格与特征——以及价值观。现实主义理论在学科中理应占据中心位置,只要该派学者不过度强调其贡献。但是,无法像该派的某些支持者所坚持的那样,现实主义不是,亦不可能是国际政治或国际伦理的普适理论。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在前一章末强调了现实主义者保持谦逊姿态的重要性。虽然笔者对此认同,但对其所说的整体性改变却没有那么乐观。例如,在我看来,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理论主张或论断很难称得上是谦逊之辞;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观点(2002;1997)——“现实主义传统具有持续性的重要意义”以及“现实主义具有进步性的力量”——也不比其老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论调谦逊多少。相反,近期的现实主义者,诸如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或是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等人,虽然一贯比较谦逊,但也不比尼布尔、赫茨、塔克尔或是格伦·斯奈德等人更谦逊。我看到的更多是延续和重复,而非改变,尤其是谦逊与夸大的奇特混合,以及一种众目具瞻之势——忘记或隐瞒自己“知道”的可适用的限度——这在未来数年内仍将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