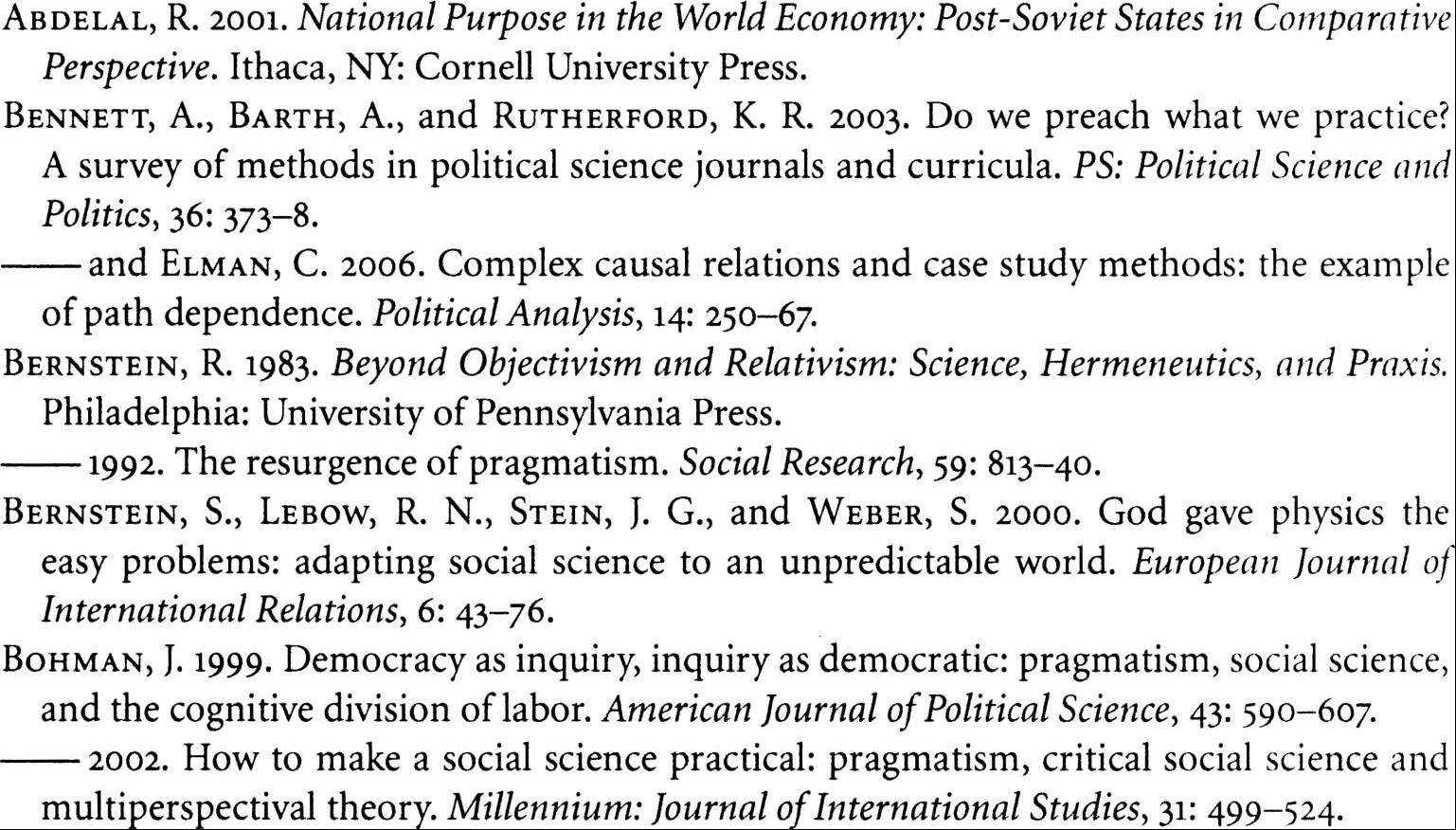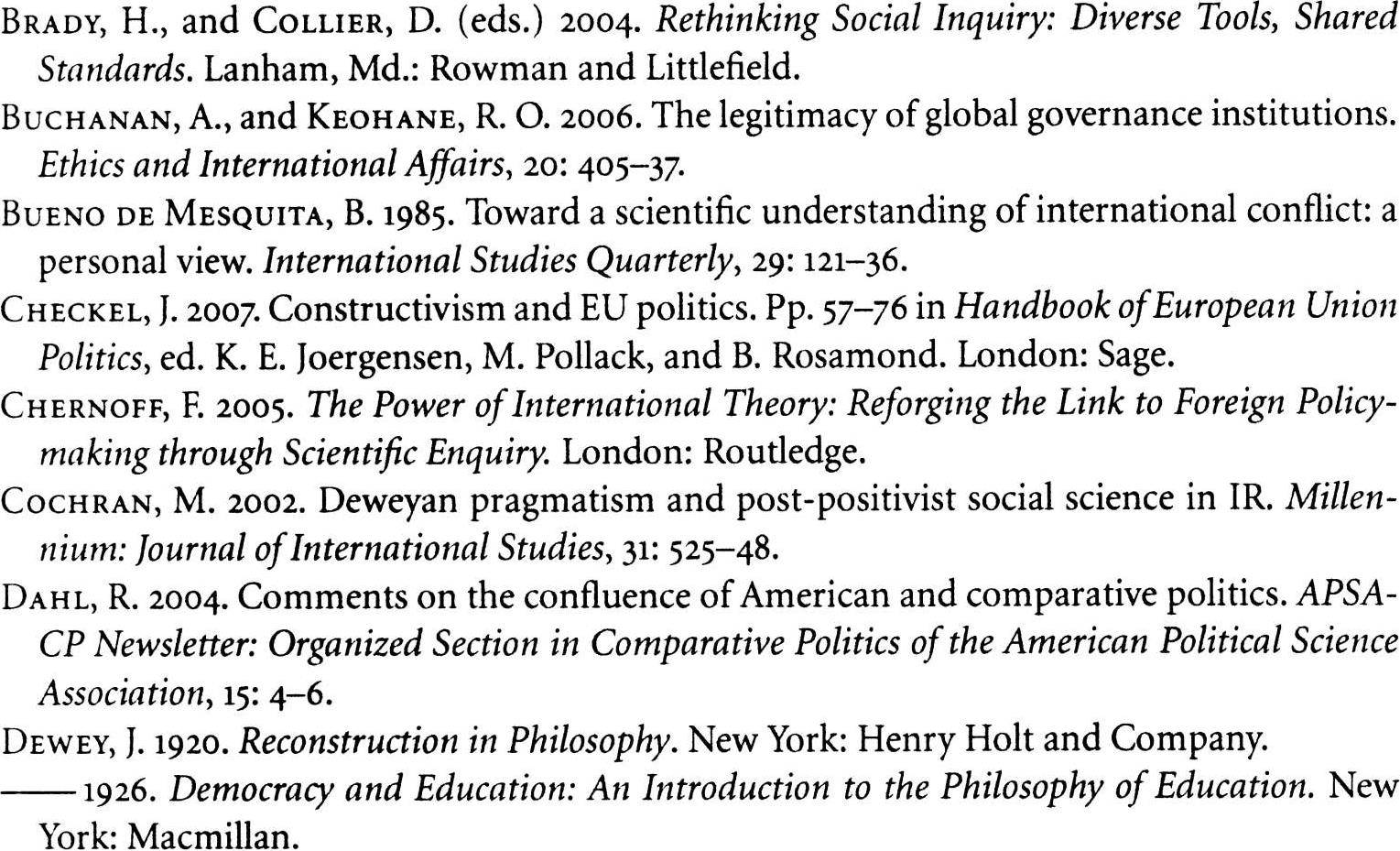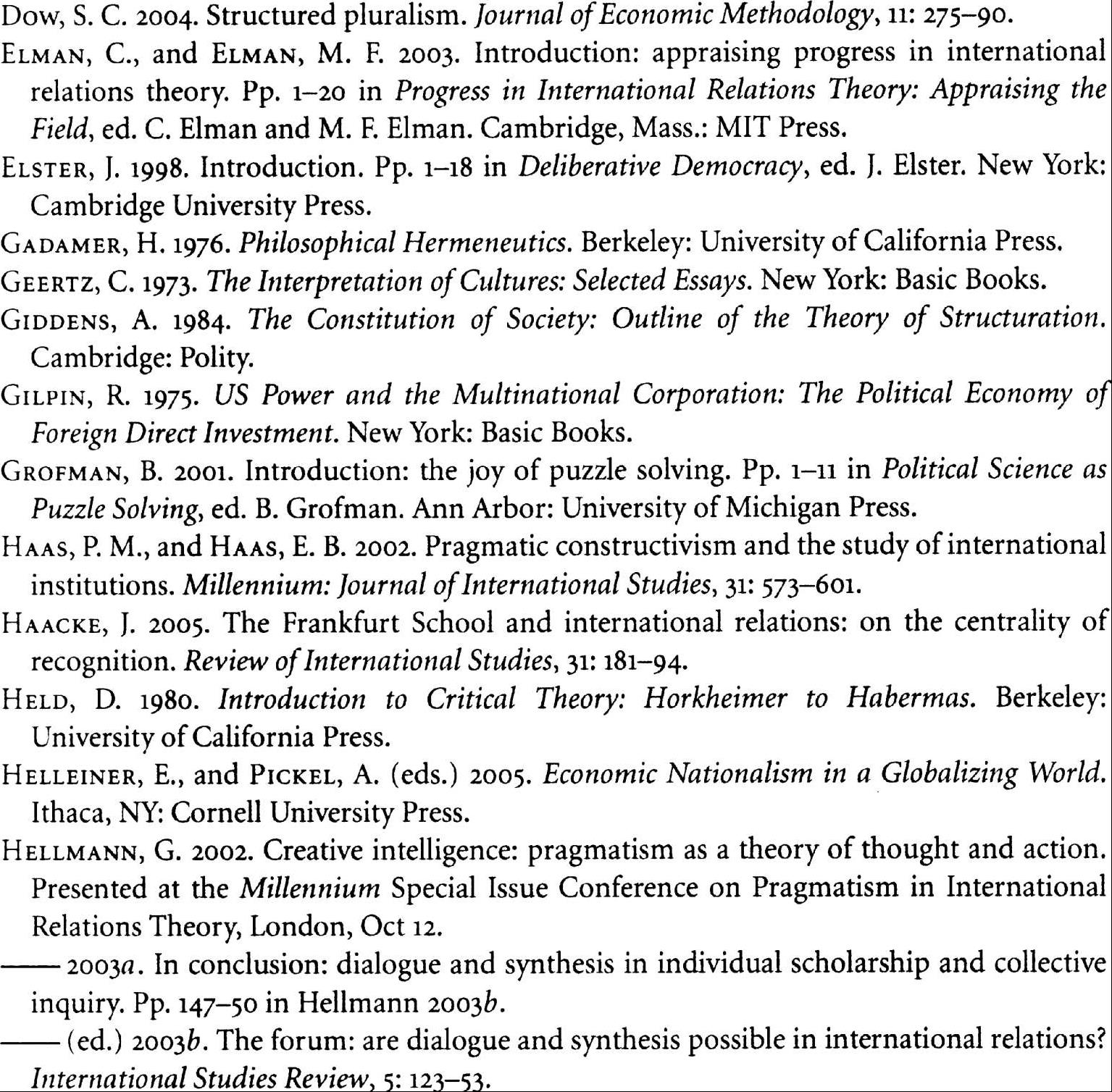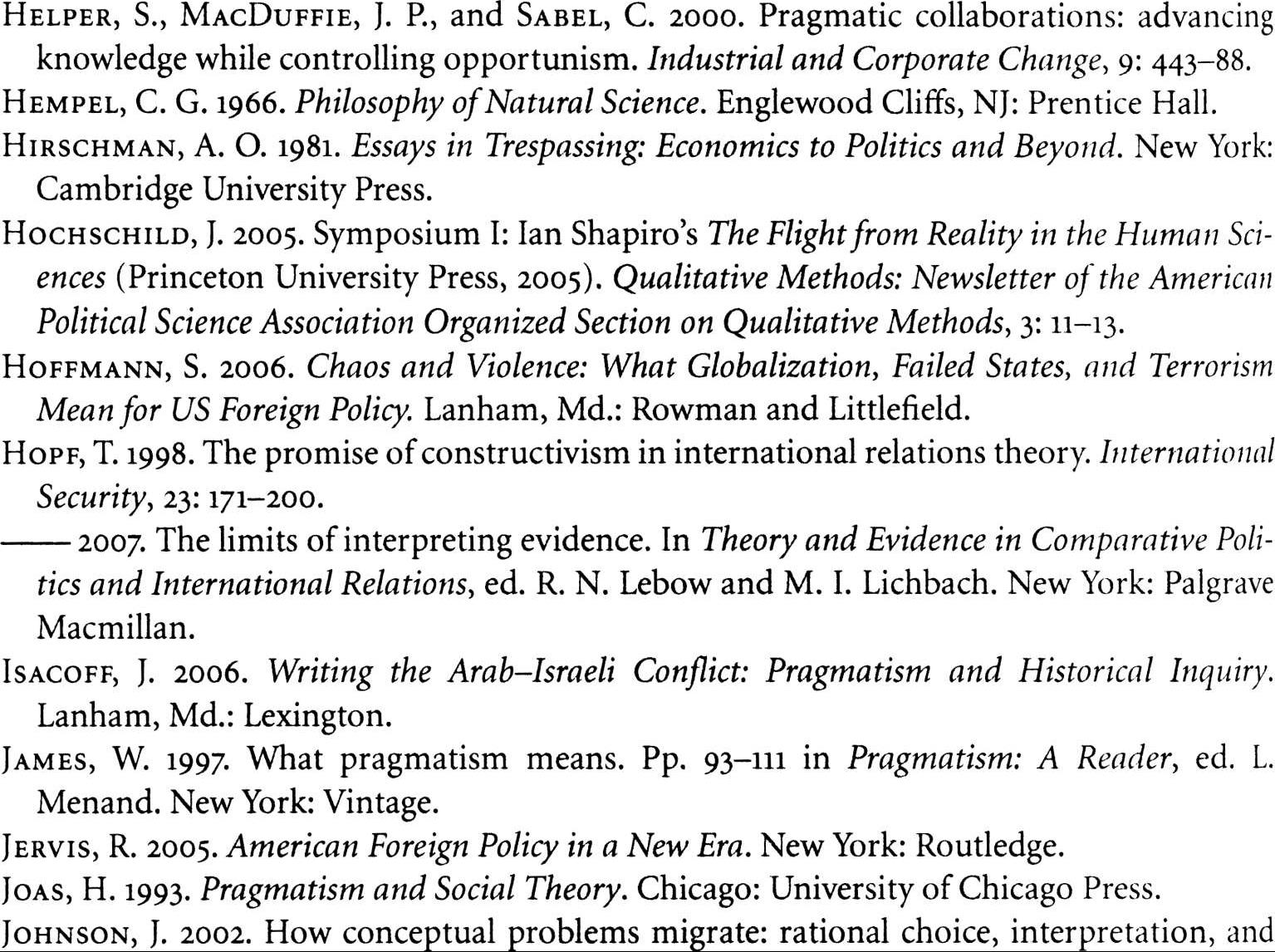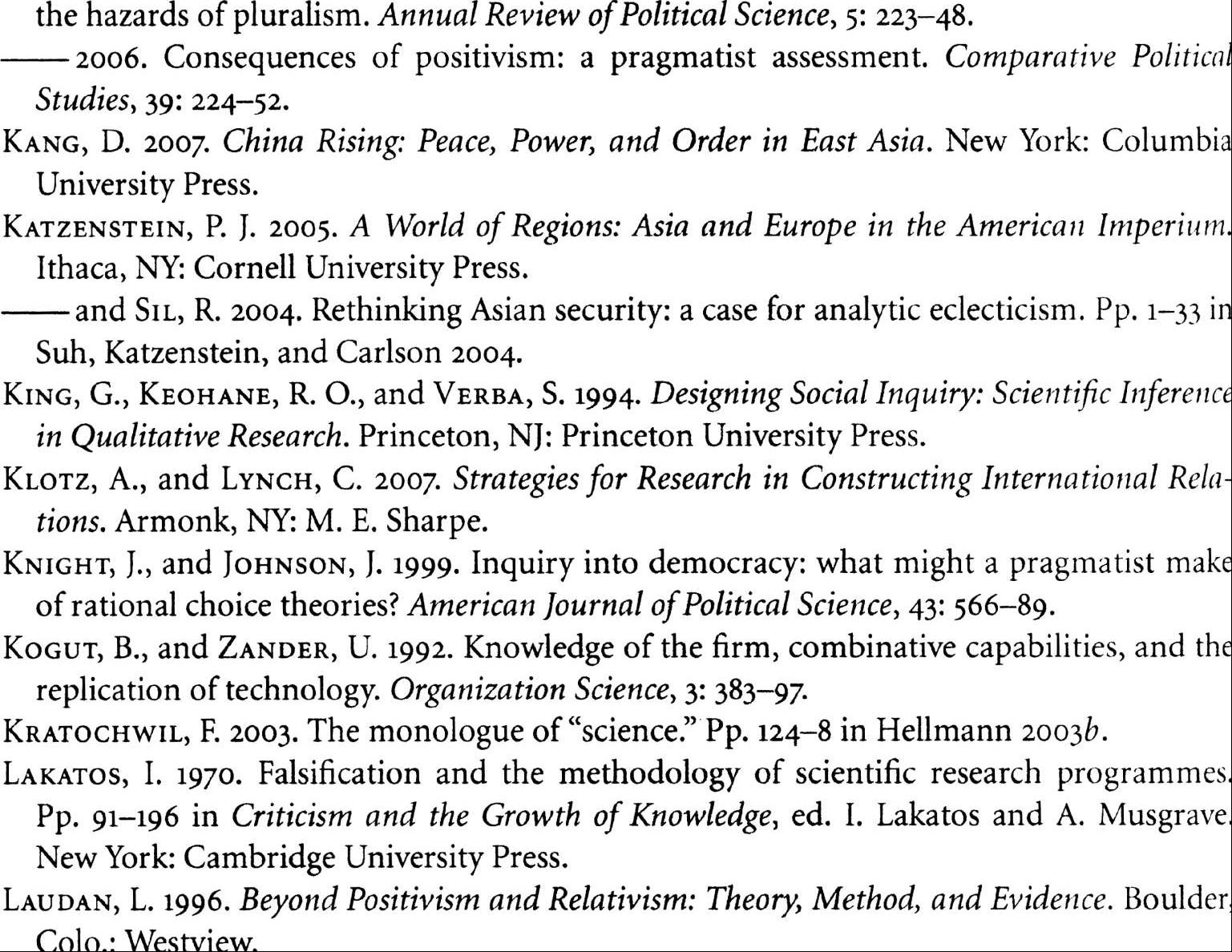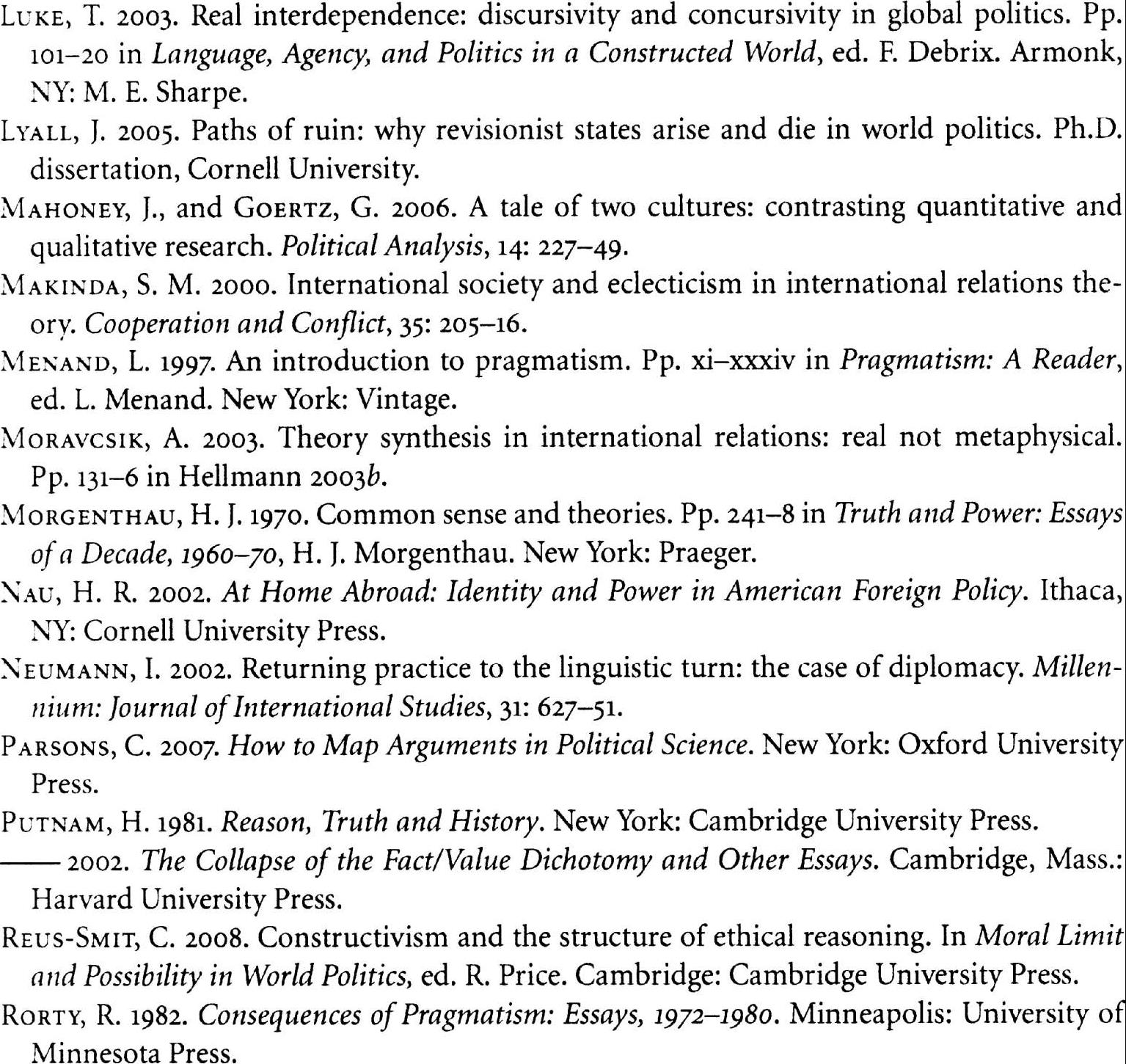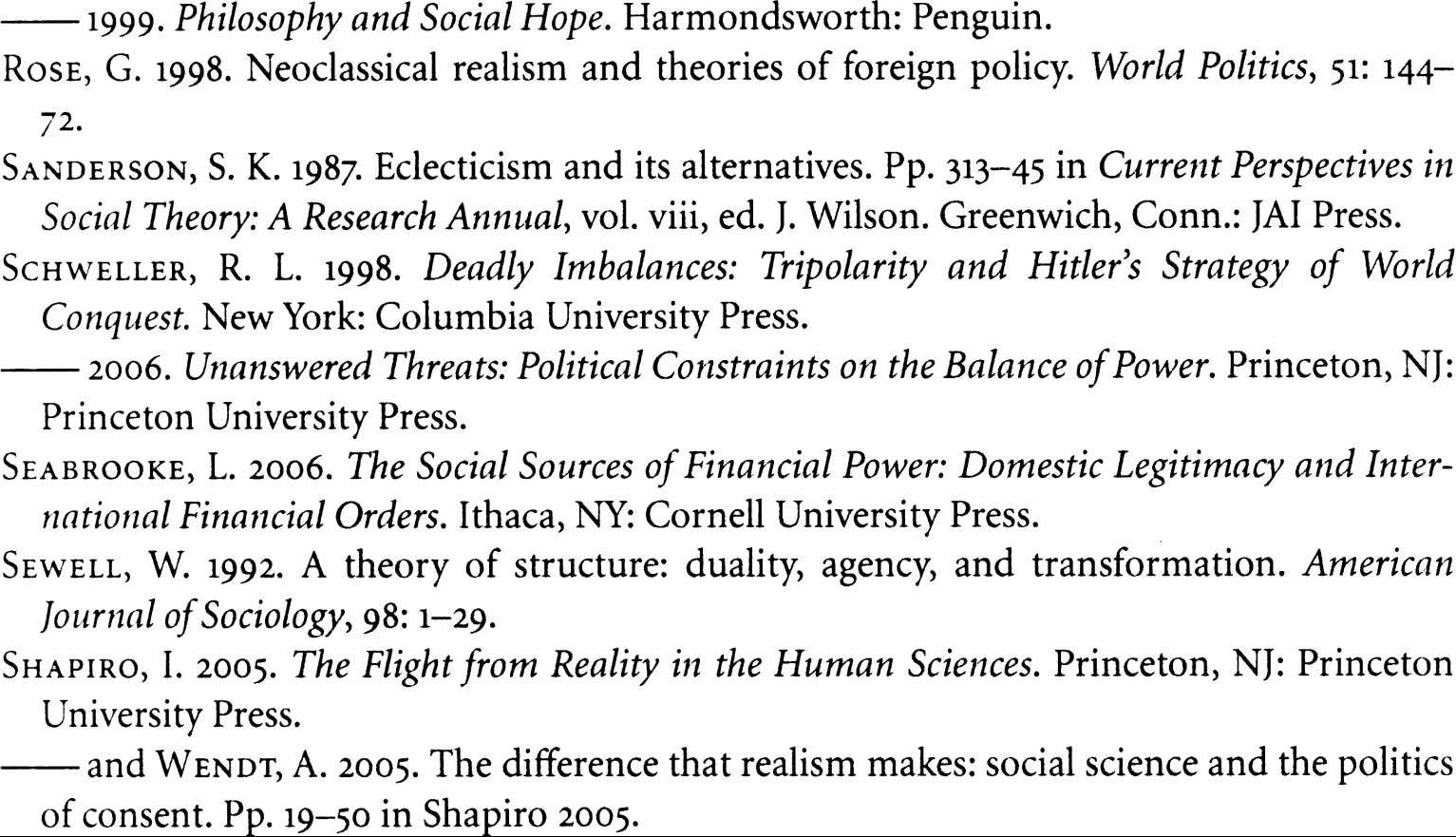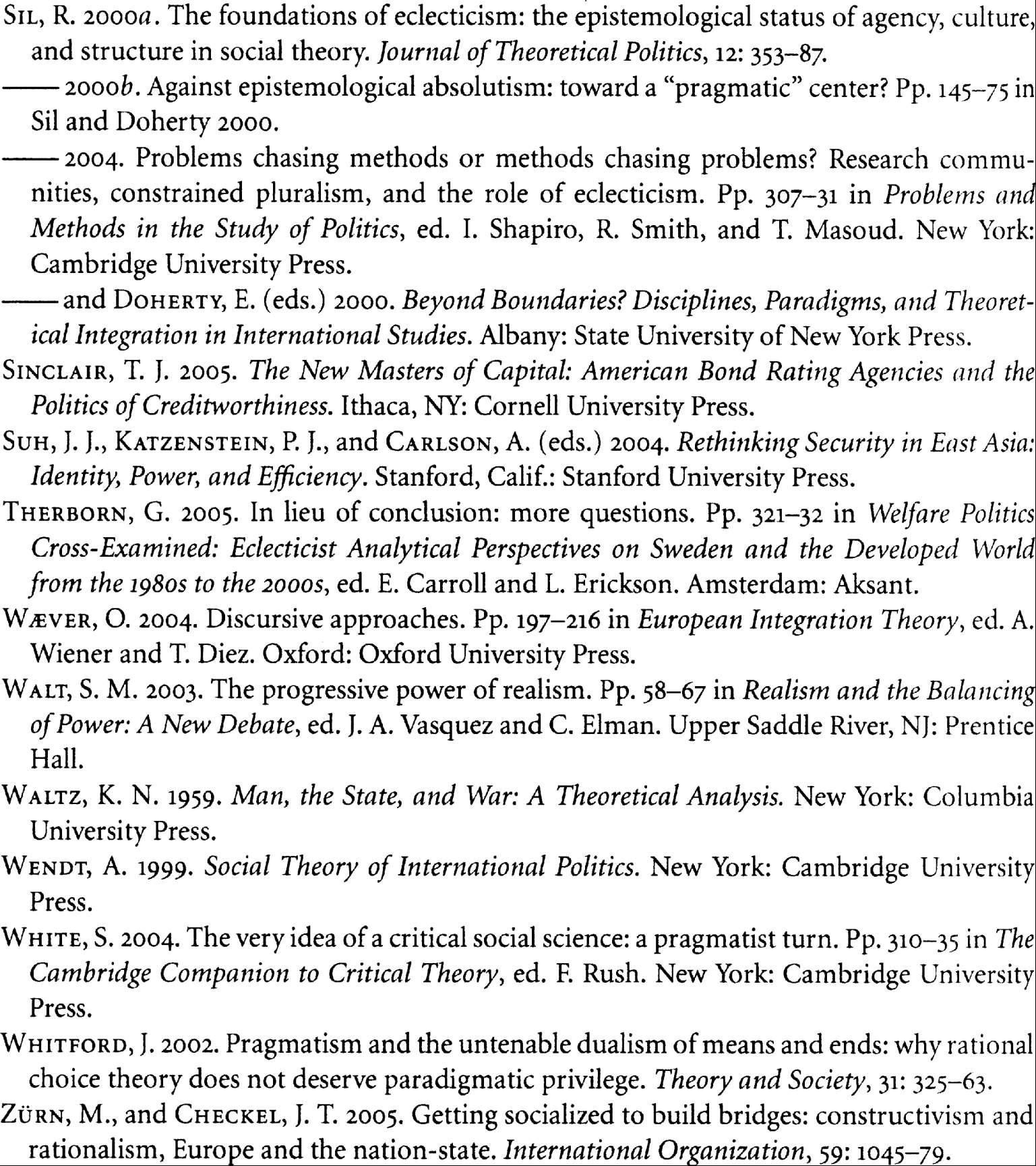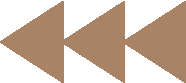
彼得·卡赞斯坦/鲁德拉·希尔
直接源于(国际关系的)单个意象的政策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们都是基于局部的分析。每个意象所具有的局部性制造了一种张力,驱使一种意象包容其他意象。……人们被引导着去寻找包容多种意象的原因汇合点。
(沃尔兹1959,229—230)
在过去30年的绝大多数时间内,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根据相互独立的研究传统展开的。每一传统的追随者都声称自己的传统具有根本的优越性,或者足以灵活到容纳其他传统。当然,不同研究传统之间的竞争是这些传统保持学术活力的动力之一。但是,某些传统的活力未必能为整个国际关系领域的进步奠定基础(Elman and Elman 2003)。正如冈瑟·赫尔曼(Gunther Hellmann 2002,3)所指出的,“沃尔兹派‘现实主义者’和温特派‘建构主义者’给国际关系带来的某种专业化受到了广泛认可,广为传颂,这当然没有错,但是不能将其误认为学术进步”。
美国政治学会主办的两大期刊之一《政治学视角》的编辑论及国际关系学科时的视角极有见地:
写一篇标准的国际关系学论文,就是先将一块理论的巨石推上陡峭的险峰,再将其滚下砸碎山脚下几块事实的鹅卵石。具体来说,一篇这样的文章模版首先要介绍一下三大标准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有时候还细分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随后,不同的文章可能略有差别:有些文章试图证明这些看似不同的理论实际上整合起来可以解释某个问题;另一些文章试图通过解释某一问题证实某个理论,而推翻其他两个理论;少数文章声称这三大理论都不足以解释这一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更多的时候是某一旧理论的改头换面)。
(霍奇柴尔德2015,11)
以往,一位好编辑会建议作者抛弃范式,聚焦一个核心问题,就该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也就是说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而不是范式导向的研究。实际上,虽然仍属于少数,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有意识地超越元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争论,他们尝试探索在看似不可通约的研究传统所涵盖的不同现实问题和理论分析之间的关联性(Bernstein et al. 2000; Makinda 2000; Sil and Doherty 2000; Dow 2004; Suh, Katzenstein, and Carlson 2004; Zürn and Checkel 2005)。
一般而言,研究传统根植于相互竞争性的元理论原则。每种研究传统本质上有一套独特的基本原则,包括研究问题的选择和界定,在这种范式框架内所表现的经验观察和因果逻辑。由于不同范式衍生的核心观点都有其自身的道理,本章提出一种比较折中的分析方式,有意识地、自由地跨越不同范式,目的是通过创造性的方式界定和探索实质性问题。跨越竞争性范式的折中主义有选择地借鉴现有和新兴的范式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关键问题的理解,从而推动整个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进展。我们所说的分析折中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以下事实:人们能够将最初深植于独立研究传统的理论分析的特征与人们刻意解释成的它们的各自基础相分隔,并重新融合为一系列原创的概念、方法、分析和经验研究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分析折中主义以务实为基础,避免元理论上的争论,鼓励学术实践培养创新形式的知识,使得坚持某种范式的学者能够就国际社会中的实质性问题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分析折中主义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激发产生超越学术意义的新理论视角,影响涉及国际关系各行为体的行为规范和政策辩论。这并不意味着摒弃或无视以范式为导向的研究成果。相反,在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之后,我们注意到有意识地“超越”不同的研究传统,可以更好地理解在各个特定的研究传统内关注重要的研究问题,提出的相关假定和阐释,并基于此做出的创新性和创造性的分析。运用比较折中的研究方式的著述在分析上是连贯的,学识上值得关注,也回应了围绕解决实际问题的规范性行为和政策辩论。
接下来,我们将首先介绍社会知识的实用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学术进步就是尽可能地扩大对话并拓展创新实验。在下文中,我们将详细讨论分析折中主义的定义,确立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以及与现有的研究传统相比的优点。然后,我们将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小样本为例,参考国际安全领域和全球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具体问题,证明分析折中主义的意义和价值。最后,我们将得出结论:通过与特定研究传统中发展的学术研究共存和对话,分析折中主义所具备的必要性及价值,能够推动国际关系学科超越不断重复的元理论辩论,并发挥学术意义和实际意义。
实证主义社会知识概念是许多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实证主义者普遍赞同一种社会研究观:假定人类行为模式反映了某些客观原则、原理或规则,后者超越了各行为体和学者的主观取向,并可在一定范围内的案例中,通过严格运用可复制的方法和逻辑加以演绎、推断或证伪。一般来说,科学进步的实证主义意象会体现出某种有关客观现实的共同概念,通过运用日益先进的研究技术以及对现实更具阐释力的理论,人们可以形成对这些规律和规则更为精确的认知(Laudan 1996, 21)。故人们认为知识积累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实证主义学派有很多不同变体,它们的差异非常大,已经无法在学术进步的指标上达成共识。例如经验主义者偏重于观察和衡量之后做出推理,期望通过对可重复方法标准化的运用逐渐为具体现象做出更好、更详尽的描述和解释。虽然定性和定量学者通常会形成具有独特实践的独立共同体(Mahoney and Goertz 2006),但是这两个阵营的经验主义者都鼓励使用标准化的研究技巧,通过重复运用这些技巧后的经验观察和经验发现(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 Brady and Collier 2004; Bennett and Elman 2006; Klotz and Lynch 2007)的一致性来衡量所取得的进展。相反,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所说的“逻辑主义”(2005,24—28)来源于卡尔·亨佩尔(Carl Hempel)构建的演绎——自然法则模型(1966),强调从公理化的规律推理出可检验的因果命题。从社会科学的逻辑主义观点来看,经验世界构建概念和提出假定,形成具有一致性的公理,由此在逻辑上得出(Bueno de Mesquita 1985)可预测的和具有解释力的主张。因此,即使是实证主义者也无法在特定研究领域就衡量学术进步最根本的问题达成共识。
与实证主义的各个研究传统不同,从各行为体赖以理解其体验和社会关系的特定视角来看,其他传统的主观主义社会现实概念是不固定的。这种立场将一般的解释理论一概排除在外。相反,他们更青睐那些受情景约束的阐释方法,专注于各行为体赋予其当时社会环境中的普通做法的意义,这一点在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深度描写”(1973)概念以及汉斯·伽达默尔(Hans Gadamer)所阐述的解释学(1976)中非常明显。即使有“理论”,通常也是批判理论,与寻求解释相比,它将批判和实践置于优先的位置,法兰克福学派的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著作(参见Held 1980)就是例证。在国际关系领域,在试图将实证研究与规范性的反思重新联系起来(Reus-Smit 2008; 另见Luke 2003; Haacke 2005)的批评视角以及强调话语分析的各建构主义流派(Hopf 1998; Neumann 2002; Wæver 2004; 另见Checkel 2007)之中明显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主观主义。在此,对我们的观点来说,重要的不是非实证主义立场之间的差异,而是事先对解读和解释(Shapiro 2005, 2)区别的明确否认,以及对社会科学分析是否可以累积进步的深刻怀疑。
在实证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各个流派中,实用主义可以视为一个理想型中心(Sil 2000b; 另见Hellmann 2002)。实用主义绝不是某个流派的残留物,其基础是何种知识值得探索,以何种方式、带着何种目的进行探索的、自洽的哲学原则。实用主义可追溯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ierce)、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等学者的著述以及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社会行为符号互动观点。实用主义在行为革命和对宏大理论的追求的冲击下,曾经一度被边缘化。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82; 1999)和其他同时代的哲学家将实用主义发扬光大,他们对实证主义进行细致批判的同时,也没有沦为相对主义者或主观主义者(例如Bernstein 1983; 1992; Putnam 1981; 2002)。虽然实用主义从不同学术背景和哲学角度(Joas 1993)产生了不同流派,但是它们对社会研究的性质、局限和运用具备一些共识。这些见解体现了一种与实证主义研究传统所假定的进步不同的进步概念,它强调社会科学家之间对话的质量和范围以及这一对话贴近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规范行为和政策问题。
这一对话中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反对过于抽象或刻板的基础性理论原则,提倡能用于处理具体问题的有益阐释。在詹姆斯(James 1997, 94)之后,实用主义者试图避开“可能无休止的形而上争论”,而在实际情况下“通过追踪各个观点在具体情境中的意义来对其进行诠释”。鉴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社会环境的多样性,对于杜威这样的实用主义者来说,包罗万象的原理或一般性理论只不过是为了将“控制”实施于现实世界的短暂努力(Cochran 2002, 527)。与此同时,与主观主义者不同,实用主义者关心的是解决社会问题(Bohman 2002)的各种真理主张的后果。形成合乎实践的知识不能等到人们就什么是“最终”真理达成确定共识之后再进行研究。正如赫尔曼(Hellmann 2002, 8)所说:“出于当下行动的必要性,我们不能等到‘获知’真理之后。”因此,人们需要在依据知识探讨113非连续情景中的具体实证和认知问题的直接实际后果时的固定时间框架内对知识加以规划和评估(Johnson 2006, 227)。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个主题,其中知识生产被视为一个通过创造性的实验,整合不同方面的“知”与“行”的过程。对杜威(Dewey 1920, 121)而言,实验科学“意味着某种智慧的做事方式,它不再是冥想,而是真正的实用”。实用主义者鼓励的实验并非科学家用来证实或证伪因果关系的控制实验,而是通过以往知识逐步适应并整合不同形式的新知识以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探索。“我们将所需知识中的一项运用到具体情境中,于是我们便会孕育出一样全新的知识,我们又将这个新知识带入我们所遇到的下一个场景。”(Dewey 1926; 参见Menand 1997, xxiii)赫尔曼认为(2003b, 149),其目的就是采用“整体性”的手段,“通过创造性地结合经验和智力,找到解决面前难题的办法”。这里并没有排除理论知识,而是要求理论知识与现实世界行为体的经历保持足够的密切联系。现实世界行为体则努力使其语汇及解读可以匹配它们的规范性承诺及不断遭遇的现实问题。
第三个主题是关于对话在日益包容和结构日益民主化的学术共同体中的核心地位。实用主义者将知识生产视为社会活动,强调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的人士都能参与流变、开放的讨论(Joas 1993; Menand 1997)。罗蒂(Rorty 1982, 165)就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在日常沟通范畴之外,对问题探索没有限制。也就是说,没有源于事物、头脑或语言本质的整体限制,而只有探究者的评论所带来的具体限制”。
实用主义者认识到知识主张是在学术共同体中提出和探索的,但是他们强调更加公平、包容、平等的共同体,促进就具体问题达成共识,并使其合法化。此外,公平、包容的思考方式不仅仅是在程序上保证决策者获得高质量的知识;其意图是减少道德上的分歧,促进共识规范出现,以支持规范人类行为的制度的合法化(Buchanan and Keohane 2006)。第四个人们达成共识的主题是个人与其所处的不同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认为,在与环境中的他者不断的对话中,“自我”得到建构和重构,这为辩证地理解行为者与结构、个人与结构化社会关系之间的多重关系奠定了基础。因为这个特征,当代学术研究一直援引实用主义,特别是米德的著述,为完全不同的学术视角提供支持。对一些人来说,在自我与社会进行的辩证交流中,理性和明智的行为者所处的角色不仅使得理性选择理论与实用主义研究之间保持一致,并且弥补了侧重根据制度本身进行分析的弱点(Knight and Johnson 1999)。乔希·惠特福德(Josh Whitford 2002)否认实用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存在联系,认为理性选择理论中手段和目的二元对立,与实用主义强调思想和行动以及知识和经验的结合是不相符的。在彼得·哈斯(Peter M. Haas)和厄恩斯特·哈斯(Ernst B. Haas)看来(2002, 586),实用主义的重大意义恰恰在于,它强调制度在促成集体学习甚至是新的共识话语产生中发挥作用。温特(Wendt 1999)认为,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关注到了与行为者身份、行动和社会环境相关的集体身份形成过程。对我们而言,实用主义与这些不同视角的联系体现了对过程和机制所采取的开放式方法,这种方法横跨不同层面的分析,将行为者个体的自我认识和共同的世界观与不断演变的社会制度联系了起来。

这些原则说明,虽然实用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在发现(Chernoff2005)为决策者所用的“真理”上存在广泛的共识,实用主义者拒绝将标准化的方法和技术应用于最终证实或证伪真理假说。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假说都是暂时性的,至多提供“对问题探索的暂时性的栖身之所”(Cochran 2002, 527)。与此相类似,一些理论批评家拒绝接受科学具有结构严谨的、价值中立的制度化知识体系(Bohman 2002; White 2004)。实用主义者和他们原则上都拒绝明晰地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Putnam 2002)。但是,批评理论进而得出结论:鉴于其政治影响,学者们应该对所有知识假说持怀疑的态度。相反,实证主义者呼吁不同学者共同体之间应展开对话,逐步减少道德争议及不确定性,为国际关系制定共识性规范和标准,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就曾呼吁(2006)为全球治理机制合法化制定“复杂的标准”。
总而言之,实用主义者以温和、非线性的视角审视进步,进步取决于通过广泛的对话而相互联系的开放的共同体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运用各种知识的实效。对实用主义者而言,学术进步的标志不是理论积累的程度,技巧的复杂水平,或者在某个研究共同体眼中复制努力的成功。真正重要的是,就某个问题感兴趣的学者之间沟通的质量,对于知识创造性地重新框定、重新组合、重新配置,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因此,实用主义对学术进步的认知,为更深入地理解分析折中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和实践的影响做出贡献。
我们赞同罗伯特·达尔(2004)的观点:由于政治包含异常复杂的现象,涉及通过各种关系相互连接的多种类型的单元,要理解这种复杂性,首先需要理解具体的要素、制度和行为者。范式导向的研究依赖于提出的基本假定、词汇、标准和技巧等,强调对某个问题的特定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这种范式导向的研究传统简化了社会现象,也因此产生了优秀的研究成果。此外,不同学术传统的追随者之间进行辩论,学者就其他传统提出的批评和不同知识假说进行回应,传统的研究范式就得以进步和发展。
但是,除非努力突出不同研究传统提出的问题、解读和机制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完全从不同研究传统的视角看待社会现象可能对知识生产具有局限性。正如夏皮罗(Shapiro 2005, 184)所指出的,根植于单一视角的学术可能反映了该视角的重点,对社会现象的探索本质上局限于利用某视角偏好的认知模式、工具方法解决问题。因此,研究范式之间的辩论使得每个范式内得以进步,但同时也阻碍了沟通、有损学术多样性,从而无法认识不同范式内的分析之间存在的可能的相关联系。例如,在安全研究中,《冲突解决期刊》(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和《国际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这两大期刊所发表的文章很少认可对方刊物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哪怕是在同一问题上也是如此(Bennett, Barth, and Rutherford 2003)。此外,形成和发展一个研究范式需要大量学术、经济、专业和心理等方面的投入,而对于在该范式认知工具和分析框架中无法反映和解决的问题,人们投入的关注往往不足。正如克拉托奇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 2003, 125)所言:“大多数的时候,比起真正找到可接受的问题解决方案的想法,维护自身立场或观点的想法可能更强烈,这也许并不令人奇怪。”
为了克服这些学术交流上的障碍,从观察中获得深刻的洞见并提高观察的精确性,特别是使得研究与现实世界行为者的关切联系在一起,“社会研究的多视角模式”在学术上是有益的(Bohman 2002, 502)。热衷于某个研究范式的学者认为:该范式得以发展的优势恰恰会在探索现实世界难题时成为 劣势 ,这些难题迫使学者直面实证的精确性问题,以及他们工作与实践、规范的相关性,而不是让他们主要在方法论或认识论上证明自己工作的合理性(Grofman 2001)。将学术根植于研究传统的益处在于可识别专业身份的培养,根据所共享的知识和技巧进行高效的沟通,与明确的方法论假说相联系的一整套评估标准,以及其他成员所提供的心理和体制上的支持。但是,当为了以更加贴近复杂的现实世界的方式识别和界定问题,为了能从不同研究传统中获取不同形式的概念、数据、方法和解读逻辑来摸索识别和界定这些问题的方法,这些培养、沟通、标准和支持都必须放弃。当特点鲜明的学术共同体试图使自己的学术成果更贴近决策者和其他行为者的时候,学术上的折中促使这些共同体认识到一个问题的相关方面,迈向更加丰富的解读框架,有选择地将最初在各个研究传统中设计的、人为分割的计划和逻辑整合起来。由此而来的理论框架,哪怕在简洁性和复制性等科学理想上存在局限,也构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生产真理的工具”(Hellmann 2002, 7)。
的确,不同理论范式是依据不同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所建构起来的,在这些研究范式之间折中可能会导致认知模糊。但是,正如西奥多·霍普夫(Ted Hopf 2007)所言,不同研究范式的分析基础之间的差异通常可能没有假定的那么大,可以对这些基础进行调整和限制,使从不同研究范式中发展起来的实质性理论和话语可以转换、比较和融合。只要概念和定义清晰,元理论假定上的差异并不会在本质上否认国际关系的各种进程间的互补性和关联性,即使它们通常出现在不同的理论词汇和不同的分析层面上(Sil 2000a; 2004; Katzenstein and Sil 2004; Parsons 2007)。
折中的方法不能忽略或取代不同范式内产生的学术成果。但是,通过拓展假定、分析工具、理论概念、方法论和实证数据,分析折中主义可以提供复杂的解释,说明不同的因果机制和进程是如何关联的。
分析折中主义不应与理论合成或构建统一理论混为一谈。虽然在与分析折中主义有关的不同方法上,有学者曾使用“合成”表达“实用的范式融合”(Hellmann 2003a, 149),真正的合成理论框架首先要与现有不同研究传统的核心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断然决裂,并构建包含概念、假设和分析原则在内的一套新的统一系统,用于范围广阔的一系列问题之上。
相反,分析折中主义以问题为导向。折中主义承认相互竞争的研究范式会继续存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融汇统合。与此同时,分析折中主义不仅仅是安德鲁·莫拉维斯克(Andrew Moravcsik 2003)所理解的理论合成中的假说叠加版。莫拉维斯克认为,合成理论(contested by Hellmann 2003b)通过严格地使用标准化数据组和可复制的方法可以测试复杂理论的不同组成部分。这种可以分解为各个部分并分别检验的合成理论,并非没有价值。分析折中主义旨在阐明某个具体问题上进程和机制的复杂互动,与合成理论是两回事。折中主义学术的增值并不是忽略目前的研究范式,而是有意让这些研究范式探索并认识到国际关系中复杂的实证和认知联系,这是任何单一的研究范式所无法做到的。实际上,分析折中主义要求对不同研究范式的优点、局限及其之间的互补性均有了解,否则在各个研究共同体内开展更加系统性的工作也无益。与目前的研究范式确实有交互的折中主义有助于产生一大批不同以往的分析和实证要素的组合,这些要素可用于重新定义和解决具有重要实际和规范意义的问题,哪怕这些要素最初是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中形成的。社会科学若想取得学术进步,开展确定性或概率性分析,与意识到各类可能性同样重要。分析折中主义旨在认识在目前研究范式构筑的理论框架之外的实证和道德可能性;与此同时,继续认可目前的范式并与其交互融合,希望能就国际关系的实际问题扩大对话的范围和质量。

有必要用不同的方法理解国际关系中的问题这一理念并非是全新的,即使传统上被认为属于某个研究范式的学者也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已经引用了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1959)一书中的观点。很久以前,汉斯·摩根索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指出了学术在界定具体视角的边界时有其局限性。他认为,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
为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提供了宝贵的屏障,使他们能够开展没有争议的学术研究。我们这一历史时代的国际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存在争议的。国际关系所要求做出的决定,事关国家的目的甚至是存亡。如果关于这一主题的理论不涉及这些决定背后的深层次议题,那么它看似为决定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持,实际上则没有。
(摩根索1970,247)

冷战结束之际,国际关系学者们再次陷入以前的一番争议。即便摩根索也不会对此感到奇怪。这场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或制度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吸引了大多数学者的关注,但是这两种范式都没有预见到世界政治的革命性转变,也无力就转变前、后世界之间耦合性的关系提供一致的建议。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范式之争掩盖了专注于问题的研究。
接下来,我们将回顾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安全和政治经济学的小样本,我们认为这一样本避免了范式之争,并提出了更加折中的视角。我们并不认为这些例证全面代表了国际关系的折中研究,也不假定这些研究中的实质性话语或假说一定是“正确的”。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些例证都是折中的典范,可以防止我们陷入如元理论议题、无法找到解决方案等方面的口诛笔伐。这样的折中有望使得学术对话产生更多成果,以及帮助解决国际关系的具体问题的行为出现。
最近现实主义发生的变化为利用折中主义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创造了空间。国家安全曾被认为完全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亨利·诺(Henry Nau 2002)将均势理论和身份平衡理论相结合,就美国对外政策本质及长期保持均势的趋势提出观点。美国作为“新世界”卓尔不群和独一无二部分的自我形象,使其与其他国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由于权力、财富和其他众多的原因,美国寻求与全世界更紧密的关系。回顾美国对外政策历史,不难得知:美国既是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孤立主义者,它不停地摇摆于两个身份之间,同时又陷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矛盾中。结果就是在相互竞争的联盟之间不断摇摆,或出现某个阵营取得暂时性的胜利,或两个阵营之间出现不稳定的同盟。因此,很少情况下,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会长时间不出问题。因此,亨利·诺将传统的均势逻辑与国家身份的平衡理论相结合之后,阐释了一系列新问题,这是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理论无法做到的。康灿雄(David Kang 2007, 11—12)在分析中国崛起时,也在寻找“偶然因素的相互连接,而非忽视其他因素,孤立看一个因素”。康灿雄提出,除了日本之外,为什么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顺应中国崛起,而非采取抗衡措施?这个问题直指现实主义者的核心关切,但是要回答好这个问题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包括偏好、意图、信念、规范、身份和对世界的判断。康灿雄一方面考虑了绝对和相对能力以及国内政治,另一方面强调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关系在过去和未来都有共同的利益。历史上,一个虚弱和分裂的中国给邻国带来的是问题,一个繁荣的中国通常会使邻国受益。几百年来,东亚地区已形成共识:中国在本地区占据着特殊的位置。
目前,中国的政策取向是与邻国一道实现繁荣,而不是牺牲它们。这一分析的现实意义就是把中国理解成国际关系中的“维持现状国家”,而不是“修正主义国家”。不论对错与否,康灿雄的复杂解读挑战了现有的理论(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这些理论忽略一些因素而专注于另一些因素,将中国崛起描绘成威胁东亚稳定的因素。这种处理方法与杰森·莱尔(Jason Lyall 2005)对后共产党时代俄罗斯的分析形成了强烈的共鸣。莱尔试图对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 1998; 2006)的研究进行改进。施韦勒遵循现实主义研究的悠久传统,强调修正主义国家的意义。莱尔认为,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本质区别,实际是做出准确预测所依据的固定身份。换句话说,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分析是依据隐藏的身份变量。莱尔的观点并不是要否认施韦勒著作中绝对和相对能力的重要性,而是要揭示其研究中不被承认的折中主义性质。归根到底,“修正主义国家”和“维持现状国家”这两个类别表明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换句话说,身份的界定表明了国家之间重要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在现实主义的认知框架中无法体现。在康灿雄和施韦勒的分析中,若没有事先对修正主义国家及其对国际体系冲突或稳定的重大意义有所认知,就无法做出解释。与此同时,他们没有追求简约性原则,考虑分析了诸多概念和事实后提出了原创性的观点,而这些概念和事实对更全面理解问题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 2005)对他认定的或许是当代世界政治安全观最令人瞩目的变化,即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这一事实,进行了研究。虽然他承认三大研究传统都存在各自的缺陷,但是他的阐释还是结合使用了三大研究传统(Jervis 2005, 16—26):建构理论所强调的非暴力规范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之间的共有身份;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民主、经济互赖以及国际组织中的共同成员资格三个要素产生的和平效应;以及传统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外在威胁、美国霸权和核威慑三个要素促成的合作。随后,他建构了(Jervis 2005, 26—29)自己所说的“合成互动理论模式……重新提出了几个因素”,具体来说是三个因素:相信领土征服非常困难;承认战争的代价高昂;民主扩散引发的身份变化,表现为尚武精神、领土争端和民族主义一齐衰弱,以及最发达大国之间不断增强的价值认同。杰维斯并不认为这些变化能够解释所有的国际政治问题,确实远远不够。但是,他对他所认为的国际政治中最惊人变化做出的分析,以及对新型安全共同体兴起的阐释,都具有折中主义的取向。这种折中的方法认识到了不同研究范式内以典型方式概念化的机制和实践运用的机制之间的互动。
折中主义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IPE)领域的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在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重要著作(1975)发表之后,一代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研究范式:现实主义——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近的研究不仅跨越了这三个阵营,而且吸收了通常被这三大传统忽略的新概念和变量,三大传统的概念因此现在已经过时。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的处理上尤为明显,对传统上重视国家权力的现实主义思想和传统上重视经济激励的自由主义思想明显地增加了概念因素。
艾儒蔚(Rawi Abdelal 2001; 另见Helleiner and Pickel 2005)的分析是采取折中方法的一个案例。苏联解体后的各继承国在经济严重依赖俄罗斯的情况下,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经济战略。在艾儒蔚看来(2001,13—18),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解释虽然有助于全面理解这些新独立国家的选择,但无法据此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战略,因为这两大研究传统的理论框架认定行为者身份是外生的。艾儒蔚从经济民族主义的概念出发,以理解这些国家经济战略中明显不同的政治选择。民族主义使得国内政策具备根本性的社会目的,即维护和加强国家认同。它使人们为了实现社会目的而做出了一些必要牺牲,同时延伸了国家和社会的时间范畴(Abdelal 2001, 2)。艾儒蔚将这些影响考虑在内,不仅能够理解具体的国家选择,而且还能解释苏联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方面所经历的不同进程。
伦纳德·西布鲁克(Leonard Seabrooke 2006)对国家金融权力的社会根源所做的探讨是折中主义分析的另一种案例。西布鲁克的关注不局限于国家和大企业之间的互动,更关注边缘经济行为体的理解和实践,特别是通常被排除在“富人阶级”之外的低收入群体。强调要素禀赋以及制度逻辑的理论过于静态,无法把握这一动态关系的复杂性,因为这些理论忽略了赋予信贷和金钱意义的社会共识的重要性。他还认为,那些强调国家能力或各种资本主义的理论忽视了政治和社会反应对国家使用金融权力的能力及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大意义。西布鲁克随后重点关注了经济活动中合法性的重要性。经济活动指的是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政治和经济实践,合法性赋予政治秩序公平和公正。因此,针对低收入群体的、积极的政府政策具有重大意义,包括降低税负、放宽授信、增加财富等方面,因为低收入群体为国家的金融权力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积极的政府政策深化和扩大国内资本储备,鼓励增加资本回流的金融实践,对国内金融体系的能力和国家塑造国际秩序的能力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20世纪初英国和德国以及20世纪后期美国和日本的案例研究,为这一新的折中方法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支持。
在强调全球金融的社会性时,蒂莫西·辛克莱(Timothy Sinclair2005)对于评级机构政治的分析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理性主义理论起到了补充作用。理性主义者认为,在当今金融全球化的时代,是评级机构而不是银行决定信誉,国家和企业现在都受自我监管的评级机构的判断。
在高度不确定和充满风险的环境中,评级机构向经济主体提供透明公正的判断,供后者决定如何有效地分配稀缺资源。辛克莱并不否认这一理性主义的分析,而是试图通过这种评估知识的创造和监督,从更深入的、政治的角度理解该问题。评级机构并不仅仅做技术工作,向其客户和公众提供自然市场发展的、经过提炼的海量数据。这些机构还提供了诠释性框架,旨在说明什么是合适的经济行为,而这些行为会因此获得额外的私人投资作为回报。评级机构提供权威的专业知识,但是这些并非传统意义上正确或不正确的专业知识。主要的国际评级机构都在美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们所代表的深层次的知识网络的特征。
最后,越来越多的文献提及地区在国际事务中的重大意义,这类文献明显可以看到将安全和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折中视角。至少有三个不同的研究范式(Katzenstein 2005,6—13)对地区进行了定义和分析。地缘政治的经典理论强调地区的物质基础: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地形的性质或者陆权或海权的必要性决定了地区政治的发展态势。地理的观念理论认为,地区并非给定的,而是通过政治和文化塑造的。地区不仅受到经济中心与边缘分离进程的影响,而且地区符号可表示特定人群在世界上特定地方占据的主导地位。根据观念理论,空间是一种社会创造和实践。
地理学的行为主义理论也对地区进行了分析,提出不同地区的空间距离变量被认为对这些地区行为者的行为存在直接、可证明的重要影响。上述每一种研究方式都提供了一部分重要的见解,但都不能独立地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如何界定和理解地区、解释行为体在地区的位置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在地理学科的内在跨学科的支持下,折中方法可以提供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揭示上述三种研究方式各自偏好的机制或进程之间的联系。当卡赞斯坦(2005)在探讨美国“统治权”背景下的欧亚差异时,他正是采取了折中主义的分析方法。
分析折中主义对学术进步的贡献并不依赖任何具体的严格标准,而是在于扩大了就某个给定问题相关的概念、要素、机制互动的范围,鼓励做出创造性的努力去认识、定义、连接和解决国际关系中的实质性问题。这些问题通常以不同形式分散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之中,并且这些问题往往以更“纯净的”国际政治科学的名义被剔除在外(Reus-Smit 2008)。我们并不主张将研究随意扩大到任何范围,或者忽视目前研究范式中的有关观点。我们也并不认为折中是两面下注的谨慎之举。在我们看来,折中主义是有的放矢,因为它试图在一定的时间内尽可能找到某个问题的最佳答案;折中主义又是富有勇气的,因为它敢于同多样化风格的思想进行学术交流,是一种完全对话式的科学(Therborn 2005, 325—326)。此外,由于分析折中主义也有意识地接触不同的研究范式,因此它能够扩大研究共同体之间交流的范围并提升交流质量,揭示不同的实证难题、规范性关注和理论解释之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在更广范围的国际关系领域内,“大多数进步的取得都依靠在我们所有人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Haas and Haas 2002, 587)。
坚持分析折中主义的方法确实需要付出成本并承担风险。第一,折中主义的方法缺乏“保护带”(Lakatos 1970),无法保护使用折中方法的学术研究免受核心认识论和形而上假定的质疑。折中主义的方法也缺乏标准和规范,研究共同体因此无法以某种标准评估学者的贡献和评判他们学术成果的质量。第二,折中主义的方法可能会在更广的范围内受到质疑和批评,这类质疑和批评来源于各个研究范式中相关的标准和实践,而各研究共同体的成果被融合应用于不同类型的折中主义分析。第三,与对理论合成的尝试一样,折中分析也面临着认知模糊的危险,因为分析折中主义研究人员需要熟谙各种范式的研究人员所使用的评价标准,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进行经验研究(Johnson 2002)。第四,跨越不同研究传统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要求学者不仅阅读广泛,熟悉不同理论话语,参与和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多元话语交流,每一个共同体都会使用某一种理论语言,这个共同体成员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与之联系在一起的。面对分析折中主义所涉及的风险及质疑,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在研究未显示出价值和所循标准的时候,是否应当将有限资源应用于分析折中主义研究?史蒂芬·桑德森(Stephen Sanderson 1987, 321)
对折中主义做了如下批评:“由于绝大部分思路不会创造任何价值,采用这种战略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好的替代办法……就是采用时下最实用的理论传统,并最大限度地根据这种传统来进行研究。”
无论如何,特别是考虑到国际关系的几大研究传统过往的情况,这些关切并不意味着有理由将折中主义边缘化。如果有什么影响的话,与研究传统内部的学术生产相伴随的利益往往导致学术研究与现实世界需要关注的问题有越来越大的鸿沟。正如夏皮罗(Shapiro 2005, 2)所言:“在一个又一个学科,学者们完全逃避现实,几乎都忘记了他们所声称的研究对象。”为整个社会科学制定衡量“进步”的标准化指标这一根本性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将资源投入被不同研究传统的假定和实践规范的学术中去,只会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虽然分析折中主义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它绕过这一问题,认识和评估不同研究传统对某些问题关注的不同方面,从经验来看,这些问题的不同方面是紧密联系的。此外,分析折中主义认识到现实世界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同战略所带来的实际后果,因此公开直接地关注往往未受认可、能够激发学术研究的问题(Reus-Smit 2008)。仅凭这一原因,就值得投入至少部分的资源——分析的折中模式可以加强我们在不同研究共同体之间对话的整体能力,逐渐为国际关系中遇到的复杂问题的各种概念、理论和经验创造更大空间以解决问题。与互相冲突的教条主义所存在的缺陷相比,分析折中主义的缺陷小得多,值得尝试(Hoffmann 2006,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