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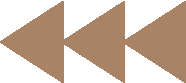
菲利普·达比
本章标题可能看似有悖常理,因为从某些视角来看,国际关系似乎正春风得意。如今国际关系学科横跨全球并提供了人们分析世界政治的一门共同语言。近些年来,该学科拓宽了视野,将从文化到生态在内的新研究领域纳入其中。正如本书所述,这个学科内一直存在一种欢迎变革政治的态势并为此任由各种方法论大行其道。尤其是自“9·11”以来,学生对该学科的兴趣使本科生注册人数激增并使研究生课程大大增加。国际危机连续发生,人们不断要求国际关系学科的学者们在媒体上发文以表达相关看法,而电台和电视节目也不断请他们进行评论。以这种标准为基础的话,该学科看起来确实十分繁荣。
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很多年来,人们一向对该学科的解释能力充满焦虑,伴随冷战的结束,以及未能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做出预测,人们开始怀疑该学科是否失去了意义。近来,人们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在帝国的继承国内部和继承国之间爆发的混乱和暴力。越来越多的位于国际关系边缘的学者认为,这些社会内部的进程对西方所想象的正被市场机制所校正的世界、民主的推广以及对发展的承诺等发起了挑战。对于“紧急情况”的构想表明被摒弃的固有学者思维是多么脱离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日常生活,这一构想将周期性的破裂描述为例外而不是常态(Calhoun 2004)。人们似乎更加认识到:现有的学科知识,不仅包括国际关系知识而且包括像发展和安全研究这种相邻话语的知识,面对这一问题都束手无策,另外由于国际关系学科横贯了不同知识构成的边界,情况就更是这样了。此类批评与一种存在时间更长的谴责存在交集,后者声称国际关系仍然坚守着某种殖民主义世界观,这一世界观对于南方国家的现状的理解是扭曲的,也偏离了其规范性视野。
本章将集中论述国际关系学科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就欧洲以外的世界进行研究,相关研究也不过被当作对照第一世界所开发的思想主体的附属部分。然后本章将探讨这一状况的变化情况以及如今国际关系是否准备开启一段对自身思维去殖民化的进程。笔者在结论部分将针对该学科的知识进程再做一些总体评论。该进程压制了其他政治议程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一直把国际关系的历程描述为兴起于欧洲、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为基础事件的思想和实践体系的国际化过程。这是一种对于进步的叙事:一种(或者更精确地说几种不同的解读)对于起于世界上某个地方继而覆盖全球的政体之间关系进行重新安排的解读。这一几乎已成为经典的理论化一向受到以下主张的侵害:1648年所达成的和解并非现代国家体系出现的标志点。相反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特征是明显的非现代地缘政治关系,植根于绝对主义式的前资本主义产权关系(Teschke 2003, ch.7)。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自诞生之时起就特立独行的叙事由于人们对在现代主权(Hardt and Negri 2000,70,103; Barkawi and Laffey 2002)和现代经济(Mitchell 2002,80—119)形成中,欧洲与其殖民地居民的关系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认识的加深而深受挑战,在某种程度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1989,89)有关“永恒欧洲”这一迷思的揭示就对此有所预示。很久以来这一点都被国际关系学所忽视,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人们非常不情愿研究欧洲帝国主义国际政治。近来有关国际关系史学的研究暗示帝国主义是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一个普遍主题(Long and Schmidt 2005)。对于某些开创性学者所理解的帝国与国际之间的关联以及此类观点的接受范围,人们还需要开展大量的研究。然而,二战后欧洲对热带世界的征服在国关学科中是被遗忘或被压制的,这一点非常明显。结果,这些塑造了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未来、为宗主国的国内政治打上不可磨灭烙印的进程被留给了其他知识形态,后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帝国主义历史学)以各自方式推进这些进程(Darby 1997,3)。这表明一代学者,其中更多的是国际关系学者,似乎乐于接受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和亚当·沃森(Adam Watson)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概括,即“国际社会的扩张”,这一表述抑制乃至粉饰了其中有关暴力、种族主义和经济掠夺的情况。
研究有关殖民主义档案的某些方式可能已经令国际关系学科获得了对于南北关系更好的掌握,如今和当时一样,我们都有必要对此进行简单探讨。现代殖民主义对于人员、理念、价值观和商品流通的建制负有责任,而我们认为这些建制是当今全球化的内在之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它极大地造成了第三世界在当代的动荡。例如,对于人们通常认为的具有内生性原因的暴力问题,仅靠当地的文化形态或国家失败现象来解释是不够的。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主义征服和统治,后者造成了传统社会内部新的分裂并加剧了其原有分裂。这里,尤为重要的是人们十分重视宗教和民族认同以及不平衡发展的进程,后者有利于某些当地民众而不利于其他民众。它们都集中关注殖民主义对其海外受害者的破坏性后果,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但是,殖民主义对胜利者也具有破坏性后果。阿西斯·南迪(Ashis Nandy)对事情的这一方面进行过深入思考。在其有关性别和性(这两者当时都不是国关学科的研究对象)的著述中,南迪(1983)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经历如何提升了其男性化价值观,如何拉低了英国政治文化中柔软的、人性化的以及与女性有关的方面予以了说明。他的某些观点颇具争议,但他从对性别的分析中暗示共同遭罪的经历有可能使主要文明体更加接近,这与今天很多西方思维仍然采用的单一文化的“共同世界”方法形成鲜明对比。上文所述及其他部分论述都提醒我们,虽然殖民主义打的是现代性的旗帜,它还具有植根于绝对主义和权力估价的黑暗一面。知道了这些,我们就可能看到这一阴暗面在近来国际干预主义中的共鸣以及其普世主义的伪装如何掩盖了它们与西方统治的共谋。不过,我们还有望通过像南迪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对殖民时期的研究找到摆脱当前这种僵局的方法。
欧洲外世界的边缘化延续到了帝国终结之后。必须指出,西方大国对于一个极其不平等的世界秩序的根深蒂固负有主要责任,但国际关系与其附属话语持续的批评成果寥寥而且非常抗拒其他思维。当时的问题是,面对来自第三世界的挑战,决策者和国际关系学者们所依据的传统学说大致相同。虽然对民族主义领导人来说去殖民化提供了建立新政治学的希望,然而从西方视野来看冷战的重要性确保了任何有关前殖民地的重新思考都从属于权力算计以及志在维系中心平衡的战略。这样,冷战所引发的暴力的全球化隐藏了一种对于资源、贸易以及基于权力和种族的国际等级制度持续的帝国主义兴趣。
民族主义领导人试图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推进其主张。这意味着对于志在获得在世界理事会中的影响力的非传统战略的追求,从某些方面看这类似于游击战,从其他方面看则预示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思想(2004,1—32)。大体上,它们并不属于既有国际关系中的惯用伎俩。这些战略包括推动不结盟运动及相关的以和平区作为一种沟通方式的计划;像1955年的万隆会议那样以及通过非结盟运动、国集团以及非洲统一组织等机构在集体行动中加入第三世界国家的数量权重;对源于殖民主义历史并为主要西方大国利益服务的国际法的某些主要方面提出挑战;
以依附理论为一种政治武器;在联合国系统内部开展鼓动性外交,尤其注重联合国大会上的经济问题。事实上,阿里·马兹瑞(Ali Mazrui)曾经说过,西方大国是《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制定者,根据该《宪章》,和平与安全被视为首要目标,而促进人权则次之。他认为亚非国家致力于将这一优先顺序反转(Mazrui 1967, 135)。
当然,第三世界的挑战以失败告终。配置散漫的力量根本不是西方经济影响力的对手,不论怎样,西方总有办法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说辞,他们至少在自己国内可以做到这一点。在第三世界之外,人们一直认为不结盟没多少可信度,1963年中印边界之战后,即使在第三世界不结盟的吸引力也大大降低了。事实证明,集体行动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第三世界各国追求的都是自己独特的利益。私有领域不断巩固的新帝国主义经济关系使改写国际法的企图基本破灭,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也因而受损(Anghie 2005, 226—244)。被西方经济学家摒弃之后,依附理论被宣告死亡,在国际关系中也只能得到十分有限而又姗姗来迟的认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激进的思想家们,像迈克尔·曼利(Michael Manley)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这样声名显赫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开始加入西方队列并接受有关发展的正统观念。尽管联合国发布了很多宣言,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未成型。
阻击了来自三个大陆的外交攻击后,西方国家找到了新的盟友并安心追求自己的议程。这一最新的篇章涵盖了20世纪80年代的结构性调整时期、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及“9·11”的余波,人们对该篇章的理解可能非常不同。不过,鉴于大家对主要的问题都不陌生,我们的陈述可以简化,可以直奔主题。随着“强国家”雄风不再,西方开始更广泛地干预第三世界社会的内政。它们经常与世界银行和国际非政府间组织结合在一起,其目标则变成了以能够进一步将其社会整合进国际体系的方式重组第三世界国家。最初的问题,而且也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的首要考虑因素,即关乎私有化、福利的削减以及更为自由的外资准入的国内经济结构的“改革”(有关这一点对世界经济政治学的威胁的精辟分析,见Ruggie 1994)。然后,其他因素被逐渐移植到这一主要问题上来。首先是良好治理,人们对它的理解从根本上依据的是西方术语。民主、“市民社会”以及社会资本不仅被视为重要术语,它们还被逐渐当作发展的前提条件。接下来,“9·11”之后,西方对有些国家(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国家)施压要求它们彻底革新其安全措施以符合美国的新战略范式。我们也可以说有关反恐战争的用语,“先发制人防御”、“无赖国家”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妖魔化威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正如我们在有关复杂的政治突发事件的文献中可以看到的,以人道主义救援作为国家重建基础的趋势以及更为紧迫的以民主和市场为导向的伊拉克重建的企图等,我们正在见证帝国主义政治的重生。然而,我们认识不到位的地方在于,如今在原殖民世界正在推行的政策比曾经的帝国时期所追求的政策更具有干涉主义色彩。
在这段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国际关系学界并未注意到中心权力的重构和延伸的实际情况。可能当时国际关系学科中面对国际范畴的扩张、互相依赖的崛起以及全球化的影响时,过于沉浸于厘清自己的语料库。其时,现实主义也正面临来自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和女性主义的挑战。当时人们也强烈地要求反思对南方带来影响的世界政治。除了约翰·鲁杰(John Ruggie)的著述以及复杂应急理论家们的见解,《千禧年:国际问题研究》(1996)的编者们也注意到了贫困问题。然而,这些启示性的思想在民主和平理论面前黯然失色,更不必说还有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当然这一学说所指的方向是相当错误的。同样重要的是,本可以提供一些批评线索的知识遭到了人们的轻忽:第三世界有关国际法主要原则的批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很少有人认为通常在国际关系读者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发展问题是对国关学科理论化的反思。斯蒂芬妮·纽曼(Stephanie Neuman)所著《国际关系理论与第三世界》(1998)是对该学科进行批评的著述之一,该书曾有所建树但随后又陷入迷思。
在此诠释性调查中有两个关键点。这两点对于后殖民主义研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如今在国际关系边缘地带正获得不少认可。第一点,在相当长时期内,欧洲外世界的构成依据的都是其所缺乏的东西(Doty 1996, 162)。尽管早些时候它缺乏的是衣物、耕作和文明,如今它缺乏的却是现代市场经济以及良好治理。似乎其指导原则仍然是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托管制原则:对于“在现代世界艰苦条件下尚无法自立的”人民进行托管必须委托给“先进国家”。然而,从女性主义思想对我们的启示来看,缺乏可以被重置为赋利而造就其他准则和政策。第二点是识别和应对差异的需要。在某一方面来说,这并不太关乎“对‘西方’的排斥”,它关乎的是“自我重塑”(Inayatullah and Blaney 2004, ix; 另见Salter 2002; Yew 2003)。
国际关系面临的挑战在于对这些相关问题的解决。总的来说,它们构成了一项方案,既需要对该学科进行去殖民化,又需要对了解这个世界的不同方法进行研究。对于当下国际关系是否准备好了实施这一方案,人们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不容置疑,差异正摆在这一议程表之上,而人们对于去殖民化的需要更为认同(见Jones 2006)。本书这一章证明了国际关系学科已经脱离了国家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模型。一方面,人们更加关注“国内政治”;另一方面,人们更加关注“全球社会”。人们还对试验方法和政治行动主义产生了新的兴趣。不过,也有迹象表明这一再思考进程可能被压缩,正如民族主义领导人相信二战后的去殖民化也可能被压缩一样。也许现实主义正走向衰亡但自由主义则不然。我不希望在措辞方面过分含糊其词,但有些用语带有连贯性或相似性。考虑到早些时候在国际关系中的使用情况,“国内政治”一词具有暗指的被排除内容而且未纳入准政治内容。“全球社会”一词养育了“世界大同主义”这一幽灵,自然需要一些减速带。在这一点上,我们大概可以从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的著作《被治理者的政治》中获得一条线索。虽然该书与此类国际关系无关,但它却是所有国关学生都应该读的一本书。正如查特吉所说,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政府事务都把政治剔除干净。“市民社会”是现代精英集团这一封闭式的联合体。如今进行真正的政治斗争的是底层群体,这些斗争大部分都发生于西方强加的或促成的政治体系之外,为此查特吉提出了“政治社会”这一短语。他暗示,真正处于危险之中的是非欧洲社会的性质以及它们如何与国际体系发生关联。
也许有人认为,北方的国际关系从南方国际关系的实践中找到未来方向是上策。然而,现实情况没那么简单。眼下该立场正在发生变化,但通常南方跟北方对于传统的执着一样强烈(有关安全问题,见Darby 2006, 457—458)。尽管第三世界的学者在指责人们继续坚持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方面一向走在前列,谈到有关学者我们会立刻想到阿明(Amin)、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马兹瑞(Mazrui)、阿希尔·姆本贝(Achille Mbembe)、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南迪(Nandy)、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等,然而国际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并未引起人们多少兴趣。结果,该学科有关著述大多无人问津。一直以来,不仅新加坡(人们可能对其有所期待),而且德里和北京(人们可能对它们无所期待)都在援引其权威;许多非洲的博士论文自始至终不离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有关国家利益的论述。像依附性或附属性这种有影响的另类路线经常出现在教学大纲上并始终渗透于人们的口头交流之中,但在某种程度上并未扰乱学科思想的大结构。
我们可以以此作为该学科普世性的标志,但笔者认为它构成的是一个基本未经验证的案例,查特吉称之为“衍生话语”(1985)。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该学科的突出要旨正在加倍失能,因为它使南方国关学者的思想被殖民化,致使他们的优先选择和对关键问题的理解失去关联。
就此而言,我们专注于国际关系对非欧洲世界边缘化的政治问题。这里我想根据认知这个世界的不同方式进行研究这一任务,对该学科既有的知识常规进行一下反思。就算人们的视野正在发生变化,我们仍然必须牢记学科沿袭的分量。正如俗话所说,孤燕不成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该学科的内部学术程序屏蔽了看似退化的、难以应付的或碎片化的知识,以及那些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但很少被当作知识的知识(例外情况,见Keck and Sikkink 1998; Sylvester 2000; Shaw 2002; Magnusson and Shaw 2003)。一直以来,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论争主要是一些内部事务,而且它们具有将国际关系与其他观察国际社会的方式相隔离的效果。
将不同学派知识进行组织并争论的过程过于针对新鲜的和有想象力的范畴。因此与熟悉的参考点、往往枯燥的词汇乃至写作风格相关联的需要,也抑制了对于既有学科落脚点的背离(Bleiker 1997)。有关这一方面,并非不存在差异空间,而是差异倾向于固化为固定立场,它象征的是一种封闭形式,似乎对于学术传统的坚持充当了对抗脆弱性的堡垒。
也许在此我们可以做两个补充说明。第一个与研究有关,不仅适用于国际关系而且适用于各种学科。随着学院的全球化以及大学之间为了资金而展开的竞争的加剧,那些在国际上著书立说的人会得到嘉奖,但人们普遍认为“国际上”就意味着要使用英语写作并在第一世界期刊上发表。第二,我们需要记住学说是国际关系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谁的知识被传播到了全世界尤其重要。有大量的证据暗示我们,非欧洲知识的传播情况不太乐观(Nossal 2001; Hovery 2004)。
这一切都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就其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而言,国际关系政治学一向受到空间的局限。传统上,国际关系学科关心的是“高政治”,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研究这个世界。即使是现在,仍有人抵制有关国际进程对普通百姓生活影响的研究。政治在草根层面与顶层表现不同,这一点对于有序世界来说令人不安。桑卡兰·克里希纳(Sankaran Krishna)对于国际关系如何成功地脱离这一困境颇有见地。对种族这一案例进行研究之后,他指出,“该话语对于抽象化的价值增值甚或崇拜是以逃脱历史的欲望为前提的”(Krishna 2001, 401)。也许还可以加上一点,不仅是为了逃脱历史,还是为了逃脱此时此刻的政治。因而,人们开始钟情于像自然状态或和平时期这样的抽象概念,而且还钟情于建模和博弈理论、理性选择的计算以及体系的权力。立足于这些方面,我们也许能够更好地回答那些人们应该提出但很少提及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对那些掌握了其他社会有关知识的国关学者的兴趣如此之少呢?为什么关于国际和日常生活的学说如此之少呢?
这些问题引导人们关注此地与彼处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政治的分野。茨维坦·托多罗夫的大作《征服美国》的出版是对他者及其危机进行理论化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以一位道德家以及面向未来的视角审视了15世纪和16世纪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对决,称之为“历史上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对决”(Todorov 1984, 4)。据他所言,仅仅理解或认同他者是不够的。有关他者的知识必须用于更好地了解自我,从而揭101示自我知识的相关性(Todorov 1984;另见Todorov 1995)。其他学者,有时以托多罗夫为基础,更多时候靠借鉴其他不同的思想传统,提出了很多鲜明的主张,比如揭示了胜利者与受害者之间的连续性,发现了二者具有受害和脆弱性这样的共同点,强调所有文化内部传统的多样性和开发隐性声音的需要以及研究发挥作用的心理进程等(尤其是,Nandy 1987;Kristeva 1991; Das 2002)。这些叙事的重要性在于,厘清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有关的历史唯物的以及类似的当代经历后,人们就可能以一种并非仅仅围绕强者的自我形象的方式来思考未来。对于自我之中的他者加上与之并存的所有的自反性的意识,是实现不同文化之间对话所需要的第一步。然而,正如托多罗夫(1984,247)所暗示的,在欧洲处于支配地位的绝大部分时期内,西方已经同化了他者。
笔者认为,这并非是对于自我/他者这一分类的过度使用以暗示它既适用于话语也适用于人和文化。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直面该学科未能对他者进行研究的另外一个方面:它不愿意与关涉国际的其他知识形式开展持续性对话。如今,优先对待自身的知识专业化、分析语言以及行动方式是学科思想的本质所在。我们有理由质疑各种形式的交叉学科能否在不经整体“简化”情况下进一步推进不同知识的整合,更不必说成功绕过人们所接受的知识生产伦理了(Klein 1990; Coles and Defert 1998)。
此外,学科对外封闭与交叉学科之间还存在一系列可能性:选择性的跨界、利用其他来源的资料和方法论、萨义德的折中主义、像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打破规则”这样的反学科动向、开始实施可能减少学科依附性的短期协作性方案(Readings 1996)。如果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倡议力有不逮,它们还是能够挑战人们的心态,记住犯错误可能具有创造性这一点是有价值的,虽然值得商榷,依附理论的情况同样如此。
然而,除了边缘地带有零星几个持异议者外,这种动向在国际关系中并不常见,因为该学科对于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能够在自己的著作内得以解决的信念过于坚定。姑且不提全球化中大多具有选择性的非法交易问题,国际关系认为与其他有关国际的话语进行对话尚无必要。然而,人们几乎无法怀疑跨界具有的实现潜力,其中绝大部分都与其他知识有关。例如,一项有关研究对穷人日常如何看待和参与国家事务进行了探讨(Corbridge et al. 2005);另外一项研究探讨了亚洲和非洲的绩效政治(Strauss and Cruise O'Brien 2007)。通过回溯到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之间盛行的互相“对峙”,我们看到回避的代价是惊人的。笔者想说,其基本结果就是,发展没有被视为国际秩序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不过,如果没有发展所抱持的救赎承诺,新自由主义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国际意识形态。
我们仍面临一个问题,即学科性国际关系批评者对自身的定位在哪里?致力于变革需要针对主流国际关系领域,因为这里是权力的归宿。一方面,最有效的战略可能在于识别出能揭示该学科的不自信和不确定性的话语中的裂隙并对之进行探究(Marcus 1999, xi)。然而,一旦置身于国际关系的领地,就很难抵抗该学科的俘获能力。风险在于新的视野可能被整合进原有知识秩序,从而令其锋利的棱角钝化(见Weber1999)。还有一种在国际关系内部建立另外一个学派的可能性,但这是否是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至少是值得怀疑的。考虑到本章为了探讨克里希纳“后殖民主义国际关系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一个有待商榷的矛盾。将国际关系去殖民化也就意味着在该学科支配性的表现方面自我脱离于该学科”这一观点时所详细论述的观点,这一点是有益的。另外,该批评者可能将自己定位在该学科边缘或外部,偶尔会进到其中心地带。处于这种位置的批评的问题不仅在于它们不可能接受多少正统思维,而且在于将该学科带回正途的机会将被大大缩减,因为它们的内部知识基础将更为贫瘠。当然,批评人士不可能以这种理性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关系结构。相反,根据他们的兴趣所在、他们的写作方式以及他们与什么人为伍,他们会向各个方向倾斜。也许这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因为国关学科既需要来自内部的批评也需要来自外部的批评。此外,由于国际日益居于社会内部(这也确系大势所趋),无论人们以某个学科的名义提出什么样的主张,有关国际政治的知识性辩论局限于单一学科的情况会越来越少。



